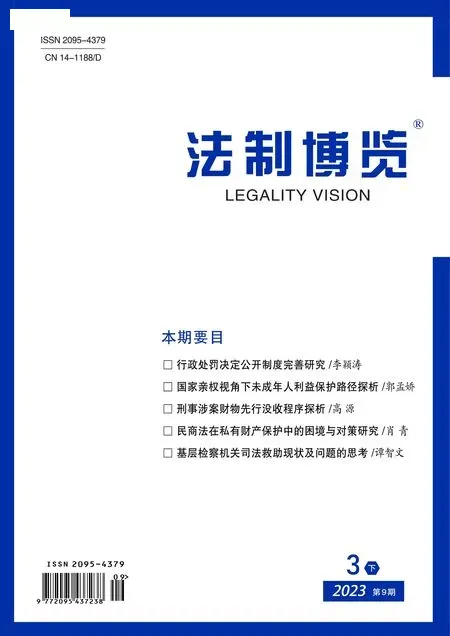我国有声读物的法律属性及规制研究
2023-10-05姜慧琪
姜慧琪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4
一、问题的提出
结合朗读者技巧,诙谐幽默并旁征博引,绘声绘色地表现优秀作品,且内容极其丰富,不受空间、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有声读物正以诸多优势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呈现爆炸式增长。
然而,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有声读物进行规制,法律学术界、实务界对有声读物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这种局面已经使得各相关方的权利边界不清,相关参与方及有声读物的公众均无所适从,不利于此行业的合法、有序发展,因此肃清环境对于其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二、有声读物法律属性界定
针对有声读物,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规制。故研究时,主要查询文献及案例进行梳理。经研读文献发现,网络环境下有声读物的版权争议一直是著作权侵权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然而,对于有声读物的定义等尚未有统一的界定,对于其是否属于著作权,学界观点不一,主要涉及有声读物是否属于著作权的合理使用、经演绎而得到的改编作品、邻接权之表演者权利、录制者录制作品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方面。
(一)有声读物合理使用的限制
《马拉喀什条约》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者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带来了福音,其定义“无障碍格式版”并未明确列举具体的表现形式,而仅说明其能达到的实际效果,使视障者感知作品内容的版式都可以归为“无障碍格式版”。主要有三种,盲文版、大字号版和有声读物,由此,有声读物属于合理使用。
为呼吁我国《著作权法》与《马拉喀什条约》衔接,在其发布之初,不少学者曾表示其虽已规定适用于盲人的版权限制与例外,但与《马拉喀什条约》相比尚有差距,因其排除了大字版纸质书、电子书和有声读物。新修正的《著作权法》未定稿之前,王迁曾建议删去草案中“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的“独特”二字,因其意味着只有盲人等阅读障碍者才能感知,这违背了《马拉喀什条约》的规定[1],所幸,最终发布的新《著作权法》删去了“独特”。故从某种程度上,对于视障者而言,有声读物属于合理使用。
(二)机器转换型有声读物的可版权性
机器转换型有声读物主要是指运用TTS(文字转语音)技术对文字作品进行有声化处理。学术界一致认为,机器转换型有声读物不具有可版权性,因其转换过程中一般不含有第三人的创造性劳动,仅是施加简单的转换,然后上传有声读物平台。因此,机器转换型有声读物不满足作品独创性的要求。
(三)人工朗读型有声读物的可版权性
1.人工朗读型有声读物不属于演绎行为而得的改编作品
有声读物制作过程中,一般包含:朗读—录音—后期加工制作。过程中有一定创新,早期不少学者认为编排设计后,有声读物凝聚了读者的智慧和贡献,具有独创性,属于自然人的劳动创作、智力成果、独特的表现形式,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
郑成思认为,要取决于新作品是否在原有表达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独创性表达[2]。王迁认为,改编是指在保留原作品基本表达的同时改变原作一部分创作以发展出新作品[3]。由此来看,即使朗读者技艺极尽完美,背景音乐动听无比,也不能将朗读等同于创作。著作权典型案例“谢某诉L 公司案”的审理法官张书青则支持“有声读物是以录音录像制品存在的复制件”。但也不排除仍有学者认为属于改编作品,如梁志文认为制作成有声读物的小说在线传播涉及原作品的演绎权[4]。目前认为属于改编作品的学者比较少,相对来说,普通民众,及非专业学者,多认为属于改编权,如“谢某诉L 公司案”合同双方都认为把阅读之后的录音上传,是表演权和改编权。
2.人工朗读型有声读物是表演但不涉及表演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认为朗诵诗词等直接或者借助技术设备以声音、表情、动作公开再现作品的行为属于表演。由此可知,朗读作品属于对作品的表演,而不属于再创作,不属于改编。《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九项中所述的表演权是指公开表演作品,因而在私人空间中朗诵文字录制成有声读物虽属表演,但因其不具有公开性,不涉及表演权。王迁也同样认为,有声读物属于表演,不涉及表演权[5]。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陈某旭与深圳市T 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时,认为朗读过程是对涉案小说作品的表演,朗读者并没有创作行为,因此朗读人是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6]。
3.人工朗读型有声读物涉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录音制作者权
张书青认为,对朗读行为的录音,实质是复制文字作品。无论是朗读、录音还是后期制作,文字的表达方式并未改变,因此改编并没有达到独创性的标准要求,故制作有声读物的过程不属于改编行为,仅改变了文字作品的载体,只可能形成复制件[7]。王迁也认为朗读是一种表演,对表演的声音录制会形成录音制品,因此对作品朗读的录制则涉及复制权。
同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第二款规定“录音制品,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他声音的录制品”。由此也不难推出,可以将有声读物视为原作品的录音制品。
如果将朗读的声音录下来上传到APP 供其他网友点播和下载,算不算公开呢?是否涉及著作权人的表演权呢?其实把录好的文件上传,已经结束了表演,自然不算公开。关于是否涉及表演权,王迁认为在我国同样不涉及,因为所涉行为是对作品表演的录音通过网络进行传播,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而非表演权。录音制作者对其录制的录音制品依法享有录音制作者权,如果他人用户未经授权上传有声读物,则侵害录音制作者的录音制作者权。
三、我国有声读物侵权纠纷司法实践
(一)我国有声读物法律纠纷整体情况
巨大的市场和前景让众多从业者满怀希望,形成了包含作品作者、朗读者、录音制作者、传播平台的产业链条,复杂的出版环节和众多的参与主体让有声阅读面临众多困局。
为研究有声读物在著作权领域的纠纷,选取北大法宝数据库,“民事案件”为类型,“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为案由,以“有声读物”为关键词,检索生效裁判文书。对比发现,司法实践中法院观点不尽相同。
(二)我国有声读物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属
1.我国首个有声读物纠纷案件及司法定性
2005 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张某诉北京T网络文化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判定被告侵犯原告网络传播权,“原告作为《张震讲故事》系列录音制品故事文本的作者、故事讲述的表演者、录音母带的录制者,依据《著作权法》享有该系列录音制品内容的著作权、表演者权和录制品的录音制作者权,他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制、发行……”。可见,法院认为有声读物属于作品。
2.法院审理有声读物时是否归属改编作品观点不一
我国现有立法与司法中缺乏有声读物相关规制,所以法院的法官只能在有限的法律范围内审判案件。针对有声读物的相近侵权纠纷,不同地区的法院及法官的观点不一,从收入案件看,大致呈现如下地域性分布。
(1)上海地区法院普遍认定有声读物为改编作品。鉴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定义“有声读物”的权属范畴,类案发生时,法官往往参考已审案件。可能受首个案件的影响,闵行区人民法院通过“许某诉Y 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认定有声读物属于作品的演绎作品,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杜灵燕,认为该作品改编为漫画、话剧、有声读物、游戏等行为均属于改编行为。
(2)北京地区法院普遍认定有声读物为改编作品。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首个有声读物案件时,将有声读物认定是作品;在“上海X 娱乐与北京K 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审理中,也认为有声读物通过平台展现,改变了载体,是新的作品。
朝阳区人民法院通过“魏某权诉北京D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认为有声读物形成过程达不到独创性的高度,未形成改编作品。
(3)杭州地区法院普遍否认有声读物为改编作品。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谢某诉L 公司案”时,认为将作品录制成有声读物并未改变文字内容,因而未改变作品的文字表达,不属于改编。较之学者很早就开始指出有声读物不属于改编作品,该案是转折性案例,引起了法律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不少学者,包括王迁在内,认可此观点。
西湖区人民法院认为改编权是对作品做出改编,从而创作出具有独创性新作品的权利。改编行为,是指在保留原作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原作品创作出新作品的行为,故有声读物不属于改编。
3.有声读物涉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录音制作者权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认为录音制作而得的有声读物不是演绎行为而是复制行为,其权利人基于其复制行为享有邻接权之录制者权。因有声读物大多都在平台播放,因此相关的纠纷案例均认可上传有声读物的行为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录音制作者对其录制的录音制品依法享有录音制作者权,如果他人用户未经授权上传有声读物,侵害了录音制作者的录音制作者权。
四、境外有关有声读物的法律规制及我国法律规制建议
(一)视障者关于有声读物的合理使用
《马拉喀什条约》的无障碍格式版未明确列出其具体覆盖的形式内容,而是仅仅说明其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因此,可将任何能够使视障者感知作品内容的版式归入无障碍格式版。由此,对于视障者而言,有声读物是其豁免侵犯著作权的合理使用的一种方式。目前我国法律文件如《著作权法》,尚未与《马拉喀什条约》衔接,故有声读物的合理使用在我国并不合法。建议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文件,合理使用并建立衔接机制,以便符合《马拉喀什条约》的内在要求。
(二)有声读物的行为表演,其朗读者享有表演者权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二条a 款明确了对作品进行朗读的人为表演者,此条款从侧面肯定了朗读属于表演行为。然而遗憾的是,b 款表示“视听录制品是指活动图像的体现物”,而有声读物很多通过声音的媒介存在,很多时候是没有可视的“活动图像”,仅通过平台播放,读者看不到活动图像;然而严格来讲,有声读物并不受此条约的规制,但也有其积极意义,最起码认定朗读行为属于表演,涉及表演者权。而我国《著作权法》的表演是指公开表演,此要求就把有声读物排除在外。虽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认为朗诵的行为属于表演,但这只是法院的解释,尚未纳入法律要求,故建议可以适当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将朗诵行为规制为表演。
(三)普遍认可有声读物涉及复制权而非改编权
依据《德国著作权法》,可知有声读物属于复制权,原著的朗读者所再现的仅仅是原作者在作品中已经设想好的东西,其智力成果并未表达出来,而是把文字里作者的声音带给读者。《日本著作权法》第二条也表示,将表演或者广播制作成的录音或者录像,属于复制。《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改编权,但是通过广义的复制权来界定侵权。《伯尔尼公约》第九条第三款直接规定“朗读小说并录制的行为是复制行为不是改编行为”。《马拉喀什条约》的盲文版、大字号版和有声读物,其发行权和向公众提供的权利均属流通环节,只可能是复制权。
早期我国很多法院认为有声读物改变了文字的载体,制作者/朗读者是著作权人,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后来从著作权条文角度思考,认为有声读物的制作行为属于复制,不是改编。目前来看,有声读物涉及复制权的呼声虽然比较高,但远不如纳入法律定义有效果,还需根据实际情况,思考涉及具体权利是什么;同时,随着有声读物的发展,相信很快全球互通,当发生跨国侵权纠纷时,以令国内外都信服的理由进行审判,也十分重要。
五、结束语
有声读物允许大众聆听绘声绘色又诙谐幽默的优秀作品,与书中内容产生亲密的交流与共鸣,感受语言的魅力和文化之美。然而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其进行规制。面对错综复杂的侵权纠纷,学习国际相关法律规制的经验,从有声读物的产业链入手,采取相应的举措、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起相应的授权机制、完善行业协会、形成多方合力,从而有效减少有声书侵权案件的发生,维护有声读物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