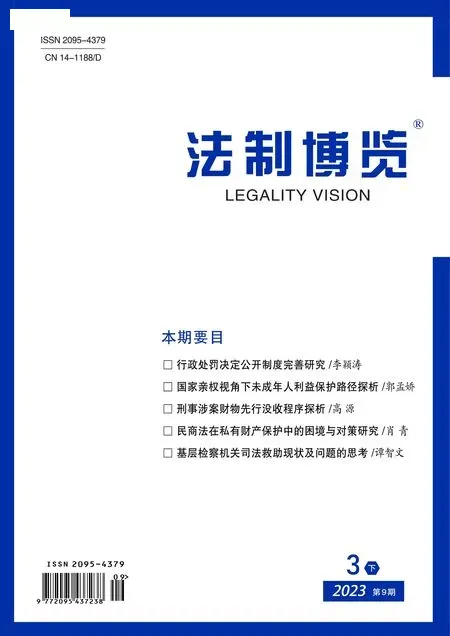网络环境下数字音乐著作权多元许可模式的研究
2023-10-05张琳蔚
张琳蔚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一、我国当前的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及发展障碍
(一)数字音乐独家授权模式及发展障碍
我国的音乐市场在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音乐版权一直不受重视,盗版作品猖獗,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为解决音乐版权普遍侵害的现状,2015 年7 月,国家版权局发布《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组织开展维护数字音乐版权市场秩序的专项整治工作,对盗版音乐市场进行治理,有效地提高了国有数字音乐版权的保护意识。[1]
在我国传统唱片行业向网络数字音乐转型的过程中,音乐录音制品的公司与网络音乐平台服务提供商普遍以独占许可的模式进行合作。这样的模式使得网络音乐平台能够获得独家的音乐资源,通过垄断曲库的方式培养兴趣用户的付费意识,从而有效地保障了音乐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网络音乐平台运营收益,遏制数字音乐盗版行为,促进音乐作品的正版化发展。然而,这种充分依靠于版权集中的许可模式在音乐产业发展中容易引发与转授权、独家版权之间的版权纠纷。[2]因为音乐版权之争发展越来越激烈,国家版权主管机关对国内盛行的独家版权现象进行规制,提出数字音乐作品应当“全面授权、避免独家版权”的指导意见,主要通过与各大网络音乐服务提供商及音乐唱片公司等进行约谈方式推动许可授权模式的发展。该项政策的出台使得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模式面临着政策阻碍,作为数字音乐版权许可主流模式缺位导致数字音乐版权授权许可运作一时难以为继。
除去国家政策对数字音乐独家授权模式的规制因素,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模式始终无法解决其限制数字音乐作品传播范围及容易造成数字音乐市场恶意竞争的缺陷。[3]音乐作品具有特殊性,如果仅由一家网络平台通过独占许可的方式掌握、垄断大部分的音乐作品版权,则可能会使这些音乐作品仅能在单一平台进行传播,无法满足大众对于音乐作品的公共消费需求。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模式虽然曾一度成为主流的音乐作品版权许可模式,但仍不能成为我国版权主管部门倡导的授权模式,仍需要其他许可路径进行补充和完善。
(二)数字音乐集中许可模式及发展障碍
集中许可相较于独占许可,作为传统音乐作品形式的著作权许可的主要模式,其以尊重著作权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集中管理音乐著作权人的版权而有效压缩了交易成本。[4]因此,集中许可模式不仅为我国音乐版权主管部门所倡导,也有学者研究观点认为数字音乐集中许可模式可以解决传统音乐产业与互联网音乐产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我国音乐作品集中许可模式的管理组织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音乐作品的集中许可模式的运作依赖于管理组织的有效管理。音著协和音集协自成立以来,通过集中许可模式提高了音乐作品的许可效率,并且通过诉讼活动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的音乐作品集体管理组织在实践管理工作中也存在诸多工作弊端,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的运作效率低而导致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我国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设立了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由政府主导的组织机构,因此其在集体管理组织市场中具有垄断地位。这样的性质容易导致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缺乏外部竞争刺激,其存在和运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使权利人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也没有完全发挥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优势,最终实际上反而降低了著作权人创造生产的积极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为了提高许可效率和简化许可工作内容,允许使用人在支付固定标准的使用费之后可以使用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全部作品。但这样的模式对于只需要获取部分作品的使用权的使用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明显会增加其获取作品的成本,构成商品的“搭售”。
二、“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与网络环境
(一)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模式及正当性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主要为录音制作者取得音乐作品权利人的许可之后,可以通过聘请表演者表演该音乐作品并录制成录音制品进行发行。发行之后,其他的录音制作无需再征求音乐作品权利人的许可,仅需支付报酬,便可自行聘请表演者表演相同的音乐作品,录制新的录音制品。因此,法律规定的关于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针对的是传统实体的录音制品的制作和发行行为[5]。
音乐作品不同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电影作品等其他作品,其数量庞大,并且整个作品的时长都比较短,从而提高了人们欣赏音乐作品的频率。在数字音乐出现之前,录音制品是公众欣赏音乐作品的主要方式,也是传播音乐作品的首要和有效的途径。音乐作品的权利人对其作品被制作成录音制品并进行发行享有许可给他人使用的权利,如果大部分的音乐作品权利人选择与录音制作者签订专有许可合同,将复制和发行的权利仅允许一家公司行使,那么将会导致音乐作品无法由不同风格的表演者进行表演,限制公众对于音乐作品多样化的选择,从而损害音乐作品的多样性。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设计的目的,便是干涉音乐作品权利人发放专有许可的权利,使其他使用人能够在法定条件下对相同的音乐作品进行各具特色表演演绎,并制成录音制品进行发行,将丰富多样的音乐作品展现给公众,保护音乐文化的多样性。
(二)“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在网络时代存在的必要性
“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针对的是音乐作品被制作成实体唱片的载体,而在互联网迅速普及发展的时代,数字音乐在我国音乐销售市场中占据超过90%的销售比例。虽然音乐作品传播的主要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音乐作品依赖于被表演后才能为人所欣赏的特性仍然存在。在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的传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对表演音乐作品的音乐会、演唱会的网络实时直播;二是网络平台按照约定的时间对音乐作品表演的录音进行播放传送;三是音乐录音的“交互式传播”,即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点播或者下载音乐。在这三种方式中,前两种依然无明显差异,属于“线性传播”,因为无法自由进行选择获取,不可能作为人们欣赏音乐的主要方式。第三种则是在网络时代最重要、最普遍的人们获取和欣赏音乐录音的主要方式,并逐渐取代传统实体的录音制品,成为人们欣赏音乐的主要渠道。如果音乐作品权利人同样在网络时代对录音制作者发放专有许可,前述专有许可影响音乐作品多样化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身处数字网络大环境下,对“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进行重新设计才能发挥其在网络环境下促进音乐作品多样化传播的正当性。
音乐录音在网络上的点播与下载,在我国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范围的行为,虽然都属于“交互式传播”,但美国版权法未将其规定入“信息网络传播权”中,而是属于表演权、复制权和发行权的范畴。因此,美国将“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延伸到网络环境中的制度经验值得参考,但不能直接套用,首先还是应以我国国情为依据进行重新设计。
21 世纪以来,网络在我国迅速发展并成为了音乐作品传播的主要渠道,但是在发展初期,因为对其的制度和监管不完善和滞后,导致先期存在大量的未经许可的数字音乐传播行为。实体唱片业本因盗版行为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现又遭到新兴网络数字音乐盗版行为的影响,实体唱片行业几乎消亡。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音乐作品权利人将大量的音乐作品的网络点播和下载的专有许可权进行发放,对于音乐作品文化的多样性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将超过传统的实体唱片行业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由此可见,我国对于数字音乐版权发展方向的规范管理,依据“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精神进行重新设计非自愿许可制度,使之适应于网络环境,仍具有正当性。同时,自2005 年来实施的“剑网行动”等执法行动,已经基本遏制未经许可肆意传播数字音乐的侵权现象,有效规范了盗版侵权行为。2017 年,各大数字音乐服务商爆发的音乐作品版权资源之争,也反映了公众对于数字音乐版权保护的重视和意识的提升,也体现了音乐作品权利人对于数字音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性得到了保障。因此,在目前重视版权保护的大好环境之下,数字音乐版权非自愿许可制度的合理设计便能发挥积极作用,克服在实体唱片时代存在的影响法定许可制度发挥作用的障碍。
三、数字音乐版权非自愿许可制度的设计
目前我国数字音乐市场的发展,仅凭自愿许可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公众欣赏多样化音乐作品的需求,因此对其设置非自愿许可进行限制便具有正当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数字音乐的网络点播和下载。[6]因传统实体唱片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规制的是制作和发行录音制品的行为,故在设计关于数字音乐的非自愿许可制度时,应当结合音乐录音网络传播的特性。
在网络环境中,录音制作者和音乐录音点播和下载服务的提供者,即“数字音乐平台”,不同于传统实体唱片时代的唱片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因此,鉴于数字音乐传播的特征,数字音乐的非自愿许可在适用范围上,应不仅及于传统的录音制作者将制作的录音制品上传提供给网络点播或者下载,也适用于获得录音制作者许可后,将上述音乐录音上传至网络提供点播或者下载渠道的数字音乐平台。《伯尔尼公约》第十三条只规定了允许对音乐作品录音制作,而没有提及发行录音制品,其内在原因在于发行制成的录音制品本就是制作的后续当然行为,是该项非自愿许可制度的应有之义。
在我国实体唱片时代,由于“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实施效果不理想,因此在设计数字音乐版权非自愿许可制度时,可考虑借鉴《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的相关规定,适用于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的音乐作品制成音乐录音并提供给网络平台点播或者下载的行为。与法定许可制度相比,强制许可的行使前提是使用者已经与权利人进行过协商,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才能向主管部门申请获得许可,因此,该项制度主要是促进录音制作者与权利人关于许可使用的协商。上述资源许可制度可主要针对数字音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提供网络平台音乐录音的点播或下载服务的持续时间作为计算许可费用的依据,便于明确许可费用的数额。同时,由于强制许可需要经过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查,因此,有利于管理和规范音乐作品的申请使用记录,便于核查,避免出现逃避付费义务的行为。强制许可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
四、结语
我国数字音乐领域面临的版权保护和发展问题,不是任一单一的许可模式可以解决的,并且建立一种一劳永逸的数字音乐运行机制也绝非一蹴而就。在实体唱片业逐渐式微,互联网行业逐渐发展壮大的时代,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亦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未来数字音乐运行机制的建构,有赖于数字音乐作品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商及网络用户三方版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自我行为的规范,在数字音乐产业的运作中发挥多方集体智慧,助力数字音乐版权保护制度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