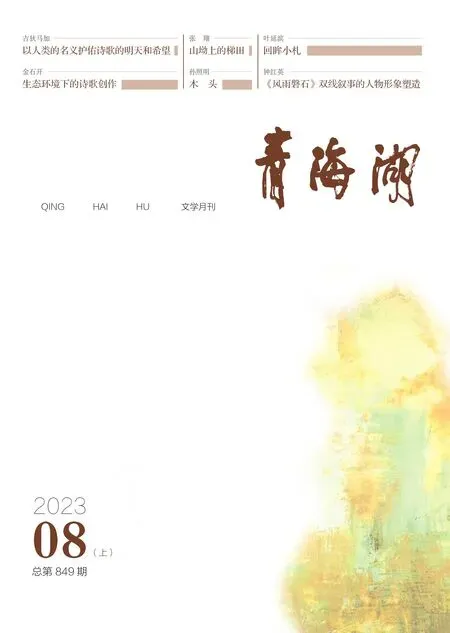生态变迁中,诗人何为
2023-09-26马海轶
马海轶
不久前,南京的朋友王方教授给我布置作业,建议我先读王维的某首诗,得到启迪之后,再写一首当代诗。这是非常有趣的创意。王维是唐代人,他在761 年去世,距今已有1262 年。他特别有文化,有情操,有思想,是我心目中当之无愧的 “诗人中的诗人”。他感到官场束缚,不很自在,经常渴望回到大自然里生活。——实际上,一有机会,他就跑到蓝田的辋川别业,享受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把自己的理想写进诗歌,成为谢灵运、陶渊明以来山水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从前念书时,也曾读过王维的诗。但毋庸讳言,年少时读诗,大抵是为了时髦和热闹。年过半百而且带着任务再读,就有了许多新的感慨和心得。文学史上所谓的山水田园诗,实际上是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环境为歌咏对象。可以看一个例证。《山居秋暝》这首诗非常有名,许多人耳熟能详。但为了说明方便,我还是引用在这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诗歌的大意是,空阔的山里,新下了一场雨。雨后傍晚的天气使人意识到已是初秋时节。皎洁的月光从松枝间洒下,清澈的泉水在石头上淙淙流淌。竹林喧响,想是洗衣的姑娘回来了,莲叶轻摇,一定是上游的小舟下来了。春天的香花芳草不妨任随它消歇,秋季的山里隐士也可以久久居留。
王维通过这首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四季宜居、生态十分友好的生存环境图画,这是肉体和灵魂理想的栖息之地。后世的诗评家不管从那个角度,如何诠释这首诗,但人们不能否认的是,在这首诗里,自然生态与人的理想高度契合而且平衡。事实上不独王维,文学史上其他的山水田园诗人,绝大多数作品,都讴歌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健康、包容以及和谐。这种和谐在中国哲学里被浓缩为“天人合一”。
读古代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时,不禁要联想到我们当下的处境。在古代诗人看来只要下定决心,归去来兮,就能不期而遇世外桃源般的生态环境,在当代已经不那么容易找到了。即使局部存在,也笼罩在全球温室效应的浓云之下,即使远离工业中心的偏远地区也不例外。就在前不久,我甘肃故乡的花椒树正在开花,却来了一场断崖式降温。突如其来的倒春寒杀死了花蕾,那里的农民担心,花椒这种做菜时必不可少的著名调料,今年可能颗粒无收了。我不敢肯定,王维的时代没有倒春寒,但根据大多数的科学研究,近代以来,生态事故越来越频繁。只要是生态灾难,也不会局限在一时一地,酿成的往往是更多人的灾难。
虽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全球变暖是科学家编造出来的谎言,美国因此退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每天打开报纸、电视,网站,都能看到层出不穷的生态事故。昨天早上我看到的消息标题是:“强厄尔尼诺或来袭:破纪录高温,逾26万亿经济损失”、今早我看到的则是:“陆天气网推高温打卡日历,多地炙烤40℃将持续4 天”。每次回乡或者通话,乡下那些粗通文墨的左邻右舍都会强调:“老天爷越来越不正常了。”
现在要回到正题了。在生态环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诗人何在?每当有特定事件或者议题出现时,诗人从不缺席,从来都是活跃的一群。就说去年前半年吧,丰县八孩事件披露,俄乌冲突爆发,一夜之间,诗歌圈子里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和表达,甚至以各自所持观点为暗号,形成了分明的阵营对峙。但在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生态灾难面前,诗人似乎缺位了,失语了,至少没有找到适当的、感人的、深刻的言说方式。2022 年8 月17 日晚,近在咫尺的西宁市大通县瞬间强降雨,引发山洪,造成泥石流。截至8 月21 日,山洪灾害已造成26 人遇难,5 人失联。如此重大的生态灾难发生将近一年,我没看到任何的文学表达。有人说:“当气候崩溃,一切都崩溃。”以王维为代表的古代诗人,厌倦了都市和官场生活,他们还有退路,还有选择,选择大自然和田园生活安放肉身和精神。但在今天彼伏此起的生态灾难面前,我们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不管诗人多么不想在现场,但他必定在现场。
在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斗争中,政治家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决定政策,亿万富翁可以捐献财富拯救生态,演说家奔走呼号,环保人士身体力行。诗人何为?古代的诗人只有笔和纸。今天的诗人,大多不用纸和笔了,但他也只有键盘,但这已经足够了。诗人的感情和激情、使命和责任尽在他的文字里。正如我们通过古代诗人的文字,了解那时的人们和他们生活的世界一样,未来的人们亦将通过我们的文字,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及其变迁。如果后人能在我们的作品中,看到我们在生态灾难面前表现的勇气、智慧和力量,那就足以证明我们存在和写作的价值。
该给王方教授交作业了。王维曾经写过一首质朴而又深情的绝句《杂诗》,诗共四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诗人接待了一位来自故乡的客人并问他:“你从故乡来,应该知道那里的事情。你来的时候,雕花窗前那株梅树开花了吗?”诗人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他想知道的事情应该很多。但他先问窗外那棵梅树是否开花了。虽然诗里的寒梅经过多重修辞,但它毕竟还是一棵树。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1262年后,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我也好几年没有回故乡了。兔年的春天,终于有人自由来往于城乡之间。如果用一首当代诗记录我们的谈话,内容如下:
很少谈及
雨水和农事
更不谈窗外的一树繁花
大家说的
无非是谁阳了
谁没阳
谁挺过来了
谁没挺过来的话题
末了叹息
不是梅树不值得问,也不是我没有自然情怀,而是在经历漫长的疫情之后,我和客人之间有更严肃、更迫切的问题。如果说王维的诗里再现的是古代的自然生态,是和谐,是宁静,是美好;那么我的诗里透露的是自然生态的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环境的凋敝,衰落,荒凉和悲怆。我希望老朋友在我的作业里,能看出千年之变。最后我要说的是,人类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诸多代价中,生态环境的毁坏最为可惜和严重。可以说,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世外桃源了,这对诗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现在,我们必须醒来,然后撸起袖子,做诗人该做的那些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