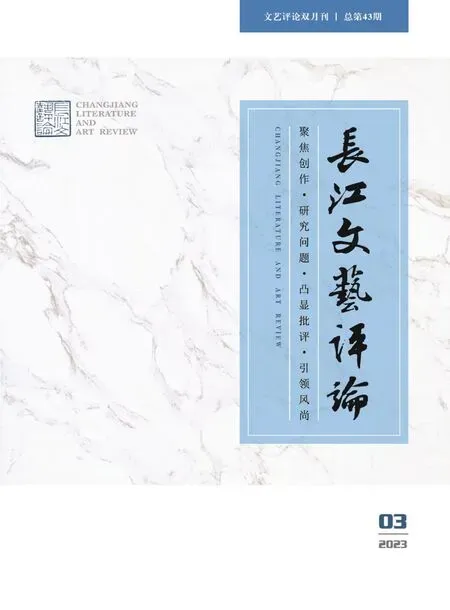时空建构和家园寻找
——林森小说创作谈
2023-09-26梁静华
◆梁静华
林森自2008 年首篇中篇小说《小镇》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后就走向小说创作道路。接着陆续出版了《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等三部长篇小说,发表短篇小说《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有几条路飞往木桥》《抬木人》《丁亥年失踪事件》《台风》《海岛奇事录》,中篇小说《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林森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海南本土作家,他基于海南这片土地,敏感于海南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变化,探究海南社会经济变化引来的人的精神变化。在他十几年的小说创作中,我们总可以看到时空建构和家园寻找之间微妙权衡下的精准呈现,他以海南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作为时间纵轴,以海南裂变中的乡村、小镇和小岛作为空间横轴,对海南的一段历史进行建构重组。在他的笔下海南一段历史变成文学的永恒。对待已经消失或逐渐消失的过去,林森以文学的方式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和对当下的反思:在城市化发展、经济建设中,我们拆除了旧家园,我们的新家园在何处?在无可阻挡的现代化发展中如何建构新家园?在回忆和反思中,林森的小说具有了厚重感,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一、历史记忆的时间:四十几年的海南进程
林森的小说有明显的记忆时间。林森将他小说故事时间设定在中国二十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阶段,讲述海南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几年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改革背景下海南人的故事,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海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密切关联,人物的心理变化总是与中央对海南的政策和海南在改革开放中一些举措相关联,历史转折时期的动荡性、冲突性,海南岛在建设过程中的浮躁感在小说中得到了彰显。《关关雎鸠》中的老人黑手义和老潘是多年好友,他们相继搬到瑞溪镇:“黑手义把灶前挥铲的功夫发挥出来,率先在镇上开了饭馆。老潘是晚他一些时日才迁移到镇上的,那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了。”[1]故事开始的时间是海南改革开放初期,叙述小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变迁。这与海南历史变革的真实时间是一致的,海南曾经孤悬海外,地理上自古远离中原大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政治上也依附两广,长期封闭的环境和依附的政治关系,使得海南岛的经济一直不发达,但经济的不发达使得传统的社会、文化等得以较好地保留。直到1980年海南开始改革开放,到1988 年建省办特区,海南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化在海南岛这块土地上加快脚步,传统的农业社会受到一定冲击。由于建省后中央对海南的政治和经济的优惠政策,吸引来自大陆各地淘金的人,传统农业社会被撕裂出一个口。小镇和城市是人群的聚落点,也是商贸比较发达的区域,有些能力或条件的农民搬到城镇居住,城镇的区域不断扩大。小说中,黑手义和老潘趁着改革的步伐相继到瑞溪镇上开始了商贸的活动,一个开饭店,一个杀羊供应不同的店铺,靠着两个人的手艺,两个家族在镇上站住了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越来越多有形的、无形的外来事物拥入到瑞溪镇以后,1993 年小镇办了大街私立小学,此后歌舞厅、赌场、吸毒在小镇明面和潜面涌现,小镇上的风气开始为之一变,滋生了黑暗,年轻人染上毒品,一夜致富的心理使很多人爱上赌博、参与非法集资。老潘的孙子潘宏亿染上毒品,小镇几乎每个家庭都参与到非法集资中,紧接着镇上家庭破碎,传统社会父慈子孝、夫妻相敬等价值观一一瓦解。
此外,引起林森小说人物命运变化的还有另一历史事件——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2008 年国家明确海南岛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始。此政策一出,进一步推进了海南旅游业的发展和房地产的开发。建省办特区和旅游岛建设两次大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使海南传统社会结构、传统生产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脚步打破了原有的传统文明固有框架,农耕文明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有些甚至土崩瓦解。2009 年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经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岛特别是海南岛的海洋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开发海洋文化为旅游资源成为一种共识。作为国家农业部定性的一级鱼港,因潭门港渔民的《更路薄》的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 年4 月到潭门港考察,此举加快了潭门海洋文化的开发,开发海洋旅游既可保护传统的渔业文化又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得到各界的大力支持,首届南海文化节——赶海节,在多方的促进和配合下在潭门港举行。传统习俗得到开发的同时,海南工艺品也得到了开发,砗磲工艺品成为潭门港一个特色产品。砗磲加工厂以及砗磲工艺品专卖店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增长。但因过度捕捞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在短短的几年内有关部门就出文禁止开采砗磲,禁售砗磲加工品。《海里岸上》的故事就是以旅游岛建设为背景,写海边渔民生活以及渔港小镇的变迁。随着时代发展,渔民传统的捕鱼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老渔民因为身体原因不再从事传统生产,渔民的下一代因为不能承受捕鱼的艰辛也不继承父辈的生产方式,他们乘着旅游岛建设的东风,依托海洋资源,做起跟海洋相关的商贸活动。老苏的儿子在镇上开了一家砗磲店,在旅游热时期生意兴隆,但因为政策禁售砗榘以及加工品,儿子的生意受挫,积压的砗磲无人购买,好不容易有人愿意收购剩下的砗磲,但作为收购的前提条件则是需要老苏把祖辈传下来的《更路簿》和罗盘一起卖给他。值得注意的是,《海里岸上》与《关关雎鸠》虽然都以海南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叙述时间,但《关关雎鸠》的时间精确到明确的年份,《海里岸上》没有确定的时间,但所写的事件与海南岛旅游建设中对琼海潭门港的政策以及潭门港渔文化的开发是高度一致的。
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始后,海南岛的房价短短一年内涨了一倍,海南出现了非常残酷的农村拆迁工程,拆迁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房地产的开发急需大量的土地,公共的项目需要更多的土地。为了获得大块完整的土地,原始村庄往往面临着拆迁,国家策略和商潮共同作用使得海南近年来的拆迁愈演愈烈。作为历史复现的林森的小说叙述,经常出现的字眼是拆迁、征地和房产开发。《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岛》都写到城市的拆迁。《岛》中渔村海涯村被整个拆除了,村民拿着补偿款,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搬离祖辈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子另寻一地居住。“我”的二堂哥因不愿接受整个村子被拆毁的事实,做最坚韧的反抗者,但最终也被强制的手段迁离,最后郁闷喝醉酒死于海里。吴志山被冤枉后栖居的小岛也在开发中支离破碎。
除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林森小说故事展开的背景外,他对历史的复现还体现在小镇神学系统的描写,如《关关雎鸠》中的军坡节,对小镇神灵信仰的介绍,《海里岸上》的108 位兄弟神,真实地再现海南民间的信仰文化。林森的很多小说从大的时代背景以及细小的情节描写都体现出海南某一历史阶段发展和变化。
其实,历史与文学的交合互融在中外文学史上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林森出生于海南澄迈瑞溪镇,求学在海口,工作在海口,在《天涯》杂志工作的经历让他拥有开阔视野,他对海南历史的了解以及对海南政策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他的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总是与海南历史事件的时间密切联系。林森小说故事时间跨越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二十年,这四十几年的时间是海南发展建设最快的几十年,传统的乡村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发生变化,熟人社会变得陌生,旧的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已经被打破,人们面对新的动荡的社会变得迷茫和不知所措,在紧张无序的状态下发生了矛盾与冲突,整个社会变得混乱、焦灼、浮躁。这些记忆都是海南历史的转折时期的记忆,可以说林森从自身经验出发,描写海南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转折点上的小镇、乡村,他的小说描述海南人的生活及心理历程。他将虚构的故事与历史的真实结合在一起,虽然文学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作品,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对某段历史的呈现,因此林森的小说是对海南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复现。
二、记忆空间转换:现实到意象
林森小说的空间呈现从小镇和城市到小岛的变化,具有从真实空间到虚拟意象空间转变的特点。瑞溪镇,从行政区域看属于海南澄迈县一个真实的小镇,它也是林森中篇小说《小镇》以及由《小镇》拓展而成的长篇小说《关关雎鸠》的故事和情节聚拢的空间。《关关雎鸠》开篇就从小镇人对新事物——私立学校的感受开始的:“私立小学在小镇上是新鲜事物,之前只是听说,哪有人见过?私立小学开办了,不会被公立学校叫人去拆了吗?私立小学的学生毕业了,有没有中学愿意招?这些都是让人困扰的问题。”[2]新兴事物翻涌在小镇的上空,标志改革的风吹到了小镇,对于新事物小镇之人存很多疑问,但总有人愿意去尝试。大字不识几个的杀猪佬们组成的校董会办起来私立学校,教室是大街(街面)东一间西一间组成的,教师是临时才想到聘请的退休教师。教育的功利性也是明显的:用两年的时间打出学校的名气来。小镇充满了动荡以及浮躁,在这样的氛围下,小镇人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常以非理性化的方式对待。博彩摊位在小镇铺面门前一路排开,啤酒机赌场公开在小镇出现……小镇的人投入新兴事物带来的新奇和刺激中,追求享乐,偷吸毒品,出现赌钱打架,更多的人则是追求非法集资。在这场人性与金钱的追逐中,小镇的人被“天上掉下馅饼”砸昏了头脑,他们不顾亲人阻拦和家底被掏空的风险,一头扎进了这场浩劫里,最终家庭破灭。与新事物涌现相反的是旧事物在时代发展中,其发展受阻或逐渐消失。“军坡节”是为纪念南北朝时期岭南圣母冼夫人而形成的民间节日。冼夫人平定海南动乱、上书设置崖州,使百姓安居乐业,冼夫人死后,在各个朝代皆被追慕,而她带兵出征的威风场面,也为之后的海南人所向往——为表达这种向往,后人模仿洗夫人当年壮观的出军程序和仪式,组织队伍举着刀枪举行阅兵;当然,也仿制当年洗夫人的百通小令旗,一令传下百事顺,模仿者自豪,旁观者尽欢,谓之“装军”。装军这一天,便是军坡节。传承了一千多年的军坡节的“装军”活动因考虑到安全问题而被取消了。因此小镇人交织着两种情感:对新事物或持观望或勇于尝试,对旧事物的流失患得患失,难以释怀。因而动荡不安和患得患失的情感飘荡小镇的上空。林森的小说读来总让人感到并不轻松,总让人感叹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挣扎和难以把控自己命运的沉重。
林森《关关雎鸠》中的小镇无疑是闭塞的,在历史的转折期,虽然不断有外来的新事物和人物拥入小镇,但小镇的步伐总是跟不上附近的小镇和城市,瑞溪镇的年轻人和觉得宝刀不老的老头总爱到跑到八公里外的永发镇去理发,那里是瑞溪镇人们受到刺激后释放精神和肉体的地方。瑞溪镇的闭塞总是使镇上的人模仿城里人的生活,镇上最热闹的“向群茶馆”,这个店因老板娘去省城海口“向群”茶店喝茶而命名,店上把包子馒头、蛋饼不叫糕点而叫“果”,据说也是老板娘带回来的称呼。连口头话语“天要崩啦”等词句都是老板娘觉得她的茶店在封闭的小镇至少用词要跟省城同步而在茶店频繁出现。瑞溪镇的闭塞让瑞溪镇总是在向它地的学习和模仿中完成它进化的脚步,在模仿中获得认同。
小镇是林森小说无限延长的空间概念,不仅在《小镇》《关关雎鸠》中出现,在《海里岸上》也出现。《海里岸上》虽然故事发生的地点还是小镇,但是这个小镇已经与瑞溪镇有些区别了,它的镇名不再是行政意义上的镇,名字是虚构的,但是镇上发生的事,能折射出这个镇与现实中琼海市潭门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里的人物、物件、经济、信仰、文化等等都可以在潭门镇上找到印记,与国际旅游岛政策下潭门镇的旅游建设相关联,到此时林森笔下的小镇由实指过渡到了虚构,只是虚构与真实有太多的吻合。但从本质上看林森笔下的小镇也由内陆封闭的小镇转变成了海边较为开放的小镇,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空间则由农耕社会小镇变成了渔耕社会小镇。两种不同性质的小镇承载了海南两种不同的文化,但无论哪一种文化,都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变化。
林森在《讲述者的忧郁》中袒露他的心胸:“我更多的写诗歌,而当有一天诗歌的抒情难以容纳一些膨胀的力量之时,小说就开始流淌,小说所具有的讲述本质注定讲述者要面对很多障碍……我曾有过这样的尝试,在故事的开头我尽量疏远熟悉的场景,让情节显得陌生,可当写到某一行的时候,故事自动发生了转变,熟悉的经验开始浮头,开始左右故事的走向,我试图隐藏、改头换面、顾左右而言他,可写下的文字仍然确切地呈现出生活内在的真实。”这些话语足以看出林森小说创作很多时候是经验的写作,而且越是早期的小说这样的痕迹就越明显,林森显然也意识到他小说的写作受经验影响很多,因此此后的小说创作开始极力避免。但我们也看到林森小说的故事都是讲述海南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过程中海南社会的变化。林森主动规避经验写作对小说故事的内容影响不大,但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和空间则开始脱离前期小说中真实的空间以及真实的名字,由实写到半实半虚再到虚,他完成了小说虚拟空间的营构,这是林森小说创作理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之后的小说创作也日趋实践他的创作理念。从《海风今岁寒》开始,他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融入写意和象征,小说也具有更多的意蕴。在长篇小说《岛》中,空间的变化、主题的挖掘等都与初期不一样,不同于《关关雎鸠》中的琐碎,小说有了诗意的象征。小说有两条明显的叙述主线,围绕两条主线的则是小说的两个空间,一个是海涯村,另一个是荒芜的小岛。小说的第一章就是围绕海涯村被拆迁写的,房地产热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海涯村的村民多么矛盾、纠结和不舍,但多方角力下村民都需另寻它处安置自己的家园。被冤枉坐了十年牢房的吴志山,觅得一处无人的小岛,远离社群生活,孤身上鬼岛,以寻得鬼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吴志山与“我”的交集则是“我”迷茫和颓废之时驾车去环岛时发生的,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无所事事之人对另一个无所事事之人的兴致勃勃,一个闲极无聊的人对另一个孤独者的好奇,但实际上则是“我”对家园的寻找被固守家园的坚持的吸引。吴志山置身于空无一人的荒岛,他感受到的并非恐惧、空虚和孤独,反而打开了一个生命原力与万物生灵相互应答的世界,人与狗、人与植物、人与环境、人与时间、人与自身之间有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文明社会的丰富性。吴志山由开始到岛寻鬼伸冤,再到后来与荒岛的融合,他的心灵也恢复了平静,荒岛成了平静的家园,因此岛不仅仅是现实的岛,而且更多的是有象征意义的岛,它是家园的象征。
林森小说空间的扩充使得他对海南社会转型时期历史和文化的概括更加完整。他试图通过小说的形式构建系统的历史,因此他的小说叙述具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历史性的叙事更加完整,他的创作在空间的拓展中也走向成熟。
三、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家园的建构
林森把四十几年海南历史变化通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作为固化的历史,海南四十几年诚然在地方志等官方史料也不缺少记载,而且史料比起小说,记载显得更加详细和更让人信服。林森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的小说很明确不是对历史的记载,是以历史为背景的虚构,他的生活经验支撑了虚构,而虚构使他的经验得以升华,使他摆脱了平庸和无趣。最初他的小说创作经常以明确的时间为纵轴,以真实地名为横轴,后期小说虽然也离不开海南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背景,但是其时间并不确切,地点也不再是行政区域中的真实地名,越到后面其创作意指的真实性更加明显。时间变化、空间的实转虚的背后则是林森思考的加深。纵观其十几年的小说创作,不难看出无论是早期中篇小说《小镇》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长篇《关关雎鸠》,还是《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里岸上》《岛》,其实都围绕家园的丢失和家园的建构问题。
林森小说家园的丢失既是物质层面的,又是精神层面的,正因物质家园的丢失,依赖于物质家园的精神文化的丧失,引起心理的不适应和无所寄托,造成了心灵的裂变和无所依靠的不安和震荡,生活中的人也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游子。
《关关雎鸠》中,黑手义和老潘到镇上谋生初期,虽然他们生产方式改变了,但小镇这个空间场域最初还是安定的,因为这里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因此,他们的新家园尚且能收纳他们离开农村这个旧家园带来的不安和恐慌,并没有引起很多心理不适。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镇的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伦理的沦落,吸毒、赌博、嫖娼等等瓦解了家庭的和睦,传统观念也随之崩塌。小镇原本的生活在现代乐感文化和糟粕文化的层层逼近下被拆解了,剩下的是年轻人对现代生活的盲目追求。曾德华作为最早的小镇吸毒人,诱惑小镇的年轻人加入吸毒的队伍,黑鬼的赌场、张小兰的麻将馆诱惑多少人沉沦其中,小镇人的疯狂更把三多妹的非法集资推到无可挽回的余地。小镇的年轻人亲手拆除了曾给过他们温暖的小镇,使它变得冰冷、陌生、恶毒。象征着小镇灵魂的军坡节“装军”活动也因某种原因被县政府阻拦而停办十年。传统聚落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陌生的生活方式,熟悉的陌生人,以及丢掉的“装军”活动使小镇的人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小镇到处是浮躁和不安的灵魂。正如文中老潘所想的那样:“赌场、毒品……像风一样,正在瑞溪镇各个角落弥漫,正在日渐渗透宁静的日子,正在把一栋建好的房子的地基抽掉,今后还会有什么呢?一切都会崩塌,一切都在沦陷”。[3]小镇不再是一个能给他们温暖的家园,而成了束缚他们心灵的另一个场域,老潘和黑手义在一次次的对话和反思中,怀疑自己离开祖辈赖以生存的农村的正确性。
既使物质的家园没有被拆除,但是强韧地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传统生产、传统生活以及精神文化一旦面对外界日新月异的蜕变,难免不引起心理的不适,这也是家园丢失的表现。《海里岸上》的老苏总在木麻黄林雕刻一艘小船,村里的门锁被海风吹得长了锈,他熟悉的港口小镇“算是焕然一新了。各级领导在镇上的行程,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的报道,把镇子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给小镇带来了很多陌生的面孔。”小镇在发展过程中变得陌生,商业不再是单纯的港口小镇,商业不再是单纯的鱼产品的交易,更多的海洋产品的出现打破了商业的单一,深海的砗磲等海底生物工艺品成为商品售卖。在开发浪潮中,老渔民无奈的叹息也难以阻拦小镇的变化。小说中,老苏的渔船被买下但并非做捕捞之船,而是成了移动餐厅。庆海爹的儿子为利卖掉了祖先留下的《更路簿》。老苏家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航海经验的汇集本《更路簿》和罗盘,在商业社会的压迫和儿子装病卖惨下被迫卖给收藏家,连寄托了精神信仰的祭海仪式也输给了现代的仪器,老一代的渔民的精神寄托也随着商业社会的入侵受到摧残。渔村渔港还是靠海吃海,但靠的不是传统,而是附加新兴产业的海,产业转型使传统的家园变得陌生,难怪阿黄说道:“一门心思只想着钱,渔村没有了……没有了……”面对新兴的陌生的镇子,老渔民内心惶恐不安,“城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噩梦般的存在,那种感觉犹如水中无根漂泊的浮萍。
诚然,林森也意识到谁也无法阻拦住现代化进程的脚步,那么在社会进程中如果建构自己的家园呢,这也是林森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
早期林森的小说对家园建构问题的思考常借小说中的人直接表达出来,正如黑手义在感受到越来越躁乱的人心后,“躁动不安的镇子,让他有搬回村里的念头了。当然搬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他们怀疑当初走出村子的决定的正确性,尤其当住在镇上的不安感加强后他们想搬回农村,但进而他们觉得回农村是不可能的。搬回了农村,心灵不一定得到安宁。其实在林森看来农村原有农耕文明在社会转型时期也受到了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农耕文明环境孕育下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逐步衰退甚至崩溃瓦解,由乡村到城市再回归乡村这一持续数千年的人才循环流动结构被完全颠覆,变成了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因此返回乡村寻找精神家园也不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那么勇往直前,随着潮流去拥抱生活,就可以找到精神的家园吗?在林森看来也是行不通的,正如老潘说“离开农村,是不是只想换一个能安稳睡觉的地方?当然了,在那时,瑞溪镇是村里人最大的向往,宛若一切活动的中心,宛若是世界的中心,不承想,这里只不过是一个狭窄的牢笼。黑手义是不是都要死了,还想着往外逃,所以才一声不吭,悄然隐蔽?现在,潘宏亿也要去三亚了,那是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城市,可,那里,难道就不是另外一个狭窄的牢笼吗?”[4]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精神的家园丢失,总是要去寻找容纳自己精神的家园,但找到的也只是心灵的暂居之地,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园又再一次失落和毁损。但人类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不断的寻找中走向成熟。因此,在他的《岛》中,我们看到两种精神家园建构的方式。一种是“我”伯父那样审时度势在合适的地方建构精神家园:当所生存的海崖村面临拆除时,伯父在离省城不远的小镇买地建房,形成了自己新的物质家园,当他把封在箱子里的祖先牌位,安放到三层半楼顶预留的祖屋时,伯父又一次完成了其建构物质和精神家园的重任。另一种则是吴志山那样在避世海岛上完成自我精神的建构:吴志山被冤枉入狱十年,妻离子散,双亲去世,生命被推到最低谷,他以赴死之心到小岛上寻鬼伸冤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岛融为一体,精神与万物齐存,生命在避世的小岛上得到延长,冤情变得不重要了,在静谧中人与物达到合一,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小岛成了吴志山的安全的庇护所和精神的归宿。但当他建立起来避难的小岛在他无比眷恋中被毁掉,他变得更瘦,眼圈发黑,眼珠泛红,好像跟无数个对手,进行过生死搏斗。这种丢掉家园的无所适从和精神萎靡使他的生命走向滑坡。族人的热情以及村里的人间香火挽留不了他,再次寻找新的小岛居住成了精神的出路,即使新的无名岛萧条、原始,也比原来的岛更小,并且没有生活所需要的淡水,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搬到小岛上。
林森的小说确实也指出来建构家园的种种可能,但这些可能并没有真正让人达到彻底的皈依,社会发展过程中总是在不断拆除不适应历史发展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但也在建构,建构符合历史发展的精神新家园。我想林森的小说建构家园的多种可能就有了深层的意味: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在不断地丢失旧家园,也在不断地追求新家园,即使新家园也可能再次面临被摧毁的命运。但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不断开掘自己新领地,不断地跨越自己的局限,人在不断开掘和跨越中,心智更为成熟,精神更加丰富,社会也在人类一次次的开掘和跨越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