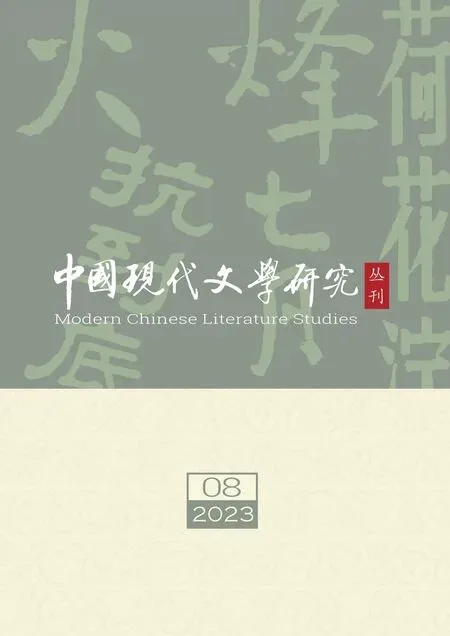晚明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建构及其审视※
2023-09-22王逊
王 逊
内容提要:以周作人为核心的现代文人对于晚明的重新发现及晚明文学研究范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学人对其贡献尚缺乏全面而清晰的表彰。周作人通过标举“源流说”,确立了晚明与五四的密切联系,并就此奠定了后续学人的基本模式。实则这一发现多系策略使然,后续阐发可谓曲解与误读,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周作人以一种特殊但却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甚至规定了晚明文学研究的基本方向。随着“源流说”的传播,“晚明”与“五四”的关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探讨。认同这一命题,肯定“晚明”与“五四”之间存在一定(甚至紧密)关联是主流论调,这一“共识”的形成不仅是对历史传统的简单继承,更是时代主潮的必然要求。但个中过程展示的多是趋势和倾向,对其间的复杂和曲折有所遮蔽,故而学人的质疑或者说辩证也就此发端。除此以外,晚明文学的研究格局也在周作人等人影响下直接或间接造就,即促成关注并阅读公安、竟陵派风潮,培养专门从事公安派研究的学生,推进以公安、竟陵派为主的晚明文学研究,并提出了若干至今仍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断。
得益于现代文艺领域的表彰与推动,以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晚明革新思潮正式走到台前,成为至今仍兴盛发达的学术研究热点与重点。寻根溯源,以周作人为核心的现代文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周作人在晚明文学研究方面未有专门投入,加之其标举晚明又有现实考量,故而我们除了强调周作人的首倡之功外,所论不超出鼓吹小品文以及此一主张引发的现实文学论争等层面,或许在论者看来,周作人的意义就是提出了一项命题或者形成了一种语境,这显然失之于简单了,至少他造就的联动效应远不止于此。
一 主张的误读
有关五四与晚明关系的确立,是周作人的重大发现,自1920年代发端,以迄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演讲,日趋成熟,及至今日,“关于晚明文学思潮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的精神联系及其差异,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1周荷初:《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相关研究亦可谓丰富而深入,但仍有一定继续思考的空间。
周作人提出的“源流说”实则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对于公安、竟陵派的重新发现,这不仅是指从历史的遮蔽处发掘他们的存在,更是指着力彰显他们身上具有现代意义的革新、解放精神;二是对晚明与五四关联之揭示,从而证明现代新文学的孕育并非全然外来影响,实有本土历史渊源,两者结合,方构成完整逻辑。但我们的注意力基本被后者吸引,着力于五四与晚明之间异同的辨析及关联程度的确认,更进一步便是梳理、提炼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自主现代化脉络。至于周作人有关晚明的若干新发现,我们则少有细致考辨,或是当作理所当然的结论予以认可。但相关判断在周作人之前未有清晰表述,他本人也不曾系统阐发,即这可谓一个经由周作人首倡却未有明确论证的话题。时人对此并非完全没有“谨慎”态度,譬如陈子展即指出“我们要论公安竟陵的散文,还得起先对于有明一代的散文作一个鸟瞰,然后才可以窥见公安竟陵的真面目”2陈子展:《公安竟陵与小品文》,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125页。,不能轻易盲从。另钱鍾书在评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时,因其方法是“把本书全部地接受,而于其基本概念及事实上,加以商榷”,自然难以避免对公安、竟陵派的讨论,且评价并不算高,在他看来,“公安派的论据断无胡适先生那样的周密;而袁中郎许多矛盾的议论,周先生又不肯引出来”1中书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1932年第4期。。但除此以外,学人基本少有质疑,并予以了充分认可。假如有关“晚明”的界定不能成立,则相关逻辑无从展开,一应后续探讨也成了镜花水月。换言之,如何认识晚明文学的精神旨趣及时代特征,看似无关的闲笔,却系我们考察“晚明”与“五四”关系的要害所在。职是之故,相关研究的前提,甚至这一命题本身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回到源头处,学人曾对周作人为何提出“源流说”予以充分考察,至于将源头溯及公安、竟陵派的原因则少有关注,新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在场事件”,故而所论多集中在这一事件的现实意义,但于我们而言,相关结论后引入晚明文学研究领域,成为重要命题,就该有全景式的观照。我们更需要了解的不是标举公安、竟陵派意在何处,换言之,我们要追究这一命题如何造就,它的机制与理由为何,而非潜台词或影响。只有从源头处明确厘清相关问题,我们才能对其在专门研究领域的申发有所判断,故而从这被学人遗忘的话题处入手,或能让我们有一些新的思考。
有学人认为“周作人之所以极力推举公安派为言志派文学的代表和现代散文的源流, 很大原因正是公安派不顾一切的反叛精神, 无视道统和文统的勇气,完全将小品当作充分表达自己的方式, 都深契他的文学无用却反抗的观念”2蔡江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散文现代性理论与公安派小品文》,《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看起来周作人标举公安派是因为彼此理念上的相通,他自己也有明确澄清,“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确是我所佩服的,不过我的杜撰意见在未读三袁文集的时候已经有了”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序》,《苦雨斋序跋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但对这话不宜太过当真,毕竟这一“共鸣”不是必然地生成,而是刻意搜求的结果。周作人虽是大力推举公安、竟陵派的第一人,但在他们相遇之前,周作人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文学主张,尤其是在散文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周作人首倡小品“美文”时,并未直接受到晚明小品的影响,而是取法英法的随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文,虽得出五四文学与晚明文学同质同源的结论,但其主旨尚在为“言志派”的新散文的兴起寻找“古已有之”的证据,而不再对晚明文学重估本身。1周荷初:《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第242页。
就此来说,“晚明”凸显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需要,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晚明”与“五四”间的关联,这一事实理应成为我们相关认识的前提。
传统文学范围广泛,他最终将目光停留此处,除了所谓主张的接近外,似乎境遇的相似更为关键。周作人曾屡屡强调明季的情况与彼时有很多相似之处,落实到文学层面:“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且不谈那建夷,流寇,方镇,宦官以及饥荒等,只说八股和党社这两件事罢。”2周作人:《关于命运》,《苦茶随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于是他注意到了公安、竟陵派。虽说他宣称“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但更多强调的还是趋势或处境方面,依照他的说法,“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但关系也至此为止”4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苦茶随笔》,第68、62页。。虽说他也肯定了公安、竟陵派反对复古、对抗潮流的功绩,但给予他更大触动的恐怕还是昔人的不幸遭遇,就古时论:
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流,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我们只须看后来古文家对于这派如何的深恶痛绝,历明清两朝至于民国现在还是咒骂不止,可以知道他们加于正统派文学的打击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5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苦茶随笔》,第68、62页。
就现实看:
近来袁中郎又大为世诟病,有人以为还应读古文,中郎诚未足为文章典范,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6周作人:《厂甸之二》,《苦茶随笔》,第31~32页。
事业虽然正义,遭遇的却是误会、批判与否定,此处不免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强烈意味。对于周作人来说,他在意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新文学运动的整体兴衰,这构成了他所有思考的出发点,包括对公安、竟陵派产生浓厚兴趣并大力提倡。他对于昔人及其作品的喜好以及彼我主张的相通固然都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具有相通主张的一群人所遭受的种种境遇让他感同身受,他是“借古讽今”,既强调自身事业的正确和重要,也反映自身事业面临的遏制和倾轧,希望就此获得世人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包括同情),避免走上昔日公安、竟陵派一样的道路。
既是策略,周作人对晚明种种便不见得会真心认同;也正因是策略,便可根据需要时做调整。他明确指出“中郎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袖,然而他的著作不见得样样都好,篇篇都好”1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苦茶随笔》,第63、64页。,具体说来,就诗论,“中郎的诗,据我这诗的门外汉看来,只是有消极的价值”,至于散文“成绩要好得多,我想他的游记最有新意,传序次之……尺牍虽多妙语,但视苏黄终有间”2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苦茶随笔》,第63、64页。。一为完全否定,一为部分肯定,但这只是表象,背后的理念更值得玩味。此时的周作人具有强烈的“进步”思想,他“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3周作人:《人境庐诗草》,《秉烛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对古代诗歌不屑一顾自在情理之中。就散文而言,他的评价只是相对僵化、濒死的旧诗来说“好得多”,且为周作人欣赏的偏偏是昔人所厌弃的作品,个中是否有刻意对抗的意味且不论,至少他是以今律古,价值立场明显有偏向,更使这“肯定”大打折扣。他高举公安派的旗帜,但肯定的只是部分理念,却不认同其实践,我们所以为的他对于公安派的高度表彰着实存疑。
作为一个起点,周作人其实并没有塑造或确立一个高不可及的示范,某署名为“主”者昔日评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就指出,“周先生仅把公安派来代表文学的革命,这与胡适之作白话文学史把杜甫白居易都拉到白话文学作家里来一样的见解,因为他们所宗的是什么,就把古来的作者当作什么了”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附录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个策略性的口号,潜藏着诸多误解与曲解,但现今却被全盘接收。或要有所辩解,周作人的阐发确存不当,但并不能就此否认晚明文学的革新与解放特征,毕竟大量专门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们无意否认晚明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但想特别说明的是,个中过程实则从未摆脱周作人的影响,包括他的缺失。
随着“源流说”的流布,于影响扩大的同时也多有扭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盲目夸大“晚明”与“五四”之间的联系,过高估计“晚明”之于“五四”的实际影响,相关论调从彼此精神气质的相似一变而为“五四”对“晚明”的直接继承,历史的片段被捏合成连续的潮流,譬如魏紫铭昔日即称:
从十五世纪(明孝宗弘治晚年)到十六世纪(明孝宗天启初年),中国文坛,曾经有过一次极其伟大的演变,厥后,这种势力虽然一度消失,可是直到清季,还在不绝如缕的潜伏着呢。迨及民国初年,她更爆炸起来,造成了等量齐观的新文学运动,来完结她的未了的夙愿。1魏紫铭:《明清小品诗文研究》,《北强月刊》1935年第5期。
就此来说,今有人声称“随后的周作人,曾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中国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中, 从文学观的具体性质出发,认为新文学受晚明‘公安派’的文学思想影响颇多”2陈宝良:《晚明文化新论》,《江汉论坛》1990年第6期。也就不足为怪了。既是源头,必有后续,但这可以是精神信念的感召、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见得是直接的作用,周作人虽有将古今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比拟之举,但多属策略使然,他自始至终只强调古今的相似或暗合,不曾有“晚明”直接干预或介入“五四”的看法,上述观点既是对周作人观点的误读,更是对历史发展的曲解。
通过上述论断,我们或能明白何以专业领域的晚明研究始终不能脱离周作人模式。“晚明”既被视为“五四”的源头,便需具备种种“现代”因子,即我们往往是依据“五四”的需要来塑造“晚明”的面貌,且彼此间的关系越是直接、紧密,则“晚明”的革新、解放色彩越加浓厚,如此一来辩证审视甚而调整视角便难有可能。换言之,专业领域的晚明研究看似以丰硕的成果完善了周作人的命题,但他们基本是在周作人的框架内,遵照他的思路予以深化,有今日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周作人的巨大感召力和渗透性始终是我们一应研究的前提,这既是启发,也是约束,他以一种特殊但却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甚至规定了晚明文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在其命题的影响下,我们所作的不是辨析题,即考察晚明文学的特征,而是问答题,即论述晚明文学革新特征的表现。譬如说言及晚明,便瞩目公安、竟陵派;论及公安、竟陵派,则着力表彰革新、解放,少有其他视野或路径,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多种理论思潮及现实诉求相混合,形成一股更强大的合力,至今仍在发挥巨大影响。
二 命题的延伸
有遮蔽,自然就会有凸显与强调,随着“源流说”的传播,“晚明”与“五四”的关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探讨。1930年代形成了一股热潮,其后受制于政治、文化因素,直至1980年代再度成为重要话题,相关情况周荷初曾有简单梳理。1周荷初:《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第290~303页。实则这里也蕴含两重话题,一是对“晚明”与“五四”之间的源流关系存有疑问,故而予以细致辨析;二是认同周作人提出的命题,并将其具体落实到近三百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众多讨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有关晚明性质的确认或辨析(两种思路目标虽有不同,但前提是共通的,即具有现代因素之“晚明”的存在),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规定了我们的研究格局,这可谓周作人之于晚明文学研究的意外收获。
及至当代社会,认同周作人的命题,肯定“晚明”与“五四”之间存在一定(甚至紧密)关联是主流论调,但这一“共识”的形成不仅是对历史传统的简单继承,更是时代主潮的必然要求。简单来说,首先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不再一味趋新厌旧,反倒着力强调文学传统及遗产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传承,故而有学人指出:
一个新时代的文化, 不仅必然是对前一时代文化糟粕的扬弃与否定,同时必然是对前一时代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展。晚明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沉淀, 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代的新学与“五四”新文学, 成为它们的民族文化的渊源。2陈宝良:《晚明文化新论》,《江汉论坛》1990年第6期。
其次,则是在探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问题时,通过对曾有深远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的检讨与扬弃,日渐强调转型说,而起点正是晚明,就文学领域来说:
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文学自身所作出的历史选择……是随着明中叶后古代文化结构系统的调整而调整、变化而变化。1朱德发:《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第一部曲》,《齐鲁学刊》1991年第3期。
周作人以“言志”与“载道”的交替演进来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显然失之于简单、粗疏,于是不断有人试图延续他的思考方式予以丰富,当然主体是落在了“晚明—五四”这一阶段,这本就是周作人的论述重心,也是他们认为存在密切联系的一段历史。首先要提及的是任访秋,因为他系周氏亲传弟子,他原本认为“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来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的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2任访秋:《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后却转变观念,步武周作人,试图探讨中国文学内在的发展动力,譬如其《中国小品文发展史》一书,可谓“源流说”的一个具体实践或印证,所谓“有明一代诗歌,竟无可述,在散文上居然能有着这么多的佳作,这追根溯源,你能说这不是当时的新文学运动之赐吗?”3任访秋:《任访秋文集·未刊著作三种》(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7、8页。至于具体的论述过程,无论是强调“越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它们就越发荣,但一到思想统一的时候,它就跟着枯萎了”4任访秋:《任访秋文集·未刊著作三种》(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7、8页。,还是循此认识,将小品文的盛衰起伏与时代的变迁联系起来,分为五个阶段5任访秋:《任访秋文集·未刊著作三种》(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7、8页。,都与周作人的论调多有呼应。尤需提及的是其效仿周作人撰成的《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把晚明文化革新运动与五四文化革命运动,这三百年间的中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索”,并自认比周作人讲得“要详细、要具体”。6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但客观来说,他虽详细梳理了晚明至晚清、五四时期思想与文学的嬗变轨迹,并试图勾连前后发展线索,但所做工作仍不免简单、粗浅。近三百年的文学历程,由于强大的文学传统、共性的精神追求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存在不少看似趋同的观念主张和共性的创作实践,故而罗列事实、描述现象本非难事,关键在于依照何种理念、基于何种标准,从多元、繁复的文学史中筛选若干现象,并串联成线,即要有整体观照和理论统领。任访秋未必没有这种意识,他也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凸显的不过是反封建云云之类模式化的说辞,我们看到的仍只是一个个的点,而非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线。
关爱和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依他之见,晚明和清初(代)“由于学风、学术指向与文化性格的不同, 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各自孕育的文学思潮自然明显有异,因此它们虽属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展现出不同形式,却有着一致的走向,故而都具备“一种文化类型学的意义”,并“形成了中国前近代期的两种思想原型,它给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1关爱和:《历史潮汐与文学回声——晚明至五四文学变动掠影》,《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这一表述至少有两层推进,第一,是力图准确、深入地把握各时段的思想、文化特征,避免简单、浮泛描述;第二,是他意识到了从晚明到“五四”的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歧异、偏差,并从分歧中抽绎出了统一的发展脉络,保证了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实现了论述的全面与完善。
陈宝良持有与关爱和类似的看法,认为“新文学的文化渊源至少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从李贽、公安派开启的‘言志派’文学, 一是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的‘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2陈宝良:《晚明文化新论》,《江汉论坛》1990年第6期。。表述虽有差别,大体意思趋同,他不惟揭示这一事实或现象,更试图说明此种延续或影响的背后机制,突出强调了这种发展轨迹的必然性,此即前文所引有关文化演进规律之概括。与此同调者甚夥,在此思维方式的启示下,有学者开始着意于重新描述近现代文学史,譬如《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依照编者意见:
这里所说的“400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四个世纪,而是泛指自16世纪晚期(大致相当于明万历年间)至20世纪末叶这个时段里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近400年文学思潮的演进,尽管头绪纷繁,事象庞杂,总体上却构成了统一的流程,其实质便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3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页。
此类探讨系对周作人命题的发展和丰富,但未必符合他本人的期待。“周作人《源流》褒‘言志’、抑‘载道’表面上看是在传达自己的文学观,实质则是通过一褒一抑达到捍卫新文学传统的目的”1王瑜:《谁在写史?——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几篇文章看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解的“误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6期。,故而作为一种策略性的表述,重要的是“言外之意”,而非字面内容。周作人有明确的现实诉求,今人亦然,对“五四与晚明的关联性”这一命题采取不同的思考角度,进而获得不同的理解亦在情理之中。但基于现实关怀的不同,随着这一命题的展开,偏离周作人昔日设定的轨道,改变“源流说”基本面貌的情况也会屡屡发生。“源流说”在流布过程中逐渐由“结论”转变为“方法”,其意义和价值也随之丰富。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学者来说,激烈的革新巨变以及随之引发的与传统的断裂亟须反思和检讨,重建二者的联系成了一时急务,故而对于他们来说,周作人提出的命题不仅是可贵的思路,更是有待践行的任务。或许是现实诉求过于急切,他们的“行动”积极而高效,却少了些冷静而必要的审视。时代命题是重新审视传统与当下的关系,即不可像过去那般肆意鄙弃传统并盲目割断古今联系,这一切实有赖于对传统和当下都有全面体认,进而总结、提炼历史经验与规律,但具体操作往往矫枉过正,在未经全面、客观审视的情况下,汲汲于重建那久被忽视的联系,故而依赖的材料是碎片化的,采用的思考方式是主观性的,一应结论并不那么可靠。前已提及,周作人虽标举公安派,却未曾对其价值有充分审视,这一“缺漏”在新时期仍然未能补足,宣扬的依旧是一空洞口号,持续不断的填补、充实也始终停留在浅表,我们并未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只是在将周作人的逻辑予以完善。从晚明至五四近三百年间的文学进程是否展示为统一的发展脉络?假使有统一路径又作何具体表现?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我们的思考显然远远不够。当缺乏根基与前提,却又要确认联系时,所得种种只可能是简单比附与浪漫想象。
有关晚明与五四的关系虽有众多探讨,但展示的多是趋势和倾向,实则其间充满复杂和曲折,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对所谓的“继承与发展”作太过草率、简单的理解,学人有关“源流说”的质疑或者说辩证也多半由此发端。譬如冯至强调,“新文学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进步文学的传统”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理应结合考察,不能偏废,但结合具体的文学事实来说,这一平面化的理论总结有待细化,即“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新文学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不是相反”。1冯至:《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换言之,就影响论,传统与西学皆发挥了作用,但二者的介入方式、程度及效果存在明显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其后有学者对此表述得更为明确,譬如朱德发指出“晚明人文主义曙光没有照亮东方帝国的现代化征程;并表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系统只靠本身的调整功能与转换机制难以完成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历史重任”2朱德发:《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观点自然是鲜明的,但何以如此立论到底缺了些翔实的说明,这便有赖就晚明与五四的差异做具体辨析,有学者在肯定五四新文学受到传统滋养的基础上,更是着力考察了彼此的本质差别。3详参张福贵、刘中树《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历史层面看,这些意见都有一定道理,并能帮助我们祛除某些误会,特别是有关晚明性质的认定。自周作人推举公安、竟陵派以来,在一股浪漫主义精神的笼罩下,“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作了同源同质的理解”4张福贵、刘中树:《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我们想当然地给晚明贴上了思想启蒙、人性解放等诸多标签,却少有精细论证,遑论慎重反思。此类探讨虽非直接针对晚明而发,却细致辨析了表面相似主张背后的巨大分歧,等于从外部打开了一重缺口。但就效果而言,我们在强化了五四“现代”性质的同时,似对晚明的“传统”色彩选择性忽略,依旧奉行一贯论调,本为一体两面的结论,却采取了区别性对待,这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都讲不通的。可能的原因有二:一则我们有关晚明的“定论”过于强大,难以轻易更张;二则学人虽揭示了晚明与五四的差别,但多是就社会性质、文化思潮等宏观层面立论,执着于古和今的时代差别,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譬如有学人就强调,时代的总体差别确然存在,但旧时代的主潮下另有暗涛,展露出新时代的曙光;晚明士人的局限性也无可置疑,但忽略细节,就总体趋势而言,“(晚明与清初)两者都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热情, 其理论命题都蕴含着丰富的启蒙和反封建精神”1关爱和:《历史潮汐与文学回声——晚明至五四文学变动掠影》,《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换言之,这到底是根本性的本质差别还是细节性的程度不同,未能清楚辨析。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我们在考察相关问题时,往往专注于情/欲、公/私等范畴,要么脱离时代语境,就其一般意涵作过度发挥,故而强调古今之同;要么强调时代差别,认定古今难以具备趋同理路,说到底这种宏大叙事也是脱离实际的一种表现。切实可行的做法应是回归历史语境,细致梳理并辨析相关范畴背后的时代语境、现实关切及核心旨趣,譬如沟口雄三有关明清之际公私问题的分析就是一个极好的示范。就此来说,上述论断虽动摇了晚明的根基,但尚缺乏细致的阐发。
三 格局的塑造
虽因周作人的标举,晚明研究方才成为重要命题,但大家的目光多半停留在命题周边或衍生线索,对他与晚明文学研究间的直接关联少有关注。概而论之,当有四端:其一,促成了关注公安、竟陵派,阅读公安、竟陵派的风潮,改变了他们少有人知、多遭恶谥的局面,这一点时人多有提及,此不赘述。
其二,周作人本人虽在晚明文学研究方面并无开拓,但他指导了两名研究生从事袁宏道研究,相关成果成为晚明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第一位即是我们熟知的、上文也已提及的任维焜(访秋),他早在周作人的观点“在社会上尚未引起关注”2黄仁生:《论公安派在现代文坛的多重回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的1931年就涉足公安派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中郎师友考》等论文,1935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更是在周作人的直接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袁中郎研究》。该论文于1936年暑期答辩通过,直至1983年,经其修改后方正式出版。公安派研究可谓任氏的终身事业,198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但旨趣仍在于“由近代上溯至晚明,探求‘五四’文化革命的渊源”,所著《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新文学渊源》二书便是明证。
另一位是魏际昌(字紫铭),有关他与周作人的渊源少有论及。魏氏早年先考入吉林大学教育系文学专业,后因抗战形势影响,吉林大学被迫解散,魏氏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在此先后完成本科及硕士学业。其硕士学位论文系在胡适指导下完成,题为《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本科毕业论文则是《袁中郎评传》,得到了胡适与周作人的共同指导。据其自述:
我在本科第四学年开始之前(1934年秋)说明志趣,请求胡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胡先生说:“……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周启明(作人)先生比我多,周先生开过‘近代散文’的课,可以去找找他,让我们两人共同来帮助你吧!”
后周作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很谦虚,只给我开了有关的参考书……并约略地指出诸书重要篇目,有助于‘评传’撰写的种种”。九个多月后,他将写成的初稿“拿给胡先生看。胡先生看得很仔细”1魏际昌:《胡适之先生逸事一束》,《河北文史资料》1991年第2辑。,并没有提及请周作人审查的情况,照此看来周作人起到的作用似乎只是提供参考书目及必要提点。但就魏氏发表的相关论文看,诸如“朱明诗文,载道者多,前后七子,大都此类,其能清新流丽超逸爽朗者,公安竟陵两派而已”之论,特别是“载道”之说,显系承袭周作人而来,其他如“与夫近世之新文学运动,又何莫非先生直接间接之流风乎”等,亦可见出周作人的影响。
其三,所谓关注、阅读,或是兴趣使然,但兴趣往往成为研究的动力,故而亦是在周作人的影响下,以公安、竟陵派为主的晚明文学研究获得了极大推进。周作人身边的朋友与学生在阅读公安、竟陵派诸人文集的过程中都有着或零星或系统的发现。前者如郁达夫通过细致阅读即意识到:“然而矫枉过正,中郎时时也不免有过火之处,如他的西湖纪游里关于吴山的一条记事……这岂不是太如明史列传作者之所说:‘以风雅自命’了么?”2郁达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人间世》1934年第7期。类似有关中郎性格的质疑其时尚有不少,虽多是零散印象,未能形成系统判断,且其中尚有意气成分3譬如曹聚仁对袁宏道多有讥讽,称其“以陶渊明潘岳自比”,却无非沽名钓誉,“出卖高雅”,又批评 “袁中郎的出游,无有不高声叫卖,直令人头痛。纪游文非无佳构,那股酸味就够使文章减色了……袁中郎本非遁世之士,谈禅说佛妄作解人,可笑”。(《何必袁中郎——书刘大杰标点本袁中郎全集后》,《太白》1934年第1卷第4期)一应批评虽有合理处,但难免有因立场不同的偏颇之词。,但多少意识到其人并非如周作人、林语堂描述的那般单纯。就现有研究来审视,不难发现他们的某些感觉颇有见地。后者如刘大杰撰有《袁中郎的诗文观》一文,将其文学主张总结为反对摸拟、不拘格套、重性灵、重内容四条1刘大杰:《袁中郎的诗文观》,《人间世》1934年第13期。,不少观点已然成为今日学界的共识与常识。
随着《中国新文学源流》的出版以及三袁和钟、谭文集的翻印发行,与公安、竟陵派相关的研究日渐兴盛,魏紫铭《明代公安文坛主将袁中郎先生诗文论辑》(《北强月刊》1934年第1卷第6期)、《明清小品诗文研究》(《北强月刊》1935年第2卷第5期)、张汝钊《袁中郎的佛学思想》(《人间世》1935年第20期)、府丙麟《公安竟陵派之文学》(《约翰声》1935年第46卷)、李万璋《谈谈公安派的小品文》[《期刊》(天津)1935 年第5期]、吴奔星《袁中郎之文章及文学批评》(《师大月刊》1936年第30期)等论文先后问世。相关论文中时时提及知堂及其论断,在在见出他们所受周作人开创事业的启发,譬如吴奔星言:
故林语堂一流人之提倡晚明小品,俾免汩没,固袁中郎之功人,而其使袁中郎受辱,又是罪人矣!我之研究袁中郎,虽不敢抱“功人”之妄想,但也不愿趋时顺俗,转入下流的幽默之漩涡。2吴奔星:《袁中郎之文章及文学批评》,《师大月刊》1936年第30期。
此系纠偏者。又如府丙麟言:
公安竟陵二派文学之价值,不在其著作,而在其力倡文学革命之精神。周作人先生……其语殊当……三袁之反抗正统派复古运动,其识见,其魄力,皆是为今日新文学运动之楷式矣。3府丙麟:《公安竟陵派之文学》,《约翰声》1935年第46卷。
此系发扬者。推而广之,论及明代文学,也多不超出周作人设定的框架,譬如郭麟阁称“魏晋文士,襟怀高迈,洒脱不羁,故其出来小品,抒情诗歌,率多言志之作,趣味盎然,魏晋以降,正统派又复得势。至明代公安竟陵出,言志派又大放异彩矣”,又称“自来言明代文学者,多囿于传统,不曰归、宋,便曰何、李,一若去此数子,明代无文学也。岂不知明代文学之所以重要,不在有前后七子,而在有公安竟陵之小文,与小说传奇也”。1郭麟阁:《论明代文学》,《期待》1947年第1卷第2期。
经由周作人的宣传、表彰,改变了明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并规定了相关判断。由于我们的关注点长期停留在时代论争方面,于此方面的成绩多有忽略,学人虽曾梳理相关文献,但仅是罗列题名,未有系统审查,以致其中的远见卓识未得彰显。综合来看,相关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接续周作人的话题,对三袁及钟、谭等人的生平交游,公安、竟陵派的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予以细致探讨,关乎此已有相对充分的学术史梳理,此不赘述。但要说明的是,在此过程中,周作人开创的命题也得到了丰富与推进,譬如朱维之强调在公安、竟陵派之前,“实际上揭出叛旗更早更鲜明的,倒是李卓吾”,且他对李卓吾的影响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即除了诗文外,还特别表现在小说戏曲批评方面,二者经由种种传承,都在五四后继续发挥影响。2朱维之:《李卓吾与新文学》,《福建文化》1935年第3卷第18期。二是批评周作人的某些曲解(部分是他的观点流布后产生的误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和完善晚明文学的研究路径。譬如曾广烈强调“袁中郎的诗确实是改革的拜古派的诗,他是向拜古派的示威;(因为他这种诗完全是随意写的自我的诗)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说他的诗是如何的好”,具体来说,“既没有唐人的热情,又没有宋人的冷味,更没有元人的细腻柔媚,只是一股粗浮矜躁之气”,即使是为他所赞许的小品文和尺牍,也不免“名士气味太多,有时使人难堪”。3曾广烈:《谈袁中郎》,《文学生活》1936年第6期。观点或许可商,趣味不免古典,但这种客观的态度与细致的辨析难能可贵。再如周木斋,他也和阿英一样,认为在周作人的影响下,中郎虽获得了充分关注,却也在此过程中遮蔽了自己的本来面貌。略有不同的是,他结合明代文学史,就相关细节予以了细致考察。譬如他指出,“在嘉靖时,对于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已经有人反抗了,如起初也学秦汉的王慎中……和他齐名的唐荆川,也响应他……又有归有光出来抗争”,既然他们与袁中郎有共通的文学追求,则“中郎的反抗复古,总受些影响的,他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一文中,就推重归唐”1周木斋:《袁中郎集》,《文学》1935年第4卷第4期。,而在周作人的论述框架下,归、唐这些人无疑都属于对立面的“载道”派。除此以外,他还特别说明中郎的思想系儒释道三家综合所致,那么当日过于浪漫主义的言说便不免简单化。特别要提及的,也是成就最高的当属郭绍虞,先后撰成《性灵说》《竟陵诗论》等文,探微抉隐,于明代诗学研究功莫大焉。他还特别指出,“近人每以公安与竟陵并称,而属之于小品文一类。实则公安与竟陵相同者,仅在反抗七子的一点。除此点外,公安、竟陵的作风正不相同。不仅作风不同,即其理论亦颇不一致”2郭绍虞:《竟陵诗论》,《学林》1941年第5期。,于时人的盲从论调实有廓清之效。三是随着公安、竟陵派或小品文研究的深入,带来了整个明代文学研究的推进,形成了不少高明论断。譬如吴奔星认为“有明一代,不特不能说是中国文学的衰微时期,而且在文学批评史上,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3吴奔星:《袁中郎之文章及文学批评》,《师大月刊》1936年第30期。,鲜明意识到了明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可谓别具只眼。再如魏紫铭,则对明代文学演进大势有精要概述:
由于七子的返古模拟,而引起唐(伯虎)徐(文长)的首竖叛旗,不过,两人只有创作,未见主张,迨至公安(三袁),方才有了极明确的口号——知文学变迁之迹,倡诗文清新之旨——然后其弊也肤浅,竟陵(钟谭)代兴,正以笃厚,但是幽峭冷僻,识者病之,于是归(震川)唐(荆川)一出,而公安竟陵两派文坛,只剩残兵偏将了。4魏紫铭:《明清小品诗文研究》,《北强月刊》1935年第2卷第5期。
所论自有偏颇、疏略处,但就其大致言,正与今日格局相当,可谓先导。
不惟如此,类似影响还溢出了文学研究领域,嵇文甫就高度评价了周作人的发现,称: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好像明代文人就没有一点性灵天才,就不会创造一点新东西。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彰公安竟陵诸子,于是我们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1嵇文甫:《左派王学·序》,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2页。
与此相呼应,他认为:
其实何止文学如此。明中叶以后,整个思想界走上一个新阶段,自由解放的色彩从各方面表现出来……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2嵇文甫:《左派王学·序》,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2页。
这一观点随之又回流到文学研究领域,郭绍虞即称赞他“这话极是”,并沿袭他的思路予以申发,“左派王学之中影响中郎思想最大者,又当推李卓吾。……中郎能不受卓吾的影响吗?能不受卓吾大刀阔斧直往直来的影响吗?王李之学,又如何牢笼得住”3郭绍虞:《性灵说》,《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
其四,论及晚明文学研究模式的确立,我们多谈及1930年代左翼文人的影响,譬如嵇文甫和容肇祖4通过《左派王学》(嵇文甫,开明书店1934年版)、《晚明思想史论》(嵇文甫,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李卓吾评传》(容肇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明代思想史》(容肇祖,开明书店1941年版)四部著作,他们基本规定了后世研究的核心理路,具体包括“王学—泰州—公安、竟陵”的叙述逻辑,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早期启蒙、自然人性论等考察视角。,实则周作人就已提出了不少论断,并持续影响了我们的后续研究。其要有三,一是以李贽为源头,认为“明季的新文学发动于李卓吾”,这一观点或受容肇祖影响,因为他“在《李卓吾评传》中也曾说及”5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如此一来,周作人与嵇文甫可谓互相影响、文学与思想彼此促进。二是与第一点相关,强调思想革命对文学革命的重要意义,具体到晚明,思想资源首先是王学,“明朝因王阳明李卓吾的影响,文学思想上又来了一次解放的风潮”6周作人:《北京的风俗诗》,《知堂乙酉文编》,第56页。,此外还应注意禅宗的影响,“明代中间王学与禅宗得势之后,思想解放影响及于文艺”7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选序》,《苦雨斋序跋文》,第95页。。三是总结了古今一致的现代精神,即“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这也就是现代精神,现代新文学如无此精神也是不能生长的”,到了现代更是“接受科学知识做帮助”1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第65页。,后世所论不超出此,只不过对其内涵或指导思想的看法不一而已。
综上,不难发现周作人对于晚明文学范式的建构产生了全面影响,不论是基本命题的提炼、核心思路的确定,还是相关话题的展开,始终都能发现他的身影。这样一个现象的昭示,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周作人的认识,这既是指他在晚明方面的专门判断,还应包括对他本人思想形成及发展的理解,与此同时,更能指引我们的晚明文学研究格局。依照前贤的看法,“晚明”是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代,但这一看法本身便是伴随现代化进程不断得以明晰和丰富的,职是之故,有关晚明的理解亟须打破现今的学科畛域,真正勾连起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两大领域。所谓“真正”即是指这不仅仅是部分概念的借用或者话题的套用,类似的所谓成功已然多矣!我们需要的是沉潜历史语境,深入剖析相关概念、命题的产生背景、基本内涵、演进历程,获得全局性和整体性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