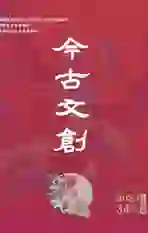先秦儒家与法家政治思想的比较
2023-09-19杜伟升
【摘要】先秦儒家提倡“德治仁政”,重视君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引导作用,希望君主“正己修身”,以自身高尚的品格来化育百姓,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儒家虽然主张“德治仁政”,但并不反对法律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只不过认为法治发挥作用的前提必须在礼制基础之上;法家反对儒家以“仁义”治国,主张以“法治”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要“因道全法”,法律“必因人情”,使百姓从中获利,同时提倡用“轻罪重刑”的方法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法家也重视君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明君能够“置法自治,立仪自正”,充分发挥人臣之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
【关键词】德治仁政;法;无为;君主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4-0070-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4.023
儒家学说是先秦百家之显学,法家思想在战国末期成为秦国指导思想,并帮助秦国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二者都在先秦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二家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本文将从儒、法二派所处的历史背景、所提倡的主要思想,以及所期望构建的理想社会等角度进行阐述,以求加深对儒、法二家社会政治学说的了解。
一、战国时期所处的历史背景
西周末年,原有的经济制度、政治模式开始瓦解。从经济方面来说,伴随着铁制农具与牛耕田的大面积推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日趋激烈,原有的奴隶主贵族直接占有土地的经济模式已不再适用,新兴的地主阶级依靠奴隶与平民战胜了奴隶主贵族,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君主集权制的转变。从政治方面来说,周代奉行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随着周天子的地位逐步衰弱,也难以起到约束各路诸侯,巩固统治的作用。鉴于此,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采取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如减免赋税、奖赏军功、重视农耕等。在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纷纷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宣传自己的思想,希望自己的救世思想得到重视。在诸多学说中,最主要的思想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孔、孟、荀为代表,他们主张“克己复礼”、称颂上古时期尧、舜、禹等圣王、宣扬“仁政”,认为王道是最理想的统治状态。另一派是以商鞅、韩非为代表,强调法治,主张“赏有功,罚有罪”,以“霸道”替代“王道”。
二、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
春秋末期,周天子的地位不断削弱,各国之间征伐不断,“子杀父,臣弑君”的事时有发生,见此情景,孔子发出感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孔子认为社会发生混乱的根源在于“礼坏乐崩”,所以当孔子得知鲁国贵族季氏在自家庭院中用八佾奏乐舞蹈时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天子和诸侯各自有自己应该遵循的礼,如果二者之间发生僭越,便会发生动乱。因此,孔子终身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他明确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孔子并非是对周礼一成不变地继承,而是对其有所损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将“仁”的概念引入“礼”,从而将“仁”作为行“礼”的内在依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认为一个人能不能实现仁完全取决于自身“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发挥,主张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来统治天下。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以其人性论思想为基础的。孟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先验的道德本心,并且这种道德本心只在内向求取,不在于外部赋予,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孟子将以上“四心”分别认为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认为只要时时刻刻“存心”“养心”就自然可以将人心中固有的善性发扬光大,“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并且只要自身肯努力就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因此孟子认为君主只要将自身的“不忍人之心”推及政治,自然可以实现天下大治,達到儒家历来推崇的王道政治,“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他也非常看重百姓在统治中的地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他强调在统治百姓的过程中要注重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取民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
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儒家传统的礼义思想之上,引进了“法治”概念。“礼”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礼”既对个人的道德修养起到规范作用,“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另一方面,“礼”又在国家政治治理上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国之命在礼”(《荀子·强国》)。荀子非常重视人所固有的“群”的特性,在他看来,人的力量、速度不及牛马,但却可以役使牛马为自己所用,关键在于人能组成公共性的群体。“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荀子的社会公共性思想基于他的“性恶”理论,在荀子看来,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然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如果不在公共群体中进行等级的划分,那么便会产生混乱。因此,社会群体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了自身与其他人的差异性。“人何以能群?曰:分。”(《荀子·王制》)而这种等级的划分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道义“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简而言之,每个人通过道德素养认识到了自身与他人的差异,因此能够各司其职,凝聚力量来应对外来的困难,从而达到“胜物”的目的。“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不可能自发地向善,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达到化性起伪的效果。“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荀子认为学习的内容起于“六经”,终于“礼”。“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礼的作用是根据不同人的能力,对其进行划分,使人们各司其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正如杨国荣教授所言,荀子的礼不仅与一定的政治、伦理体制相关联,而且表现为一套规范系统,后者同时构成了社会秩序所以可能的担保。[1]但礼毕竟依靠人的内在自觉性,在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人无视礼的要求,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肆意妄为,破坏社会公共秩序,荀子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援法入礼”,用法来矫正违背“礼”的行为。因此,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礼与法二者是并用的,“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如同史华兹所认为,只有设计一套礼和法的体系,才能保证人们安全,并满足他们合理的欲望。[2]同时,荀子也非常看重人在社会公共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因为无论是“礼”还是“法”都需要人去加以发挥、引导,所以荀子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虽然礼、法二者共同维持社会秩序,但荀子更重视礼,认为礼是为政各项措施的根据。“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并且荀子主张“刑有差等”,认为法只对规范平民有效果,对于君子仍需要用礼来管理。“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三、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
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结合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构建了一套以法为基础的政治理论。韩非子在《有度》篇中首次提出了“以法治国”,“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在韩非子看来,人性本就是自私自利,毫无任何仁义道德可言,即使亲如父子,也不过是为了自己做打算。“父母之于子也, 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韩非子·六反》)正是因为人人都有这种“自为心”,所以君主才能运用赏罚二柄推行法治。“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相比于荀子注重“人治”,韩非则是对其丧失信心,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在他看来,实行“人治”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丧失法律的公平性,不利于国家的统治,所以,他说“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则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另外,韩非子认为法令要由官府编撰,同时要让百姓们知道遵守法律会得到奖赏,触犯法律会受到惩罚。“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
早在前期法家时,商鞅就已提出“轻罪重刑”“刑无差等”等思想,他认为无论是平民、还是卿相如果不遵守法令都应接受法律的制裁。“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同时采取“轻罪重刑”的方式就不会有人违背法令,“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君书·赏刑》)韩非充分吸收商鞅“轻罪重刑”“刑无差等”的思想,认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认为重刑可以达到“以刑止刑”的目的,“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韩非子·六反》)基于此,韩非反对儒家所主张的以“仁义”治国的理念,认为以“仁义”治国会导致君主地位低下,使国家产生混乱,只有抛弃仁义,实行“法治”才能使民治国安。“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韩非子·说疑》)韩非认为只讲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术”,他批评商鞅只言“法”而不讲“术”,申不害只重“术”而不谈“法”都只是各讲一边,韩非主张“法术并用”,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认为术是君主统御群臣的工具,既要让群臣各尽其能,又要让名实相符,“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法与术的实施要依靠势,所以韩非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在韩非看来,势是君主的“爪牙”,是君主所独有的,必须由自己牢牢掌握。“此人主之所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韩非子·主道》)
在“难势”篇中,韩非探讨了“势”与“材”的重要性,韩非区分了“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关于“自然之势”,韩非解释说“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不能治者,則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在这里,韩非将生来就处于君主地位的情况称为“自然之势”,尧舜处于势位时,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而桀纣处于势位时,虽有十个尧舜也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但像尧舜一般的君主“千世而一出”,而世上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是中人之资,因此,如果期望等待如尧舜一般的君主治理天下的话,就会导致“千世乱而一治”的结果。韩非所谈论的“势”是针对中等资质的君主而言,他说“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弭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所以,在“势”与“材”之间,韩非更加看中“势”,他认为不应该期望那种等待贤才的出现,然后才使社会得到治理的情况,“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应该主动创造一种即使没有贤才的出现,依旧能使社会得到治理的“势”,君主只需占据一种合乎治理之势,就可以“君执柄以处势,则令行禁止”,从而治理好天下。
总的来说,在韩非的思想体系中,“法”“术”“势”三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法”起到规范社会全体成员的作用,“法”的制定与实施则需要百官的参与,因此君主也需要有驾驭百官的权术,而“法”与“术”的推行与运用都要建立在君主的威势之上。
四、从“无为”的角度看先秦儒家与法家政治思想的比较
儒家和法家都主张“无为”的思想,但究其根本则大为不同。早在春秋末期,孔子在赞美舜帝时便提出了“无为”的思想,“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舜便是“无为”君主的典型代表。关于儒家的“无为”,宋代朱熹解释说“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为也。”在朱熹看来“无为”就是君主以德治为其治国主要手段,从而达到化育万民的作用,“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政,亦不是块然全无所作为,但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盖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岂无所作为。但人所以归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为,而天下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也。”可见,儒家的“无为”强调君主以其自身为表率先正己后正人,“子帅以正,熟敢不正。”(《论语·颜渊》)诚如张星久所言“无为就是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治仁政为根本的治国之道,限制刑罚政令的作用范围。就是说,在‘德’的方面是‘有为’,在不德、不仁方面才是‘无为’”。[3]
总的来说,儒家虽然将“德治仁政”看作其为政根本,但儒家的最终目的是将其道德理想付诸社会实践,在个人道德品性完备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干政的抱负,因此也不能忽略刑法的作用,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但刑法的公正性必须以礼乐为其前提“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同样,孟子虽然主张“仁政”治国,但他并没有忽视法治,相反也非常强调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他在《离娄》篇中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因此,孟子不是不用法,而是强调要尊先王之法,不能滥杀无辜,要以争取民心为主。在《尚书·大禹谟》中更有“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的类似于商鞅“以刑去刑”的表述。因此,儒家并不反对法治,而是主张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有关法家的“无为”思想,早在《管子》一书中就已提及,《管子》把“无为”看成君主统治臣下的一种方法,认为君主心中不应存有好恶之心,应以平常之心对待人和物,这样,才可以使百官各安其位,发挥自己最大的效用,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管子·心术上》)在《商君书》中虽未提及“无为”二字,但在其中已有“无为”思想的端倪,如在《壹言》篇提到“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即君主只要“审权以操柄”“公明法令”,那么朝堂上就不会有奸邪之人,官员就不会作恶。到了慎子时,“无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说“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在他看来,“无为”就是君主自身不任劳,善尽人臣之力以成事。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无为”在韩非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大的地位。韩非引进了道家的“道”,并将其改造,来为“法”作依据,抬高“法”在政治治理中的作用。道家的“道”具有形而上的特性,恍惚悠远,捉摸不定,不可把握。“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韩非取消了“道”的形而上的特性,将“理”引入“道”,他说“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理是每一个事物所具有的具体规律,而道是自然界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一切具体事物,“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因此,“道”随时变化,存在于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之中,“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韩非子·解老》)所以,韩非认为道是可以“执其见功处以见其形”。在此基础上,韩非提出“因道全法”,明确反对君主通过自己的好恶来统治国家,主张“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在韩非那里,“无为”是君主统御臣下的一种手段,君主排除自己的主观意见,以“法”为施政标准来进行统治,这样,臣下就会各司其职,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韩非子·用人》)诚如,陈奇猷所讲“以法为治,用法治使人无为”。[4]综上所述,儒家的“无为”是以“德治仁政”为其施政根本,强调以君主的德性来化育百姓,虽然儒家也强调法治,但是以“礼乐”为其前提的。法家主张以客观公正的“法”作为君主“无为”政治的前提,反对儒家包含强烈个人意向的君主之德,提出“因道全法”,使臣下各尽其职,反对统治者根据个人喜好来治理国家,主张“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
五、先秦儒家与法家所期望构建的理想社会
(一)儒家期待构建的理想社会
在儒家眼中,尧舜禹时期便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社会秩序崩溃,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发动战争,导致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孔子以“仁”释“礼”,希望以“仁”的理念重构上古时期的理想社会。关于儒家理想社会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1.君子在为政中的重要性。“君子”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郑玄注“君子,止谓在官长者。”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般指社会中地位较高的人,孔子以后,“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之人。孔子认为君子应该以“义”为立身之本、行事要合乎“礼”的规范、言语要谦逊、为人要诚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孔子强调“君子”对百姓有示范引领的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他认为君主在政治治理中应该先端正自身行为,这样不必发布政令,百姓也会跟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在《离娄》篇中也强调君主自身的品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2.德治仁政为主要治国手段。孔子认为如果用政令刑法来统治百姓,虽可起到避免犯罪的效果,但并不会为自身的行为感到可耻,只有以德治来感化百姓,百姓才会真正认识到自身的过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有类似的言论,如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认为君主如果实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3.保证人民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孔子重视“物质”基础在为政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使民众富起来之后,然后才能更好地教育他们,“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之后,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思想,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恤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认为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为物质基础,再加上仁政措施贯彻,就能使“老者衣锦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总而言之,儒家希望在百姓生活富裕的基础之上,实行“仁政”,以君主高尚的品格为百姓表率,在无形中起到使百姓向善的效果。
(二)法家期待构建的理想社会
战国时期,社会处在大变革的阶段,伴随着宗法等级制度的瓦解,自西周以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治基础无法继续维持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势必会产生与社会形势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同样,作为指导社会制度的相应的理论也会伴随而生,法家思想便由此产生。正如蔡景仙所说:“一种理论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有外在的社会条件。在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发展的时代,对奴隶主贵族在权利上的削弱,实行功过赏罚严明的法治,实在是对地主阶级的保护和支持,所以从历史背景上来说,法家理论产生自有原因。”[5]关于法家理想社会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奉法利民。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有“奉法利民”的思想,他认为法律的功能是建立功业,震慑暴行,解决纷争的,人们只有服从法律才能从中获利。“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在《说文解字》中“法”作“灋”,对其解释是“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即法即是刑,法如水一般平正,廌,是抵触不正者,使不正者离开。因此,“法”即公正的代表。韩非在《五蠹》篇指出仓颉作书以自环者为私,背私为公,公私不两立,进而,他主张“去私心,行公义”“奉公法,废私术”,认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韩非的“立公”旨在维护并使民众获利,他说“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正如章太炎所论“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以法家之觳,终使民膏。”[6]
2.提倡“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变化史观。法家反对复古的思想,坚持发展的历史观,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商鞅认为在伏羲、神农时期“教而不诛”,在“黄帝、尧、舜”时期“诛而不怒”,在“文、武”时期,则“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他认为“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因此,他下结论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在战国末期,韩非对商鞅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各个时代都有其所独有的社会问题,因此,解决方法必定也不会相同。韩非将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认为上古时期,人民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因此,有巢氏构木为巢而王天下,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王天下;中古时期,人民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天下大水”,因此,“鲧、禹决渎”治水;近古时期,人民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是“桀、纣暴”,因此“汤、武征伐”。所以,韩非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3.强调君主的作用。法家重视君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管子·法法篇》:“凡民之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而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认为君主对于百姓起到表率作用,君主应“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这样百姓就会心悦诚服。韩非也强调君主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他在《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韩非那里,明君的形象通常是体道者“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君主既然是体道者,那么君主就是立法的权威,由此,韩非为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主张将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利集中在君主手中,构建了一套“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治理手段。
总而言之,法家希望君主可以“置法自治,立仪自正”,以自身行为为表率引领民众,并根据当世之事,制定当世之法,以公正之法治理百姓,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并使百姓从中获利。
六、余论
春秋末年,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中,先秦儒家倡导的以“德治仁政”来治理天下的方式在这种环境下不被统治者接受。从根本上说,儒家所提倡的恢复周礼,世卿世禄等措施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而存在的,随着原有的经济制度、政治模式开始瓦解,新兴的封建地主势力取代奴隶主贵族而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是必然的。相比儒家而言,法家所主张的“奖励耕战”“立法除奸”“重本抑末”等思想则更容易被接受。
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家思想主张“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罚”,是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如司马谈对法家的评价“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笔者认为,秦朝的灭亡与法家根本精神并无关联,韩非主张“因道全法”,治理天下“必因人情”,认为“缘道理以从事,无不能成”,秦朝在统一天下之后便大兴土木,疲敝百姓,已经背离了法家“立法为公”的基本思想,正如童书业所指出,法家真正思想在秦代已逐步消亡。[7]
参考文献:
[1]杨国荣.荀子的规范与秩序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6):5-13.
[2](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09-310.
[3]张星久.儒家“無为”思想的政治内涵与生成机制[J].政治学研究,2000,(2):74-87.
[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65.
[5]蔡景仙.韩非子权术人生[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0.
[6]章太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86.
[7]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2:287.
作者简介:
杜伟升,男,汉族,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