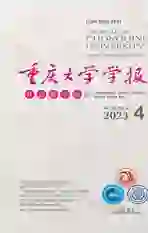传统邮驿体系的时—空结构与清帝国权力网络
2023-09-19王含梅
王含梅

摘要:清帝国依托庞大的邮驿体系,建构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的帝国权力网络。集权国家需要克服距离越远对地方控制越难的问题,因而在长期保持对里程信息收集整理、补充校正与记录存储的传统,驿程的记录与实际运行与之互为表里。《大清会典》及《则例》中的驿程信息主要有三类:节点(包括原点)、路线和数据,其记载有着复杂而又一以贯之的结构与模式,用“链条状”和“树状”两种方式呈现了驿路的分布结构,其向心性和层级性表达了古代王朝国家中央顶层设计“中心—边缘”的地理格局、空间秩序与特定的政治思维。道路里程信息既是日常邮驿工作开展的实用资料,也是国家持续掌握交通权力的知识来源。由于交通“用时间置换空间”的特殊属性,交通史的研究也应重视时间—空间的关系。驿置里程不仅仅是空间距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实际的运行和操作中,“到京日期”就是时间信息与地理信息对应的产物,是“距离时间化”的表达方式,能直观反映交通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驿程空间可以作为邮驿时间的参考标准,反过来,时间也是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计量距离可重复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在实际邮驿事务运行中,里程距离是固定的,但运行时间是变动的,这种变动带来不确定性体现了邮驿网络的动态变化和帝国权力的伸缩与强弱。传统驿站已有的突破限于地域上的向外扩张和向内深入,以及中央集权之下向心性的强化;而时间上的突破很小,时效困境也成为清末驿站体系僵化最为突出的问题,影响着国家对既定空间秩序维持的效力。
关键词:《大清会典》;驿程;排单;邮驿体系;时—空关系
中图分类号:D691.7;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4-0153-13
传统的驿站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先秦至清代发展了数千年,日臻成熟[1]。吉登斯对清帝国的通讯系统作出总结性的评价,指出此通讯网络的改善被提高到前现代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这里的通讯网络正是依托邮驿体系而建构的帝国权力网络,即由星罗棋布的驿站网点、纵横交织的水陆线道和数目庞大的车马、驿夫组成,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垂直的受清廷和各级官府支配与管控的国家机构。刘文鹏对清代的驿站制度有系统的研究,他认为“驿传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使清朝建立起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信息等以接力方式长距离输送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央对邊疆地区直辖性管理体制的确立”[2-4]。可以说,在集权体制的背景之下,驿传体系对国家军事、政治统治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源于交通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
“距离”,是地理学中常见的一类知识,就像一把尺子体现着两地的空间关系,是交通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道里远近也成为空间描述中最为普遍的一个量化指标,供我们了解自身所处的空间秩序与制度环境。交通史的研究非常强调交通与空间距离的关系,如严耕望先生曾有经典概括:“交通委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5]1交通延展是空间拓展、运输流通、信息传播的载体。交通史、历史交通地理学界的主要工作是古代交通道路开辟与路网的复原、对交通设施、工具及遗迹的考证,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5-12]。然而,在已有交通史的研究中,甚少关注时间的问题。阅读史料不难发现,驿站里程不仅仅是体现空间距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实际的运行和操作中,也有时间距离的含义。由于交通“用时间置换空间”的特殊属性,因此交通史的研究理应重视时间—空间的关系。
笔者通过对清朝政典乾隆《大清会典》及《大清会典则例》(以下简称《会典》和《则例》)所记录的里程信息的内容、价值和知识特点等方面的梳理,揭示附属清代邮驿路网之上的道路里程信息既是日常邮驿等工作开展的实用资料,更已成为国家持续掌握交通权力的知识来源,因而在历史典籍中长期保有对于里程信息的收集整理、补充校正与记录存储的传统。里程信息不外乎节点(包括原点)、路线和数据,在传统社会呈现出多元复杂而又一以贯之的结构与模式,表达了特定的政治地理思维和时间—空间关系。清廷通过具体的手段控制时效以监管邮驿系统,其控制力的强弱体现了国家力量的变化,迭至清末面临着重重困境。以下试作阐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大清会典》驿程数据的结构及其渊源
《大清会典》卷66《兵部·邮政》概述了置邮、邮符、驿费、驿程、驿夫、驿马、驿船、驿车等方面的内容;而《则例》卷120—121《兵部·邮政》分上下两篇对应进行解释说明。会典与则例,“一具政令之大纲,一备沿革之细目,互相经纬,条理益明”(清)允祹等纂:《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6),第346-348页;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20—121《兵部·邮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虽然分开编录,但在记述上体现出原本的一体性,统而观之,驿程结构一目了然。
首先是《大清会典》中的《驿程》部分记载了从京师皇华驿出发的驿程方向、过境和抵达省域:
凡驿程自京师达于四方,一曰东北路达盛京,一曰东路达山东,一曰中路达河南,一曰西路达山西。由盛京以达于吉林、黑龙江,余省皆由山东、河南、山西以达。由山东者二路,一达江宁、安徽、江西、广东,一达江苏、浙江、福建。由河南者二路,一达湖北、湖南、广西,一达云南、贵州。由京师至山西二路,一经关内,一经关外,由山西以达于西安、甘肃、四川……(清)允祹等纂:《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6),第348页。
京师是全国驿路的起点,由此向东北、东、中、西四方放射,通过直隶周边四省再向更外围延伸出分支。盛京、山东、河南、山西是分成四道后各分支道路上的第一站,并以之作为节点,东北分一路,其余各分两路,每道形成的结构,全国7条主干道构成了以“京师”为中心向外延伸的树状结构。
紧随其后以“A—B、A—C、A—D……”的形式记录了京师到全国22省长官驻地的驿程里程数,是对上文方向性记载的数据化,同样呈放射状,其中包括了干道里程、分支路线,以及水路里程:
纪程。直省以督抚,关外以将军、都统驻扎之地为准,至直隶三百三十里;盛京千四百六十里;吉林二千八百八十里;黑龙江四千一百二十七里;山东九百二十里;山西二千九十有五里;河南千四百九十里;江宁东路二千五百五十七里,中路二千二百九十五里,水路二千八百七十里;江苏二千七百三十七里,水路三千九十一里;安徽二千六百十五里,水路三千四百三十里;江西三千二百二十五里,水路四千九十里;福建四千八百六十二里;浙江三千一百十有七里,水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里;湖北二千七百七十里,水路四千三百三十里;湖南三千六百七十里,水路五千九十里;西安二千四百七十五里,甘肃四千三十有五里;四川四千六百七十五里;广东五千六百七十里;广西四千九百有九里;云南五千九百三十里;贵州四千七百七十五里。(清)允祹等纂:《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6),第348页。
而《则例》进一步对“纪程”中每条驿路干道路线及该省内其他重要路线进一步具体化,逐段详细记载了里程信息,呈现为节点串联的链条式结构,例如:
一驿程自京师至直隶保定府:七十里良乡县固节驿,七十里涿州涿鹿驿,五十里涞水县驿,四十里易州清苑驿,九十里易州上陈驿,百里广昌县香山驿,六十里大宁村,七十里蔚州驿,由上陈驿百里至广昌驿倒马关驿。七十里定兴县宣化驿,六十里宣化县深井堡驿,六十里宣化县滹沱店驿,六十里西宁县东城驿,六十里西宁县西城驿。七十里安肃县白沟驿,五十里保定府清苑县金台驿,共三百三十里。至喜峰口,四十里通州潞河驿,七十里三河县三河驿,七十里蓟州渔阳驿,六十里遵化州石门驿,六十里遵化州遵化驿,五十里迁安县滦阳驿,六十里喜峰口,共四百有十里。至独石口……至张家口……至古北口及热河……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21《兵部·邮政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5-596页。
总体上,从《大清会典》到《则例》,从大纲到细目,驿程信息逐渐具体化,从方向性到数据化再到路段化,层次也逐渐深入地方和边陲,由近处京畿到远处边陲,由高层省府到基层县驿,由核心干线到旁出支线。全国7个方向的路线具体由一条条干道及支线所组成,《则例》中的链条式结构隐含于树状结构之中。链条式结构具有实用性,树状结构更多是一种指示意义,更具王朝地理的知識性和政治权力触角的隐喻。
树状结构记录的是从中心向四周延伸的路线,就全国而言,都城是毋庸置疑的原点,而各省督抚、将军、都统驻地是一个个区域控制点,都城与各省治所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了“原点—控制点”的基本模式,这是《会典》驿程背后的思维;而地方上,同样以各级长官治所为原点,下级治所为控制点,两者之间的里程信息作为整个区域里程信息进行记录和汇报,类似表达在地方志中较为常见。
这种总记京师到各地里程“A—B、A—C、A—D……”,或反映各地到京师里程的形式在古代典籍中自有渊源,最典型的就是疆域概念中的“四极”和“四至八到”。先秦典籍《五藏山经》以“又XX(方向)XX里,曰XX山……凡XX山,XX里”的句式描述山川及道路,谭其骧业已指出这些道路及里程数的实际意义[13]391。具体观察可以发现,“大多数次经所对应地理单元的山岭间道路分布呈现树状结构”[14]。相对系统的里程记录出现在秦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为驰道的修建,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测绘、舆地图制作提供了条件,也成为记录中央到边地驿道里程数据这一政治习惯的源头,各级地方政府存有里程类相关资料以为文书行政和邮人邮驿事务考核等事宜[15]196-203。而中央汇总、藏于丞相御史府库的图书籍簿更多体现出“九鼎”一类政治权力的象征。
二十四史第一篇地理专志《汉书·地理志》中未记全国驿道,但在部分郡县之下记了河道里程。例如,陇西郡“首阳,《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东至船司空入河,过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16]1610。这句话是讲渭水自首阳县鸟鼠山发源,向东过陇西、天水、右扶风、京兆尹四郡,全长一千八百七十里。虽然河道里程不能完全等同于水路路程,但原点、方向、过境(区域控制点)、总里程数的结构并无二致。而该篇汉代政区部分之后的总括里有一段记载疆域范围,记“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16]1640。其计算或是以都城为中心,这段内容与全国政区数、提封田数、垦田数、户口数并列,显然也是秦汉上计制度的产物,是由各地逐级汇总的结果[17]231-238。另外,《汉书·西域传》中有西域某国都城距离长安的里数,或距玉门关、阳关和西域都护府的里数,也有相邻国都之间的距离[18]。《续汉书·郡国志》记录有郡国至都城洛阳的方向和里程。如河内郡,“洛阳北百二十里”;辽东属国,“洛阳东北二千二百六十里”[19]23,420。《宋书·州郡志》的道里记载终点也都指向了都城建康或州治,如会稽“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陆同”;吴郡“去京都水六百七十,陆五百二十”[20]12-15。唐初李泰主持修纂的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括地志》,虽然原书散佚面貌不清,但也可大致看出是以州治和县治为控制点。如记太行山“在怀州河内县北二十五里”,雷泽县“在(濮)州东〔南〕九十一里”[21]77,146。只是,无法确定在已亡轶的州情介绍中是否有州治到都城的里程记录。而对《括地志》多有参考的《元和郡县图志》,不仅延续《括地志》记县方位+至府或州多少里,以及县内地物距县治里数,还在州(府)情部分出现了更为系统的“州(府)境”和“八到”。州境分东西和南北里数;“八到”数目不一,仅是泛称,但都包括了到上都和东都的方位与里程,是对以往形式的继承。《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一·京兆府》记府境八到:
府境:东西三百一十里。南北四百七十里。
八到:东至东都八百三十五里。东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西南至洋州六百三十里。东至华州一百八十里。南取库谷路至金州六百八十里。正西微北至凤翔三百一十里。西北至邠州三百里。东北至坊州一百五十里。正东微北至同州二百五十里。
其下三原县条目:
三原县:次赤。西南至府一百一十里。
高祖献陵:在县东十五里。[22]2,3,7
类似的记录形式自唐宋以降成为一定之规,地理典籍中不胜枚举。汪前进指出,这里面所记的“里程不是两地直线距离,而是路程(包括水路、陆路)。起点为各府(州)治,止点为二都(上都、东都 )、府、州、县治等”[23]。严耕望默认“四至八到”和一些距离的记载具有实际意义,在研究唐代交通时,爬梳各类史料考证驿道、驿程时使用了相关数据。虽然他也发现各类志书之间的数字互有出入,甚至同样两地之间距离也不相同,如不同书籍对唐代两京间里程的记数就出入很大,不过仍然坚持认为“书所记各有所指,非多伪误也”[5]22。曹家齐也认为“四至八到”所记载的就是州县与周围地区实际交通线之里程,并从志书编纂程序角度分析了数字出入的主要原因:“在唐宋地志中,相邻州县里程不相吻合者为数不少……甲州和乙州两方彼此之间交通线,或方形不一致,或里程有悬殊。或可从诸志编修方面进行解释。无论‘八到‘地里还是‘四至八到都不可能全部囊括一州县所有交通线。诸志是根据各地上报本州县情况汇总而成的。但各州县在草拟本地情况内容时,多是各自为之,未能与相邻州县互相协调一致,故所记路线、方向互有不同,对道里之推算也有出入。”[24]成一农认为,四至八到并非直线距离而是道路距离[25]。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四至八到”道路里程数据不完全来源于驿程数据,驿路交通不是“四至八到”方向里程书写的唯一参照,府州“四至八到”走向不以驿路交通为主,而与府州县“四至八到”的界至和道路类型有一定的相关性[26]。
《清史稿·地理志》中《直隶省·天津府》对到中央的里程和府境有记载,亦是四至八到的模式:
西距省治四百六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三百八十里。《清史稿》卷54《地理志》,第1906页。
人的日常生活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和社交活动半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十里八村”,在这个圆圈之中以人居(即“家”)为原点,向农田、亲戚家、集市等地点放射,构成了最原始的“四至八到”[27]1-12。而古代县的设置也有一定的范围标准,“县大率方百里”,理想状态下以普遍脚程计算,“如果起早贪黑的话,可以在当天徒步往返”[28]141,方便行政工作的开展。县治作为原点,最合理的方式莫过于将其设置在县的几何中心上,但各地地貌和人文环境并非铁板一块,所以实际的里程并不一样,这种差异化才使得四至八到的记载具有实际意义。从以个人到以各级行政中心为原点,“四至八到”的数据依照实际情况,这种模式来源于地方经验传统,在郡县时代逐层上报汇总,形成中央掌握的全国性地理知识,并最终括大升级为国家的疆域四极;“四至八到”形式也随着疆域拓展进一步向边疆与内地的边缘扩散,而在内地也更趋数字精确、层次细化。
正因为全国主干交通的里程数据是各地路段信息汇总的结果,京师到各地总里程“A—D,XX里”实际上是由“A—B、B—C、C—D……”这种“接力式”的记录形式组成,也成为传统社会里程记载中采用较为普遍的链条模式。
秦汉出土文献中就不乏里程类资料,目前主要出土于地方政府衙署遗址和边塞的侯官烽燧、传置遗址中,里程的记述方式不一而足,里耶秦简、居延新简、悬泉汉简中的就属于相对单线的链条式记录,如汉代邮传机构悬泉置中出土的悬泉汉简90DXT0214·1:130记载: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里,……(A第一栏)
……坻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A第二栏)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A第三栏)
……出二匹六百八十五钱,出一匹三百卅五·凡千 廿。出……米卩。(B第一欄)
出二□……出二□……出二□……(B第二栏)[29]56
简文正面的记述由A及B,由B及C,自东向西用接力的方式记载武威郡至敦煌悬泉置所经传置及里程数。居延新简74EPT59·582的书写体例与之颇为相似,由东至西,点与点相互串连依次记载了长安至氐池的传置信息[30]。“两枚简”连在一起,基本可以复原出当时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路线。除此之外,也有以某地为中心,加方位直接记录起止点之间的里程。这些资料的出土具有偶然性,内容多有残缺,信息相对零散,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实用意义。虽然难以从史料碎片中清理出全国里程信息,但是综合其他资料,可以想象全国性道路网络体系存在的事实,以及每个地区、驿站里程数整理之后向上汇总的情形。
这种链条式或者说是接力式里程记载,不仅是地方官府掌握的实用地理知识,而且随着宋元以降市民社会的活跃、印刷出版行业的兴起以及王朝知识权力的释放与下移,民间对地理知识的需求和应用逐渐广泛,在社会层面普遍流行起来。南宋时一首无名题壁诗写道:“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其中的“地经”就记有各地通过一个个亭驿与都城临安相连接的里程,以往兰台秘密封存的地理里程信息资料成为市井交易的商品。可以想见,宋代以后地理作品大量涌现的趋势之下,类似有关道路里程的内容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地方志和商书的兴起代表了掌握里程数据资料权力的扩散与下移。
明清商书中有很多商路道里的记载,这类“地经”作为商旅行路指南的同时,更重要是一种“生意经”,有别于以往的官方色彩,它是民间自发根据个人或行业的社会需求制作的结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天下水陆路程》《士商要览》[31]。张海英系统论述了商书的基本概况、相关内容和时代背景,解析了明清商书大量涌现的原因,并重点分析了江南商路网络的发展以及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32]。商书取材于民间,或根据一些流传的地理书籍,或是行商贩卖人的实际经验编写而成,因此他们对里程数字有现实的需求;从另一角度看,商书的编纂流传也成为了地理知识传播的新路径。根据王振忠对徽州文书的整理,仅徽州地区相关商编路程就大约有十几种,且地经里程文献常常配有地图[33]。《祁至安化水陆路程底》记载了晋商从山西到两湖贩卖茶叶的茶路,其中“祁县至三十里子洪,四十里来远打尖,三十五里至土门宿”,就以链条结构记录一天近100里的行程[34]483-488。商书中的里程信息无疑具有强烈的实用性以及明显的区域性,记载路线往往与官方驿传体系略有不同,尤其是不会忽视和省略乡村一级的小地名,每日行程、住宿何地都力求详备,是经商出行之人的实用指南,从而使里程信息赋予了更丰富的经济属性。
总体而言,先秦至明清,驿程知识在官方的知识获取和传承中从未中断,且随着驿传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相关记录和体系越发完备。而民间汲取相关知识的途径和需求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版本链条”,近世随着地理知识的下移、商业发展和区域性贸易的兴起,以行程经验和旅行指南为核心的路程数据出现井喷且广泛传播。可见里程数字的表达和书写在不同人群和场合中,有不同的方式和内涵。
因为道路的复杂和灵活性,单一链条结构的记录之外还有一种复合模式,如《则例》中“凡驿程由大路旁出者,用双行小字以别之余仿此”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21《兵部·邮政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5页a。,也就是说采用双行夹注的形式呈现干线之外的驿路支线。树状结构以“我”为中心,是直达目标地的方向性、结果式的模式,具有指向意义;而链式结构更具实用性,亦强调中间各个站点的重要,是过程式的模式,具有参考价值。两种模式在秦汉时期成为王朝地理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时期定型为特定概念术语,明清时期走上巅峰并在典籍中系统化。
至清代,政治中心京师是道路里程毋庸置疑的原点,由内向外发散出多条线路,每路依托节点(或言之控制点)进行链条状延伸和分化,总体呈现为树状结构,这大体是古代王朝国家中央顶层设计所呈现的一般格局和空间秩序。同时,基于地方实际需求和自主发展的经验,不同路线上的节点之间也存在相互连通的可能,借以缩短交流距离,最终从整体上构筑起全国意义上的交通网状格局。
二、中心与节点:传统邮驿体系对空间秩序的维护
驿置里程信息主要传达的是一种空间关系,寄寓着统治者的空间政治理想。
清代的邮驿体系大体上可以从两个互为表里的方面去理解:一方面,驿、站、塘、台等实体机构站点和水陆、干支交通路线编织起了静态的邮驿网络;另一方面,配套人马传车与具体的行政运行、邮驿事务使整个网络成为动态的流量(清)允祹等纂:《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6),第346—348页。。通过这一动一静的运行,采用原点聚集和控制点辐射的模式,清代中央政令藉以到达疆域内星罗棋布的驿站并覆盖绝大部分地域,对于疆域的形成与稳固十分重要;作为一种集权制下的国家治理工具,邮驿体系在清代的进一步壮大、完善,传统社会也随之进入巅峰。
统治者对距离的关注,不仅基于区域差别存在的客观事实,更源于他们对政治关系和空间秩序的基本认识。在先秦典籍《尚书·禹贡》中就已经表达了以道路里程远近确定关系的基本思路,构建了理想政治关系蓝图。《禹贡》分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三部分,其中的九州是“以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为表征”的对空间认识的新思维,其中也能体现出如何通过人为作用的“道路”去改变或顺应“距离”的固有空间秩序和联系;五服是“以王都四面五百里为甸服,而后每隔五百里往外增加一个圈层,形成甸、侯、宾、要、荒五服的圈层结构”[28]47。这种理想化的模型尽管被后世人称之为“纸面”文章,不太可能付诸实践,但它更多地反映出统治者对空间秩序的简化和政治空间关系的最初印象。
受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空间秩序不可能依照直線距离的排列而存在,对统治者而言挑战来自于“治理”之术既要维护其“向心性”的集权体制,又要打破绝对的限制和变动的因素。唐晓峰说:“向心性,是《禹贡》天下秩序中十分明显的原则,在关于九州的叙述中,达河之道是极有特色的内容,显示了《禹贡》地理知识的价值取向。达河之道就是通向‘中国核心的通道,对于每个州的通向中国的路径的专门描述,使人感到‘中的聚合力量。有些通道是对天然水道的利用……有些通道则是人为的安排设置……[35]279”可以说五服制和九州制的两种政治地理思维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空间、秩序、天下等观念的认识。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驿站的设置布局、驿路的开拓延展,都不是凭空而来,也恰好是与《禹贡》一脉相承的集权体制的现实需求的客观反映。
里程是距离的一种表达。道路的扩展和站点的设置需要考虑山川形便、考虑交通运输等条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方面的需求,而建立了两点之间的联系,所以里程的记录和书写意味着对真实的、在地的客观空间联系的一种记录。在运输工具以相对固定的车、马、牛等畜力为主动力,道路开拓修筑技术稳定的时代,除了新开辟的道路,旧有的路网里程长期具有参考价值。里程信息、数据及记录形式也会随着时代层累,并逐渐演变成一种记录传统,确定基本的书写模式,《会典》中的清代驿程的结构与层次就是其集大成和最终呈现。《会典》依次记录以京师为中心到达各省首府的路线,通过节点和驿道连接四方,《会典》驿程完整诠释了传统政治关系的结构和模式。
古代里程数据的记录流传,大多是借助藏于官府的档案或地理专志,这些知识也通常被视为“统治术”而不向民间开放,驿程的记录及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统治者对空间秩序建构的几点原则。
首先是方向层面的向心性和指向性。道路基本由两端的起点(原点)和终点(控制点)所范定。驿路的起点往往是确定的,它是整个结构的“中心”,就帝国整体而言,驿程的记录每一条都是以全国行政中心所在地为起点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各条路线向中心汇聚。《大清会典》中就记述了以京师为中心,以周边四省为中介,依次记录四方七路的驿程。在地方,传统时代的四至八到也是以各级治所为中心,依托驿程驿站向外拓展而构筑起体系。看似獨立的地方上各省记录的干道驿路实际上是跨越省区的,可连为一体,向心是其主要目的。
驿路的具体形成和终点一方的位置所在取决于控制点的“资源”属性,具有指向性。《禹贡》所记贡道就是各地将贡赋汇聚于中央的道路,也就是一条资源输送之路。由于中国地形的不规则和资源分布的不均,道路走向不可能如同“井”格一样横平竖直,驿路的延伸和分布需要考虑山川形便等地形地貌,驿站的设置要考虑政治、军事、经济等“资源”因素,集权的意义在于占有土地、人民、贡赋等资源分配的权力,所以网点和线路的铺设不可能均质。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邮政·置驿》记载各省的驿站总数,可以看出,毗邻京师的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设置驿站较多,各省之间差距不大;西北边疆四省陕西、甘肃、蒙古、新疆驿站设置基本都在130处以上;而东北、西南、云贵地区设置驿站数较少资料来源: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55—卷658,书中记载的部分省的驿站数,如“直隶185、山东139处、山西125处、河南120处、甘肃184处、陕西130处、新疆160处、四川65处、贵州23处、云南81处、盛京29处、江苏40处、浙江59处、安徽83处、江西49处、湖北70处、湖南62处、广西19处、广东10处、福建68处。”。驿站网点的空间分布和指向就体现了统治者对空间秩序的改造和利用,在建立中心—边缘的圈层结构的同时又要通过连线打破空间限制,指向和控制地方资源,目的都旨在强化集权。
其次是结构层面的层级化和节点化。驿路延展的方向性是放射状的、发散的,表面上看“接力式驿站体系是传统王朝国家解决远距离信息、资源输送问题最主要的途径”[4]。接力式的运输模式体现在里程记录形式就是驿程由点及线的线性结构;实际上驿路的主干、分支是有层次的,干路的重要性显然是要优于支线的,干线、支线各自类型之间,不同路段也有差别。各线上节点或控制点的数量、距离、意义并不是一致的,总体上呈现一种由近及远降低的差序格局,这一结构是通过链条式和树状的驿程驿路网络实现的。但是因为行政层级、经济资源等因素上的“中”的突出,造成这种差序并不是简单地因远近关系逐级衰减,而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起伏,控制节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向心性和层次化的取向是统治者统筹各方因素,由上到下宏观布局规划驿传体系的最基本原则和核心思维,也是集权政体极力维护的空间政治秩序的主要形态,在疆域的形成过程中更趋强化。历史时期驿路的发展方向,一是随着边疆开拓将路线向外延伸,如汉武帝开边之后建立河西传置体系,元代清代开拓蒙古地区和北边驿路;另一方面是内地空白地带的填充,随着区域开发的深入,湖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驿路得到覆盖,其中支线驿路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两个过程都并非线性上升的,尤其因为政治军事关系而时有盈缩。古代驿站和近代邮政在空间形态方面都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同样受到“中心—边缘”的圈层制政治地理思维的支配。
三、到京日期:里程的时效目标
驿置里程信息背后也有时间目的,在实际应用层面时效是里程的核心要义。
不论记录模式是树状直达式还是链条接力式,驿程首先是作为日常实用地理知识的直观呈现,描述方位、道路类型、距离中心里数,但随着它被上计、整理、典藏、传承,在此基础上传达的是一种空间观和秩序观,成为王朝地理知识、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这种象征意义之外,里程也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通过地点、路段的规范来约束时间。由于古代的日常时间记录并不十分“科学”,时间未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一直到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机械钟运用于社会生活进行时间规范之前,时间都一直是与空间(和地点)相联系的[36]15-18。换句话说,前现代因为时间规范技术多样而不精确,时间往往借助空间来进行表达,中外莫不如是。
在帝制早期的行书规定中,不乏有关邮人行书时间和逾期惩罚的规定,而秦汉里程简就是作为考核官吏外出办公是否无故“纡(迂)回逗遛(留)”(清)允祹等纂:《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6),第348页。而超时的参考。到帝制晚期,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了岳州江防兵备和辖三哨官兵侦治各站点及里程数,最后却记为“备兵岳州时刻图”[37]294。《大清会典》在驿程方向性记载之后,也注明“勘合火牌均注道所,由纡(迂)回逗遛(留)者有禁”(清)允祹等纂:《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6),第348页。。驿程是表面的、静态的数据,作为参考标准,其背后所寄寓的是邮驿事务的正常进行,按时递达才是关键,故而在京师去各省里程的记载之后详加说明,目的是“赍进本章,分别缓急,日行有限,司驿官无故稽迟,计其时刻议处。至奏章有关机要不可缓待者,许由驿立限驰递,寻常之事不准”(清)允祹等纂:《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6),第347页。。《事例》在驿道里程之后更是具体记录了各地的“到京日期”,从分开到集合,可以看到传统社会“驿程+时刻”模式至少在明清时期已经成型(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00)《兵部·邮政·驿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第718-727页。。
人每日行走的路程是相对稳定和有限的。一般来说人力单日行程大约一百里,“方百里为县”就是以此为标准所设定的理想状态,这样的话,日行百里就成为里程与时刻相挂钩、转换的内在逻辑,附着地理信息的里程从而也暗含了时刻区间,所需花费的时间不言而喻,可用于日常公务考核。在早期简牍等文书行政成本较高的时代,复合了里程和时刻的里程记述理所当然成为节省行政成本的首选;而后期随着纸张和印刷术的流行,可以做到事无巨细地将里程和时刻分别详细记录和对照,尤其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要求下,各个控制点到中心之间的时刻,亦即到京日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大清会典》及《则例》中的全国驿程资料具有全局性和高度的概括性,是王朝中央掌握地情、军政的必备情报。这套资料的汇总与提炼,旨在对驿传制度进行分析、控制和调度。《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在传递文书中邮符、勘合、火牌均为信使凭证 邮符是“发给往来人员准许其在驿站食宿及使用车马的凭证”;勘合是核验符契。“古时以竹木作符契,上盖印信分为两半,当时双方各执一半,用时二符相合、堪验真假”;火牌是“兵役驿递的符信,沿途凭牌向各驿站支领口粮。”(清)允祹等纂:《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6),第347页。,地方各级驿所验证物件合格方予放行,与之相应的是需要注明到达的时间和站点信息。因此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集合里程与时刻的“排单”。
“排单”多为左右或上下两联,一联是相关规定,以文字形式告知文书传递须沿线州县驿站配合,还规定传递文书时限和马力,再次敦促不得有违,不得延误等语;并写明该排单的发出时间、地点。另一联为表格形式,动态记录文书传递所到之处的时间、站点名称等信息,可视为清代文书的传递轨迹。图1是清光绪年间的一张空白排单。
图1中右侧书“为饬递事今本 发投 公文一角事关紧要仰沿途州县驿站即选派的役健马昼夜限行百里飞递毋许藉延倘有违误查出照例参处不贷须至排单者火速 右仰经过地方各州县驿站准此 光绪 年 月 日 时 自 发”。
左侧排列有时刻表“ 年 月 日 刻 到 驲(驿)”排单是清代驿站传递公文填注的单据。中国邮政博物馆、中国邮票博物馆收录了多张排单。《中国邮票史》、一些集邮丛书、杂志也有收录,但未形成资料专辑或图集。。
排单一般都具有程式化的书写格式和内容,流传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驿站、驿务机构,至今仍保留下不少实物。从排单透露的信息来看,地方衙门管理驿务运行和文书传递时,非常看重时限和马力。而清朝对递运程限也有一定之规:“驿设驿马与驿夫,运载重量兼设驿车。南方水运之区,亦设驿船,定制以百里为一站。通常文书,以日行一站为准。凡军机处公文,签发马上飞递者,定限日行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得日行六百里,惟驿道可驰六百里者,仅限于平坦康庄之道;凡崎岖多山之地,日行三四百里,已为极限。清制凡各省官员觐京引见,行程均有定限,奉旨驰驿者,以日行二站为准,其他则以日行一站为准,为边疆僻地,则速率迟缓,每不足此数。”[38]马匹是驿传运输的主力,爱惜马力保护马匹是传递文书中需要注意的,目力所及,现有排单中规定时速多是四百里以内,六百里加急的非常少见。所以在右侧时间记录列,对传递的考核不仅需要看是否按要求和规定路线由上一站传送,还要看时间不可延误超期,更不可不惜马力奔驰无度。排单中的地理信息与时间信息是对应的,可以看作是一种“时间距离”的表达。这种表达,在行政考核中有不同层次的含义。于文书发送者而言,按时送达之限制和把握精度多以日为单位;于沿途各站接管收发单位而言,还要考量时刻和所用具体时间,从经验的角度衡量两站点之间耗时之出入。
结语:时空关系与传统邮驿的时效困境
西方谚语有云“时间和距离是集权的天敌”,集权国家需要克服因远距离对地方控制力度的不力,驿程的记录与传承与之互为表里。传统社会,不仅时间往往通过空间进行表达,驿程空间可以作为邮驿时间的参考标准;反过来,时间也是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计量距离、里程可重复的实际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既有空间秩序动态的掌握。不过,在实际邮驿事务运行中时间的影响因素不少,带来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体现了邮务的活力和可塑性。
里程是相对固定的,而时间是变化的。驿站和驿路确定,则表示里程数据的相对固定,以里程远近构成的空间秩序也基本定型。但在驿递过程中,不可控的气象灾害,以及工具动力的变化和人为因素等造成的速度和效率的变动直接结果就是耗时的不同。吉登斯说“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36]16,一语道破了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时间变量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经验中相较于里程更为切要和易于感知。不仅里程与地经、地图在传统时代大都是藏于兰台、束之高阁的机密,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官吏的具体办事而言里程远近更多只是一种感觉,需要换算为时间计量,才能实实在在地感知、体会,影响也更为直接具体,因为时间差往往关系到自身的利益。对邮驿时间的有效控制,体现着驿传体系的运行与效率,而这种效率折射出集权体制下国家力量的强弱,又影响着国家对既定空间秩序维持的效力,在晚清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之下显得异常突出,传统邮驿和新式邮政在时效经营上大相异趣,国家治理能力显露无遗。罗兹曼从时间的角度纵向上对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的通讯效率的作了比较,18世纪“清王朝的确不曾忽视改善通讯系统……这个通讯网络的改善被提高到前现代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但在清朝后期,当新的通讯技术渐次传入中国时,政府在使其设备现代化,从而可能在新的水平上满足其需要上却反应很迟钝”[39]68。“清初那一套用于民族融合的前现代手段,原来是相当可观的,但到19世纪末年,这一套已经差不多被历史所淘汰,成为老掉牙的陈年旧货——这就是我们在观察整个19世纪的中国所见到的情况。”[39]69他还横向对比了中国、日本、俄国在提高通讯效率中的政府作用,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已拥有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现代化的国内银行系统和重要的轻工业基地。日益发展的铁路系统促进了某些地区市场的统一。但是兴办大工业、邮政系统和全国通讯所需要的那种管理体系,却未能在中国像在现代化中的日本和俄國那样,表现出惊人的进步。日本和俄国在采取措施以适应私人组织和政府的管理需要时,表现出‘不寻常的社会工程技术。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官员在中央一级集中指导国家资源和技术的使用。在日本和俄国,政府的作用特别的广泛和有效”[39]252。
兩千年传统邮驿一方面是稳定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尤其是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迭至清代已进入“过密化”阶段,不仅发展上遇到瓶颈而且也陷入了驿站兴衰的怪圈之中,驿站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相当有限的。总体上,传统驿站已有的突破主要限于地域上的向外扩张和向内深入,以及中央集权之下向心性的强化;时间上的突破很小,时效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的改进不大,运输时效的改善还有待于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背景下邮政现代化事业的开展。
参考文献:
[1]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
[2]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刘文鹏.清代驿站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刘文鹏.驿站体系与清代远距离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N].光明日报,2020-01-13(14).
[5]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张伟然.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95.
[7]白寿彝.中国交通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8]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1]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2]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3]谭其骧.长水集续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黎阳.根据《五藏山经·北次三经》再现上古太行山川道里图:《五藏山经》地理解析新思路[J].中国史研究,2015(4):25-57.
[1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M].长沙:岳麓书社,2007.
[16]地理志上[M]//汉书(卷28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葛剑雄.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M]//中国人口史(卷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8]陈世良.《汉书·西域传》记载道里之特殊方法[J].新疆社会科学,1990(1):112-121,93.
[19]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20]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1]李泰.括地志辑校[M].贺次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2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3):273-288.
[24]曹家齐.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4):37-42.
[25]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6]梁晓玲.疆理天下:中国传统地学视域中“四至八到”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7.
[27]韩茂莉.十里八邨: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8]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0]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薄》考述[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1):62-69.
[31]黄汴.天下水陆路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32]张海英.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9.
[33]王振忠.清代徽商与长江中下游的城镇及贸易:几种新见徽州商编路程图记抄本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18.
[34]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35]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279.
[3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7]王士性.五岳游草 广志绎[M].新校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8]胡焕庸.国内交通与等时线图[J].地理学报,1936(4):761-774.
[39]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The temporal-spati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postal system and the
power network of the Qing Empire: Time constraints of
communication means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vel
distance in The Comprehensive Statutes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
WANG Hanm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a vast postal system, the Qing Empire constructed a vertical network of imperial power from the central to local levels. As a centralized state, it need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controlling distant areas, and thus maintained a tradition of collecting, organizing, supplementing, correcting, and storing information on mileage, with the records of travel and actual operations being interdependent. The postal information in the The Comprehensive Statutes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 and the “Regulations” mainly comprises three categories: nodes (including origins), routes, and data, which have a complex and consistent structure and pattern, presenting th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postal roads in both chain and tree formats. Their centripetal and hierarchical nature reflects the central-to-edge geographic pattern, spatial order, and specific political thinking of ancient dynastic states. Information of road mileage is not only practical data for daily postal work,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state to continuously exercise its transportation power. Given that transportation trades space for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study of transportation history. Postal mileag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spatial distance, but also the product of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ime information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rrival date in the capital” (到京時间)represents the “time can measure the distance” and intuitively reflects the control of transportation over space and time. Postal road space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standard for postal time, and conversely, time is a way of expressing space, summarizing experiences of measurable distance repetition. In actual postal affairs, while mileage remains fixed, operating time vari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stal networks dynamic changes and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imperial power. Traditional postal stations had already expanded and intensified their centripetal force under centralization, but made little progress in terms of time. The timeliness predicament became the most significant obstacle to the rigid Qing postal system in maintaining the established spatial order.
Key words:The Comprehensive Statutes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 postal station miles; schedule; post system; space-time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 傅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