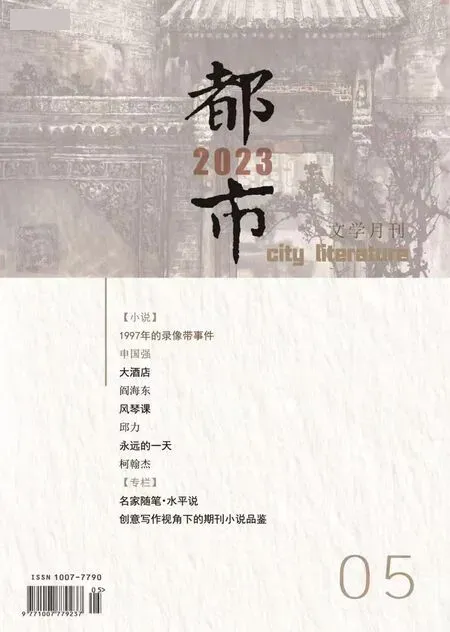烟大岭一去不返
2023-09-13万小刀
文 万小刀
1
小路像一条麻绳慵懒地搭在烟大岭肩上,山那边系着一串村庄,山这边也系着一串村庄。村庄像打在麻绳上的结。
迎亲的队伍敲锣打鼓,从“麻绳”上走来。路过一个又一个“结”,点燃一串又一串的“十八响”。跨过竹竿河,翻上烟大岭,下一道长长的坡,坡上倦躺着一块块空白的花生地。地边生长着一些乌桕树和柿子树,乌桕树被秋风染红了头发,柿子树的枝头则挂满红灯笼。有鸟雀扑棱着翅膀,啄食着熟透的柿子。
天空有老鹰在盘旋,就像命运在睥睨众生。
我年轻的母亲,就在那个秋天的上午,嫁给我年轻的父亲。
那时的烟大岭风华正茂,郁郁葱葱的松树,将整座山包裹得严严实实。两道山岭一撇一捺,将我的村庄环抱,再呼啸的北风,都对它无可奈何。所以老人们都说我的村庄是块风水宝地。
烟大岭的风景也很美,特别是在炊烟四起或秋雾时节,总有一团或一缕烟雾,在山腰飘飘袅袅,经久不散,烟大岭因此得名。
很多年后,母亲仍然对烟大岭念念不忘,就像念念不忘她的青春。她嫁给父亲的时候,哪里会想到,十年后,父亲会留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意外去世。
2
有关父亲的往事,多是从一些知情人的闲言碎语中拼凑而成的,当然我也脑补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细节。
比如我的三个姑姑,她们对我很好,在我的童年,她们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感叹:你跟你伯长得极像哦。然后会一遍又一遍在我面前讲起我父亲的往事,不说得泪眼婆娑绝不罢休。
在我四十岁生日的一个饭局上,偶遇一名退休局长,他见我也姓万,便问我是哪个村的,三言两语一聊,才知道我是他发小的儿子。因为他比我长两辈,我喊他爹爹;因为他曾是局长,我喊他局长爹爹。那个热情的中午,局长爹爹拉着我的手,一起坐在主位上,他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亲人才有的关切和慈祥。
他说,你跟你伯简直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趁着酒兴,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往事。他说在20 世纪70 年代,村里有一个保送大学的名额,原本父亲和他竞争一个名额,然而父亲却放弃了。父亲说要跟母亲结婚。但也许,是因为局长爹爹从小是孤儿,父亲把机会让给了他。
局长爹爹大学毕业后,在县里当了官。我父亲下葬那天,他回来过,还抱过四个月的我。那之后他定居县城,鲜少回村。转眼四十年过去,他已退休,而我也近中年。好在我混得还不差,饭桌上那些在小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对我交口称赞。这令他很欣慰,所以他说很替我高兴,也替我父亲高兴。
几天后,我在接母亲去省城的车上,轻描淡写地说起这段故事。
母亲沉默半晌,说,如果你伯去上大学,我可能就不会跟他成家了,也许他就不会……母亲有些哽咽。
我连忙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不就没有我了嘛。
母亲沉默半晌,又悠悠地说,你婆婆因为这事对我有很大的意见。
3
在我家乡,称爷爷奶奶为爹爹婆婆。
我婆婆是我外婆的堂妹,母亲叫她姨妈。因为这层亲戚关系,父母少时相识,这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了一份青梅竹马的浪漫。我姨妈曾说,母亲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放在现在都可以演电影当大明星了。也难怪父亲宁愿放弃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也不愿意放弃他的爱情。
婆婆当时没有反对,一个旧社会的小脚农村妇女,根本不知道上大学的机会意味着什么。后来得知我那位局长爹爹之所以在县城当了官,是因为上过大学后,婆婆对父亲的抱怨这才姗姗来迟。
然而,令婆婆恨铁不成钢的是,父亲明明错失了一个当官的机会,但他却不以为然,仍然和母亲恩恩爱爱,一副就算让他当皇帝也不稀罕的态度。这令婆婆怒火中烧,即便母亲是她的儿媳妇兼外甥女,她仍然对母亲心生恨意,甚至还有点妒意。
父亲兄弟四个,姐妹三个,父亲排行老二。大伯带着三爷四爷在城里搞副业,也就是当泥瓦匠,过年回家会给婆婆扯各种时髦的布匹,给我三个姑姑做新衣裳,乃至置办出阁的嫁妆。当然还会给我婆婆一些钱。而父亲在生产队当会计,和母亲一起挣工分,供一家人口粮,还要种菜养猪养鸡。父母挣的口粮虽然能解决一家人温饱,但是大伯挣回来的钞票,显然更具有震撼人心和笼络人心的力量,所以婆婆对大伯更加偏爱。相比之下,我父亲就太没用了,在村里当会计,好歹是个“官”,却一点油水都不会捞。
母亲在我记事起,提起我婆婆,心里免不了怨恨。但在当时,母亲一直隐忍着。直到我一个哥哥掉进池塘淹死后,母亲和婆婆的矛盾才开始白热化。
那时,我大姐四岁,哥哥不到两岁。怀着我二姐的母亲,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大姐去生产队干活。不到两岁的哥哥还不太会走路,只会在地上乱爬,母亲只好把哥哥放在家里,给婆婆照看。那时婆婆还照看着我大伯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哥。
结果我哥哥却掉进池塘淹死了。
母亲每每提及,就伤心地自责,怪自己不该把我哥哥交给婆婆照看。此后母亲再也不指望婆婆帮她做任何事,即便是她分内之事。
母亲恨恨地说,让她专心去带她其他几个孙子吧。
而婆婆呢,却说是我母亲命硬,克死了我哥哥。确实有算命先生说我母亲命不好,一生要吃很多苦。一年后,我父亲也去世了,婆婆再一次找到母亲命硬的佐证。
母亲和婆婆的矛盾像煮沸的水。就在沸水快要把锅盖都掀翻之际,生产队解散了,各家各户按人头分了田地。父亲的几个兄弟,也就此分了家。眼看家里的房子不够四兄弟分,三爷入赘到别的村,再过几年四爷结婚也要房子,于是父亲和母亲一商量,找了一块地,盖了三间土坯房,而且离老屋远远的。
不在一个屋檐下,眼不见心不烦,矛盾和摩擦也少了许多。
搬进新房的第二年,父亲去世,母亲“命硬”一说在我婆婆心中被盖棺论定。
4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父亲健在,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我还会经历那么多坎坷和挫折吗?我会过得更幸福吗?
我出生于1982 年春天,在父亲离世前,我每天的“工作”除了吮吸母亲的奶水,就是在父亲的怀里撒尿。这是多年后母亲告诉我的。她说,只要你伯抱你,你就会在他怀里撒尿。
我问,我伯有没有打我屁股?
母亲说,没有,他会哈哈大笑。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在父亲怀里撒尿,他表现得很高兴,而我为了讨他欢心,只要他一抱我,我就撒尿。
但是,在1982 年春天行将结束之时,我再也没机会在父亲身上撒尿了。
那年5 月底,烟大岭的映山红都快开败了,我家的五月桃终于红了。父亲一大早就摘了两筐,挑去镇上的集市售卖。集市在十五里山路之外,路上要经过七八个村庄。那个年代,村庄里到处是狗,它们见了陌生人就会群起而狂吠。
农村人对付狗可谓经验丰富。像我们小孩,如果有狗胆敢冲我们耍威风,我们会突然蹲下身子,做出在地上摸石子状,就能把狗吓跑。如果狗多,那得拿一颗货真价实的石子,货真价实地扔过去,这样才能货真价实地把狗吓跑。大人则不一样,大人如果蹲下身子摸石子,就太失大人风范了。况且大人一般都挑着担子,蹲下身子摸石子有些太费周折。大人通常不搭理那些张牙舞爪对着空气瞎叫唤的狗,如果有狗胆敢靠近,他们会朝着空气踢出一脚,狗同样也会退却。
那天父亲着急赶路,没有注意那条狗拖着尾巴,也没注意那条狗嘴巴里流着涎水。正值壮年的父亲伸出他的大长腿,踢了虚张声势的一脚后,那条狗并没有被吓退,反而冲过来咬住父亲的腿脖子不撒口。父亲大怒,另一只脚朝狗肚子使劲一踢,那条狗“昂昂”叫唤着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儿,这才远远跑开。父亲提了提裤管,几个牙印渗着血丝,便放下担子,在地上抓了一把尘土,往伤口上胡乱一抹,然后继续赶路。
一个月后,父亲因狂犬病发作去世。所以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疯狗的两个特征:其一拖着尾巴,其二嘴里流涎。母亲说,碰到这样的狗,要躲得远远的。
5
父亲去世的那段时间,是母亲人生最煎熬的日子。想想也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奶着一个出生四个月不会走路只会哇哇大哭的娃,身边还有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她该怎么办?她能怎么办?
我没问过母亲是怎样度过那段煎熬的时光的。我不想提起她的伤心往事,我担心她会哭,她一哭,我的情绪也难以控制。一个大男人和一个老太太抱头痛哭,场面实在尴尬。
外婆和姨妈,作为母亲娘家的亲人,没有置身事外。母亲往后日子该怎么过,成为她们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直到那年冬天,她们将目光锁定在我二爷身上。
二爷是我四爹爹的第二个儿子。他兄弟五个,大爷结婚了,三爷也即将结婚,四爷在建筑工地搞副业,五爷还在读初中。二爷相了几次亲,都没成功。原因是他身体不好,经常咳嗽,有时候还能咳出血丝来。再一打听,原来他十几岁时,不小心将一个圆珠笔帽吸进了气管里。那时医疗条件有限,一直没取出来。
那个圆珠笔帽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哪个年轻的姑娘,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他身上呢?
跟我二爷同龄的青年,都去城里搞副业。他们农闲搞副业,农忙回来收庄稼,这样既能保证一家人的口粮,又能存钱娶媳妇。而我二爷去不了,因为这颗不定时炸弹,没有包工头敢带他,一来他身体瘦弱,看上去干不来重活,二来怕万一他体内的不定时炸弹爆炸了,担不起这个责。
父亲健在时,对我二爷很好。二爷也经常到我家,帮忙干农活。
基于以上情况,外婆和姨妈就出主意,让我母亲和二爷搭伙过日子。这对双方都是不得已的选择。只要那颗不定时炸弹暂时不爆炸,他能帮母亲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也就谢天谢地,还要谢我二爷了。至于将来的事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我母亲来说,好像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于是,在1982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大舅和姨父就去找我二爷,他们具体怎么说的,我不太方便仔细打听。
二爷思量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来到我家。我外婆对两个姐姐说,快喊爷。
6
在我的老家,称父亲为伯,称继父为爷。
很多年后回望,其实继父对我很好。即便在我不懂事的少年时期也恨过他,但他对我真的视如己出。
继父来到我家后,就天天抱着我去玩。那时的我,自打父亲去世后,就天天哭,把没爹的孩子的悲惨境遇表演得淋漓尽致。继父抱着哇哇大哭的我,在村里四处转悠。村里人对继父说,这娃不认你这个老头。“老头”也是父亲的意思。后来他在货郎那儿买了个拨浪鼓,天天在我眼前摇来摇去,我刚开始还觉得新鲜,睁着圆溜溜的黑眼珠,盯着拨浪鼓看,两天后,就不管用了。继父又想了一个绝招,他弄来半包红糖,放在口袋里,只要我一哭,他就用手指蘸满红糖,塞进我嘴巴,我果然就不哭了。不明就里的村里人,纷纷啧啧称奇,说这娃认你了,认你了。
可惜这段往事是很多年后继父才跟我说的,如果早点跟我说,我也许能早些懂事,对他的恨意也不会持续那么久。
7
弟弟出生时,我不到两岁。母亲和继父起早贪黑,地里有干不完的活。为避免我和弟弟像哥哥那样爬进池塘,念小学二年级的大姐只好退学,在家负责看娃,顺带洗衣做饭。
母亲说,我们一家最对不起的,就是大姐。没办法,二婆婆指望不上,四婆婆也不待见,只有靠我们自己。
从小,我就管婆婆叫二婆婆,其中有点微妙的亲疏差异。按理说,她是我父亲的母亲,我得叫她婆婆。但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叫她二婆婆,毕竟她是我继父的二妈,所以最好统一称呼,我也叫她二婆婆。不然小孩子家家的,不懂事会问,为什么弟弟叫她二婆婆,我叫她婆婆呢?
同样,弟弟是四婆婆的亲孙子,为了跟我统一称呼,弟弟也被剥夺了婆婆的叫法,称他亲婆婆为四婆婆。
这样称呼,自然是母亲教的。母亲出于一碗水端平的考虑,让她的四个孩子不亲二婆婆,也不疏四婆婆,跟两位婆婆保持同样的距离。母亲没想到,她一碗水端平的结果是,二婆婆不疼,四婆婆不爱。
但也只能这样了。
后来,二婆婆眼瞎了,跟小妈生活在老屋,她俩天天吵架;四婆婆呢,也跟几个儿媳不太对付,为此她经常哭哭啼啼的。
母亲以前也许恨过她们,但此时又同情起她们来。时不时安排弟弟给四婆婆送饭,安排我给二婆婆送饭。
那时二婆婆一年到头躺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有一次,我送饭给她吃,她用颤抖得像枯枝一样的手摸我的脸,摸我的头,然后又用颤抖的声音说,都长这么大了。在黑暗中,她给了我一个略带慈祥而又满嘴空洞的微笑。
那是我记忆里她给我唯一的一次微笑。
后来没多久,她就去世了。
在二婆婆的葬礼上,做法事的道士不让我送殡,说我和二婆婆的命理相冲。
8
母亲和继父种了两年地,起早贪黑,也只勉强填饱肚子。如果年成不好,还要借粮度日。那时我二姐在上小学,再过几年,我和弟弟也要上学,如果家里有三个娃上学,靠种地就捉襟见肘了。所以,继父得想办法去城里搞副业。
搞副业就是去城里当泥瓦匠。他没经验,得从小工干起,小工需要大工带。继父身体不好,村里很多大工都不愿意带他。好在他有个发小,晋升为大工了,看我家实在困难,便带他去了城里。他将病情瞒着包工头,先干起了小工,几年后也晋升成了大工。
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继父为了不让包工头得知他的病情,随身带着一个行军壶,里面装着热水,在咳嗽剧烈之前,就赶紧喝几口热水压一压,这样能暂时止咳。再后来,继父去城里大医院检查,医生说肺部有阴影,继父说是一个圆珠笔帽,医生说已经长进肺里了,没办法取出来。医生开了些药,继父在工地偷偷吃,不敢让人知道,后来,他咳嗽的毛病好多了。
就这样,继父长年在城里搞副业。他在城里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别人一年上200 多个工,他从不休息,除去过年回家耽搁些时日,他一年能上300 多个工。
母亲在家负责种地,犁田耙地这些男人干的活儿,母亲都会,她甚至还能像男人一样,挑起100 多斤的担子。
母亲因此变得粗枝大叶起来。
9
20 世纪90 年代呼啸而来,我记忆的羽翼也逐渐丰满。随着“要致富多修路”的口号响彻全国,一条蜿蜒的公路修到烟大岭山腰。
那时的烟大岭,表面上树大林深,挖开表皮的沙土,里面全是坚硬的岩石。那年月,修路既是公家的事儿,也是百姓的事儿,我们每家都得派出一个劳动力参加劳动。在外搞副业的男人,纷纷被召回。他们用钢钎在岩石里打洞,然后埋上炸弹和雷管。放炮的时候,村干部敲着锣在村里吆喝:放炮了,放炮了,在屋里躲到,都莫出来。
随后几十个炮眼接连爆炸,一些石子飞落屋顶,把瓦片砸得哗啦啦直响,就像露天电影里演的那些战争片,令人惊心动魄。
大人们修路的时候,不时能捡到子弹壳。据村里老人说,烟大岭上曾发生过很多次战争。有打日本鬼子的,有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我的小学校园里,就有一个烈士墓。清明节,老师带领学生代表上过坟,扫过墓,只是年代久远,墓已斑驳,烈士的名字模糊不清,老师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们对铜质的子弹壳充满好奇,但玩两天就兴味索然了。后来不知道谁,用子弹壳吹出了悠扬又刺耳的哨声,自此,子弹壳又变得奇货可居。
继父修路时也捡到了一个子弹壳,拿回家后,我和弟弟都伸出手,想据为己有。继父犹豫了一下,把子弹壳放在我手里。弟弟很生气,哇哇大叫着跑进灶房找母亲哭诉。母亲出来,一边用围裙擦手,一边对我说,弟弟还小,哥哥应该让着弟弟。我不答应,我说爷给我了。母亲板着脸说,交出来!我一气之下,把子弹壳扔进了门前的水沟。母亲一手抓住我肩膀,一手打我屁股。我开始哇哇大哭。母亲又转身去灶房,提着火钳去水沟里拨弄。水都被母亲搅浑了,哪里找得到。母亲又气呼呼地回来:不找了,你们俩都不许玩。
母亲继续做饭。弟弟说,哥哥,我们去摸子弹壳吧。
我没理他。
弟弟运气很好,没几下就摸到了子弹壳。他甩了甩上面的泥水,又用清水冲洗一遍,鼓起腮帮吹起来。结果却吹不响。弟弟一摇一摆地走到我跟前,让我吹。我用衣角擦去弟弟的口水,把子弹壳贴在嘴唇上,沿着壳壁往下吹气,果然响了。
弟弟模仿我的样子,又吹了一下,仍然没响。我只好一边说着你真笨,一边手把手地教他吹子弹壳哨子。
弟弟终于吹响了。他把子弹壳递给我:哥哥,别生气了,子弹壳送给你。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才不稀罕呢,我自己去烟大岭找。
那几天,村里很多小伙伴去烟大岭找子弹壳。后来大人们说,烟大岭山顶上,住着一位白胡子老头,专门抓小孩的。小伙伴们果然好骗,都不敢去了。其实是因为修路时每天都要放炮,小孩子去山上捡子弹壳太危险,所以大人们才编这样的谎话吓唬人。
去烟大岭找子弹壳就这么不了了之,弟弟执意要把那个子弹壳送给我,我执意不要。它最后消失在记忆的尘埃里,不知所终。
10
公路通车后,烟大岭的怀抱里再也没有飘袅的云烟,有人说公路破坏了烟大岭的风水,让这一景观消失不见。年轻的时候,我不信风水。我分析是因为修公路,砍断了烟大岭一撇一捺两只臂膀,北面来的风,从缺口蜂拥而出,即便有云烟,也会被冲散。如今想来,这也算风水的范畴。
但家乡人并不为此惋惜,风景算什么,发家致富才是硬道理。因为有了公路,进城搞副业更加方便,回家也方便。搞副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壮年劳动力去北方搞建筑,年轻人则成群结队地去广东打工。大姐把我和弟弟带到上小学的年纪之后,便随着打工的人群去了广东。后来二姐上到初中也不读了,也去了广东打工。
因为我们家有三个人在城里搞副业,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村里有什么新鲜玩意,比如三洋电风扇、电视机,我们家也一一配备。在我念小学三年级时,村里有人推倒瓦房建平房,继父不甘人后,计划推倒我父亲留下的三间土坯房,扩大面积,建六间平房,等将来我和弟弟成家时,一人三间。
那几年,继父过年回家,就会跟母亲算账。他一本正经地坐在堂屋的饭桌前,手里拿着一本翻烂了的笔记本。先算他一年上了多少工,比别人多上了多少工,一共赚了多少钱,比别人多赚多少钱。他这一生都喜欢跟别人比。然后再算两位姐姐一年寄回家多少钱。母亲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听讲,假如因为纳着鞋底或者干着别的活儿而分心,继父会像老师一样,对她提出严厉的批评。母亲一开始听得津津有味,等父亲算完账,会让母亲再算一算家里的开销,母亲就像没写作业的学生,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她没念过书,不会写字,一年下来,学校交了多少学杂费,人情往来随了多少份子钱,农药化肥花了多少钱,自然无法记清楚。便只好报个家里存款的数目。而这个数目离继父的心理预期总是有点少,继父就会发脾气:
“我在外挣点钱容易吗?这都是血汗钱,你们在家大手大脚,不知道把钱花到哪去了,像你们这样花钱,我就算干到死,也建不起新房……”
继父一生气,就会咳嗽不止,母亲只好一边哭,一边给继父的行军壶添热水。
那两年,继父一发火,母亲一哭,我就想辍学。我甚至把课本和寒假作业都统统扔进灶膛里烧掉过。心里恨恨地想:把你的钱留给你亲生儿子读书吧!
但没用,来年春上开学,母亲又会拿着扫帚把我赶去学校。
11
为了节省建房成本,暑假寒假,乃至每个周末,母亲都带着我和弟弟去屋后的花生地里捡火石头。这种石头呈白色,也有些呈褐色,石子碰撞会生出火花,所以叫火石头。
因为地里火石头太多,影响花生的收成,母亲很早就想除之而后快,现在让我和弟弟捡火石头,一来可以增加花生收成,二来又能给建房提供必需的材料,一举两得。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秋天,继父从工地上回家,准备在冬天来临之前,把新房建起来。那些天,每天下午放学,继父都会拉着一辆板车,带着我和弟弟去烟大岭公路边拖石头回家。
我和弟弟虽然觉得很累,但谁都不敢有怨言。
最终继父耗尽积蓄,还借了一屁股债,也只建起四间平房,两头各留一间瓦房,相当于我和弟弟一人两间平房加一间瓦房。继父说,平房里做饭不方便,留一间瓦房做灶房比较好。
因为建房子,家里出现了财政危机。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总是拖欠学费。但继父给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晚点交学费,让你们知道赚钱不容易,这样才会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
而我,赌气般地并不想读书考大学,因为那得花掉他多少钱啊,那得让母亲受多少气啊。我开始破罐子破摔,上课也不听讲,跟同桌一起看武侠小说。同桌家里有很多武侠小说,我们上课看,放学回家继续看,甚至晚上躲在被窝里还看。
我盘算着像村里的小伙伴们一样,初中走个过场,就出去打工。我觉得,在武侠世界里,打工就是闯荡江湖。
很快,这个机会来了。
12
1995 年秋天,我念小学六年级,我命运里的一个重大变故,正在悄然酝酿。
一天下午,班主任说,没缴清学费的同学全部回家,什么时候拿到学费,什么时候来上学。
全班60 多人,有十几员“大将”站了起来,这当然包括我。我们强憋着兴奋,收拾完书包,佯装一脸苦瓜相地走出教室。一拐弯,到了老师看不见的地方,一群人抛起书包,又叫又跳又笑。
书包扔得最高、笑得最放肆的,一定是我。
那是下午3 点钟的样子,我们的父母多数在地里干活,就算回家也拿不到学费;就算父母没干活,拿到学费,也要第二天上学才能交上去。
我提议去烟大岭打野鸡,烤着吃,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因为那会儿武侠电视剧里,经常出现大侠和女侠在野外烧烤。我们梦想当大侠,除了可以行侠仗义之外,多半也是因为可以在荒郊野外和女侠烧烤。
这种孤男寡女行走江湖的感觉想想都令人陶醉。
我们一行十多人,悄然潜行,像游击队穿过密林,以免被地里干活的大人们发现。潜行到山脚,我给大家安排任务。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在山腰驱赶,另一路去山顶包抄。这种法子,是从村里猎户那里学来的。其实,就算有野鸡或野兔从山腰逃窜到山顶,我们没有猎枪,仅凭石子,很难将之擒获。但很奇怪,同学们居然都听从我的安排,也许觉得新鲜刺激好玩吧。
那天下午,一辆小轿车从烟大岭山腰上的公路上滴滴滴地驶过来,我想吓唬一下他们,朝山腰扔了一块小石子,石子被一棵树挡住了,并没有落到公路上。不料,山腰处有位心有灵犀的同学,也扔出了一块石子。
很快,小轿车停下来,里面下来几个年轻人,他们一边往山上跑,一边大声吆喝:都给我站到,别跑!我的那些同学们就像小鸡见到老鹰,吓得腿都迈不动了。唯有我成为漏网之鱼。我逃跑的时候,被一个树桩绊倒,跌倒在茅草丛里。前面有座坟,我爬过去,躲在坟后。我看到那几个年轻人把山上的同学都赶到公路上。我躲在那座坟后,大气都不敢出。公路上,年轻人在大声呵斥:是谁扔的石头?!我听见有同学说是我扔的石头。我站在坟头大声说,不是我扔的,我扔的石头被树挡住了。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解释。
那几个年轻人把我打了一顿,然后押送我们去学校。学校让每位学生赔偿五十块钱,我是主犯,需要赔偿八十块。
那事之后,学校虽然没有开除我,但我趁此机会成功地退学了。
13
第二年正月十六,我跟继父和几个堂哥一起,去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包工头是我堂哥的小舅子,我喊他表哥,他看我年纪小,安排我开吊篮,这是工地最轻松的活计。不用吊篮时,我就去筛砂。
吊篮是老式的龙门吊,顶部有个滑轮,长长的钢丝绳穿过滑轮,一端连接吊篮,另一端连接50 米开外的卷扬机。卷扬机有两个把手,按着右边的把手,钢丝绳就一圈一圈地被吃进卷筒,从而通过顶部的滑轮带动吊篮上升,到达目的楼层,按下左边的把手,吊篮就停止不动。如果抬起两个把手,吊篮就开始下降。
这种龙门吊操作简单,但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吊篮要开到指定楼层,不能高,也不能低,否则吊篮里的斗车无法拉下去。一般人开吊篮,不是高了就是低了,楼上接车的工友就会大喊,“高了,再低一点”,或者“低了,再高一点”,我开吊篮很快就能做到一次到位,不高也不低。
包工头表哥啧啧称奇,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其实办法很简单,在钢丝绳上缠上不同的塑料作记号,只要记号抵达地面上某个位置,吊篮就刚好停在某一楼层,可以高个5 到10 厘米,这样方便将斗车拉下去,一定不能低几厘米,不然这样拉斗车有些吃力。别人开吊篮都要仰头瞄准,通常情况下仰头也不一定能瞄准,而我开吊篮不用仰头,盯着地面的钢丝绳就能做到。
我得意扬扬地一边跟包工头表哥聊天,一边表演我开吊篮的高超技艺。包工头表哥一手插在兜里,一手抚摸着被他剃得寸草不生的下巴,然后说,照这样来看,晚上也是可以开吊篮的喽?
我说,当然,别人晚上开不了,我能!
于是,每天晚上包工头表哥就要求我们几个堂兄弟,免费给他加班,把第二天要用的红砖连夜运上去,以免第二天因为运送物料耽搁时间。
我的几位堂哥对我一肚子火:就你能!叫你能!
大工们也怨声载道,以前缺点水泥砂浆或红砖,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竹排上休息,现在却有用不完的红砖,楼下的小工只负责搅拌和运输水泥砂浆,轻而易举就能做到供大于求。
这真的是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原本那一栋楼由我们湖北和河南两帮农民工施工。开发商希望两帮农民工比拼起来,这样施工进度会更快。结果我们这一半的工程进度很快,每层楼都提前两天完工,搞得河南民工看我们很不顺眼,两帮人还差点因此打起来。
因为河南民工施工进度慢两天,我们这边的活儿干完了,就休息两天。我利用这休息时间,去附近一家书店看书。那家书店的武侠小说不多,我就东翻翻西看看,最终看《平凡的世界》入了迷。
书店老板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退休语文老师,当他得知十四岁的我在工地打工,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要找我父母理论,读书的年纪为什么在打工?!
我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他问我学习成绩怎么样,我支支吾吾说语文还可以,数学勉强及格没好意思说。
他说,喜欢看书的孩子一定能考上大学,你回去继续读书,将来一定能上大学!
那年8 月,母亲托人带信,要我回家继续上学。一开始我不愿意,我觉得我这个开吊篮的高手,干工地有天赋。继父说,你不想上学,那就来学抹灰贴砖,当小工是没出息的,早日学会早日当大工,大工工资翻倍。
抹灰我一学就会,但贴砖,特别是贴踢脚线,就有点复杂。在毛坯房打地坪之前,先依照水平线在墙脚十几厘米处,打好墨线,然后沿着墨线,在上方贴一溜12厘米高的瓷砖。别人贴踢脚线,刚好和墨线对齐,我贴的几块,总是往下滑,压住了墨线。贴了半天踢脚线,成功的不到十块,其余的全部要返工。包工头表哥还因此骂了我一顿,甚至扬言要扣我工钱。我开始对自己干工地的天赋产生了怀疑。
继父说,你不是干这块的料,还是回去上学吧。
很多年后,我把老家继父盖的六间房推倒,起了一栋小别墅。继父在贴踢脚线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动手贴了几块,发现贴得很完美啊。继父一笑,说,当年是我故意把水泥灰和稀了一些,这样贴的踢脚线在墙面粘不牢,就会往下滑。
我才知道,原来他那时是想逼我回家上学。
14
重读小学六年级,我跟弟弟成了同班。我上课没再看武侠小说,天天都专心听讲,甚至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都在温习功课。我觉得跟弟弟同班,如果成绩比他差,就太丢人了。结果就这么认真了几个月,我的成绩突飞猛进,数学题基本没有不会做的,经常考100 分,偶有疏忽才会跌到99 分,语文成绩也很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念。只过了半学期,我就被同学们推选为班长。
一个学期后,家里就贴满了我的奖状,有总分第一名、单科第一名,还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等。母亲很为我高兴,仿佛我中了状元。
我的命运,走了一段弯路,又回到正轨上来了。
多年后回首往事,假如我没有去打工一年,继续混到初中,我还能考上大学吗?可能像我弟弟,初中二年级就退学打工去了。后来继父也想依样画葫芦,让弟弟回来继续上学,但是小学的基础没打好,重读初中,还是跟不上。所以,在小学六年级这个关键节点,我退学打工,又回来重读,为我的人生起到一个柳暗花明的转折。
不过,弟弟后来混得还不错,在广东打工十几年后,一步步从小组长成为工厂主管,现在已升为一厂之长了。有一年,我们在年夜饭上谈论往事时,他说,如果有学历有文凭,他会晋升得更快,上限也会更高。
而我,经过多年的奋斗,现在混得也还不算差。回老家建别墅的那个秋天,母亲让我带着镰刀去烟大岭。我问去搞嘛事,母亲说到了就知道。那时的烟大岭,就像一个秃顶的老人,记忆中的树木被砍伐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油茶。这是一种经济作物,然而却疏于管理,万亩油茶被茅草占领。枯黄的茅草,像极了母亲花白的头发。
母亲来到一座坟前,她说,这是你伯的坟。你现在有出息了,我也有脸面带你来见他。
我想起那年在烟大岭打野鸡,我曾躲在这座坟后,那时还不知道,原来这座坟里,埋葬的是我父亲。
母亲坐在父亲的坟前,诉说着往事,讲起当年她就是翻越烟大岭才嫁给我父亲的。只是当年那条小路,自打公路通车后,已人迹罕至,如今已被茅草覆盖。
母亲讲着讲着,就开始抹眼泪。我背过身,弯起腰,挥舞镰刀,割起坟后的茅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