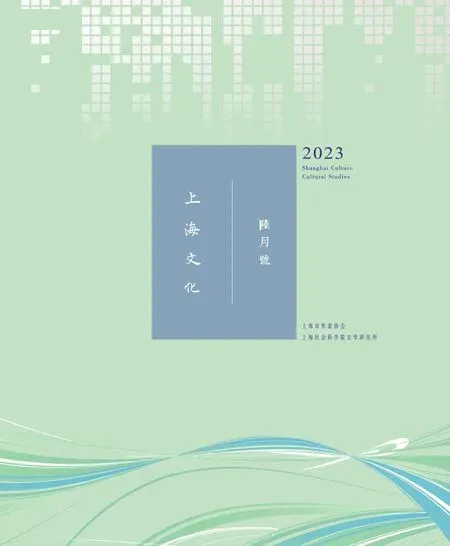海派钢琴音乐文化的建构历程及传播路径
——以《申报》为线索的讨论
2023-09-11朱昊冰
朱昊冰
一、《申报》与上海钢琴艺术的历史
对于钢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关于钢琴在近代以来的“传进来”与“走出去”,即钢琴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如何再传播至海外方面的研究。具体而言,对于钢琴传入中国的过程,通常的论述模式都会将此置于“全球化”的框架之下。发端于欧洲的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重要的现代乐器——钢琴的产生与演进,也让全球跨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正是在17至18世纪的全球化初期,钢琴来到中国,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从清朝时期中国出现古钢琴,到钢琴音乐在抗战时期走过的历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呈现出的繁荣景象,有研究者基于以上长时段的综合比较,将中国钢琴文化的特点概括为:大众性、审美世俗性和跨地域性。①陈瑾:《我国钢琴文化的现代传播》,《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4期。
如果把视线进一步聚焦到沿海口岸城市,会发现这里实际上蕴藏着钢琴音乐与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的基本模式。教会学校、学堂乐歌促进了钢琴音乐与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从而加快了城市阶层的分化进程。与此同时,钢琴艺术也与本土传统的教育、音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结合。例如,有研究者探讨了钢琴音乐在福州的传播案例,认为钢琴对福州城市的社群结构产生了影响,因为一部分女性因钢琴而接触到西方音乐和新文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钢琴的使用也与福州本地的传统音乐有了初步的融合。①参见王玮立、毛波:《清末福建钢琴音乐的萌芽与发展》,《兰台世界》2014年第36期;廖红宇:《20世纪上半叶钢琴音乐与福州城市音乐文化的变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钢琴在福州的传播和发展体现了钢琴音乐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的特点。目前研究对钢琴传入中国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同时也关注到钢琴作为西方乐器“在地化”的过程,以及相关的城市和代表人物。但总体来说,对于钢琴艺术在中国传播问题的研究还较为宽泛,对钢琴本身区别于其他西方乐器的特点关注不足,对特定城市和地域中(尤其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市和地域)钢琴音乐作为“文化”的发展历程的研究还比较少。
具体而言,在上海——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钢琴艺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其特殊性又体现在何处?本文将上海的钢琴音乐文化置于“海派文化”的场域中,回应海派钢琴音乐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建构起来的问题。
《申报》关于钢琴的记录,最早见于1890年12月17日的一则“全利广洋货公司”的广告。③《全利广洋货》,《申报》1890年12月17日。之后的59年里,《申报》刊登了大量与钢琴相关的报道。据笔者分类统计,其内容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团体活动中使用钢琴的新闻报道;(2)关于钢琴的商业广告;(3)文学作品、电影、广播中对钢琴的描述;(4)宗教活动及场合中的钢琴音乐;(5)专业钢琴音乐教育方面的报道;(6)钢琴演奏会的相关信息。另外,报道涉及的社会群体主要为:学校师生、商界、租界工部局、宗教界等。
通过这些史料信息,我们不仅可以窥见中国钢琴音乐的早期传播路径,还能了解与近代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背景相伴的大众生活娱乐及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此外,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持续呈现的器物文本以及相关的人、事、物,我们发现,钢琴已经超越了乐器本身的独立意义,而体现出一种特定的身份和文化的建构。
二、钢琴文化在上海的起步:欧洲侨民的引入与华洋接触的渠道
作为西方音乐重要的乐器,钢琴与宗教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个特点也体现在钢琴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基督教进入中国后,钢琴是宗教活动中最为常见的伴奏乐器之一。最早可追溯至明代万历年间,当时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就将古钢琴带到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引入本是为在华传教士传播宗教的目的服务的,然而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钢琴艺术也在中国传播开来了。①靳昊:《乱花渐欲迷人眼——论利玛窦的跨文化音乐传播》,《人民音乐》2014年第11期;李明静:《宗教信仰与钢琴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这些在华西方传教士以及欧洲信教的侨民在宗教活动中使用钢琴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使中国人有了接触钢琴及西洋音乐的机会。
教堂和教会学校是钢琴使用最多的场所。建立教堂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教堂也成为那些“异乡人”寻求精神寄托和集体认同的重要场所。上海是中国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聚集于此的传教士人数较多,城市中也有多处教堂。每逢周末教堂做礼拜时,演唱圣诗、圣歌,往往需要用钢琴作为伴奏乐器,钢琴乐声由此便在上海奏响。比如《申报》上就记录了在虹口南浔路天主堂的弥撒中,教民们的诵经声和洋琴(钢琴)的演奏声相伴的场景。②《教堂弥撒》,《申报》1899年6月9日。另外,传教士还热衷于兴办学校,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城市就涌现出许多教会学校。在这些学校中,钢琴是一种新颖而富有吸引力的教学设备。例如1881年,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就添置了一架钢琴和两架风琴,日后又因课程扩容的需求,增补了若干架钢琴。③《圣玛利亚女校设琴科》,参见孙继南编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8页。传教士林乐知、海淑德于1892年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同样设有钢琴课程,以及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琴科”。④陈晶:《中国近代女性音乐教育的先锋——上海中西女塾音乐教育研究(1917—193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尽管这些传教士的教学内容和技能未必十分“专业”,但还是培养了一批对西方音乐感兴趣且有基本知识储备的青年,其中不少人有早年在教会学校受到“启蒙”的经历后又留学海外,为中国更长期的钢琴音乐教育和传播事业培养了最初的人才队伍。⑤汪毓和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这种宗教与音乐相叠加、相融合的传统,直到民国时期依旧是钢琴在上海被使用和传播的重要特点。除每周固定的教堂礼拜需要用到钢琴伴奏之外,《申报》还频繁地对当时在上海开展的基督教庆祝活动进行报道,如自1916年开始,常见有“耶稣诞生日之庆祝会”“基督教勉励会”“基督促进会之游艺会”“基督教大学同学大宴会”“夏令营同乐会”等多种庆典和集会。在这一系列仪式和庆典活动中,大多设有“钢琴合奏”“钢琴独奏”的环节,⑥《基督教会勉励会今晚开会》,《申报》1918年8月1日。也经常出现“甚为优美”“颇为精彩”等称赞词,反映了上海城市听众对钢琴音乐的欣赏和喜爱。当时,每次的宗教活动必有钢琴演奏。就这些活动的名称、形式和规模来说,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活动远比明代更为丰富和盛大。在华洋接触的初期,钢琴与其他的西方器物和知识一起,随着传教活动的发展,逐渐为上海民众所了解和喜欢。
除了传教活动之外,外国人在中国的其他社会活动也促进了钢琴在中国的传播。许多团体和个人在上海举办的钢琴音乐会,不仅为在华侨民进行表演,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同时也让钢琴乐声超越了宗教的范畴,为更多的人所听闻。
上海的各类演出场所和演出活动在晚清时期已初展风采。据《申报》载,1874年,英国著名女钢琴家亚拉白可大(Arabella Godard,今译为戈达德)在上海大戏院举办专场演出。①《英国著名女乐至上海演戏略》,《申报》1874年4月7日。有关此次演出的记录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这并非完全因为这场演出本身的质量有多高,或其关于是否能配得上“近代以来第一场由职业演奏家带来的演出”的先锋地位的讨论,②张凯:《略论晚清钢琴普及概况》,《北方音乐》2018年第10期;榎木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赵怡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3—14页;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而是因为这次演出得到了《申报》这样的中文媒体报道的“特殊地位”。因为晚清时期“钢琴记录”的主流载体仍然是英文报纸,阅读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在华西人。所以,偶尔有中文媒体刊发此类消息,即使消息源是转载和翻译的,也备受瞩目。另外,既然谈到了媒体与钢琴音乐传播的关联,就不能不提到上海字林洋行发行的日刊《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及其周刊版《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对于当时外国人在上海的钢琴演奏活动的翔实记载。③以这两份英文报纸为史料基础,可窥见钢琴在晚清上海传播的诸多特点,此宜另撰文详述。它们不仅刊布音乐会的日期和演出内容,还会详细地介绍演出者的国籍、行程和钢琴技艺等“扩展信息”。报纸编辑部更乐于充当乐评人,对每次音乐会给予细致而专业的点评。由此,媒体也构成了上海钢琴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对国家电投江西电力公司、福建华电集团、国家电投江西水电检修公司等进行毕业生跟踪调研,卓越班培养的学生在企业中的适应能力更好,毕业生成长速度明显加快,涌现出一批有实践能力、懂技术、善管理的人才,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三、钢琴文化在上海的推广:专业教育与社会演出的繁荣
至民国时期,钢琴在中国的传播变得更加广泛,影响的群体范围也更大。这与辛亥革命推翻了旧制度的时代背景也有一定的关联: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观念逐渐变得开放,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④李喜所、刘集林:《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钢琴作为西洋新文化的典型代表,见证了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申报》对这一时期钢琴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推广,有大量的记载和报道。从中可见,钢琴艺术已不再局限于教会学校和教堂等应用场景之中,而开始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
钢琴艺术的传入与上海本土其他学科的教育教学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晚清时期,已有学堂开始开设钢琴课程,进入民国以后,这样的现象变得更加常见。一些学校在举办庆典或放假期间,不少学生会弹奏钢琴来表达愉悦的心情。崇德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也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在该校1915年的恳亲会上,学生们带来了一场钢琴独奏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⑤《崇德女校开恳亲会》,《申报》1915年4月11日。1920年东吴大学法科毕业典礼上,中西女塾的邱贞爱和俞素青分别进行了钢琴独奏。①《东吴大学法科举行毕业礼纪》,《申报》1920年6月25日。除了国立音专这样的专门院校,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东南大学、南洋大学等学校的典礼活动上亦有钢琴演奏的出现,有的学校甚至还举行钢琴比赛。②《沪大筹备钢琴演奏竞赛》,《申报》1948年3月29日。除中学、大学外,盲童学校、幼稚园的表演会中也出现了钢琴。从演奏者的身份来看,师生均有。例如在盲童学校,进行演奏的是学生。部分盲童“手指敏捷,琴声清澈”,在音乐演奏中表现出一定的天赋。③《盲童学校同乐会纪》,《申报》1920年4月11日。在一些常规学校举办的庆典活动中,钢琴的表演者多为该校学生,形式为独奏或合奏;有时演奏者则是学校的教员,如在徐汇公学第十届毕业典礼上,“由校长翟公奏钢琴”,圣芳济学校在筹备扩建校舍的宴会上由一名教师演奏钢琴数曲。④《各学校消息汇纪》,《申报》1921年7月3日;《圣芳济校筹备扩建校舍宴纪》,《申报》1922年7月27日。1937年1月《教育简报》记载:“本埠南市大东门外紫霞路普益成年女子补习学校,由基督教普益社附设,现有学生近百人,分国文、英文、钢琴等,三午后授课三小时,为成年失学或因家事不能入普通学校者求深造之所。”⑤《教育简报》,《申报》1937年1月10日。到1940年,基督教青年会推动“一技运动”,在学生暑假期间举办各类技艺培训班,不仅有化学工艺等“实用技能”,也包括钢琴班这样的艺术技能。除正式的宗教活动之外,教会学校或有宗教因素的机构开设钢琴课程并进行双语教学,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也说明钢琴艺术已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
民国初期,学校范围内对钢琴演奏和钢琴课程的推广,主要受到教会的影响以及江苏省教育会的推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钢琴的演奏者并不局限于专业钢琴家,很多演奏者是学校的教员与学生,从另一侧面说明钢琴在近代上海新式学校中的传播是广泛而深入的。20世纪40年代之后,上海诸多学校开设的钢琴课程,不仅介绍钢琴的历史、教导如何弹奏钢琴,还进一步教授制造钢琴乐器的技术,为中国的钢琴制造业进步提供助力。这也反映出钢琴的普及化,已然从“远在天边”的高级乐器,成为“近在眼前”的一件寻常器物。
民国时期,有共同兴趣或共同建设目标的团体集会变得日益频繁,各类联谊会、音乐会、读书会、体育竞技会、恳亲会等时常举行,借以联络和增进团体成员间的感情,既陶冶情操,又可集体商讨要事。在这些活动中,钢琴演奏是十分常见的助兴节目。例如1907年商学两界共同举办“上海禁烟大会”,在此次大会上就有“奏风琴,各学生合唱庆祝歌”的环节。⑥部分报刊的活动报道见于:《青年会演剧助账志盛》,《申报》1911年6月2日;《尚贤堂之西国音乐会》,《申报》1913年6月4日 ;《寰球中国学生会开会纪》,《申报》1915年12月17日 ;《女界交谊会纪事等》,《申报》1917年2月8日。报纸对1911年之后30余年时间内的多个社会团体开展活动都进行了报道,其中有涉及钢琴演出的就超过200篇。
民国时期的这些社会团体的活动,逐渐成为推动钢琴在华传播的新兴力量。钢琴在这些团体活动中,或以独奏的形式“唱主角”,或以伴奏的形式“做配角”,但钢琴始终是这些集会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些社团如寰球中国学生会、中国青年会、上海青年会、公教服务团、华光社等,其成员人数众多,且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将钢琴音乐从口岸城市传播至全国,从而更广泛地影响中国各地的民众。比如,1905年9月,中国寰球学生会在苏州河礼堂举办音乐会,“节目包括合奏洋风琴”;1915年,寰球中国学生会举行江苏省教育会体育传习所的学员欢迎会,会上有钢琴独奏表演;1916年12月,寰球学生会举办新成员欢迎大会,其中一项流程就是由郭志超进行钢琴独奏的表演。①《寰球学生会欢迎新成员》,《申报》1916年12月9日。又比如,1918年,寰球学生会举行演说会,教育次长袁观澜到场,由金永清表演钢琴独奏;次年,寰球学生会在举行华侨学生恳亲会时,再次邀请金永清、江贵云演奏钢琴;②《寰球学生会演说会纪事》,《申报》1918年9月21日;《寰球学生会之华侨学生会》,《申报》1919年2月4日。1921年、1923年有该会主席出席的重要宴会上也有钢琴合奏的节目。③《寰球学生会年宴之秩序》,《申报》1921年3月3日;《寰球学生会今晚举行年宴》,《申报》1921年3月5日;《寰球学生会宴会纪》,《申报》1923年10月28日。在重要会议和各项庆祝活动中将钢琴演奏作为固定节目,并不是寰球学生会所独有的,其他类似的学生界和工商业界团体如女青年会、留美同学会、普益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就形式上来说,社会团体的活动有助于钢琴在上海的传播。一部分社会团体更是将钢琴演奏的节目视为重大活动的必要环节,这也体现出学生、知识分子和商人群体对钢琴音乐的接纳和重视。钢琴演奏带来的不仅是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体验,而且还有现代的、文明的和进步的生活方式。
民国时期,各位来沪音乐家常常在公共场所进行演出活动。歌舞大会、音乐会和赈灾演出中多有钢琴独奏,钢琴艺术在音乐演出中大放异彩。《申报》的报道,既有对活动的整体宣传,也会对部分节目单独着墨:“所奏各种音乐,俱以工部局音乐队和之。个人之奏曲,则有范拉锡夫妇之独奏,奏乐则有福奥君之胡琴与璧旦女士之钢琴,尤以璧旦女士之钢琴独奏最能引人入胜。声浪高时霹雳惊人,低时宛转尽致。奏毕,即有人赠以花篮,以示钦仰。”④《筹赈俄灾之音乐会》,《申报》1922年3月3日。这里,作者运用华美的汉语,对当时音乐会钢琴独奏之引人入胜的场景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绘。相比于晚清时期《点石斋画报》《北华捷报》等报纸对于钢琴的记载和描绘,《申报》的篇幅往往更多,语言也更生动、通俗,同时也包含更多的主观情绪和态度。到了20世纪30年代,《申报》不仅报道相关的演出活动,还会以系列文字的形式对诸如“法国女钢琴家来沪”以及“法国女钢琴家在沪表演及演奏活动及效果”等事件进行跟踪报道,有时也会写专稿介绍国内部分有名的钢琴演奏者。由此可见当时钢琴演出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受欢迎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很多演出还带有筹款赈灾、助童、办学等慈善因素,钢琴演出是这类慈善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亮点。这种相得益彰的特点为钢琴艺术的传播增添了动力,上海广大市民的艺术审美需求也因此得以满足并不断提升,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机制。
早期由外国侨民组成的艺术团体对于钢琴音乐在上海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上海工部局乐队是最具代表性的。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前身是上海公共乐队,它由外国人创办,乐队成员均为外国人,只负责在租界区域内为外侨演出。1881年,意大利音乐家韦拉(Melchiorre Vela)被任命为乐队指挥,他开始接受租界娱乐基金的资助和管理,并由工部局编列预算,乐队从此开始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1900年,上海工部局正式接管该乐队。①上海工部局乐队是近代音乐史上研究比较深入的一个案例。相关的专著就包括榎木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年。乐队早期演出的报道,主要载于《字林西报》等西文媒体,向公众介绍乐队定期举办的音乐会。1919年,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Mario Paci)开始担任乐队指挥,这对于钢琴在乐队内部的作用以及钢琴在华广泛传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海派钢琴文化的生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伴随外国人在上海的传教活动和社会演出活动的兴盛,以及钢琴作为一种乐器的普及,钢琴艺术逐渐融入了上海各社会阶层,尤其是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之前,因钢琴自身体积过大,单价偏高,所以天然就带有一种“贵气”,而且钢琴表演活动主要流行于社会较高阶层,所以购买钢琴、学习钢琴和演奏钢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随着钢琴艺术的逐渐推广,作为西方重要乐器的钢琴,带给上海市民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乐器的全新审美体验,在演奏钢琴时传导出来的震撼性和表现力,极易激发受众的多维情绪。因而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对钢琴艺术产生了喜爱之情,并以此寄托自己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愿。为了满足这些渴望享受“体面生活”的新市民的心理需求,以及教堂和教会学校原本就有的刚性需要,上海等“中西交融”的前沿城市陆续开设琴行,销售小提琴、钢琴和风琴等西洋乐器。这些琴行善于借助在当时较为流行、影响力较大的《申报》和《点石斋画报》等媒介进行商业宣传,比如刊登销售和拍卖钢琴的广告、钢琴演出的预报、以钢琴为奖品的抽奖活动的宣传等。民国初年,《申报》上关于出售、转卖钢琴的广告逐渐增多,而且开始强调不同品牌与款式的钢琴的各自优点,实现更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竞争”。②《新到偕士倍克之八十八音钢琴》,《申报》1916年3月29日。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款式更加新奇、更便于使用和普及的桌上钢琴,成为百货公司招揽顾客的“王牌产品”,并在《申报》上占据了更多的篇幅。③《最新发明桌上弹琴桌上钢琴》,《申报》1925年9月18日;《最新发明桌上弹琴完全国货音乐明星》,《申报》1925年9月26日;《最新发明桌上弹琴首先发明桌上钢琴》,《申报》1926年3月15日。通过这些媒介刊载的与钢琴相关的商业广告可知,实际上原先只属于上层社会的对于钢琴的兴趣和需求,已经开始扩展到各阶层的民众之中,钢琴消费与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联系起来。
随着商业消费需求的提升,钢琴在上海本地的生产制造也日益发展起来,相关业务也不断拓展。稍向前追溯,大约在1895年前后,英商的谋得利琴行(此琴行由创办人Moutrie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作为最早在上海开业的钢琴销售公司,首先研制和生产出上海“地产”的第一批钢琴。尽管各种关键的零件和原材料仍依赖进口,真正能在中国境内完成的只有零件组装环节,但迈出这一步也是很有创新意义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参与到了钢琴组装生产的过程之中。中国的本地工人原先对钢琴的构造完全是一窍不通的,在谋得利公司的精心培训之下,他们渐渐成为合格的专业工匠,还受到了前往该公司采访的英文报纸记者的夸赞。①Messrs. S. Moutrie & Co.’s Piano Factory,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97-11-19.且不论这种夸赞背后可能隐含的某种歧视与怀疑论的预设,但至少说明和证实了中国人也有能力参与钢琴制造。这种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将来中国人独立自主的钢琴制造事业奠定了基础。②今天的上海钢琴有限公司,正是在这些中国工人开办的钢琴制造小作坊、小企业的基础上合并改建而来的。详见郑晓丹:《中国钢琴教育发展史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7页。
正是社会的接纳和需求催生了生产钢琴(琴厂)、销售钢琴(琴行)、钢琴修理商等众多配套产业和职业。③钢琴修理未必能成为一项单独业务,但也属于部分制造业企业的业务范畴之一。见《九华制造厂兼修理乐器》,《申报》1925年10月7日。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钢琴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普及。1920年以后,《申报》上招聘钢琴琴师和相关从业人员的招聘信息也多了起来。④《聘请钢琴琴师》,《申报》1921年7月31日;《上海东方钢琴有限公司开幕露布招聘启事》,《申报》1924年7月26日。钢琴艺术是一种陶冶情操的兴趣爱好,钢琴的生产、销售、维修也成为一部分人谋生的职业技能。至少就这群人的感受而言,钢琴与他们生活的关联性大大增强了。
在这些“直接证据”之外,还有一些有趣的“旁证”也能说明钢琴与市民生活的关联和普及程度。例如,《申报》上出现的有关“钢琴保养方法”的科普信息,很值得引起注意。1917年2月28日,《申报》刊登了一则以“家庭常识”为主题的文章,列举了数条家庭日常生活中所需用到的基本知识和“小妙招”。有意思的是,“防止钢琴生锈”也位列其中:“批爱拿(piano,即钢琴)内部之金属机关日久恐有锈坏之虑,若以极干之石灰盛小囊中,安置内部,时时更换,则其机关可保不锈。”⑤《家庭常识》,《申报》1917年2月28日。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是一方面,报纸编辑将其视为一项“家庭常识”,认可报纸的读者中一定会有人需要了解这项“常识”的事实本身,恰恰证明了钢琴能够被当时的上海市民家庭接触到。或许正是因为市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样恰当地使用和维护这件“新物件”,才不敢轻易下手尝试,所以才需要将这样的“常识”和“好方法”通过报纸介绍给公众。类似的介绍并非个案,《申报》上还有另一则消息专门讨论了钢琴的“保护方法”:“欧风东渐洋琴(指钢琴与风琴)渐成为家庭一种娱乐品,我国解抚之者近亦颇不乏人。惟琴价颇昂,苟不求所以保护之良法,则经济上之损失甚巨,故译此篇以备用琴者之参考焉。”⑥《钢琴与风琴之保护法》,《申报》1921年3月15日。这篇文章的作者开宗明义地承认钢琴“渐成为家庭一种娱乐品”的社会背景与普遍风气。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广泛应用”的基础,才有在家庭生活中养护钢琴的必要与可能。
民国时期,不仅有关钢琴的商业广告开始出现,亦有类似音乐研究会的社团组织开始招募成员,以及西方的钢琴家来华访问指导等信息出现。20世纪20年代,上海音乐研究会就多次在《申报》刊登消息,招募学员参加暑假补习班和常规课程,其中教授的科目就有钢琴、风琴、音乐理论等。①《上海音乐研究会消息》,《申报》1922年7月4日;《音乐研究会消息》,《申报》1922年9月14日;《音乐研究会之征求会员》,《申报》1923年3月9日。1927年5月21日,由音乐家张若谷、谭抒真、潘伯英等组织发起的上海音乐传习所,也同样教授提琴、风琴、钢琴、声乐和音乐理论,亦招募学员。②《上海音乐传习所之发起》,《申报》1927年5月21日。同年9月至11月间,外国音乐家勃兰(Brain)等人来到上海,他们都具有欧洲的艺术教育背景,寓居沪上期间,招募学员以面授钢琴音乐等课程。③《音乐家勃兰来沪》,《申报》1927年9月22日;《各团体消息》,《申报》1927年10月20日。从这个层面来看,此时钢琴在上海的传播已经具有一定的普及度,不再局限于教堂、学堂,而是逐步渗入市民日常生活之中。
钢琴与日常生活融合的另一个典型场景,就是婚礼。如1919年8月31日的《申报》,记录了一对璧人的订婚宴场景。宴会上,新娘“独奏钢琴”,伴其他宾客歌唱以欢度时光。等到“散时已钟鸣十一下矣”。④《刘大钧与金永清订婚》,《申报》1919年8月31日。⑤《南国社访问记》,《申报》1926年12月8日;《新春同乐记》,《申报》1927年2月14日;《新婚曲》,《申报》1927年3月19日;《巧筵记》,《申报》1927年8月7日。这虽然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案例记录,但却很能够说明钢琴为市民生活增光添彩、提高幸福感的重要功能。
民国时期,钢琴也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除了聆听钢琴、演奏钢琴和观赏钢琴,有人在欣赏钢琴演奏之后,还将这种审美感受真实地记录下来,融入生活化和纪实性的散文之中。举例来说,《申报》在1927年前后就刊载了《南国社访问记》《新春同乐记》《新婚曲》《巧筵记》等多篇描绘或涉及钢琴的散文作品。⑤在这些作品中,钢琴成为烘托环境气氛或人物心境的元素。更有甚者,索性把钢琴作为小说创作的标志意象之一,以文学性的语言将钢琴的曲调和表演者的形象展示在读者眼前,充分发挥其高贵、华丽、新潮、洋气的象征意义,使原本基于虚构的小说增添了几分感觉上的“真实性”与“可信度”。⑥如《心上温馨(十)》,《申报》1930年4月7日;《欢乐与悲哀(五)》,《申报》1932年7月18日。此外,一些评论性散文作品还会以著名音乐家为主要对象,或介绍人物生平,或以人物为线索,寓“说理”于“叙事”。如1926年9月4日的《关于音乐的谈话》一文,以贝多芬为例,意图说明钢琴与西方音乐、作曲能力的密切关系,展现音乐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⑦谭抒真:《关于音乐的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有趣的是,《申报》上另一篇同时提及贝多芬和钢琴的文章,更以《恋爱狂贝多芬》为题,讲述“文艺家的故事”,无论故事的真实性几何,总令读者丰富了有关西方音乐的见闻。⑧《文艺家的故事(二)》,《申报》1930年5月24日。
有时演奏钢琴的画面也会出现在“大荧幕”上,观众在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就能从影片中感受到钢琴乐曲的艺术之美。另外,随着广播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进入人们的生活,有较多的音乐节目是通过广播的形式向人们宣传推广的。这样一来,观看现场表演和收听广播相辅相成,为人们了解钢琴音乐、欣赏钢琴乐曲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渠道。
正如熊月之所言:“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的国际联系,指的是上海与英、法、美、德、俄、日等国家及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一类是内嵌式的国际联系,指的是经与上海租界内各相关国家团体、个人发生的联系,进而延展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①熊月之:《上海城市的国际性与中共的创立及早期发展》,《世界历史》2021年第2期。钢琴艺术在上海的传播,同样很好地体现了这两种不同的国际联系,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包容性是它的宝贵特质。上海的钢琴音乐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将钢琴固有的高雅属性与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市民精神结合起来,就像一条河流汇入大海那样,最终形成了与总体海派文化相一致的“中西融合、雅俗共赏、海纳百川”的特质。通过以上的历史梳理和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上海的钢琴音乐文化得益于广阔的海派文化的天时、地利、人和,它自身又是丰富厚实的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
综上所述,钢琴在上海的传播方式及受众接受过程体现了钢琴艺术的社会性。其涉及的社会文化活动和大众消费,同整个城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成为市民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它的传播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在此过程中,尤其应当注意到上海这座城市及其孕育的海派文化,赋予了适宜钢琴这颗外来“种子”在中国本土扎根生长的理想土壤。
总结来说,海派钢琴文化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有以下四大原因:
第一是历史环境因素。上海的较早开埠,为西方的宗教、器物、音乐等舶来品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盛与现实需要,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留学人员回国后积极倡导效仿西式生活图景,加之市民们本就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需求,共同促使钢琴这种艺术兴趣和文化形态从侨居的外国人到一般市民群体的扩散传播。
第二是宗教因素。早期传教士为了传教目的,透过教堂仪式及教会活动,在顺应当时信教人士的需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钢琴文化引入了上海。而且上海早期的新式学校多为教会所办,宗教、钢琴艺术与教育由此结合起来,后又逐渐为其他学校所仿效和引进,钢琴教育成为培养学生艺术素养与人格健全发展的方式之一。
第三是经济、技术的聚集因素。因为上海对外开放的环境,加上相对发达的经济水平,吸引了众多海内外人才,反映在钢琴相关领域,从设计、制作、生产、交易,到教学、培训、表演等各方面都具备了相当的人才优势,不断递进式地推动钢琴的普及。
第四是钢琴艺术自身的因素。相对于中国传统乐器而言,钢琴作为西方主要乐器的代表之一,带给受众一种新鲜的审美体验,它的震撼力和表现力更易激发受众的多维情绪,因此受到市民的普遍喜爱。不仅如此,钢琴也是现代音乐文化传播中重要的器物媒介,具有古典与现代兼容的魅力,符合现代文明的特征。
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与积淀,钢琴在当代的上海乃至全中国范围内,早已不再是少数西人自娱和专享的道具,而是以各种方式融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尤其是成为许多少年儿童接触音乐的“启蒙老师”。这固然与钢琴在诸种乐器中具有的基础地位有关,但结合钢琴在近代上海的传播历程,仍然不难发现这得益于钢琴传播始终注重教育、注重平民化、注重新事物和新技术与传统素材之间的平衡关系的特征。这一点也正契合学者对于中国当代钢琴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①被誉为“这40年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曲家脑海中最中心的艺术课题”正是“如何在现当代作曲观念和技法的语境中,以钢琴为媒体去深入地表达‘民族性’和‘中国性’”。这一问题自钢琴最初传入上海之日起便已开始酝酿,时至今日终于有了若干种比较成熟的回答方式。详见杨燕迪:《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音乐研究》2019年第4期。也反映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新旧融合”“中西合璧”的历史特点,同时这又是上海这座城市及其崇尚多元、兼容并包的海派文化气质所赋予钢琴的艺术魅力与生命力的源泉。在当今及未来的中国钢琴音乐传播之路上,坚持本土传承性、开放吸收性、创造开拓性相结合的特点与优势,是使得钢琴能够更加普及、更加为人喜爱,并在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中更富突出价值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