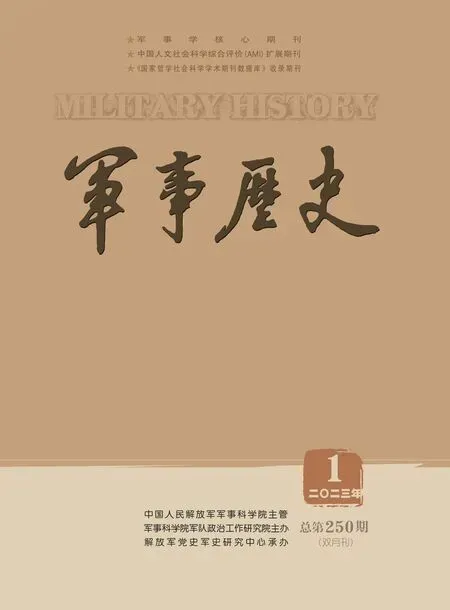论元末明初的兵学革新和局限
2023-09-10武鹏飞
★ 武鹏飞
元末明初,大致指元顺帝即位(1333)至明成祖逝世(1424)之间的历史阶段。它是中国古代兵学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次高潮过渡的关键发展时期,①刘庆:《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次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97 年第4 期。在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火器技术的发展与元末明初的兵学革新
宋元时期,中国南北之间乃至东西方之间经济、科技、文化的频繁交流,带来了社会生产的巨大变化,以火药、火器为代表的军事技术亦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元代中期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金属管型火器,被视为热兵器开始全面应用的重要标志。②熊剑平:《明代火器技术的发展与古典兵学的变革》,《军事历史》2021 年第6 期。元末明初,火器装备在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优化,并广泛地运用于作战实践,而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化,也正式确立了冷、热兵器共用这个新的战争形态。
(一)战术、战法的革新。北宋时期,火器对战术的影响较为轻微,南宋至元代中叶仍影响不大。此后,随着火器数量、种类的增多和战斗性能的改进,战术变化日益显著。元末明初,火器装备的大量使用不仅推动着步、骑、水、炮等兵种协同战术的革新,而且为了突出其杀伤效能,还专门为火器制定了特殊的战术战法,表现为火器对这一时期战争胜负贡献值的不断上升。这种演进和变化的过程虽鲜见于专业兵书,却在史籍记载中一览无余。
一是水战战术从传统的接舷、撞击、跳帮向重视发扬火力转变。中国疆域广阔,南北地貌差异巨大,“南水北马”是对南北作战形式差异的经典总结。先秦以降,水战中虽不乏火攻歼敌的先例,但碍于其严苛的触发条件,传统水战仍以接舷、撞击、跳帮等战法为主③接舷战是指战船以舷侧靠近敌船舷侧,通过近距离厮杀决出胜负的战法,通常战船高大的一方能居高临下地使用冷兵器,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发挥武器的杀伤效能;撞击战是把敌船撞破或撞沉,使其完全丧失战斗力的战法,为了提高撞击的效果,当时的军舰首尾都装有坚硬的金属撞角;跳帮是指通过跳板、荡索或直接登船方式,与敌方船员进行白刃格斗。参见唐志拔:《中国舰船发展史略》,《船海工程》1990 年第5 期。,如晋灭东吴、隋灭陈朝等均是凭借强大的水军优势以及步水协同取得胜利。元明时期,燃烧性、爆炸性、射击性火器大量出现,不仅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火攻触发条件严苛的先天不足,而且具备射程远、威力大等方面的客观优势。在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军出动“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④[明]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第4 卷《汉陈友谅》,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103 页。等各式火器装备,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出于焚烧陈友谅军巨舰的需要,还临时创制了燃烧性火器“没奈何”。①参见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明代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66 页。战时,朱元璋命舟师分为20 队,采用疏散阵型充分发挥火力优势,而后“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②《明太祖实录》卷12,癸卯年七月丁亥。。其中,火枪、火铳等属于单兵装备的手持火器,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等属于管型较大的射击类武器,“没奈何”则属于燃烧性武器,加之弓弩、短兵器的投入,冷、热兵器在空间上形成清晰的杀伤面和覆盖层。与此同时,通过热兵器来提高对敌作战的杀伤力,用冷兵器来弥补热兵器在射击精度和击发速度上的不足,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杀伤效能。
二是野战战法加入了炮兵与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新内容。洪武末年,沐英率军镇压云南叛乱时,曾下令在军中置火铳、神机箭,分为三队,“俟象进,则前行,铳箭俱发,若不退,则次行继之,又不退,则三行继之”③《明太祖实录》卷189,洪武二十一年三月甲辰。。大抵此后,有明一代的野战战法均逃不出“置火铳、神机箭,分为三队,轮番射击”的主体框架。永乐时期,火器装备进一步运用于野战,如安远伯柳升“将神机火器为前锋,大败阿鲁台,进封为侯”“将大营兵战忽兰忽失温,以火器破敌”④《明史·柳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4236 页。等战例。频繁的战争实践,使明初将帅对步、骑、炮的协同作战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朱棣将其总结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阵密则固,锋疏则达”,战斗开始后,“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如此“则敌不足畏也”。⑤《明太宗实录》卷262,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丙寅。其实质是根据步、骑、炮的作用距离以及杀伤方式不同,分层次、多梯队地轮番打击敌人。在具体布阵上,炮兵居前,采用疏散阵型拓宽战场正面,实施轮番齐射,遏制敌人攻势,打乱敌方阵型;若敌阵溃乱,则遣骑兵迅速冲击敌方中坚,切断其指挥,使其应对不及;步兵随马队冲入敌阵杀敌,直至作战胜利。当然,所谓战术战法的总结乃是用兵常法,战时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来定。同时,也应看到,明初的野战战法是漠北大规模集团作战背景下的产物,这较后世为应对倭寇入侵而演绎出的丘陵地带野战协同战法又有所区别。但无论如何,重视和发扬火力优势、使冷热兵器协调配合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三是围绕火器装备专门设计的特殊战法。为充分发挥火器毁伤效能,达到必要的作战目的,这一时期,将帅们还以火器为中心专门设计了一些特殊战法。如洪武八年(1375)纳哈出寇辽东,朱元璋命都指挥叶旺采取“坚壁清野”之法使其掠无所得;同时,命于纳哈出回撤的必经之路上布设大量火器部队,待敌进入埋伏圈后“炮发伏兵四起,两山旌旗蔽空,鼓声雷动,矢石雨下”,予敌充分杀伤。这种积极防御的守城之法和于谦组织的北京保卫战有相似之处,但发生时间却早了近百年。另外,从现存明代火炮实物来看,洪武十年(1377)前后建造了一批堪称古代形制之最的大型火炮,如山西平阳卫制造的铁炮全长可达1000 毫米、口径210 毫米、尾长100 毫米。⑥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85 页。从中不难推测,凭借火炮强大的杀伤力,实施“婴城自守”等战法或是其中应有之义。
(二)体制、编制的革新。热兵器的大量使用还引起了军队体制、编制的新变化,表现为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螺旋上升发展的态势。
在冷、热兵器共用的初级阶段,表现为在军队现有编成内,火器使用人数的增多和冷兵器使用人数的削减。元末农民战争时期,明军的火器编配并无定则。洪武中期以后,明确规定卫所部队的火器装配率不能低于10%,“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⑦《明太祖实录》卷129,洪武十三年春正月丁未。。但此装配比例大概只是通则,具体火器装备的种类、数量以及装配比率等,视不同地域的敌情威胁程度而存有差异。如洪武二十年(1387)五月,命云南金齿等卫“葺垒深沟,以固营栅,多置火铳为守备”①《明史·云南土司传二》,第8112 页。。但无论无何,经洪武一朝的发展,军队火器装备数量持续扩大,构筑军队建制内步、骑、炮混编新格局的结论是肯定的。
在冷、热兵器共用的中高级阶段,表现为火器部队脱离原有编制,开始独立成军,并向技术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朱棣即位后不久,成立三大营,其中包括专司枪、炮操演的神机营,火器部队得以独立成军。神机营拥有更大的自主性,既可独立集中使用,又能与五军营、三千营等步骑单位协同作战,其职能略近今炮兵部队。其编制,《明宣宗实录》载:“神机营设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中军十五司及随驾马队官军,共七万五千七十一人。”②《明宣宗实录》卷42,宣德三年闰四月辛卯。另据史载,永乐时期,包括“得都督谭广马五千匹,置营名五千下,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③《明史·谭广传》,第4255 页。的五千营及“专司侍卫”的千二营均置于神机营的管辖之下。千二营虽具有临时抽调性质,但终永乐一朝,也从未从神机营的编制中退出。可见,神机营在建立之初并不是一个全火器装备的单位,而是以火器编配为主,炮、步、骑混编。战时,炮兵主要负责火力输出,步骑则承担相应的警界、保护之责,各司其职,使神机营得以正常发挥作用以及生存保全。
(三)训练内容的革新。火器部队单独成建后,训练内容开始朝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永乐初年,朱棣即提出:“神机铳炮,兵之利器,攻战所不阙者,必操习精熟,然后临机得用,尔提督不可不严。”④《明太宗实录》卷144,永乐十一年十月癸丑。明确要求提高神机营的训练质量。《明英宗睿皇帝实录》亦载:“都指挥佥事王淳言:臣访求太宗皇帝旧制,参为束伍法……遇敌,牌居前,五刀居左,五刀居右,神机枪前十一人放枪,中十一人转枪,后十一人装药。隔一人放一枪,先放六枪,余五枪,备敌进退。前放者即转空枪于中,中转饱枪于前,转空枪于后。装药更迭而放,次第而转,擅动滥放者,队长诛之。”⑤《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193,景泰元年六月乙酉。从中可知,神机营本级的训练科目包括单兵射击、射击队形切换以及步(骑)炮合同等内容。其中,队形有序切换是训练重点,要求分队根据敌方阵型密度、移动速率及我方弹药装填时间、对敌杀伤效果等因素合理部署和调配,做到自身衔接有序的同时,又能为战场提供持续性的压制和火力杀伤。这些专业化训练要求的提出,大大提升了火器部队的训练质量和实战本领,也为后世的军事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参照。
二、关于兵学诸问题认识的深化
元末明初,虽鲜有兵书传世,但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却很丰富,在固有兵学内容的基础上,创新了关于战争指导、陆海协同、建军治军、冷热兵器共用等诸多问题的认识。这些对传统兵学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一)对作战指导认识的深化。关于如何更好地指导战争实践,朱元璋提出了“略胜、势胜、机胜、力胜”的四维战争指导体系。“略胜”是关于战争准备的思想,包含“积粮训兵”的物质准备以及“伐敌制胜贵先有谋”⑥《明太祖实录》卷20,丙午年夏四月癸亥。的谋略准备,内容上略同于今战略指导;“势胜”是指给战争赋能,能动地调配战争力量,积极地布势造势,在战前形成“攻之必无不克”⑦《明太祖实录》卷17,乙巳五月戊午朔庚申。的综合对敌优势,这是战役指挥员要努力完成和实现的目标;“机胜”是关于临机决胜的思想,或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变化佐胜,或根据战场局势“奇正分合”战胜,是战斗指挥员应变、指挥和谋略水平高低的综合体现;“力胜”是战胜攻取的保底手段,“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⑧《明太祖实录》卷58,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丑。,但“矢石之下,罹害者众”⑨《明太祖实录》卷119,洪武十一年八月己巳。是在特定情况下达成战役战斗胜利的必要方式。
这一时期虽没有具体的战略、战役、战术之分,但从朱元璋的提法来看,对这一问题已有一个大体认识。①在军事框架内,首次提出类似于如今战略、战术等相关概念的是南宋的陈亮。他在《酌古论》中指出作战指导有两种术,第一种“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这实际是现代意义上的战术概念;另一种“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利害,次第收之,而无一不酬其意”,类似如今的战略概念。元末明初虽无明确的战略、战役、战术概念,但大致的认识应当是存在的。参见高锐:《中国军事史》(中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261 页。略胜、势胜、机胜、力胜四者围绕“胜”这一目标,构成了层次有别又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实际操作上,略胜和势胜主要是为增加战争把握性而服务的。朱元璋提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②《明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八月庚子。此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上》。,认为战争态势一旦形成,即便再睿智的指挥员也很难完全扭转,坚持将“庙算”“先谋”等作为规避战争偶然性、增加把握性的主要手段,反对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开战;机胜主要是通过各种临机手段获取胜利。“战阵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③《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乙酉。,战事的多变性既为弱势一方扭转被动局面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是优势一方将主动地位彻底转变为胜利的重要方式;机胜不成,则付诸于力胜。“两军相斗勇者胜”,力胜不仅取决于军队人数众寡,更是人心怯勇、训练水平高低以及步调一致、统一指挥等之于作战能力的综合反映。由此,朱元璋提出“略胜、势胜、机胜、力胜”这个战争指导的一般流程和规范总结,当中又融入其关于战略指导、战役指导、临机制胜和建军治军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基于实践的一种理论深化。
朱棣在作战指导方面亦有所阐发。相比于朱元璋长于战略而言,朱棣在战术方面的风格更加鲜明。“迅雷之下,其势不及掩耳”,他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视作取胜的重要手段,认为若待敌“布阵若定,则难猝破”,主张兵贵神速。④《明太宗实录》卷6,建文二年五月己卯。为达此目的,朱棣高度重视“兵以诈立”和“以谋取胜”的作用,或声东击西调动对手,或诱敌深入伏击取胜,或百里奔袭奇袭对手,靖难时期佯攻大同、漾桥伏击、奇袭沧州等皆可为例。这种不拘一格、以诈取胜的方式颇具胡风,也是朱棣常年与北元作战的军事积累,丰富了元末明初兵学关于作战指导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他还高度重视战争法理的特殊作用,并与诈谋取胜之道相结合。如靖难时期的多次上疏,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舆论支持,还有效分化了建文帝群臣。迫于重压,建文帝不得不“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以说于燕人”⑤《奉天靖难记》卷2,洪武三十二年十一月乙未,济南:齐鲁书社,1995 年。,并反复申谕不得伤燕王性命,避免背负杀叔之名,显示朱棣于政治攻势上的高超驾驭能力;再如在《北伐诏》中,朱棣历数北元“肆逞凶暴、其人钞边、拘杀使者”⑥《明太宗实录》卷101,永乐八年二月辛丑。等罪行,树立政治优势的同时,更保障了军事的顺利展开。从这个意义来说,朱棣不失为将儒家道义与兵家诡诈充分结合与运用的典范。
(二)形成关于陆、海战略统筹的新认识。一般来说,某一阶段内国家的主要战略方向通常只有一个,即便存在多个需应对的方向,也有主次之别。明初,朱元璋鉴于现实威胁考量、经济承受能力以及战略手段局限等,制定了陆防这个主要战略方向:“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⑦《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明确将北元作为主要军事斗争方向,其他如“限山隔海”的西南陆上和东南海上威胁,则坚持“彼不为中国患者,朕绝不伐之”的原则,只有在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时才予以坚决回击。然而,尽管其意愿如此,东南海上的安全形势却很严峻,面对倭寇的不时入侵,附以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因不甘失败逃亡海上、为祸海疆等现实威胁,维护海上疆域的安全亦十分必要。由此,如何在物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既突出陆防这个重点,又正视海防的建设,在增加应对多个方向军事威胁能力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维护国家完整统一的大局,成为明初陆海战略统筹的重点。
一是在海防建设中优先发展海上战略威慑力量。元末战乱之后,社会凋零、民心思治,加上北部边防牵制了明朝大量的兵力、物力、财力,故能够投到海防建设的国防资源相对有限,这决定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构建完整的海防体系难以迅速实现。为此,统治者提出了优先建设海上作战力量的主张,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海上实战能力的快速提升能够有效遏制倭寇及群雄余党入侵的上升势头;另一方面,在海防体系整体建设尚存短板的情况下,有重点、有侧重地发展拳头力量也是海防建设的内在要求。洪武三年(1370)七月,朱元璋下令成立水军等24 卫,每卫配战船1200 艘,成立一支完全隶属中央的海上战略机动部队,担负海上侦察、巡捕以及作战任务。为了提供海上作战力量建设所需的战船,特于龙湾附近水域开建龙江造船厂,此后包括郑和下西洋所用之“宝船”在内的明初主要大型水面作战舰船均出于此。洪武七年(1374),诏以吴祯为总兵官,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为主的中央直辖海军“出海巡捕海寇”①《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春正月甲戌。,不断追击,“捕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俘送京师”②[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840 页。,一度将战略防线推向琉球海域。七年以后,每年春天命师出海,秋天返还,特别是在“春汛至五月终,小阳汛至十月终”③[明]郑若曾、邵芳:《筹海图编》卷12《固海岸》,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355 页。这两个利于倭寇入侵的风讯时期,严令水军加强警备、分路防倭,击寇于困乏疲惫之中。上述措施,至永乐时期仍较好地保持,有效应对了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
二是剿运复用。剿是指运用海上军事力量抵御倭患,运是指水师同时还承担海运的职责。这是在明初国防资源相对有限情况下,应对陆海两个战略方向矛盾的又一个解决思路。也就是说,发展海军除了有抵御倭患的现实考虑外,靖通海道为陆防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也是海防的重要职责。元末开始,因黄河常年泛滥、漕运运力不济,不得不仰仗海上运输,这是剿运复用提出的历史背景。但消化矛盾的对立面,并使其向统一方向转换,是剿运复用背后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如,洪武元年(1368)二月命“御史大夫汤和还明州造海舟,漕运北征军饷”④《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癸卯。;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命靖海侯吴祯督浙江诸卫舟师,运粮往给辽东军士”⑤《明太祖实录》卷112,洪武十年五月丁亥。等,均是剿运复用的现实例子。
三是北方安全局势趋于明朗后开始建设完整的海防体系。大抵洪武十九年(1386)以前,海防建设遵循总体适度、部分优先的原则。因而,这一时期的海防建设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体系建设的完整性而言仍有欠缺。此后,随着北方安全形势的明朗以及国力的逐步恢复,建设完整海防体系开始提上议程。朱元璋问策于方鸣谦,对方给出了“量地远近,置卫所,陆具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⑥《明史·汤和传》,第3754 页。的建议;此后,“陆具步兵,水具战舰”成为了海防体系构建的中心指导思想。翌年四月,命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⑦《明太祖实录》卷181,洪武二十年三月戊子。;十一月,汤和与方鸣谦前往浙东,令“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⑧《明太祖实录》卷187,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己丑。,得步兵5 万余人。同时,鉴于倭寇经常占据无人岛礁作为自身的前进基地,特命于倭寇必经岛礁处设立水寨,作为陆上防御力量的延伸。此后,陆续在辽东、山东、广东等沿海及附近岛屿增建卫所、巡检司,加筑城、堡、寨、营及烽墩、塘铺等。海军卫所的扩编和海防体系的建设一直持续至永乐时期,陆上有重兵把守,海上有舟师巡剿,海陆之间水寨遥相呼应、墩堡烽堠星罗棋布的有层次、有纵深的海防体系全面建成。其构成,大致包括58 个卫所、99 个守御千户所,加上300 个左右的巡检司,总计军力约40 余万人。得益于完整海防体系的建立,从洪熙元年(1425)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127 年中,倭寇侵扰行动仅有8 次,①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年,第555 页。故《明史》载“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②《明史·兵志三》,第2244 页。。
(三)其他散见于史籍、奏折中的兵学论述。元末明初,其他杰出人物关于军事的有关论述对后世也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兵学论述的主体既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又有充分的实践导向,在军队和国防建设等方面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
如刘基在战略决策方面颇有新见。元末,朱元璋起步较晚、实力较弱,又处在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包围之中。遵循“先弱后强”本是军事战略运筹的通则,但刘基却一反常态,向朱元璋提出了“先陈后张、先强后弱”的建议:“士诚自守奴,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③《明史·刘基传》,第3778 页。,“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④《明太祖实录》卷58,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应将陈友谅作为首要歼灭对象。若先攻张士诚,“志骄好事”的陈友谅必定空国而来攻应天(今南京),届时自身将无法摆脱两面受敌、“疲于应敌,事有难为”的困境;反之,若先进攻陈友谅,小商人出生的张士诚出于利益考量,必会先盘算观望,或只出动小规模军队,尔后根据朱元璋和陈友谅战局的发展状况来决定自己的用兵程度。这种以联合为名、行渔人之利的做法,反而能够大大减轻朱元璋的军事压力。由此可见,刘基的建议不仅是基于对阶段性军事强弱形势的现状分析,还充分考虑到政权领袖性格、认知因素之于战略决策的影响。也就是说,政权内部的重要人物虽均可对战略决策施加影响,但决断权大小的不同、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力也有所不同,而这当中,政权领袖的意见无疑是最重要的。有鉴于此,刘基认为即便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仍应以征服陈友谅为首要目标,这个过程可能充满挑战,却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他的建议得到朱元璋的采纳,也为朱元璋的军事斗争指明了方向。
又如叶伯巨谏分封太奢。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诏求言,叶伯巨上书言三事,其中极力指陈分封诸王太奢的危害。认为分封太奢容易形成诸王尾大不掉之势,待其威胁显现,“削其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⑤[明]叶伯巨:《奉诏陈言疏》,《明经世文编》卷8《叶居升奏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52 页。,汉代七国、晋代诸王之乱的景象或将不可避免。应当来说,叶伯巨的谏言是有针对性的,也预见了明初重大政治变局的产生。但是,分封诸王作为明初制度设计的重要一环,是完成军权由勋贵重臣转移回中央的重要过渡,哪怕经验教训历数在前,分封藩王、“夹辅王室”也势在必行,反映出明初兵学“家天下”思想的客观局限。
又如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著名建议、群臣谏朱棣迁都北京等,这些著名论述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的重大军事问题,对后世也有可资借鉴的成分,是窥探元末明初兵学面貌的重要视角。
三、元末明初的兵学局限及影响
一般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从“区域史”迈进“世界史”的关键时期。⑥陈支平:《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92 页。但明初以后,中国非但没能保持住自身的领先地位,反而沿着“领跑”到“跟跑”再到“掉队”的路径快速跌落,至晚清时已陷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的全面落后。期间,中国社会虽有所发展,甚至一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总体上游离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之外却是不争的事实。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仅就军事科技、军事理论的停滞乃至衰退而言,就不得不归结于军事本身“兵能弭乱,亦能召乱”的双刃属性,以及极端专制中央集权背景下对兵学又利用又提防的复杂心态。在此背景下,元末明初的兵学又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一是军事科技在战争背景下推陈出新,威胁解除后又停滞倒退。军事技术的发展为传统兵学突破“言必由孙子”的瓶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秉承军事技术发展引领军事变革的路线,元末明初,统治者在这方面确曾做出过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如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曾高度重视新式火器装备的研发和战船的制造,凭借优越的装备性能屡屡获胜。明初,为有效应对北部边防和东南海防的双重军事压力,朱元璋一边鼓励边地卫所自行研制和制造火炮,一边招募工匠在京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建设不同规模的造船厂。此举不仅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也为边防、海防的巩固提供了很大的助力。然而,当内外部局势有所改善和企稳之后,朱元璋便于洪武十三年(1380)设立军器局,敕令地方不得擅造火器,又先后六次发布禁海令,规定“片板不许出海”①《明史·朱纨传》,第5403 页。,给快速发展的军事技术按下暂停键。上述政策的出台,诚然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但通过抑制军事技术发展来规避潜在政治、军事风险的倾向也是明显的。此后,军事技术除在朱棣时期又有所发展之外,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势一直延续到嘉靖倭乱时才得以改善,嘉靖之后至晚清的数百年间,则是一个更长的停滞和衰退期。长时间的技术停滞,不仅使明代中期开始丧失了制造“宝船”的能力,连“四百料”②一料即一石,约合今120 斤。参见范中义等:《中国军事通史·明代军事史》(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266 页。等大型船只也难以制造,客观物质上的局限反过来又作用于军事实践,戚继光等将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采取陆上歼敌的方式来平稳东南局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二是兵学理论在纷争年代发展突破,和平时期便鲜有问津。元末明初,是上承“兵儒合流”之余,下开“以儒统兵”之河的历史过渡期。与军事科技发展的境遇相类似,兵学发展同样也面临缺少养分的尴尬。首先是相较儒学地位的不断上升,兵学主要徘徊于“术”“用”的层次。元末,宋濂曾劝朱元璋多读尚书、二典、三谟等儒家经典,朱元璋回复道:“非不知典谟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时务,所先耳。”③《国初礼贤录》卷上,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既以兵学为时务和功用,而非“祀与戎”的并列,战争威胁解除后兵学被束之高阁就难以避免,反映到兵学本身,则是兵学发展的动力基本源于对现实威胁的解决,而非理论牵引军事发展的自觉。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种功利、实用主义倾向很难不形成军事上的落后。其次是强化儒学对兵学的渗透改造。历史证明,集权统治的强化与儒学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这倒不是说儒学在诞生之初就以强化社会治理为目的,但宗法制度、“纲常名教”等价值观念的提出确又与统治者的需求不谋而合,行之后世得到不断地强化。儒学官方显学地位确立之后,其对兵学的渗透改造同样不可避免,如“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重义轻利”等价值观念的持续输出以及治军环节中“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恭不伐”④《明太祖实录》卷58,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丑。等忠君德行观念的反复强化,使得兵儒合流之于兵学发展的某些正面意义,开始更多地向着维护极端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一元方向发展。
总之,元末明初的兵学局限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时代性的强化,二者的结合,又附着和固化在制度、意识形态等长久作用于社会生活的领域之中,并多为明清统治者所继承,引发兵学发展土壤的进一步缺失。这种缺失,如同资本主义萌芽消失一样,难以从社会内部打破,最终,在列强的全面侵掠面前,迎来全面的肢解和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