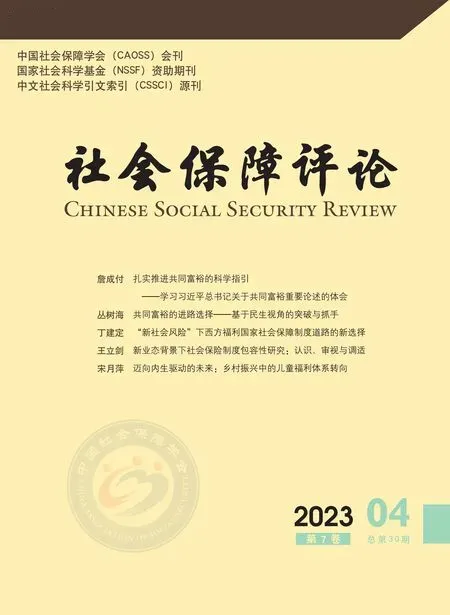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践探讨与案例分析
2023-09-09金炳彻
金炳彻
一、引言
近些年,伴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社会不平等程度扩大,加之固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不合理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逐渐得到了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包括智力劳动在内的工作正在趋于消失,传统的“相对过剩人口”正在演变为“绝对过剩人口”,“结构性失业”问题愈发突出。①万海远等:《全民基本收入理论与政策评介》,《经济学动态》2020 年第1 期。在美国,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与发展,预计在2023—2028 年,将有200 万卡车司机被替代。同时,由于金融危机、收入差距扩大与新冠疫情的影响,相对贫困、收入不平等、中产阶级持续萎缩等问题十分严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于2030 年前“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值得学术界深思。
围绕全民基本收入的争论不仅在学术界与政界得到关注,还提高了人们对未来社会应该建立何种形式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认识和关注,从而开启了全新局面。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主张,在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过渡的过程中,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失败的,由此导致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化的迅速扩大,今后这一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他们主张从收入保障制度的基础开始,重新确立收入保障的构成和运营原则。在这些重新定位的工作过程中,欧洲近年来取得进展的基本收入思想可以成为其主要思想来源。然而,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却质疑全民基本收入所需的财源及其普遍的支付效果,因而对引进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持怀疑态度,他们主张通过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来重新建立收入保障制度。因此,全民基本收入方案虽不容易被立刻采纳,但包含革新性想法,对其进行研究并采取积极措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即旨在探讨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和理论及其存在的主要争论和实践。
二、无条件发放现金,开启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新征程?
近年来,学术界与政界对未来社会保障体系方案的讨论非常活跃。这种讨论始于社会变化,现有的福利国家未能正确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风险。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国家经济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基本的经济活动和消费需求大幅萎缩,国民生活和整体经济的困难扩大,经济基础薄弱的平民、小工商业者和个体户等急需稳定的社会安全网。在这样的认知与背景下,曾一度被积极讨论的全民基本收入开始重新受到关注。
面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许多人预测将迎来严重的经济萧条,于是“无条件向所有公民发放现金”这一想法逐渐在欧洲普及。自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包括了全面发放直接补贴或者现金红包的方式。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促进了消费,但同时也引发了通货膨胀、财政风险等问题。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实施了以全体国民或部分阶层为对象的“生活补助”或“属于灾难基本收入的现金支援”。这类措施虽然有约束条件(比如收入限制),但大多规定得比较宽松,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部分人群。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2020 年3 月27 日签署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救助法案,涉及资金量达到2 万亿美元。法案的核心是以现金或支票的方式向美国人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援助金额基于收入水平。根据相关规定,年收入低于75000 美元的每个单身成年人可以获得1200 美元,超过75000 美元的,每增加100 美元收入则减少5美元的援助,超过99000 美元的则不会获得援助;年收入不超过150000 美元的已婚夫妇将获得2400 美元,年收入超过150000 美元的依上述同样的方式递减;每个16 岁以下的儿童可额外获得500 美元。①参见Kathleen Elkins, This Calculator Tells You Exactly How Big Your Coronavirus Stimulus Check Could Be, https://www.cnbc.com/2020/03/27/the-stimulus-payment-calculator-tells-you-how-much-money-you-could-get.html, April 16,2020.英国政府为所有受疫情影响而无法工作的居民,补贴其工资的80%,补贴上限为每人每月2500 英镑;对于没有雇主的自雇人士,直接现金补贴为平时利润的80%,为期至少3 个月。加拿大政府对在疫情中失去工作,或者没有失业但失去收入的民众,发放每月2000 加元的政府紧急救助金。
日本也采取了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2020 年4 月7 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确定应对新冠疫情的第三轮紧急经济对策,其中包括直接面向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的家庭发放“生活支援临时给付金”,符合条件的每户家庭将获得30 万日元。随着疫情的加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4月16 日新型冠状病毒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应替换该方案,采取扩大发放对象的措施”,于是日本政府决定不设收入限制,向每位国民发放10 万日元,同时撤回向收入减少家庭发放30万日元现金的措施。这使得需要的财源从约4 万亿日元增加至约12 万亿日元,但覆盖面从约1300 万户家庭扩大到超过1.2 亿的全体人口。①赵柯、李刚:《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经济救助政策新取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 年第3 期。
在韩国,2020 年4 月29 日,国会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灾难补贴追加更正预算,决定从5 月开始面向全体国民,以4 人家庭为标准,为每户提供100 万韩元的紧急灾难补贴。新冠疫情初期,韩国政府把重点放在了“选择性优先支援”上,支付对象限定为处于收入下游70%的国民。2020 年4 月15 日举行第21 届议会选举后,灾难补贴的范围扩大为全体国民,不论其收入或财产的多寡。灾难补贴是向因灾难遭受损失的“特定”地区或被“挑选”的对象,依据损失的“比例”提供补助;而灾难基本收入则是从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出发,将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暂时运用于新冠疫情等危机。②노대명, 재난기본소득논의를통해본한국소득보장제도의문제점과향후과제, 보건복지포럼 vol.3, 2020.韩国历史上首次实施的灾难补贴表明,在韩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是可能的。事实上,灾难补贴是在新冠疫情引发经济危机时,政府直接向消费者而非企业提供支援的措施,这是通过推行基本收入以促进经济复苏的一个成功案例。
此外,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工作岗位的减少导致就业焦虑,担心失业的人正在增加,而少数人垄断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超额利益可能会造成通过劳动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崩溃,这种忧虑也正逐渐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基于共享社会共有资产所创造的利益的哲学思想,在就业困难和低增长成为常态的时代,其被认为是能够促进经济复苏并保证持续增长的政策。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改变现有的社会保障观念?
三、全民基本收入与社会保障的关系
全民基本收入不仅涉及多个学术领域,也是如今为政界所重视的划时代的创新性社会政策。这是因为基本收入不是单纯的社会政策,它蕴含着自由主义和进步性的思想背景,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③参见Robbert-Jan van der Veen, Loek Groot, Basic Income on the Agenda: 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tical Chance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0.如今,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对其原则的认知,进入了思考如何将其具体化为政策的阶段。围绕着全民基本收入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问题,不仅引发了对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反思,还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一)全民基本收入与社会保障的关系
全民基本收入是指无需资产调查与劳动要求,无条件地向公民或共同体成员个人定期提供的收入。④Philippe Van Parij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asic Income Idea, https://basicincome.org/history/.根据这一定义,它主要呈现以下特征:定期给付、现金给付、基于家庭成员个体给付、无需家计调查的普遍给付、无条件给付,即不是一次性而是以有规律的间隔进行支付、不是提供代金券或实物而是提供现金、不是以家庭而是以个人为对象,以及不论收入或所有资产、劳动状况或劳动意向如何,都无条件支付。全民基本收入可区分为无条件基本收入、修整型基本收入、利益相关者补助三种类型。无条件基本收入指政府无条件地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转移收入,充分满足个人基本需求,将个人从劳动力市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保障个人真正的劳动自由权。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最符合全民基本收入的宗旨。修整型基本收入在无条件基本收入中加入了一些标准,并进行了一些调整。根据政府提供收入的时间、标准、互惠原则等,可以划分为临时全额基本收入(Full Basic Income)、部分基本收入(Partial Basic Income)和参与性基本收入(Participation Basic Income)。利益相关者补助是基于公民身份理论的一种普遍的再分配,为达到一定年龄的人提供更为慷慨的福利,有利于促进正义、平等和个人自由。
全民基本收入是由政府向社会成员基于公民身份,以货币形式按时定量派发的社会福利金。领取人可以自由地使用福利金,摒弃了父权主义下“控制使用范围”的限制,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原则,是获得“实质的自由”的重要途径,①Phillipe Van Parijs, "Why Surfers Should Be Fed: The Liberal Case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91, 20(2).有利于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②参见Philippe Van Pariis, Yannick Vanderborght, 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全民基本收入不与工作激励、家计调查等挂钩,是否具备工作动机、是否工作、是否贫困等并非领取的必要条件。有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保障后,公民可以不必将过多的时间耗费在劳动生产中,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参与社会工作、慈善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从公民的获得感层面考量,全民基本收入不仅让公民有了可以自行支配的现金,还提升了对政府的信任与获得感,并增进个体的幸福感。③徐富海、顾天安:《全民基本收入:社会福利制度的创新还是空想?》,《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4 期。
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需求或问题:公共补助旨在解决贫困、促进自立,社会保险旨在弥补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等带来的收入损失,社会津贴旨在弥补养育儿童、残疾、老龄等带来的额外支出。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条件逐渐提升,不属于传统社会性需求范畴的活动也被认定为社会性需求。在这个方面,基本收入可以涵盖社会成员多样化的需求。换言之,如果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解决特定的社会需求,那么基本收入就是使得社会成员以公民身份可以自行规定多种需求并加以解决的手段。
然而,如果基本收入制度是为了解决多样的社会性需求,则也需要思考应该如何处理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④Authors and Research at Kela, From Idea to Experiment: Report on Universal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in Finland,Kela Working Paper 106, Helsinki, 2016.即在基本收入制度包含的多种社会性需求中,是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包含的特定社会性需求?特别是社会津贴是否应该与基本收入制度合并?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整体社会保障体系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应有机地连接和配合。因此,从以政府预算为财源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看,厘清基本收入制度和与其有较多共同点的社会津贴的关系非常重要。
与基本收入制度适用于所有个体相比,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具体的情况适用普惠性与选择性。也就是说,虽然追求全体国民的幸福和稳定,但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重点保障处于社会危险之中或有社会保障需求的对象,可以缓解不平等和减少收入差距,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综上所述,基本收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最终归结为将基本收入支付给谁的问题。①参见Bruce Ackerman, et al.,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Basic Income and Stakeholder Grants as Cornerstones for an Egalitarian Capitalism, Verso, 2006.
几乎没有人反对引入社会保障制度,但对于为什么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提出基本收入作为替代方案,人们的意见不一。比较基本收入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衡量两者的地位将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基本收入制度的适用对象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和基本收入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收入制度采纳的具体方案将有所不同。从制度的普遍性和替代性来看,可以引入完全基本收入制度的方案,全部替代社会保障制度;也可以让部分基本收入制度替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实施部分普遍性+选择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可以在维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适当使用对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的社会津贴。②Luke Martinelli, Assessing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 the UK, IPR Policy Brief, University of Bath, 2017.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普遍性+选择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收入的支持者主张阶段性地引进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而基本收入的反对者则拥护福利国家体系,主张重建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引进基本收入(见表1)。

表1 关于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赞成与反对的争论
(二)基本收入的支持者:阶段性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认为,共同财富(Common Wealth)非个人所有,而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所以由此产生的收益应该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③参见Brent Ranalli, Common Wealth Dividends: History and The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21.他们主张,在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过程中,现代社会对财富的再分配是失败的,其结果是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加剧,预计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同时,随着非正式员工和平台劳动者规模的扩大,以及以劳动者为中心的社会保险体制的局限性凸显,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因此重组以基本收入为中心的福利国家是必然趋势。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管理费用,促进国民消费(内需),稳定和促进自由劳动。①参见[比]菲利普·范·帕里斯:《全民基本收入:实现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方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年。因此,从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角度出发,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既是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促进国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保障制度。
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提出了分阶段引进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构想,主张将全民基本收入逐步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内,逐渐向部分替代和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向发展。②Anthony Atkinson, "The Case for a Participation Income,"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1996, 67(1).即最终目标是实现完全基本收入制度,但分阶段性推进。首先从部分基本收入制度开始,通过减少及代替现有社会保障给付的部分、整顿非课税制度、强化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累进性、开发新财源(碳税、土地税、机器人税、数据税等)等方式来筹集财源。③Ville-Veikko Pulkka, "A Free Lunch with Robots—Can a Basic Income Stabilize the Digital Economy?"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017, 23(3).
对这种基本收入支持者的立场存在一些批评,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基本收入制度所倡导的“从工作的权利(Right To Work)转移到不工作的自由(Freedom From Work)”的实质自由并不能得到保障,任何人都不能实现去劳动化(Delaborization)。第二,由于必须耗费巨额的政府财政才能为全体国民提供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的资金,全民基本收入制度难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时,调整、完善和废除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并不简单。社会保障体系是由多个提供主体、传达体系以及工资和财源以复杂的方式组合而成,各要素发挥不同的作用,不可能仅通过一种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来实现。
(三)基本收入的反对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对上述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进行了批评。他们主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质疑全民基本收入所需财源及其效果,因此对引进全民基本收入持怀疑态度。④Soomi Lee, "Attitudes Towar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A Research Note," Basic Income Studies, 2018, 13(1).福利国家的支持者认为筹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所需的巨额财源是不现实的。此外,他们主张,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国家可以保护所有国民免受社会危险(育儿、失业、残疾、疾病、养老、居住、灾害等),保障人的正常生活,显著缩小不平等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构筑克服当前痛苦和未来不安的社会安全网,建立不造成社会落伍者的社会,在再分配方面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从成本效用角度分析,建议维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同时对其加以完善。换句话说,首先向没有获得收入能力、有权接受抚养和教育的儿童(与父母收入无关,包括大学生),以及获得收入的能力明显下降、患有疾病的老人、失业者(包括未就业青年)、残疾人等处于社会危险状态的国民提供资金。他们认为,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性调整,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和公平性,也能提升劳动力去商品化的程度。⑤Vida Panitch, "Basic Income, Decommodific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1, 37(8).同时,他们主张通过整合目前正在实施的多种现金性给付(如老年人基础年金、残疾人年金、儿童津贴、国民基础生活保障金、劳动奖励金、子女奖励金、失业给付等)来改善社会福利服务。
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全民基本收入的普遍性和无条件性原则不同,拥护社会保障制度的一方坚持选择性支付的原则,导致在申请和资产审查的筛选过程中产生“贫困污名”,实际上符合领取资格的人中也会出现因担心污名效应(Stigma Effect)而选择不申请的情况,其后果就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保障的结构性盲点。①Tijs Laenen, Dimitri Gugushvili, "Welfare State Dissatisfaction and Support for Major Welfare Reform: Towards Means-Tested Welfare 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23, 32(2).另外,弱势群体和陷入危险的人绝非少数,因而很难对他们进行筛选。更何况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作岗位减少,标准的雇佣关系逐步瓦解,建立在雇佣关系之上的传统社会保险制度已无法再为逐渐扩大的低收入和收入不稳定的劳动者群体提供保障。
另外,全民基本收入的重要批评者是全民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 UBS)的倡导者。全民基本服务的倡导者认为,忽视集体责任的现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无法满足人的需要,而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需要建立在以管道、电缆、交通、食品、能源以及银行等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性基础经济(Material Foundational Economy)和以整个福利国家体系(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治安、应急以及公共管理等)为核心的干预性基础经济(Providential Foundational Economy)之上。②岳经纶、吴高辉:《全民基本收入与全民基本服务——当代两大社会政策思潮的比较与论争》,《广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1 期。全民基本服务的倡导者认为,在需要满足方面,实施全民基本服务比实施以商品化服务为基础的全民基本收入更加优越和独特,全民基本服务将构建一个“基于需要”而不是“基于能力”的公共供给制度。③Ian Gough, "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A Theoretical and Moral Framework,"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2019, 90(3).全民基本服务的倡导者认为,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普遍、免费、公共或集体的基本服务更加高效和有效,而市场在满足人们的需求方面可能并不可靠,特别是在对消费者不利的私人垄断和复杂的定价结构系统中。④Milena Büchs, "Sustainable Welfare: How Do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Compare?"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1, 189.
四、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践案例可行性分析
通过已经实施或试验基本收入的国家的案例,可以探讨影响基本收入制度可行性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引入基本收入制度的可行性。
(一)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分析框架
以下将介绍美国、芬兰、韩国三个国家的全民基本收入实践案例,分析这些案例的可行性。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Permanent Fund Dividend, PFD)制度虽然不以国家为单位,但在典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美国阿拉斯加州将石油收入红利分红给所有居民,进而成为美国国内经济最为平等、贫困率最低的州之一,这使得该案例具有重要研究价值。⑤Matthew Berman, "Resource Rent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Poverty Among Alaska's Indigenous Peoples,"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6.芬兰作为先进的福利国家也备受瞩目,其基本收入试验具有社团主义政治体系的特征,同时引进了作为替代性政策的基本收入政策,因此具有重要意义。韩国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项目体现了后发福利国家围绕福利国家的重组,对其结果进行考量具有独特意义。①参见김교성, 이지은, 기본소득의 ‘실현가능성’에 대한 탐색, 비판사회정책 제56 호, 2017.
对这些国家全民基本收入案例的可行性进行说明时,可以大致分为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两方面。经济因素与全民基本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是关于是否有能力支付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多少预算、如何获得资金的财政可行性因素。②参见Malcolm Torry, The Feasibility of Citizen's Incom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政治因素意味着某种政策所需的背景条件,这种条件能使政策在可预测的未来合理运行下去。③Jurgen De Wispelaere, José Antonio Nogueramm, "On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 Analytic Framework," in Richard Caputo (ed.), Basic Income Guarantee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Viability of Income Guarante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虽然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决定实现基本收入可行性的最重要因素,但为了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各方政治势力和市民的支持、政策设计、立法推进以及政策执行等政治因素也需要纳入考察范围。因此,可从经济要素的财政可行性以及政治要素的战略可行性、行政可行性、心理可行性、行为可行性等五个领域(见表2),来分析美国、芬兰、韩国的全民基本收入实践案例的可行性。
(二)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践案例
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制度每年为本州所有居民提供同等额度的现金,在世界范围内是目前与全民基本收入最为接近的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斯加州的州长杰伊·哈蒙德(Jay Hammond)设立了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该制度在1976 年以阿拉斯加州宪法形式得以确定,资金主要来源于阿拉斯加州每年矿产资源拍卖所得收入。阿拉斯加州政府每年要将上述收入的50%划拨到这个基金中,基金收益用于向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等额的现金。1982 年,阿拉斯加州立法部门通过了第一个资源基金分红方案,赋予所有在阿拉斯加居住六个月以上的公民平等的基金分红权利。1982 年的首次分红额为人均1000 美元,此后各年的分红支付视永久基金的投资收益而定。2015 年,年分红数额创历史新高,达到了人均2072 美元。2021 年人均分红为1114 美元。①参见Department of Revenue,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Division 2021 Annual Report, State of Alaska, 2021.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制度是公有资源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典范,其设立兼顾了公平与效率,考验了全体公民的决策能力,也激发了公民对共同财富的责任感。
芬兰基本收入试验始于2017 年1 月1 日,是欧洲首个由国家支持的无限制发放基本收入的试验。该试验由芬兰社会保险局负责,为期两年,随机挑选2000 名未就业的25—58 岁公民发放560 欧元的月基本收入。样本从目前领取失业援助的受益者中挑选,为了防止选择性偏差,被选中者强制参与这一计划。考虑到试验主要是为了测试对就业的影响,学生和老年人被排除在外。2018 年12 月,芬兰政府对实验组的2000 人和控制组的5000 人进行了调查,并分别访谈了实验组586 人和控制组1633 人。随后发布的《2017—2018 年芬兰基本收入试验》显示,全民基本收入对就业和收入影响都不大,但民众的幸福感上升了。值得注意的是,当芬兰研究机构表明,要保证全民基本收入可持续运行,需要将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到55%的时候,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芬兰人比例从70%下降到了30%。②[英]托马斯·史班达:《那些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事儿》,《IT 经理世界》2018 年第7 期。
韩国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项目是从2019 年4 月开始实施的一项宏大的基本收入项目,其以基本收入思想为基础,融合了京畿道城南市青年津贴。青年基本收入项目不是中央政府委任的事务,而是地方政府的固有事务,是京畿道自身拥有财源的事业,旨在提高京畿道青年们的福利并助其建立稳定的生活基础。该项目特征如下:第一,每季度向在京畿道持续居住3 年以上或总计居住10 年以上的满24 周岁的青年(以每季度起始月份1 日为基准)发放青年分红;第二,每季度最多支持25 万韩元,最多支持4 个季度,每年一共支付100 万韩元;第三,京畿道内31 个市郡联合以地区货币支付,地区货币(商品券)的发行途径分为纸质、手机等,各市郡可根据地区情况选择单独或组合类型。青年基本收入虽然反映了相当程度的全民基本收入思想,但实际上与完美的全民基本收入存在一定差异。在基本收入的5 个构成要素中,青年基本收入部分满足了适用对象是所有满24 周岁的青年(普遍性)、不询问他们劳动与否(无条件性)、直接支付给青年个人(个体性)这3 个要素,但由于仅限1 年内支付4 次、用地区货币支付,从而未能符合其他2 个条件。青年基本收入大体上满足了基本收入的构成条件,只是由于现实原因出现了一些变化。
(三)全民基本收入实践案例可行性分析
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制度的可行性得到了实践验证。第一,该制度通过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等共享资源筹集资金,因此财政可行性很高。第二,为确保制度的稳健运行,阿拉斯加政府修改了州宪法,并建立了合理的政策体系,以平衡居民之间的关系,战略可行性方面也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第三,永久基金分红是无条件的、普遍的支付,不需要投入大量额外的管理费用,行政可行性得以提高。第四,阿拉斯加政府直接将基金收益作为现金补助支付给居民,这得到了居民的支持,具备充分的心理可行性。第五,虽然永久基金分红导致劳动供给有所减少,但劳动报酬的上升和分红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进而促进了消费,提高了企业的利润,企业也由此获取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①参见Ioana Marinescu, No Strings Attached: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U.S.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NBER Working Paper No.24337, 2018.
芬兰基本收入试验具有较高的可行性。第一,试验向每个参与者支付560 欧元,主要资金来源于对现有福利制度的重组,财政可行性方面具有充分的依据。第二,芬兰不仅采取社团主义性质的政府运营方式,而且具有政府与社会间长期政治协议的传统,同时拥有作为福利国家的丰富经验,从这一点来看战略可行性非常高。第三,作为实施基本收入实验的主体机构,芬兰社会保障局能够执行高达6.9%的GDP 的预算,具备了充分的行政能力。不仅如此,通过基本收入试验,执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职人员的官僚主义有所减少。②参见Olli Kangas, Ville-Veikko Pulkkam, From Idea to Experiment: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Publications of the Government's Analysis,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Prime Minister's Office, Helsinki, Finland, 2016.第四,芬兰民众对基本收入没有强烈的反对心理。第五,试验结果显示虽然基本收入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但基本收入领取者的生活满意度比失业金的领取者更加高。
对韩国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如下:第一,该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向每位满24 岁的青年每年支付100 万韩元,因此财政可行性没有太大的问题。第二,该项目旨在增加地区货币量以促进地区经济,随着地区消费的提升,基本收入制度不仅让青年获利,同时为商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可能,因此战略可行性较高。③参见유영성, 김병조, 마주영, 경기도청년기본소득, 청년의반응과시사점, 경기연구원이슈와진단, no.384.第三,与筛选低收入阶层或贫困阶层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同,该项目以满24 周岁的青年为对象,无条件、普遍地发放补助,因此不需要过多的行政费用和时间成本,具备较高的行政可行性。第四,该项目仅限于满24 周岁青年,导致非该年龄层的人群出现了不满心理。第五,青年基本收入领取者的劳动时间每周增加了1.3 个小时,没有出现劳动时间减少或劳动诱因减弱等副作用。
综上,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制度利用共享资产提高了财政可行性和心理可行性,并形成跨越党派的政策联合,提高了战略可行性。芬兰基本收入试验是为了改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低效率问题而推进的,从而很容易达成政治协议,以此为基础的战略可行性很高。福利国家的长期传统也提高了财政可行性和心理可行性。此外,劳动供给和劳动诱因也没有减少,行为可行性也很高。韩国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项目为了提高战略可行性,试图通过发放补助来激活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障收入和自由消费的战略可行性有效果。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如能扩大对象范围则可以减少被排除的其他年龄层青年对制度的不满,政策效益也会更大。
与强调普遍性和无条件性的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原则不同,芬兰基本收入试验和韩国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项目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虽然为劳动年龄段的人们无条件支付现金,但最大受惠者其实是被排除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群体。全世界对这些全民基本收入实践案例的高度关注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未能用社会安全网实现充分保护的现实困境。因此,需要考虑如何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包容性。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当前的实践案例是否成功?
由于美国的实践案例局限于一个区域,芬兰的实践案例涉及的人群规模很小,韩国的实践案例则是面向一个特定群体,这使得很难明确区分实践案例的成功与失败。对于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集中统一的国家更是难以简单类比。因此,设定成功与失败的概念和范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进行实际的讨论,以下内容排除了实践案例成功和失败的模糊领域,对“实践案例是否达到预期目的、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和消极结果”进行重点探讨。
首先,美国阿拉斯加州意识到经济存在的问题,即基于自然资源的经济是缺乏稳定性的,商业收益不会回到居民手中。因此,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州宪法制定了居民可以通过石油资源采集来分享收益的法律依据。自1982 年以来,石油资源的投资收益一直作为财源,每年向所有居民发放1000 至3000 美元的永久基金分红,劳动供应虽然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出现劳动积极性下降的情况。①参见Damon Jones, Ioana Marinescu, The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Universal and Permanent Cash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4312, 2018.分红不仅带来了可支配收入增加和消费增长,还产生了一系列积极效果,如就业率增长、金钱相关的犯罪减少、低收入家庭新生儿体重增加、婴幼儿肥胖度减少、贫困率下降、不平等减少、地区经济更加活跃等。1999 年曾有人提议取消永久基金,但在居民投票中,84%的阿拉斯加居民表示反对,这可以解释为居民承认和肯定永久基金分红带来的效果。当然,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是依靠石油资源的投资收益,可以不用太依赖税收。有人指出,每年分红金额不同,数额也不充分,与基本收入有些不同。因此,为了研究引入基本收入的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芬兰和韩国已经试验的基本收入制度。
芬兰基本收入试验和韩国青年基本收入项目是在政府的领导下,以一定的实验及业务目的实施的。芬兰基本收入试验旨在通过支付基本收入增加劳动力市场参与,并减少与社会保障相关的行政费用。两年的实验结果显示,对比基本收入领取者和失业补助领取者两个群体,就业促进效果并不明显。基本收入群体的雇佣天数(1 年平均78 天)比失业补助领取者群体的雇佣天数(1 年平均73 天)多出约5 天(8%)。然而,在关于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的问卷调查中,基本收入领取者的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等都有所改善,不仅如此,基本收入领取者感受到的收入苦恼、精神压力、忧郁感、悲伤、孤独等比普通失业者要少,记忆力、注意力等认知能力也更加向好。②参见Olli Kangas, et al., The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2017-2018 in Finland: Preliminary Results, Reports and Memorandums of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Helsinki, 2019.因此,评价分为两派,基本收入怀疑论者认为没有雇佣效果就是“失败”,而基本收入支持者们则关注积极效果,他们认为,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得到了改善,这些会对促进雇佣有间接促进效果。
韩国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项目的实施是为了促进青年参与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权利、增进地区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要看到就业效果,而是要看到青年政治意识和福利意识的变化以及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青年基本收入对心理健康、运动频率和饮食产生了积极影响,带来了幸福感,也带来了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增加了对平等社会的认识,在人生梦想、想象力、希望、乐观性、恢复弹性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有意义的结果。①参见유영성, 윤성진, 정원호, 김재신, 마주영, 김교성, 백승호, 서정희, 조문영, 한치록, 김미리, 이지은,경기도 청년기본소득 정책효과 분석(II): 사전 및 사후조사 비교, 수원, 경기연구원, 2020.
综上,三国的政策目标非常不同: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制度以分享自然资源收益为目的;芬兰基本收入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就业;韩国京畿道青年基本收入项目是保障青年基本收入的社会政策,跟劳动市场参与无关。就美国、芬兰、韩国三个国家的全民基本收入实践案例的结果而言,虽然没有产生就业诱导效应,但稳定的基本收入可以减轻生活压力,从而改善领取者的身心健康。
(二)推进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对政治家来说,毫无条件地向所有国民提供保障基本生活的收入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承诺,但将其制度化的学术依据却非常薄弱。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以国家为单位来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案例。在财政状况非常薄弱的国家,全民基本收入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全民基本收入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来源,政府必须有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筹资的主要方法包括国家的债务负担、支出调整型政策和增税等,②参见Ugo Gentilini, et al., (eds.), Exploring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 Guide to Navigating Concepts, Evidence, and Practices, The World Bank, 2020.但是这三种方法都不容易实现。增加国家的债务负担有其上限,而且最终会给未来一代带来负担,因此反对声音很大。支出调整政策也称为支出增减型政策,通常指通过调整政府的支出规模来应对社会保障问题,主要通过削减财政支出、财政补贴改革、公共部门改革等措施来筹集资金。然而,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时,调整政府的支出规模并不简单。在主张推进全民基本收入者之间,也存在着反对取消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意见。
目前讨论最多的财源安排方案就是增税,大多数全民基本收入支持者也主张通过增税的方式来筹集财源,但是未能达成国民充分共识的增税很有可能遭遇强有力的反对。例如,提高向企业征收的法人税或财产税,将难以被企业所接受。即使通过提高增值税等,让所有国民按照消费的一定比例缴纳增税的方式抵补财源,也还是阻力重重。为了通过增税筹集用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财源,首先要增进国民对增税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认识和共识。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分红制度表明,在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方面,筹集财源是可能的,重要的是需要改善人们对筹集财源的认识。为了稳定实施全民基本收入,不仅要在国民共识和社会协议的基础上,准备充分的财源,维持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和雇佣支援制度,还要在税收制度上进行大胆的改革,协调其与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三)全民基本收入与社会保障是何关系?
大多数主张基本收入的讨论指出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性。许多发达国家为了支援儿童、老人、残疾人等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最低生计,实施了儿童津贴、老年人津贴、残疾津贴等制度,但其给付金额太少。另外,在经济活动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无法从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中得到任何支持。基于这些原因,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认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
在理解基本收入时,将其与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比较,有助于衡量其定位。目前,普遍性与选择性原则在许多国家是相伴而行的,这些国家在逐渐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全方位满足国民对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需求,最终迈向福利国家。而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则提出全部替代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全基本收入制度,或提出部分基本收入制度和参与性基本收入制度。前者主张合并或废除现行现金支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其转化成基本收入进行支付;后者则主张在缩小和改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引入部分基本收入。无论是完全基本收入还是部分基本收入的支持者都认为,基本收入的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使人们免于焦虑的自由和解放。①参见Philli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通常,主流立场是引入部分基本收入制度,取代和改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
(四)全民基本收入的实践案例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理论和模式多种多样,正处于形成支配性模式的过程当中。学界和政界在区分对象、收入水平、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替代幅度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观点。全民基本收入具备消除臃肿的官僚制度、减少污名效应和福利死角地带的潜力,并有助于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这将重新定义工作与福利的关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部分运用了全民基本收入理念,以青年一代为中心,在保障收入、促进社会参与和消费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再分配作用尚不明确。
尤其是作为对策方案,应该制定全民基本收入的基本条件的标准。在它被引入时,有必要优先审查其是否可取、是否可行,然后讨论可成就性。②参见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Verso, 2010.可取性是评价替代方案所指向的目的、价值、社会、政治正义等的标准,可行性是评价变革性替代方案能否在该社会的历史脉络、文化脉络、社会对替代方案的信任以及其他附带条件可以实行的标准,可成就性是讨论变革性备选办法时评估当前社会条件下该替代方案能否实现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无法确切知道哪些是可行的未来选择。因此,如果方案是可取的,则有必要扩大人们对其的信心,以扩大方案实现的可能性空间。
对中国而言,共同富裕是明确的国家现代化目标,而公有制无疑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③郑功成:《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新制度文明》,《社会保障评论》2023 年第1 期。然而,中国作为快速发展但又存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偏大现象的人口大国,短期内并不具备实现完全基本收入的条件,因此,现阶段考虑实现部分基本收入的阶段性方案会更加有效。建议在地方政府层面优先针对低收入者、残疾人、青年和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实施部分基本收入制度。与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共存的部分基本收入制度可以在有限的水平上进一步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为了提高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需要通过部分基本收入制度验证全民基本收入不会破坏社会劳动伦理,而是可以使各种社会活动成为可能,对社会发展是积极的。与此同时,为了使部分基本收入制度可行,需要其与现行社会救助制度相辅相成,并设计制度以提高人们对其可行性的心理认知,证明部分基本收入制度的社会效益。财政问题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完全基本收入制度需要高水平的增税,从这一点来看,其可行性也很低。然而,通过调整税收结构、推进税收制度的合理化等,部分基本收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实现,因此可行性较高。
总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是把社会成员统合起来,以共同体的维系、发展作为原动力来实现其运作,并在此过程中定期向所有公民提供一笔收入,用于购买日常所需的物品和服务。①参见[英]盖伊·斯坦丁:《基本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年。这将促进购买力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创造,从而为生产活动奠定物质和财政基础,使多种生产方式成为可能。从这一逻辑来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既是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促进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