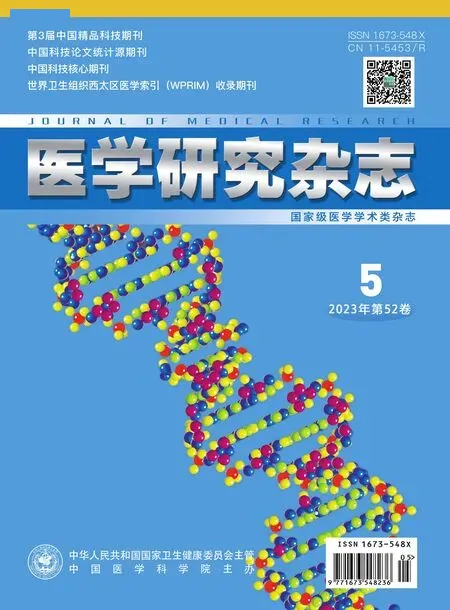胃肠道微生物群与胃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2023-09-06唐宝元田彬彬罗长江
唐宝元 田彬彬 刘 倩 魏 红 罗长江
人体胃肠道微生物群是一个主要由病毒、真菌和1000多种细菌组成的微生态系统,其中许多微生物参与了新陈代谢和免疫调节的过程,对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重要作用[1]。研究表明,胃肠道微生物群可以通过诱导细胞氧化应激、DNA损伤和慢性炎症来促进癌变[2]。胃癌是消化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胃癌的病理演变中,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是慢性胃炎向胃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故称之为胃癌癌前病变(gastric premalignant condition,GPC)[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胃肠道微生物群在GPC和胃癌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癌发生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但研究表明只有3%的幽门螺杆菌患者最终会发展为胃癌,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根除幽门螺杆菌后仍会观察到癌症进展[4]。因此,在胃癌发生中,胃肠道中的其他微生物群可能与幽门螺杆菌发挥协同作用,并且,其他细菌、真菌与病毒也可能与胃癌的发生有关。Coker等[5]研究发现,胃癌与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和肠化生等疾病之间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度的差异,表明微生物生态失调也促进了胃癌的发生。本文主要就不同种类的胃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物以及菌群失衡与胃癌的关系进行综述。
一、健康人体的胃肠道微生物群
过去人们认为健康人体的胃是无菌器官,胃部的强酸环境也被认为不利于细菌和真菌的定植,但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和培养消除了胃是“无菌器官”的传统观念,分子技术的发展也证明了胃内存在多种微生物群落[6]。并且,不同的细菌群落会定植在胃的不同区域,根据丰度不同,可将其分为优势微生物群落和次级微生物群落[7]。目前,胃肠道微生物群形成的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明,人们普遍认为幽门螺杆菌感染,长期使用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等多种因素都可以改变胃肠道微环境并影响微生物群的定植[8]。总体而言,变形杆菌、厚壁菌、拟杆菌、梭杆菌和放线菌门是健康受试者胃微生物群的主要细菌成分,而乳酸杆菌、链球菌和丙酸杆菌是胃中最具特征性的细菌属[9]。
真菌在胃内微生物群所占比例很低,但真菌也是人类胃肠道微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健康成年人的胃肠道都可以检测到真菌,人类胃肠道中最常见的真菌属是念珠菌属、酵母菌属和枝孢菌属[10,11]。胃肠道真菌群落不仅在维持胃肠道稳态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以与其他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调节人体免疫系统[12]。由于对真菌菌群的研究较少,人体免疫系统和真菌的相互作用尚未明确。Zhu等[13]研究发现,肠道真菌可以引起细胞炎性反应和肿瘤发生,表明其作为潜在的病原体不容忽视。肠道微生物中病毒的组分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年龄、生活方式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微生物群。近年来研究发现,人类疱疹病毒7(human herpesvirus 7,HHV-7)可能与胃上皮细胞中胃蛋白酶原等基因的转录和表达增加有关,并且其有助于保护和修复胃肠道黏膜[14]。综上所述,尽管人们对胃肠道微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关于胃肠道微生物群调节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机制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胃肠道微生物群在不同胃病中的潜在致病作用。
二、胃肠道微生物群与胃癌的关系
1.细菌:近年来许多研究证实,胃病患者与健康个体的胃肠道菌群在组成、数量和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可以诱发胃炎、胃溃疡或其他胃部疾病,促进了GPC和胃癌的发展。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引发胃癌的主要因素,其通过多种机制引发慢性炎症,胃黏膜免疫功能抑制和胃酸分泌减少,直接或间接促进GPC和胃癌的发生、发展,根除幽门螺杆菌可以预防胃癌已经成为共识[15]。然而,一些研究指出,根除幽门螺杆菌会引起胃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发生改变,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减弱,进而促进胃癌的进展。因此,正常胃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的改变也可能会引起胃癌。
研究表明,Ⅱ型固有淋巴细胞(type Ⅱ innate lymphoid cell,ILC2s)维持了胃菌群在人体内的平衡,并且,ILC2s的存在依赖于胃内微生物群。幽门螺杆菌可能会引起胃肠道微环境的改变,导致胃内菌群失调,进而通过维持黏膜表面的慢性炎症,诱导遗传毒性来促进胃癌的发展[16]。一项回顾性研究通过16SrRNA测序的方法分析了胃活检样本中的细菌成分,研究发现,在根除幽门螺杆菌1年后的胃炎患者中,鲁氏不动杆菌、咽峡炎链球菌和罗尔斯顿菌增加,而罗氏菌属和鞘脂单胞菌属的数量下降,并且在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胃炎患者中检测出不动杆菌属、罗尔斯顿菌属、放线杆菌属和欧文菌属的富集。研究还发现,胃萎缩和化生的持续进展可能与链球菌、细小单胞菌、普雷沃菌、罗思氏菌和粒状菌等病原微生物的增加有关[17]。上述研究表明,单独的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并不能防止GPC的发生,胃肠道菌群的改变也会促进GPC和胃癌的发生。
微生物群多样性与胃癌之间的关系尚在探索中,但已有一些研究表明,微生物菌群失调可能与胃癌的发生有关。目前,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幽门螺杆菌对胃肠道微生态的影响[18]。一些研究认为,幽门螺杆菌定植对胃肠道菌群的影响并不明显。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幽门螺杆菌的定植可以改变胃肠道微环境,使得条件变得适合某些微生物群落,但不再适合原始微生物群落的生存[19]。与慢性胃炎患者比较,胃癌患者中螺旋杆菌和奈瑟菌的丰度明显降低,而无色杆菌、柠檬酸杆菌、叶状杆菌、梭状芽胞杆菌、红球菌和乳酸杆菌的丰度显著增加[20]。此外,通过计算生态失调指数发现,与使用单个菌属比较,生态失调指数可以提高检测胃癌的敏感度和特异性,这表明微生物群落的改变比单个种属群的变化更有助于胃癌的发展[18]。综上所述,幽门螺杆菌是导致胃癌发生的主要细菌,但胃肠道微生态失调也会引起胃癌进展。并且,胃肠道菌群组分和丰度的改变可能与各种胃肠道疾病的发生有关。
2.真菌:虽然真菌菌群在胃肠道肿瘤中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研究,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真菌菌群失衡与癌症的发生有关。研究表明,在健康人体中,白色念珠菌与其他真菌和细菌共同维持了胃肠道微环境的稳态[21]。但有研究发现,胃内的白色念珠菌通过降低胃中真菌的多样性和丰度来介导胃癌的发展,并且,白色念珠菌在胃癌患者中过度定植,具有作为胃癌生物学标志物潜力。此外,有研究发现,缺乏C型凝集素受体dectin-3会触发异常的免疫细胞代谢和致瘤细胞因子信号转导,使得白色念珠菌数量增加,直接促进结肠癌的发生和发展。并且,白色念珠菌超负荷引起会小鼠肠道上皮巨噬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7,IL-7可以诱导IL-22的分泌,促进胃肠道炎症和癌症发生[22]。综上所述,真菌可能参与了胃肠道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但是,由于对真菌微生物群的分布及其功能知之甚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胃内真菌的丰度和多样性的改变对胃肠道疾病中的潜在致病作用。
3.病毒:病毒也是肠道微生物群的一部分,在人体内的比例低于细菌,但已证明病毒在胃肠道内微生物生态系统中稳定存在。病毒可以通过改变在胃肠道微生物的丰度、感染上皮细胞或调节细菌群参与胃肠道癌症的发病。目前,已知有几种病毒与癌症的发生有关,包括巨细胞病毒、人疱疹病毒8、人乳头瘤病毒、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和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其中,EBV是最先被发现与人类肿瘤相关的DNA病毒。据估计,EBV相关胃癌(EBV-associated gastric cancer,EBVaGC)占全球所有胃癌病例的10%。EBV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涉及其自身基因的表达和宿主基因组的调节。有研究指出,EBV主要通过与其感染的B淋巴细胞进入胃上皮细胞,随后,EBV基因组作为游离基因被转录为EBER、EBNA1、LMP1、LMP2A、BARTmiRNA和BARF1,其中, EBNA1和LMP2A可以通过宿主抑癌基因启动子的CpG岛甲基化促进肿瘤发生[23]。EBV非编码RNA(EBV-non coding RNAs,EBERS)通过下调miR-200家族基因,降低E-钙黏蛋白表达是EBV致癌的关键步骤。此外,EBV与幽门螺杆菌在促进慢性炎症和组织损伤,以及细胞癌变的过程中具有协同作用。
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血浆EBV水平是胃癌复发和化疗敏感度的良好标志。血浆EBV水平在手术和化疗后降低,并在疾病进展期间增加,这些结果表明,EBV在胃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EBVaGC具有明确的分子特征,TCGA分析显示,80%的EBVaGC具有PIK3CA突变,以及JAK2、CD274(PD-L1)和PDCD1LG2(PD-L2)基因的扩增。ARID1A(55%)和BCOR(23%)基因的突变也很常见,而TP53缺陷在这种胃癌亚型中却不常见。
PD-L1的过表达是EBVaGC的特征之一。有研究发现,PD-L1高表达的EBVaGC细胞强烈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并且IFN-γ信号通路参与了PD-L1的表达上调。将EBVaGC细胞与PD-1阳性T淋巴细胞共培养后,EBVaGC细胞周围的T淋巴细胞生长停滞在了G0/G1期,而用抗PD-L1药物处理EBVaGC细胞后可以部分消除T淋巴细胞的生长停滞[24]。此外,EBVaGC内高密度的 CD8+T 细胞和低密度的 CD204+巨噬细胞组成的特定肿瘤微环境有助于肿瘤的进展及其免疫抑制[21]。因此,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可能会使EBVaGC患者获益。综上所述, EBV通过多种方式促进癌症发生和发展,EBVaGC是与EBV感染相关的一种独特胃癌亚型,进一步探索EBV感染在胃癌发生中的具体机制,将为EBVaGC的肿瘤和预防提供有效的线索。
三、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与胃癌的关系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在胃肠道肿瘤发生和进展过程种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包括包括短链脂肪酸 (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多胺以及N-亚硝基化合物和乳酸。其中一些细菌代谢产物如多胺,可以引起细胞周期的改变,并通过转录和表观遗传调节免疫反应,在肿瘤发生及其免疫抑制中发挥重要作用[25]。SCFAs主要由不消化的碳水化合物经细菌酵解而成,主要包括丁酸盐、丙酸盐和乙酸盐,有研究证明,丁酸盐有利于维持微生物群的稳态和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可以抑制炎症和肿瘤的发展。此外,在胃癌早期,脲酶和细菌鞭毛的合成显著减少,碳水化合物降解减少而糖酵解增强,表明微生物代谢产物可以影响细胞的代谢和正常的生理功能。综上,微生物代谢产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调节细胞的代谢以及人体的免疫反应,进而影响癌症的发生,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为饮食、肠道菌群和癌症发生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理解。
四、展 望
目前,胃肠道微生物群在胃癌病理机制中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但研究者已经确定胃肠道微生物群与胃癌的发生机制密切相关。不同的微生物群都可能影响胃癌发生和进一步发展,但环境和宿主遗传等因素也会影响致癌过程。因此,不能单一分析癌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落,而忽略了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生理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肠道微生物群的作用机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通过对胃癌患者的微生物群进行分析,筛选出胃癌中高度特异的微生物群,特殊菌群及其代谢物可以作为胃癌的潜在预后、诊断和治疗标志物。此外,根除某些细菌可以带来短期的疗效,但也会导致菌群失衡,促进疾病进展。因此,未来研究应该将胃肠道菌群视为人体微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试图从共生的角度来恢复机体与微生态系统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