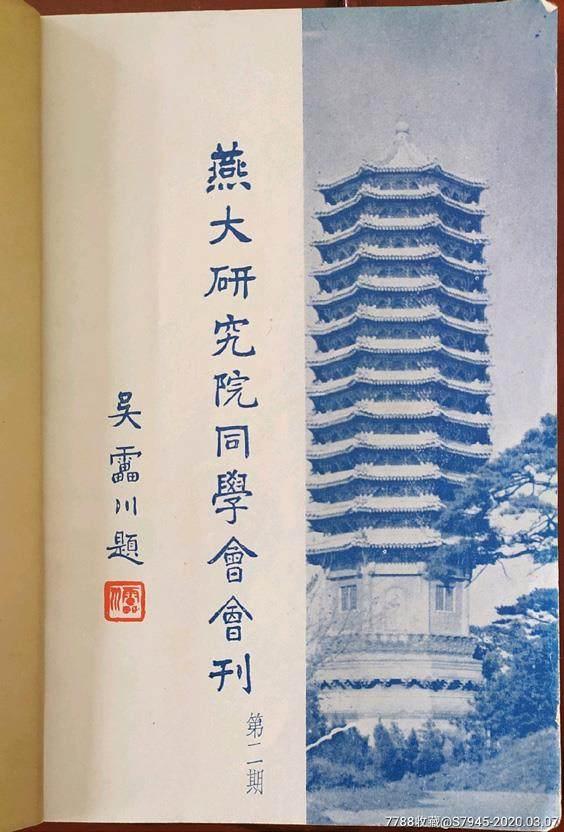燕京大学简史:一座园、众新人
2023-09-05叶飞
叶飞

自洋务在华夏大地推行以来,如同文馆、清华学堂、南开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等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开始建立。这其中,燕京大学你或许很熟悉,但多少有些模糊,而它的重要性一定超乎你的想象。谭其骧、侯仁之、韩素音、王世襄、宋淇、吴兴华、周汝昌、资中筠、黄宗江、齐思和、贺宝善、王钟翰、张芝联……这些都是燕大培养的大师。燕京是北京的另一称法。燕得名于召公姬奭受封于“北燕”,燕地也曾短暂被称为匽,燕与匽本是通假字。
1918年,通州协和大学(长老会和公理会合办,1889年建)、北京汇文大学(卫理公会1888年建)重组成一所大学,起名Peking University,这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由程静逸启发命名),不过稍晚些时间,其英文名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改组后,校长一职需要一个中间人或利益无关者来做,经过几次邀约和被拒,邀约发给了司徒雷登。1919年后,燕大历任校长有司徒雷登(1919-1929、1937-1945)、吴雷川(1929-1933)、梅贻宝(1942-1946)、陆志韦(1934-1937、1945-1952),其中司徒雷登是最重要的校长。
校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父亲曾创办一所学校,也曾参与创办中国第二座女子学校,后并入了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1371年,罗伯特·司徒(Robert Stuart)成为苏格兰罗伯特二世国王。但后来,家族受到宗教迫害,遷徙北爱尔兰,以及美洲。在其家族故事中,较重要的还有,叔祖父约翰·托德·司徒(John Todd Stuart)曾与林肯共事。
在10至20多岁时,司徒雷登多数时间在美读书,他先后就读于潘达珀斯学院、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等学校。最终,司徒雷登选择回到中国做传教士。
1904年,司徒雷登再回中国时,他所见全部都是太平天国破坏后的痕迹,街道上刚有零星的摊位,郊区乡村反而相对完好。然而,司徒雷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开创的事业中,他曾执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并创办之江大学前身的育英学校。
与此同时,1900年代、1910年代,清政府和国民政府被动或主动向欧美“列强”敞开,西方的机构、基金会、人物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的格局也随之改变。司徒雷登在赴京接任时就决心,让燕大根植在中国的社会中,并且不受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筹建校园和筹办学科的时候,司徒雷登在中美进行了大量的宣讲和募捐。美以美会、美以美会差会、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等基督教差会,以及洛克菲勒财团、普林斯顿财团等机构给予燕大以相当大的赞助与支持,其中铝业大王遗嘱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执行人向燕大捐款150万美元(其中部分用于创办后来名重一时的哈佛燕京学社)。
墨菲的园
燕大的主要建设者是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来北京后,司徒雷登开始为燕大寻找新址,大多花时间骑驴、骑自行车到处看。直到有次在清华大学,同行者向司徒雷登指出隔壁一块空地,而这已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先前他的努力主要在北京城及其近郊,但涉及产权等原因都无法执行。而燕大所涉及的米万钟的勺园、康熙皇帝的畅春园、和珅的淑春园、王绵愉的鸣鹤园、奕訢的朗润园、奕譞的蔚秀园……一一赎买也相当麻烦。
墨菲采取的策略是“中国建筑复兴”(renaissance ofChinese architecture),或者“具适应性的中国建筑复兴”(adaptive renaissance of Chinesearchitecture)。不过从具体的施行来看,墨菲更像是推销商,燕大的建设更像是他商业版图的一环。
1910年代,中国园林开始被西方命名为伟大的文明成就,它“亲近自然”的特性被清晰地标记出来。1914年,墨菲来北京首次瞻仰故宫即紫禁城,他在其中感到震惊,在一封报道里他将其与希腊式、哥特式作比。其时,无论是刚恒毅,还是梁思成,都在采用中国化的方式治理中国建筑。如梁思成所言,中国新建筑师应该认真地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构架、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致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讥。
虽然墨菲采纳的是中国园林、中国风景,但是其最后落成的建筑却与其有相悖之处。最典型的是,墨菲没采用“面南而王”,而采用的是“西向为尊”,也即燕大的立面和入口是相当西式的。墨菲在燕大即将竣工时写作了《建筑中国》(Building in China),文中以“新瓶装旧酒”概括自己的建筑理念。后来燕大人自己也认识到,燕大校园是由各种旧日园林以及“零零碎碎的小组织”“七拼八凑而成的”。
曾在燕大教英国文学的包贵思(Grace M. Boynton ),也兼研究中国园林。包贵思用其在中国的见闻、游历、研究,写作了小说《河畔淳颐园》(The River Garden of PureRepose)。小说讲述了抗战时期在华美国人简·布里斯苔德病重,并在某处疗养的故事,但主角更像是那座园林。包贵思也曾这样描述朗润园:“房外小桥流水,短篱曲径,具有中国古典苑林建筑的幽静雅致;室内铺着地毯,沙发壁炉,又有着西洋客厅的舒适温暖。课余她除了从事中国苑林艺术研究外,最喜欢组织朗读会,约同学们晚间去她家。”
博雅塔非木结构,而是混凝土预制而成,它的功能是供给自来水。博雅塔的建设以通州燃灯塔为蓝本。在唐克扬看来,博雅塔规范了它所从属的外部空间,但它本身却不保有可以居住或登临的空间,也不符合“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的高妙定义,而它似乎内外脱节,“形式主义”严重,却是一座实实在在,而大名鼎鼎的“实用”建筑。
1929年10月1日,燕京大学在海淀新校址上隆重举行了正式迁校的仪式,同时举办了开放参观活动。
迁入新址这一年,冰心漫步其中,直感叹“美轮美奂”。由于来得晚,冰心入住了外籍教师所居的燕南园53号,早西餐,午晚中餐。冰心像“婴儿”一样做教授,与学生们交知心、话生命,交往甚多,如王琇瑛、林耀华。
而十年前正值五四运动,新思潮空前高涨,冰心看到,新式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学生群体争先购买、传阅。为冰心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的鲁迅,《狂人日记》批判力度不可谓不强。差不多同一时间,协和女子大学改成燕大女校,“哲学”“教育学”等课程在男校上,“社会学”“心理学”等在女校上。男女合校还尚开创,男学生和女学生都比较拘谨、腼腆,女生到男校读时事先会把头上的玫瑰花蕊摘下。与男学生不同,女学生有监护人。
战与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大学纷纷南迁,而独有燕大留守。根据《燕大三年》,沦陷区的青年们不甘忍受“奴化教育”,又来不及撤退到大后方,唯一的希望就是“走向燕京”,而燕大也宛如一座孤岛,它身为教会大学,收容了很多革命党人和遗老遗少。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教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还睡在自家花园里,被远近的枪声惊醒后,她几乎没意识到战争正迫近,而平日里,海淀警察与日本“便衣人”的对决也尚未入其耳目。
迟至11月,《燕京新闻》才发布“学生生活条例”,规定社团组织“以无政治目的的活动为限”等。
司徒雷登认为,当时当地,大学应为学术之“净地”,以及社会之鼓呼。“其一,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净地,应不受时局的侵扰,不受偏见与宣传的影响,可以自由进行教学工作,于知识的探求与应用外,别无目的;其二,大学应与其所在的社会、国家发生密切的关系,自视为外在环境中不容割弃的一部分,并从环境中汲取新的材料、动力,以应付国家的需要,包括危机时刻的特别需要。这两种特性并不冲突,因为大学在国族延续中的特殊功用,及对社会所能履行之义务,是以保持自身的绝对自由与清白为前提,但绝非以与世隔绝的方式,保持其自由与清白。”

根据《燕京新闻》,燕大学生注册人数1937年秋是499人,尚有所下降,但到了1938年后不降反增,到1939年秋竟达978人之多。周汝昌就于1939年从一法国教会学校考入燕京大学。
在萧乾的回忆录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杨刚(杨缤)与萧乾多有书信往来,信中内容多是革命宣言。有次两人漫步,萧乾冒出一句,“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果!我要采访人生。”杨刚反问道,“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在司徒雷登的治学方针下,燕大特别重视社会实践。燕大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服务实践,应该是于1920-1921年师生共同参与的华北五省的旱灾赈济工作。事后,学生制作了《燕京大学青年会赈灾报告 (1920-1921) 》。冰心为其撰写了发刊词,她感受到“在1921年的时候,社会服务的精神,已经蓓蕾萌茁”。
科系规划
1922年,燕大开设社会学系,燕大是中国较早成立社会学系的大学。此前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清华大学等也曾开设社会学课程,部分大学也主持了社会学系。1918年到1919年间,步济时(J. S. Burgess )、甘博(S. D. Gamble)仿照春田調查(spring field survey ),在京开设大规模城市调研,这就是后来名扬一时的《北京:一个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 )。此后,一股“社会调查热”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燕大学生费孝通(1929年到1933年在校)不满于此类肤浅的社会调查,提出“要理论”和“社会学中国化”,谋另一种社会调查,梁漱溟、晏阳初、陈翰笙等人主持的社会调查使中国社会学步入了新的阶段。
1924年,燕大开设新闻系,仅比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晚三年。聂士芬(Vernon Nash)、梁士纯、蒋荫恩等先后担任系主任。燕大新闻系可以说是密苏里模式(missouri model)在中国的托钵者。1908年,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在密苏里大学开设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沃尔特·威廉的教学与实践很快成就了一段学院传奇(college saga),它被称为密苏里模式。
密苏里模式概括来讲就是“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需知,新闻教育的发生与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提出,沃尔特·威廉于1914年制定的《新闻记者信条》正是在此氛围下开始落地。由于方针得当、实践有方,密苏里的学子还是扎根在业界,形成“密苏里帮” ( missouri mafia),为读者所知的埃德加·斯诺就是“密苏里帮”的一员。沃尔特·威廉多次访问中国,还曾协助燕大新闻系为其提供赞助。
仿效美国新闻模式办学,并取得相当成就的,非燕大莫属。燕大学生自主创办了新闻学会、以及学报《燕京新闻》(首称《平西报》),并围绕燕大新闻学系协助委员会与报界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报界名流不少也赴燕大任教,包括成舍我、张友渔、斯诺、张恨水、罗文达(Rudolph Lowenthal)、田丕烈(Harold John Timperley)等。其时国内媒体驻外记者多是燕大人。萧乾、叶祖孚、徐宝璜、赵泽隆、张馨保等都是燕大的毕业生。新闻系也越来越受到追捧,根据1946年注册学生人数统计表,文学院九系共303人,单新闻系就约占三分之一,83人,比仅次的西洋语文学系和历史系加起来还要多。
1928年,燕大由历史学系师生成立历史学会,及《史学年报》。从1929年5月20日第一期到被占前,《史学年报》共发行12期,韩叔信、周一良、侯仁之等先后任主席。除此之外,裴文中成立的史前博物馆,顾颉刚等主持的《禹贡》半月刊,萧一山、姚从吾等的讲座讲义,也是燕大历史系的重要痕迹。历史系师生积极联络外界,比如邀请埃德加·斯诺等展演纪录片和幻灯片。
1934年4月,《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后,燕大与清华大学的师生也轮流主持、编辑。而随着局势加深,师生们主持编撰很多通俗读物,以及民谣、大鼓书等书册。1938年,历史学会及《史学年报》十周年纪念,齐思和特表,“反视国内其他同类刊物,或发刊数期而中途夭折,或昙花一现而寂焉无闻。及至今日,惟本刊硕果仅存,巍为灵光,实非始愿所及,则同人亦不得不私自庆幸矣。”
1929年,燕大开设音乐系,由范天祥夫人(Mrs Mildred Waint)任系主任,此前音乐仅为艺术组内的选修。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发轫于1910年代,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中华美育会、西什库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上海国立音乐院等先后建立。在范天祥的带领下,燕大不仅教授西方音乐,还务实于中国音乐。学生群体每周会办一次“留声机音乐会”。其学生中,阎述诗、李抱忱、李维渤都曾为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不少贡献。
除此之外,周作人的新文学讲义、吴兴华的德文翻译,都是值得记录的故事。
1951年2月12日,人民政府正式接管燕大,燕大成为公立学校。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序幕的拉开,燕大最终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虽然燕京大学不再存在,但是围绕燕大的故事仍在继续,它的体系和魅力经由活生生的人物不断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