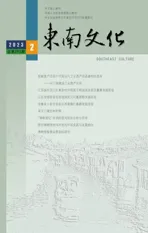“博物馆化”术语的使用现状分析与思考
2023-09-05黄洋
黄 洋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学界目前关于博物馆学的很多术语尚未达成共识,有时使用甚至较为混乱,这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术语是在描述博物馆业务工作中被创造的,另一方面是学界对不同术语的含义有不同理解。“博物馆化”对应的英文为musealisa⁃tion 或musealization,西班牙文为musealisación,德文为musealisierung,意大利文为musealizazione,葡萄牙文为musealisaçāo。该术语为博物馆学研究中的重要词汇,同时,其也被广泛运用在其他学科或领域。因此分析“博物馆化”的使用现状,厘清其内涵,对于今后学界准确使用该术语及博物馆学研究非常重要。
一、博物馆学研究中的“博物馆化”术语使用
“博物馆化”作为博物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术语,最早出现于何时?在博物馆学研究领域又是如何演变的?有学者基于1969—1986年在捷克布尔诺(Brně)出版的《博物馆笔记》杂志(Muzeo⁃logické Sešity)等,从博物馆(muzeálie)、博物馆性(muzealita)、博物馆化(muzealizace)三个术语探讨了“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brněnské muzeo⁃logické školy)的博物馆学思想。其中“博物馆化”一词是最晚出现的。布尔诺博物馆学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维莱姆·汉克(Vilém Hank)在1972年第4期的文章《未来博物馆》(Das Museum der Zukunft)中使用了“博物馆化”一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虽然许多学者也都探讨了博物馆对现实的定义,但这一术语并未被使用。该词直到1979年第7 期中才又出现,威廉·恩恩巴赫(Wilhelm Ennenbach)明确表达了对“博物馆化”的理解,使用的不是德语的musealisierung,而是musealisation。根据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的说法,这个英语发音的词有捷克-德国的背景,在英语中,museumization一词经常被首选,而在法语中则是museification。当然,恩恩巴赫也使用了术语musealization或muséalisation[1]。
通过检索发现,国外有关“博物馆化”的表述很多,musealization 与musealisation 最常见,这两种写法可以认为是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区别:美式英语的写法以zation 结尾,而英式英语则以sation 结尾。抽象名词后缀fication 来源于拉丁语,表示“……化”“做……”“使成为……”等含义,因此museumification 也表示“博物馆化”。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musealisation 与museumification两词才有所区别,在此之前,两词的含义通常被认为是相似的[2]。其实,两词虽然从构词意义上略有区别,但在实际使用中的含义基本一致。
首先,在博物馆学研究领域,更多学者将“博物馆化”置于博物馆学基础理论下研究,如基于斯贝尼克·斯贝斯拉夫·斯坦斯基(Zbyněk Zbyslav Stránský)提出的“博物馆化”概念进行探讨[3],或在环境语境下剖析物的博物馆化实现[4]。有学者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对“博物馆化”表征意义的研究,提出“‘博物馆化’是从原初情景解构与新情景再建构的过程”[5]。
其次,研究者跳出学科的基础理论,将“博物馆化”与博物馆事业发展联系起来,又开始关注实践。201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杰弗里·约翰逊(Jeffrey Johnson)指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是前所未有的博物馆建设热潮,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的彻底“博物馆化”[6]。有学者从“博物馆性”看到博物馆物数量与类型的扩张,即“博物馆化的拓展”[7]。博物馆化表现为博物馆数量空前的增长、博物馆化物件的扩大以及对博物馆感兴趣人数的大量增加[8]。博物馆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指的是安德烈亚斯·胡森(Andreas Huyssen)所说的“扩张的历史主义”(expansive historicism)以及与之相关的20世纪后半叶的博物馆热潮[9]。这些“博物馆化”都表达了博物馆数量的增加。
再次,在更具体的实践上,学界也用博物馆化来指代实体博物馆的建设。故宫文化的博物馆化是以对公众开放的古物陈列所和存放文物的宝蕴楼建成为表现[10],这都是博物馆建设的特征。文物建筑再利用的博物馆化就是成为文物建筑类博物馆,即依托古建筑建设的博物馆[11]。为了保护利用好珍贵古籍,其中一个方式是博物馆化,成立国家典籍博物馆[12]。可见“博物馆化”的含义就是将已有建筑改建转化为博物馆,大多表现为将不可移动文物建筑改建为博物馆,或新建博物馆。
二、遗产保护领域的“博物馆化”术语使用
遗产保护是与博物馆学紧密相连的领域。遗产博物馆化的逻辑终点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过去的艺术被视为全人类的遗产[13]。地方空间转化为遗产的过程被比作博物馆化的过程,因为它具有高度的仪式化、职业化和权威性。具体来说,城镇保护、考古遗址、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都使用“博物馆化”来表达不同意义。
(一)城镇保护“博物馆化”
城市更新、村落保护都是近些年遗产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以文化为主导成为城市更新的广泛策略,许多历史建筑被改造为博物馆,城市或考古遗址被打造为露天博物馆,博物馆和历史城市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
就城市而言,在宏观层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座城市就是一座大博物馆。博物馆的概念从单个建筑的边界扩展到历史城市本身,而这种扩张就可被定义为“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14]。城市大博物馆的概念从根本上讲,就是城市各种文化资源的博物馆化[15]。2004年日本松本市制定的“松本市全域博物馆化构想”也是将松本市全域视为一个露天博物馆[16]。在微观层面,城市细节的改造等都可以融入博物馆的方法和理念。如“博物馆化街道”是以街道为“展柜”,以街道设施为“展品”,以博物馆的理念将街道博物馆化,来展示城市地域文化特色,使街道成为“旧遗产的投影机、新文化的发生器”[17]。
就村落保护而言,博物馆化是将整个村庄和风景保存为博物馆、复古时尚、家庭和个人视频、电子数据库中的详细描述等当代现象(contempo⁃rary phenomena)[18]。我国台北的城中村经“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发展成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Treasure Hill Artist Village),这也是一个类似博物馆的机构(museum-like institution)[19]。这里的博物馆化主要是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大博物馆的意涵。
(二)考古遗址“博物馆化”
在西方权威遗产话语影响下,中国遗址保护试图用物质原真性概念将其凝固在过去,以致遗址利用长期局限于后工业时代的旅游化、博物馆化及遗址公园化[20]。关于考古研究的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阐明社区直接参与等都是博物馆化进程的问题[21]。波兰克拉科夫工业大学(Craco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以动态艺术装置的形式将考古遗址博物馆化[22]。我国台湾学者以台北十三行遗址为个案进行剖析,描述了遗址从文物陈列馆到遗址博物馆再到生态博物馆的“博物馆化”过程[23]。简单地理解,遗址保护的博物馆化就是将遗址打造为最重要的展品,与建筑一同构成完整的博物馆[24]。考古遗址现场保护大棚、考古遗址博物馆就是遗址博物馆化的典型结果。这样的现场博物馆化保护与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在于博物馆将展品移往展柜,而现场博物馆化是将展柜“扣”到展品上[25]。今天,欧洲对考古遗迹的“展示”中非常关注日益增长的“壮观化”需求,尤其是户外遗迹。道德规范让展览设计师必须平衡传统和创新的叙事方式,因为他们过度沉迷于强调和戏剧化技术,有可能取代真实的历史事件或文化信息建构,成为博物馆化行动的主角[26]。考古遗址博物馆化最简单的直接成果便是转变为考古遗址博物馆。
(三)工业遗产“博物馆化”
工业遗产的博物馆化保护广义上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传统博物馆方式对工业遗产中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一种是在工业遗产原址建立工业遗产博物馆[27]。对于矿区,有案例重新利用建筑物,将选定的采矿工业区、地下空间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将它们用作娱乐[28]。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俄罗斯很多国家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博物馆化出现了新目标和新范式,即提高城市环境的表现力和人性化,形成创意空间和“人力资本资产”(human capital assets)[29]。俄罗斯学者考察了伊万诺沃州(Ivanovo oblast)尤扎(Yuzha)的一个工厂,描绘了这座由工厂建筑、医院、学校、俱乐部和其他物品组成的历史建筑群的“博物馆化”前景[30]。此外,也可以在文化和工业旅游之下将工业遗产博物馆化(musealização)和就地保护[31]。1960年,查尔斯·施耐德(Charles Schneider)去世后,施耐德家族在法国勒克佐(Le Creusot)的工业及城堡的何去何从成为大问题,奥克塔夫·德巴里(Octave Debary)认为其可通过“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的方式变为生态博物馆[32]。可见,工业遗产博物馆化的主要途径是基于原址建立工业遗产博物馆。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化”
从苗族服饰[33]、无锡惠山泥人[34]等非遗项目到民间艺术[35]、手工艺类[36]非遗门类,再到国外的拉丁美洲土著遗产[37]等,这些研究中的博物馆化都是从建设博物馆的角度论述。也有学者认为民俗的博物馆化是“退而求其次,是无可奈何之举”[38],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博物馆化是一个大的概念,是现代社会给传统文化的一个宽敞位置[39],是必要的[40]。也正因此,当下各级政府从出台的政策法规到实践层面,都在建设综合或专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三、旅游及其他领域的“博物馆化”术语使用
“博物馆化”也在旅游领域广泛使用。18世纪和19世纪初,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等名人的出生地成为旅游目的地,他们的住所也发展成为博物馆,这些房子的早期导览指南都记录了旅游文化和博物馆的类似做法[41]。当下旅游中的“博物馆化”现象日趋明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是如此[42]。
“旅游景观吸引系统的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是旅游社会学研究中对旅游景观吸引系统发展范式的理论提升。旅游景观吸引系统‘博物馆化’的核心是旅游景观借鉴‘博物馆’在展示内容、展示手段和解说系统等方面的强大功能,充分挖掘旅游景观的文化内涵,综合展示景观的资源风貌及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的景观发展模式”[43]。旅游景区的博物馆化是以博物馆模式进行景区开发[4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文化、商业机构的博物馆化[45],越来越多的非博物馆组织也开拓收藏部分,大部分以投资为主,也对外开放,同时有许多机构为博物馆提供展览空间[46]。古典园林[47]、工业遗产[48]、宗祠[49]、宗教场所[50]的博物馆化,都是将这些机构变成博物馆,但在过程中也会运用博物馆方法等,如公园景观的设计[51]等。商业机构、医院、学校等机构都可以博物馆化。如商业机构受博物馆的影响,创造出与现实疏离的空间[52];医院博物馆化可以发挥其社会教育之最大功能,进而对病患的就医经验、与医病的沟通产生正面影响[53];学校可以将“博物馆的精神和技术”运用于学校教育,在“空间博物馆化”或“行为博物馆化”(mu⁃seumlization)方面努力[54]。如针对曾是糖厂的台湾乌树林休闲园区的博物馆化改造,在精神上,应该更强化以公众利益为使命;在方法上,利用博物馆的研究、搜藏、展示、教育等功能,发展对公众的服务。这种动态的博物馆化过程,让以类博物馆方式存在的乌树林园区,更能为公众利益而努力[55]。
四、“博物馆化”的含义与思考
(一)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博物馆化的关系
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博物馆化是科学博物馆学的重要术语与思想。斯坦斯基奠定了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特的科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定义了博物馆学、博物馆学及其方法、术语和系统[56]。他关于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博物馆化的阐释,对博物馆学理论研究贡献很大,尤其是他将博物馆性看作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也正因此,博物馆化也是围绕博物馆性展开的。
博物馆性是描写人与现实生活特殊的关系,博物馆化是此关系的发展过程,博物馆现象代表表现出来的结果,博物馆理论是博物馆性的理论,博物馆体指一切涉及博物馆性的观念、事物、设备及过程,博物馆学指包含广泛的博物馆性的学科[57]。可以说,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就是围绕物如何具有博物馆性,将其博物馆化后成为博物馆物。物的博物馆化就是博物馆中对物固化、象征化的现象[58],博物馆将制造“博物馆物”的过程称为“博物馆化”[59]。
(二)狭义的博物馆化内涵
博物馆化最重要的使用领域还是博物馆学领域,“指的是置于博物馆,或更为一般性地将一个生活场所——如人们的主要活动地点或自然景点变为一个博物馆。博物馆化是将一件事物的物质性与观念性自其原有的自然或文化脉络抽离,并赋予其一个博物馆的地位,将其转变为一件博物馆物或使其进入博物馆领域的操作”[60]。
由此可见,博物馆化发生的重点是自然或文化环境创造的物,物从先前环境转移到博物馆,就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博物馆主动收集物品,让其脱离先前的环境,把它们变成博物馆物(museum objects)[61]。物的博物馆化必然是以脱离为前提的[62]。无论物的来源是什么,博物馆化的过程不全是从物脱离其原始环境开始的,而是从决定赋予其博物馆地位时就开始了[63]。
那博物馆化的过程如何?博物馆化过程的第一步就是上述的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物品。物一旦进入博物馆,就会经历一系列过程,被赋予各种角色和身份,在博物馆承担新的功能。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意味着一种本体论的转变(onto⁃logical shift)。物体经过这种转变,失去了它们以前的关系和关系效应。通过保存、记录、研究和传播,物被插入其他本体中。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内,博物馆化可以被分为几个相关的具体实践:收藏、记录、保存、研究和传播[64]。弗朗索瓦·梅雷斯(François Mairesse)也认为博物馆化在其最传统的意义上必然意味着博物馆的一系列活动:保存(选择、获取、管理、保护),研究(用于编目目的)和传播(通过展览、出版物等方式)[65]。博物馆化的过程意味着博物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活动的一个关键范式(key paradigm),越来越多的观众在活动中寻找强调的体验[66]。一件物品通过博物馆化的过程成为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是某特定历史意义和事件的载体,而不是历史本身。当涉及通过博物馆化过程将遗产/博物馆的对象制度化时,博物馆应该与对象所在社区保持联系[67]。
(三)广义的博物馆化内涵
博物馆学不应该只处理关于博物馆的方面,而应该包含其他方面。博物馆不是一种目的(an end),而是一种手段(a means)。博物馆学体系中的博物馆仅是将这种特殊人类方法具体化的方式之一[68]。博物馆化过程并不是博物馆的特权[69]。因此,我们不能将“博物馆化”看作博物馆学领域独有的术语,它也可以用于其他领域,我们应从更广义的范围来理解。
从汉语字面意思理解,“化”这一字眼置于名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状态或性质,“博物馆化”也就是转变成博物馆的状态或性质。博物馆化可以理解为将某物放入博物馆的行为(the act of putting something into a museum)[70]。社会机构和社会场所开设博物馆所呈现的是非博物馆的博物馆化风潮[71]。从前文可见,在其他领域,“某某+博物馆化”也就意味着将该领域的某事物建成博物馆,或利用博物馆的方法运营,我们也可理解为“博物馆方法的社会化”。
(四)博物馆化的思考
上述可见,博物馆化已经是文化遗产及相关领域的常用方式。但运用领域广泛,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化都是利大于弊。有博物馆化,就有去博物馆化或反对博物馆化[72]。
博物馆化在各领域的弊端都有所体现。“冻结”(museification)表达出将一个有生命的地点“化石化”(或“木乃伊化”)的负面概念,这可能是博物馆化过程带来的结果,也是许多批评“将世界博物馆化”的内容[73]。在遗址保护方面,对“活的”遗址进行“博物馆化”有很多不利影响[74]。世界遗产日益被“博物馆化”,或作为“文化产业”被充分开发来促进大众消费,这都是很危险的情况[75]。
城市、乡村的保护也是如此。城市历史街区博物馆化到一定程度时,对街区将造成价值的流失[76]。城市历史地区的保护要使之具有活力,避免“博物馆化”,与社会生活相融合[77]。迁移村民的村落保护会让文化“博物馆化”[78],逐渐“空心化”[79]。多米尼克·波洛(Dominique Poulot)指出在实施生态博物馆项目的过程中,“要避免‘物的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采用不同的策略来传播当地身份、传统技能和社区价值观”[80]。
这一现象在旅游领域更为突出,在旅游过程中,城市会出现绅士化和博物馆化(gentrification and museumification)[81]。随着旅游的发展,大批当地人离去,城市中心的功能变得单一,通过“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或“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的过程失去了城市特征[82]。如新加坡学者通过对公民文化区保护项目的调查,发现该地区以“博物馆化”或“精英化”鼓励旅游业,但却未能有效保护他们的遗产[83]。鉴于此,在开发旅游产品中,也要便于游客体验,避免走入“博物馆化”的传统误区[84]。或者“打破传统的博物馆式开发模式和运营管理模式,将文物遗址类旅游资源开发建设成为一种以文物遗址所承载并衍生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具备参与、体验、休闲等现代旅游功能和多元赢利能力的综合性旅游景区”[85],这是大型文物遗址类“去博物馆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一种新思路。
在当前让文物“活起来”的趋势下,我们要警惕让文物“死去”的做法。在博物馆学领域,我们在让“物”博物馆化,即脱离其原生环境脉络的同时,也要注意将其再脉络化,挖掘物的信息并营造物使用的情境。而在其他领域,博物馆化在减缓城市更新中城市记忆的消失、古村落的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临灭绝以及促进文物资源的旅游化合理利用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要把握“度”的问题,在博物馆化的同时把握平衡点。
五、小结
“博物馆化”术语的使用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理解:狭义的博物馆化指博物馆学研究领域的博物馆化。“从严格的博物馆学观点观之,博物馆化是将一件事物的物质性与观念性自其原有的自然或文化脉络抽离,并赋予其一个博物馆的地位,将其转变为一件博物馆物或使其进入博物馆领域的操作”[86]。广义的博物馆化指博物馆学领域外的其他学科或除博物馆外的其他机构,采用博物馆的方法或功能进行操作。但在博物馆化过程中,我们也要认识到,博物馆化不是固化,“将活的变成死的”,否则,博物馆化就成为反面案例,我们可能又要反过来更大范围地开展“去博物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