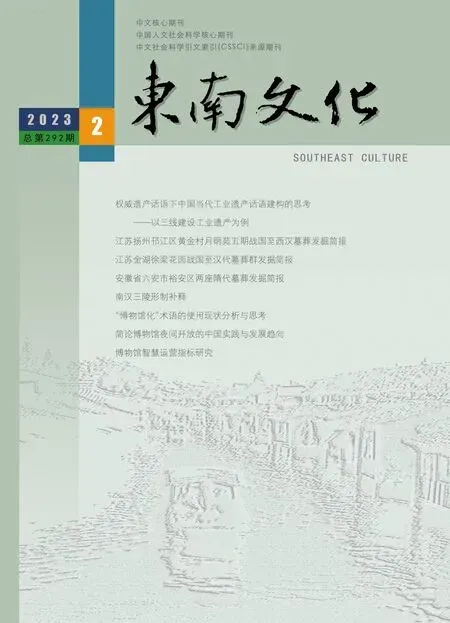王弘撰笔记《山志》的文物史料价值探析
2023-09-05李竞艳
李竞艳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山志》是明末清初士人王弘撰所著且在世时已经刊刻的笔记著述。书中记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史料,这些文物史料涉及门类众多,包含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同时,包含许多对当时而言年代久远的古代器具和书画,以及一定数量的当世珍贵文物,体现了作者“古今同重”的文物学思想。书中王弘撰对文物的创作(制作)过程、流传经过、现收藏之所、功能、用途以及鉴赏等多元视角展开研究,揭示了文物的历史、艺术和文化等多方面价值,丰富了后世文物学研究内容,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王弘撰(1622—1702年),字文修,又字无异,号山史,又号待庵,今陕西华阴人;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和古书画金石收藏家,潜心治学、读书不辍、游学不倦,被誉为“关中四君子之一”。王弘撰酷爱金石,收藏古书画、金石极其丰富。同时,其一生著述颇丰,有《周易图说筮述》《正学隅见述》《山志》《友声集》《待庵日札》《北行日扎》《西归日扎》《砥斋题跋》等数十种。其中,《山志》是其在世时已经刊刻的读书及见闻随笔,内容包含史学、经学、小学、书画金石之学等。目前学界对王弘撰及其著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年谱、文学思想和理学思想、书法成就等方面[1],而对其丰富的文物学思想关注较少,尤其对《山志》中的文物史料价值的挖掘还存在很大空间。“文物”虽是一个现代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古代文献中的“古物”“古器物”“古董”“骨董”“古玩”“古书画”等,大多指具有一定时间属性的且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性的珍贵物品,和今天的“文物”概念比较接近,可以为今天的文物学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王弘撰在《山志》中对文物的创作(制作)过程、流传经过、现收藏之所、功能、用途及鉴赏等方面进行了多元视角的研究,揭示了文物的历史、艺术、文化等价值,丰富了后世文物学研究内容,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而学界对此关注较少。所以,有必要对《山志》的文物史料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不揣谫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撰小文,以请教于方家。
一、《山志》中文物的种类
《山志》是王弘撰在世时已经刊刻行世的著作,可见作者对该书的重视。同时对于该书,王弘撰自述说:“偶触随记,雅俗并收。”[2]书中所载不仅是作者亲历亲记,而且雅俗并收、门类众多。其中,涉及文物类的记述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初集》部分,如《初集》卷一对《定武兰亭》的记录,《初集》卷二对《淳化阁帖》的记录,《初集》卷三对印的记录等;《二集》中也有零星记载,如《二集》卷五对《兰亭》的记录,但不及《初集》中多。王弘撰酷好金石,又擅长书法,这在晚明时期并非只有其一人。但不同的是,王弘撰所关注的文物门类众多,不仅有大量的可移动文物,还有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如石碑、古井、棂星门等;不仅包含许多对当时而言年代久远的古代器具和书画,同时涉及一定数量的当世珍贵文物,体现了作者“古今同重”的文物学思想,这与当时士人普遍的“厚古薄今”观点相比,更显难能可贵,《山志》也因此为后世文物学研究保留了大量明代当世文物史料。
《山志》中涉及的古代文物(“古代”是相对于明末清初)有:大禹鼎、有虞氏敦、夏后氏琏、殷瑚、周簋;《鹊华秋色》《寒林大轴》《潇湘八景》《定武兰亭》《上林图》《淳化阁帖》《大观太清楼帖》《富春山图》《怀素贴》《十万图》《唐中兴颂》《华岳碑帖》;湖南岳麓山禹碑、永州(今湖南永州)宋万安桥碑,成都后蜀石经、浣花夫人石刻、简州(今成都简阳)汉碑,京师(今北京)定水带,金陵(今南京)胭脂井、文庙棂星门等。
书中涉及的当世(明代)文物有:《霖雨舟楫图》《白岩图》《永乐大典》《〈华岳碑帖〉跋》等。
《山志》中关于古代文物的载述主要是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其中如《定武兰亭》《淳化阁帖》《怀素贴》《寒林大轴》《潇湘八景》《富春山图》等都是稀世珍宝,书中对于这些珍贵文物的流传经过、名家鉴赏等进行了详细记述,为后世的文物研究和展示提供了宝贵史料。
更难能可贵的是,《山志》中载述了明代当世著名书画家作品,突破了前代士人偏重古物的思想束缚。由于当世人对当世文物的记录和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详细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流传经过和名家鉴赏情况,为后世对这些文物的研究提供了更具真实性的材料,也为后世对文物的时间属性范围的认知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山志》中文物的研究内容
王弘撰在《山志》中的文物学研究主要从文物收藏家及收藏现状、文物功能与用途、文物流传经过、文物鉴赏等方面进行,视角较为多元。
1.文物收藏家及文物收藏
文物收藏方面主要从对收藏家的记述和对珍贵文物的收藏之处等方面进行考证和研究,为后人追根溯源、鉴定真伪提供了参考。
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一些专门性的文物市场相继出现,文物买卖交易变得更为顺畅,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大量文物收藏家的出现。《山志》中所记录的文物收藏家主要有项元汴、董其昌、仇紫巘、郭徵君、孙退谷等。晚明社会大家所公认的最大的文物收藏家为项元汴,其收藏品种类繁多。在众多的收藏家中,仇紫巘书画收藏颇丰,《山志》中云,“仇氏书画之富,甲于山右,其所藏盖千有余种”,而且由于其与董其昌、陈继儒交往甚密,所以,“凡有所得,辄求董仲伯、陈徵君为鉴定,往往有二公题字”,这也大大提高了其书画收藏的地位和声望,为其书画交易提供了社会声誉资本。王弘撰亲眼所见仇氏所藏就有三百五六十种之多,其中,仇氏藏画最著名者,有李成的《寒林大轴》、马远的手卷《潇湘八景》等[3],这为后世书画文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晚明社会文物收藏家除了酷爱书画之外,在印章收藏方面也表现出了很大热情。《山志》中对于印章收藏家郭徵君如此记述:“郭徵君好收藏古印,积五十余年,共得一千三百方。中有玉印、银印各数十方,文皆古健朴雅,非近世临摹者所能及。”[4]
对收藏家及其收藏的研究,为后世文物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晚明的著名收藏家往往都有自己的印章,会在自己的收藏品上标记独特的收藏印记,如王弘撰曾得到小画一帧,其上有项墨林收藏印记。这些印记可以使研究者顺藤摸瓜,从对收藏家相关信息的研究,梳理出大量文物信息,为文物学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除了对收藏家进行研究之外,《山志》中还对一些特别珍贵文物的当世收藏之所进行了挖掘,为文物研究和鉴赏提供了重要线索。如《山志》中关于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名作《鹊华秋色》收藏之所的记载,“于密庵云:‘其平生得意之笔曰《鹊华秋色》,今在山东张氏家。’然予旧闻在松江董宗伯处”[5]。不同的收藏地之说为名画鉴定带来了一定难度。但我们知道,名家某一画作一般具有唯一性,不存在多件大小尺寸内容品相一模一样的作品,所以当存在一件名作有不同收藏之所的说法时,只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有赝品存在,另一种可能是名作从一收藏地流传到了现在的收藏地。鉴赏家可根据文物的不同收藏之处对其进行详细探索,为鉴定提供可靠线索,以免以假乱真。
2.文物的制作过程和流传经过
制作过程和流传经过是文物的重要信息内容,早期的文物学家往往忽视此方面研究,而《山志》作者王弘撰却在此方面有先见之明,对文物的制作过程和流传经过有详细记录,这不仅丰富了文物学研究内容,也为后世文物展示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信息材料。
对文物制作过程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对文物有更加全面的认知,如《富春山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三年乃成的一幅名作,关于其制作过程及其名称的由来,《山志》中如此说:“黄子久为画一卷三年,舟至富春山下而始完,因题为《富春山图》,初非写富春山也。”[6]此段记述使《富春山图》的创作动机、过程、内容跃然纸上,为此名作的后世研究和展示提供了珍贵史料。
除了文物制作过程,其流传经过也是《山志》中文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为文物鉴定提供了一定信息参考。《山志》中对《富春山图》的流传经过如是记述:“旧藏宜兴吴孝廉问卿家,问卿将死,令出所有书画焚之以殉。时问卿昏乱,侍妾于火中窃出二卷,其一为《怀素贴》,其一即此图也,然已焚去丈余。后归丹阳张氏,今归泰兴季氏。”[7]此流传经过以及保存状态清晰可见,如果后世有人将《富春山图》全图而非残图拿出说是真迹的话,据《山志》中此流传经过的记述,其真伪便不言自明。
被世人极为推崇的《定武兰亭》在《山志》中曾被多次提及,其中对其流传经过的记述,为后世《兰亭序》版本真伪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线索。王弘撰在《山志》中记述:“予得《定武兰亭》五字未损本,盖秦府物,乱后落在民间者。旧为宋仲温所藏,有米元晖诸君跋。”[8]这一流传经过符合晚明社会状况特点,藩府中大量珍贵文物流入民间,被有识者购得。王弘撰也正是借此时机获得《定武兰亭》真迹,并充分发挥这一稀世珍品应有的价值。“尝携至都门,为孙北海、龚芝麓、刘鲁一、王燕友、汪苕文诸公所赏,因而知之者众。”[9]王弘撰收藏、鉴赏《定武兰亭》数年后,将其出售给其他有识者,出售的原因是“虽以贫故,亦念天下尤物,未可久据也”[10]。
3.文物功能、用途
功能和用途是文物所蕴含的重要信息,也是文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王弘撰在《山志》中对文物的功能和用途着墨较多,为后世文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对古代器物的功能和用途可能渐渐出现了理解上的分歧。为此,《山志》对盘、杅、盆的功能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临川吴氏谓:‘盘,承盥手余水器也。古人将欲盥手,别以一器盛水置盘上,用杓㪺而沃之,余落盘中。故盥文从水、从臼、从皿,两手加于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加盘也。’《内则》曰:‘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盘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余水。武王铭诸器载在《大戴礼记》,于盘曰盥盘,明盘之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浴器用杅,沐器用盆。盆、杅皆以盛水,浸发于盆之内,裸身于杅之内。浸发、裸身槩亵且汙,不可刻文。盥盘承余水者,不亵不汙,故可刻文而铭也。按《内则》:‘凡家之夫妇,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内外使令之人,每日晨兴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兴一盥’而已。虽无事,大约一日五盥,有事而行礼,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然后请浴,三日然后具沐,亦或过三日、五日之期。无一日一沐一浴之理,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谓之日新矣。”[11]由此可知,盥器之盘可刻文,沐浴器具之盆和杅不可刻文;盘是用来接盥手余水之器皿,而非盛水之器皿。这些既是对这些水器具体使用功能的辨别,同时也是对古代礼制的具体研究,在文物学研究中具有极高价值。
4.文物鉴赏
鉴赏是文物收藏者最为普遍的行为,也是文物学研究中特别重视的内容。鉴赏分为鉴定和欣赏两个行为过程。在晚明社会,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往往也是鉴赏家,鉴定和欣赏能力同时具备。鉴定主要是辨真伪、判价值。虽然文物的真伪是绝对的,但鉴定真伪的方法是多元的,而且也往往会因为鉴定方法的不同导致真伪认定上的偏差。
文物鉴定方法不一而足,不同类型的文物鉴定方法不一样,同类文物也有不同的鉴定方法。对于书画的鉴定,《山志》中呈现出不同方法。如可根据书画上收藏家的印记进行鉴定。王弘撰曾经得到一幅赵孟頫的画作,王氏主要根据其上有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收藏印记来判断真伪,“予尝得小画一帧,有项墨林收藏印记,定为承旨笔”。另外,也可根据鉴定者对于书画特点的熟悉程度来判断。如于密庵因“深心内典,幼从张鹤涧学画,临仿古人皆得其要,故鉴赏极精”,所以,当王弘撰将其收藏的一幅赵孟頫书画给于密庵鉴赏时,“密庵曰:‘此承旨真迹也。君欲见《鹊华秋色》,即此是矣,但大小不同耳’”[12]。可见于密庵对赵孟頫书画艺术特色了解之深。
关于《淳化阁帖》的真伪,不同鉴定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辨识。王弘撰说:“《淳化阁帖》者,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书王著临搨,以枣木镂刻,厘为十卷。于每卷末篆题云:‘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而有人认为《淳化阁帖》是宋重摹本,王氏认为这是错误的认知。其认为汪逵所著《〈淳化阁帖〉辨记》对于鉴定《淳化阁帖》的真伪具有重要价值,认为其“极为详备,末云:‘其本乃木刻,计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银铤印痕则是木裂。其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丰腴,比诸刻为肥’”。此外,王氏认为尤伯晦在《淳化阁帖》的鉴定方面也卓有建树。尤氏认为:“夫真帖可辨者,有数条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数在上,版数在下,惟此本卷数、版数字皆相联属,二也;他本行数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数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浓,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纸无接粘处,一部十卷无一版不与端明所记合,乃知昔人装褙之际,宁使每版行数或多或寡,而不肯裁剪凑合者,欲存旧帖之真面目,四也。”王弘撰认可尤氏的鉴定结果,而且综合各家所说,最后得出自己的鉴定意见,“《淳化阁帖》以枣木镂刻,而卷末篆题云‘模勒上石’,不应一人之记,自相矛盾。意当时本属木刻,因得南唐石增定,故遂题作‘上石’耳。马传庆云:‘增作十卷’为版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一二卷,是明为两本。柳衍卿、陈简斋所云‘祖石’,当时指南唐之石而言,而诸人所云,则是王著所模者耳”[13]。
在古代,文物鉴赏除了鉴定真伪、评定价值外,还包括文物欣赏,特别是晚明时期,许多博雅好古的士人更是将赏鉴文物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活动。如王弘撰与收藏家孙退谷的交游媒介主要是鉴赏文物,并从中体悟古人之风。“京师收藏之富,无有过于孙少宰退谷者。盖大内之物,经乱后皆散佚民间,退谷家京师,又善鉴,故奇迹秘翫咸归焉。予每诣之,退谷必出示数物,留坐竟日。肴蔬不过五簋,酒不过三四巡,所用皆前代器。颇有古人直率之风。”[14]二人由鉴赏文物而获得的愉悦心境不言而喻。
文物鉴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个人性,但也要遵循客观实际。正如《山志》中王氏与刘公勇对《定武兰亭》的跋文赏析存在分歧,《定武兰亭》“旧为宋仲温所藏,有米元晖诸君跋。仲温录赵魏公十三跋于后,而又自为之跋者九。……近刘公勇著《识小录》中有云:‘王山史亦有五字未损本《兰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晖跋与宋仲温跋,若出一手。’”王弘撰认为刘氏对跋文的赏析不客观,所以要求其加以删改,“予尝驰简公勇云:‘米元晖跋,弟固疑其赝。然与宋仲温跋用笔迥异。足下谓如出一手,何也?’因读佳著,著意寻求,欲摘其一笔稍似亦不可得。今遂望足下删改此稿,不然失言矣”[15]。由此可见王弘撰对于文物欣赏的标准要求之严,同时也反映了王氏对待文物欣赏的严谨态度。
鉴赏家有时将文物鉴定与欣赏融为一体,鉴定的过程也是欣赏的过程。如《山志》中王弘撰在欣赏收藏家仇紫巘最著名藏品《寒林大轴》和《潇湘八景》时说:“俱贾平章物也。李画有贾平章题云‘营丘李夫子,天下山水师。放笔写寒林,千金难易之。’”王氏由此对《寒林大轴》的价值评价很高。同时,王氏根据该画作边上有董宗伯题字来鉴定此画的真实性。董其昌在欣赏马远的《潇湘八景》时为其题云:“马远《潇湘图》,四段作八景。”这表明董氏既鉴定该画作为真品,又将对其“烟云缥缈之致”的赏鉴意境具见笔端。同时,这幅有着董其昌题字、贾似道印章,以及明朝多名鉴赏家题咏的画作,令王弘撰不禁感叹:“令人不动步而作楚游,真南宋名手也。”[16]这鉴中有赏、赏中有鉴、鉴赏融合的赏鉴方式在《山志》中多有载述。
三、《山志》中文物的价值
明代金石学虽然没有宋代繁盛[17],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士人精力及兴趣的转移,文物在明代社会被关注的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了。其主要表现为,除了前文所述的士人关注文物的类型更加丰富,同时对文物价值的认知也更加多元。《山志》中士人不仅对文物历史价值多有关注,同时对其诸如艺术、文化、经济等方面价值也有不同程度的欣赏和研究。
1.文物的历史价值
金石学重视文物的正经补史作用,为后世注重发挥文物的历史价值奠定了基础。《山志》中不乏士人重视文物历史价值的史料。如“《孙叔敖碑》云:‘三九无嗣。’洪景伯注云:‘无相继为三公九卿也。’此语似误。《国绝》注云:‘二十七年国绝,不续。’则三九者,正二十七之说也。《战国策》有九九八十一、三七二十一之文,古人往往用此”[18]。王弘撰对《孙叔敖碑》进行历史性解读,为人们科学合理理解碑文及石碑主人的生平事迹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碑文的历史性价值。
2.文物的艺术价值
书画本身就具有艺术的本质,其艺术价值更容易体现。晚明社会士人或商人在把玩文物时,更多看中的是其艺术价值,从鉴赏文物中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如沈绎堂为王弘撰所藏《华岳碑》题跋时说:“华阴王子山史,博雅好古,所藏《定武兰亭》率更醴泉旧搨,皆精妙入微,而郭香察隶书《华岳碑》,尤冠绝今古。”跋文中对《定武兰亭》和《华岳碑》的书法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跋文随精湛的书法精品一同流传后世。无独有偶,董其昌在谈颜真卿真迹时说:“颜鲁公《送刘太冲序》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别有异趣。米元章谓‘如龙蛇生动,见着自惊’不虚也。”[19]在董其昌看来,颜真卿的书法作品《送刘太冲序》在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艺术之外又别具他趣。这种他趣正如书法家米芾所说,就像龙蛇在舞动,栩栩如生,使人惊叹。
3.文物的文化价值
晚明士人在通过鉴赏文物提高自身审美情趣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文物在社会文化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王弘撰认为印章是信文化的代表,应该“以端方正直为主”,从而体现“古朴庄雅之致”。他特别认同汉代马援通过印章而使汉人“知正”的做法:“马援曾上书云:‘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由此,王弘撰批评当下的印章文化:“今人不究六义,谬矜章法、刀法,或用钟鼎诸文,令人不易识,以夸奇巧,则非为印之本指矣。”[20]
晚明士人通过鉴赏文物,悟道养神、体悟人生,日渐涵养着自我精神世界,同时也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积极努力,这为后世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借鉴。如沈绎堂在赞王弘撰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精神时说:“恐神物易化,风流渐邈,当亟谋抚泐,如岣嵝、介休故事,使汉隶面目犹存天壤间,山史之重图之哉!”[21]王弘撰担心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出人们的视野,呼吁应当积极谋划保护;他为了使汉隶真迹能够存续世间,而特别注重收藏和研究。也正是像王氏这样具有强烈文物保护意识的有识之士,使中华民族大量的文化珍宝得以流传至今。
《山志》对文物的种类、收藏、流传、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记述,不仅为当世的文物收藏、研究、欣赏提供了丰富资源,同时为后世文物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借鉴。明代特别是中晚明时期,类似的笔记和文集还有许多,如董其昌的《香光随笔》和《骨董十三说》等,这些古籍都不同程度地记录和描述了大量珍贵文物信息,成为中国古代文物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这些具有丰富文物学价值的著作,大致具有以下特点和价值。
第一,注重文物的真实性。书中所涉及文物多是作者所藏、所见,而非道听途说,为后世文物学研究提供了真实可考的文物文献资源。如前文所说的《山志》中王弘撰收藏不同版本《兰亭序》,并对此研究颇深,当遇到相关研究时,便能够给予很中肯的评价。同样是《兰亭序》,董其昌也有真迹收藏,正如其在《香光随笔》中记录:“《兰亭序》,六朝时已有刻石,余收开皇本是隋时刻者。”[22]此外,《香光随笔》中还有许多董其昌收藏珍贵文物的记录,如:“余曾有右军《行穰帖》真迹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种书。及武林杨侍郎自安福传来唐摹《绝交书》,纸墨用笔与《行穰帖》同,中缺‘鸾’字,乃悟为右军书,萧齐所摹,避子鸾讳,而后人误以为李怀琳耳。”[23]正是这些真迹记录,为后世文物学研究提供了真实可考的文献支撑。
第二,重视对文物流传脉络的梳理。古代大收藏家一般会有自家收藏印章,往往会在收藏的书画类文物上留下自家印章标识。同时,在书画类文物流传过程中,还会不断增加一些信息,如题跋之类。所以,古籍中对于珍贵文物流传脉络的梳理和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后世研究者根据收藏印章或题跋判断真伪。王弘撰对颜真卿书法作品《送刘太冲序》真迹流传经过的记录,也为后世文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董其昌认为,“真迹在长安赵中舍士祯家”,而且还“以余借摹”,但后为好事者购去,再未见过。王弘撰说:“真迹实为吾乡南子兴宗伯以善价得之赵中舍。中舍出入宗伯之门,凡宗伯所购书画,皆中舍鉴定。宗伯之孙鼎甫为河南同知,王中丞固索之去,既乃知为王燕友纳言阴讬也。”[24]由此可知,《送刘太冲序》最后落入王燕友之手。虽然其后王弘撰曾向其借观真迹,其托辞说已丢失,但之后王弘撰与好友谈及此事时,好友说数日前还在王燕友处见过这件书法真迹,看来当时《送刘太冲序》真迹在王燕友处便是无疑了。这对后世鉴定《送刘太冲序》的真伪提供了可靠依据。
一般认为,古人对于拥有的珍藏往往秘而不宣,但在《山志》《骨董十三说》等这些具有丰富文物学史料价值的笔记和文集中,不乏提倡文物信息交流的记录和描述。如王弘撰研究、欣赏文物,但不独占文物,而是使文物能够被更多人欣赏。这样的意识和行为对今天文物信息公共化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综观《山志》《香光随笔》《骨董十三说》等多部具有文物史料价值的古籍,它们都从不同侧面记录了大量珍贵文物信息,为后世文物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这些作品中所包含的作者丰富的文物保护和鉴赏思想,为世人搭建起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公众审美自觉之间的桥梁,激发一代又一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形成代代相传的保护意识与机制,极具时代价值。然而,仔细比较这些文物史料著作,可以发现《山志》对珍贵文物的信息记录更为全面深入,文物史料价值大,更值得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文物内容更加丰富,包含了金石书画等不同种类,而其他笔记记录文物信息相对单一。这与王弘撰酷爱金石和对书法造诣极高,以及其善于交游,对于当时南北方珍贵文物的了解更加全面等有密切关系。第二,文物的形态更加全面,既包含可移动文物,也包含如胭脂井、棂星门等不可移动文物,为后世文物分类研究提供了参考。而一般笔记往往忽略不可移动文物,认为不可移动文物鉴赏价值不如可移动的传世文物大。第三,文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信息包含全面,即将珍贵文物的创作者(或生产地)、流传经过、现收藏之所以及鉴赏内容和方法等全面记录,为后世对文物的追根溯源、鉴定真伪、品鉴价值等提供了丰富史料。而其他笔记往往只记录文物的某方面信息。第四,从文物的时间属性上,《山志》较之其他笔记,记录的文物信息也更加全面。作者不仅重视记录年代久远的古代文物,同时对当时的珍贵作品也独具慧眼,不吹毛求疵,而是以一种包容心态去对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明代文物信息。同时,由于《山志》中的文物信息都是作者“所触随记”,亲历亲闻,所以文物信息的真实性更强,为后世文物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信息。上述因素都为《山志》丰富的文物史料记载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由于该书所呈现的文物信息主要是作者依靠个人经验性判断而形成的记录,没有经过权威机构有组织地鉴定和汇总,所以也可能存在主观性、片面性等问题,我们今天进行文物学研究时还需要采取选择性、批判性的态度,对其所记载信息进行科学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