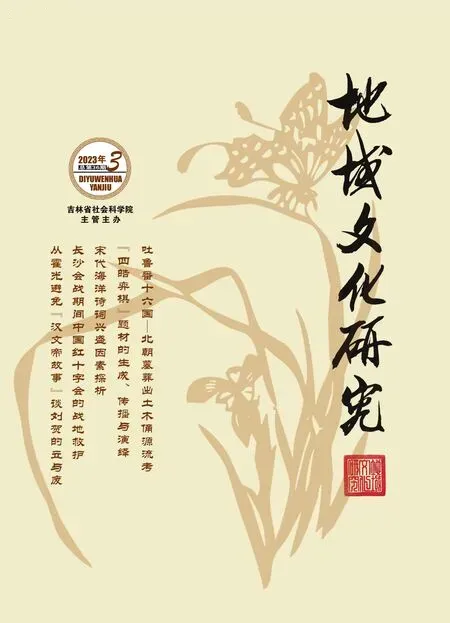从霍光避免“汉文帝故事”谈刘贺的立与废
2023-09-04刘荣晖
刘荣晖
2011 年,随着海昏侯墓开始发掘,考古成果相继发布,海昏侯相关研究成为热点。对刘贺的废立问题在海昏侯墓发掘前就有讨论,海昏侯墓发掘后更成为热点讨论问题。廖伯源先生讲:昌邑王贺即位27 日后废,其真正的原因是昌邑王贺与霍光争权。①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秦汉史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4-36页。吕思勉认为: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②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宋超认为:刘贺的立而复废,症结也不完全在于其行为不端,而是与霍光争权密切相关。③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微”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黄今言和温乐平认为刘贺被废,有刘贺行为不轨、霍光把持朝政、朝野存在一股支持宣帝的政治力量三个原因。④黄今言、温乐平:《刘贺废贬的历史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2期。臧知非认为刘贺被废是权力斗争失败的结果,但刘贺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是这场权力斗争的发起者和责任人。⑤臧知非:《刘贺立、废的历史分析》,《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孙晓从经学的角度谈刘贺的废立,认为刘贺被废的真正原因是只用自己200多个旧臣,不信任霍光政治集团,也不信任可能是霍光对立面的朝中大臣。⑥孙晓:《从“为人后者为之子”谈汉废帝刘贺的立与废》,《史学月刊》2016年第9期。符奎认为对霍光立废刘贺的评价,应当走出权利斗争说的窠臼,刘贺的特立独行,对整个政治体制乃至汉王朝的稳定都造成威胁,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威胁汉王朝的稳定与命运,从而被废。①符奎:《专制主义视角下的霍光权力与刘贺立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6期。卜宪群从政制、政事及政治三个方面讨论刘贺立与废,认为刘贺被废与“内朝”政治有关,与昭帝时霍光形成“政事一决于光”的权力格局相关。②卜宪群:《政制、政事与政治:也谈刘贺的立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王子今从宗宙的角度来讨论刘贺的政治沉浮,认为是否“可以承宗庙”是帝位继承人选择的决定性要素。③王子今:《“宗庙”与刘贺政治浮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邹水杰从昌邑群臣的角度来讨论刘贺被废的原因,刘贺政治能力的缺失,昌邑群臣并没有掌握长安的权力,从而被废。④邹水杰:《从昌邑群臣看刘贺之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1期。张朝阳从法制的角度看待刘贺被废的过程,认为霍光推动汉朝群臣通过严肃的程序,公开、和平地罢黜皇帝刘贺事件具有一定的法制特色。⑤张朝阳:《从法制的视角看罢黜刘贺事件》,《唐都学刊》2016年第6期。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刘贺欲提携昌邑群臣,而夺霍光之权,霍光为自保而废刘贺。也就是说,权力斗争始于刘贺,而霍光是在为保自身权力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废除刘贺。本文欲从霍光如何避免“汉文帝”故事,来看待这场权力之争背后的复杂性。
一、汉昭帝时的权力格局:政事一决于光
汉文帝和刘贺入主长安,都是藩王继位,都面对权力转移的问题。刘贺面对的是霍光,汉昭帝死后,政事一决于光。霍光辅佐汉昭帝,目的是什么?霍光是为了汉朝繁荣昌盛,还是为了权力集中于一己之手?从史料来看,霍光是为了“政事一决于大将军光”。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病逝,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年仅8岁。霍光和其他辅政大臣一起辅佐汉昭帝。
霍光初辅昭帝,权势未能一手遮天,还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的掣肘。“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⑥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34页。。为了将权力集于自己,霍光欲夺皇帝玺印。“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⑦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3页。。在封建王朝,皇帝玺印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拥有皇帝玺印,谁就拥有最高权力。霍光想夺皇帝玺印,不论其是否有夺皇位的想法,霍光想通过控制皇帝玺印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
霍光夺玺印不成,为了将权力集于一身,利用汉昭帝将其他托孤大臣打倒。《汉书·昭帝纪》:“初,桀、安父子与大将军光争权,欲害之,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罪。时上年十四,觉其诈。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谮毁者,坐之。’光由是得尽忠。”⑧班固:《汉书》卷7《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7页。汉武帝托孤的大臣有哪几位,《汉书》记载不一。《汉书·宣帝纪》:“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⑨班固:《汉书》卷7《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7页。。《汉书·霍光传》记:“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⑩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2页。《汉书·车千秋传》:“后岁余,武帝疾,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①班固:《汉书》卷66《车千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86页。而《汉书·霍光传》复载侍中王忽语“安得遗诏封三子事”②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3页。,三子指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汉书·金日磾传》载:及上病,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磾。日磾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③班固:《汉书》卷68《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62页。《汉书·孝昭上官皇后传》载:“武帝疾病,以霍光为大将军,太仆桀为左将军,皆受遗诏辅少主。”④班固:《汉书》卷97上《孝昭上官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57页。
从《汉书》记载来看,托孤之臣有可能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车千秋五大臣鼎力辅佐。汉武帝如此安排托孤人选,这样使内外朝⑤内外朝的形成,除了汉武帝时期形成说,还有一种汉昭帝后形成说,这里取汉武时期形成说。互相牵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为内臣,而丞相车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属于外臣。
在汉昭帝时期,霍光为了进一步将权力集中于自己,便与其他功臣展开了权力斗争,政治家之间的斗争打破了权力平衡的局面。金日磾在汉武帝托孤两年后去世;车千秋放弃权力,明哲保身。《汉书·车千秋传》记:“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于大将军光”⑥班固:《汉书》卷68《车千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86页。。上官桀父子伙同桑弘羊、燕王旦和盖长公主等人,欲谋反,后计划失败,伏诛。“九月,鄂邑盖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骠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⑦班固:《汉书》卷7《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页。霍光尽诛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等。从此,在汉昭帝一朝,政事一决于光。
霍光扶持汉宣帝继位之后,为进一步集中权力,将朝中各主要军政岗位,都归于霍光的亲戚或亲信,正所谓“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汉书·霍光传》:“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⑧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8页。亲信方面。杨敞,丞相,“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厚爱之”⑨班固:《汉书》卷66《杨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88页。。蔡义,丞相,“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⑩班固:《汉书》卷66《蔡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98页。。杜延年,太仆,本大将军霍光吏[11]班固:《汉书》卷60《杜延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62页。。张安世,车骑将军,“昭帝继位,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安世笃行,光亲重之”[12]班固:《汉书》卷60《杜延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62页。。赵广汉,京铺都尉,“初,大将军霍光秉政,广汉事光”[13]班固:《汉书》卷76《赵广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04页。。
汉宣帝即位之后,霍光已将权力尽收己手,以至于“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自己的亲属尽掌军政大权,以至“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即使霍家权倾朝野,但霍光的妻子霍显还毒杀了许皇后,让霍光的女儿为皇后。霍光死后的葬礼也超出了规格,有金缕玉衣和黄肠题凑。
所以,霍光不论辅佐哪位皇帝,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将权力集于己身。通过打击异己,培植亲信、任人唯亲,达到权隆于主,势陵于君,独揽朝纲的目的。
二、皇帝候选人
既然霍光辅佐汉昭帝和汉宣帝,都是为了独揽朝纲。那么,霍光在昭帝死后,另立新帝,其目的也是权集于己,不能大权旁落。
汉昭帝死后,无子嗣,后立昌邑王为帝,但昭帝死后,与昌邑王被立之时,两者隔了43 天。《汉书·昭帝纪》载:(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宫①班固:《汉书》卷7《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2页。;《汉书·宣帝纪》:六月丙寅,王(昌邑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曰皇太后②班固:《汉书》卷8《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8页。。“四月癸未”,根据陈垣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四月十七日;而“六月丙寅”,根据陈垣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六月初一。两个日期相差43天。
帝位空置四十三天,当然有举办汉昭帝葬礼的原因,也有征刘贺至长安的时间。但从刘贺至长安所用的时间,可以窥其一二。《汉书·武五子传》记:“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③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4页。。王子今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刘贺这段行程换成今天的速度,时速应在18.7 公里或至28.1 公里。④王子今:《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南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同是宗藩入继型,从汉成帝崩至汉哀帝继位,用了二十天的时间。《汉书·成帝纪》: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丙戌(十八日)⑤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21页。,帝崩于未央宫。⑥班固:《汉书》卷11《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3页。《汉书·哀帝纪》:“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初八)⑦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21页。,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⑧班固:《汉书》卷11《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4页。。关键汉哀帝的封地在定陶。《汉书·哀帝纪》记:“孝哀皇帝,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岁嗣立为王”⑨班固:《汉书》卷11《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3页。。而昌邑在定陶的东面。⑩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7-8页。两者相差一百三十五里。《汉书·武五子传》:“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11]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4页。。陈梦家认为:汉代日中为正午一段时间,相当于13时,晡时在日昳之后,相当于15 时至16 时左右。[12]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页,第250页,第253页。而这135 里,来回也就一天的距离。况且汉哀帝继位并不着急,在路上所用时间必多于刘贺。汉哀帝继位用时20天,而昌邑王继位用了43天,两者相差23天。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霍光在昭帝死后选谁为帝时,犹豫不决,考虑了很久。那么,霍光在忧虑什么呢?当然,霍光忧虑的是,皇帝没选好,轻则权力尽失,重则身首异处,全族覆灭。汉文帝继位后的殷鉴不远。
从汉昭帝之前的西汉历史来看,宗藩入继的情况只有汉文帝。汉文帝即位当夜,就夺取了南北军,取得了京城卫戍部队的领导权;又以张武为郎中令,取得了宫廷戍卫的权力。《史记·孝文纪》记: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①司马迁:《史记》卷4《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7页。拥立汉文帝继位之大臣虽受到了封赏,但也逐渐退出权力的中心。后来,也有功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绛侯周勃后期无故下狱,后经受狱吏提醒,由薄太后说情,才能勉强保身。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②司马迁:《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72页。
霍光明白,自己不仅是立一个皇帝,而是立一个皇帝集团。霍光为了保证自己权力不受损害,为了不为他人作嫁衣裳,霍光要找的是一个能绝对服从他的皇帝。而这样,皇帝的候选人则必须听命于己。汉昭帝驾崩后,从史料来看,纳入皇帝候选人的有广陵王刘胥和昌邑王刘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特广陵王……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③班固:《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7页。。而霍光之所以违背群臣的意见,违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度,正是由于刘贺比刘胥更好控制。但除了刘胥和刘贺两个候选人,有没有可能有第三个候选人呢?
西汉中后期,谶纬观念盛行,皇帝的确立也与谶语有关。昭帝时期也有一条关于“公孙病已立”的谶言,而这条谶言,印证了汉昭帝之后皇帝的确立。《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④班固:《汉书》卷75《眭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3-3154页。
孝昭元凤三年(前78 年),出现一条谶语:“公孙病已立”。眭弘解释此谶语,是要汉昭帝禅位,由故废之家公孙氏立。眭弘后被霍光所杀。汉宣帝为帝之后,眭弘的儿子被征为郎。那么,汉宣帝为什么征眭弘之子为郎,是不是有可能与眭弘曾为汉宣帝解释的谶言有关?其中“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与“病已”和汉宣帝刘病已的特点相吻合。张小锋也认为,公是指戾太子,孙是指刘病已①张小锋:《“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胡三省注曰“公孙病已立”为“宣帝兴于民间之符”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汉纪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67页。。谶言出现后,霍光恶之。这说明霍光知道“公孙病已”的存在。
霍光在昭帝时期,独断专权。“公孙病已立”的谶语,必然威胁霍光的统治,按西汉深信谶语的风尚,霍光肯定会去找到“公孙病已”,并消除威胁。就像汉武帝在晚年,方士讲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为保证汉家江山的稳固,即将罪犯统统处死。
那么霍光有没有可能知道刘病已的存在呢?首先,朝中众多霍光亲信大臣知道刘病已的存在。《汉书·外戚传》:
贺弟安世为右将军,与霍将军同心辅政,闻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③班固:《汉书》卷97上《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64页。
帝崩,昌邑王即位,废,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议所立。时,宣帝养于掖廷,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佗相爱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④班固:《汉书》卷60《杜延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65页。
从此可看出,在汉昭帝时期,霍光的心腹张安世是知道刘病已的存在,也知道他是汉武帝的曾孙。杜延年通过其子佗也知道曾孙刘病已的存在,并且在刘贺被废后,劝霍光和张安世立刘病已为帝。这说明,刘病已当时作为汉武帝的曾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知道他的身份,更知道他现处于何处,了解他的品性。
霍光的另一宠臣丙吉,也知道刘病已的存在和身份,并且丙吉一直以来在保护刘病已。《汉书·丙吉传》记:
贺即位,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览其议,遂尊立皇曾孙,遣宗正刘德与吉迎曾孙于掖庭。⑤班固:《汉书》卷74《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43页。
刘贺被废,霍光与张安世等大臣讨论立谁为皇帝,没有结果。后丙吉推荐刘病已,霍光才接受立刘病已为帝。仅从此来看,霍光在立刘病已为帝之前,似乎并不知道刘病已的存在。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霍光立刘贺为帝之前,是有可能知道刘病已的存在。昭帝贺崩,无子嗣。这时霍光就必然会思考皇帝继承人。汉武帝共六个儿子。昭帝无子,无法实施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只能用兄终弟及制。昭帝的兄弟,只有广陵王刘胥,刘胥不能继承帝位,那么其儿子也不行;接下来,只能在昭帝侄子当中选了。戾太子两个儿子均亡;齐王刘宏无子;燕王刘旦在昭帝时期谋反,被排除;昌邑王刘髆只有一个儿子刘贺。
对于霍光,一个政治家,在思考废掉刘贺帝位之前,他肯定要考虑继承人。广陵王刘胥因难以控制被否;燕王刘旦因谋反被否;刘贺这一支因其已废也不行;齐王刘宏这一支因无子嗣也不行。所以只能从戾太子刘据这一支寻找了。霍光不太可能再去汉武帝的兄弟中找继承人了。
政府雇员主要指那些政府据其工作特需所雇用的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员,他们从事政府部门的一些专业性的工作,这种制度被称为政府雇员制[2]。政府雇员制既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总结和改进。
从霍光从政的习惯来看,一般他的意思他自己不表达,要借人之口。立刘贺之时,欲废长立幼,跳过了广陵王刘胥,但霍光自己说,喜欢借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汉书·霍光传》:
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①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7页。
在昭帝幼时,有“公孙病已立”的谶言,霍光恶之,又杀了解释谶言之人,说明霍光是知道“公孙病已”的存在;霍光的宠臣张安世和丙吉都知道刘病已的存在,霍光是知道刘病已的存在;况且重立新帝,国之大事,不可能丙吉上一书,霍光就确定刘病已为帝。立刘贺为帝时,还走了与群臣商议这一过程。立刘病已为帝是霍光深思熟虑的结果,只不过借丙吉之口说出。刘贺只做了27天的皇帝,时间比较短,刘病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被霍光接纳为皇帝,事先肯定对刘病已做过一番了解。况且霍光在欲废刘贺时,必须想好谁为新帝。这一切都说明,霍光在昭帝时期就知道刘病已的存在。
也就是说,昭帝死后,霍光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广陵王刘胥,二是昌邑王刘贺,三是戾太子孙刘病已。刘胥因难控制已被排除,霍光只会在刘贺和刘病已之间选择。那么,我们来比较刘贺与刘病已成为皇帝候选人的优劣势。
刘贺的优势只有一个,而劣势却有很多。刘贺的优势是其为昭帝的侄子,从宗法制来看,刘贺的排序是靠前的。因刘胥被否,刘贺就是最佳继承人。但刘贺的劣势却有很多。其一,汉武帝时期刘髆参与到争夺太子位的权力斗争,使霍光对于刘髆一脉存在一种排斥心理。戾太子刘据死后,齐王刘宏薨。燕王旦,“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例狱”②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51页。。广陵王刘胥“多过失”③班固:《汉书》卷97《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56页。。戾太子死后,只有刘髆和刘弗陵争帝位。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牦巫蛊武帝,欲立刘髆为帝,后东窗事发④班固:《汉书》卷66《刘屈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83页。,刘髆也与帝位无缘。而霍光辅佐刘弗陵继位,对刘髆的儿子刘贺会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担心。刘贺最大的劣势是他比刘病已更难控制,更有实力。刘贺被废之后,霍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将刘贺的势力清除干净。这说明刘贺在封国时,实力不俗。而刘病已起于布衣,养于掖庭,除了丙吉有抚养过他之外,再无其他。况且,丙吉也是霍光的宠臣。所以,刘贺比刘病已更难控制,比刘病已更有实力。刘贺作风不好,“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⑤班固:《汉书》卷72《王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59页。、“贺动作多不正”⑥班固:《汉书》卷89《龚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37页。等。
刘病已可谓劣势较少,优势很多。刘病已有三大劣势:其一,从宗法制来看,他是昭帝的孙子。霍光可以废长立少,但一连跳过刘胥、刘贺,似乎并不合理;其二,霍光在出现“公孙病已立”的谶言之后,认为这是妖言,将眭弘杀了。如果刘病已为帝,对霍光势必有防范之心。其三,刘病已是戾太子之后,汉武帝和昭帝并未对戾太子进行全面的平反。立刘病已的优势有四。其一,符谶纬之言,即符合天意。既符“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①班固:《汉书》卷74《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42页。,又符“公孙病已立”②班固:《汉书》卷75《眭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3页。两条谶言,这在谶纬学说盛行的西汉,极有影响力;其二,刘病已毫无外部势力,布衣之身,没有汉文帝、刘贺那样的利益集团,不存在立一皇帝,即立一个利益集团的隐忧。况且刘病已的恩人丙吉,也是霍光的亲信;其三,霍光和刘病已有血缘关系,刘病已的爷爷是刘据,而刘据又是卫子夫所生。卫子夫是卫青的三姐,卫青是刘据的舅舅。霍去病是卫青的二姐卫少儿的儿子,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所以,霍光与太子刘据都是卫青的外甥,所以,刘据是刘病已的爷爷,那么霍光是刘病已“表爷爷”了。其四,刘病已的名声很好,“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③班固:《汉书》卷74《丙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43页。
霍光不论选谁,都很难达到完美。霍光从“谁最好控制,谁实力最弱”的标准来衡量,会更倾向于刘病已。可宗法制的阻碍和对刘病已的担心,使霍光选择了刘贺为帝。霍光立刘贺为帝,还是有权力丧失的担心,因为刘贺有效法汉文帝的可能性。立刘贺为帝,如果刘贺听命于己,那皆大欢喜。如果刘贺欲与光争权,则废掉刘贺,这样又可能在下一任皇帝面前“杀鸡儆猴”,即使立了刘病已,能使刘病已完全听命于霍光。
从此可知,霍光在汉昭帝死后,对于选择立谁为帝,曾犹豫再三。在排除汉武帝儿子刘胥之后,昌邑王刘贺与刘病已都有可能是皇帝的候选人。根据霍光“谁最好控制,谁实力最小”的选择标准,刘病已更占优势。但囿于宗法制的制约,不可能越过汉武帝的儿子刘胥之后,再越过汉武帝的孙子刘贺,直接选择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昌邑王刘贺就力量而言,弱于广陵王刘胥,但也有足够的力量,也是一个力量集团,也有可能让霍光大权旁落,汉文帝的继位已是前车之鉴。而刘病已孤身一人,起于布衣,即使是刘病已的恩人丙吉,也是霍光的心腹。刘病已又自带“谶纬”的光环,所以说,刘病已也应是皇帝的候选人之一。
三、霍光立刘贺为帝的权力布局
从废立刘贺的时间线来看,很难看出霍光立刘贺为帝的诚意。刘贺为帝27 天被废,但霍光废刘贺的想法很早就有。《汉书·夏侯胜传》:“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④班固:《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5页。刘贺为帝27天,十余日前,霍光与张安世使开始商量废帝。虽不知十余日具体天数,但说明刘贺为帝约15天左右时,霍光与张安世开始商量废帝之事。《汉书·霍光传》又记:“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⑤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37页。霍光与张安世商量废立之事在后,与田延年商量废立之事在前。虽然不知两者相差多少时间,但可推测的是霍光与田延年商量废立之事,可能在刘贺为帝十余日之后。这就说明,霍光自己想废刘贺的时间则更早,可能在刘贺为帝几日之后。霍光立刘贺为帝,事先肯定对刘贺进行全方位了解,而且在汉景帝之后,诸侯王国四百石以上官员都由中央朝廷派遣,作为“政事一决于光”情况,霍光对刘贺“不好书术、好驰骋”等品行应有所了解。刘贺继位仅几天,霍光就起废立之心,很难看出霍光立刘贺为帝的诚意。
霍光不论立谁为帝,都有大权旁落的可能。为了消除这种可能,霍光在立刘贺为帝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布局。刘贺权力斗争失败,“昌邑群臣二百余人悉见杀”,但有两个人未被杀,“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①班固:《汉书》卷88《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0页。,从此可得,王吉和龚遂因为曾经向刘贺进言,要刘贺改正失德之行,而免于死刑。从官职上看,王吉为中尉,龚遂为郞中令。历史似乎有着惊人的巧合,汉文帝同是藩王继位,汉文帝之所以能成功夺权,正是得益于中尉宋昌及郎中令张武。《汉书·文帝纪》:“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中尉宋昌进曰。”②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5页。而张武和宋昌,则在汉文帝夺权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汉书·文帝纪》:“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③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8页。汉文帝入主未央宫,则让宋昌掌握南、北军,即掌控守卫宫廷及长安的武装力量。让张武为郎中令,安作璋、熊铁基认为郞中令实为皇帝的顾问参议、宿卫侍从以及传达招待等官员的总首领,或者说是宫内总管。④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701页。也就是说,汉文帝通过中尉宋昌及郎中令张武,夺取了长安和宫廷之内的军权,巩固了帝位。
刘贺的父亲刘髆是汉武帝与宠妃李夫人所生,巫蛊之祸前后很受宠爱,有可能成为汉武帝更换太子的人选,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氂密谋立刘髆为太子,事情败露,李广利投降匈奴,刘屈氂被族灭,刘髆也因此而失宠,丧失了成为太子的机会。但无论如何,昌邑王刘髆曾经作为太子候选人之一,昌邑王国本身也会拥有一定的实力,昌邑群臣二百余人,即是体现。这必然会引来朝廷的注意与防范。汉景帝以后,诸侯王国定制四百石以上官吏均由中央派遣,王国仅得自置四百石以下官。⑤班固:《汉书》卷44《衡山王传》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国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54页。中尉在中央政府,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规定为二千石⑥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安作璋、熊铁基认为:王国中尉,位比傅相,秩二千石。⑦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741页。郎中令,汉武帝改郎中令为光䘵勋,王国仍名郎中令,减秩千石⑧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1页。,后更为六百石⑨孙星衍:《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汉官旧仪》卷下。。也就是说,昌邑王国的中尉和郎中令皆由中央朝廷任命。中尉王吉,也有过任中央郞官的经历。王吉字子阳,琅琊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⑩班固:《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58页。。龚遂昌邑郞中令之前所任官职,未见史载。王吉和龚遂常直谏刘贺,行为要合乎礼制法度。除此之外,作为昌邑王国的中尉和郎令,竟均建议刘贺要远离昌邑群臣,甘当傀儡。《汉书·武五子传》:“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①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6页。从此可看出,龚遂认为自己与昌邑故人有别,昌邑故人是祸害,要远离,要亲近先帝大臣,即要亲近霍光。王吉也是如此,《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②班固:《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1页。王吉说得更加直接,赞扬霍光,建议刘贺政事皆听命于霍光,要甘愿为傀儡。从此可以看出,中尉王吉和郞中令龚遂与昌邑群臣还是有区别,昌邑群臣与刘贺相谋,考虑如何夺取霍光的权力;而王吉与龚遂与昌邑群臣不同,他们劝刘贺依靠霍光。况且,刘贺入主长安之后,除了任命王相安乐为长乐卫尉,并没有其他夺权之举,也没有学汉文帝利用王国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来夺权,是不是也说明王吉和龚遂不是刘贺的亲信,而是霍光的亲信?由此可见,昌邑国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免死,他们又是朝廷派遣至昌邑王国的官员,又劝刘贺依靠霍光,远离昌邑群臣。朝廷任命王吉和龚遂为昌邑国中尉和郎中令,是不是霍光为了防止刘贺按汉文帝路线夺权所进行的权力布局。也就是说,立刘贺为帝,即使刘贺拥有一定的实力,在霍光这种权力的布局下,刘贺没有办法按汉文帝路线夺权。
霍光对于刘贺的防范不止于此,在皇帝继位过程中,刘贺未谒高庙。西汉时期,皇帝即位存在“即天子位”与“即皇帝位”两个步骤,“即天子位”意承接“天命”,需“谒高庙”;“即皇帝位”指权力传承,获得皇帝印绶。只有这样,其皇位或权力、身份合法性方被确认。刘贺仅“受皇帝玺绶”,只完成“即皇帝位”,并未“见命高庙”,获承“天命”。有学者认为,从西汉皇帝的即位过程来看,刘贺之所以未见命高庙,是西汉中前期并未形成固定时间的“谒高庙”礼制③吴方浪:《宗庙天命与君主立废:论刘贺“未见命高庙”》,《秦汉研究》,第十三辑,第20页。。但我们所对比不是西汉中前期所有皇帝的即位过程,而应对比的是霍光在辅佐三个皇帝时所“谒高庙”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霍光未让刘贺谒高庙是有意为之。《汉书·昭帝纪》:
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④班固:《汉书》卷7《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7页。
这表明,汉昭帝即皇帝位与谒高庙在同一天,即后元二年二月戊辰(公元前87 年二月十五日)。《汉书·宣帝纪》:
秋七月,光奏议曰:……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⑤班固:《汉书》卷8《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8页。
这表明霍光立汉宣帝,即皇帝位与谒高庙在同一天,即元平元年(前74)七月庚申。
从史料上看,霍光辅佐汉昭帝、刘贺及汉宣帝三个皇帝继位,在他们的即位仪式中,唯独刘贺未谒高庙。从这可以看出,霍光让刘贺未谒高庙,是有意为之。刘贺未谒高庙使得刘贺即位未合法,这是霍光为合法废除刘贺帝位埋下伏笔。刘贺被废时,未谒高庙,让刘贺合法被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①班固:《汉书》卷68《霍光金日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45-2946页。从此来看,霍光不让刘贺“谒高庙”,就是防止刘贺夺权的布局。刘贺被废诏书得到了上官皇太后的认可,可上官皇太后只有15 岁,又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皇太后也是霍光权力不容旁失的保障之一。
刘贺被废,原因是权力的斗争,学界已成共识。对于刘贺罪证,吕思勉认为: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②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廖伯源也认为刘贺的罪状皆不足信,尤其重点论述了“行淫乱”罪名是霍光强给刘贺的罪名。③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秦汉史论丛》,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2003年。李振宏认为班固对刘贺罪状的记载是可信的。④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纵论海昏》,合肥: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1页。不管刘贺的罪状是否真实,刘贺被废后的局势使霍光的权力达到鼎盛。
刘贺被废后,本应徙至房陵县,可又改为昌邑故地,又给封邑。《汉书·霍光传》:“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⑤班固:《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6页。太后年幼,不知世事,此乃霍光之意。从权力之争的角度来看,将刘贺徙往房陵县,会使刘贺变成孤家寡人,势力尽无,对霍光及汉宣帝来说,都是利好。可霍光不仅将刘贺放归故国,后又将所有财物俱还刘贺。“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⑥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5页。刘贺归故国,又加王家财物,这不是放虎归山吗?刘贺在与霍光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刘贺回到故国。刘贺在昌邑毕竟还残存一些力量,是完全有可能蓄积力量,重整旗鼓。汉宣帝继位之后,是非常忌惮刘贺的。“上由此知贺不足忌”⑦班固:《汉书》卷63《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8页。。
霍光保留了刘贺一定的实力,这是不是霍光要给下一任皇帝活生生的警告。毕竟任何一人继承帝位,都希望权力掌握在刘氏手中,而不应掌握在霍氏手中,姓氏之争自古就是争夺权力的核心。废除刘贺帝位,是让下一任皇帝看到,霍光能立你,亦能废你,必须听命于霍光;将刘贺放归昌邑,并且不完全削弱刘贺的势力,是告诉下一任皇帝,我还有一个刘贺可用。这也使汉宣帝明白自己的处境,完全听命于霍光。作为皇帝,为什么会害怕一个被废的帝王,当然是怕自己会被刘贺取而代之。所以,汉宣帝不得不完全听命于霍光,即使自己心爱的许皇后被毒死,也只能不了了之,之后,又不得已娶霍光的女儿为皇后。
霍光为保证权力不被削弱,通过控制昌邑王国掌握军权的中尉王吉和掌握昌邑“禁军”的郞中令,来防范刘贺按汉文帝路线夺权;又故意在刘贺继位之时,不让刘贺“谒高庙”,使刘贺继位不合法,从而使刘贺被废“合法化”。又通过将刘贺贬回昌邑,归还财物,使刘贺保存了一些实力,从而使后来的汉宣帝对刘贺产生忌惮。而霍光的这些布局,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会失去自己的权力。
结 论
我们将历史的视线从刘贺与霍光之间的关系,放到霍光从辅佐昭帝到霍光死亡,其间安排亲属尽掌朝廷军政大权、立废刘贺、立汉宣帝,这是一个霍光权力的增长史。而在霍光权力增长过程中,霍光所有的行为都是为“集权”服务。在权力增长的道路上,皇帝也成了牺牲品,刘贺和汉宣帝成了霍光手中的傀儡。霍光废刘贺,当然是权力之争,但这场权力之争,并不是始于刘贺欲夺霍光之权,而是始于汉昭帝死后。这场权力之争,是霍光的一场政治阴谋,刘贺只是在霍光的布局下作困兽斗,而这场困兽斗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霍光以“谁实力最弱,谁最好控制”为选择皇帝的标准,来衡量昌邑王刘贺以及刘病已两个候选人。为保证“政事一决于光”,在立刘贺为帝前,通过控制昌邑王国中尉王吉和郞中令龚遂,使刘贺无法按汉文帝故事夺权;在刘贺为帝时,故意未让刘贺谒高庙,使霍光在后期合法废除刘贺;又通过保留刘贺一定的实力,来羁绊下一任皇帝。所以,刘贺的立与废,汉宣帝的确立,都在霍光的掌控之中。
政治都是波诡云谲。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通过其墓中出土的器物,使我们对刘贺的认知不再仅局限于史料,考古资料的出土给我们认知刘贺提供一个新的窗口。在权力斗争面前,尤其是在霍光深谋远虑主导的这场权力斗争中,刘贺在27 天内做的1127 条罪状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说,不论对刘贺的认识有何争执,刘贺始终是在霍光主导下一起汉宫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