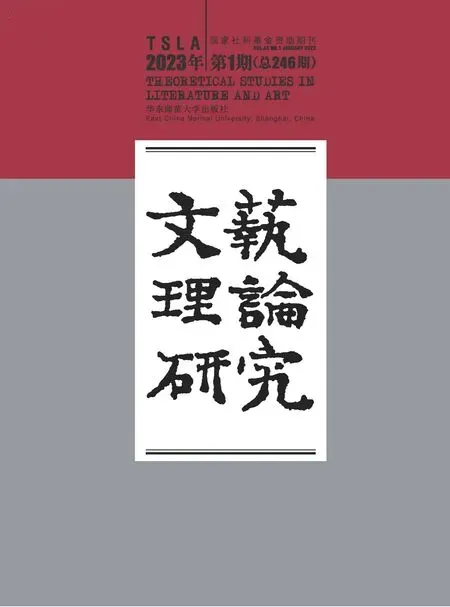走出“性中心主义”
——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研究
2023-09-03黄馨瑶
黄馨瑶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以来,精神分析是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女性主义最重要的话语资源和对话对象。然而精神分析在为女性主义提供丰富话语资源的同时,也对女性主义形成了一种话语桎梏,这突出表现在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偏执使用所造成的“性中心主义”倾向上。酷儿理论虽然在打破异性恋霸权、丰富对边缘群体的差异性研究等方面发展了女性主义,但“性中心主义”的问题在酷儿理论中依然存在。这种“性中心主义”至少有两种表征:第一是在语言或理论框架上将“性”作为理解主体的核心,第二则是对“性压抑假说”以及相应的“颠覆”“揭露”“祛魅”的反压抑策略的迷恋。前者如克里斯蒂娃、伊利格瑞和西苏,尽管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但她们的基本术语也还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内视镜/阴道”“阉割”“子宫”等弗洛伊德式的“性”话语。后者如朱迪斯·巴特勒,在她的作品中,“揭发”“祛魅”“去自然化”“暴露”等都是高频用语。
本文认为,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1950—2009年)“酷儿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的提出,正是以“情动”(affect)①的主体取代“驱力”(drive)的主体,走出“性中心主义”的一种尝试。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情动”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也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思考“后理论”“批评范式的变化”“情动理论的谱系”等话题时,将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作为其中一种话语资源而有所涉及②;另一类则是对塞吉维克情动理论的专文研究③。这些研究虽然都在不同层面上推进了对塞吉维克情动理论的思考,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两点:第一,侧重于横向介绍,对塞吉维克情动理论中一些关键概念的论述存在含混之处。例如,塞吉维克的“情动”与“情感”之间、情动的“羞耻”和情感的“羞耻”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中就并未得到有效的解答。第二,缺乏对于概念背后理论逻辑的深入思考。塞吉维克不愿提供一个关于她自己的完整理论,而更强调一种能够使人产生不断质疑的理论位置(Fawaz9-11)。因此,在塞吉维克那里,概念只是切入问题的一种视角,她更关注的是这种视角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摩擦”人们的惯性思维。这种对惯性思维的反思,应该是研究塞吉维克的基本思路。而在现有的研究中,这一基本思路却并没有得到凸显。
结合塞吉维克的研究现状,本文以“酷儿操演”为切入点进入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详细梳理塞吉维克对汤姆金斯情动理论和克莱茵客体关系心理学的挪用,并在这个过程中反思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在何种程度上“摩擦”了“性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
一、 情动的主体
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建立在“情动”的主体模式基础之上,这一主体模式主要来源于西尔文·汤姆金斯(Silvan S. Tomkins, 1911—1991年)。尽管塞吉维克对汤姆金斯情动理论的挪用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识,但国内却鲜有学者具体探讨塞吉维克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汤姆金斯进行了挪用,以及这种挪用的基本目的。这也限制了研究者对塞吉维克的“情动”和“酷儿操演”的深入思考。因此,重返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变得十分必要。
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需要放在他对于人的动力问题的思考中来理解,“人究竟想要什么”是汤姆金斯理论的基本出发点(Demos17)。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弗洛伊德的驱力模式占据着心理学领域中解释人的动力问题的主流,在驱力理论中性驱力则居于核心地位。但在弗洛伊德那里;“性”并非一开始就是人类行动的核心动力。在早期的婴儿诱惑理论阶段,弗洛伊德虽然“使得性成了神经症过程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因此就说性是所有人类体验的驱动力”(格林伯格 米歇尔21)。但在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建立以后,性驱力逐渐成为人类最为核心和基本的驱动力,即使在弗洛伊德随后不断发展的双驱力理论中,弗洛伊德也始终认为“力比多驱力本质上比对立的驱力更加重要”(25)。性与驱力的捆绑也因此发展起来。
汤姆金斯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驱力”(drive)模式,他试图以“情动”的主体取代驱力的主体,与此相应,“性”也不再是汤姆金斯情动理论重点关注的对象。
汤姆金斯191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他在16岁时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剧本创作,随后又在该校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35年,24岁的汤姆金斯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后奖学金。26岁时,汤姆金斯又以心理学博士后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心理医疗中心。④这种跨学科的教育背景,赋予了汤姆金斯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汤姆金斯关于情动理论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四卷本《情动,想象,意识》(AffectImageryConscious, 1962年,1963年,1991年,1992年)中,但其情动理论的正式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早期的一份名为《驱力理论已死》(“Drive Theory Is Dead”)的报告中,这份报告直到1956年才在拉康编辑的一份选集中发表(Frank and Wilson13)。在汤姆金斯开始关注情动时,美国学界关于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心理学、生理学以及实验的方法、联系的方法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汤姆金斯并未直接选择争论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从理解人的动力和思维的角度出发,巧妙地将不同的方法融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颇具创新性的心理学理论(133)。
值得注意的是,汤姆金斯关于“情动”的思考,深受维纳“控制论”影响和启发。20世纪中期,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出版的《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标志了“控制论”这门科学的诞生。受维纳影响,汤姆金斯将许多控制论的话语(如“硬件”“固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外,控制论还影响了汤姆金斯对人类有机体的认识(Lucas46)。在汤姆金斯看来,某种程度上,人作为一种有机体,其运转和机器的运转没有太大差别,它们都是以信息为中心开展通讯与控制过程。
汤姆金斯认为,情动系统是人体首要的动力系统(Sedgwick and Frank,ShameandItsSisters36)。这里的“情动”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在神经学层面上,“情动由神经元放电的某些分支所决定”(Frank and Wilson4);在生理学层面上,“情动由一系列肌肉、腺体和皮肤的反应所描绘”(4);在审美的层面上,“情动被有意识地体验为不同的感受”(4)。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虽然也注意到了“情动”的存在,但在弗洛伊德那里,“情动”还是从属于“驱力”的。与弗洛伊德不同,汤姆金斯则认为驱力不足以为主体的各项活动提供动力,它在时空上也过于局限。以最广泛和典型的“性驱力”为例,它实际上位于呼吸、吃饭、喝水甚至排泄的需求之后,并且“很容易就因羞耻、焦虑、厌倦或愤怒而萎掉了”(塞吉维克 弗兰克33)。汤姆金斯另辟蹊径,将“情动”从“驱力”系统中分离出来,以“情动”取代“驱力”作为主体活动的动力来源。汤姆金斯并没有抛弃驱力系统,只是否认驱力系统的首要地位。汤姆金斯强调“情动”的自由性和普遍性,他认为,“驱力”只有在被情动“放大”以后,才会具有产生心理学的效果。而“情动”则在时空上更为自由,它是先天的,驱力和其他情动,都可以引起神经元放电密度的增加、减少或持续,从而成为情动的触发物。汤姆金斯关于情动的论述在当时非常具有创见性,他是第一个将情动从驱力和认知中分离出来、并将情动作为人们各项活动的首要动力的理论家(Demos18-19)。
汤姆金斯区分了九种基本的情动⑤,每种情动都可以时刻通过放大刺激物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些情动本质上只是一种短暂的、转瞬即逝的生物学现象,它们无法充分解释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汤姆金斯在九种基本情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场景(scenes)和脚本(scripts)的概念。场景是“生活最基本的要素”(Sedgwick and Frank,ShameandItsSisters179),“最简单的场景必须包含至少一种情动和一个刺激物”(179)。“脚本”则是对“场景的解释、评估、预测、制作或控制的一套次序规则”(180)。情动是短暂的,“如果我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情动,我们就会成为毫无创造力的人类。但我们并不是毫无创造力的。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将我们经验的场景作为资源,重新对它们进行共组装,思考它们的关系,并设计将来应对它们的策略。我将这组规则——精简的规则——称为脚本”(Tomkins289)。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虽然都天生具有“情动”,但每个人经历的“场景”不同,相应的也会产生不同的“脚本”,不同的“脚本”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对“场景”的归纳和判断,并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的行为和认知产生解释性、预测性的影响,进而,每个人的差异和变化就产生了。
塞吉维克借助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来思考酷儿操演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汤姆金斯为塞吉维克在传统的“性中心主义”话语之外,提供了一种描述酷儿主体的语言和理论框架。汤姆金斯以“情动”“共组装”“放大”“脚本”等概念取代了弗洛伊德的“驱力”“俄狄浦斯情结”“压抑”等精神分析话语,他虽然保留了驱力系统和性驱力的概念,但它们的特殊地位已经丧失,驱力系统只是众多系统中的一种系统,它需要与情动系统的共组装才能产生心理学上的作用。这为塞吉维克跳出对弗洛伊德驱力模式和经典精神分析话语的依赖提供了可能。
这种“非性中心主义”模式还是一种流动和变化的主体模式,它能够为塞吉维克解释酷儿的差异性提供借鉴。塞吉维克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在塞吉维克前期的代表作《暗柜认识论》(EpistemologyoftheCloset, 1990年)中,她就明确提出了“公理1: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22)。塞吉维克认为在“当下的批判和政治思想”(22)中,现有的概念工具如“性别、种族、阶级、民族、性取向都是有用的区分”(22),但无法解释同一区分(如性别)内部人们之间的差异。因此,塞吉维克一直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更细致地解释人们差异的理论工具。汤姆金斯关于情动、场景和脚本之间关系的思考,为塞吉维克提供了一个能够容纳巨大差异的理论框架。
去除了对“性中心主义”的迷恋,主体“非性”的个人经验和主观情感也得以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尽管汤姆金斯和大多数情动理论家一样,也区分了“情动”(affect)和“情感”(emotion),但这种区分并不是为了强调“情动”、否认“情感”。在汤姆金斯的那里,“情动”是先天的、普遍的,“情感”则是在“情动”基础上结合个人后天经历形成的,正如内桑森所说,“情动是生物学的,情感则是个人传记的”(Nathanson50)。也就是说,“情动”就像色彩中的“三原色”,它以一种生成性的方式与其他情动、驱力、认知等组合,从而“提供一种思考不同情感状态的本质及它们与其他精神的、社会的、生物学的事件间关系的概念框架”(Frank and Wilson6)。这也使得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与以布莱恩·马苏米(Brain Massumi)等人为代表的更强调“情动”的强度变化,而忽视“情感”个人化维度的情动研究路径区分开来(6)。
二、 偏执与修复
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 1882—1960年)是除汤姆金斯外,另一位对塞吉维克的情动研究有颇深影响的理论家。尽管塞吉维克关于“酷儿操演”的论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克莱茵,但在《梅兰妮·克莱茵和情动的影响》(“Melanie Klein and the Difference Affect Makes”)中,塞吉维克指出,对克莱茵的阅读帮助她更好地理解了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Sedgwick,TheWeatherinProust129)。因此,要想更深入地研究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克莱茵的客体关系心理学同样不可或缺。
本文认为梅兰妮·克莱茵的客体关系心理学,不仅丰富了塞吉维克对汤姆金斯情动主体模式的理解,进一步帮助塞吉维克反思以“性”为核心的主体框架,也为塞吉维克打破性别研究中“压抑/颠覆”的二元论思维、寻找一种“修复”的理论模式提供了借鉴。
梅兰妮·克莱茵原本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忠实信徒,在学术生涯的关键时刻,也分别得到过弗伦奇、亚伯拉罕、琼斯“三位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弗洛伊德合作者的赞助”(格林伯格 米歇尔93)。尽管克莱茵的思想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但与弗洛伊德以成人为主的临床分析实践不同,克莱茵更侧重对儿童的精神分析,这也使得克莱茵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心理学道路。
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与“压抑假说”密切相关。在弗洛伊德那里,出于对被阉割的恐惧,主体需要不断“压抑”自己的力比多冲动,才有可能建立可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主体模式。但过度的压抑也可能会诱发精神疾病,因此“揭露”并“释放”主体内心被压抑的原始冲动在弗洛伊德那里就变得十分重要。在《梅兰妮·克莱茵和情动的影响》中,塞吉维克指出压抑理论早已溢出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当下的西方文化中,“压抑的首要地位构筑了一个近乎普遍的、二元论的政治观点”(Sedgwick,TheWeatherinProust132)。塞吉维克认为,福柯在《性史》中虽然从话语和权力的角度分析了压抑假说形成的原因,却并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压抑假说的话语增殖。克莱茵的心理学,则为塞吉维克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借鉴。与弗洛伊德带有二元论色彩的压抑理论不同,在克莱茵的客体关系心理学中,压抑仅仅是诸多防御机制中次要的一种(133)。在克莱茵看来,主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体验到爱、恨、焦虑等,是这些情感体验而不是力比多的压抑潜移默化地建构了主体的精神世界。
具体来说,克莱茵首先修改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驱力的含义。克莱茵保留了弗洛伊德的驱力概念,但她将客体关系纳入驱力之中,从而改变了弗洛伊德关于驱力的基本思考。在弗洛伊德那里,客体并不重要,它只是满足驱力的工具,是“个体从驱力满足和挫折的经历中‘创造’出来的”(格林伯格 米歇尔35)。而克莱茵认为客体并不是次要的,相反,“每一种本能冲动、焦虑情境、心理过程都牵涉到(外在或内在的)客体。换句话说,客体关系是情感生活最核心的部分”(克莱茵,《嫉羡与感恩》59)。通过在客体关系中思考客体(Sedgwick,TheWeatherinProust126),克莱茵将弗洛伊德更侧重生理基础、强调能量性质的驱力,转变成了一种更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强调个人体验的概念。
而在这个过程中,“性”在主体的构造和人格的形成中也不再占据着核心地位,主体的社会化也与性的压抑无关。“性欲必然会浮现,但很大程度上并未定型,而是在早期关系背景中获得其意义。”(米切尔 布莱克253)克莱茵的客体关系心理学对“性”的淡化,也为塞吉维克进一步摆脱“性中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话语借鉴。塞吉维克也曾明确指出,在后拉康的传统中,精神分析的思想并非首先围绕着菲勒斯的“性差异”组织起来的(TouchingFeeling133)。但许多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研究者依旧不屈不挠地坚持“菲勒斯”和“性差异”在主体构造中的中心地位,这种常常是“同义反复”的研究使人“很难去了解到——弗洛伊德之后,包括,如克莱茵后期的作品——精神分析思想的历史为思考人的个性、意识、情感、父子关系、社会的动力学和性等方面提供了丰富和异质的工具,这些方面虽然与性别和酷儿化的经历有关,但往往并不是以‘性差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它们可能仅仅是在‘性差异’旁边被概念化,偶尔与‘性差异’相关或完全不相关”(132)。
克莱茵进而提出了“偏执-分裂心位”(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和“抑郁心位”(depressive position)来代替弗洛伊德压抑假说基础上的人格发展阶段论。在克莱茵看来,因为死本能、出生时遭遇的创伤和出生后哺育的挫折,婴儿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一直被一种“被摧毁冲动和迫害焦虑主导”(《儿童精神分析》8)。由于婴儿此时还没有一个整合的自我,因此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婴儿采用了分裂的防御机制,在幻想中将生本能和死本能以分裂的方式投射到外在客体(即母亲的乳房)上,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理想化的“好乳房”和一个迫害性的“坏乳房”,前者与爱和满足相关,后者则与挫折和沮丧有关。正常情况下,在四到六个月时,婴儿就会从“偏执-分裂心位”逐渐过渡到“抑郁心位”,此时婴儿具有更强的整合能力,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爱和恨的对象为同一个客体。由于担心会伤害或失去所爱的客体,婴儿会产生修复的冲动,这种修复的冲动会帮助婴儿建立更强大自我,并与他人建立起真诚的、友善的爱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抑郁心位”某种程度上算是对“偏执-分裂心位”的发展,但克莱茵认为,这两种位置并非泾渭分明(《嫉羡与感恩》18),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18)。进入“抑郁心位”的人也随时可能会退回到“偏执-分裂心位”,人一生都会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来回震荡。“偏执-分裂心位”和“抑郁心位”之间这种动态的变化的关系,也为塞吉维克跳出“压抑/颠覆”的二元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发。
塞吉维克还创造性地将克莱茵的“偏执-分裂心位”和“抑郁心位”与对批评范式的反思连接起来,提出了“偏执性阅读”(paranoid reading)和“修复性阅读”(reparative reading)的概念。塞吉维克认为,包括自己前期的代表作《暗柜认识论》在内的许多酷儿理论和女性主义研究,都带有偏执性阅读的色彩。塞吉维克还特别对酷儿理论中偏执性阅读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塞吉维克看来,这与酷儿理论出现的时代背景有关。酷儿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早期,在酷儿理论兴起之时,艾滋病作为一种当时无法治疗的“绝症”也开始肆虐,这不仅给同性恋和关心同性恋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也加剧了社会的恐同情绪。“这种恐惧带来的惩罚性压力,以及应对这种恐惧所带来的强大抵抗力的需求,确实在那个时期的理论和行动中刻下了偏执的结构。”(Sedgwick,TheWeatherinProust138)但这种“偏执”的思维在当下的酷儿理论中却不再适用了。正如偏执性阅读的特征之一是“相信暴露的力量”(Sedgwick,TouchingFeeling138)一样,酷儿理论偏执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揭发”的迷恋。沉浸于“揭发”中的酷儿理论,也逐渐远离了丰富的酷儿经验。因此,塞吉维克指出“许多最近的酷儿理论保留了早期艾滋病年代的偏执结构,但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它所反映的对特定的、明显的日常生活的赢得”(TheWeatherinProust139)。
而克莱茵的关于“抑郁心位”和“修复”的思考,也为塞吉维克摆脱“偏执性”的思维方式打开了可能的空间。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克莱茵认为由于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所遭遇的创伤,从出生开始,痛苦和焦虑就将不可避免的伴随着人的一生。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及时的“修复”是十分必要的。而“修复”只能在“抑郁心位”的状态才能发生。这也就意味着,个体不再以分裂的方式看待世界,而是接纳创伤和焦虑的体验,并以一种整合的方式不断地将各种体验纳入自我的修复进程中。受到克莱茵的启发,塞吉维克也试图寻找一种更具“修复性”的理论路径,这种“修复性”的理论路径,不再拘泥于“压抑/颠覆”的激进二元论,也不再以分裂的方式否认现实的创伤,而是以一种更加平和冷静的方式反思批评的多元路径,以及不同的主体“修复”自身的可能。这也使得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具有鲜明的修复指向。
三、 羞耻的情动经历
提到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也就无法回避另一位酷儿理论家巴特勒的“性别操演”。虽然二者都建立在奥斯汀操演句的基础上,也都是关于主体的理论,但它们的主要内容并不相同。用塞吉维克的话来说,她对巴特勒的作品进行了“警告和修改”⑥(《情感与酷儿操演》90)。
巴特勒借助福柯的“权力”、阿尔都塞的“质询”、德里达的“引用”等概念,在奥斯汀操演句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性别操演”理论。在她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性别主体,性别也不是一种稳定的身份,相反,性别只是“一种建构的社会暂时状态(social temporality)的模式”(巴特勒184)。巴特勒“性别操演”的核心是通过对主体建构过程的剖析,揭露性别的流动性、过程性,以及自然化的性别规范背后所隐含的暴力性。因此,在《性别麻烦》中,“揭发”“祛魅”“去自然化”“暴露”等是巴特勒的高频用语。
受到汤姆金斯和克莱茵等人的理论启发,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与巴特勒的“性别操演”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样态,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更侧重“修复”而不是“揭发”⑦。在塞吉维克看来,巴特勒对“揭发”效力的迷恋是一种“偏执”,其目的是“服务那个可以被粗略称为‘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的认识论事业”(《情感与酷儿操演》96)。塞吉维克并不是完全否认“揭发”的价值,只是在当下许多性别歧视的现实早已经被揭示和周知,甚至“反对性别歧视和压迫”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时候,“揭发”可能已经不再是最合适的手段了。
因此,与巴特勒的“性别操演”不同,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将“揭发”的事实当作已知的前提,通过关注在这种性别观念的暴力中成长的主体(特别是酷儿主体)的个人经验来思考主体“修复”自身的可能。具体到酷儿主体那里,就是“羞耻”(shame)的情动经历。
结合酷儿的日常经验,塞吉维克在汤姆金斯九种基本的情动中,着重突出了“羞耻”的情动的重要性。这里的“羞耻”与人们通常理解的“羞耻”含义不同,而这常被研究者们忽略。
在汤姆金斯那里,情动的“羞耻”虽然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学机制,但它结合不同的经历则会形成不同的心理学效果。例如“害羞”(shyness)、“内疚”(guilt)、“羞耻”(shame)三种情感虽然名称和体验不同,但它们都涉及同一种羞耻的情动的变体,因此本文也将它们统一称为“羞耻的情动经历”。实际上,除了上述这些通常被人们认为与“羞耻”相关的情感外,“羞耻的情动经历”十分广泛和普遍。汤姆金斯将情动的“羞耻”触发理解为积极的情动的受阻,“羞耻的内在触发机制是兴趣或喜悦的不完全减少。因此任何妨碍进一步探索并部分降低兴趣的阻碍……都会导致头和眼睛因羞耻而低垂,从而避免进一步的探索和自我暴露”(Sedgwick,TouchingFeeling97)。也就是说,“羞耻”的情动首先需要积极情动的唤起,而人会本能地寻求积极情动的最大化。因此,“羞耻”的情动经历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内桑森也指出,“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那么这个人就在经历情动的羞耻”(Nathanson233)。
塞吉维克在探讨克莱茵的客体关系心理学时,曾类比了克莱茵的抑郁心位和汤姆金斯的抑郁脚本。在塞吉维克看来,二者有颇多相似之处,它们都贯穿于主体的一生,也都是主体动态人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汤姆金斯那里,抑郁脚本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从童年开始,他或她就对拟态交流的关系有一种激情[……]然而这种拟态的激情却与这种关系失败后极易引发的羞耻结合在一起。”(Sedgwick,TheWeatherinProust140)而在克莱茵那里,这种羞耻就类似于在客体关系体验中所遭遇的挫折和创伤。由此也可以看出,塞吉维克的对“羞耻”理解,确实与我们平常对羞耻理解有所不同。
不少研究者在讨论塞吉维克“酷儿操演”中关于“羞耻”的论述时,往往会忽略这一理论背景。如塞吉维克曾记录了“9·11”事件发生后,自己走在路上忽然意识到熟悉的世贸中心已不复存在时所产生的“羞耻”体验(Sedgwick,TouchingFeeling35)。莉莉·谢(Lili Hsieh)对此非常不解:“为什么是羞耻?我感到很困惑。难道不应该是悲伤,害怕,焦虑或生气吗?——况且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区分这些短暂而复杂的主观感受?”(Lili231-232)塞吉维克这里的“羞耻”是一种情动的经历,它由愿望“我向南眺望的风景再次被“9·11”事件前熟悉的双子塔所挡住”(TouchingFeeling35)的受阻而触发,而莉莉·谢则直接将人们对“羞耻”的一般理解代入了塞吉维克那里,从而造成了误读。
情动的“羞耻”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它会对主体的自我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其他的情动不同,“羞耻”会唤起人们对自我的关注和体验,它与人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羞耻在干扰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建构认同。事实上羞耻和认同之间维持着非常动态的关系,互相解构又互为基础,因为羞耻不但有着奇怪的传染性,也有其特殊的个别化效果。”(塞吉维克,《情感与酷儿操演》102—103)因此,羞耻也会影响到酷儿主体的身份认同和个性发展。
在异性恋霸权的主流文化下,对于酷儿主体而言,积极情动受阻的现象会更加普遍,这使得“羞耻”成了很多酷儿在日常生活中最常遭遇的情动体验,它意味着被拒斥、排挤和边缘化,意味着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被打断。羞耻与酷儿认同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使得塞吉维克反对“那些想要直接消除或解决个人或群体羞耻的治疗策略或政治策略”(105),因为“羞耻所浮现的形式并不是群体或个人认同中可以被切除的‘有毒的’部分,而是在认同本身被形塑的过程中就统括在内而且残存下来的”(105)。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酷儿”这一命名的由来。“酷儿”本身就是一种污名化命名,塞吉维克认为,“没有任何肯定的夺回能够成功的把这个字从它和羞耻的连结、从它和性别认同失调的或是污名的童年的可怕无力感中完全脱离”(101)。
值得注意的是,塞吉维克虽然认为“羞耻”是一个有用的情动来想象酷儿操演,但她无意于将“羞耻”的情动经历归结为酷儿的本质属性⑧。她对羞耻的关注主要来自她对被迫成为少数群体的感受的浓厚兴趣,以及主流是如何开发、扭曲和忽视这些差异的(Vincent627)。因此,出于对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深刻认知,以及对酷儿身份的流动性和变化性的理解,塞吉维克一直谨慎地强调,“对于有些婴儿、儿童、和成人而言,羞耻是他们形塑认同的最主要中介”(《情感与酷儿操演》106),“至少对某些(‘酷儿’)人士来说,羞耻可以说是第一个、而且一直是一个永远的、结构性的认同事实”(107)。一些研究者将塞吉维克的“羞耻”归结为酷儿的“人格属性”,认为塞吉维克之所以对“羞耻”感兴趣,是因为“羞耻”提供了一种“将酷儿身份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的工具”(Vincent627)。这种观点不仅将酷儿身份等同于一个固定静态的事实,同时也忽略了塞吉维克对个体差异和体验的重视。
贾森·爱德华兹(Jason Edwards)在《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KosofskySedgwick, 2009)中指出,塞吉维克的作品强调“关注当下的个人体验,然后对它进行严格地反思,即使不是解决问题最有价值的方式,也是最好的方式之一”(Edwards4)。他对塞吉维克1996年发表的诗歌《树上的熊猫》(“Pandas in Trees”)的解读就可以反映这一点。在贾森·爱德华兹看来,这首诗歌中的“熊猫”是一个颇具“酷儿性”的存在,比如熊猫黑白两色组成的皮毛,使它无法被纳入黑人/白人的种族划分;熊猫中的男孩和女孩长得一样,诗歌中的孩子们也无法对熊猫进行性别的二元划分;熊猫妈妈和熊猫宝宝长得也一样,它也不符合成人/儿童的二元划分。诗歌的主人公凯莉由于对熊猫的喜爱而遭到了其他女孩的嘲笑、羞耻和排挤,她们对熊猫充满了偏见,甚至认为熊猫是由中国小男孩假扮而成的。与此相应,凯莉对熊猫的喜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not normal)”“无疑很奇怪(definitely queer)”。女孩们的拒斥让凯莉感到非常难过。幸运的是,凯莉的朋友路易斯及时声援了她,在路易斯的激励下,凯莉也开始勇敢地辩驳其他女孩们的荒谬想法。最终双方达成了理解,女孩们又欢快地坐在了一起,互道晚安,等待夜幕的降临。就像诗歌结尾的勾勒出的温馨画面一样,贾森·爱德华兹认为,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对个体经历的关注,或许可以帮助包括“熊猫爱好者”在内的其他酷儿主体“有一个快乐的、喜剧的结局,而不是悲剧的结局”(Edwards91)。
本文认为,借助对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和克莱茵的客体关系心理学的阅读,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提供了一种走出“性中心主义”的思考路径。这里的“走出”并不是完全抛弃“性”的问题,也不是完全否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颠覆”“揭露”的反压抑策略的重要意义,“走出”的只是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对这些话语资源的偏执依赖。通过“酷儿操演”的论述,塞吉维克使我们意识到“性”只是丰富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经验,精神分析内部也早已对弗洛伊德思想进行了丰富的修改和拓展,“颠覆”“揭露”的反压抑策略也只是摆脱父权制社会中不平等的性别机制的一种策略,它们不应该遮蔽其他更加多元和丰富的可能。
“酷儿操演”走出“性中心主义”的尝试,背后则与塞吉维克对“理论”有效性的反思有关。至少从接触汤姆金斯起,塞吉维克就开始有意识地反思“理论”有效性的问题。在《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阅读西尔文·汤姆金斯》中,塞吉维克开篇就明确指出自己的对话对象“非指主要理论文本中的理论,而是‘应用理论’例行公事化的批判计划中的理论;是作为一个横跨人文学科,现已扩展到历史和人类学的广阔计划的理论;是福柯和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之后的理论,弗洛伊德和拉康之后、列维-施特劳斯之后、德里达之后、女性主义之后的理论”(塞吉维克 弗兰克30)。塞吉维克认为,对“理论”的迷恋使人们形成了某些思维上的“习惯和程序”(31),而塞吉维克则试图摆脱这些“理论”惯习的束缚,打开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理论空间。从这个角度出发,塞吉维克的“酷儿操演”的意义和价值远远溢出了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研究之外,它不仅在传统的“性中心主义”之外,找到另一条将主体广泛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概念化的路径,也提供了“后理论”视野下一种更具生产性的理论范式。
注释[Notes]
① 对于“affect”,国内目前大致有“情感”和“情动”两种译法。前者如台湾学者金宜蓁等翻译的塞吉维克的讲稿《情感与酷儿操演》(《性/别研究》1998年第3、4期合刊),后者如刘芊玥的《“情动”理论的谱系》(《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6期)。为了突出“affect”为人提供动力这一特征,本文将“affect”译为“情动”。
② 这类文章有,李俐兴:《“后理论”的缘起及其三大问题域》,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杨玲:《症候阅读、表层阅读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革新》,《文艺理论研究》4(2018):179—187;刘芊玥:《“情动”理论的谱系》,《文艺理论研究》6(2018):203—211;等等。
③ 这类文章有,郑国庆:《试论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9):6—11;杨玲:《羞耻、酷儿理论与情感转向:以美国学界为中心的考察》,《文艺理论研究》6(2020):192—203;刘芊玥:《塞奇维克的“情动”转向与女性主义“情动”理论的缘起》,《文化研究》38(2019):248—262;等等。
④ 许多关于西尔文·汤姆金斯作品的选集中都附有相关年表,这里不再单独列出。
⑤ 汤姆金斯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两种积极的情动,即享受-喜悦(enjoyment-joy)、兴趣-兴奋(interest-excitement),这两种情动会使人感觉良好,推动人们对世界积极地探索和发现;六种消极的情动,即害怕-恐惧(fear-terror)、不幸-苦恼(distress-anguish)、生气-愤怒(anger-rage),以及羞耻(shame)、厌恶(disgust)、恶心(dissmell),这六种情动都会使人感觉很糟糕,人们会努力去回避这些情动经历;还有一种中立的情动,即惊讶-惊吓(surprise-startle),它会推动人们寻找下一个刺激物。其中,羞耻(shame)、厌恶(disgust)、恶心(dissmell)被定义为辅助的情动(auxiliary affects),因为它们虽然和其他情动的特征有些许不同,但它们有和其他情动同样的激发和放大功能,因此也被作为内在的情动。需要注意的是,汤姆金斯的情动经历了从八种情动到九种情动的发展,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情动,想象,意识》出版期间,汤姆金斯不仅将蔑视(contempt)和厌恶(disgust)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动,而且将蔑视(contempt)修改为恶心(dissmell)。(Sedgwick and Frank,ShameandItsSisters74)
⑥ 金宜蓁等在翻译《情感与酷儿操演》时,将“affect”译为“情感”,将“shame”译为“羞辱”。为了行文统一,本文在引用时将“情感”改为“情动”,将“羞辱”改为“羞耻”,后文不再单独标出。
⑦ 塞吉维克质疑了“揭发”的有效性:“到底在什么基础上我们可以假设人会因为发现某个社会现象是人造的、自我矛盾的、模仿的、幻象的、或甚至暴力的,因而大为吃惊或感觉困扰?[……]事实上,有些揭发、有些除魅、有些见证确实有很大的实质效力(虽然时常不是被期待的那种),然而有些同样真实而且令人信服的揭发、除魅、见证却没有任何实质效力。而只要世界继续这样运作,我们就必须承认,‘揭发’的效益和施力方向并不在于它们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而在别处。”(《情感与酷儿操演》98—99)
⑧ 塞吉维克认为,“把羞耻和酷儿操演连在一起想的用处,不管如何,并不来自它额外帮助确定什么样的言语或行动可被归类为‘操演’,或者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归类为‘酷儿’;它更不会假装去定义酷儿和同性爱欲间的关系。相反的,它所做的是为指涉和操演之间、为酷儿和其他经验认同和欲望的方式之间,所出现的扭转或异常,提供一些心理学、现象学、主题上的浓厚和动机”(《情感与酷儿操演》10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Butler, Judith.GenderTrouble:FeminismandSubversionofIdentity. Trans. Song Sufeng,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Demos, E. Virginia. Ed.ExploringAffect:TheSelectedWritingsofSilvanS.Tomki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Edwards, Jason.EveKosofskySedgwick.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Fawaz, Ramz. “An Open Mesh of Possibilities: The Necessity of Eve Sedgwick in Dark Times.”ReadingSedgwick. Ed. Lauren Berlan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6-33.
Frank, Adam J., and Elizabeth A. Wilson.ASilvanTomkinsHandbook:FoundationsforAffect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
杰伊·R·格林伯格 斯蒂芬·A·米歇尔:《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理论》,王立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Greenberg, Jay R., and Stephen A. Mitchell.ObjectRelationsinPsychoanalyticTheory. Trans. Wang Litao.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8.]
梅兰妮·克莱茵:《爱、罪疚与修复》,杜哲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
[Klein, Melanie.Love,GuiltandReparationandOtherWorks, 1921-1945. Trans. Du Zhe, et al.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House, 2017.]
——:《嫉羡与感恩》,段文静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
[- - -.EnvyandGratitude. Trans. Duan Wenjing, et al.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17.]
——:《儿童精神分析》,林玉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
[- - -.ThePsycho-AnalysisofChildren. Trans. Lin Yuhua.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House, 2019.]
Leys, Ruth. “The Turn to Affect: A Critique.”CriticalInquiry37.4(2011):434-472.
Lili, Hsieh. “Interpellated by Affect: The Move to the Political in Brain Massumi’sParablesFortheVirtualand Eve Sedgwick’sTouchingFeeling.”Subjectivity23.1(2008):219-235.
Lucas, Duncan A..AffectTheory,Genre,andtheExampleofTragedy:DreamsWeLearn.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陈祉研、黄峥、沈东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Mitchell, Stephen A., and Margaret J. Black.FreudandBeyond:AHistoryofModernPsychoanalyticThought. Trans. Chen Zhiyan,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Nathanson, Donald L..ShameandPride:Affect,Sex,andtheBirthoftheSelf.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92.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情感与酷儿操演》,金宜蓁、涂懿美合译,何春蕤校订,《性/别研究》3—4(1998):90—108。
[Sedgwick, Eve Kosofsky. “Affect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 Trans. Jin Yizhen and Tu Yimei.WorkingPapersinGender/SexualityStudies3-4(1998):90-108.]
伊芙·塞吉维克 亚当·弗兰克:《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阅读西尔文·汤姆金斯》,杨玲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9):30—39。
[Sedgwick, Eve Kosofsky, and Adam Frank. “Shame in the Cybernetic Fold: Reading Silvan Tomkins.” Trans. Yang Ling.JournalofGuangz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4(2019):30-39.]
Sedgwick, Eve Kosofsky.EpistemologyoftheClos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TheWeatherinProust. Ed. Jonathan Goldber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TouchingFeeling:Affect,Pedagogy,Performativit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edgwick, Eve Kosofsky, and Adam Frank, Eds.ShameandItsSisters:ASilvanTomkinsRead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omkins, Silvan.AffectImageryConsciousness:Cognition. Vol.4.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1992.
Vincent, J. Keith. “Shame Now: Ruth Leys Diagnoses the New Queer Shame Culture.”Criticism54.4(2012):623-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