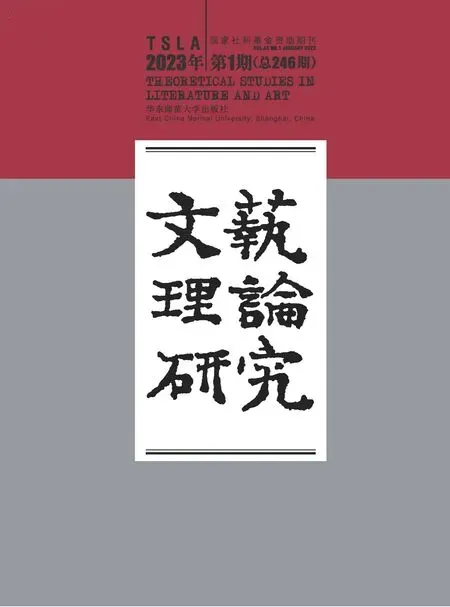德里达论文学语言
——以《罗米欧与朱丽叶》为范例
2023-09-03肖锦龙
肖锦龙
一、 语言的实质:述行性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借助语言符号表征出来的。那么语言符号的实质是什么?文学语言是怎么样的?这是德里达前期(1990年前)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他发表于1967年的三大巨著《言语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书写学》探讨的都是各类所指与能指的关系问题,根本上是围绕着语言表征问题展开的。1971年,他发表了名作《签名事件背景》,对英美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解构主义改造,提出了解构式的语言理论。
英美言语行为理论最早是由英国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奥斯汀提出来的。西方符号学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人是语言动物,没有语言符号人无以为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语言这个媒介以外。语言就像某种精神的氛围,渗透在人们的思想、感情、知觉和概念的各个方面。”(Cassirer145)关于语言,人们普遍认为它是记述事物和思想经验的工具,是描述性的。奥斯汀在对日常语言的细致考察中发现,语言不仅有描述事物和表现真理的“陈述”(constative)功能,而且有用词做事的“述行”(performative)功能。譬如:我不小心撞了人,我会对他说“对不起!”此话不是描述一件事,而是做一件事——向别人致歉。奥斯汀将语言用词语做事的功能称作是述行功能。他进一步指出,语言的陈述功能和述行功能密切关联,我们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Austin95)。他摒弃了陈述话语和述行话语之二分法,将它们归并到“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旗帜下,明确指出人类语言根本上是述行性的。
奥斯汀说,述行句本身有固定的程式,“此程式包括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中说出特定的词”(14),从而取得特定的效果。奥斯汀将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述行句称作恰当有效的(felicity),将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述行句称作非恰当有效的(infelicity)。举例来说,现实中一个新郎在结婚典礼上宣称:“我愿意娶她为妻。”此述行句是恰当有效的述行话语,因为发话者在说此话之际娶了“她”,借它做成了一件事。而戏剧中一个扮演新郎的男演员在舞台上说的同一述行句是非恰当有效的,因为那男演员实际上未娶任何人。奥斯汀认为,一般日常语言中的述行话语是恰当有效的,而玩笑和文学作品中的述行话语是非恰当有效的。恰当有效的述行话语是非恰当有效的述行话语的源头和范本,非恰当有效的述行话语是恰当有效的述行话语的引用、褪变形式,是弱化的述行句。
“奥斯汀将述行言语分析从真理价值的统治,从真/假二元对立中解放了出来。”(Derrida,MarginsofPhilosophy322)他的言语行为理论首次深刻揭示了人类语言除陈述说明事物功能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用途,即促使事件发生或用言语做事的功能。但它将言语行为视作一种由语境(包括主体意图和传统、习俗、语言习惯等)制约的决定性行为,是可计算的行为,未意识到它是一种由语言结构、法则或密码(codes)支配的非决定性行为,有不可计算的一面,显然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
德里达一方面同意奥斯汀关于人类语言的主要功能是述行,是用来做事的观念,另一方面又认为奥斯汀的理论受传统的主体论思想影响太深,因而未能对人类语言话语的述行性给予充分有力的说明。他一面沿承奥斯汀的以言做事观念,一面解构了后者的主体论思想基础,从根本上颠覆了它。
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1.奥斯汀认为,语言是交流工具,人类言语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言说者的意识或意图。一个人说话主要是为了传达他的思想情感,一个人只要按既定的程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听话者会明确理解他的想法,他的言语能取得预期效果。言语受制于主体,是表现性的。德里达指出,语言是人的栖身之地,言语行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人的意识或意图,而是语言结构、法则或密码。世界是在人的意识经验中呈现出来的,人的意识经验一开始就被语言格式化了,是由语言建构成的,所以世界最终是由语言文本建构的,“文本之外无物”(Derrida,OfGrammatology158)。语言的本质属性是重复性。一个语符如果不能重复出现,就无法流通,无法变成语言符号。一种大脑意念如果不在声音、文字中重复显现,它无处存身,无法为人们所了解,无法成为语言要素。语言从能指到所指都是重复性的。言语根本上受制于语言的内在运行法则重复性。2.奥斯汀认为,言语活动受主体控制,意义是确定的。在一种恰当有效的述行言语活动中,说话者的意识或意图可以在言语中得到完满传达,听话的人可以明确理解他的意识或意图,可以“既正确又完全地履行”(Austin14-15)。德里达指出,言语活动不受主体控制,是非决定性的,意义不确定。言语活动的本质是重复性。一种言语从一种语境进入另一种语境中时,其意义必然会发生变化。正如奥斯汀所言,当日常语言中的言语(如在结婚典礼上一个男人宣称:“我愿意娶她为妻。”)进入文学语言的语境中(如在舞台上一个男演员宣称:“我愿意娶她为妻。”)时,它就从“恰当有效”的言语变成“非恰当有效”的言语。所以任何言语都有两个方面:一是“恰当有效”,即一定程度上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非恰当有效”,即多多少少会言不达意,事与愿违,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否定的可能性必然是结构性的可能性,在如上言语行为运作过程中失败是必然性的风险。”(Derrida,MarginsofPhilosophy323)说话者的言语进入听话者耳中的状态是一种言语从一种语境进入另一种语境中的状态,它的意义随着语境的变化必然发生变化,所以说话者的意识或意图无法得到完满传达,言语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而当说话者将他的意识或意图借口语或书面语重现出来时,是将无形的意念转换成了有形的声音文字,将一种东西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这样意识或意图与言语形式之间不可能完全等同,必然有间隙,说话者的意识或意图不可能得到完满表现。从言语的运行法则出发看问题,主体永远无法完全控制他的言语,他所说总是与他所想说有间隙,言语总是超出和背离人的意识或意图,总会引发新异的、意外的东西,其意义随着语境的不同不断变异,是不确定的。3.奥斯汀认为,言语是人的意识或意图的传达工具,作用主要是传达和实现主体的意识或意图,是表现性的。德里达认为,言语是开发世界的方式,功能主要是借词语分辨、梳理、组构人们丰富多变的经验意识,为大脑意念命名,打造新语言话语,建造新生活图景,开辟新思想和生活境界,是述行性的。美国的著名政治文本《独立宣言》是人们以言做事、开发新世界的述行话语的范本。它曾对美国人的经验意识进行创造性命名组构,缔造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即“所有的人天生是平等的”,后者与传统话语“人是上帝创造的、有高下贵贱之分”完全对立,它树立了一种新生活范型即人人自由平等之范型,创立了一种新机制即西方现代民主社会机制,开拓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境界。
由此,德里达得出如下结论:人类语言根本上是用词语做事的,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本质特征是人和语言、陈述和制作、重复和变异、复制和建构二元互补,矛盾杂糅,是双重的,丰富复杂的。德里达将此状态称作“言语的事件”(the event of speech):“因而,我回到了对我而言基础性的问题上,即思考总体事件的地位,思考言语事件的地位或借言语做事的地位[……]重复给自己结构了一个前提,后者引入了一种本质性的开裂和分割。”(MarginsofPhilosophy326)
简捷地说,在德里达那里人类言语行为是述行性的,既说事又做事,既重复又创造,既可计算又无法计算,既是可能的又是不可能的,是对可能之不可能状态的体验和表征:“我们这里应该说此不-可能,或一种不-可能不仅仅是不可能,不仅仅是可能的对立面,它也是可能的条件或机遇。不-可能是关于可能的完全体验。指的是转变预想、体验或者说是关于可能和不可能的体验。”(Derrida,ACertainImpossiblePossibility254)
二、 文学语言的形式:格言
所有的语言都是述行性的,文学语言当然也不例外。德里达在很多著作中反复申述文学是生产活动(production)、文化机制(institute)、以言做事的行为(acts),集陈述与制作于一体,是述行性的。如他在文学专论《“这种被称作文学的奇怪机制”:与德里达的访谈》中一再宣称:“我的写作通常是对当代作家们的思考,如马拉美,乔伊斯,或策兰,巴塔耶,阿尔特,布朗肖等。[……]他们的问题与文学述行行为和批评述行行为结为一体”(Derrida,ActsofLiterature41-42);“文学作品和论说文学的作品,以及关于文学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述行性在最小的可能性空间中显现出最大的可能性”(ActsofLiterature46)。
那么文学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以言做事的行为?德里达在《“这种被称作文学的奇怪机制”:与德里达的访谈》中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说任何东西的机制”:
对我而言,文学以混合的方式表现为允许人们说任何东西的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机制性虚构空间,也是虚构性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可以说任何东西。说任何东西无疑是借助转换将所有形象,一个又一个地集中起来,借形式化将它们组成一个整体。说任何东西也是打破禁忌。所有的领域都自己解放自己:法则推翻法则。文学的法则根本上就是挑战或摒弃自己的法则。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这种“说任何东西”的经验中思考法则的本质。它是一种淹没现有机制的机制。(ActsofLiterature36)
也就是说文学不是记述建构社会历史现实的其他话语机制如政治、历史、哲学等的符号,相反,它自身就是一种建构社会历史现实的话语机制,它与其他机制的关系不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而是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它的本质特征就是“打破禁忌”“淹没现有机制”。换言之,就是突破和超越现成的机制,拓制新机制,是一种逆反的开发性的独特机制,所以德里达将之称作“奇怪机制”(ActsofLiterature36)。
这种逆反的开发性的独特机制具体是怎么样的?德里达分析说,文学不像人们一般理解的那样是有机统一、界限分明的,而是矛盾混杂、跨界模糊的。第一,它跨越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是实证话语与想象话语的二元混合体:“在文学‘故事’中事件已跨越了其内在的‘真实’文档与‘虚构’文档的界限。”(ActsofLiterature35)文学世界既以现实事物为基础又是语言建构物,既是历史又是叙事,是被叙事毁了容的历史或者说叙事中的记忆:“它是毁灭了的历史,记忆的叙事。”(ActsofLiterature42)第二,它跨越了外在多元社会话语与内在个人单一话语的界限,在那里“百科全书式的尝试与自传式的尝试无法分离”(36),因而是广泛的社会话语的个性化,是普遍性的独特化:“这种对历史、语言、百科全书的压缩,与绝对的独一无二事件浑然不可分。是一种独一无二性签名。”(ActsofLiterature43)第三,它跨越了规则与无规则的界限,是规则的无规则化:“文学是承载着传统、规则等的历史性虚构机制,但这种虚构机制在本质上又授权人们说任何东西,突破所有规则,置换所有规则,因而构建、发明甚至悬置了自然与机制、自然与传统法则、自然与历史的传统差异。”(ActsofLiterature37)也就是说,文学机制是一种突破现实中的一切现成的分类、界限、规则的机制,是一种还原事物原初无二元对立式分类、界限、规则的多元混杂性式蛮荒境界的机制,是一种开发超现实的境界或者说不可能状态的机制。
他在《存留》中称“文学没有本质只有功能”(Blanchot and Derrida28),它没有家屋,寄居在别人家里,“直接刻写在社会身体中”(Blanchot and Derrida28),寄生于其中。它的目标是见证真理,不过却又无法见证真理,因为虚构既是它的特权也是它的本质属性。从法律和历史等日常机制的角度看它根本无法见证真理,是伪证。但它确实能见证真理,此种真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在事物之真,而是特定的内在经验之真,这是其他的机制所无法具备的独特品质。由此,德里达说:文学“既是实证又是虚构,既是法则又是非法则,既是真理又是非真理,既是实情又是谎言,既是忠实性又是伪誓”(Blanchot and Derrida30)。它超越了现成的所有二元对立观念、范畴如实证与虚构、法则与非法则、真理与非真理、实情与谎言、忠实性与伪誓,穿越了一切现实结构形态,完全是事件性的。
因此,文学本质上是对事物之边界阈限的体验:“体验存在,体验形而上学的边界阈限,不多也不少。文学也许站在所有东西的边界上,差不多超出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它自己。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物,也许比世界本身更有趣。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学的名号(如果文学有定义的话)下被宣告和被拒绝的东西,不能与其他任何话语混同的原因。文学从来不是科学的,哲学的,对话式的。”(Derrida,ActsofLiterature47)也就是说文学语言超越所有的现成陈述,超越所有的概念,是对前概念的“存在”“所有东西的边界”的体验和表征。
那么这种穿越现成的语言概念、回到事物原初本真状态的文学语言具体是如何样的?它的本质特点何在?德里达进一步指出:
现成的机制是保守的,但反-机制也是保守的,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特定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保守的。(ActsofLiterature58)
体验书写就是“服从”必然性:给独一事件以充分空间,在不再包含理论知识的书写行为之形式中、在陈述性描述中发明新东西,给自己以诗歌-文学的述行性,至少提供期许、祈使,提供建构或确立法规的行为,提供如上的各种述行性,后者不仅会改变语言,或在改变语言中,而且会改变大于语言的东西。它永远比语言有趣。(ActsofLiterature55)
在德里达看来,走向前概念的事物本身的文学语言不像很多后结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是与现成机制相反的“反-机制”或与现成语言相反的超语言,因为世界上没有这种相反的“反-机制”或超语言,这种“反-机制”或超语言是人们用二元对立思想推断出来的,是陈述句的副产品,而非实存,因而是虚幻不实的。后者与传统的机制或语言没有本质差别,是“保守的”。真正可以突破现成机制、抵达事物本身的“诗歌-文学”语言则是一种“在陈述性描述中发明新东西”的语言,一种介于陈述和制作、重复和创造之间的“述行话语”。因为只有后者才可“穿越语言的界限”(Derrida,ActsofLiterature60),恢复事物既普遍又独特的二元矛盾、双重化本相。
为了将文学语言从一般语言中分离出来,现当代批评家们给它取了一系列新名字,如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英美新批评的“反讽”“悖论”“张力”,解构主义者德·曼的“修辞”,等等。德里达认为,这些新名字将文学语言与一般语言清楚明白地区别开来,使人们明确认识到了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具有开拓意义。不过它们完全否定文学语言与一般语言的联系,明显不符合实际,是错谬的。他通过反思德·曼的“修辞”术语澄清了它们的错谬之处。他在1989年与阿特里奇的访谈中明确指出:“虽然我不总是、在所有方面都同意他的观点,但保尔·德·曼关于所有的修辞总体上最终是自我解构的看法没有错,它是对你称作是反讽的东西的实践。当然,问题不这么简单。‘反讽’不是指代‘悬置’、指代新异性的最好的范畴。在诗歌或文学体验中存在着肯定无法完全简约的东西。”(ActsofLiterature50)换句话说,文学体验中存在着哲学思想,文学语言中存在着一般语言,文学经验和哲学思想、文学语言和一般语言不是泾渭分明、截然相反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无法分离的二元互补关系。真正的文学语言是陈述句与述行句、文学经验与哲学思想的二元矛盾体。为此,德里达另起炉灶,给他理解的这种集经验与思想、一般与独特为一体的文学语言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格言”。1986年,德里达发表了一篇格言专论《格言错乱》,对之进行了极详细的阐发论证。
1969年,法国思想家和作家布朗肖将之从语言修辞领域引渡到语言本体领域,用之指代一种与一般逻辑有序的思想言说方式相反的方式。他在短文《反思虚无主义》中说:“尼采那里有两种言语。一种属于哲学的话语,一致的话语,他有时渴望通过创作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类似于传统的伟大作品——来终结这种话语。[……]但这样一种话语——哲学本身——显然总已经被尼采超越了;他假定这种话语,而不给它一种陈述,这是为了进一步根据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言说:不再是整体的语言,而是零碎的语言,复多的语言,分散的语言。”(布朗肖297—298)布朗肖将尼采的“零碎的语言”称作“格言”:“的确,它似乎接近格言(aphorisme),因为格言的形式被承认为尼采所擅长的形式。[……]这是一种独特的、孤独的、零散化的言语,但作为断片,它已在如此的破碎中得以完成、整全。”(298—299)
正像约翰·麦克基尼(John McKeane)指出的,布朗肖与德里达是深交多年的挚友,相互影响很大(McKeane111-125)。布朗肖对格言的论述先于德里达,后者的格言概念显然取自布朗肖,是对布朗肖的格言理念的进一步发挥。他在《格言错乱》中解释说:
格言是名字。正像其名字所暗示的,格言是分离,它标志的是没有关联,它自我设定、圈限、立足,它分离以便终止——从而进行自我界说。
一句格言是一个名字,但每一个名字以格言的构形存身。
格言曝露为错乱,它暴露话语——将话语移交给错乱。
开初是错乱。开初是速度。词和行为取代之。格言超越了它们。(ActsofLiterature416)
德里达说,格言首先是一种给事物命名的独特的语言形式。其独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是集合式的话,而是分解式的,不是将无限多样的个别语词依语法规则集合到某种完整有序的语言共同体如句子、篇章、文本、话语中,而是自我“设定”“圈限”“立足”,孤立自在,将自己从语词背景中抽离出来,与周围的语句、篇章、话语拉开距离。德里达在其临终前的最后一个系列讲座《野兽和主权者Ⅱ》(2002—2003)中直接将格言称作“孤岛”:“一个没有背景的句子,仿佛是一个孤岛。既没有其他句子在它前面,也没有其他句子在它后面。完全是分离、脱节、孤立的。”(Derrida,TheBeast5)第二,不是有序的,而是混乱的。德里达称格言是以“错乱”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他解释说:错乱,英法文同形,为counter-temp,“在英语以及法语中指‘反时序的事件,不幸的意外,预料不到的灾祸或故障’(OED),而在法语中也指‘脱节’或音乐意义上的‘离乱’,指‘坏的或错的时间’、‘错乱-时间’”(ActsofLiterature416)。错乱,简而言之,就是反时序、不合法则、出人意料、混乱无序。也就是说,格言本质上是不合规范、错乱的。
德里达进一步说,除了命名,格言还有一种功能就是叙事,主要包括三种形态或环节:第一,“开初是错乱”,人们首先面对的是自然无序的事物本身或初始的错乱经验;第二,“词和行为取代之”,人用词和行为等形式将事物或错乱经验表征出来;第三,“格言超越了它们”。格言将事物、人的原始经验转化成语词、文字的言语行为,是集事物经验与语词文字、存在物与叙事、所指与能指为一体的综合形式,是二元矛盾、双重化的。
总之,在德里达看来文学语言是一种以言做事的言语行为,不是记述世界的,而是开发世界的。其本质特征是既与其他话语相互关联又迥然有别,既是陈述性的又是述行性的,二元互补、矛盾背反。格言是文学语言的典型形式或标本。格言主要包括名词句和动词句,给事物命名和叙事事物两种形式,本质特点是分离零散化和矛盾双重化。
三、 格言的特征:零散化和双重化
在德里达看来,莎士比亚的千古名作《罗米欧与朱丽叶》是以分离零散化和矛盾双重化为本质特点的格言方式的最好的实践文本。因而他在《格言错乱》中对作品的格言性作了极详细的分析阐发,借以说明他关于文学语言的基本看法。德里达明确指出,格言的首要特征是分离性零散化:
当然修辞可以会转化为一种修辞设置,一种用来最强有力地、最经济地或最策略地进行控制的诡秘的计算术,它熟知如何发掘意义的潜能。但在以诡秘的方式自我控制之前,格言首先呈现为无任何人为防御机制的错乱经验,那种在任何计算之前、在计算本身之外的错乱经验
格言或分离的话语: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都献身于自我分离,都在自身之纯正绵延的孤独体中将自己封闭起来,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它与其他句子永远是随机的,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好或坏。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确定的,从句子与句子间的链接到秩序都是不确定的。(ActsofLiterature417)
德里达认为,格言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在一般语言中每一个句子或段落都是它所属的整体结构中的一部分,而在格言中每一个句子或段落都是分离的孤立的,自成一体,独立于它所属的整体结构。这种状态正像南希在《不作为的共同体》中所说的人类“独体”(singularity)的状态:它不是某种人类“共同体”(communities)的一个螺丝钉、组件或曰人类个例,而是一个设备、元件或曰人类独体(singularity)(Nancy1-43)。莎士比亚的剧本所表征的就是罗米欧与朱丽叶这样的分离孤独的人类独体:“罗米欧和朱丽叶就是格言,他们首先在他们的名字中,在那里他们又不是他们自己。”(Derrida,ActsofLiterature417)他们虽属于他们的名字所指代的共同体如蒙太古和凯普莱特家族,但他们又与他们所属的共同体是分离的,是他们自己。
从句子联结或系列的角度看,格言与格言之间不是一个从属于另一个的必然关系,而是一个与另一个随机相遇的偶然关系:“每一个格言系列具有其特别的绵延过程。它的时间逻辑阻止它与另一个地方的话语共享它的所有时间,不可能共时同步。我这里说的是时间的话语,它的标记的话语,它的日期的话语,时间过程及其本质上脱轨的时间话语,它扰乱欲望的时间,带着相爱之人的脚步偏离时间流程。”(Derrida,ActsofLiterature418)也就是说,在格言形式中,一个句子与另一个句子永远无法完全共时同步,相互之间永远有间距,永远无法取得一致。一个句子永远是自成一体的、分离的、孤立的。
莎翁的戏剧所表征的正是人类世界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无法共时同步的情景,有如格言中一个句子与另一个句子之间无法共时同步的情景:“罗米欧与朱丽叶实际经验到的东西是典型的混乱无序,是绝对的共时同步的不可能。而相反他们则经历了——跟我们一样——一系列无序,如脱节、混乱、空间的分离、由格言引出的故事传播和变调。”(Derrida,ActsofLiterature417)《罗米欧与朱丽叶》所密切关注和着力表现的不是事物的必然性、有序性,而是偶然性、无序性。具体到罗米欧与朱丽叶身上,它重点展示的不是他们谋求相遇约会、长相厮守的愿望和行为最后得以达成的情景,而是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情景。“没有对共享的现在的期许就没有格言,没有誓约、没有对共时同步的期望、没有对共享人生的欲求就没有格言。这种共享是格言的另一称谓。”(Derrida,ActsofLiterature421)罗米欧与朱丽叶两个人邂逅相遇后,萌生了炽烈的爱恋之情,产生了强烈的共享对方感情的愿望,渴求共栖同处、心心相印、结为一体。但由于时空环境的差异,他们的爱恋之途云遮雾罩,荆棘密布。为了清除各种阻挡他们两人之间和他们与周围世界之间和睦共处的障碍,他们运用各种人为手段如“日期、时间表、财产登记、地名以及所有可以用来编织时空实况的文化网络符码,即错乱-捕捉器,借以减化或控制差异,捕获差异,主宰差异”(Derrida,ActsofLiterature419),但事与愿违,最后不但没有控制、捕获、主宰差异混乱,相反却被差异混乱所控制。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偶发事件层出不穷,无休无止,他们根本无法应对。所以他们期盼共时同步、结为一体的愿望只是黄粱美梦,仅存在于幻想中,无法在现实中兑现。整部《罗米欧与朱丽叶》全描绘的是各类超出两个主人公的理解力和控制力的意外事件以及由之所导致的约会流产之混乱景象。其中对他们的最后一次约会的失败状态的表现尤为醒目和令人震撼。德里达对之作了详尽分析:
罗米欧与朱丽叶,两种欲望的连接是格言式的,但又密不可分,是在爱或期许的当下错位状态中持续的。他们在其名字中期许,但跨越和超出了他们自己给定的名字,期许其他的名字。失败的约会,意外的事故,信件没有及时送达目的地,迂回的时间拖延了一封失窃的信件。第三方、教胞、劳伦斯神父的救助方案,同时使用药物和信件,都流产了,良药变成了毒药。[……]对罗米欧和朱丽叶来说,所发生的一切,各种处于若干个系列交叉点上和超越一般理解力的、以偶然的和不可预期的形式呈示出来的事故,只能是其所是的东西等等,都是偶然事件。实质上,偶然事件在其发生之前,早已出现了。[……]意外的错乱说到底是本质的错乱。换个说法,意外不是意外。(ActsofLiterature419-420)
德里达认为,罗米欧和朱丽叶两个相爱之人无法共时同步、合为一体看似是由意外事件造成的,是偶然的,实际上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因为意外事件是世界的本质属性即时间性的外显形式,它是世界内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本无法完全克服。因而他们两个注定无法完全共时同步、合为一体,他们的约会和完美结合注定不会完成,注定会失败流产。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从两个人物最现实本真的存在状态出发,用非语言逻辑的方式或言格言直觉的方式将世界人生的这种极度丰富复杂性最真切最深刻地表达和呈现了出来。
德里达进一步分析指出,格言不仅在处理句子与句子的关系上与一般语言大相径庭,而且在处理句子内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也与一般语言完全相异:不是统一一体化的,而是矛盾双重化的。如前所述,格言的首要功能是给事物命名。所谓命名,就是把事物转化成语词文字,说得直白些,就是把事物装进语词文字中,其中必然包含着事物与语词文字、实体与名字两个相反的方面,必然是二元矛盾、双重化的。莎士比亚在《罗米欧与朱丽叶》中不仅是用这种双重化的格言方式描绘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的,将之归结为他们两人的名字与实体、名字所代表的社会文化规则与实体本身洋溢的个人生命冲动激情之激烈矛盾的结果,而且还对之有明确意识,体察到了名与实、文化与自然之间无法调和的二元矛盾性和张力。这在他笔下的人物朱丽叶的那段极负盛名的阳台感言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罗米欧啊,罗米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米欧呢?只有你的姓名才是我的仇敌;你即使不姓蒙太古,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你,姓不姓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不是手,又不是脚,又不是手臂,又不是脸,又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啊换一个姓名吧!姓名本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罗米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他的可爱的完美也决不会丝毫改变。罗米欧,抛弃你的名字吧;我愿意把我的整个心灵,赔偿你这一个身外的空名。(莎士比亚36)
朱丽叶的这段话强调了如下不争的事实:一个人和他的名字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个人的实体,有血有肉;后者是一个人的代号,只是一个空壳。所以朱丽叶断言,罗米欧的名字既不是罗米欧之人的手、脚、臂,也不是脸,不是他身上的任何东西。他不叫罗米欧,还是同样可爱完美,就像玫瑰不叫玫瑰也同样芳香一样。因此,她请求罗米欧抛弃他的名字。为了补偿罗米欧,她发誓自己也要抛弃名字。德里达认为,朱丽叶的这段感言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人与人之名、物与物之名之间不是一种前者决定后者的必然关系,而是一种二者矛盾互补的偶然关系:“名与人没有关系。不属于人的身体、精神、本质。就像人的名字不属于人一样,事物的名字也不属于事物。”(ActsofLiterature427)两者本质上是差异关系,而不是同一关系。
德里达分析说,朱丽叶虽然在意识的层面上认识到了名与实的差异,提出了抛弃名字、保留纯正实体的去名存实主张,但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并未将名与实截然分开。“她呼唤罗米欧放弃名字时是如此说的:‘罗米欧啊,罗米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米欧呢?’而不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你偏偏叫罗米欧?为什么你要顶着这个名字(就像披着一件衣服,一个装饰品,一个符号)?”(Derrida,ActsofLiterature426)显然在无意识中朱丽叶不是将罗米欧的名与实当成两种东西,而是当作同一种东西:罗米欧的名等于罗米欧的实。足见人的名字已经是人的实体的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或者说人的实体已融合到名字中了。
进而言之,没有人的实体,人的名字无驻足之地,无法存身。反过来,没有人的名字,人的实体没有栖身空间,无法具形显现,无法呈示出来。人的名字与人的实体二元互补,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离。所以德里达认为,朱丽叶要求罗米欧抛弃他的名字,实质上既是在拯救他又是在毁灭他。之所以说是在拯救他,是因为抛弃名字后,他可以找到自己的本体,找到自己真正的存在,找到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活在他自己的爱情中”(Derrida,ActsofLiterature427)。之所以说是在毁灭他,是因为他的名字与他的实体捆绑在一起,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实体。“罗米欧的个人名字承载着父亲的名字,它使人想起了谱系法则。罗米欧自己、名字的承载者,不是名字,但确实是罗米欧,他所承载的名字。”(Derrida,ActsofLiterature423)“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名字,他存在于名字中。”(Derrida,ActsofLiterature427)抛弃名字就等于抛弃实体、生命。朱丽叶想要罗米欧抛弃名字就等于是要他抛弃实体、生命。这充分说明人作为一种被文化化了的独特存在者生来就有文化与自然、实体与名称两种既无法分离又矛盾互补的方面,无限复杂多样,无法减约(irreducible)。“罗米欧是罗米欧,罗米欧又不是罗米欧。只有摒弃他的名字,他才是他自己,只有凭借名字他才是他自己。”(Derrida,ActsofLiterature427)罗米欧既是实体又是名字,是实体与名字两大相反相成因素的混合体,是矛盾差异、双重化的。
由此德里达得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命名方式的格言的运作法则是双重化法则:“没有名字的双重化法则,就没有错乱。这种法则,这种错乱的法则是双重化的,因为它是内在分裂的;它作为真理,在其内部承载着格言。格言就是此双重化法则。”(ActsofLiterature430)正因为莎士比亚对集实体与姓名、自然与文化、所能与指能为一体的双重化法则有深刻的理解和明确的意识,所以他的文学命名活动或言戏剧述行行为才能入木三分,才揭示出了人类生活的无限丰富复杂性,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人生的本相真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不朽经典。
德里达在接受阿特里奇的访谈,谈到他为什么接受梅斯吉什的请求、为法国版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写剧评时说:“此剧本以‘范例’方式提供了我要说的东西,提供了我认为关于纯正名字、历史、错乱等不得不深入反思的东西。”(ActsofLiterature66)也就是说,剧本说出了他想说的东西,即他关于文学语言的基本看法。他通过分析阐发《罗米欧与朱丽叶》独特的书写方式即格言方式,最充分有力地说明了文学语言的实质:它是一种以开发揭示世界的无限丰富生动真相为出发点的分离零散化和矛盾双重化的独特语言方式。
总之,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学是一种记述反映事物的工具,功能是逼真表现事物,理路是模仿再现,方式方法是整体有序化和统一一体化,目标是揭示事物的恒定不变的本质。与之相反,德里达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反映记述事物的工具,而是一种以言做事的行为,功能是开掘发明事物,理路是陈述制作,方式方法是分离零散化和矛盾双重化,目标是开发事物无限丰富生动的本相。德里达的这种文学语言观念一举突破了千年传统,可谓旷古烁今,独到新异,很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开发。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ustin, John L.HowtoDoThingswithWord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Blanchot, Maurice, and Jacques Derrida.TheInstantofMyDeath&Demeure:FictionandTestimony.Eds. W. Hamacher and D.E. Wellbery. Trans. E. Rottenber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莫里斯·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Blanchot, Maurice.TheInfiniteConversation.Trans. Wei Guangj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Cassirer, Ernst.Symbol,Myth,andCulture:EssaysandLecturesofErnstCassirer,1935-1945.Ed. Donald Phillip Vere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Derrida, Jacques. “Aphorism Countertime.”ActsofLiterature.Ed. Derek Attri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416-33.
- - -. “A Certain Impossible Possibility of Saying the Event.” Trans. W. Gila.CriticalInquiry33.2(2007):441-61.
- - -.TheBeastandtheSovereign,VolumeII.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London 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 -.OfGrammatology.Trans. Gayatri C. Spivak. London an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 “Signature Event Context.”MarginsofPhilosophy.Trans.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307-330.
- - -. “This Strang Institute Called Literature.”ActsofLiterature.Ed. Derek Attri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33-75.
McKeane, John. “‘Périmer d’avance’: Blanchot, Derrida and Influence.”QuestionsofInfluenceinModernFrenchLiterature. Eds. Thomas Baldwin, James Fowler, and Ana de Medeiro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111-125.
Morson, Gary S. “The Aphorism: Fragments from the Breakdown of Reason.”NewLiteraryHistory34.3(2003):409-29.
Nancy, Jean-Luc.TheInoperativeCommunity.Ed. Peter Connor. Trans. Peter Connor, et al. Minneapolis and Oxford: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1.
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Shakespeare, William.TheCompleteWorksofShakespeare. Trans. Zhu Shenghao. Vol.8.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2.]
Waite, Maurice, ed.OxfordEnglish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