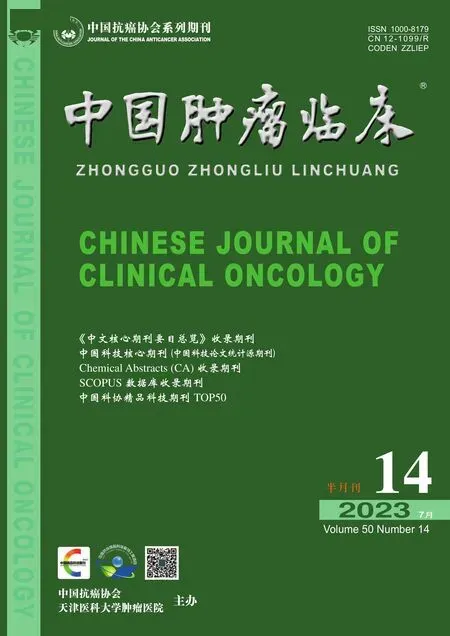三级淋巴结构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2023-09-01董丽媛王燕妮鲁智豪
董丽媛 王燕妮 鲁智豪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是肿瘤发生、发展和转移的“土壤”,除肿瘤细胞外,还包含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及肿瘤血管系统等,其中三级淋巴结构(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TLS)是反映TME 状态的重要标志物[1-2]。TLS 是在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感染及肿瘤等慢性炎症刺激下,在非淋巴器官内形成的异位淋巴样结构,反映了外周组织在长期暴露于由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介导的炎症信号时出现的淋巴新生[2]。多项研究表明,B 细胞和TLS 与不同肿瘤患者更好的预后相关[3-5],但是TLS 塑造肿瘤微环境,发挥抗肿瘤效应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楚,因此深入解析TLS 有助于充分挖掘其在抗肿瘤免疫反应中的潜在应用价值,指导肿瘤精准免疫治疗。
本文重点介绍TLS 的组成及其形成过程,检测方法,同时强调了TLS 对肿瘤免疫反应的影响并讨论通过诱导TLS 形成增强抗肿瘤免疫疗效的可能性。
1 TLS 的形成和细胞组成
在肿瘤微环境中,TLS 的形成过程极为复杂,涉及多个细胞及细胞/趋化因子的调控作用。目前普遍认为TLS 的发育与形成过程类似于次级淋巴结构(secondary lymphoid organ,SLO),由淋巴组织诱导细胞(lymphoid-tissue inducer,LTi)和淋巴组织形成细胞(lymphoid tissue organizer,LTo)通过相互作用在特定部位形成。在小鼠肿瘤中,LTi 可以是T 细胞和B 细胞[6],在人类肿瘤中,LTi 可以是固有淋巴样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ILC)NKp44+ILC3 细胞等[7]。LTo则主要是基质细胞,如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CAF)等[6]。
在TLS 形成过程中,一方面LTi 通过表达淋巴毒素α1β2(lymphotoxin α1β2,LTα1β2)与LTo 上的淋巴毒素β受体(lymphotoxin-β receptor,LTβR)结合,促进LTo 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C,VEGFC),介导HEV 的形成,同时HEV 也可以分泌多种黏附分子(ICAM1、VCAM1、MADCAM1),进而促进B 细胞和T 细胞的发育[2]。另一方面,LTi 通过分泌IL-17,与LTo 上的IL-17R 结 合,促 进LTo 分 泌CXCL12、CXCL13、CCL19 和CCL21等趋化因子,这些趋化因子可以从附近的HEV中募集CXCR5(CXCL13受体)和CCR7(CCL19/CCL21 受体)阳性的淋巴细胞[8],组织形成T 细胞和B 细胞区(图1)。
成熟TLS 的结构是T 细胞区包围着含有生发中心的B 细胞区,由免疫细胞和基质细胞组成的有组织的聚集体。基质细胞除了作为LTo 分泌趋化因子招募免疫细胞外,还能进一步转分化为滤泡树突状细胞(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s,FDC)和成纤维网状细胞(fibroblastic reticular cells,FRC),分别支持B 细胞区和T 细胞区[6]。免疫细胞主要包含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FDC,CD20+B 细胞,CD3+T 细胞,CD4+滤泡辅助T 细胞(follicular helper T,Tfh),CD4+辅助T1 细胞(helper T1,Th1),CD8+细胞毒性T 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和调节性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等,DC 和B 细胞可将局部抗原呈递给T 细胞,从而导致T 细胞活化和增殖。Tfh 和Th1 则可以通过共刺激分子或受体配体相互作用,促进B 细胞转化为增殖的B 细胞簇,即生发中心(germinal centre,GC)。在这个过程中,B 细胞经历了亲和力成熟,类别转换和体细胞超突变的过程,成为具有成熟免疫功能的B 细胞[2]。
总体而言,TLS 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多步骤、动态变化过程,免疫细胞衍生的促炎信号作为诱导剂,活化的成纤维细胞通过建立并维持淋巴细胞结构或产生关键的趋化因子来充当组织者,将多种细胞招募到相应位置,这些细胞通过广泛的细胞间相互作用,最终分化成熟,并发挥免疫效应。
2 TLS 的标记与检测方法
目前,TLS 已在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和黑色素瘤[3-5,9]等多个瘤种中被检测,然而不同瘤种对TLS 的标记策略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导致不同癌症类型的数据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常用的方式主要有苏木精—伊红染色(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mmunohistochemistry,IHC)、多重免疫组织化学(multiplex immunohistochemistry,mIHC)/多重免疫荧光(multiplex immunofluorescence,mIF)染色以及测序检测(趋化因子-score 等),见表1。
H&E 染色是表征TLS 最简单的技术,在形态学上,TLS 被识别为明显的淋巴滤泡样结构和致密的细胞聚集物,但是H&E 染色无法精准评估TLS 种类且受观察者影响较大,评估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IHC和mIHC/mIF 是对TLS 的检测较为准确和特异性较高的检测手段,主要应用多种细胞的标志分子对连续的肿瘤切片进行双重或多重标记,然后利用定量数字病理学软件来评估TLS 的位置、数量、大小及成熟度等,实现定性及定量分析。一般情况下,由T 细胞(CD3+细胞)包围着致密B 细胞(CD20+细胞),并存在HEV、FDC 等细胞的区域可定义为TLS(图2)。

图2 食管癌中TLS 的表达
现有的研究使用不同的标记分子组合来识别这些结构。mIHC/mIF 检测相比于传统的IHC 检测,可同时标记更多分子且不受抗体类型的限制,节约了时间成本,但受染色过程复杂、成本较高等因素限制,此方法暂时无法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此外,考虑到基于活检或手术等取样方式检测TLS 存在异质性,更多研究尝试利用与TLS 相关的细胞/趋化因子等分泌蛋白表征TLS,解决了对TLS 的研究完全依赖于石蜡切片的局限性。如有研究利用经典的12-趋化因子(CCL2、CCL3、CCL4、CCL5、CCL8、CCL18、CCL19、CCL21、CXCL9、CXCL10、CXCL11、CXCL13),根据特定趋化因子的基因表达特征来定义TLS,如CXCL13、CCL19 和CCL21 的高表达预示着淋巴细胞的募集和淋巴新生[10-11],但是这种方法由于组织测序成本较高,又不能完整表示TLS 的成熟度及空间表达和定位,临床应用价值有限。由此可见,目前TLS 的检测方法各有利弊,未来有待开发既可全面表征TLS 信息,又具备成本低、操作简单且便于临床推广应用等优点的新方法。
3 TLS 对免疫反应的影响及预测价值
B 细胞和TLS 是免疫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免疫治疗的疗效和患者预后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治疗的过程中,应答者和非应答者之间TLS 的成分有明显的差异,提示TLS 对ICIs 反应可能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如位于TLS 内的PD-1+CD8+T 细胞的浸润情况可预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PD-1的阻断反应[14]。既往研究表明,TLS对PD-(L)1或PD-(L)1 联合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阻断等免疫治疗的影响大多是积极的,这在黑色素瘤[5]、膀胱癌[13]、肺鳞癌[15]等多个免疫治疗队列中均已被证实。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并未发现TLS对患者预后的积极影响,提示不同肿瘤组织中TLS 的作用存在差异,除受肿瘤类型、分期的影响外,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TLS 的大小、形态、成熟度、空间位置和内部组成多样性等。
3.1 不同成熟度的TLS 对免疫反应的预测作用
TLS 在肿瘤微环境中存在不同的分化阶段,分别为早期TLS、初级滤泡样TLS 及次级滤泡样TLS[16]。早期TLS(CD21-CD23-)是密集的淋巴细胞簇,含有HEV,不含FDC。初级滤泡样TLS(CD21+CD23-)含有HEV 及FDC,但不含GC。次级滤泡样TLS(CD21+CD23+)更为成熟,含有HEV、FDC 及GC。不同成熟状态的TLS 发挥作用不同。如在肺鳞癌中,只有含有GC 的次级滤泡样TLS 高表达免疫反应相关基因,若GC 形成受损,TLS 将不再有预后价值[15]。Posch等[16]评估了TLS 成熟度作为结直肠癌辅助化疗标志物的预测价值,发现与未成熟的TLS 相比,含有GC的次级滤泡样TLS 的肿瘤富含免疫原性抗原,其免疫评分更高,同时具有更优的预后结果。因此,成熟的TLS 可能预示着更强的免疫应答和更好的预后,甚至可独立于PD-L1 表达来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疗效,并且这种预测作用不受肿瘤类型的限制,即使在胰腺癌或肉瘤等对免疫检查点阻断(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ICB)治疗不敏感的肿瘤中依然适用[17]。
不同成熟度的TLS 引起免疫反应强度的不同,可能与免疫细胞的丰度、功能状态和分布有关。早期TLS 存在T 细胞和B 细胞的聚集,但不存在B 细胞滤泡和FDC,其中的幼稚或记忆B 细胞也不会进一步成熟[15]。在次级滤泡样TLS 中,CD21+FDC 可能参与向B 细胞的抗原呈递,B 细胞进一步成熟,但可能不会经历B 细胞滤泡中免疫球蛋白类别转换和亲和力成熟的过程。而在完全成熟的次级滤泡样TLS 中,CD21+CD23+FDCs 可以通过抗原呈递选择具有高亲和力BCR 的B 细胞,以及能够促进B 细胞成熟和分化的Tfh,使得B 细胞进一步成熟,分化为浆细胞[18]。因此,TLS 的成熟过程与B 细胞成熟过程相辅相成,TLS 中B 细胞的成熟度可能是影响患者免疫应答和预后的重要因素。
3.2 不同位置和密度的TLS 对免疫反应和预后的影响
TLS 在肿瘤组织内、肿瘤浸润边界和肿瘤周围组织中均有分布,位于肿瘤不同位置的TLS 对免疫反应和预后的作用也可能不同。在一项软组织肉瘤的研究中,TLS 多位于肿瘤的中心,招募更多的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促进患者对ICIs 的应答[19]。在乳腺癌中,肿瘤周围区域TLS 与较差的无病生存期相关,且密度越高患者预后越差[20]。在肝癌中,靠近肿瘤浸润性边界和肿瘤组织内部的TLS 可以促进主动免疫反应和各种免疫细胞的浸润,且TLS 密度越高,免疫反应越强,患者预后越好[21],并且瘤内的TLS 降低了术后复发的风险,提示持续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存在[22]。然而,位于肿瘤周围的肝组织中的TLS 却与晚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复发风险升高相关,这可能是由于TLS 为HCC 祖细胞提供了富含细胞因子的微生态位,HCC 祖细胞在其中茁壮成长,然后获得独立并离开生态位,最终形成了完全成熟的HCC[23]。由此可见,即便在同一瘤种中,位于肿瘤不同位置的TLS 也会影响免疫反应以及患者的预后和生存。
由于TLS 强大的免疫功能,TLS 的定位和密度可能对患者的治疗产生很大影响,而在关于TLS 对ICIs 反应预测价值的研究中,大多并无细致区分TLS的具体定位或探究TLS 定位与ICIs 反应之间的联系。因此,探究TLS 与肿瘤组织的位置关系对免疫治疗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3.3 不同内部组成的TLS 对免疫反应的预测作用
TLS 对免疫治疗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成熟度、位置及密度等,还依赖于其内部的细胞组成、功能、活性以及细胞因子的表达。在TLS 中,PD-1+CD8+T 细胞产生杀伤性细胞因子的能力降低,但却高表达趋化因子CXCL13,通过与B 细胞和Tfh 上的CXCR5 结合,促进B 细胞的激活[14]。B 细胞可能通过产生对抗肿瘤的抗体来促进抗肿瘤反应,也可能通过改变T 细胞的激活和功能以及其他机制(分泌TNF、IL-2、IL-6和IFN 等细胞因子),与TLS 的其他关键免疫成分一起发挥作用。因此CD20+B 细胞、PD-1+CD8+T 细胞和PD-1+Tfh 细胞聚集的TLS 可能预示着患者对ICIs 的反应更强。然而,TLS 中的某些成分还可以抑制ICIs 的疗效,如TLS 中的Treg 细胞和Breg 细胞可以减少T 细胞的浸润,从而削弱免疫治疗的疗效[24-25]。也有研究表明,富含Th 细胞的TLS 可能会干扰抗肿瘤免疫反应,并与晚期结直肠癌的复发有关[26]。因此,TLS 中不同的成分对于肿瘤免疫反应的影响不同,应用TLS 预测免疫疗效时需考虑TLS 独特的内部特征。
由此可见,TLS 的成熟度、密度、位置和细胞组成对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至关重要,B 细胞和TLS 的浸润情况,很大程度上能够预测患者对肿瘤的免疫反应以及ICIs 的疗效,并有助于筛选出更适合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因此,深入解析TLS 对免疫治疗的影响,对于精准预测免疫疗效和优化临床获益人群筛选策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 诱导TLS 形成的策略
TLS 是肿瘤微环境产生抗肿瘤免疫应答的核心,其可能给肿瘤患者带来更好的生存获益,加之大量的临床前动物模型结果表明,TLS 可自发或诱导形成,如Finkin 等[23]在肝癌小鼠模型的肝脏组织中先观察到TLS 样结构后发生肿瘤,TLS 形成提示肝癌的不良预后,而抑制LTβR 信号可有效阻断TLS 形成并降低肝癌发生。Fleig 等[27]发现血管内皮Notch 信号的缺失可以介导动脉去分化和高内皮细胞表型转换,可诱导小鼠肾脏、肝脏和肺组织中TLS 的形成。此外,在黑色素瘤小鼠模型及肺癌细胞系异种移植模型中均观察到具有HEV 的TLS,并且腹腔注射比皮下注射的肿瘤形成TLS 的丰度更高[1]。这些动物模型为诱导TLS 形成的可及性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因此,在免疫原性低的肿瘤中通过诱导TLS 形成增强免疫反应和免疫治疗疗效已成为关注的重点。目前诱导TLS 产生的策略主要包括:细胞因子或趋化因子诱导、肿瘤疫苗诱导、常规放化疗方案及免疫治疗诱导等。
4.1 细胞因子或趋化因子诱导
TLS 形成过程依赖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因此多项研究通过控制关键细胞因子或趋化因子的分泌诱导TLS 形成。Delvecchio 等[28]发现将CXCL13和CCL21 注射到无法自发形成TLS 的胰腺癌临床前小鼠模型的肿瘤内后,B 细胞和T 细胞会浸润到肿瘤位点组装形成TLS,甚至可观察到TLS 形成的过程,从单纯T 细胞的聚集到B 细胞、T 细胞和FDC 区域形成。Ukita 等[29]利用同样的方法,在小鼠卵巢癌模型中注射CXCL13,诱导了TLS 形成,促进了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协同抗肿瘤反应。Drayton 等[30]发现通过调控LTα1β2 的表达可以促进HEV 的形成和CCL19、CCL21 及CXCL13 的分泌,进而诱导B 细胞募集和TLS 形成。
TNF 超家族细胞因子LIGHT 是LTβR 的另一种配体,也是TLS 形成的关键分子。在非免疫源性胰腺癌RIP1-Tag5 小鼠模型中,利用LIGHT-VTP(一种具有调节肿瘤血管和诱导 TLS 形成的双重能力的化合物)靶向肿瘤血管,可以重塑肿瘤血管并促进内源性T 细胞流入诱导TLS 形成,LIGHT 还可以将大量效应和记忆T 细胞募集到肿瘤中,显著增强免疫治疗疗效[31]。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是一种内质网膜蛋白,可诱导抗肿瘤免疫应答。Chelvanambi 等[32]发现,B16-F10 黑色素瘤小鼠模型中瘤内注射低剂量的STING 激动剂ADUS100 可以使肿瘤血管正常化,改善免疫细胞募集,诱导肿瘤微环境中的局部TLS 形成,延缓肿瘤生长。
细胞/趋化因子诱导TLS 策略并非均能增强抗肿瘤免疫,这些细胞/趋化因子的数量或来源可能影响免疫应答和免疫耐受之间的平衡,并且诱导免疫抑制性细胞的募集。经基因工程改造大量分泌CCL21 的肿瘤可以吸引FOXP3+Treg 细胞和髓源抑制细胞,反而削弱抗肿瘤免疫反应[24]。在以免疫抑制微环境为特征的神经胶质瘤小鼠模型中,免疫刺激性激动剂CD40抗体(αCD40)可成功诱导LTα、LTβ 和LIGHT 的产生及肿瘤附近TLS 的形成,然而αCD40 同时诱导抑制性CD11b+Breg 细胞增加,削弱并损害对ICIs 的反应[25]。因此,通过控制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诱导TLS的方法仍需深入研究,调控免疫应答和免疫耐受之间的平衡,避免抑制性免疫细胞产生,增强抗肿瘤免疫治疗疗效。
4.2 肿瘤疫苗诱导
部分研究发现对免疫原性较差的肿瘤进行治疗性疫苗接种也可诱导TLS 形成。HPV16 阳性宫颈癌患者接种针对HPV 抗原的疫苗后可在间质形成TLS,并产生强大的组织局部免疫应答效应[33]。Lutz 等[34]发现胰腺患者接种分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的同种异体疫苗(GVAX)后,85%(33/39)的患者瘤内可形成明显的TLS 结构,这些结构与部分接受GVAX 治疗患者的生存期延长相关,为非免疫原性肿瘤免疫治疗方案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在肿瘤抗原刺激下,相关免疫细胞的活化和重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Wen 等[35]开发了一种用单宁酸装载EB 病毒核抗原1(EBNA1)和Mn2+和CpG 双佐剂组成的纳米疫苗,这种纳米疫苗可以激活LT-α 和LT-β 通路,增强肿瘤微环境中下游趋化因子CCL19/CCL21、CXCL10 和CXCL13 的表达,通过促进TLS 的形成显著增强了局部免疫反应,增加肿瘤组织中CD8+T 细胞浸润比例,延缓肿瘤生长。这是利用肿瘤疫苗诱导TLS比较成功的范例,随着新型肿瘤疫苗研究的不断发展,TLS 或许可以作为评估肿瘤疫苗有效性的预测因子,并进一步探索疫苗使用背景下免疫微环境重塑的具体机制。
4.3 化疗诱导
化疗药物可以通过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ICD)增强抗肿瘤免疫疗效,并伴随着免疫微环境的重塑[36]。有证据表明,这种免疫重建部分伴随着B 细胞聚集和TLS 形成。如Lu 等[37]在接受新辅助化疗后的乳腺癌标本中检测出更多的TLS,其中ICOSL+B 细胞显著富集并与T 细胞相互作用,引起抗肿瘤T 细胞免疫应答,显著提高患者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接受过新辅助化疗的肺癌[3]和胰腺癌患者CD8+T 细胞、HEV、CD163+巨噬细胞和Ki67+TLS 比例显著增加[9],提示更多TLS 的形成。因此,化疗诱导TLS 的形成可能是化疗后免疫疗效增强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分析化疗后TLS 出现的时间,部位和特征,前瞻性、针对性地在特定瘤种中使用化疗药物,可以有目的地诱导TLS 形成,从而达到使免疫治疗反应倍增的效果。
4.4 ICIs 疗法诱导
已有大量证据证明TLS 可以对于ICIs 的疗效产生重要影响,然而TLS 的形成与ICIs 疗效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尚不清楚[5,19]。在一项晚期尿路上皮癌的研究中,患者在肿瘤切除前接受了PD-1 和CTLA-4抗体的联合治疗,虽然基线TLS 与治疗反应之间无相关性,但治疗后所有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TLS 的丰度明显升高[13],这提示TLS 可以在ICIs 治疗期间被诱导,并有利于局部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产生。在接受新辅助ICIs 治疗的黑色素瘤队列中,应答者包含更丰富和多样化的BCR 序列以及更高的B 细胞特异性基因的表达[8]。Petitprez 等[19]通过分析肉瘤标本的基因表达数据,发现ICIs 应答者存在更多TLS,并且CD20+B细胞被幼稚T 细胞包围。新辅助抗PD-1 治疗响应的黑色素瘤肿瘤组织中TLS 富含大量反应性B 细胞,并通过改变T 细胞的激活和功能以及其他机制与TLS 的其他关键免疫成分一起发挥作用[5]。这表明TLS 可能在ICIs 治疗期间被诱导和募集,并通过激活B 和T 细胞启动新的适应性免疫反应来重启抗肿瘤免疫反应。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TLS 可以在肿瘤微环境中通过各种方法被诱导,虽然TLS 诱导的时机和方法尚无一致定论,但利用趋化因子、肿瘤疫苗、化疗和免疫治疗的方法已显示出强大的效果,在今后的肿瘤治疗策略中,TLS 的诱导极有可能成为增强肿瘤微环境免疫状态调节的新靶点。
5 结语与展望
多项研究表明肿瘤内TLS 的存在与局部较高的炎症状态及免疫浸润密切相关,可促进淋巴细胞浸润、肿瘤抗原激活和分化以增加抗肿瘤免疫应答[1,12,32]。在部分瘤种的回顾性研究中,TLS 作为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标志物的潜能甚至优于临床中常用的PD-L1[17]。而不同成熟度、密度、空间位置和内部组成的TLS 对不同癌种免疫疗效、肿瘤复发和患者生存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提高TLS 作为癌症治疗标志物的预测价值,需开发新的检测方法准确评估TLS 的各项特征。目前研究发现使用趋化因子、细胞因子、肿瘤特异性抗原、放化疗及免疫治疗等均可诱导TLS 形成,但对于不同方法诱导成功率及调控机制罕有报道。未来仍需开发新型治疗策略发挥TLS 介导免疫反应的优势,克服肿瘤免疫逃逸,从而改变ICIs 的临床效用。
目前肿瘤中TLS 与患者临床预后的相关性研究多为回顾性研究,有必要将其纳入筛选标准,在不同瘤种中开展前瞻性、大规模临床试验进行探索。综上所述,TLS 将有望成为评估免疫疗效的重要生物标志物以及癌症治疗的重要靶点,肿瘤微环境中TLS 的全面解析将为深入认识肿瘤微环境提供新思路,为肿瘤精准免疫治疗提供新方法。
本文无影响其科学性与可信度的经济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