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记忆的跨媒介传播分析
2023-08-31夏依旦居来提
□ 夏依旦·居来提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艾依提·依明
中国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1]保护和利用非遗资源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文化发展重点,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保护、抢救、利用、传承发展等多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指导方针。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各种场合反复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及其重要意义。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所难免,再加上新技术的冲击,我国非遗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文化记忆淡化,记忆主体后继乏人,艺术与传统习俗消逝等问题,个别类型的非遗文化更是处在记忆丧失的边缘,因此对于非遗资源的保护、传承变得十分迫切。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一个重要载体。长期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传播内容陈旧、传播渠道单一、传播方式互动性差等问题。在跨媒介叙事视角下,通过由“内容传播”向“品牌传播”转换、由单向传播向多媒体平台互动转换、由独立叙事向互文性叙事转换、由单纯认知向沉浸式体验转换,这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非遗文化的传播水平,对推动非遗文化创新发展,提升文化自信有重要意义。
一、非遗文化记忆的传播主体与记忆载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主体
文化记忆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记忆。在文化记忆的转移与传播中,人类毫无疑问地起着关键性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记忆通过人的语言和行为等多种形式使信息得到直接或间接的传递、接受与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传播主体:
1.相关文化保护部门
斯宾塞在谈到文化记忆时,把文化记忆视为与形塑身份认同,社会国家发展相关的过往记忆。[2]以此来看,政府部门是文化传播的最有力主体,其因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公信力与权威性,在对人和事物的串联协调以及文化记忆的传承推广上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因此,政府建立的与文化保护相关的工作部门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最佳主体,其可以科学且系统地对非遗文化记忆进行传承与构建,进一步统一非遗文化记忆,扩大非遗文化记忆的传播力度,实现非遗文化记忆的多元发展。
2.非遗传承人
非遗传承人等同于文化记忆理论中提出的专职承载者,他们对于有关非遗文化记忆的所有知识都了然于胸,且能熟练应用,因此在享有特殊权利的同时肩负着重要的义务与使命。[3]他们作为政府指定的非遗文化记忆的传承人,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着文化的传播实践,通过他们的行为和语言,文化记忆得以代代相传,他们是人们了解非遗文化的重要窗口,非遗文化记忆也在他们的演绎下得到延续和发展。
近几年来,中央与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对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细致严谨地遴选并予以公布,按照国家要求,政府对各个级别的传承人也会给予不同力度的保护和支持,包括千元到万元不等的资金支持,以及鼓励传承人积极展开传习活动。这反映了国家对于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视,也对传承人为我国文化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3.主流媒体
在当前的数字媒介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文化记忆的展现方式也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各大地方报纸、县市级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等社会主流媒体作为非遗文化记忆的权威传播主体,掌控着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肩负着向社会大众传递非遗文化记忆的责任和使命。它们需要把与非遗有关的重要活动、信息、仪式等内容,借助主题报道、文化节目、人文纪录片、创意短视频等媒介形式,形成非遗专属报道矩阵。此外,社会主流媒体还是客观及时的资讯传播方,通常掌握着第一手信息资讯,担负着引导社会舆论、影响大众对于事物的认知与态度的责任。因此,主流媒体在向大众输出文化记忆的同时,需要引导大众更加深入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社会大众对于文化的认知,扩大非遗的传播范围,提升非遗的传播力度,增强了非遗的传播效果。
4.自媒体
随着互联网媒介技术的普及和自媒体行业的发展,催生了大批的自媒体工作者,他们充分运用各种社交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景观、仪式等记忆进行传播与推广,无论是以创作为目,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自媒体都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唤醒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记忆,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推广,促进非遗的传播。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刘庭坤通过抖音展示技艺
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作为各年龄段群体聚集和活跃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随手拍”“云上传”发现和记录身边的非遗文化,普及非遗知识和保护理念,共同守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众借助自媒体对文化记忆进行传播的行为是自发的,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他们凭借自己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广泛传播非遗文化记忆,使停留在少数人脑海里和书本上的记忆渐渐走入更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并体验到这份文化瑰宝。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载体
1.文本
在扬·阿斯曼看来,即使时空日异月殊,但文字、文章、书籍等文本形式可以将事物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形态进行跨时空的连接,以此来保证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从而避免对传统记忆的丧失。[4]因此,文本也被视为非遗文化的重要记忆载体。现阶段兴起的各类非遗科普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网络媒体的文本也成了文化记忆得以保存的重要载体。
2.仪式
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一书中指出,仪式归于文化记忆的领域,某一文化的意义可以通过仪式向大众进行现代化演绎,并在演绎中得以传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记忆也正是在仪式传播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的助力下,贯穿于一代代人们的生活之中,其内涵与价值也在一次次的展演交流中得以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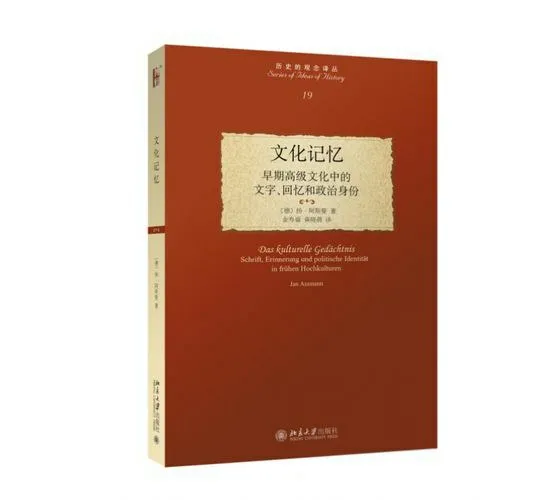
《文化记忆》扬·阿斯曼著
二、非遗传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媒介生态的演进,利用信息技术激发非遗更广泛地传播,推动非遗的创新发展,是重要的时代课题。但以跨媒介叙事的视角观之,当下非遗的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传播内容:知识性与故事性割裂
从传播内容上看,现阶段的非遗传播过程中,其知识性和故事性之间存在较大的裂缝。在詹金斯看来,跨媒介叙事改变了单一语言形式的文本呈现,更加注重文本之外的环境以及受众的作用。如今非遗的传播虽然已经开始重视不同媒介渠道在非遗保护与推广中起到的作用,但是却依然忽略了对能够吸引别人关注,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性”的构建,非遗的故事没有得到深入解读,久而久之,导致信息闭环,传者与受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互动频率难以提升,对于非遗的认同感随之下降,传播也就难上加难。
(二)传播渠道:内容文本与不同媒介的叙事性匹配程度低
非遗传播过程中,内容文本的生产与不同媒介之间的叙事性匹配程度还远远不够。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传播的重要主体,有着极为扎实的知识体系。但是由于大部分非遗传承人年龄较大,观念较守旧,受偏远地区技术普及度低等因素的限制,他们对于新兴媒体的运用还存在着较大的技术和思维盲区,导致非遗传播在表达形式上缺乏创新性和趣味性,难以吸引受众阅读和自发传播,从而使得非遗内容无法取得切实的传播效果。
(三)传播方式:偏重于独立叙事
在内容表达方面,非遗的传播更加侧重于独立叙事,以单方面的输出为主,却忽略了传受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造成了受众参与度不高的现象。非遗的传播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对一段历史故事的叙述,但目前许多地方对于非遗建立的叙事结构还存在着过于传统和封闭的问题,在内容的传播上更多地依仗“我说你听”或者“你问我答”的单向传播模式,这种没有反馈的传播方式导致了非遗的叙事文本被视作一个独立的叙事体,难以吸引受众主动接近并参与到对非遗故事的汲取、创作以及传播之中。
三、非遗传播的改进策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新”“短”“快”“活”成为大众信息消费的具体要求。在媒介技术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非遗传播系统更为优化、传播方式也更为新颖。相比于先前文本记载、口头传达,如今,借助数字科技的方式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非遗传播的单一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非遗传播的即时性、大范围性和传播主体的多样性。新媒体在时间、空间上突破了非遗传播的局限。同时,在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下,以新媒介技术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播,更能获得年轻群体的关注,对推动非遗的创新发展、传承保护,提升国民文化自信有着重要作用。在非遗文化记忆跨媒介传播中,不妨试行以下改进策略:
(一)由“内容传播”向“品牌传播”转换
“品牌传播”概念由整合营销之父美国学者唐·舒尔茨提出,他指出品牌不仅能将最优秀的价值主张传达给客户,而且还能给企业、品牌所有者和股东带来最佳经济价值。[5]品牌传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为出发点,是非遗年轻化表达的重要体现,在非遗的市场化创新和全球化宣传推广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今网红经济市场将网络的超越时空性和开放性充分运用到了品牌传播之中,使得传播主体能够更好地掌握和把持品牌的传播信息。因此,对于非遗文化的传播要在建立非遗品牌的基础上,把目光聚焦于非遗的文化底蕴,挖掘非遗蕴含的价值信息、审美意象和深层情感内涵,塑造别具一格的非遗品牌形象,借助不同传播渠道提高非遗品牌的曝光度,从而进一步提高非遗品牌形象的知名度。

“汝山明”品牌产品
如今,以非遗产品的创新设计为发力点,非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而建立起来的品牌越来越多,如成立于2017 年聚焦汝瓷的非遗品牌“汝山明”,其将传统技艺与创意设计巧妙融入服装配饰、食器酒器等产品之中,经过几年的品牌沉淀,“汝山明”现在已拥有了将近20 万的忠实用户,即使受疫情影响,整体销售额仍呈上升趋势,“汝山明”品牌的建立不仅将代表宋代审美和生活功能的汝瓷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当中,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当地非遗文化的知名度。
(二)由“单向传播”向“多媒体平台互动”转换
传统媒介的传播往往是点对点的单向传播,这种建立在“点”上的传播方式因传播渠道有限,传播内容单一、缺乏新意的原因慢慢被社会淘汰。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各类社交媒介占据了大众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大众可以通过更加畅通且多元的渠道完成对于生活中各类信息要素的接收、双向互动以及反馈。因此在非遗文化的传播中,为了切实提升其传播效果,需要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进行有机整合,利用算法机制,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分发,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介的优势。例如可以利用文化热点,在社交平台制造话题,吸引大众的参与,如抖音美食博主“江寻千(九月)”在平台发起的“糖画挑战赛”,这种借助短视频的再创作实现了对糖画这类民间手艺的传播推广,美食达人糖画挑战赛在抖音的播放量已经超过2.9 亿次,使“糖画”这种非遗文化重焕生机。
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共建、共享的特点,与国外受众进行互动,如可以借助当下流行的“xx 国人看中国”的“反应视频”形式,为国外反应视频类博主推荐非遗相关的视频片段,吸引并鼓励国外博主通过其“他者”的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读和传播,不仅可以拓宽非遗文化的传播半径,使国外观众更多维度地了解中国文化内容,同时也能使国内观众通过观看外国博主在反应视频中发出的赞叹、羡慕、惊讶等反应,提升自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三)由“独立叙事”向“互文性叙事”转换

电视剧《梦华录》——斗茶场景
非遗的传播从本质上看属于一种叙事表达,非遗在传播过程中,需要利用跨媒介传播视角,将其叙事文本中的各组成单元与多个媒介传播渠道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协调统一的叙事模式。此过程需要多种媒介的默契联动以及媒介传播内容的有机串联,正如互文性理论所阐释:由于世界以一种无限文本的形式而存在,因此世间万物都已经被文本化,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彼此之间构成互文关系,他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6]为了使非遗传播中的各类文本能够通过不同传播渠道实现多元有效互动,完成非遗传播中内容和情境的生动展现,其生成的叙事文本就需要突破独立叙事的束缚,切换为互文性叙事模式。如之前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中出现的“煮茶”场景与小红书“围炉煮茶”相关的话题笔记就形成了互文性传播,两种不同的传播形式之间的互文性加大了“围炉煮茶”的传播声势与氛围,使“围炉煮茶”成为都市人追捧的新的潮流。
(四)由“单纯认知”向“沉浸式体验”转换
跨媒介叙事平台丰富了受众认知与感受故事世界的途径,也增加了受众进入并亲身参与到故事当中的入口。传播内容得益于跨媒体的全方位传播模式随时随地进入了受众的生活中,并给受众带来无与伦比的全身心沉浸体验。因此在非遗的传播中,需要加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化,让非遗以更便捷的形式来到人们身边,从而消除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陌生感。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将AR 与VR 等技术应用于游戏、展览、音频、视频等情境中,为受众营造身临其境之感,使其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听得见”“摸得着”“带得走”“学得来”。运用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拉近非遗与人们的距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们的情感产生交融共振,进而激发传承保护的自觉性。
四、结语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在当代的传播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现状。如今,社会对于非遗的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大众对于非遗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但这并不代表着非遗传播实践取得了成功。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分非遗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瓶颈,甚至其生存和发展也处于令人担忧的状况,提升非遗的知名度和公众对非遗传播的参与度迫在眉睫。因此,需要将非遗传播提升为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行为,促使公众自觉地加入传播实践的行列之中。扩大非遗的传播范围,并确保有效传播,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