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和欲望的颜色(下)
2023-08-30陈冲
当年岀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无论是去美国还是去苏联或者是去古巴,都叫出国。除了中国人就是外国人。我们对境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出国前朋友们给我礼品,出国后可以送人,都说是外国人喜欢的。今天看来这句话有点唯我独尊,也有点愚昧。除了中国以外,好像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当时听上去很自然。对我来说,出国意味着走出现实,是一种模糊的向往。
——陈川笔记
哥哥带着太太娜莉娜和六岁的女儿萨夏,从洛杉矶驾越野车到旧金山来度假,住在我家。我一搬进这栋房子,就开始跟哥哥要画。他是个完美主义者,画得很慢,有时他忍不住反复地画一个细节而影响了全局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放弃,重新开始。一晃三年过去了,这回他终于把画给我搬来了。
一个女孩走在野地里,泥土和斑驳的草地都在暗区,是不同层次的褐色、棕色、绿色,黄昏最后的日光勾勒出她的侧影,浅色的长裙在光里隐约透出一点腿的形状。陈川捕捉光线,好像那是流淌的阳光,或者玻璃瓶中的萤火虫。女孩在画的上方,没有地平线和天空。她是刚从什么特别的情景离开?还是正向着它奔赴?她的步伐显然不是在散步。
画中的女孩让我心中隐痛,我想到三千英里以外的两个女儿,她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对我也是如此神秘……
我们在厨房的小桌旁坐下喝茶,哥哥突然说,侬晓得?赵以夫死了。我们感叹。
赵以夫是哥哥在上海美术学校的同学,后来在加州湾区住过。我在旧金山结婚搬进新家后,他帮我从画册里临摹了一张巴比松派的风景——好像是多比尼的湖水、树林和黄昏的云彩——仿佛为我搬来一段祖屋的记忆。他们那班人曾经迷恋巴比松派的画家和他们的作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柯罗、米勒、巴斯蒂昂·勒帕热的画跟卡夫卡的《变形记》同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文革”后上海的第一个西方艺术展览,是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品都是法国卢浮宫与奥赛博物馆的名作,展馆内外如饥似渴的人群浪潮一般。印象中哥哥在那段时间处于亢奋状态,家里墙上也不断出现各种巴比松派画家的照片。
哥哥说,赵以夫老早每天骑车从虹口到平江路来跟我一道画图。我想起来了,他的好多画画朋友都是家里的常客。小保姆莲芬总是用一口溧阳话进门通报:小头来哉,长脚来哉——全是用平常他称呼他们的外号。
好久没有想到莲芬了,她曾经为我们家带来不少活力。初到我家时她大概只有十五六岁,面黄肌瘦,扎了两条又细又黄的小辫子,眼睛盯牢了脚前的地板。她娘跟姥姥家在溧阳好像有什么远亲关系,把她带到了上海。她娘几次三番说,莲芬开年就十七岁了,会烧饭、洗衣服,还会做针线活,很能干的。我至今记得她系着围裙,捏一块抹布发愣的样子。姥姥说她家欠了不少债,所以要她出来挣钱,叫我领她去认菜场、米店、酱油店。
大声喊着“小头来哉,长脚来哉”的莲芬,已经是个结实苗条、满面春风的大姑娘了。她爱一切新潮时髦的东西,穿皮夹克、喇叭裤,走进走出一阵风,只有一口顽固的乡音未变。
扁豆、蚕豆,电线木杆长杠豆
阿姐来梳头,梳个芋艿头
嫁给大块头,养个小毛头
宝宝跑到田横头,一跤跌个大跟头……
不知道这是她娘教她的,还是后来姥姥教她的,也忘了她在什么情形下会唱这条顺口溜,但她一定多次唱过,不然我和哥哥怎么会如此朗朗上口。
萨夏问,你们在讲什么?我说,我们以前在中国的事情。她说,老师说我是黄种人,现在有同等权益,以前没有。她似乎对这事有些困惑。学校为什么在他们还毫无种族概念的时候,强硬地教他们种族政治?不能让他们在懵懂的童真中再待一会儿吗?我没有接她的话,说,你爸爸来美国的时候,带了一个巨大的木箱,里面装满了他的油畫、画册和书籍。她问,有多大?我说,里面可以舒舒服服装下你。她问陈川,那么大的箱子你怎么带?可是他却怎么也记不起来,离开上海那天是怎么去的机场。那只又重又大的木箱,既上不去公共汽车,也上不去脚踏车,唯一的可能性是从哪里借了“黄鱼车”骑过去的。陈川画了一张“黄鱼车”的样子给萨夏看。他说,到达美国后,木箱从超大行李出口出来,我实在搬不动,是海关人员帮着一起搬的,放到今天这是不可能的事。
前一阵搬家,发现一盒在我出国那天姥姥给我的画笔。都快四十年了,打开笔盒,还能闻到上海油画笔特有的胶水香味。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想到姥姥了。我的心跳加快。并不是因为那盒笔唤起了我的回忆,而是因为发现自己走到了记忆的边缘而变得警觉起来。当年那漫长的、无所事事的年月,已经被我小心翼翼地埋藏起来。岁月年复一年地盖在上面,即使苦苦思索,也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我拿那盒笔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出国,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在我眼前缠绕的却只是一些琐碎的细节。记得我和姥姥在家门口。那扇门原来是家里的边门。“文革”时客厅里搬进了另外一家人,通往客厅的正门就变成了人家的门了。日子久了,虽然“文革”时期搬进来的人家已经走了,但我们已经用惯了边门,它就成了平时我们进出的门了。那门是猪血色的,中间镶嵌了一条很窄的玻璃,玻璃外有一个铁框,铁框里有一排字图案。进门后有一个“宽敞”的过道。门关着的时候过道总是黑洞洞的。记得出国那天天气非常好。一开门,阳光亮得刺眼。姥姥那只被关节炎折磨得畸形的手,捧着那盒画笔。家门口阴沟的墙缝里有一棵蒲公英,长得又肥又壮充满了生命力。我跟姥姥说:再会了。她一面说一面把那盒笔塞进了我的手提包里:“不会再会了。”我看着地上又说了一遍“再会了”。
——陈川笔记
陈川在一本画册中这样回忆过他初到美国的感受:
一九八五年第一次到纽约时,我还年轻,也很穷。我母亲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她希望我也能来美国,就把挣到的几乎每分钱都存了起来,回国前交给了一位老太太保管。我到纽约后去拜访了老人,取回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大约一千五百美元。
我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国家赚钱,觉得不花钱便是最好的办法。我每天步行一百多条路口,到大都会博物馆。街上,每个人都那么匆忙,在地铁通气口冒出的白色蒸汽中进进出出,让我想起牛群在非洲丛林中奔跑。是的,纽约是个丛林。
每天我都在博物馆对面的斯坦霍普酒店的餐厅吃午餐。我先点菜,然后观察街上路过的行人。我特别喜欢那里的意大利烟熏鸭肉,一片片切得那么薄,就像画在盘子上的一样……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餐馆。
那些日子,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家。它让我感到一种亲和力,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在母亲艺术的保护下。
傍晚,我走过中央公园。就像我想象中的中央公园那样,昏暗的路灯下空荡荡的长椅,路灯后面是漆黑的树林,一轮月亮挂在树梢上空。我想起在上海读过的一本书,《珍妮的肖像》。一位食不果腹的年轻艺术家,在中央公园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孩,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我坐在长椅上,希望珍妮能出现。背景的树木漆黑而深邃,像一片无底的湖水,其中的生命依旧是个谜。一阵晚风带来花香。树叶在地上旋舞,仿佛她的幽灵从我身旁经过,让我脊背发凉。一辆马车经过,车厢里坐着一对年轻夫妇,也许是在度蜜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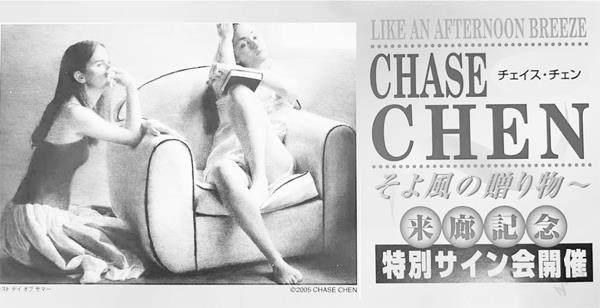
那天晚上我睡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张长椅上。我是被一家面包店的香味熏醒的。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面包师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一天。微开着的门透出温暖的光芒,仿佛一个巨人试图睁开他的眼睛,城市正在苏醒。街角处,有人在吹萨克斯,乐声随着面包店的炊烟袅袅升起,在天边萦绕。这有点悲伤,但非常美丽。
我为朋友们画了些素描。我没有画油画,因为这需要工作室和颜料。母亲留给我的钱几乎花光了。有几次我去了一家艺术材料商店,仔细看了每一件物品。对于一个刚从中国来的人来说,种类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我触摸和闻过那里几乎每一种颜料和画纸。这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一无所有,因此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城市里,我的生活如此简单。所有的梦想和幻想都还完好无损。所有的可能性都敞开着……(注:以上文字由笔者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卖掉了几张大木箱里的油画以后,陈川买了画布和颜料,开始创作。到美国的第二年,他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办了他第一个画展。那以后,他在美国许多重要画廊办了个人画展,也成功地参加了佳士得拍卖、纽约艺术博览会、艺术亚洲等展会。
然而对他来说,绘画依旧,理想依旧。一位记者问他,到美国后画画有什么变化。他说,我通常画我周围的东西。在中国的时候,我画家里的厨房,我的邻居、朋友,来了美国我就画这里的邻居、朋友——就这点变化。
陈川和我在月桂树峡谷的房子里同住了一阵。我们一起装修,把蓝色和绿色的瓷砖混贴在浴室;我们一起做家具,早上一醒来就迷迷瞪瞪用砂皮纸磨木头,眉毛、睫毛、鼻毛上都是白粉。
一天,陈川看见邻居家的女孩在后院里玩耍,觉得她有一种乡村姑娘的淳朴,就以她为模特,画了《篱笆边的女孩》和《后院的女孩》,非常动人。同阶段,他还在房子里画了《椅子上的雏菊》《加州的小木屋》等作品。忘了是哪位作家说的,艺术家必是诗人,他不一定写诗,但是他眼睛里能看到诗。哥哥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诗,看到那些小小的奇迹。
陈川第一个真正的缪斯是一位前苏联来的女孩,叫娜伊拉,二十出头,刚从拉脱维亚艺术学校毕业不久。一连几年,陈川画了几十张以娜伊拉为主题的画。在一次采访中,他对记者说,“遇见她时我们都刚来美国,远离了各自的家乡,彼此有着无需言说的经历和感受……我爱画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她反映了我。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成长起来,人们崇拜苦难、崇拜悲剧英雄。生活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乐。即使在阳光明媚的、享樂主义的加州文化中,我们创作的驱动力仍然是生活中的悲情。在这里住了十年后,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
另一个反复出现在陈川画中的,是泰迪一家的生活——他的太太、女儿、农场、狗、马——他们有滋有味的日子。泰迪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朋友,后来跟我失去了联系。陈川说,他跟老婆离婚后,女儿就再也不理他了,不过最近他又当新爸爸了。我想起那幅泰迪女儿坐在他大腿上看电视的画,那么本真,像森林里的动物。陈川说,物是人非,那张画还挂在日本仙台的一个人家里。
几年前,有一次 Narina 给我发了个短信:Never hesitate to trade your cow with a handful of magic beans. 她对我的了解使我暗暗吃惊。我就是童话 Jack and the Beanstalk 中的那个傻儿子。
岀国前我的美国是作家杰克·伦敦。出国前看过一个美国来的画展,好像是在美术馆。主要是Winslow Homer 和 Rockwell Kent 的作品。还有一两幅 William Michael Harnett 的静物。
我出国前妈妈在纽约的 Sloane Catherine 工作。她的助手叫 Steven,他在我出国前来上海第一医学院合作工作。Steven 的妻子 Michelle 当时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她喜欢艺术,问我讨了一张静物。她说我的画使她想起 Andrew Wyeth 的作品。他们是朋友。第二次回上海时她给我带了一本 Andrew Wyeth 的画册,里面还有他的签名。她说她拿了我的画和一些我的画的照片去看他。她说 Wyeth 喜欢我的画。我怀疑这话是否真实。因为我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不满意。
出国前在美国领事馆看过一个牛仔片叫 Shane。
——陈川笔记
从九十年代开始,陈川几乎每年去仙台一家高档百货公司办画展。一个傍晚,他从展厅出来,走进一条小巷,看到一间很小的卡拉OK酒吧,里面有人在吃饭、喝酒、唱歌,就挤进去坐了下来。妈妈桑到隔壁小店买回食材来做给他吃,等他吃完,外面那一桌喝醉了,把他堵在店里没法离开,一直待到深更半夜。
第二天,妈妈桑带着那群唱歌的人去了展厅,看了画以后十分喜欢,就每人买了一幅,有的是素描,有的是油画,还有的是丝网画或铜版画。他们不是富人,但是在商场买画可以分期付款,这样普通老百姓家里也可以挂上艺术品。妈妈桑的小店从此成了陈川在日本的食堂,他说她做的菜味道特别好。
后来妈妈桑每年都会带着这群人去看画展,还清了一笔贷款就再买一张。其中一个护士,每年买一张陈川的画,欠的贷款越来越多,还不过来,终于上了黑名单,只许看不许买了。另一个人,搬家去了其他城市,但画展时必会坐火车来看画、买画。
百货公司对面有一家很时尚的咖啡厅,那里的老板也很爱陈川的画,每年买一幅,家里和店里都挂满了。陈川去喝咖啡他从来不肯收钱。
在美国买他画的大多数也不是特别富有的人,而是像医生、律师那样的专业人士,或者导演、演员、音乐家、画家那样的艺术界人士。他们买画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喜欢。
当下的时代,商业对艺术的影响和控制日益加剧,画经常被当成股票那样来投资。人们往往用人为的金钱价值——而不是它内含的精神价值、情感价值——来衡量作品与其创作者的成败。看完一个画展他们会说:很成功啊,画都卖掉了。很少有人会提到,哪一幅画、哪个细节、哪片色彩使他感动、欣喜或忧伤;很少有人会在意那些更神秘的、无法言喻的东西——也就是艺术本身……我不是说不再有真诚的信仰者,这是世道而已。
现在陈川回上海看望父亲的时候,仍然会跟夏葆元、魏景山——那些当年在孟老师家里的人一道画人物素描。画室里的模特大多是热爱艺术的妇女,她们在摆Pose的时候谈论艺术,休息的时候帮画家们做做飯、搞搞卫生。
那里有一个被“所有画家”反复画过的女人,是个狂热的艺术(家)追随者。按她的观点,没有画过她的根本不算画家。认识了陈川的第二天,她跟他说,我在网上看了你画的油画,让我想起威廉·哈姆绍伊的作品,那种宁静的感觉,那种柔和的光线。他听了有些惊讶,这位一百多年前的丹麦画家并不那么出名,但正是自己很喜欢的画家之一,看来此人的确不是个一般的模特。不过陈川更爱画的不是模特,而是作画状态中的朋友。他们老了,但在哥哥思绪的目光中,想必还叠印着他们早已逝去了的青春。
那一代画家,大多脸皮很薄,或者不是脸皮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审美,不允许他们参与到当代的厚颜无耻和自我吹捧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被时代淘汰。
但那些贷款买陈川画的人,一定从作品中看到了什么,使他们欲罢不能。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多年前的观后语,也许可以替他们描述出那种不可名状的感受。
“陈川画中宁静的空,是某处响着蜂鸣、某处萦绕着歌声、某处有渐渐沉去的钟声那种空。”这让朋友联想到伍尔芙《到灯塔去》中那种人去楼空的微微心痛。“陈川那深绿的、灰色的空也留下了极浓的怀旧情感,怀旧是那个抛掷白丝巾的女孩:什么失落了?什么一去不复返了?怀旧成了那束弃于农庄的玫瑰,还带着露水,带着刺鼻的新鲜气味,却是无以寄托,无以施予;还有那个拧身而卧的少女,恬睡了,也那样任性,许久前一个秘密的遗憾,只有梦能够给她重来一次的机会。画中的一块空间留下了人的感情和动作,那是人的空缺,而不是灵魂的空缺。人的灵性充斥在这空间里……这样又甜又苦的情致、景致怎么如此似曾相识?
“它们是被怎样的眼睛看进去,被怎样的心灵滤过,又被怎样的手和笔表达了?生活原来是可以这样被汲来,这样美妙地被重新配置和处理……每个艺术家都希望通过自身来注解生活……陈川以他的画笔和色彩注解一种偶然:光和影、气温和体温、风和呼吸、梦和现实,突然融汇在一个点上,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也再不会出现的点上。陈川捉住了它:一个欢乐和伤感的和弦,一个绝妙的情景交叠而发生的瞬间休克……”
朋友后来把她有感而发的文字,发表在了一本散文集里。我好几年以后才知道,陈川自己从未看到过。
我再次想到那条童年的“猫鱼”,它仿佛从未失去过它的魔力。陈川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在冥冥之中诉说那份永恒的怀旧与渴望。
萨夏打开手机,给我看她的狗和四只母鸡,她说,鸡棚还是不够结实,黄鼠狼又来把鸡吃掉了。我说,哎呀,那太糟糕了。她说,我们会再去买小鸡回来养,这回爸爸会用很粗的木头做一个鸡屋。我问,这些照片是你自己拍的吗?她说,是啊。说着就举起手机冲我按了一张。她说,我用“人像模式”拍,你就更好看。哥哥在一旁感叹照相技术的发展,就连不会说话的小孩都会拍照了。以前他无论去哪里都背着个很大的相机包,现在这个习惯也渐渐消失了。
陈川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收藏古董摄影器材,几十年来买了三百多个相机,一千多个镜头。世界上仅剩三十几台的沙克梯16(Cirkut16)相机,他拥有两台,其中一台是一九〇五年首批制造的——贴皮的外箱,桃花芯木的机身、精致的镜头,完美的齿轮——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沙克梯是三百六十度可变焦全景照相机,十六代表底片的宽度为十六英寸,长度可达六米,一张底片的面积可达二点七六平方米。哥哥家的车库基本上不是用来泊车,而用来泊相机和镜头的。
这个庞大的收藏始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陈川开始制作凹版印刷时需要相机,正好有个朋友的朋友急需用钱,就把一套七十年代的仙娜摄影器材卖给了他。之后,陈川在摄影杂志上看到了仙娜配套镜头的广告,去买了回来尝试。不同镜头产生的不同视觉效果,引起了他对光学的好奇。为了理解其中的奥妙,他去书店买了几本鲁道·京斯莱克关于镜头的书籍,学习镜头设计的历史和原理。从一个镜片、两个镜片的镜头,到六七个镜片的镜头,能拆的他都拆来看。
许多人搜集相机和镜头是看品牌,陈川更看重的是结构和设计。有一些在历史上“失败”了的产品,有它们十分独特的优点,但是它们的结构太怪太难造了,因无法推广而被淘汰。就像任何生命或文化一样,存活和广泛流传,看的是物种或现象的繁殖能力和传播能力,而并非它是否“最优秀”。今天这类镜头变得越来越稀罕了。
陈川对创造影像的兴趣,从机械延伸到化学。有几次我去他家时,屋里弥漫着各种化学药水的气味,到处都是翻开的杂志、书籍和各种容器、试管,他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那样,把厨房、饭厅和客厅都变成了实验室,制作干点蚀刻铜板画。
我问他,那时候你在搞什么东西?他说,我需要把酸从氯化铁中提取出来。传统报纸印刷用大量氯化铁,报纸改用胶印技术后,许多化学品工厂处理不掉他们的氯化铁,又不能随便倒掉破坏环境。我打电话给一个家厂,请他们给我寄一点样品,过了几天收到了老大一桶,根本用不光。网络兴起前学东西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全靠自己试,还好妈妈来看我,就帮我一道把酸提出来了。

我想象母亲跟哥哥做出第一张铜版画的样子——她喜悦和腼腆的笑容——深深的思念涌上心头。母亲离开一年多了,我仍然无法平静地回忆她或讲述她,也许永远都不会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号岀国的。虹桥路边,春天的田野里覆盖了一片新绿。砖红色的洋房在树林中时隐时现。田园风光像安徒生童话,带有一丝忧愁。我的心仿佛风筝一样,在天上毫无目标地荡漾。路边的树在我耳边有节奏地呼呼闪过,那韵律把我推向远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开始担心起姥姥,后悔自己只说了声再会就离开了,但思索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字。我和姥姥的关系就是这样。我和很多亲人的关系都是这样,也可能我们当年的上海人都是这样的。那些表達感情的话到嘴边就消失了。
多年后我第一次回国,姥姥已经去世了。吴芝麟请我在淮海路上的“夜上海”吃饭。吴芝麟在我出国后常去看姥姥,他说姥姥最想的就是我。我知道她会想我的,但心里还是一酸。
——陈川笔记
家里墙上挂着几张陈川最初的凹版印刷和干点蚀刻,随着经验的积累他的铜版画越做越纯熟了,但是这些“实验作品”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迹,对我来说更意味深长。
“实验作品”中有一张是我嫂子娜莉娜,她跟哥哥画过多次的娜伊拉一样,也成长于前苏联。娜莉娜是一名卡通艺术家,获得过两次艾美奖,她目前最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绘画能力。
我们围着电脑,在网上看MidJourney和Dall-E 2人工智能创造的图像。半个世纪前,我和哥哥曾怀着同样的好奇心,围着一本苏联画册。那时我们对世界和未来的向往多么单纯,如今面对势不可挡的未来,我们的期待中不免夹杂着不安。
这些AI作品不是画出来的,而是用文字“写”出来的。陈川在一本画册中曾经这么写过,“房间一点点暗下来,影子在每个角落伸长,我企图留住那最后一线阳光。这是我的艺术灵感。画出这种感觉,远比用任何其他方式谈论它更有可能性。绘画萌生于语言哑然之处。”AI的“绘画”萌生于语言,而不是它的哑然。对于视觉艺术来说,这是巨大的颠覆。
我觉得有趣的是,目前AI艺术做得最吸引人、最成功的,并不是二三十岁的人,而是四五十岁的人。我想象,那是因为他们已对想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深思熟虑,也已尝试过了其他途径。
我比较喜欢的AI作品,是电影导演贝尼特·米勒的“黑白摄影”,他用模糊的图像,描绘一个遥远时代的风景和儿童,仿佛他在脑后黑暗的虚无中看到了那些影子,那些似是而非的“记忆”。一个叫Jonas Peterson的婚纱摄影师做的“肖像”,也很有意思。画面里,很老的男人女人,穿着崭新有型的衣服,站在不同形状的“远洋轮的舷窗”前,复古而又时尚。舷窗给人时光机的感觉,乍一看像是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但细看全是幻想。
其实任何对未来的幻想,都是一种怀旧。人类似乎在一条混乱的单向道上茫然狂奔,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喘息间我们蓦然回首,瞥见一眼远古和永恒,唤起莫名的惆怅与渴望。
人工智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取代艺术家吗?到那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没人知道。但我们都看得见,人的绘画能力,连同他的心算能力、辨别方向能力等等都在退化。那么,未来的人站在那些辉煌的艺术殿堂,应该比我们更为惊叹吧?心灵和意识是人类智能最后的疆域,那块神秘之地也是艺术的起源和归属。我用Lensa软件做了一张“凡·高画的”我,任何人看了那个平庸的东西都会说,哇!这像凡·高画的肖像。人工智能对艺术家最大的威胁不是取代,而是抄袭和庸俗化。
什么是艺术?站在凡·高的《柏树》或者《星空》前时,我们也看到割掉了左耳的他,关在精神病院的病房里,望着窗外的柏树、星空,在痛苦中感受到一种美丽与狂喜;看到他在贫困、病痛、怀疑和讥笑面前的挣扎及信念;看到他对爱、知音和自我完善的思考及憧憬……其实,真正打动我们的是人类的局限性和超越极限的勇气、人类的肉体欲望和它的精神升华。人工智能以它无限的潜力,不具备人的局限和脆弱。伟大的艺术能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敬畏感,而敬畏感并不仅存在于结果中,也在我们绝望、鲁莽地超越自身的企图中。无限的潜能里怎么可能有这般超越与升华的华彩?
也许会有一日,在人类经历了濒临灭绝的巨大灾变后,又会从残存的文明中得到某种复兴;那时自然环境已经变得对人的生存不那么友好,人在山洞中想起传说中曾经茂盛和多彩的万物,像几万年前一样,在岩壁上用手画出心中的涌动。
新闻里传来坂本龙一先生去世的消息,虽然知道他生病已经很长时间,仍然感到震惊。
我恍惚看见,夜晚,他拿着一只很小的相机,我们去了什么已经关闭了的地方,不知是在北影还是故宫,我穿了件蓝色牛仔夹克趴在一扇门上,他拍下了那张相片。谁能告诉我,记忆的追光为什么照在了这么一个偶然无序的画面?
两年后的奥斯卡晚会上,《末代皇帝》的音乐响起了九次,坂本龙一也上台拿了最佳原创音乐奖。那晚庆典我们一定见了面吧,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几个月后,他来洛杉矶Wiltern剧院演出,邀请我去参加,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黄色魔力交响乐”时期的音乐。结束后,他送我走到我的车子前,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我在车里向他挥了挥手,他站在路灯下的身影,与Wiltern剧院那栋蓝色的艺术装饰建筑,在后镜中远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接着的几十年我们失去了联系,偶尔,我会在听到他的音乐时想起他。我依稀记得,第一次听到Async时的震撼和感动,那是使人联想到生与死的声音。二〇一九年许知远来旧金山采访我,他说接着要去纽约采访坂本龙一,我说那请你代我问候他。
二〇二〇年我在北京筹备《世间有她》时,许知远给了我坂本龙一的邮件地址,我写了封信请他为电影作曲。很快,我接到了他回信——都是小写字母。
亲爱的joan,
几个世纪都过去啦!你好吗?我相信你会保持安全和健康的。谢谢你邀请我为你的新电影作曲,非常遗憾我的时间已经排到二〇二一年底了。真的很抱歉这次不能帮你。如果未来再有机会的话,请在需要音乐前的一年就联系我。
另外,我想告诉你,二〇二一年春季我将在北京搞一个大型艺术装置展览,希望我们能相见!
最温暖的祝福
坂本龙一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坂本龙一的“观音听时”展览在北京开幕,母亲患癌症正在上海住院,我又即将奔赴重庆拍摄《忠犬八公》,就错过了。六月的时候,我接到木木美术馆的来信,跟我说,坂本龙一想把他珍藏的一张他与我在《末代皇帝》现场的合影用在画册中,希望得到我的许可。
二〇二一年十月,我从美国回上海看望母亲,在隔离酒店收到了坂本龙一的画册。看完后我给他发了邮件。
亲爱的Ryuichi,
你好吗?
我终于又回到国内,可惜没有赶上你的展览。在隔离期间我反复看了《观音听时》的画册,让我在单调狭隘的四壁中,有了宽广和奇妙的想象空间。
我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陈冲
母亲走后的第二天,我在悲痛中接到坂本龙一的邮件,很短。他感謝我给他写信,希望我一切好,最后祝福我有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新年”。这几个字的真诚让我感触——他没有写“快乐的新年”——那时他在与病魔痛苦地斗争。
那以后我们没有联系。rskmt@kab.com不再会有收件人。
进入四月后北加州的日照长了,八点多钟天才黑下来。我走出家门,耳机里放着坂本龙一为《呼啸山庄》电影谱写的主题曲。下了几天狂风暴雨后澄澈的夜空,像童话一般——我没有词汇可以形容这样的深蓝。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这样写过蓝色:一种情绪的颜色、孤独和欲望的颜色,是从此岸望到的彼岸,是你不在了的地方……
你不在了的地方——最深的蓝色——在一本叫《维尔纳的颜色命名法》(Werners Nomenclature of Colours)的书中,它被命名为“苏格兰蓝色”——就是柏林蓝混合了相当一部分的丝绒黑,极少的灰色,还有淡淡的胭脂红。
你能想象吗?在这样的天上布满了星星是什么景象?我只能无声地见证它的奇异,这不就是我生命的意义吗——来见证。家的屋顶上空就是以希腊神话中的Orion命名的猎户星座,它的腰带由三颗明亮的恒星组成,剑在腰带的南面,沿着它的腰带往东看就是夜空中最明亮的一颗星——天狼星……
过去、现在、未来都聚在这片苍穹下——从时间的开始直至永远——守着“猫鱼”的哥哥、画肖像的哥哥、艾斯利和麝鼠、赵以夫和多比尼、坂本龙一、卡夫卡、泰戈尔和所有的诗人、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坟墓……一切转瞬即逝,一切无限。
现有的科学告诉我们,生命是宇宙中无足轻重的一个副产品,它对宇宙来说没有必要。但生命便是我们的一切。哥哥和我都六十多岁了,说出来我都吓一跳,人生的冬季仿佛在某个清晨突然就降临了,令我措手不及。仔细想想,还是有预兆的:失眠更厉害了,到嘴边的人名卡在那儿出不来了,穿高跟鞋走不了路了,阅读比以前慢了,最糟糕的是,有时我觉得创作的源泉好像被封藏在什么无法挖掘的深处……
然而,同代人的死亡提醒了我,老去的确是莫大的幸运,年岁的确是可以炫耀的东西。它好比大树漂亮的年轮,一圈一圈写下了所有的斗争、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幸福和繁荣,那些贫瘠的岁月和丰腴的岁月,那些经受了的袭击和熬过了的风暴。
坂本龙一的音乐进入了高潮,令我的眼睛湿润。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失去对艺术的虔诚,没有停止对新生事物的探索与拥抱——新的声音、新的思想、新的感知。他燃尽了,但从未衰老。
仰望浩瀚星空,我感到我还有那么多想知道的事情——从细胞的奥秘到灵魂的奥秘;我还有那么多的渴望和爱——无论用胶尺的尺度还是星系的尺度都无法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