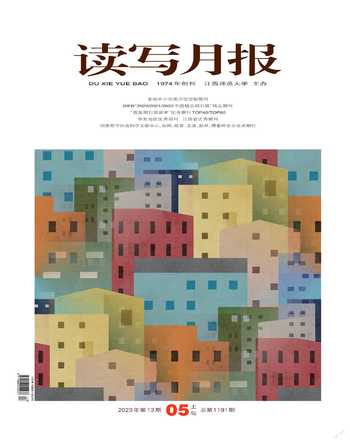《百合花》中的“被子”意象解读
2023-08-28齐金颖
齐金颖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经典短篇小说名作,也是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冊第一单元中的必讲篇目。小说依托战争题材,歌颂了主人公百合花般纯洁高雅的人性、人情和心灵。小说虽然以《百合花》为题,却没有把花作为主要物象融入文本,而是让撒满百合花的“被子”成为文中重要的线索和元素。“被子”在文中以不同的形态多次出现,即棉絮、被子和百合花被,寄托着一定的价值与情感。那么“被子”在文中到底有何寓意?这个道具、这个特定的“符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内涵和文化意蕴?它的出现对于读者解读文本有何作用?本文拟通过鉴赏文本具体的语言和细节,解读“被子”这个物象,带领大家感受特殊时期人与人之间的无限温情。
一、边缘词“棉絮”——象征社会环境的艰辛
何为“棉絮”?“棉”是一个会意字,从木,从帛。一说是种植物的名字,即木棉。《吴录》云:其实如酒杯,中有绵如蚕绵,可作布;二说棉花纤维。此处取棉花纤维之意。“絮”是一个形声字,从“糸”,如声。一说粗丝绵,《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絮,敝绵也;二说经过弹制的棉花胎。此处取“经过弹制的棉花胎”之意。综上所述,“棉絮”是指棉花纤维经过弹制做成的棉花胎或是指采用棉花纤维做的被芯,是没有被单装饰的简易品。换句话说,“棉絮”属于“被子”的初始阶段,是勉强替代被子盖在身上御寒的物品。“棉絮”这个意象第一次出现在小通讯员与“我”初到包扎所时的情景中,由于“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哪怕”一词表示姑且承认某种事实,相当于“就算”“即便”之类的词,“哪怕……也好”情感色彩浓郁,期待中带着些许无奈。可即使是借棉絮,小通讯员与“我”在短时间内也只是借到了两条,这与预期中的“一二十条棉絮”在数量上相差甚远,可见战争年代物资的匮乏,当时社会环境的艰辛。作家茹志鹃借“棉絮”再现了1946年解放战争最艰难时期百姓生活的真实状态,即使是半成品的“棉絮”都成了百姓生活中的奢侈品。这更加凸显了此时老百姓手中的“棉絮”是温暖流血伤员身体的“保命伞”,凸显了“棉絮”的重要性。
二、过渡词“被子”——象征百姓革命思想的觉醒
从表层意义看,“被子”是完整形态下的“棉絮”,是经过加工之后的“完美用品”,其成本和价值要高于“棉絮”。从物品本身看,“被子”贴身而盖,属于亲密性物品,人们一般不愿外借,不愿随意被他人使用。从这两点看,文中的小通讯员和“我”想要借到“被子”,可谓难上加难。可即使这样,还是有“被子”存在的。文中是这样写的:“不一会儿,我已经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首先,这里的“不一会儿”从语义的角度解释为时间短,速度快,从该词可以看出老百姓的真诚无私,即使是那个年代较为珍贵的稀缺物品,他们也毫不吝啬,可见老百姓的思想觉悟高,军民鱼水情深。其次,1946年,百姓的物质生活极度贫乏,大多数家庭可谓一贫如洗,连一条干净像样的棉絮都可能无法拥有,更别提“被子”了。可即使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境下,老百姓却能慷慨奉献出自己仅有的“被子”以支援部队。可见这时的“被子”已经不单单是能御寒保暖的日用品,而已升华为精神层面的象征物,是一种精神符号,象征着百姓革命思想的觉醒,是军民上下一心的外化表现,更是军民联结的重要纽带。
茹志鹃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一个小意象,也可以写出大韵味。《百合花》中“借被子”事件让我想起发生在1934年的经典红色故事《半条被子》:3位女共产党员借宿于百姓家中,夜晚盖的只有一条破棉絮和一条红军的被子。第二天临行前,3位共产党员把随身携带的被子一分为二,将其中一半给了老百姓。我想那是一段艰苦的奋斗历程,但风雨同舟的鱼水深情却格外令人难忘。正如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写道: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三、升华词“百合花被”——象征人性纯洁美好的心灵
在众多的被子中,新媳妇的“百合花被”无疑是最具深意的物象,在小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百合花”的花语是百年好合,它是美好爱情的象征,这就使得这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充满了浪漫气息,因而这床“百合花被”一出场,就带有浪漫色彩。“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里外全新”说明被子一次没盖过,没使用过;“假洋缎”说明被面的材质好,价格相较于普通材质的被面要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被子显得尤为珍贵。“枣红底”说明颜色鲜艳,且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喜庆,一般用于结婚和寿宴上。这样一条喜庆且珍贵的被子,其主人是一位刚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这条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唯一”一词,更加凸显了这条被子对新媳妇的重要性。它不仅是陪嫁品,更是新媳妇美好爱情的见证。“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儿,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读到这里,读者会明白,为何开始时新媳妇会拒绝借被子,不仅因为它珍贵,更因为它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新媳妇最宝贵的东西,因而不外借在情理之中。本以为借被子一事到此结束,但没想到新媳妇听到“我”说借被子是为了部队,为了老百姓时,她犹豫思索片刻,将被子抱了出来。这一令人意外的举动,意味着新媳妇将自己的全部家当奉献给了革命。此时,新媳妇的传统观念开始发生转变,革命思想觉悟开始苏醒,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新媳妇在包扎所帮忙时,将自己的“百合花被”铺在了包扎所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供伤员使用。这是一床新的漂亮的被子,却被放在了外面,且是一块上面没有铺任何防脏物品的门板上,从中可以看出新媳妇心灵的纯洁、无私和善良。也正是这一动作,预示着“百合花被”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写,推动其最终的走向是“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一半铺在了棺材底部,一半“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此时这床花被不再是新媳妇的嫁妆,而是烈士的殉葬品和勋章,它的“毁灭”是对烈士的尊重,对死亡的尊重。由此,“百合花被”神圣的地位得以确立,新媳妇的精神境界得以获得超脱。《圣经》中记载,百合花由夏娃的眼泪变化而成,被人们视为纯洁的礼物,因此世人认为百合花象征纯洁和高雅。献出“百合花被”凸显了新媳妇的人性美和心灵美,也更加凸显了军民之间的情感如同百合花一样纯洁、高尚、美好。
从“棉絮”到“被子”再到“百合花被”,变化的是被子的形态,不变的是特殊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的无限温情。上海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曾经这样评价这篇小说:“茹志鹃似乎并不在意战场中敌我双方的进退胜败,而专注于战场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和交流。”无论是具有保暖功效的被子、作为嫁妆和爱情见证的喜被,还是承载烈士功勋的荣誉之被,都彰显着“战争无情人有情”,正如毛泽东《采桑子·重阳》所写:“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那散发着迷人香气的不仅只有战地菊花,还有那象征纯洁与感情的战地百合花被。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第一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