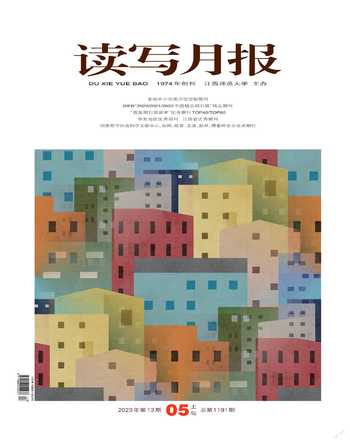漫长的一天
2023-08-28钟培旭
钟培旭
《百合花》故事动人,牵动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这篇小说以“我”(一位文工团女兵)的视角展开,写了“我”被小通讯员带到包扎所,后来一起去向老百姓借被子,遇到一个刚过门三天的年轻媳妇,颇有些曲折地借到她唯一的嫁妆——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小通讯员牺牲后,年轻媳妇献出自己的新被子给通讯员陪葬。情节虽然简省,读起来却蜿蜒跌宕。因而,初读之时,很容易觉得这些事前后已过了几天。
然而,仔细一看,这篇小说所有的事件都被安排在一天之内。作者并没有刻意模糊时间,相反,作者生怕读者误读,把时间交代得十分清楚。小说开头,直接以“1946年的中秋”单句成段,似乎有意告诉读者,这些事都发生在中秋节这一天。通讯员带“我”到包扎所,是从“早上”到“下午两点钟”。“我”和通讯员去借被子,是在那天下午“刚到(包扎所)不久”之后的事情。打海岸的部队在“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之后发起总攻。通讯员英勇扑手榴弹,从战场上被送下来的时间——“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
时间的表征如此清晰,怎么还会有时间不止一天的错觉?这一天,到底是如何被拉长的?有何蕴藉?
一、营造两种氛围,形成对峙,透露战争的真相
西方的叙述学理论一般将小说分为故事层和话语层,相应地,小说涉及两种时间,即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故事时间是故事本真的自然时序,叙述时间是叙述文本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应该说,《百合花》的时间呈现比较传统,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基本合流。
但叙述时间还是有“被拉长”的效果。首先源于这篇小说前后部分形成两种迥异氛围,前者像是田园牧歌,安静祥和;后者像是人间炼狱,死伤惨重。两种氛围形成对峙之势,相互撕扯,相互彰显,使小说的叙述时间具有张力。
小说开篇通讯员护送“我”去包扎所的片段,整体氛围是轻松的,虽然是在赶路,却没有压迫感。
小说的第一处环境描写,带有女性视角所特有的细腻与清新:“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新鲜湿润的香味。”这幅“雨后秋景图”,寥寥几笔,就把战场还原为田园,战争的硝烟被这新鲜湿润的香味遮盖,透着一股慢下来的诱惑。“我”因为“脚烂”“路滑”,也确实走不快。
“我”与通讯员赶路的过程,也写出了日常的况味。一写通讯员的带路实在太有特点了,“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能够随时根据走在后面的“我”的情况调整距离和节奏。这个场景画面感极强,像是速写一般勾勒出人物形象。二写“我”与通讯员攀家常,“我”发现小通讯员是同乡,便问起他的家里情况,甚至有些打趣地问起“娶媳妇”的事,与日常闲聊无异。
然而小说最后描写包扎所施救的场景,整体氛围却极为沉重,侧面写出了战况的紧张与惨烈。
如果有镜头的话,前一个镜头还是中秋节品尝家做的月饼,下一个镜头就变为包扎所忙乱的场景。伤员一个个被送下来,救助条件却明显过于简陋,包括新媳妇等害羞的妇女被安排着给伤员拭洗伤口。一架架担架送过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战争中变得残损,近乎压抑却无能为力。
小通讯员就在这时被作为重伤员送过来了。他看到反动派投过来手榴弹,让身边的担架员快趴下,却选择自己扑上去,此时他的脸色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很快,他就被医生宣布药石无灵了。
小通讯员年轻的生命遽然消失,把悲情一下子推到了顶点。死亡本身就会让时间突然产生一个巨大的空洞。这篇小说读到结尾,任谁都有一种迷离和恍惚之感——那个青涩的小伙儿真的没了?那个一听回团部就兴奋的小战士就这样英勇牺牲了?因而,时间上虽然没过去多久,生死相隔却拉长了接受与消化的时间。
小说前后两部分形成两种氛围、两种节奏,像是两个世界,悄然增加了时间感。小说两种不同氛围相互张本,平静的日常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是如此脆弱,而惨烈的战争现实更表明战火中平静的日常是如此难得与虚无。战争的恐怖,正在于它无处不在。所有的战事稍歇、生活复旧,隐藏着杀机。
就在一前一后两种节奏的夹击中,借被子的情节刚好张弛有度,新媳妇把通讯员前来借被子视为“笑料”,像是家务事般显得日常、琐碎;而老百姓们最终把自家被子借出去,当然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尊崇,但多少有些生活早已失序、人人自危的意味。
小说前部分慢,意在让人体验美好;后部分快,意在警示战争疯狂。一慢一快的悖谬拉长了阅读的时间体验,也正说明战争没有差序,对美好事物的摧残从未停歇。
二、插入联想画面,开拓绵延,反映时代的沉重
法国文学评论家热奈特是叙事学的代表人物,他根据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不同把“时距”分为省略、概要、场景和停顿等四种情形。其中停顿是叙述时间无穷大,故事时间为零。根据这一理论,《百合花》中有兩处“我”的联想,它们延缓了情节发展,打破了时间的自然流动,可以将其归为“停顿”。“我”的这两处联想和沉思,在故事中的时间极短,可以解读的空间却很大,值得慢慢品味。
第一处,是“我”知道通讯员是同乡,并了解到他在老家是“拖毛竹”的,马上浮现的画面: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儿,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哔哔作响……
这一段描写颇有意识流的味道,眼前的现实与过去的印象相互交织。在故事里,“我”可能只是一个瞬息的闪念,但这一段自由联想在头脑里却可以无限延长。“省略号”是这种无限延展外化的体现。
竹海、石级山道和肩膀宽宽的小伙儿构成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这个画面里,有故乡最具特色的风光,也有故乡人最常见的营生。据“熟悉的故乡生活”这个说辞推断,“我”的祖辈、父辈和兄长可能就是这样以拖毛竹为生。甚至还可猜想,“我”年轻时心许过的青年也是其中一员。这或许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小伙儿有宽宽的肩膀,估计是个拖毛竹的好手。战争胜利之后,小伙儿可能有其他职业,也有可能回到天目山娶媳妇、继续拖毛竹。然而这个志愿加入战争的小伙儿最后牺牲了,天目山的竹海里再也没有他的身影……
第二处联想,是中秋之月升起之后,枪声打响之前,“我”吃到了家做的干菜月饼,又在脑海里产生一番畅想: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儿,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我”的自由畅想大大拓展了时空维度。先是开拓空间,想象当下故乡每家每户的中秋祭拜,通过孩子的欢乐来表现中秋节应有的模样。紧接着,又从时间上做手脚,猜测拖毛竹的小伙儿几年前也曾有过唱儿歌的懵懂欢快。最后,想象小同乡当下在战场上干什么。开头就已昭示的“中秋”节日,终于在这里得到演绎。如果没有这一段联想,全文就再难找到中秋节的气息了。
这一段节日的想象里透着沉重。首先,故乡家家门前的祭月其实未必如想象中那般美好,或许故乡也已惨遭战火侵扰。其次,对小同乡当下行动的想象为下文他的牺牲埋下了伏笔,深思黯然。
这两处跳脱开故事线的联想,都直接指向了故乡。而把家乡描摹得越美好,就越反映时局的动荡和人事的无奈。“我”和通讯员一时都无法回到故乡是时代的缩影。这种时局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和拖毛竹的小伙儿这样背井离乡,仰望中秋之月思乡,甚至直面战火无暇望一眼月亮。
如果說小说前后的不同氛围在警示战争的残酷,那么这两段联想则以横截面的形式反映时代的沉重。在那个时代,人们想过最简单朴素的生活却不可得。他们面对的,是残忍的战乱,是回不去的故乡。由此观照,茹志鹃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确实不仅是书写英雄人物和歌颂军民鱼水情,还深入时代肌理,反馈当时人们的痛痒。也因此,这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三、描摹两类转变,立体动态,体现人性的升华
一篇小说的成功往往在于能够塑造一些深入人心的经典人物。《百合花》全文5000余字,塑造了新媳妇、通讯员和“我”三个立体多面的人物形象,个个生动,人人有灵魂,甚至引发了到底谁才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核心人物)的讨论。
细论起来,在《百合花》中,人物是饱满丰富的,其多面让人感觉他们是相识已久的“老友”。“我”和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的情感升温挺骤然,这种骤然不同于平常的情感发展。要做到如此,小说必须有丰富细节让读者慢慢品,让一切发生得可能、进展得自然,才算逻辑自洽。
(一)性情的多元
《百合花》里的人物都立得住,读起来生动;传得开,叫人印象深刻:这归功于人物创设是圆融动态的。
通讯员,在“我”那里是拖毛竹的小伙儿——他走路要跟女同志保持距离,说到娶媳妇他就脸红,他会给自己的枪筒加点装饰……与此同时,他在新媳妇那里是“同志弟”——他是来借被子时慌里慌张说不清楚的小战士,是不好意思让她帮忙缝衣服的青年,是会赌气不肯抱过被子的弟弟……也是他,一听回团部上战场就活泼开心,上了战场为了救下身边的战友宁肯放弃生的机会。一个“扑”字,就把他大写的英勇写出来了。
或许,慢下来读,全面地读,更能读懂这个人物。他是青涩忸怩的,甚至有些笨拙;但他更是浴血奋战、英勇无畏的。这样一个人,他是英雄,更是一个本真的人。相比起“高大全”式的人物,通讯员更亲切,也更真实。
当然,《百合花》中的新媳妇是更富有变化的一个人物,一开始她不舍得把自己的新被子借出去,但后来还是转身进去抱被子了;她曾俏皮地捉弄过通讯员,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他可受我的气了”,然后一到包扎所就开始找“同志弟”;她刚被安排去拭洗伤员的身子时又羞又怕,但在通讯员牺牲后,“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小媳妇的这些转变,正见出老百姓对军队的认可,但更为深沉的,是人们对于英勇战士的崇敬,对一个美好生命的消逝发自内心的疼惜。
在小说中,人物都有动态的变化和成长。因着这些变化,我们读到生命的本真状态,读到青春的悲歌,读到生命的消逝,读到人类情感的饱满与庄重。在这种“沉浸式解读”之后,才会猛地发现:小说里的这一天,真的是既“短”又“长”。
(二)态度的转变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我”的态度最为清晰。“我”对拖毛竹的同乡,一开始观感不佳。因为刚开始带路时,“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撂下几丈远”。这么不管不顾的“大男子主义”走法,自然让“我”“生起气来”。但是很快,发现他不是一味蛮走,而是用仿佛长在身后的眼睛,一直体贴地照顾着“我”的节奏,由此“我”对他“产生了兴趣”。攀谈中,“我”得知他是天目山的同乡,在老家是拖毛竹的,就对他“越加亲热起来”。在借被子事件中,通讯员既憨直又天真,知道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后,甚至想还回去,这让“我”“从心底爱上了”他。
而新媳妇对通讯员的感情变化,则写得较为隐晦深沉。根据文本的暗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应是充斥着生疏、尴尬与不满。然而,后面新媳妇到包扎所工作时东张西望地寻找“同志弟”,可见“她”对他已有了关切,许是被这个纯真的少年打动了。最后,新媳妇发现重伤患者就是这个“同志弟”,发出了一声惊讶伤心的“啊”。听了担架员介绍“同志弟”扑手榴弹的过程,新媳妇又发出了崇敬疼惜的一声“啊”。在这两声“啊”之后,小媳妇开始自顾自地给“同志弟”缝补袖子的破洞,并且夺过被子为他裹好送葬。从这处细节不难读出小媳妇夹杂着懊恼不舍的巨大悲痛。“当然还不能把这种感情说成是男女之爱情,但这确实是一种比同志、同乡、军民更为微妙、含蓄、纯洁、美好的感情,是青年男女之间潜意识的自然流露,这本身来说就是青春人性的自然表现。”[1]
“我”和新媳妇与通讯员都是初识,但“我”对这个拖毛竹小伙儿的牵挂,新媳妇在“同志弟”牺牲后献被子随葬,都体现了极深的情感。这种感情,倒像是经历了悠长的岁月、繁复的人事构筑的。
对此,作者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有明确的解释:“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2]那么,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战时极短的交流时间,却等同于平时漫长的情感建设?
总的来说,在这“悠长”的一天里,《百合花》营造了两种氛围,揭示了战火之下安宁不再,也插入了两处联想,暗示时局混乱与时代沉重。然而正是在这些灰暗中,《百合花》描摹了人与情的转变,彰显了人性升华与生活微光。
借着这些丰富蕴藉,《百合花》成功超越“一天”,走向经典。
【注释】
[1]田刚.再论《百合花》[J].唐都学刊.1993(4):81~83
[2]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49~52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