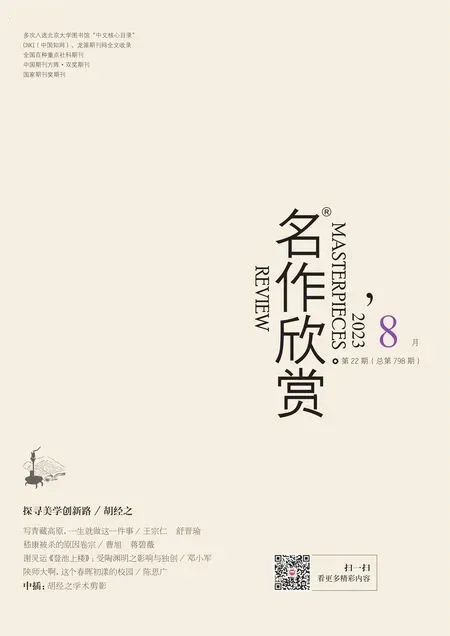嵇康被杀的原因卷宗
2023-08-27上海曹旭江苏蒋碧薇
上海|曹旭 江苏|蒋碧薇
嵇康被杀,离现在已经有一千七百五十多年了。
为什么还要回溯他?因为嵇康是醉酒和被杀时,姿势最优美的男子,是当时的知识人对抗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最具象征意义的高标。
其实,回到一千七百五十多年前,杀的一方和被杀的一方,都还有许多细节没有弄清楚,假如我们今天重新以新的理念为之立案,真有许多被屏蔽的事件需要恢复。
于是,查阅相关的资料,尤其是读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分析、研判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嵇康方面和司马昭方面看一看其中历史的偶然和必然。
“单亲家庭”出身的嵇康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銍(今安徽宿县)人。其先人本姓奚,避怨迁徙到銍;而銍地有嵇山,遂与山同姓。嵇康早年丧父,由母、兄抚养长大,是一个出生在“单亲家庭”的人。嵇康一生的性格,颜延之说得最准确,是“龙性谁能驯”,其实也和他出身“单亲家庭”有关。直到嵇康三十八岁那年,母亲死去,哥哥入军,嵇康仍然很在乎,说:“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可见对他心理的影响。
但他少有奇才,学什么好像都不用老师教,自己看看,很多东西都懂了。人长得高大而帅气,文章写得辞藻华美,而且有骨气,出身儒业世家而笃好庄老,志向远大,超迈不群。
因为太帅了,二十岁时,就被沛王曹林看中,招为女婿,这使嵇康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成为曹魏宗室的姻亲。因为姻亲的关系,他被朝廷征为郎中,成为一个不怎么管事也没有多少薪水的“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
“中散大夫”是西汉平帝时开始设置的官,魏晋南北朝沿用,官虽然是七品,有六百石俸禄,但没有实际职务,唯有皇帝的诏令来,有什么问题就问问,是属于养老疾性质的官。所以嵇康读读书,锻锻铁,灌灌园,优游山林,清谈清谈,身份在官吏和逸士之间。
一是地缘,二是精神上的需要,他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神交,又与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阮咸、琅琊王戎为山林之游,世称“竹林七贤”。嵇康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
嵇康善辩,又喜诘难,什么东西都要弄出个究竟,所以他的文章论辩很多。现存文章十五篇,论就有九篇。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指出:“嵇叔夜文,今有专集传世。集中虽亦有赋箴等体,而以论为最多,亦以论为最胜,诚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譬如《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每一篇都有针对性,具有挑战社会和世俗观念的意味。不仅表达了他的观念、审美、趣味、逻辑和思辨,同时也表达了激越的思想情感;笔端带有锋芒,具有时代压迫下的叛逆精神;他甚至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放在文章里表达出来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书”,不是“论”,但嵇康是把书也当成论来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不仅在魏晋,在整个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上也是一篇奇文。所以,读“竹林七贤”,读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非读不可。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题中的“山巨源”,就是山涛,巨源是山涛的字。嵇康与山涛有“神交”。与嵇康有神交的,一个是阮籍,一个是山涛。因此,即使在竹林七贤的小团体内部,他们也是最好的朋友。
在有神交的朋友之间,因为什么决裂,导致要写“绝交书”呢?因为嵇康和山涛的脚,各踩在魏、晋“两大板块”之间,当板块分离,变成两个大洲,嵇康和山涛在政治上,也随着板块决裂,变成两个大洲;“绝交书”就完整地记录了原来连在一起的土地是如何变成两个大洲的。
除了嵇康与曹魏有姻亲,山涛与司马氏有表亲,成了一种象征以外,还有就是两个人的人生态度不同:嵇康要“隐”,山涛想“仕”。在司马氏企图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王朝的态度上,一个不合作,一个要合作,成了绝交的断崖。
魏元帝曹奂景元二年(261),山涛由吏部侍郎迁为散骑常侍,空下吏部侍郎的位子,山涛推荐嵇康继任。这触动了嵇康刚肠嫉恶的神经。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山涛的举荐是“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腥膳”。嵇康写这封绝交信时,三十八岁,正当壮年气盛之时;绝交书就成了烧红的炭,成了火山喷涌而出的岩浆。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羶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以前读《与山巨源绝交书》,怪嵇康怎么不讲人情。其实,嵇康不是不懂人情,不讲人情,《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说,嵇康不是不知山涛的知遇之情,《与山巨源绝交书》一书,乃是借此机会向晋司马昭下战表,表明自己对司马氏的决绝态度。
嵇康为什么要借“绝交书”向司马昭下战表呢?我们只读断崖式的“绝交书”,是莫名其妙的。其实,要知道,嵇康虽然是个七品的清闲的“中散大夫”,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可以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而且夫人又是曹操的曾孙女。因此他对当时司马昭一步一步的篡权举动还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的。
俗话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嵇康岂能不知?早在嵇康写绝交书的前七年,正元元年(254),司马氏和曹魏宗室的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李丰和夏侯玄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想诛杀司马师,但计划败露,反而被司马师一网打尽,夷灭三族。最后司马师废曹芳为齐王,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而忠心耿耿的曹魏名将嵇康的朋友毌丘俭,因为不满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杀害好友夏侯玄、李丰,遂矫太后诏,起东南之兵,西进讨伐。但终因势单力薄,失败被杀。司马师在征讨毌丘俭回师途中病死,于是司马昭上台。眼看曹魏的大权渐渐旁落,可以说,每一件朝廷大事都牵连着嵇康的内心。而在这一过程中,山涛始终忠心耿耿地站在司马氏一边。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山涛竟然推荐他去代他原来的官职。以前总认为,嵇康过于高蹈,朋友山涛推荐他做官他不做,还要痛骂朋友。现在知道,山涛是要嵇康像他一样,名为曹魏的官,其实是去为司马氏效劳。也许嵇康深藏不露,山涛一直不太了解嵇康的政治立场。而嵇康无名的烈火便烧向竹林的“神交”;终于到了要摊牌的时候,忍无可忍的嵇康写了这封“绝交书”。
“绝交书”看起来针对山涛推荐自己做官,但明显是冲着司马昭去的。
嵇康对山涛说,我和你,以前是朋友,只是一场误会,熟悉以后的陌生是更可怕的陌生。然后句句痛诋山涛作为司马氏帮凶的无聊,表示对儒家礼法的蔑视,以“七不堪”宣告自己与做官不可调和的立场:
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文中嘲笑做官,说,睡懒觉比做官重要;弹琴、钓鱼比做官重要;搔痒也比做官重要。不做官可以无案牍,少应酬;不做官可以少开追悼会;不做官可以少丢人现眼;不做官可以少烦心,少焦虑;《六经》未必是太阳,不做官可以非议圣人;不做官可以随便发脾气,不用担心得罪人。
在“七不堪”的后面,嵇康还写道: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即使在当时的“乱世”,讲“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仍然是违反了基本原则的不得了的事。何况嵇康自己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九患”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对当时的社会,对官场,可谓蔑视到极点。尤其是自诬自戕,皆成文章。此皆嵇康思想新颖处,亦魏晋文绝佳处。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没有什么嬉笑怒骂的文章可以与之相比。
其实,在嵇康的内心,他还是希望认认真真、小心翼翼地生活的。作为一个出身礼教世家的人,他是尊重和信奉儒家礼教的。房玄龄等《晋书·嵇康传》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说与嵇康在山阳住了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孙登言于嵇康:“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嵇康都是知道的。还有,嵇康也非常爱惜自己,谈及家常,嵇康为人子,亦为人父,有家庭之责任。临刑前,仍索琴弹《广陵散》,顾视日影;或读一读他的《家诫》,那是走向刑场的爸爸最后一次对十岁的儿子说话。你就知道,嵇康是很热爱生活,留恋生命的。
嵇康代表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想做一个老好人,不想在脸上表现出“喜愠之色”;但是,被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激烈的内心,决不允许任何邪恶存在,决不允许玷污了礼教又拿礼教作幌子,仍然会向社会上的政治强人端出最赤诚的内心。
在不与魔鬼打交道,不拿真诚做交易的原则面前,嵇康用激烈甚至偏颇的语调,大肆嘲讽。峻急刚烈的个性与玩世不恭的态度结合在一起,随心所欲的、挥洒自如的、宣泄式的语言,时见析论的绵密、辞气的锋利、思想的新颖、词采的壮丽,其气势和不可正视的思想光芒,后世很少有文章可以与之比拟。
像他自己预料的那样,两年以后,嵇康因写《与山巨源绝交书》而被杀。
魏明帝法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即是死罪
为什么司马氏要非杀嵇康不可呢?因为嵇康在“绝交书”中,对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做了深刻的揭露与蔑视,说了他们最忌讳的那些话,尤其是他“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政治见解,都是针对一心想篡权夺位的司马氏集团的,聪明的司马昭比谁都看得清楚。司马氏集团要上台,必须理论先行,因此主张“以孝治天下”,而汤、武和周、孔作为一种秩序的象征,是谋逆者夺取政权的思想基石。嵇康否定抨击的,正是剥夺篡权易代的基石和理由,这使司马氏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必欲杀之而后快。
其实,在中国古代,凡是干犯,包括仅仅以语言诋毁或不敬,并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没有损害危及统治者的,同样是大逆之罪,处以“腰斩”,连坐家属。这就是《公羊传》说的:“君亲无将,将而诛焉。”而按照魏代的法律,嵇康即使没有任何行动,仅仅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也一样可以定为死罪。《晋书》卷三十“刑法志”载,魏明帝时“承用秦汉旧律”;魏明帝又命陈羣、刘邵等六人“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一百八十余篇,改定的魏法上也明写“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而且,以前处决犯人,诸郡可以各自选定日期,魏明帝新改的法律里对这条也做了修改,即决定处决日期的权力,也一律由中央统一决定,集中处决可以显示更大的震慑力,这些在魏明帝的法律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以嵇康的“罪行”对照,也够了,何况他还为吕安的“不孝”辩护。
但是,也许嵇康不是一般人,既有社会影响,又是魏室的姻亲,因此,司马昭并没有仓促行事,而是在网罗罪名,准备上纲上线到谋反罪。谋反罪虽然也是死刑,但处置要重得多。
嵇康与钟会的死结
钟会(225—264),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人。三国时期魏国军事家、书法家,太傅钟繇幼子、青州刺史钟毓之弟。钟会比嵇康小两岁,才华过人,弱冠入仕,历任要职,深得魏帝和群臣赏识。精通玄学,但一直对比自己出道早也更有声名的嵇康又敬又畏。公元253 年,钟会二十九岁,写成《四本论》,想让嵇康看一看,但又不敢。根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这是一个心理极端复杂又极端自私封闭的人才会有的举动。刚写成《四本论》,想让嵇康见到,想必钟会对他的《四本论》也非常自信;于是把它放在怀里,带到嵇康家门口;但又突然害怕嵇康诘难,不敢拿出来。最后慌慌张张地把他的书稿朝嵇康家开着的窗户扔进去,随即掉头快步跑掉了。
此后他屡次出谋划策,帮助司马氏征讨叛乱,做了高官,甚至有人把他比作张良;钟会这种在曹魏和司马氏之间的态度,使嵇康与他有了死结。
做了高官的钟会仍然想会会嵇康,也许是司马昭的授意,他对嵇康仍然保持一份敬畏和警惕,决心再去拜访一下。
这次他骑着马,带了很多随从。到嵇康家后,发现嵇康在打铁。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简傲》篇记载: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房玄龄等《晋书·嵇康传》把这一段改成:“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以前我们没有深究这段记载的时间以及钟会拜访嵇康的用意,但从嵇康冷落钟会,并在钟会灰溜溜要离开的时候,突然问:“你听到什么消息来的?你看到了什么情况走了?”我觉得钟会此来,应该是有打探嵇康状况的目的。这就可以解释,嵇康为什么不理钟会,并在他要离开的时候,问这两个问题了。
嵇康讥讽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样,钟会也不含糊,也针锋相对地回答:“我听到了消息,所以来了;我看到了所看的,所以走了。”
钟会来前,听了什么?前面已经有了逻辑;来了以后,他看到的,并不是嵇康在“大树下锻鉄。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而是看到了嵇康对他的蔑视和仇恨。够了,走了。余下的并不是空白。
嵇康被杀的导火索
根据东晋干宝《晋纪》记载,直接导致嵇康被捕入狱的原因与他的另一个朋友吕安有关。吕安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吕巽,平时也和嵇康等人在一起玩。据干宝《晋纪》说:“(吕)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这是说,吕安的妻子徐氏貌美,吕巽用酒把她灌醉了以后奸污了。“丑恶发露”,吕安知道以后,便告诉嵇康,希望嵇康帮他拿主意。嵇康从珍惜他们家庭声誉的角度出发,劝吕安算了,原谅哥哥一下,吕安听从了嵇康的劝说。
想不到的是,“(吕)巽善钟会,有宠于太祖”,“反告安谤己”。吕巽自恃与钟会是朋友,司马昭也欣赏他,就恶人先告状,告发吕安不孝,罪名是他“打过母亲”。
司法机关逮捕了吕安。感觉冤屈的吕安请知情的嵇康出庭做证。嵇康觉得事涉自己,于是与吕巽绝交——这是他写的第二封绝交书——《与吕长悌(字)绝交书》,并决定出庭证明吕巽是真正的罪犯。但去了司法机关的嵇康,就再也没有能回来。吕安不孝,嵇康为之辩护,这正好是给司马昭一个送上来的理由,司马昭遂将嵇、吕收捕下狱。
嵇康最后被杀的理由是——谋反。统治者要杀一个人,总要上纲上线。但嵇康怎么会“谋反”呢?
嵇康“谋反”的公案
嵇康“谋反”的公案,与一篇文章有关,这就是后来被《文选》收录的《赵景真与嵇茂齐书》。
事情仅仅过了七十多年,由王导推荐,干宝在为东晋司马睿写的《晋纪》中,就写到这件事。干宝《晋纪》已经亡佚,但唐代无名氏《文选集注》八十五《赵景真与嵇茂齐书》注引公孙罗《文选钞》,引到干宝《晋纪》说:吕安不孝,罪名成立,被判流放到边地。吕安临走前,写给嵇康一封书信,信中说:“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啸大野,虎睇六合。猛志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难,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也。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哉?”
《文选》唐张铣注:“昆仑、泰山,喻权臣也。”权臣即司马氏,这不是吕安联合嵇康造反的信号吗?
早在唐代以前,针对当时的误传,嵇康的儿子嵇绍专门写了一篇《叙赵至》的文章。在文中,附有专门的更正,说:“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安)与先君(嵇康)书,故具列本末。”景真是赵至的字,茂齐是嵇康的哥哥嵇喜儿子嵇蕃的字。嵇绍的《赵至传》,为《晋书》所采入。《晋书》说:“初,(赵)至与康兄子(嵇)蕃友善,及将远适,乃与蕃书叙离,并陈其志。”可以证明。
但是,嵇绍写《叙赵至》时,嵇康已被杀二十多年,文章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只能证明父亲没有谋反。这篇文章,后来被昭明《文选》收录,题目是《与嵇茂齐书》,作者赵景真。
唐代李善注《文选》的时候,也弄不清这篇文章到底是干宝《晋纪》中说的吕安写给嵇康的,还是赵景真写给嵇茂齐的,就把两种说法并列在一起。至六臣注《文选》时,李周翰就是支持干宝《晋纪》的,唐代为李善《文选》注作注的《文选钞》,也是支持干宝《晋纪》观点的。《赵至传》后为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六十五所收录。
对这些问题,1976 年,在日本,作为小尾郊一主持的《〈文选集注〉研究》课题成果的一部分,森野繁夫、当永一登已对此问题做过研究;国内的周振甫、戴明扬先生认为信是吕安写的,要联合嵇康造反;樊荣先生对此也做过深入的研究,否定“吕安联合嵇康造反”说。
我也相信嵇绍的说法,信不是吕安写给嵇康的。我觉得,当时嵇康被杀已过了六七十年,社会流传的,都是吕安联合嵇康造反的舆论和消息,这种舆论和消息其实幕后是由司马昭、钟会、吕巽主导的。六七十年过去,编造的“罪证”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社会上流行的舆论;干宝根据这些舆论和消息写成《晋纪》,“吕安联合嵇康造反”就成了历史。连儿子的辩白和这篇文章上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都可以视而不见。
到了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世语里,已变成:“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又把嵇康与起兵反对司马氏的毌丘俭联系起来,嵇康的罪名真的成了谋反了。
虽然到了唐代,房玄龄等人的《晋书·嵇康传》里,就已经认为钟会对司马昭说的那些话是“谗言”。钟会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于是追回流放途中的吕安,和嵇康一起处死。
房玄龄等《晋书·嵇康传》其实也不同意“吕安联合嵇康造反”说,认为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的坏话,是“谮”,是捏造事实,还说“帝既昵听信会”。
真实的情况,也许当时司马昭就觉得勉强吧!也许因为嵇康姻亲的身份,所以最后被处以斩首,并没有用“污潴,枭菹”,把人剁成肉酱之类或“夷其三族”的酷刑。
司马昭杀嵇康的时间,各种史书记载混乱。按照《嵇康传》,嵇康当死于正元年间(254—260);按照《嵇绍传》,嵇康死在景元三年(262);《三国志》称死在景元中(260—264),裴注称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255),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具体时间已难以确定。
可以确定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说:“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明代江进之《亘史外记》说:“此等文字,终晋之世不多见,即终古亦不多见。彼其情真语真,句句都从肺肠流出,自然高古,自然绝特,所以难得。”明代李贽《焚书》:“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
嵇康、阮籍相比,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比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更值得一读。因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和古时旧说反对。”
司马昭杀嵇康,杀的是当时的精神领袖,杀的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