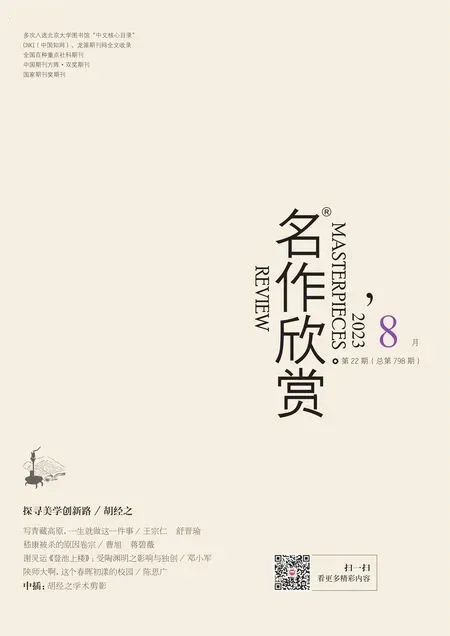独辟蹊径,寻找新诗经典化的秘密
——评郭勇《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
2023-08-27江苏王珂
江苏|王珂
7 月21 日,收到神交多年却未曾谋面的郭勇寄来的《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一书,该著2022 年4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题字说“师兄雅正”。只读了绪论,便觉得酷暑不再那么难耐。读完全书的第一感觉是“师弟可畏”,很自然地想起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庆炳教授在2001 年10 月19 日为我的第一部诗学著作《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与诗的创作》作序时写的那两段话:“文体问题尤其是现代汉语诗歌问题,是当前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虽然是热点,谈论也很不少,但系统深入的研究迄今还基本上是空白。王珂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地填补了这个空白。我阅读了全书,感到王珂治学的谨严与锐利。谨严,是说他的著作搜集了大量丰富的资料,他的研究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这里有求是之心,没有虚玄之论,并且对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周详的考虑;锐利,是说他的著作,不囿于陈言旧说,有学术创新的勇气。这两点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实是在很重要的。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一个学者应有的品质。”①“王珂的这部著作从立意之新鲜、视野之开阔、资料之丰赡、分析之详尽、概括之深刻、举例之多样、逻辑之严密、文字之流畅,都可以看出在这部著作中倾注了他全部的学力和积累。这种认真的治学态度,正是我对青年学者所期待的。”②童老师当时是为了鼓励刚过而立之年的我,让年轻学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写了这样的“溢美之词”。我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位老学者对年轻学者的学术期望。郭勇的这本书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作为学者,他具有“治学的谨严与锐利”;作为学术著作,这本书的特点及优点正是:立意新鲜、视野开阔、资料丰赡、分析详尽、概括深刻、举例多样、逻辑严密、文字流畅。这个出自内心的“表扬性”结论与我的学术经历休戚相关。
我1990 年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获得中国各体文学专业(后来统一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诗理论与创作研究方向硕士学位后,一直专业从事新诗研究,主要研究新诗文体学(新诗生态学、新诗功能学、新诗诗体学),系统研究过新诗的文体生成与流变,重点考察过现代新诗,尤其是从1897—1937 年的新诗历史,特别是诗界革命与新诗革命的发生史,2002 年负责“中国新诗大系”(1917—1927)的初选工作。对诗界革命、白话诗运动等诗潮,《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新月》《诗》《新文学大系1917—1927》《大公报》《小说月报》《创造周刊》《创作日》《新月》等现代原始报刊、选本等做过系统研究。我比较熟悉这本书的研究对象,对第一章《新诗选本的初创与发展》涉及的内容相当熟悉。本书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十分仔细,不但借鉴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总结出的1922 年及以前共有四部新诗集问世的研究成果,还认真研究了这四部新诗选本的历史。第一部是《新诗集》,新诗社编辑部编,1920 年1 月新诗社出版部出版。第二部是《分类白话诗选》,许德邻编,上海崇文书局1920 年8 月出版。第三部是《新诗三百首》,新诗编辑社编,上海新华书局1922 年6月出版。第四部是《新诗年选》,北社编,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年8 月版。甚至找出1920 年何仲英编的《白话文选》第二册还收了新诗三首: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和沈尹默的《生机》。前四部诗选我做过研究,《白话文选》收诗三首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认为“新诗”这一称谓在社会中得到传播和认可,与“新诗社”和《新诗集》有关,考察出“新诗社编辑部”编辑《新诗集》(第一编)由上海国光书局印刷,收入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等创作诗103 首和翻译诗6 首。还收入了3 篇诗论: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与刘半农的《诗的精神之革新》。
因为本科是外语系,大三时准备考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读了较多理论书,对理论很感兴趣。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又是“理论”与“创作”结合,导师吕进主要是诗论家,我的这门课程的论文《新诗史上的三个诗的定义》发表在《争鸣》上,美学家李敬铭上过美学课,课程论文《中西方诗本体论探微》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又长期在文艺理论教研室,读的是文艺学的文学基本原理方向的博士,担任过中文专业的文艺美学方向和哲学专业的美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所以我的新诗研究格外重视理论。但是这种文艺学的“依靠脑袋做学问”的方式常常被现当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的“依靠屁股做学问”的方式轻视。所以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将两者结合,要求写论文“言必有出处”和“言必有理论”。操作起来却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没有经过“文献学”的基本功训练,加上长期不生活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史料中心”城市,想“依靠屁股做学问”,却没有条件。所以2016 年当我知道郭勇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现代新诗的经典化研究”课题时,既觉得他是负责这个课题的最佳人选,因为现当代专业的新诗学者普遍缺乏理论思辨能力,他是有文艺学博士学位的文艺学学者,这个课题在申报时也属于“文艺学”而不是“现代文学”。也有些为他担心,他完成这类既需要理论材料更需要事实材料的研究与我有相似的处境,他工作的江南大学在江苏无锡,过去工作的三峡大学在湖北宜昌,离“史料中心”甚至“学术中心”更远,更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读完此书,惊讶地发现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啃下了这块新诗研究的硬骨头,较完美地完成了“新诗选本”这个课题。
缜密的理论思辨和翔实的史学考察能够有机结合,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尤其是史学考察部分的完美令长期研究新诗的生成与流变的我赞叹不已。
虽然新诗只有百年历史,作品数量却惊人。1935 年5 月1 日,洪球在湖州为他编的《现代诗歌论文选》作序说:“新诗集的出版,在最近略记不少有千余种……”③1988 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收录了1917 年至1987 年70 年间的诗集4244 部,诗评论集306 部。2006 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的《凡例》说:“一、本书为《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的诗集诗诗论集卷,收录1920 年1 月至2006 年1月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诗论集一万八千余种。二、本书收录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为主,并尽量收录海外出版的汉语新诗出版物。三、本书收录区域包括出版社出版的和作者自印的新诗集、诗论集以及散文诗集、儿童诗集、诗剧、诗及诗论与其他文体的合集等。”④由于长期处在革命、运动、战争此起彼伏的动荡年代,很多诗集都是诗人或诗群自印,流传保存下来的很少,导致新诗的史料工作很难开展。2001 年我应孙绍振先生邀请负责《中国诗歌大系(1917—1927)》的初选工作,踏破铁鞋遍查群籍,也收效甚微,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做此类工作。
新诗研究界只有陆耀东与刘福春迎难而上。陆耀东2006 年在武汉大学告诉我,他多年暑假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查找现代时期的新诗文献,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史(1916—1949)》,堪称史料最翔实的“新诗史”。他的《前言》说出了“以史实为依据”做新诗研究的辛苦。“本书名曰《中国新诗史》,没有涉及同时代的旧体诗词。它以新诗中特色突出的作品和重要的诗学论著为主要考察对象。一切均以客观存在的史实为依据。不主张‘以论带史’,更反对以‘以论代史’。历史有它自身运行的轨道,并非按某人或某些人的指令或主观愿望向前发展。‘以史实为依据’前提是必须全面掌握史料,但搜集资料之难,唯个人知道。1917—1949 发表新诗的刊物约千余种,发表的新诗在十万首左右,出版的诗集达一千五百种以上。我从七十年代末起集中精力搜集史料,除诗集有过半到三分之二外,我掌握的刊物仅一半而已。”⑤
近年新诗研究界出现急功近利的文风,中青年学者中只有姜涛、张桃洲、易彬、段从学、孙晓娅等少数人像陆耀东、孙玉石等老一辈新诗学者那样重视史料工作,强调“以史实为依据”,写论文或著作时追求“言必有出处”。我近年经常当刊物发表论文或课题结题的评审人,发现好多都像陆耀东所说的“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有的著作甚至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由于文献工作没有做到家,不愿意下苦功夫或笨功夫“钻故纸堆”,导致浮光掠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郭勇不但极有耐心地“钻进去”了,而且“钻”得非常到位,不仅详细地梳理出百年新诗史上的新诗选本的历史,总结出这些选本的特点,还对同行学者的相关研究相当了解。他以文艺学学者的身份获得这个国家课题时,我有些担心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诗研究者不熟悉,因为新诗研究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和几大“门派”,不仅主要是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而且主要是几位名家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有“吕家军”(西南大学吕进的学生,如李震、蒋登科、王珂、江弱水、杨四平、张德明、段从学、向天渊、梁笑梅、熊辉、颜同林),“吴家军”和“王家军”(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和王光明的学生,如孟泽、张大伟、霍俊明、张立群、王士强、龙扬志、荣光启、伍明春、赖彧煌、罗小凤、陈培浩),“谢家军”“孙家军”和“洪家军”(北京大学谢冕、孙玉石与洪子诚的学生,如臧棣、周亚琴、钱文亮、姜涛、冷霜),“陆家军”和“龙家军”(武汉大学陆耀东和龙泉明的学生,如方长安、陈卫、王毅、罗振亚、李润霞)。
郭勇的博士生导师王一川也研究过新诗,尤其是研究过新诗的现代性问题,还建立起“现代性诗学”。他在《文学评论》1998 年第2 期上发表过《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他曾高度肯定过伊沙的《车过黄河》是“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的代表作。他甚至还解读过于坚的诗《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他带的2021 年毕业的博士陈太胜既研究诗还是诗人,出版过诗集《在陌生人中旅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这些来自老师和师兄的“新诗因素”显然对郭勇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让本书“纲举目张”的“纲”就是“现代性”,明显继承了他导师的“学统”,高度重视现代性。郭勇读博士时也上过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童庆炳的课,也受到了他的影响。所以本书的两个关键词“现代性”和“审美”在“理论上”是出自“名门正派”——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派。本书的“文学经典化”也是受此学派影响,如作者所说:“选本研究还会涉及文学经典化问题。1993 年佛马克与蚁布思来北京时在大学讲演而成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为中国学界思考经典问题提供了域外视角,开启了一个经典讨论的热潮。童庆炳、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是新世纪经典化讨论的重要成果。”⑥本书一共分为四章:新诗选本的初创与发展、在审美与政治之间的一体化选本、回归审美与追求现代性的新诗选本、21 世纪新诗选本的多元化景观。从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题目中的“审美”和“现代性”就可以看出两位导师的巨大影响,这两个关键词正是打开新诗选本研究的金钥匙。
我一直主张新诗著作的最高境界是“言必有出处”和“言必有理论”。本书在理论上的最大优点正是对“现代性”的高度重视,始终把新诗视为一种“现代性文体”,这也是本书超越了“资料汇编”式的“新诗史”或“文学史”的历史价值,获得了可以指导当下及以后的诗歌选本选编工作的现实意义,这也是让我这位广义的师兄对郭勇产生“惺惺相惜”的原因,正是两人对“现代性”迷恋的“共情”。我俩相差多年在北师大获得文艺学博士学位,王一川老师给我们上过博士生课程《西方文论》。尽管我一向宣称“王珂宁愿做工具知识分子不愿意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愿意做一个“知道分子”,但是对唐弢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独立分子”十分偏爱,因此也主张今日学者应该有一点“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性”,但是必须采用学术的方式来呈现思想,为现实社会服务,强调现代文学学者如同现代汉诗,最大的任务就是培养现代中国人和打造现代中国。新诗本来就是一种思想性和政治性极强的文体,如果说新文学是启蒙文学,启蒙功能更是新诗的主要功能,新诗现代性的基本概念是:世俗性、先锋性、断代性、叙事性、相关性、启蒙性和审美性,先锋性是新诗的主要品质,追求现代性是百年来新诗诗人的最大追求,新诗的历史即是包括启蒙性建设和审美性建设的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历史。所以“新诗”更应该叫“现代诗”甚至“现代汉诗”——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记录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表达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
2008 年5 月在安徽桃花潭,我的博士后导师吴思敬告诉我,他和谢冕在2004 年设计新世纪中国新诗研究界最重要的系列研讨会时,为了强调这种抒情文体的“现代”品质及改革社会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功能,谢冕主张用“现代诗”取代“新诗”,称为“21 世纪中国现代诗研讨会”。这个系列会议已经举办了十届,“21 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是我在福建武夷山操办的。2016 年11 月9 日,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现代汉诗研讨会”在南京召开,谢冕在我主持的开幕式上说:“我们的会议题目叫作‘现代汉诗’,我没有用这个概念,王珂用了,王光明也用了现代汉诗。我用的是‘中国新诗’。”⑦实际上谢冕最喜欢的是“现代诗”称谓。1986 年10 月,他的《中国现代诗人论》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让“现代”一词进入书名,标志着谢冕高扬起“现代”大旗,他因此成了“现代诗”的旗手。作为文艺学博士,尤其是王一川的博士,郭勇自然熟悉现代性理论及文艺学界的现代性研究,本书也显示出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现代性及现代诗研究状况的熟悉。第二章的标题“在审美与政治之间的一体化选本”呈现的正是“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既和解又对抗的存在方式。第三章的标题“回归审美与追求现代性的新诗选本”直接用了“现代性”。
我一向主张“学者的最大竞争是知识结构的竞争”和“学术研究的一大竞争是方法论的竞争”。本书呈现出郭勇既有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学者的知识结构,也有古代文学甚至文学以外的统计学的知识结构。书的附录《中国新诗选本举隅》统计出400多部新诗选本,全书还采用了10 多个表格。第一章《新诗选本的初创与发展》就用了6 个表格:1928—1936 年出版的新诗选本、30 年代知名新诗选家、30年代选本选录诗人情况、30 年代新诗集、《战前中国新诗选》与《现代中国诗选》、流派选入的情况。这些表格也具有将文艺学的理论思考与现代文学的史学考证融为一体的特点。如“流派选入的情况”表中列入了四项:诗派、入选诗人(人)、入选诗作(首)、作品基调。“作品基调”是典型的文艺学的“定性”研究,与前三项的“定量研究”有机结合。如果不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是无法在“作品基调”⑧一栏填入以下文字的:新月派对生命和爱情的狂热歌颂,初期自由诗派对个性、自由的热烈呼唤,七月派对民族的深切忧虑和对理想的深情系念,现代派对社会绝望的自我呻吟低叹,学院派对命运皈依与反抗的含泪悲歌,抗战派对正义战争和和平的明朗歌唱。
六大诗派的划分与命名也独具匠心,是现当代新诗学者在此类研究中不会也较难进行的。当然,这样的划分及作品基调的确定在现当代学者看来可能有些主题先行式的“拉郎配”,甚至有些强词夺理,却显示出郭勇身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锐气。近年新诗研究界越来越重视“史学研究”,从“材料”一词变为“资料”最后成了“史料”的演变史,从国家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常常有“资料库建设”一词,就可以看出。201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名称就是“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现代文学界及新诗界出现了陈子善、刘福春、易彬等致力于“史料学”的优秀学者。尤其是刘福春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新诗史料的搜集工作,获得了“新诗司库”的美名。但是也导致一些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有“学问”没“思想”,危及他们的前程及新诗研究界的前途。
目前中国大陆有近百位新诗学者和十多家新诗研究机构,分为三类:一、宏观研究,如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新诗研究院。宏观研究中也有微观研究,如诗体学研究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传统强项,从20 世纪80 年代的邹绛到21 世纪10 年代的吕进,都是新诗文体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二、专题研究,如东南大学的现代汉诗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的现代汉诗研究中心,专门研究现代汉诗。三、微观研究,如南开大学穆旦诗歌研究中心是穆旦研究的权威机构,也做专题研究,如罗振亚的小诗研究及日本经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研究,卢桢的旅行诗及城市诗研究,李润霞的“文革新诗”研究,都颇有特色。山东大学(威海)现代诗歌研究中心致力于新诗叙事学研究,孙基林是学术带头人。四川大学新诗研究院的特色研究是新诗史料学研究,刘福春是学术带头人。
新诗研究界出现了四世同堂现象,有影响的大陆学者主要有:第一代:谢冕、吕进、吴思敬、洪子诚、杨匡汉、孙玉石、陆耀东、骆寒超、冯中一、吴开晋、吕家乡、袁忠岳、蓝棣之、任洪渊、刘士杰、苗雨石……第二代:龙泉明、王光明、罗振亚、孙基林、程光炜、刘福春、沈奇、陈仲义、陈超、耿占春、张清华、燎原、吕周聚、周晓风、彭金山、耿建华、章亚昕、方长安、王泽龙……第三代:敬文东、何言宏、江弱水、李怡、陈卫、杨四平、段从学、蒋登科、赵思运、周亚琴、陈希、王毅、粱笑梅、陈爱中、张桃洲、张洁宇、孙晓娅、张德明、钱文亮、李润霞、向卫国、易彬、谭五昌、姜涛……第四代:傅元峰、荣光启、张立群、霍俊明、伍明春、罗小凤、王士强、熊辉、王东东、李章斌、龙扬志、陈培浩、刘波、世宾、卢桢、张光昕……港台及海外学者有:叶维廉、杜国清、简政珍、郑慧如、孟樊、李树枝、郑政恒等。中国港台及海外学者有:叶维廉、杜国清、简政珍、郑慧如、孟樊、李树枝、郑政恒等。专门从事新诗研究的汉学家有:奚密(美国)、柯雷(荷兰)、安敏轩(美国)等。这些学者各守一个“滩头阵地”。有特色的成果有:吕进和骆寒超的文体学及诗体学研究、吴思敬的心理诗学研究、孙玉石的现代主义诗潮研究、孙基林的新诗叙事研究、姜涛的新诗诗集生成研究、张桃洲的新诗语言研究、张松建的现代主义诗人研究、王泽龙的新诗意象研究和新诗节奏研究、方长安的新诗接受传播研究……
郭勇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后在三峡大学任教多年,受到了湖北学界研究文学传播热的影响。郭勇的新诗选本研究属于新诗接受传播研究,是其中的一个更小却十分重要的“滩头阵地”,一直没有合适的守将。本书的问世证明郭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名副其实地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⑨。这项研究的价值不仅在新诗乃至文学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在中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传播”是“现代文学”兴起后的事情,是报纸、刊物等现代媒介进入现代生活后的产物,更是诗歌以个人的抒情文体到公共的启蒙文体的“现代性”转换的结果。如英语文学的“现代运动”大约开始于1880 年,更早可以追溯到1800 年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1911 年英国政治学家罗布豪斯结论说:“19 世纪可以被称为解放主义(Liberalism)的年代,尽管深入观察那个伟大运动,其结局带来了最低潮。”⑩诗歌自问世起,就存在传播接受问题,经历了“口头传播”“书面传播”和“电子传播”三大阶段。在书面传播中,“诗选”传播非常重要,中国古代诗歌,如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和中国现代诗歌,如朱自清选编的《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都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西方现代诗歌早期,“诗选”不仅传播“诗作”,还传播“诗论”,如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就在他编的《抒情歌谣集》1800 年版序言中结论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⑪这个诗的定义是世界诗歌史上影响最流远的定义。
“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住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在这种圈子的各个关节点上都提出不同的问题;创作者提出各种心理、伦理及哲学的阐释问题;作为中介的作品,提出美学、文体、语言、技巧等方面的问题;最后,某种读者集体的存在又提出历史、政治、社会,甚至经济范畴的问题。换言之,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文学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及集体结构这三个世界的情况,给研究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尤其当我们必须为它编写一部历史时,这种三维现象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事实上,在几个世纪里,而且直到现在,文学史还是过多地局限在研究人和作品(风趣的作家生平及文本评注)上,而把集体背景看作是一种装饰和点缀,留给政治编年史作为趣闻轶事的材料。”⑫“任何价值系统都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很明显,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存在于通过转移而被重新构建的境况之中。”⑬新诗选本不仅源于“一种交流圈”,也可以形成新的交流圈,还可以通过转移而被重新构建“一种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正是“经典化”过程。如本书推崇的“现代性”,有助于重新构建“新诗”。既有学术又有思想,既史料丰富又思想先进,正是今日学术著作应该追求的境界,如同新诗诗选的选家们的最大理想是编出既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的选本。本书的内容简介呈现的正是这样的学术理想:“本书第一次将1920—2020 年百年来的新诗选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加以研究,揭示选本对新诗经典化所起的作用,强调新诗选本涉及文学、教育、社会心理、出版、传媒等多种要素。本书的研究,对于新诗、中国文学、教育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⑭
在当下数十位比较活跃的新诗研究者中,郭勇并非出自“名门正派”,与北京大学派、西南大学派、武汉大学派、首都师范大学派、南开大学派等都无“学缘”关系。知人论世,考察郭勇的“学缘”及本书的“学源”,明显发现郭勇采用了“先天不足后天补”的“笨鸟先飞”的方式,“扬长(文艺学学者擅长思辨之长)不避短(文艺学学学者缺乏文献学基本功之短)”,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国家课题,写出了这部优秀著作。
①②⑨童庆炳:《序》,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第3 页,第3 页,第3 页。
③洪球:《编者序言》,洪球:《现代诗歌论文选》,上海仿古书店1935 年版,第1 页。
④刘福春:《凡例》,刘福春:《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作家出版社2006 年版,第1 页。
⑤陆耀东:《前言》,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1 页。
⑥⑧⑭ 郭勇:《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4—5 页。第64—65 页,封1。
⑦王珂:《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教授致辞》,王珂:《三十八位诗论家论现代汉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422 页。
⑩L.T.Hobhouse,Liberalism.London:Richard and Sons,Ltd.,1911,p.214.
⑪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 年版序言》,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17 页。
⑫ 罗贝尔·埃斯皮卡:《文学社会学的原则和方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 页。
⑬Judith Williams.Decoding Advertisements.London:Robert MAClehouse and Company Limited,1978.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