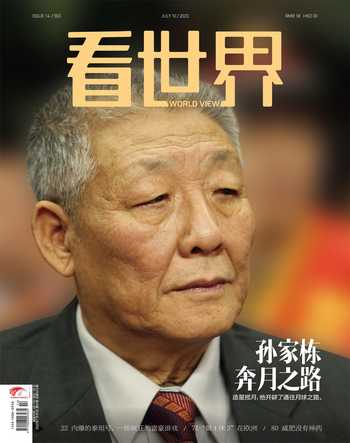费兰特:消失的作家
2023-08-26刘肖瑶
刘肖瑶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莉拉(左)与莱农
关于埃莱娜·费兰特的一切都是“自称”。
她自称是一名女性,出生于1943年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她自称对“讲故事”比对“写作”更感兴趣。她还自称:我没有匿名,我的名字不是印在书上了么(指“费兰特”)。
有多狡猾,就有多神秘,也有多可爱。
自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意大利作家费兰特从未公开过真实身份,也从不在公开场所露面或暴露自己的声音,接受媒体采访仅以书面进行,也从未在网上留下任何有关自己的照片。严谨到像一位文学界的间谍,也像江湖传说里的完美杀手,对冠以自己真实姓名的荣誉与聚光灯毫无兴趣。
我国作家钱钟书先生曾表达过著名的“鸡蛋论”,费兰特有异曲同工的表达:“作品一旦完成,就不再需要作者了。”因此,关于费兰特的踪迹,我们只能在她作品中去追寻,且真假莫辨,那些犀利而精准的、探索女性友谊或母女关系的故事,但从不落在她本人身上。
虚构让一名作家神秘,也让TA的读者如坠迷雾之境。
对读者来说,反而是在认识作品之后,作者才有了存在感。因此,对于费兰特身份的揣测、好奇与千方百计的推理,二十年来从未停止。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费兰特的代表作《那不勒斯四部曲》在文学界引发海啸,几乎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波“费兰特热”。书中主人公“莱农”,也名“埃莱娜”,与费兰特同名,生活时代也与费兰特自称的同期,都让外界对她的窥探变得更富挑战性了。
人们怀疑TA的一切。包括籍贯、年龄、身份职业,乃至性别。常被用来与费兰特作对比的那不勒斯小说家多梅尼科·斯塔诺内就曾无奈表示,他已经厌倦了“每个人都问我是不是费兰特”。
作为读者,脱离作品文本去构想作者是不现实的。那样震慑、直击灵魂的女性友谊,那样细如发的女性心理与情感,怎么可能不是出自女作家之手?因此,关于莱农·费兰特,多数人都有合理理由相信:她就是“她”,是一位有了一定年龄,对生命与时代有相当穿透力之见的女性。
书一旦写出来,就不需要作者了。

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
文学史上从始至终匿名的作家不是没有,比如长期匿名发表作品的勃朗特三姐妹,比如《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表面上是乔纳森,其实当时出版社收到手稿时,信函上的寄信人是“格列佛的表亲”。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决定将作者藏起来。
而费兰特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她生活在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近几年掀起的女性主义思潮,更将以书写女性故事为主的费兰特,推到了青年文化的热闹客厅。
不过,用“女性主义”去解读费兰特,其实相当局限。
数不清的女作家,描写女性个体的苦难与坚韧,或将大量篇幅交给她们“离经叛道”的话语与选择。但费兰特紧盯着一种刁钻而隐秘的罅隙:女性在漫长一生中不断经历与积蓄的暴力与恐惧、爱与失去、自我厌弃与堕落的强烈欲望。费兰特告诉你:崩坏是独属于女性的一种本能,自我修复却并非她们的义务。

由小说《烦人的爱》改编的意大利电影《肮脏的爱情》
她关心的,永远是心灵的指向和灵魂的切面。对女性内心世界的精准把控与情感末梢的细腻包裹,建构起一份跨越时空与民族的情感共振。她的准确,超出了作为文学创作基本要求的“词语”的准确,抵达了一种对情感纠察和诊断层面的准确,像一把手术刀,剖开我们滔滔不绝的女性主义外表,从内里找到一些难以启齿而又真实存在的病灶。
对一名读者而言,费兰特的魅力使人幻想她永生或长存,而对于一名写作者而言,费兰特对写作的解构和审视,不能不令人战栗。
但毋庸置疑的是,费兰特其人,因匿名而无限宽阔。隐藏让她毫无保留,让她的文字准确无误,恰恰是作者的消失,为创作本身留下了更宽裕的空间和自由。
人在暗处,她的文字却照向超越国别、语言与文化的一种生命共同体。
“鬼”一样的作家
文字,是费兰特本人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唯一支点。
她在1991年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书一旦写出来,就不需要作者了。”作者的结构性缺席,帮她保留及探索了更宽广的写作空间,同时,最大程度维系了故事本身的独立性。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保留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创意空间,包括技术上的可能性。”
在费兰特看来,写作是一种十分虚荣的行为。作者利用自己的经验、他人的经验,利用社会、国家、历史等等方面的经验来写作,这个过程会让写作者本人产生强烈的羞愧心理,因而想要隐藏自己,就像躲在角落里写作的简·奥斯丁。
费兰特的中文出版人索马里则认为,对于费兰特而言,写作或许会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因为你越抵达真实,真实是越想把你推开,你越会容易陷入一些虚伪,或者是因为恐惧,因为耻辱等等,没办法抵达的那些地带。”

HBO导演萨维里奥·科斯坦佐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产后的莱农
科斯坦佐既沮丧又振奋地形容费兰特:“我简直像是在与一个鬼一起工作。”
1992年,费兰特将长篇小说处女作《烦人的爱》(Troubling Love)寄给出版人桑德罗·费里,那时起她就明确提出,自己将以彻底匿名的方式写作:没有读者见面会,没有签售、沙龍,也没有当面采访。
但随着这本书被导演马里奥(Mario Martone)改编成电影,读者的关注,还是疯狂转移到了费兰特本人身上。这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焦虑与压力,接下来整整十年,费兰特都没有发表任何东西。
后来,她在接受媒体书面采访时回忆,那些年,自己“忍受着剧烈的焦虑”,但也越发明确“要将私生活与公共领域分离开”。
2006年,物理学家维托里奥·洛雷托、安德里亚·巴龙切利与记者路易吉·加莱拉,利用文体分析将费兰特的小说与大量意大利文学进行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费兰特很有可能是意大利小说家多梅尼科·斯塔诺内(Domenico Starnone)。
这一流言给梅尼科带去了一些烦恼,但并未影响到费兰特本人。
十年后,意大利记者克劳迪奥·加蒂在《纽约书评》上撰文,自称已经发现了费兰特的真实身份。证据是他从线人那里获得的一份“那不勒斯系列”图书出版方汇款记录,一位女性作者的收入获得了戏剧性暴涨,且时间与小说的蹿红同步。
但这一行为遭到了强烈的公众抗议与谴责,即便对费兰特的身份感到好奇,读者依然认为记者“破坏了乐趣”。费兰特的出版人费里也公开表示对克劳迪奥行为的震惊:“去一个决心避开公众的作家钱包里翻来找去,我认为这种做新闻的方法是可耻的。”
神秘的费兰特,本身活成了一部神秘的小说。多年来,为数不多知道费兰特身份的人,都在帮她精心维系着这个充满想象的空间,而每一位读者,都是这部小说的共同创作者,而每一位尊重艺术与文学的人,都会尊重作家的神秘性本身。
在2017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费兰特在全球不同国家的几十名出版人有一场聚会,其中,中文责编索马里后来向媒体回忆,现场“所有人都很默契,没人打听和提及这些八卦”。
为了拍摄《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编的网剧《我的天才女友》,整整十年内,HBO导演萨维里奥·科斯坦佐(Saverio Costanzo)一直与素昧蒙面的费兰特通过书面保持长期沟通与联络。

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那不勒斯
即便看不见作家的模样,听不见她的声音,但科斯坦佐依然感受到了费兰特“强烈的存在感”。她通过不厌繁多的文字对导演的剧本给出细节性意见,比如,“她不喜欢太戏剧性的处理,她希望将那不勒斯的粗鲁宴会放进剧情里”。
科斯坦佐既沮丧又振奋地形容费兰特:“我简直像是在与一个鬼一起工作。”
费兰特存在于大家都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她在多次采访里批评这个时代出版业对作者个人名气考量大于作品的风气,即首先考虑的不是作品质量,而是作者是否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用中国的语言来说,即是否有“流量”。
费兰特认为,这里面隐含了一种倾向:一个作者与他/她所有的经历、容貌、情感、性格,都将成为和作品一起打包出售的商品。
“一个作者是否可以选择,只有他写出来的东西才是‘公众的呢?”
让她真正欣慰且自豪的结果是,“我的小说比我本人的名字更出名”。一位神秘作家,恰恰是因为匿名而有了更强的存在感,主体的抽离和“消失”,才让故事真正的内核与表达得以被烘托出来。
结合费兰特笔下反复运用的一个意象,读者可以更确恰地理解这种抽离主体后腾让空间的操作方法,它是一种叙事手法,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消失”,“抹除所有痕迹”,“删除自我”。
那不勒斯的孤儿,以及疯子
那不勒斯,一座位于意大利南部的海滨城市,地势起伏不平,在城区可以看见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费兰特笔下的大多数故事,都关于或发生在此地。
她在《成年人的谎言》里这么形容那不勒斯:“在这座城市,许多大家庭把很多人连接在一起,即使是尖锐的矛盾和争吵也很难彻底断绝彼此的联系。”
这蛮像我们熟悉的中国小城镇,靠家族与血缘联结起来的某种共同体,却又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原因,这种共同体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既牢固又脆弱的黏性,可以互相伤害、撕扯,又总是能被囫囵的人际关系黏糊糊地糊弄在一起。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两位女主人公,莱农与莉拉,从一出生开始就承受着那不勒斯的诅咒和压迫—暴力、贫穷与混乱。
作为叙述者的莱农,主观上最想冲破这个世界。她不如好友莉拉聪明,却比莉拉更渴望逃离小镇,离开她母亲恶毒的眼神、街坊里歇斯底里的寡妇、热衷暴力与性的野蛮男性。
“疯女人”莉拉,蕴含着令所有体面人胆寒的无穷力量。
莱农和莉拉的友情,看起来其实有些别扭。除了原生环境,两人之间的共同点很少。她们完全不像“阳光姐妹淘”和今天被符号化的“girls help girls”,而是泛滥着占有欲、嫉妒与隐蔽的破坏。
起初,她们之间的确存在较为鲜明的所谓“命运共同体”特质,比如都曾寄希望于读书和写作来改变命运,都通过文字固守秘密,幻想逃离。在遍布崩坏与混乱的童年找到对方后,两人互为镜像,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通过不懈的、敏感而紧张的努力,莱农一步步走进了自己渴望的世界,最终变成了那种说着文雅词语、受人尊敬的一员。若放在今天泛滥的女性主义叙事里,到这里,她已足以被解构为一种自强和独立、契合女性觉醒和反抗命运的一种范式。
但费兰特从没打算以充满戏剧张力的“女性的遭遇和逆袭”作为主题,她真正关注的,永远是内在的、精神上的暴力。
莱农始终意识到自己内心的虚伪和挣扎:跻身上流阶层,在婚姻和爱情里受尽背叛与屈辱,却愈发察觉到自己长久以来的迷失。“我的整个人生,都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

《我的天才女友》劇照,莉拉(左)和莱农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莱农和莉拉童年时期是亲密的玩伴
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费兰特这么谈及莉拉与莱农之间的关系:“她们俩都经历了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女性处境发生了变化,这是故事的核心。”
从始至终,莱农都带着一种“有节制的自豪”,讲述自己成为知识分子的历程。但内心深处,她明白自己始终是那个“不接受风险,不了解命运的人”,“在角落里日渐衰落”。在撕毁一切的莉拉面前,莱农感觉怯懦的自己“就像泥潭,像吸了太多水的泥浆”。
莉拉完全不同。她没有提升阶级的欲望,也拒绝世俗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当这个地球在打破所有地域的限制时,她却越来越封闭。她从来都没坐过火车,没去过罗马。她从来都没坐过飞机,她去过的地方少得可怜。”
“贫民小镇里最聪明、漂亮的女孩”这一配置,几乎注定了莉拉命运的悲剧性,但这种悲剧是一种具有抗争意味的悲剧。她表达抗争的方式,并不是像莱农一样上进、自救,冲破阶层与泥潭,而是一种高烈度的孤独与绝望。
作为费兰特笔下个性鲜明的反叛代表,莉拉是某种特定能量的集中化身:情感复杂,心思深重,游走在道德边缘,偶尔混乱、陷入失序和崩坏。
因为天性里的倔强,莉拉拒绝向命运低头,拒绝平息。长大后的莉拉几乎“自暴自弃”,将自己的人生狠狠砸在地上。尤其是婚后,她开始不断向自己生命里的人发泄挑衅和报复,这号人物的存在,有点像中国近现代文学里热衷塑造的“疯女人”。
作家们创造出疯女人是为了嘲讽、躲避和打压她们,而费兰特笔下,“疯女人”莉拉,蕴含着令所有体面人胆寒的无穷力量。
消失,以及失踪的母亲
莉拉在她66岁这年离家出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书信、相片和生活用品,仿佛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这是《那不勒斯四部曲》整个故事的开头第一句。看上去,莉拉似乎是一夜之间失踪的,但为了这场漫长的消失,费兰特其实密谋了很久。
她提前让莉拉患上子宫纤维瘤并切掉了子宫,切除了女性身份的重要生理象征。这符合莉拉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不断念叨的,想要将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删除”的概念。
加速堕落的欲望,让莉拉对周围世界产生一种失序和扭曲的错觉,就像不断介入生命里的暴力。“暴力有自己的语言,这意味深长,尤其是在意大利语中:我要打破你的脸,要让人认不出你来!”
在费兰特看来,这些表达都是对一个人的面貌和身份进行干预,抹去她的个性。
到了第四本,莱农才终于察觉莉拉身上这层恐惧的源头。“她(莉拉)害怕东西的抖动和弯曲变形,她痛恨任何形式的病痛,她痛恨失去意义的语言。”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莱农和她的跛腿母亲
冒着被吃掉的危险,费兰特期待母亲会感知到自己的绝望。
这不是一种自杀念头,而是灵魂上的自弑。头脑聪明的莉拉,早早意识到自己命运里摆脱不掉的暴力与噩梦、嘈杂与混乱,枉然地想要参与世界,却遭到周围一切力量的压制,她始终感受到自己无依和无根的本质,如浮萍也如炸弹般存在于那不勒斯。
为了保持对自己的忠诚,莉拉只剩下一个选择—“消失”。
“消失”是费兰特孜孜不倦书写的一个重要意象。她的不少女性角色,都选择了以“消失”的方式存在或结局,亦有书名直接或间接与“消失”相关,如那不勒斯系列的最后两部《离开的,留下的》与《失踪的孩子》、出版于2006年的《暗处的女儿》。
在她笔下,“消失”表达的本质上是一个灰度状态,并非代表终结的死亡,也不是象征希望的释怀,而是犹如未完成的逗号那般,将一切痕迹从这个世界上抹除。
费兰特不仅让莉拉消失,也在第四部里让她的女儿失踪,仿佛一个轮回。
或许有些出乎意料,“母女关系”是费兰特自认为的几乎所有作品的核心主旨,不是女性友谊,也不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我没有写过母女关系之外的话题”。
她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主人公莱农设置了一个令人厌烦的跛腿母亲。她阻挠女儿读书上学,对一切不耐烦,后来莱农结婚、生子,母亲也总是站在莱农的对立面,让后者歇斯底里,让她绝望和崩坏。
“消失的母亲”,本身也是费兰特笔下反复出现的,关于“消失”的重要设定。
《失踪的孩子》中的勒达,小时候常被母亲威胁要抛弃她离家出走。而当勒达长大后,自己做了母亲,却兑现了母亲的威胁,在两个女儿分别长到六岁和四岁时抛弃了她们。

《暗处的女儿》同名改编电影
后来,勒达遇见了一位令人窒息的年轻母亲尼娜:不论走到哪里,尼娜都带着她未满三岁的女儿和一只布娃娃,尼娜总是微笑,充满耐心,满足女儿所有幼稚的、反复的要求。女儿则会假装布娃娃怀孕了,打算给它吃药。
在勒达眼里,尼娜、莱农、布娃娃,构成了一种畸形但“完美”的母女关系缩影:将自己完完全全、毫无怨言地奉献给孩子,沉浸在对母爱的美妙幻想和赞誉中。
在更早的《烦人的爱》里,“我”的母亲在离家出走后离奇死亡,而“我”却在母亲的葬礼上暗暗流下了经血。一种不受控制的难堪和难受,伴随着一股“恶心与眩晕”,这是女性的独特体验,它以一种不可回避的突发感,逼迫人记住当时场景的现实和譬喻。
2003年6月,费兰特在回答《目录》杂志提问的信件里,第一次展示了一部分自己的故事。
她的母亲很美,美到激起了父亲畸形的占有欲。家里常常因为母亲的出门而爆发激烈争吵,活在恐慌与不安中的费兰特,既无法保护自我,也害怕家庭战争,她更害怕母亲真的会像父亲假想的那样,打扮得明艳动人,只是为了离开他们。
然而,母亲最终还是出走了。九岁左右的费兰特将自己关在狭窄的储物间里,嗅着杀虫剂的味道,想象那里面住着吃人的苍蝇怪。冒着被吃掉的危险,费兰特期待母亲会感知到自己的绝望,然后在母爱的驱动下回来找她。
与鲁迅抛出的“娜拉出走后怎样”这种社会层面的拷问不同,费兰特笔下重复的“母亲出走”,侧重于生命的忽然崩坏和坍缩,无关家庭结构,也无关子女之爱,而是一种历经痛苦的心理动机的外部实现。
关于女性主义有一句较为主流的说法是:女性是一种处境。

《成年人的谎言》改编剧集《成年人的谎言生活》
费兰特的中文出版人索马里对“界限消失”这一意象的理解,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层次地剖析费兰特笔下抽象的母亲与具体女性之间的关系:“与女性身体相关的血液、精液和出生时我们身裹的羊水,其存在都意味着界限的消失。”
删除自我,抹除痕迹,一种“在场”与“离场”的对抗。本质上,都是女性对于自身根基认知和判断。
女性的回声
目前,关于女性主义有一句较为主流的说法是:女性是一种处境。
近年来,它被日本女性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通过书籍提出,但早在这之前,无数文学及艺术界都曾以各种方式共认着这一点:女性象征一种存在的形态,作为性别概念和作为群体的她们,都离不开整个时代与社会对她们的包裹与挟持。
费兰特书写的女性,并不直接、固定地处于某种单一或集合的处境里,而是在一种流动的境况下,洞察主体内外的无数种细微变动。
“我故事里的女性都是真实的女性回声,她们所经历的痛苦,她们的抗争性,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想象力。”
不过,在费兰特刚开始发表作品的九十年代,“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成熟,她只是诚实地、尽情地,袒露了自己的女性视角、女性心声。
莱农与莉拉的故事原型,与她前几年去世的一位女性朋友有关,但后来费兰特渐渐有了私人的“库房”:“很多难以控制的女孩和女人,她们的男人、环境想压制她们,她们虽然精疲力竭,但依然很大胆,她们总是很容易迷失于自己脑子里的‘碎片中。”
“碎片”(frantumaglia),这个词语也是费兰特母亲教给她的。“当一个人遭受各种矛盾情感的折磨时,她内心一团‘碎片。”神秘的“碎片”使人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同时,也会引起那些难以名状的痛苦。
“我们女性是坚强的、有智识和自尊的,她们明确知晓自己的权益,但很多时候她们会被一些意想不到的困境打倒,会向一些微小的、狭隘的感情屈服。”
《烦人的爱》里的主人公形容自己,“我身体里的一部分一直都很警惕,防止另一部分崩溃”。“我害怕身体会背叛我,我带着一种自毁的冲动吐了。这种冲动是我小时候一直很害怕的,长大后我一直试图控制自己。”
作者的消失,为这份诚实留下了广阔空间。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莉拉的婚纱照
这种一击即中的描述,不直接关于女性的独立意识,不关于向上的、理想化的阶级提升,而是一种线性的,不断波动的意识回流和自我否定。
它更诚实,也更精准。
不少女性读者对费兰特产生的最强烈的共鸣来源于此,甚至超过了终身联结的女性友谊:我们不断审视内在的自我,又不断在外界的粗俗里陷入自暴自弃的欲望黑洞,在人生不同阶段,总有各式各样的混乱和迷离拉扯着我们。
如果你立誓自强,似乎便再也不能渴望爱。如果打定主意挣脱命运,冲破牢笼,却似乎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童年、故土这些东西在自己体内留下的痕迹。不知为何,我们永远无法坦荡,无法不对未来担忧,不对过去耻辱,总是时时刻刻忍受着撕裂与冲突。总有各式各样的心碎,如碎石走沙一样嵌入我们的命运里。
就像费兰特在访谈集《碎片》里这么解释的:“她们(女性)的痛苦源于周围环境,过去那些女性的遭遇和她们期望的未来同时出现,像影子、幽灵。”
下坠的欲望、抹除一切的欲望,这是一种暴力的女性表达,一种女性独有的,不可以共享与互通的情感韧度。
费兰特捕捉并放大了这一点,它更本质地掀开了女性主义的一切障眼法:那些横亘在眼前,看似可以通过文化与法律来解决的问题,没办法触及内心那些建立在代际、历史等矛盾上的伤痕。
在费兰特看来,反复书写同一类主题,是一种“对痛苦的清算”。“人生的痛苦总有一些相似性,存在的伤痛无法治愈,你不断写作,就是希望迟早能写出一个故事,对一切进行清算。”
“清算”,不知道这个词语在意大利原文里的文化表达与概念,但至少它让身为中文写作者的我如壶灌顶,凛然一惊。
总有一些主题是被重复书写的,看似雷同,却并非每一个写作者都能做到绝对的诚实和彻底。
作者的消失,為这份诚实留下了广阔空间。诗人济慈曾说:“诗歌并不在诗人身上,而在于写诗的过程中,语言的转化和具体的写作。”这句话给了费兰特很大触动。她认为,作家本来没有身份,“唯一重要的身份是读者在阅读时,作品中散发的、他所呼吸到的气息”。
责任编辑何承波 hcb@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