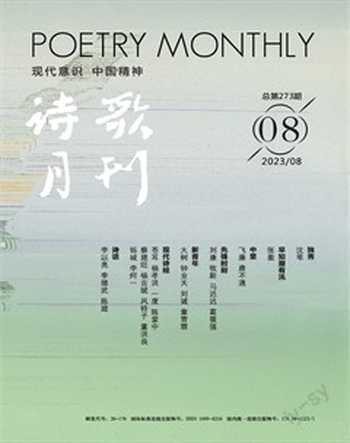猛兽与主角
2023-08-26陈建
陈建
20多年前,我写过一首关于工程师的诗,工程师的状态被我写得生猛又忧伤,大意是我可以随意弯曲、折叠钢铁,装配出一只只非碳基的猛兽,这些猛兽假装驮着人类前进,随着我的忧患意识随时可能反咬一口。实际上,我只是拖拽着鼠标的光标在屏幕上罗列着点、线、圆。当然,从显示屏的二维世界看过来,我的手势动作有可能类似画符,一副妖道作法的状态。
如此之后多年,我再没写过自己职业主题的诗,尽管我依旧生活在画图的职业之中。刚工作时,时代正从手绘向电脑制图转移,我赶上了那种几百年传统的最后几天——对着大型制图板“爬图纸”。但就时间赋予的结果来看,电脑制图除了出图量有指数级的提高,工程师依然是手工艺人,依旧付出同样的秃顶、腰颈椎病、老化散光以及腱鞘炎……
对了,我的职业是:产品研发,这是工牌上标明的。工牌很有意思,戴在胸口,向公司或客户标示我是谁。在日常生活中,我好像没发现还有什么别的事物具备工牌这样的直接性。它直接定义了你的职业,它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也兼示隶属与阶级。它是行为模式中规范化的一部分,是法与令最基本的表现形式。陌生的同事间偷瞄一眼对方工牌,然后给出相应的言谈举止,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工位上时,我时常感到我是一颗活字印刷术的字模,当我的手放在鼠标上时,秘不可知的系统会自动将我使用,构成它需要的句式、产品。朋友们有时候说我的诗设计感很强,反正在褒贬不明的情况下我一般把这当作赞扬。毕竟,我在设计那些猛兽的间隙,在它们一去不返、满心油腻、偶尔回头的垂涎瞬间写诗。
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说作为一个自我定义的职业诗人,我也企图认为我的工程师职业根本影响不到我的诗歌写作。毕竟,一方面是按部就班、规则、准确、以產品安全性为第一的蓝领设计。另一方面,从诗人的角度来看,世界毫无浪漫,繁复无序,而诗人却企图用几行作品清晰表达这个世界内部的网络。当然,这种分裂完全合理于人类的常规行为,并没有异于上班下班这种日常方式更多。
任何有文学艺术倾向的人,都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世界改造一番……编程出专属于自己的世界。比如我常把人们对利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误读为笑话,以之幽默我的平衡。十分准确地说是我对那些庞大、天经地义、巨塔一样的典范缺乏恭敬。面对雕像五体投地的人,我很想扔去一个啃过的苹果。我旁观的姿态决定了我总爱在暗处冒点想法,并陶醉于语言中的冒犯。
在40岁那年,我自印了自己第一本诗集《断常诗》,扉页上颇为自豪地留下几个致敬:
谨以此集向拼尽一生,只求一无所获的先行者致敬
向应有之物,绝不严重致敬
向无关指证无限致敬
如今,快要过去10年了,我开始为我的无耻担忧,毕竟,口号喊得太响了,手上的技术却有些拉胯,根本配不上致敬。我的朋友游太平先生颇有先见之明,他赞美过:此论出自往圣,贤弟溺得逼真!他是对的,他深谙自我的潜规则,即:每一个较真的诗人,都注定把自己驱向语言的战场。
1994年的上海,我刚开始写诗。整整一个冬天,凛冽而微腥的海风中,我自觉行走云端,轻盈而高大,枯燥如水泥地都生动而透明——我深刻怀疑自己因主角的独特性而被神启……而事实证明,那与青春有关,与生命的浓烈有关。当然,多年之后,当诗已沾染爱恨情仇、生与死、混乱与秩序、浮肿肉身,我又固执地认为:让你体验天空,是为了将你陷入大地。
看嘛,这种自珍自爱多么坚忍不拔,同时充斥着人性的钻石与污秽。我们给了自己暗示的火箭,以慌乱的加速度来脱离下坠,于是有人当了真,有人拼命满足它,有人被现实打了两个耳光后发觉自己是刍狗,有人眼睛睁得更大,有人把它忘了……反正都是一副智商欠缺的人类状态。
事实上,在通常的职业上满足自己的独特性和试图成为一个更好的诗人在生命层次上又有多少差异呢?想清楚这点,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区别于懵懂的本能,虽然其结局并不一定比懵懂舒适。嗯,我其实没说为什么写诗的问题。
胡戈·弗里德里希在《现代诗歌的结构》里非常粗鲁地说:“不和谐音的张力是整个现代艺术的目的之一。”其实他是在说自波德莱尔以后,抒情手段向现代性技术文明的转向,在技术化与商业化的文明中,诗歌如何成为可能。然而,米沃什对象征主义引发的诗歌导向非常不认同,他抨击了现代诗学的一个宗旨——“认为真正的艺术不能为普通人所理解”,最终导致诗歌在“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上沦为小丑。
现代性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单一的手段和技术很难完成我们的时代复调,相互争议的语言方式恰恰是诗人们散发的触角。但基于勇敢的诗人注定要去抵消神圣的律法这一基本事实,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显著特征,即我们所处的文明,在信息量表达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在生活节奏行为范围上,我们已与几千年来的人类不一样。百年来,新的文明方式几乎是瀑布一般倾泻在人们面前,我们的思维、身体在这瀑布前其实呈现了大面积的迟钝。至于诗,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主义兴起,诗歌的语言方式从经典的抒情感性移向了复杂的理性构建,这属于合理的逻辑。我说的不是什么语言上的赶时髦,甚至这都不算时髦,我说的是诗人这种人类古老的职业为何没有消失,甚至在未来也不会。嗯,我其实也没说怎么写诗的问题。
诗人与工程师大概是“本质的自我”与“存在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它们一个与人性特有的东西有关,另一个与生存的物质框架有关。这两种自我的关系,其实在人类中具有普遍性,它并不因诗人与工程师两种职业倾向显得特殊。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处在这样相似的心理格局与现实框架中,并出于理智、出于责任,去完成自己生命中理所应当的那部分。生存其实本就是精神关系的试验室。这种试验大概率上谈不上成功,当然也很难定义失败,它只是一种试验的进行时,一种呼吸的状态,且只能用开始或结束来概括。
那么,朋友们认为我的诗有设计感应该是对的,毕竟是一个做设计的工程师嘛。设计的思维方式必然在我诗歌的搭建方式中露出得逞的笑容。其实设计有一个更美好更庸俗的词语:创作。但我对这个词天生有些敬畏,这个……还是莫高估自己了。
但设计并不能完全注明一首诗的诞生过程,于我而言,如果一首较长的诗,大约在它的前期是有设计的,但往往随着诗行的不停增加,建筑物会产生自己的美学需要,甚至开始产生自发搭建新结构的能力,这大概是诗人最幸福也最痛苦的阶段,因为你从语言的浑浊中把它打捞起来,它开始长得不像你想象的样子,但是又是多年后你喜欢的样子,它是活的,它在你手上摆动、挣脱,将伟大的力反馈给你。
幸运的是,在美学价值上,诗的意外往往会大于标准化的设计。对于工程师,标准有最基本的本能:更简洁、更高效。标准是工程师最喜欢的工作界限,在这个界限之中,所有猛兽都按程序驱动,规范而无害,猛兽的一切行为都在预设的极致之内。但于诗人,最好的方式是遇见标准,然后再笨拙地翻过去。当然在此之前,诗人呕心沥血的,只不过是为了抵达那堵标准围墙的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