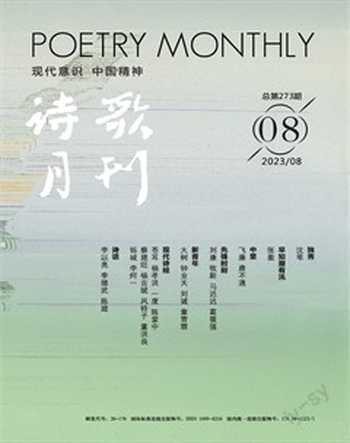我唯一认同的身份是诗人
2023-08-26李德武
李德武
我羡慕那些一生不用工作,一心创作的诗人。这样的诗人要么出身富贵,家境殷实,要么有贵族供养,前者如拜伦,后者如里尔克。但这样的诗人实在太少。古今中外,绝大多数诗人需要工作,尽管他们从事的职业不同。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入仕者不在少数。古代诗人的精神高度和诗歌抵达的深度是否与入仕有关呢?我没有做过考察。前两天我拜谒了黄公望墓。作为画家和诗人的黄公望一生都在官府和道观之间往返,最后皈依道教,出离尘世,融生命于山水和笔墨之间。按照德勒兹的理论,入仕让他看清了人世的边际线,山水为他提供了逃逸线。这种先入后出的案例在古代诗人中屡见不鲜,著名的还有陶渊明、王维等。
以上案例,让我们看到写作和职业的对立性,有的诗人把这种对立性表述为“生活妨碍伟大”。有的诗人却把这种对立性转化为精神的放达和创作独有的机缘。现实的困顿和窘境对小诗人来说,无疑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对于大诗人来说,显然是创作出不朽杰作的良机。比如,一生颠沛的杜甫。当然,也有写作和职业相得益彰的案例,比如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博学以及他诗歌迷宫般的叙述与他做图书馆馆长不无关系。正如他所说,图书馆里储藏的不仅是图书,还有时间和无尽的人生,一座图书馆也是一本没有扉页和封底的“沙之书”。
也有写作与职业完全不相干的案例,比如美国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他的职业身份是医生,而他的诗却并不以“诊疗”见长,而以“不抽象思考”的直觉见长。有些“逆天抗俗”的现代诗人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也惊世骇俗,比如兰波选择远离城市,到非洲贩卖军火,他的兜里经常揣满做交易的金子。加里·施奈德选择了到山野间过一种近乎原始的隐居生活。在当代,有些诗人不想委屈自己,选择以画养诗。正如唐伯虎当年说的那样:“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当然,基于对诗歌教育的重视,诗人受聘为大学教授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奥登、布罗茨基等。诗人的天性是自由,但我们也很少看到一个缺乏生命根基和现实担当的诗人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今天的诗人不像古代诗人享有至高的荣誉和尊重,面对现实,诗人要想活得纯粹就需要独自完成人格和语言双重净化。就像一颗蒙尘的珍珠,诗人一方面需要在尘土中保持自己的光洁;另一方面,还要努力从尘土中获得呼吸和力量,以便有能力擦去覆盖在自己身上的尘埃,显示出诗人的本来面目,放射出语言的耀眼光泽。就此而言,一个诗人的生存压力远比一个普通人要大得多,也更辛苦得多。因为,诗人在获得肉身基本安顿后,还要耕耘词语,在更大的荒芜中播种诗意和光明。且这样的播种是以无回报为代价的。诗人尽管也像普通人一样吃饭睡觉,但他们的价值观和幸福感已非普通人可以理解。诗人需要职业,有时就像一艘船需要压舱石,使他免于滑向轻浮流荡。
当然,敏锐的诗人总是能够从他所接触的人与事、事与理中获得独特的诗性启示和诗歌语言。反过来说,什么样的职业是诗人最不能接受的,或是需要保持距离和警惕的?我认为就是对他的诗性语言具有破坏力的工作。诗人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最终表现为语言的独立与纯粹。我们对那些具有多副面孔和带着极强功利心诗人的语言总是持有怀疑。他们不是因为虚假和伪装而受怀疑,而是他们的能力太全面了,太全面了就不像一个诗人。一个优秀的诗人往往表现出某种现实能力的欠缺,他因为不全面而真实,他因为不完美而纯粹。
今天的诗人指望不工作还能活得有尊严简直就是神话。选择做诗人不是选择一种职业,所有职业诗人都是可疑的。如果说工作或职业是一种谋生手段,那么,诗歌就是对这种被动的束缚予以解放的内生力量。又何况,作为纯粹的语言,诗歌语言是多么排斥来自外部的指令。我认为今天的诗人要保持尊严首先要能够自养,一个有骨气的诗人不能吃嗟来之食,也不能弄到食不果腹,而要基于诗歌的自由独立精神,先活出人样,再活出诗人样。
我的职业经历可谓丰富。最初我并不是基于要做诗人而选择职业的,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选择就读测绘专业时压根就不知道测绘是何物。毕业留校教书也基本属于服从分配。我选择诗歌写作和我留校工作密切相关。就在留校的第二年,我萌生出对测绘专业的厌恶,那时,我就把一生的追求转向了诗歌。但我也要感谢学校的环境,它给了我阅读和创作的空间。如果我不是在学校工作,可能现实的残酷性也容不得自己如此任性。1998年我被学校从测绘工程系调到基础部教大学语文和写作课,算是圆了梦,就是实现个人兴趣和工作的统一。这段时间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基本不用为生存发愁,也没有过多的物质欲望,在教书、阅读和寫作中贯穿着我对诗歌的思考和探索。
这种稳定的生活在2002年被打破。这一年出于对苏州的向往,我举家搬迁到苏州。作为人才引进,我从学院调入政府部门工作。起初我也满怀热情和自信,想在新岗位上干出点什么,但渐渐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个环境。我开始担心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纯粹性问题。我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了离开。这次离开让我由参加工作以来对生存无忧无虑突然变得一无所有。
2003年初,我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起初我的想法非常单纯,我认为依靠自己的文笔和才华,自养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写作和挣钱糊口这两件事便扯到一起。我收集了国内一些报刊信息,开始写随笔到处发。的确,我靠着写稿获得了一定收益。但当我每寄出一份文稿就期待稿费单时,我发现自己内心的卑微和龌龊,我痛骂自己在侮辱文学和诗歌,侮辱一个诗人的荣誉。我深深醒悟到自己写作动机的不纯,文学不是供我吃饭用的。当然,这之间我也接了某出版社长篇小说的约稿。我开始了自己最不擅长的小说写作。假如我不附带有挣钱的目的,写小说也不是问题。可一旦附带着这样的目的,我就被自己的质疑所打断。这时,我意识到要保持写作的自为、自由和独立,有一份合适的工作必不可少。因此我放弃了继续做自由撰稿人的打算。
2003年,在朋友帮助下,我面临两个职业选择,一个是去学校继续做教师,一个是去保险公司做管理者。基于我当时的脾气和认知,我的第一选择毫无疑问是去做教师。学校工作环境单纯,能够宽容一个诗人的任性,最主要的是多少能够懂得一个诗人的价值。在学校,一个诗人还可以凭借诗人身份获得尊重,但在保险公司,一个重视绩效和服务的企业,诗人如果以此自居是没有存在空间的。但命运总是有意考验我。2003年6月,我竟然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一做竟是19年,直到2022年退休。
我选择接受这份工作主要出于两点,第一,薪酬高;第二,史蒂文斯不也在保险公司工作吗?前者让我放下了文人的清高,我靠劳动换得薪酬,没什么不好;后者让我免除了担心,史蒂文斯没有因为在保险公司工作而影响他在诗歌上的成就。我说服自己接受这份工作,并不断从工作中发现自己人格、修养、学识、能力上的不足。特别是通过做服务学会了低调做人,克服了自己身上因为写作养成的傲慢气。
但是,平心而论,保险职业生涯对我写作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甚至因为工作繁忙,以至于我从2003年到2015年,十几年时间几乎没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其间,2005年我曾萌生出为写作再一次辞职的念头。那一次,在西山的雕花楼里,屋檐的滴水启发了我学会顺势而为。2022年退休后,我退出了所有与保险相关的微信群,删掉了曾经与我做买卖的合作人。我和保险作了告别。40多年来,我变换了很多工作,印过标有多种头衔的名片。我很欣慰,现实的浮华没有改变我。今天,我唯一认同的身份还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