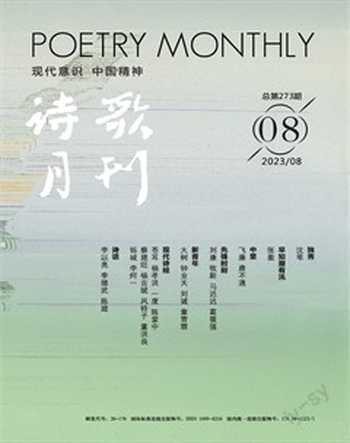挂车河野史(组诗)
2023-08-26苍耳
岱鳌山中
苍莽的草黄深处,大片野菊
把钟摆停掉。仿佛我们遗忘了
那些蛮荒的岁月。但这只是一种假设
脚扭了好比喝醉了,一旦走成习惯
悟道便遥遥无期。事实上
积年的腐叶远没有我们速朽,如同
把野猪列为保护动物,便自以为
梦境会长出好看的獠牙
三县界碑提供了一种尺度。谁相信
那个土地测量员能走出城堡?跟它拍照
意味着把自己一分为三,标上
“桐枞庐”三地之名。当然,不要忘了
乱荆丛中,火炭似的小野柿提供了
另一种尺度,仿佛有人从未受骗过
青岚袅袅四起。时间飘来荡去
想想看,山风才是制定法则的始祖
一座建筑稳坐于巅顶。但住在里面的人
会为我们敲下那么甜软的柿子吗?
挂车河野史
挂车的河潜行于江北之旷原
众多龙骨水车是它的脚
亦是它的翅羽。荷花开得多美呵
它在雨蛙孤鸣中认出了我
一道涸辙隐入杂草,它证实
我的前生曾在其间挣扎
河滩如此开阔,恣肆无章
哪儿去寻挂满战车的遗痕?
什么多隆呵、陳玉成呵,不过沉入
河心的系马石而已。堤上有青牛
无绳无轭,充任河之思想家
可是还有谁能听得懂
青牛的真言?当智者和愚者
兴冲冲赶马车而来,河拒绝“挂”它
智者败兴,看见牛屎饼
贴满农舍破败的土壁;愚者
终于认出:马即牛,河水即野草
我也好奇。假充观星空的人
赶第一场春风,却一无所获
半夜忽闻咕噜咕噜的车水声漫卷而来
懵然坐起——直觉巨流横贯我而去
无上无下,无内无外,汲我
如牛粪里的一粒草籽
他在冬夜离去
——写给父亲
他在冬夜离去。零点十五分
双腿还会再度冻伤吗?这不是某处
但霜降从未停止。他的身影被不同的
闪电所交织、分割。我从乔木公社走到江边
走进雪暴深处。他说:不要跟着我
我停下来。白色床单像一生的黎明
黑衣役者从城西朝这边赶。逝水在上涨
慢慢把他抬高,隐去面廓。巨河把他带走了
仿佛三官殿李村的一条船。芦苇柔弱,一根根
镂出夜之深度。他说:心寒。我渴
电梯门开了又闭。最后的灯火青荧
历史像曝光的底片。他在掩体里
一动不动。三个黑衣役者
加上我,执行这严冬的密令。而他想必听见
申诉者与断桥在交谈,以及声声鸟鸣
白色走廊尽头。当年笔下的负伤者
再度从弹坑边被担架抬走。他是边缘人
余生只采访自己。被命运刮掉的鳞片
在河底闪闪发亮。苇丛像灰皮书
在风中翻动。风说:影子长成了树
云泥同时飞翔。下弦月隐去
道路弯曲若闪电裂空。巨河波光闪耀
而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光点
河说:那枝笔已在岸边发芽
逝舟与礁岩共存。监护仪里的地平线
不再抖动。他开始逼近那丛野菊和群星
乔木飞黄,长桥蓼蓝
若非松鹰,还有谁划过这霜野的笔记本
采访蒲公英将从冬至开始
初冬的酒糟气息
这个镇子像姚鼐那年写下的句子
秋深了,你说河流看似不流
一阵风便吹来了酒糟的气息
龙眠山因此不眠。粮食酿出的酱香
不似意识形态可以强制发酵,然后
装入蛇形的瓶子。那天下午
我钻入巨大阴暗的酒窖,像封缸坛子
你说古法酿制让武松一跃而起
倘灵魂部分醒来,也不至于
被蒙汗药合谋算计得太久
但酒量还是被虚高了,因为你
常醉于假寐,而迷于水话连篇
桃花盛开被说成桃色事件
所谓谣言,竟飞絮般落地为实
酒甑蒸腾不已。酿酒师终于说出
早年品酒曾被蝇矢和蝶梦扰乱过
不必说了,醉鬼似的光阴最后成了品酒师
而一旦候鸟分不清南北,岩羊失却自性
如同方苞一度晕眩于皇城飘满红叶
美于幻美,而丑于丑陋
那支秃笔如何摇动并发出酒糟的气息?
苍耳,作家、评论家,著有随笔集《纸人笔记》,散文集《一阵风吹来稗子》《内心的斑马》,文学理论专著《陌生化理论新探》,现代诗学论集《徜徉在语言之途》,长篇小说《舟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