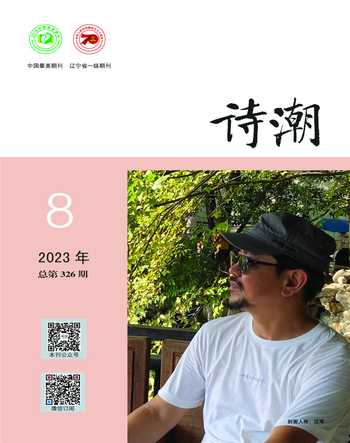为尘世打磨智慧的钥匙
2023-08-23空灵部落
空灵部落

写诗是危险的,其极大的诱惑性往往使人孤独终老。如果穷极一生来写诗而又神清气爽不后悔,那必定是诗道中人的强者,在生存的困境之中具有逢凶化吉的真本事,并对诗歌富有沉潜一生的终极梦想。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新泉正是这样一位使人敬仰的著名诗人。最近,他以82岁高龄将过去的诗歌作品精选成集,既是一次对生命回望的诗意总结,又是对诗歌来者的友情馈赠。
张新泉,1941年出生于著名的“才子之乡”富顺县。其早期从业异常艰辛,在江码头扛过包、船头前拉过纤、火炉旁打过铁……都是底层劳动者无法可选的活路。诗歌是他的倾情之星、希望之星的星星之火,写诗改变了他的命运。读他的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劳动者的气血、平民阶层的生命感与质朴的民间立场和视角,真实而动情,尤其是在人们难以决策“写什么”这个困惑问题上,给人以示范和启迪。在漫长的岁月中,诗人们对平民生活视而不见,他却在写《渔人》《一个盲人在爱他的孩子》《带伤的人》《带红枣的人》《剃头匠》和《韩二哥走了》等等。这些诗作既是诗人维系情感之需,也是诗人立命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虽然自选此类的诗还不够多,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漂浮之物,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坐标,是诗人写作的根基,其诗也就有了辽阔的气场和旺盛的生命力。诗人曾在《烤薯店》一诗中写道:“我想我注定是民间的土著”,并用隐喻写了一首《在低处歌唱》,充分表明了诗人的精神维度,并由此倾情呈现了诗歌的生命底色。
生而为人,识天识地识人是人的生存之道。张新泉着力将人生阅历和生命感悟写入诗中,特别是在物象之中挖掘诗意、顿悟生命、思辨哲理,如《好刀》《好人》《好水》以及《文火》等佳作,收获颇丰。而以《好刀》为主打诗的诗集《鸟落民间》(成都出版社,1995年)更是荣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笔者有幸珍藏了这部诗集,之于我,它是一个标杆的存在,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诗人对“好刀”秉性的深入挖掘,有了前人未有之发现:“好刀在主人面前/藏起刀刃/刀光谦逊如月色/好刀可以做虫蚁/渡河的小桥/爱情之夜,你吹/好刀是一支/柔肠寸寸的箫……”好刀的刀性乃手握刀柄之人的人性,鲜明的象征意义将好刀作为好人的标准,于数十年的功夫,岁月打造了诗人“好刀”的形象,确乎已经人诗合一,使诗人张新泉与“好刀”互为镜像。而之后的《文火》则是表现社会意识的处世之道。之于水,有细水长流、滴水穿石;之于火,“所谓文火/即是火中智者”,以攻心为上。也许,一个曾经身为铁匠的诗人,不可或缺地对铁与火有着深入骨髓的情感和毫不意外的另类思考。
诗歌是孤独者的言寺,也是一个人的宗教。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一书中明确写道:“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面对自然,诗人张新泉是如此禅定。他以自我的身体与思想去度量自然、认识自然、理解自然,从而“道法自然”,以及客观地反映社会的现实存在,坚持以小博大,真诚走心,面对千山万水显得镇定自如。如《过江之鲫》《缘分》《骨子里的东西》等等,诗人从自然的生息之中摸到了生命的命门,由此打开了生命的空间而豁达、宽容与仁慈。诗人常常专注于某一对象物,深入其内部,进行灵魂体验与感悟,去获得并展现独有的认知,不入派、不站队,独辟蹊径,自成一路。诗人不是从上而下的“社会实践”,而是生于乡间,在主观上隐于自然与社会的生命体,从诗歌的小径走向四川省作家协会,并任《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直至退休,阅人无数,更阅诗无数,对诗歌传统和西学没有照搬套用、移花接木,而是坚持己见,成竹在胸,一路将诗写成了澎湃的江河。在《牛吃草》中,诗人绘声绘色写牛吃草的过程与细节,牛与草各自内心的变化与态度。他并不是去寻求盖棺定论的结果,对牛来说,结果与人的命运一样。在东方诗学中注重生命的过程而轻结果。因而你看到了牛对吃草过程的享受,以及草被啃过的愉悦。诗人以禅宗觉悟的方式去呈现大自然的道理,去顿悟庄子的“游鱼之乐”,这与“牛吃草的欣喜”有异曲同工之妙。
读张新泉的诗,必然会注意到,诗人对人生命的终结之死亡甚有研究。人生不过百,这是生命的归宿,也是自然注定的宿命。尊崇自然之道,紧握直抵终点的单程车票而沿途观看风景,乐意将余生再续诗歌之路,彰显了一个诗人的执着和定力。也许,诗人灵魂的超脱异于常人,的确能坦然面对死亡,如《冥衣铺》《送一个人去天国》《陪母亲去墓地》《我的葬身之地》《太平间》等等,乐此不疲地写到生死而泰然处之。他在《宿命知道》中仿佛在告诉人们,该来的终归要来,生命中没有省略模式。他写《活着》:“越活越旧和越写越淡/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写得再黑,最终都将归至无痕/活得再久,骨灰盒的形状都不会变”。《在墓地打盹》更是直接表现了诗人正视死亡的心境和直面人生的妙趣:“在墓地打盹//约等于/为长眠热身”。面对历史长河,应该说,读史即是阅读死亡。正如诗人的名句“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一样,其艺术表现力和对灵魂的冲击力都不可复制,也不可多得。
张新泉的铁匠生涯对写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诗歌的生命气息具有明显的打铁节奏。其语言多有金属之声,具有雄浑、劲健的力道和一锤定音的效果,而诗以短句见长,以口语直接表达,阳刚、率直,敢于亮剑,将诗作为阳光下的事业,见人见事见心境。正如《撕》,一个动词的背面是人性的惊涛骇浪。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工作者,太清楚白纸上的黑字意味着什么:“笔使纸张获罪/纸在无法解释的绝境/被撕得叫出声来/文字的五脏六腑/散落一地……/人对纸张行刑时/是一种比纸更脆弱的/物体”。他明确地告诉你:“撕是一种暴力”。确乎每一个动词后面都隐藏着暴力,自古以来概莫能外。张新泉在《骨子里的东西》一诗中写道:“这种东西/不太好说/因为深及骨髓/关系骨头的名誉/……/我们敬仰的/美德和品性/也住在206块骨头里/与之相逢/是我们的福分/它们阳光一般/使生命神清气爽/气宇轩昂”。面对八方而来的诱惑,要珍惜生命,走好自己的路,人的一生就这把老骨头,需要“美德和品性”塑造“气宇轩昂”的傲骨。诗集中有大量态度鲜明让人警醒的诗歌作品,也是铁锤下的扛鼎之作。
何诗可以留世?诗人自有答案,其选入的都是深入詩人灵魂与骨髓的诗,是使诗人彻夜无眠,甚有自我写作冲动的诗。诗人自律以民间立场和视角为其诗道。他在《民间事物》中告诫自己:“向民间的事物俯首/亲近并珍惜他们/我的诗啊,你要终生/与之为伍”。我们敬重有根的诗人,民间的智慧与力量是诗歌创作的源泉与动力。艺术都是相通的,即便西方美学的“真、善、美”也同样能在东方诗学中找到答案,这在张新泉多年的诗作中随处可见。数十年的跨度,这个诗人和他的诗歌,已经成为一个用诗歌构建的生命体,既有其现代性,也有时光雕刻的印痕。张新泉在《自画像》中写道:“已是资深老年/却迟迟未能痴呆”。这便是智慧,这便是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