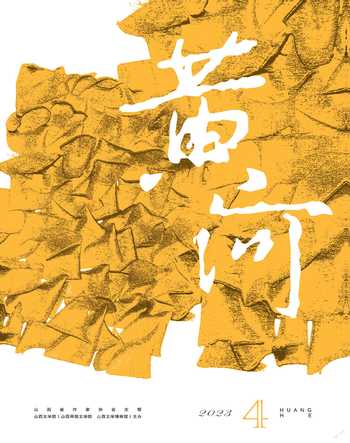桥上的舅舅
2023-08-22许建国
许建国
一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畅想外面的雪。一朵朵,一片片,扭着秧歌下来,不小心撞上,又扭着秧歌分开。到地上,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挤在一起说悄悄话。我喜欢雪,相比于阳光和雨,雪地能留下鲜明印记。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东西能留下印记呢?没雪的日子,我盼雪。打记事儿起,每年都数着下雪的次数,一次也没落下。下雪的日子,我就扑进雪地里,丈量自己的身高。直到现在,年过半百了,仍然像个孩子。可以说,是雪看着我长大的。
手机突然响起来,我划开屏幕,喊一声舅舅。舅舅,下雪啊,你咋还没睡呢?舅舅喘着粗气问,你在哪儿?话里充满酒味,隔着屏幕也能闻到。下雪嘛,我在床上。酒味飘过来,没有说话。我说,舅舅,你有啥事?你说。舅舅说,我没得啥事,我要日噘你。日噘是方言,咒骂的意思。事实上,我是跟着舅舅长大的。亲舅如父,舅舅日噘我,便是日噘他自己。啥事惹恼舅舅,让他直言不讳要日噘我?我不敢相信,又重复一遍,舅舅,你有啥事?你说。舅舅恶狠狠地说,你个白眼狼。我松一口气,这个日噘沾不着他自己。
我生下来十九天,还没满月,母亲和父亲为一碗豆芽汤起了争吵。当时的父亲不是后来的父亲。后来的父亲与我确立父子关系是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生下我,缺奶水,我饿得嗷嗷直叫。母亲看木盆里有豆芽,泡了三天或者两天,嫩芽刚露头,遂小心抓一把,煮了一碗豆芽汤。当时的父亲挖地回来,看见冒着热气的豆芽汤,没把挖锄放地下,而是直接撂到床上。幸亏我小,脑壳刚好卡在两根挖锄齿之间。拿挖锄的人,日噘人像挖地一样下力气,急作包、败家子、懒婆娘、丧门星劈面而来。母亲给我塞几块尿片子,抱着我甩门而走。
娘家是母亲唯一能落脚的地方。可是,黄土河的规矩,月母子不能踏进别人家门。倘若进娘家,更是灾星,会带来数不清的霉运。舅舅扯一张晒席,在门楼搭一个棚子,安顿下我们,听母亲讲缘由。母亲的陈述,肯定添油加醋了。我的记忆,皆源于母亲和舅舅。懂事儿后,我暗自揣测,两根挖锄齿之间,仅有半鳰宽,便是刚出生十九天,我的脑壳也该超过半鳰。更不可思议的是,那挖锄齿居然长了眼睛,不偏不倚恰好迈过我的脑壳。舅舅本来是留有余地的,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呢。听母亲哭诉完,舅舅霍然起身,一把扯了晒席,让我们到屋里。舅舅的举动,宣告我自此没了父亲,直到三年后,一个叫叔的人娶走母亲。
母亲的新家,我也去过。母亲指着一个高个子男人说,喊叔,喊叔。我赶紧躲到母亲身后。母亲便不再要我去,让我跟着舅舅。
舅舅的房子,像猴娃洞一样,黄土河上下没有比得了的。猴娃洞只是传说,舅舅的房子就在眼前。迎面一座门楼,屋脊上有奔跑的野兽,屋檐上有飞翔的鸟儿,这些我都叫不出名字,只是觉得有气势。黛瓦下面,两扇门板厚如城墙,一开一关,都像牛喘气。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脑壳溜光水滑的,我总是试图爬上去。门楼两侧,是东厢房和西厢房。舅舅说,原来有院墙连着。我记事儿的時候,已经没有了。进门楼,过天井院,就是堂屋。门口两个门墩,方正而又圆润,像深水潭一样,能照见人影儿。我不喜欢堂屋,高高在上的屋顶,仰起脑壳都看不真切,冬天冷不说,夏天也凉飕飕的。
记事儿后,我和黑子们玩石子。门楼下面,青石板上,小娃子们席地而坐。黑子之一把石子撒开,取一颗抛起,迅速抓一颗到手里,再接住上面那一颗。又抛抓两颗,还抛抓三颗,最后把石子拢在一起,正要全部抓起时,舅舅过来了。舅舅跺掉脚上的泥巴,说,好狗不挡路,哪个叫你们到这儿玩的?去,各到各门上玩去。黑子们是东厢房和西厢房的崽子,他们的祖辈已经伏法,他们的父辈戴罪改造,他们自己,不管男女,一律叫黑子,黑子之一、黑子之二、黑子之三……不料,黑子之一咕叨,哪个门上还说不到呢。舅舅怒火中烧,把他打倒在地,踏上十八脚,喝骂,还想翻你们的变天账?不错,这是你爷盖的房子,你爷在哪儿?早被我们镇压了。现在是我们的天下,我们说了算,我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你们说半个不字试试。骂着,照黑子之一的屁股又踢一脚。黑子之一“嗷”一声,爬起来就跑,其他黑子作鸟兽散。
舅舅顺手拉我进屋说,晚上放电影啊。我立即抱住他的腿喊,我也要去,我也要去。舅舅怕我摔着,抱我起来。我没有松懈,又喊,我也要去。舅舅说,行,去吧。
那时候放电影,没有确定时间,天黑下来,银幕上能映出影像,就可以开始了。早一点,晚一点,全凭放映员说了算。说不定放映员吃饭早呢,我们不能落在他后面。我端起碗,扒上两口,就到舅舅身上磨蹭。舅舅说,慌啥子,放映员今天晚上“炖牛肉”。并不是真的“炖牛肉”,牛金贵,没人敢杀,是说放映员吃饭晚。我不管,怕舅舅趁我瞌睡来了偷偷出门,粘在他身上不下来。
路不远,也不近。舅舅背我就很快,我自己走,戏末都揽不到。舅舅蹲下来,喊我上肩,骑到他脖子上。舅舅带我出门,从来不抱,总是背背驮。舅舅说,男子汉大丈夫,抱着算啥子,婆婆妈妈的。我骑上脖子,舅舅就唱歌。背背驮,背背驮,我要背你换酒喝,酒冷了,我不喝,我还要我的背背驮。我学着唱,舅舅说,我唱我的,你唱你的。于是,我分清了你我。背背驮,背背驮,你要背我换酒喝,酒冷了,你不喝,你还要你的背背驮。
路上要过河,河是黄土河。不深,浅水处勉强能盖住脚背。也不宽,像舅舅那样的小伙子,打个踺蹦就过去了。黄土河没桥,只在水里垫上石头,我们叫河墩子。舅舅喊,过河啦,坐好。我便抱住舅舅脑壳,两腿夹住他的脖子。舅舅说,莫夹这么紧,尿骚味都窜到嘴里了。说话间,踏上河墩子。左脚踩稳了,右脚才迈出去。小心着呢,河墩子一晃,一只脚跌进水里,身子跟着歪倒。舅舅顺势把另一只脚踩下去,我才没掉下来。舅舅骂一句,转过身,把我搁到地上。哪个搭的河墩子,圆不溜丢的,咋叫人踩得稳当?就像我摔了跤,舅舅总是把路抽几鞭子。舅舅摸出烟,吧嗒点着,猛吸几口,然后说,你等着。我还没反应过来,舅舅已经转去。转去干啥呢,换鞋子吗?平时下秧田,都是一脚泥水,不会这么讲究啊。我低头看脚下,河水唱呵呵的,绕过河墩子,向远处奔去。我抬头看天上,鸟儿乱蹿,越过山顶,不见了踪影。
舅舅回来,肩上扛一块石头,吭哧吭哧的,径直到河里,慢慢往下放。我喊舅舅。舅舅说,搭河墩子,重新搭。说着,移过圆不溜丢的石头,摆上自己扛来的。舅舅,这不是门墩吗?舅舅挺起腰说,原先是门墩,现在是河墩子。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你再等一会儿,我把那个也搬来。没等我吭声,舅舅又转去了。
天色暗下来,河水还在唱歌,鸟儿都飞走了。我害怕野东西下来饮水,顺便吃了我。我担心放映员不炖牛肉,只能揽戏末。正要哭泣时,舅舅又扛一个门墩回来,三下两下摆好,伸出脖子让我骑。
舅舅没走河墩子。之前不留神滑下去,这又来回摆治,双脚早已湿透,何必多此一举呢。他锳水,灌一鞋水,每走一步都有咕叽声响。一路咕叽到放映场,电灯泡还亮着。舅舅说,来得正是时候,再晚一点,电影就开始了。乡村电影,只在稻场上扯一张银幕。前面的人席地而坐,后面的人只能站着。舅舅背着我,在后面站定,电影就开始了。放的什么,我真是不懂,只看到忽喇喇一队人马过来,轰隆隆一阵炮声响起。舅舅看得高兴,一时哈哈大笑,一时失声跺脚。我只好揪着他的头发,免得摔下来。过一会儿,眼皮就涩了。我说,舅舅,我瞌睡来了。舅舅说,不叫你来,你要来,看这屁大一下子。我说,你没说不叫我来。舅舅拍拍我的脚说,好了好了,睡吧,趴到我脑壳上睡。
一觉醒来,电影还在放。我却不能安分,扯着舅舅的耳朵说话。舅舅,我要撒尿。舅舅说,撒啥子尿,憋着。我倒是憋了一会儿,但憋不住,只好又跟舅舅说。舅舅摇摇头。尿吧尿吧,就尿到脖颈子里。不,我要下来。下来就看不成了。我憋了一会儿,把尿撒到舅舅脖颈子里。
看毕电影,舅舅才反应过来,脚是湿的,头也是湿的。你看你这弄的,下回坚决不带你来了。我在舅舅肩上唱歌,背背驮,背背驮,你要背我换酒喝,酒冷了,你不喝,你还要你的背背驮。
二
我以为,我远走高飞了,打个转转,又回到老家。黑子之一說,你这是衣锦还乡呢。我说,兔子满山跑,老了归旧窝。没得锦衣,还是那身皮囊。黑子之一连忙摆手,可不敢这样说,我都还在蹄跳,你能说老?
我回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主持精准扶贫工作。上面有组织,下面是乡亲,我不过上传下达,负责落实一下。舅舅日噘我,应该跟我回村任职有关。之前在外面,逢年过节回来,给他买一些烟酒,他已经很满足,还夸我没有忘本。现在,咋就成了白眼狼呢?
雪过天霁,阳光照在积雪上面,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踩着泥泞,到舅舅门上。门楼已圮,东厢房和西厢房也拆了,只有堂屋兀然而立。门墩位置仍然空着,像豁牙。我推开门,喊舅舅。堂屋空旷,喊声冲上屋顶,有灰尘落下来。我又喊一声,才听到角落里有声响。舅舅坐着或是蹲着,我看不真切。舅舅,忙啥子呢?舅舅站起来,猴着腰,双手在膝盖上乱揩,一遍过来一遍过去,确认没有灰尘了,才插进裤兜里摸索。舅舅是在找烟,其实不用找,不在左边就在右边,直接掏出来就是。
舅舅没提白眼狼,我就不提。我说,舅舅,我昨晚做梦,还梦见你背我看电影呢。背背驮,背背驮,你要背我换酒喝。过河的时候,身子一歪,掉进河里。那天晚上,你一双湿脚站着,我一直坐在你肩膀上。我没说撒尿,估计舅舅也忘记了。
舅舅把烟点上,深吸一口。你还说我,你没掉进河里?扔了铁环,哭哭啼啼跑回来。
哎呀,舅舅,人没掉进河里,铁环掉进去了。还不是你帮忙捡起来,顺顺当当滚下去,才有了今天嘛。舅舅,你抚养我长大,我的童年都是你的故事啊。
我们上学,背着书包,唱着歌儿,高高兴兴去,平平安安回。这是三好学生形象。多数孩子顽皮,不正经走路,拎一只铁环,一路滚到学校。过河墩子怎么办?这就见功夫了。有铁环在前人在后的,刚过两步,铁环一歪,滚进河里。有铁环在后人在前的,以为铁环听使唤,不料铁环比人还会耍赖,抱住河墩子不走了。能不能在小伙伴中树立威信,学习成绩是其次,滚铁环上见高低。
黑子之一的铁环,滚得神出鬼没。早上出门,分明只有书包吊在屁股上,一转身,从衣襟里抖出铁环来,当啷落地,就滚开了。便是等候小伙伴,铁环也没停下,一直绕着人转圈。一路前行,爬坡,过坎,所向披靡。到河边,戛然而止,人和铁环一起立正站好。黑子之一抬头扫视一眼,不为看人,只为显示威严。起步,昂然跃上河墩子,人一步,铁环一步,稳步前行。滚过去,人和铁环都不抬头,扬长而去。
我当然不甘落后,临近河边,突然加速,单足起跳,飞身跨越。相比黑子之一的优柔寡断,我要当机立断。为此,我曾经趁着夜色,苦练本领。无数次的失败,只为这一次成功。我的设想是,到河心轻触河墩子,借势再起,人和铁环都稳稳地落到对岸。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河墩子一晃,我和铁环一起跌进水里。
黄土河的存在,就是让人摔跤的。没人会在意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摔跤。我在意。我捡起铁环,又恶狠狠地砸进水里,折身往回跑。路上没哭,自己不踩稳,有啥子好哭的。到舅舅面前,终于忍不住,轰隆一声涌出泪水。舅舅,他们欺负我。舅舅伸出手,帮我揩去泪水。哪个欺负你?我直是哭。舅舅说,说嘛,到底哪个欺负你?我哽咽一番说,门墩欺负我。舅舅瞪起眼睛说,门墩,河墩子吧?我点头。怎么欺负你了?它不稳当。不稳当……不老实嘛。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这样的人才可信任。河墩子不老实也不行,我们让它滚蛋。说着起身,到门楼卸门板。
门板厚如城墙,一开一关,都像牛喘气。舅舅不担心,他把门板推至半开,顺势一掂,移出门墩窝。舅舅以为,自己的力气扛得住,但门板的重量还是超出他的想象,咣当一声砸到地上,门楼和天井院都跟着抖动起来。舅舅骂一句,低头拱到门板下面,使出猛劲,硬是将门板背起来。
于我的委屈,门板是莫大的安慰;于舅舅的身体,门板是极大的摧残。我的印象中,舅舅的身板就是从那一天猴起来的,从此再没有挺直过。路上,舅舅像乌龟一样,几乎趴下来。我说,舅舅,你歇一会儿吧。重负之中,舅舅挤出几个字:歇……不……得……到了河边,舅舅说,你来……帮一把……于是斜了身子,我顺手一推,门板滑进河里,舅舅也滚倒在地。
舅舅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只能大口喘气。我看着他,吓得不敢出气。舅舅说,莫愣着,给我点一根烟。我从他兜里掏出烟,点燃,喂到他嘴里。他吧嗒吧嗒吸了,才缓过劲儿来。舅舅起来,猴着腰,把门板支好,上去走一遍,又到河里捡起铁环,递到我手里。舅舅说,滚吧,滚到学校去,滚得远远的。
三
舅舅,我有些辜负你啊。河墩子是你搭的,门板是你架的,我该一步一步,一直往前走才是,这又折身回来……舅舅吐一口烟说,这倒没什么,就像我们上山,上一会儿,还要歇一气,攒足了劲再上。大政策嘛,回来歇歇再走。我说,十个指头有长短,我回来,就是把短指头抻一抻,让大家伙撵上来。指头多,一时抻不到恁好,还得慢慢来。舅舅说,你算不上长指头,也不是短指头,可以在中间,帮忙做些工作,跟大家伙说道说道。舅舅又去摸烟,这个兜里摸摸,那个兜里摸摸,终于摸出来,衔一根到嘴里。舅舅说,不长也不短,倒是好说话。说着,兀自笑起来。你莫操心,有想不通的,我再日噘你。我说,舅舅,有啥想不通的,你现在就说。舅舅深吸一口,烟又从鼻孔冒出来。
我上初中,舅舅买了一辆自行车,送我接我。舅舅说,我们原来上一趟街,七十二道脚不干,七十二道河墩子嘛,不是每一道都会掉进河里,掉一回,湿一路。每回上街,不是背就是挑,背柴去卖,挑粮食回来。心里想着街上的热闹,巴不得天天去;脚下害怕路上的艰难,走一趟怕一回。你争气,一下子考到街上,在黄土河上下都是说头。你有福气,不背不挑,只要带着心窟眼儿,走大路,打飞脚都行。走吧,沿着大路往前走,走出这个山沟就莫转来。
本来没想买自行车。那年,田地包到各家各户,肚子能吃饱不说,仓里也有了库存。驻队干部说,大家伙不用担心,今年包下来,明年还是包下来。有余粮了,要敢于改善生活条件。吃的解决了,住的怎样儿?住的不行嘛,都是草房,晚上睡觉,就有蛴螬掉到脸上,肉乎乎的,把人吓个半死。于是,都卖粮食盖瓦房。舅舅说,别人盖房子,那是别人住草房。我们住的啥子,瓦房,青砖上顶的瓦房,还有四角头的院子。黄土河上下数一数,哪家像我们这样气派?拆了再盖,那是吃饱了撑的。
舅舅也卖粮食,跑回老家卖。按说不是舅舅的老家,是外公的老家。那一年,天下大饥,四岁的外公只能拄起拐棍要饭。哪里有饭?赤地千里,没有一根禾苗活着。寒门万户,没有一户冒烟儿。要饭队伍逐步壮大,要饭队伍又不断缩小。命算啥子,没有吃的,连蚂蚁都不如。蚂蚁能吃土,蚂蚁能喝水。人不行,吃土是死,喝水也是死。说是白善土止饿,吃进去拉不出来,说是喝水长精神,喝得浑身浮肿。外公到河边,打算像蚂蚁一样自生自灭,却幸运地捡到白菜蔸子。河边有洗衣石,本该是光滑的,没人洗衣服,已经长了绿苔。外公想尝尝绿苔,却意外发现洗衣石下面的嫩白色东西。这无异于生命的转折点。外公打起精神,沿河而上。事实上,白菜蔸子珍贵无比,外公捡到纯属偶然。
天色将晚,风来了,雪也跟着来了。外公到一户人家门口,小心地爬到粪堆上,偎依着睡下。舅舅讲这一段,我不敢想。雪天里,我缩着脖子,已经冻得瑟瑟发抖,怎么能睡觉,还睡得着呢?
粪堆像白菜蔸子一样,是外公生命的转折点。第二天早上,黑子们祖上起来倒尿罐,看到粪堆上异样,扒拉扒拉刨出一个娃子。于是收留下来,随其姓氏,按晚字辈起名。
外公是怎么长大的,我无从知晓。只知道,他先住西厢房,又住东厢房,后来结婚,有了母亲。我问舅舅,你不是在东厢房出生的?舅舅掰着指头跟我说,我今年多大,哪一年出生,怎么可能在东厢房呢?
舅舅卖了粮食,赶一把自行车回来,一条黄土河都沸腾了。盖房子倒是大事,大家伙都盖,没啥出众的。自行车少,就像舅舅的院落,显得气派。黑子之一从西厢房上来,双手握住车把,嘴里呜呜有声,又摩挲座子,想骑上去的,被舅舅喝止。他便蹲下来,捉住脚踏子,使了劲猛转。舅舅说,又不赶路,你这不是白费力气吗?黑子之一才站起来,前前后后看一遍,叹一口气说,你咋像我哥哥一样,娶了个寡妇回来?舅舅哼一声。你有本事,你娶一个新媳妇试试。黑子之一摇摇头,回去睡觉。
舅舅说,大路好走,步行也慢。有了自行车,送你接你,省時间又省力气。嘴里说着,脚下用力,自行车昂然前行。我喊舅舅,抱紧他的腰。舅舅说,坐稳当,我让你尝尝风驰电掣的味道。我心头一震,莫名兴奋。此前,我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仅限于课本。《林海雪原》里,狗拉着雪橇奔跑,两侧的桦树纷纷向后面倒。《牛郎织女》里,牛郎乘着牛皮,耳边是呼呼的风声。黄土河没有雪橇,我更不能像牛郎一样飞升,我只能坐稳当,任凭舅舅脚下生风。到河边,舅舅没有犹豫。他俯下身子,双手握着车把。他抬起屁股,双脚粘住脚踏子。我不敢看,闭着眼睛乱喊。
我们摔倒了。我在河里,舅舅在河里,而自行车还在桥上,也就是之前搭的门板上面。舅舅拉我起来,胳膊腿捏捏,说声没事儿,才去赶自行车。我以为,舅舅拍拍屁股,就送我走。没想到,他支好自行车,又到门板上面查看。先在左边踩一踩,感觉没事,又到右边,还没使劲,门板就歪了。饶是舅舅敏捷,还是倾了身子。舅舅弹跳起来,再次跌进河里。我赶紧去拉他,舅舅挥挥手,自己爬起来。他说,同一个错误不能犯两次,我还是犯了两次,这可不行。说着,丢下我,径直回去了。
我心里有气,你回去干啥,也该跟我说一声啊。没头没脑一句话,哪里听得懂?上学又不是种地,早一点晚一点,不耽误庄稼生长。我晚去一分钟,都要站到教室外面。那时候,我还没学会骑自行车,只能干气。
舅舅回来,挑一担砖头,手里还拎着一个木桶。舅舅说,我把门楼拆了,没有门板,门楼不是摆设吗?说着,挑一下眉毛。正好有灰浆,一起拎过来。我们把桥砌结实,免得又掉进河里。舅舅对体力活儿有天然的迷恋,他不怕下力气。
先清基。黄土河本来浅薄,沙子下面就是岩石,舅舅用手扒用脚踢,直到把沙子清理干净。
再砌桥墩。砖头上打浆是要用泥刀的,没有泥刀,还是用手,凸凹不平的地方,就用石头敲平。眼看着天黑下来,我很着急。舅舅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今天耽误一会儿,往后就顺畅了。
最后搁门板。这相当于桥梁合龙,是要放鞭炮庆祝的。舅舅说,我们没有鞭炮,就喊号子吧。搁好门板,我和舅舅齐声喊: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生产……
四
眨眼就到年关,天气越来越冷了,黄土河的静水处已经结冰。我们单位的干部都到村里来,挨家挨户走访,给大家伙送去米面油肉。我还别出心裁,给一家添一箱桶装方便面。黑子之一迎面走来,要拍我肩膀,又缩回手,眯着眼睛笑。黑子之一说,这些方便面,肯定会先吃完。
现在的黑子之一,人人都喊他黑老板。由板车到自行车,再到摩托车,黑子之一把山里的东西驮出去,再把街上的东西运回来。又到外面,说是挖金矿或是开石场,总之,发了财回来,弄了自己的建筑公司,黄土河上下跑得欢实。
舅舅不符合走访条件,我到他家里,要跟他喝酒。舅舅喝酒爽直,我端杯子,他端杯子。我不端杯子,他自己端杯子。几杯酒下肚,舅舅双手捉了筷子,不搛菜,红着眼睛看人。我说,舅舅,马上就过年了,等儿子媳妇回来,你跟他们商量一下,我们把房子盖了。我没看舅舅,低着头看桌子。舅舅说,哪个出钱,你们出钱?我说,不是我们,是我,我肯定要出,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舅舅不吭声,端起杯子,一口喝下去。我说,舅舅,你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从尺把长到几十岁,没有你,哪儿有我的今天。舅舅摆手。黄春良的哑巴搬进高楼大厦,不是你们出钱吗?谭国民的房子翻盖了,他到哪儿弄一分钱?我说,这不一样嘛。啥子不一样,都是穷人出身,咋就管一个不管一个?舅舅喝了酒,不能讲道理。我说,舅舅,我们先过年,房子的事儿,开年再说吧。
开年后,我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黄土河桥。招标结果是,黑子之一中标。我跟黑子之一说,这桥是几代人的心病,祖辈想,父辈想,我们大家伙都想,现在到你手里,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说,这算不算历史机遇?你来干这个工程,活儿不大,意义不小。修路架桥,行善积德。你干了这么多工程,有几个是给大家伙干的?所以,要讲奉献,哪怕贴本,也要经得起洪水考验。要把奉献精神凝聚到桥上,建成大家伙的连心工程,建成子孙后代的示范工程。黑子之一愣着,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你这样说,我还要不要钱?我笑着说,不要也行。
舅舅的房子没有翻盖。其间,我到他家里,话里话外是谈过的。舅舅说,你喊我舅舅,我们是舅甥关系,心里面,我没把你当外甥子看,当亲生儿子看。我对不起你,除了供一点吃喝,没有尽到任何责任,要是多尽一点,你就能走得更远,再不回这个山沟。我面前这几个,都是指望不上的。打生下来,就不是读书的料,怎能成气候呢。土里刨一刨,外面跑一跑,勉强糊个嘴儿。房子就不盖了,我老了,也活不了几年。我喊舅舅,无话可说。
黄土河桥建起来,黑子之一问我,要不要举行通车仪式呢?我说,行,你准备两副铁环。黑子之一愣了一下问,通车仪式要铁环干啥子?我说,你去准备就行。
天气很好。灿烂的阳光照在身上,像菲薄的衣衫,和煦的风吹在脸上,像温柔的小手。我和黑子之一手握鐵环,并排站在桥上。桥那头,有一条红色绸带扯开。我说,按照国际惯例,先撞到线者为赢,负责今天中午的酒钱。黑子之一伸出手掌,我顺势击上去。
一……二……三……铁环落地,双脚跟上,我们一起向前。桥不长,眨眼就可以冲过去。体力还是有差别,黑子之一明显比我有劲,接近绸带的瞬间,黑子之一缓一步,我冲到了前面。
隔天,我专门到舅舅家里。舅舅,桥架起来了啊。舅舅明知故问,啥桥?黄土河桥嘛,我们心心念念的黄土河桥。从此以后,到省城,上京城,走再远的路,都不用过门板了。舅舅掏一根烟,自己点燃。我说,舅舅,我们去看看吧。舅舅闷声闷气地说,架一个桥,滚一趟铁环,你们可有本事了。舅舅,这事儿还当真?舅舅长出一口气,咋不当真呢,你们搞工作不当真?
舅舅尽量不出门,非出门不可,也绕路走,坚决不上桥。
眼看就到冬天了,又下一场雪,山上山下白花花的。我在村委会,没能回家。半夜时分,有电话进来,我以为是舅舅的,拿起来一看,是黑子之一的。黑子之一说,你快来,到桥上来。我穿上衣服,立即赶过去。
桥上有个人影,蹒跚着脚步唱歌。背背驮,背背驮,我要背你换酒喝,酒冷了,我不喝,我还要我的背背驮……我喊,舅舅。我跑过去,舅舅满身酒味,挨上我,就像面条一样,倒了过来。
责任编辑:柏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