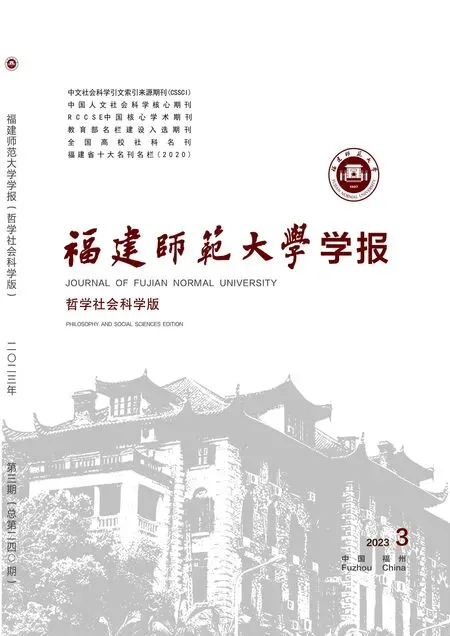论古诗词教学的文化记忆建构
2023-08-21董小玉李林原
董小玉,李林原
(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400715)
全球化暗含的文化同质化风险和人类现代性困境促使人们回望自身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民族寻求身份认同的文化自觉,也是碎片化时代个体追寻生命整全与文化向善之间意义共生的理性选择。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了国家意志、国家关切。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中华诗词的扶持,使包含古诗词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年第6期,第18-23页。。古诗词教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构成,也是语文学科教学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如何“化”传统的问题,同时也肩负着如何“促”创新的使命。
对于古诗词教学的文化价值定位与落实,目前学界主要有两个层面的研究:一是聚焦语文教育自身的学科性叙事研究。冲破学科囿限是古诗词教学的发展自识。已有研究吸纳文艺学、积极语用学等理念,创造性提出古诗文“演绎”教学课型(2)冯铁山:《小学古诗文演绎教学:内涵、价值与课型》,《课程·教材·教法》2019第10期,第104-110页。;统合文化记忆、学习心理学负反馈理论,构建传统文化课程转化机制与经典文本教育路径(3)赵晓霞:《文化记忆视角下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与策略》,《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2期,第112-118页。;以文化记忆为理论关照,切入语文教科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问题(4)翟志峰、董蓓菲:《文化记忆视角下语文教科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中国教育学刊》2021第4期,第80-84页。;等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宏大叙事研究。这类研究更多是从理性建构着手,如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理念前提是“去圣化、去经化、去派化”(5)刘学斌:《去圣化、去经化、去派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理念前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42-150页。,逻辑进程包括分解、汰选、融入三个环节(6)刘学斌:《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逻辑进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18-126页。;也有立足大教育观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与内容,意在建构大中小学一体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体系(7)任翔:《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初探》,《中国教育学刊》2019第1期,第58-63页。。相较于学科层面的实践自觉,宏观意义上的转化与建构多停留在理论操作层面,未能与古诗词教学实践进行有机融合。本研究选择文化记忆理论作为解析古诗词教学的方法论工具,不仅在于其能为深入挖掘古诗词教学的文化基因及其“文以化人”功能提供一个极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更在于它能激活富有文化品质的古诗词教学理念并使之与实践相融合,从而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实现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助力培根铸魂这一教育理想的稳步实现。
一、古诗词教学与文化记忆的耦合逻辑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他指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御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8)[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代序第4页。。这说明,文化记忆既是一种集体共享知识的连接手段,又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实践方式。文化记忆通过对以仪式、文本、纪念物或其他媒介物为象征的集体共享的过去知识进行现时化来巩固群体的文化认同,而文化意义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确保了文化延续。文学承担着唤醒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在有文字和没有文字的社会中,诗人和历史学家都曾经是文化记忆的喉舌”(9)[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源远流长的中华古诗词及其教学价值取向与文化记忆功能在文化与育人的双重指向上有着极大耦合性,将古诗词教学置于文化记忆框架中考察可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新思路。
第一,古诗词是文化记忆的典型载体。文化记忆理论中的民族经典往往是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统一体。文学文本以创造性想象与审美形式表达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而文化文本“包含了一个群体所尊重的规范性和定型性价值”(10)[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3页。,以文化一致性维持着群体的身份认同,确保了一个社会的凝聚力。作为中华民族经典,古诗词“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11)[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译序第2页。。进言之,古诗词以最为简隽精微的审美形式积淀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等关系对象联结的经验与智慧,蕴含着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所说的“共同人性”和“本族群的属性”(12)夏秀:《“经典热”“泛经典”与经典重构》,《学术界》2017年第5期,第158-166页。,并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阐释而形成自身的“凝聚性结构”,进而在文学文本演化为文化文本的过程中塑造并维持着群体的自我形象,从中不断回答中华民族成员“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做什么”等重大问题(13)翟志峰、董蓓菲:《文化记忆视角下语文教科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中国教育学刊》2021年第4期,第80-84页。。如绵延千载的“风骚”传统所传达的道德承担与哲学品质已深入民族血脉,建立起社会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生活准则和文化行为。其中,《诗经》以“温柔敦厚”规范着中国人温厚、包容、中庸的审美追求与人格品性;《离骚》所书写的志向抱负、理性追问至今仍然激励着社会成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可见,无论是感物吟志还是比兴寄托,无不浸润着中华民族的诗性智慧与中国人朴厚深远的生命哲学,同时诗词与人的共鸣皆化作一种胸襟、一种情趣、一种人格,成为古诗词的定型性价值,且超越时空在每一个当下焕发勃勃生机。总之,古诗词是保留了民族文化底蕴的记忆文本,是蕴藏情感要素和生活意义的关键记忆载体。
第二,古诗词教学是塑造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文化记忆通过文化文本在机构化的交流中得到延续。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言,“文化文本以教与学、阅读和解释的形式进行交际”(14)[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页。。教育教学是塑造文化记忆的重要机制,古诗词的文化记忆是在教学框架内承续和再生产的。历时地看,教学活动参与了古诗词文本经典化的过程。纵览中国传统教育史的流变轨迹,三千年来诗教绵延不绝,厚重的诗教文化既助推了历代诗人参与诗歌建设,从而造就了中华诗词发展的璀璨星河,也使以《诗经》为源头的古典诗词在教育系统中确立了文化文本的权威性,并作为经典的文本教育代代相传。古诗词文化文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通过教材选编,并经过最为庞大的、代际绵延的读者群不断阐释与建构而生成的。自语文设科以来,尽管古诗词在语文课程教学领域中时隐时现,但从未缺场。进入21世纪,古诗词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愈发凸显。从教材加大古诗词比重到国家出台系列文件可见一斑。教学对古诗词经典文本的形塑从未中断,这一过程也是古诗词以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15)[德]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译,见陶东风(执行)、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0页。的过程。在教学框架内,古诗词是集体共享的知识,教师与学生是回忆这共享知识的重要群体,而文化记忆是师生与古诗词文化产生良性互动的自觉转化过程。进言之,师生在教学对话中对古诗词文本进行的创造性阐释,在现时化中复活古诗词文本背后的民族“根魂”,使师生于群体性情感共鸣中体认深层民族文化结构,从而获得文化归属感和应对外界的文化力量,塑造民族属己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实现对优质民族精神的高扬。
第三,文化记忆功能能够实现古诗词教学的价值旨归。古诗词作为文化传承的永久性工具,其教学价值在“以文化人”。就此而言,文化是古诗词教学与记忆产生关联的中介点,二者在目的与效果之间有着文化共生的共同价值指向。一方面,二者均以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为深层旨归。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要“学习古代诗词律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页。,并提出要“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体会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理解、认同、热爱中华文化,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1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7页。。而文化记忆则通过传递文化规范和共有价值维系集体身份认同、确保文化的连续性和发展自身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实现文化认同过程中,古诗词教学与文化记忆都关涉个体与群体,呈现出从个体走向群体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共生意义的文化共同体图景。美国教育人类学家乔治·D.斯宾得勒(George D. Spindler)认为,把教育看成文化传递意味着文化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人群共享的一个共同的文化体系(18)[美]约翰·辛格莱顿:《教育作为文化传递的含义》,见冯增俊、何瑾等译:《教育人类学》,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换言之,教育教学承担着个体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古诗词教学的要义是“人文化育”,包含个体文化涵育与群体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记忆重在履行一种群体共育的社会责任,目的是巩固群体身份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表面上看,古诗词教学与文化记忆有着群体指向的不同立场,但实际上,文化记忆依赖于个体,是个体“通过融入到‘整个民族具有规范性的意识当中’(哈贝马斯)来实现自我”(19)[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从而使个体有条件说“我们”的过程。这与古诗词教学以文化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过程相偕同。可见,古诗词教学在促使学生人格与社会文化相吻合的过程中有着以“诗性自觉”塑造文化记忆理想状态的功能体现。
二、古诗词教学文化记忆建构的内在机理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要使文化文本能够让群体获得身份认同并提供灵魂住所,“需要崇拜、反复学习和富有感情的接受关系”(20)[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对文化文本的接受实际上是从由表及里的符号解码中获取意义,最终让“意义”成为勾连民族文化与群体认同的价值统摄。事实上,这种意义生成方式同样符合古诗词教学文化记忆建构的内在机理,具体表现为构建回环式重复激活机制、层级式解码阐释机制、融合式移情认可机制、情景式生产创造机制等方面。其中,审美移情是文化记忆建构的精神内驱,情境中的意义再生产是文化记忆的外化表现。古诗词教学在文化记忆“内生外化”机制中所摆明的观念体系和经验图示,对推进立德树人、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回环式重复激活机制
文化文本的凝聚性结构包含“可以再次被辨认的模式”,“每个凝聚性结构的基本原则都是重复”,通过重复,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21)[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导论第7页。。在教学的纵横轴上,不同层面的不断重复使古诗词文化语码中那些巩固认同的知识重新被激活并再次进入循环与再生产。
纵向地看,从古代诗教及至现代教学的发展时空中省察“重复”机制。其一,一般而言,古代诗教包含以诗为教和诗歌创作两个方面。如果说以诗为教重在古诗词教化功用,那么诗词创作就是古代文人外化诗教的显性行为。无论内化还是外显,一代代人因其遵循了同一套符号体系中的语用习惯和文化习俗,总是以相似的方式在古诗词的研习与创作中互认并承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学文化传统。这种相似的方式主要是对古诗词的典型意象、共通语境、语言结构诸要素的反复凸显与循环使用。诗教的代际重复使民族的记忆触点被不断激活,民族文化语码得以积淀延续。其二,在当前学校教育中,古诗词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它以语言学习及文化素养教育的承载形式进入并复现于各学段。可以说,经典诗词的文化记忆与认同价值在重读中不断生发,甚至贯穿人的一生。如在某些特定场景下,“写入”记忆中的古诗词会不自觉地跃然于口,震撼心灵,回忆也因此随时发生。这些“重复”能够让我们根植于心照不宣的传统、习俗与往复回环的传承之中。
横向地看,激活古诗词文化语码的重复动作表现在内容和方法两个层面。一是教学内容的“重复”。这并非机械简单的重复,而是遵循一定的记忆逻辑与学习规律,表现为对同一作家、同一首古诗词在不同学段深浅有别的学习。同时,具有文化原型特质的古诗词教学内容以有规律性的分布图示,不断提醒学生去回想这些文化符号及其附载意义。二是激活古诗词语码依赖反复诵读。朱自清曾言:“文言文和旧诗词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声调里;不吟诵不能完全领略它们的味儿。”(22)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8页。可以说,反复诵读是对汉语音律、语感的认知,是对古诗词文本生命的复活与文化感觉的累积,对生发文化记忆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二)层级式解码阐释机制
“文化文本只在理解的行为过程中传达标准和形式的动力。”(23)[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页。理解,意味着从符号中释读出意义。古诗词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伟大编码”,是“一个多样性阐释的群集,一个有着众多变量和参数的模糊性群集”(24)金元浦:《大美无言》,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9页。。对其符号所指的逐层挖掘是释放文化记忆、建构价值认同的重要机制。
首先,文字“去蔽”。“世界语言发展史表明,母语不仅是开启民族文化记忆之门的钥匙,更是创造民族文化未来辉煌的工作母机。”(25)潘涌:《祛蔽当前“读经热”:表达为本——由“读经热”引发的对古今母语教育的建设性反思》,《教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6-142页。汉字作为中国母语系统的核心支撑,是形、音、义一体的表意文字,其构成“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完形,它有外形和骨架、思想和神韵、情感和精神”(26)曹明海:《本体与阐释:语文教育的文化建构观》,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引语第4页。。古诗词是最为精炼的民族表达形式,往往于寥寥数语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基因,其文化密码隐藏于诗眼、炼字、谐音之中。古诗词讲究咬文嚼字,表面上看是追求做诗技巧,实际上是在调整思想与情感表达。比如“推敲”典故家喻户晓,“推”是一种意境,“敲”又是一种意境,“敲”比“推”禅味更甚。此外,谐音是古诗词表达隐情的文字功用,如“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中“莲”与“清”分别谐音“怜”与“情”,传达着民族内敛含蓄的性格。古诗词教学的文字“去蔽”应以训诂理念接通汉语古今源流,从汉字字形演变的轨迹中挖掘和阐发文字的文化内涵,在文字解码中深潜古诗词文脉。
其次,意象“解喻”。朱光潜盛赞中国诗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非西诗所能及。中华古诗词多以婉曲蕴藉、意趣悠远为胜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象。《周易》提到“立象以尽意”,即从“象”中可以达至“意”的基本解读。“意”与“象”联结而生的意象是情景的契合,是解锁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及文化人格的密钥。典型的“岁寒三友”——松、竹、梅意象,是烙刻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君子人格象征,它既有专属于中华民族“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又深藏“不论在外地还是异国都有回乡之感”(27)[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等人类共通性情感。古诗词教学不仅要从意象中分析显性的感知和隐性的情绪,更应将视野延伸至古诗词发展过程中的意象固着与更新,在“熟悉”与“惊异”间触摸诗人精致的心灵与民族文化密码。
最后,文本结构解码。“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28)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页。中华民族的本质与本源可在诗词文化中得以溯源与呈现。古诗词独特的文本结构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定式”自在统一,揭示中华民族精神可以通过理性辨析古诗词的文本结构来实现。古诗词文本的固有结构包括诗行形式、对偶、押韵等样式,每一种结构表现都蕴藏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从二言、三言、四言到五七言的诗行结构到词的长短句的固化与演变中,不仅可见经典的语言演进,同时昭示着思想的解放。在平仄、格律、声响、节奏、气息等“先在规定”中反映出经典语言与生命律动的同频共振,而律诗所讲究的对仗则潜存着一种朴素的博爱精神与“圆照”思维。可以说,语言体现了使用它的这个种族的精神生活,透过文字、意象、文本结构层层解码,古诗词的文化记忆才能穿透时空被释放出来。
(三)融合式移情认可机制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认为,“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作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29)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5页。。强烈的情感是记忆内部的机制,是回忆的重要稳定剂之一。古诗词是“有意味的形式”,它不仅是“超越生活之大”的信息,还具有“美感性”(30)高长江:《文化记忆的美学经验》,《社会科学战线》2020第7期,第36-43页。。只有通过审美移情,借助回忆形象、情感共鸣才能真正激发古诗词教学的文化记忆功能。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生动的形象、饱满的情感及深永的艺术意味是古诗词文化记忆的支撑点。“思想只有变得具体可感知才能进入记忆,成为记忆的对象,概念与图像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一体。”(31)[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页。随着图像公式被重复唤醒,文字符号的存储记忆将重新启动。审美的超越性能突破古汉语屏障与语境阙如的双重障碍,拉近人与文本符号的距离,令读者的生命感悟与诗人的生命表达产生共鸣,从而激活文化基因。如《慈母吟》虽历经千载,但翰墨间的母亲形象早已凝定为中华民族独有的“诗性经验”,即“由诗人的感觉模式转化成特定的艺术表象,构成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艺术表现方式”(32)孟洋:《影像语言叙述文化记忆的策略——以纪录片〈诗词中国〉为例》,《河南社会科学》2016第1期,第113-117页。烙刻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中,当这一审美形象在当代读者心灵中激荡,中华民族的“母性”文化价值观便在“现时化”中重新被体认。另一方面,审美移情的“内模仿”机制能在共感中加深信息摄取与记忆。古诗词是景、境、情的融合,需要读者在披文入情的审美体验中调动个体的内模仿心理机制,达至身体、价值与情感共同在场,在情感共振、审美愉悦中使个体记忆成为集体记忆的入口,即构筑一种读者以自身感受体验与情感迁移进入诗词世界,为其中的人物、情境所震撼,在研读鉴赏中获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的主客体融合的理想境界。如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刚毅坚定令人肃然起敬;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的慷慨豪情振奋人心。总之,教学中侧重审美移情,强调对古诗词的声文之美、形文之美及意义之美的体悟,这是情感联结进而巩固文化认同的重要内生机制。
(四)情景式生产创造机制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体系中的“凝聚性结构”,“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出希望和回忆”(33)[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导论第6页。。文化记忆绝非复制,而旨在建构。“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Geltungsansprüche)。”(3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5页。古诗词教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其中掺杂着“培养什么样的人”的价值诉求,这意味着古诗词教学的文化记忆及其“现时化”的价值选择需在当代语境中被重新赋义。《意见》强调,要“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年第6期,第18-23页。。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要求,要“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3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4页。。古诗词教学的文化记忆建构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淬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点,通过挖掘古今相通的情感信念,拓展一脉相承的思想价值边界,并以“创造性地阐释”彰显原初生命底蕴,构筑具有同一性与社会内聚力的文化体系。具言之,只有寻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民族地区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审美意趣等方面的“同核同构”,在一个共享的过去和正在共同经历的当下解开中华文化基因的密码,才能在联通文化血脉的进程中确立并稳固自身的文化坐标。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与“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的信念如磐一脉贯通;前仆后继的民族英雄与革命志士、扶贫攻坚战线上涌现的先进人物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爱国主义精神异代共鸣;新冠疫情中的互助奉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与古诗词“尚和合”的生命美学追求一以贯之,等等。当且仅当古诗词教学置于近代先进文化、世界文化精华、当下语境“多声部复调”的同频共振中,才能让学生真正体认古诗词的时代价值,避免抱残守缺与文化怀旧,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总的来看,古诗词教学是一种文化记忆实践机制,它以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双重身份进入文化记忆建构过程,以个体审美体验、情感跃动为内驱力,在由表及里的符号解码以及 “内生外化”的意义再生产中获得古诗词作为有约束力文本的额外意义维度——文化的、民族的、集体的价值观和标准,并在现实语境中被不断激活与创生,诠释并丰盈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质。
三、古诗词教学文化记忆建构的实现路径
“没有个人的激情,共同体将是一潭死水;没有共同体的共鸣,个人的激情终将消退寂灭。”(37)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页。古诗词教学的文化记忆建构是“个人激情”走向“共同体共鸣”的过程,也是文学解读的有关经验转入文化记忆重构的历程,其核心在于以充盈的情感畅游诗意世界、深潜文化根脉,在触及灵魂的研读中架构主体的精神结构。依循古诗词教学文化记忆的建构机理,探寻基于诵读、对话、文化通约与走向生活的教学路径,使学生“‘靠自身、从自身引出知识’,去达到对真理的认识”(38)[日]佐藤正夫:《教学原理》,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在“知情意行”的统一中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写入”心灵,孳生文化记忆。
(一)以诵读为基点,唤醒文化记忆复现
《论语》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之说,诵读是古代最基本的阅读方式,诵读诗歌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多学科透析诵读记忆学理,有助于澄明其核心要义并建立古诗词教学文化记忆的复现机制,实现古诗词教育的文化价值。
从内涵审视,词源学里“诵”侧重通过“声”(音韵、节奏等)而“背”,目的在于“得其文辞”;“读”包括“诵”,侧重通过“抽绎”(感悟、理解),目的在于“得其义蕴”(39)张心科:《论诵读的内涵、意义及要求》,《教育学报》2009第1期,第60-65页。。诵读重在声音与意义结合,是基于理解、体悟的诵记、积累,绝非“不求甚解”的呆读死记。 正如叶圣陶所言:“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40)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9-10页。因此,构建多维诵读法作为古诗词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声、文、情循环互发中,以最朴素的方式贴近经典。如朱自清所强调的“为己的朗诵”与“为人的朗诵”同时并进(41)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95页。可资借鉴;还可从学生生命成长视角出发,构建吟诵、讽诵、吟哦等梯度式古诗词诵读课程。值得注意的是,诵读不必泥古,“关键是要把自己的感情放进诗里,表达出来”,“在声音的帮助下进入诗的内容和境界”(42)叶嘉莹:《吟诵、背诵与传统文化教育》,《教师博览》2014年第2期,第52-53页。,从而实现“感发生命”及深层理解文本的目的。
从过程探微,诵读重在“熟读精思”(《朱子读书法》)(43)(宋)张洪、(宋)齐熙:《朱子读书法》,北京:中国书店,2018年,第12页。与“口诵心惟”(韩愈《上襄阳于相公书》),是“声入心通”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语言心理学研究表明,语言意义的理解与生成伴随着发声系统的肌肉活动。诵读是眼、口、耳、脑等多器官的整体参与,是诵读者大脑的原有图式通过预测、选择与文本对话,同时不断以元认知监控自己的语速、语调、节奏,以传达自己理解的过程(44)周庆元、于源溟:《诵读法的历时演化与现时解读》,《中国教育学刊》2004年第10期,第45-48页。。古诗词诵读含括认知、涵泳、感悟、审美等环节,即通过声音的高低起伏、语调的抑扬顿挫、语气的徐疾轻重而抵达文本肌理,复活文字背后的意境情感,于心领神会中烙刻文化印记、滋养精神品格。探明诵读作为教学过程的文化记忆复现机制,可搭建符合古诗词教学特点的“诵读”教学模型:疏解的读-逻辑的读-审美的读(45)张心科:《重建“诵读”:诗歌教学的问题与对策》,《语文教学通讯》2019第4期,第15-20页。,确证每个版块都有明确的教学重点与方法,通过教学设计的结构化联结来实现教学过程与文化记忆的深度互嵌。如语文教学名师王崧舟的经典课例《长相思》,正是在多层次的反复诵读中联通学生与古人的情怀,使之深切领会将士征人心系故园与渴望保卫家国、建功立业的复杂情思(46)王荣生:《古诗词教学:植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王崧舟〈长相思〉教学艺术与原理解析》,《今日教育》2016年第1期,第52-55页。。
从功能考察,诵读有利于获得语感、濡染情感,它以两种方式参与古诗词教学的文化记忆建构。一是以即时方式回忆文化。诵读调动读者感官,刺激语言感觉,并经由语言中介进入诗人的精神空间,达至朱熹所谓的“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和“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47)(宋)张洪、(宋)齐熙:《朱子读书法》卷一,北京:中国书店,2018年,第26页。,在情感寓身中识别民族文化密码。二是以延时方式回忆文化。对古诗词的理解无法一次性完成,因为“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48)[意大利]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3页。。在此意义上,古诗词诵记可视为存储记忆,它将在人生的某些场景中被再次提取、唤醒。为此,可通过构建仪式化的诵读重复机制,如举办诗歌节、诗词读书会,建设“中华诵”等校园诵读品牌,使学生在“声”临其境的语言世界中“养其根而俟其食”(韩愈《答李翊书》),从而唤醒古诗词的文化育人力量。
(二)以对话为路径,激活“历时-共时”多层场域
文化记忆涉及回忆、认同和文化延续三个问题,是历时与共时的对话与合谋,而“对话的进行显然是向着未来这一时间意义敞开的……就这一意义而言,历史文本压根无法再属于过去,它只能属于现在和未来”(49)路文彬:《理论关怀与小说批判》,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33页。。古诗词教学如若脱离历时语境,则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密码必将流失;倘若忽视共时情境,又会面临降格为“惰性知识”的危险。因此,需要主动搭建“历时-共时”对话的古诗词教学场景,充分发挥叙事教学的文化记忆建构功能。
第一,营造基于文化回应的“回溯-延展型”教学语境。传承文化是经典教育的题中之意,只有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置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回溯经典,才能使古典诗魂在时代视域的融合中返本开新。如将古诗词中士大夫的家国天下情怀拉入到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考察,不仅能拓宽学生文化视域、增强其社会参与意识,而且可以延伸古诗词的文化生命力。王昌龄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送柴侍御》)在新冠疫情期间就被赋予了这样的新内涵——跨越国别的同舟共济。这是古诗词教学意义“现时化”生产的衍生点,也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共鸣的专属印记。
第二,构建指向“凝聚性结构”的语文知识体系。充分借助教材这一“延伸的场景”,打通中西文化壁垒,主动寻求古今中外诗词的对话契机,引领学生在现代开放的语境中塑造文化记忆。如语文教材应提炼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精选与古诗词“同核”的现当代诗词作品、外国诗歌作品乃至散文、小说等文体样式,引导学生在当下及域外时空中重复体认自身文化基因。如讲解张继《枫桥夜泊》时,引入汪曾祺小说《侯银匠》末尾的相关段落,可以体会古诗词简隽形式及其情味穿越千年时空与今人相通的别样情怀。此外,戴望舒、闻一多、余光中等一批现当代诗人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传承较多,可为联通古典-当下的诗意空间提供可能的文本选择和言说方式。
第三,开展指向学生生命意义阐发的文化叙事教学。文化记忆建构的场景中,“对话”理应成为“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50)[英]戴维·伯姆著、[英]李·尼科编:《论对话》,王松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叙事作为过程哲学,为古诗词教学提供了“意义之溪”形成的可能,而个体通过叙事在多重对话中生成切己的意义,又在自我建构完成的同时融入了群体的价值共识。叙事介入教学有多重意味:一是教学中嵌入学生生命历时性发展的视野,展开基于个体经验的具身阅读,消解学生与古诗词的隔膜、避开“自动化”理解,将教学对话推向纵深。如通过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白居易《池上》等童趣盎然的篇章,以古诗词蕴含的“父子兄弟之爱的亲情和对所处自然的自然之情”奠基儿童成长的本源性情感(51)刘向辉、皮军功、刘莉:《诗可以兴:古代儿童诗教的发生逻辑和启示》,《学前教育研究》2021 第9期,第 29-35页。,以切近儿童主体经验的对话为其精神生命打底。二是叙事作为知识组织的结构,利用教材或教学内容的叙事化呈现,充分设计基于阶段性、整合性、渐进性的经典循环复现的教材面貌及教学活动,在经典重读中不断深化对文化的感知与认同。如在小学阶段以赞美祖国山河、自然风光的古诗词为主,旨在激发学生对国家的自豪与热爱;初高中学段则逐渐增加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题材,以及传达民族忧患意识的古诗词,将爱国情怀上升到责任感、价值观的高度。这种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教学内容安排,能够形成文化意义的“滚雪球”效应。三是叙事作为教学过程的载具,发挥其核心元素,即故事的修辞力量与教化功能。如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融入辛弃疾“传奇英雄”、王安石“邋遢宰相”、苏轼“大磨难成大风流”等精彩故事,可以使历史人物、诗词意境走出概念化而变得亲切可感,同时还能从中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力量,帮助学生建立文化自信。可见,探索叙事融入教学的理论、方法、范式,是古诗词教学文化记忆建构的可为方向。
(三)以通约为样态,拓展媒介延伸场景
文化文本是可“再次接收的消息”,而“延伸的场景”为文化的存储和传达提供了支撑和框架。在教育场域外,存在诸多古诗词文化记忆的延伸场景,如经典诗词的诠释文本、影像传播、书法、音乐、绘画等诸多文化艺术形式。古诗词教学需充分发挥“延伸的场景”及“文化通约”功能,通过公共符号的确认促使个人重塑共同记忆与实现身份认同。
其一,跨学科的文本在场。冲破学科界限,发挥古诗词在语文学科之外的教学黏合力与文化渗透力,在跨学科教学视域中释放其理应承载的文化记忆功能。如古诗词以多层次应用参与地理等学科教学,通过古诗词提取地理信息、解释地理现象,开展古诗词与地理课堂的深度融合研究(52)李勤艳、彭蕾:《古诗词与地理课堂深度融合的有效策略研究》,《地理教学》2020年第7期,第49-52页。,而科学与文学的奇妙相遇给课堂以“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又使古诗词在多学科的相互阐释中从抽象的符号走向清晰的意义辨识、从严肃板正走向可亲可近。
其二,跨媒介的场景聚合。技术的发展使文化记忆场域超出了文字文本,扩大到影像语言,通往数字化之路。“每种媒介都会打开一个通向文化记忆的特有的通道。”(53)[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导言第13页。我们需立足时代,在数智化时空场景中“锚定”古诗词教学。如借助《经典咏流传》《跟着唐诗去旅行》等有代表性的文化节目或者三联中读APP出品的精品课程《听吧,唐诗》等拓展古诗词教学资源,同时借助教学与技术的联动重构文化记忆媒介,增强文化记忆。此外,还可利用影像语言实现古诗词文字文本与数字文本交互,如《杜甫》《苏东坡》《人文地图 诗词之旅》等纪录片中借以整体感官的感知来推动古诗词文化价值的传播。
其三,跨文本的互文教学。文化文本享有被注释的特权,通过不断的阅读,其内容日渐丰满……而且能够反映最新现实(54)[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历代诗话、词论是对古诗词注释和扩展的过程,也是以回忆和唤醒的丰富交叠来向前推进文化传统的过程。如《毛诗》对《诗经》的阐释、有宋一代对杜诗的研究以及《文心雕龙》《诗品》等重要文论,皆可作为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文化资源。将古诗词置于诗史或诗评互文中,拓宽古诗词教学的对话空间,增进文本理解层次;还应总结中国诗学思想、提炼教育智慧、对古诗词解读理论进行教学转化等。只有在多维意义符号体系中开展古诗词教学,才能对中华传统文化达到“立体的懂”。
其四,跨门类的“文化通约”。“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各构成要素之间都有其通约性”(55)王鹏伟:《汉语文教育传统与汉语教育的民族化方向》,《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63页。,中国古典艺术的通约性尤为显著。从历史起源看,诗、乐、舞本是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三者间的美感是可以感通并且相互唤起的。如融贯于古诗词、书画、舞蹈、筝乐等传统艺术之中的“气、神、韵、境、味”等独特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可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内核。古诗词教学应有意识地以此为共轭点,联动多感官鉴赏、互通多门类教学,如以诗书结合、诗词配画等方式加深艺术通感,丰富对传统文化内核的感知,在深层次的民族审美体验中生成文化认同。
(四)以生活为境脉,厚植生命体验空间
古诗词教学旨在将纸上的诗词转化为“诗意栖居”的精神力量,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向心力。然而,古诗词早已从“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第十六》)的生活场景中退场,沦为碎片化、镶嵌式的浅层使用,或由于概念化的文化传递降格为消极语用学习。古典文本要焕发出不竭的生命力,应与现实生活充分接触,使其在文化意义互动的空间中生成文化记忆。
第一,联通课堂内外活化古诗词的生存土壤,以言语实践培育诗性情感。如果说语言唯有在交际中才能唤醒活的灵魂,那么在活态的言语实践中古诗词才能发挥其潜移默化的文化记忆功能。评诗、改诗、写诗等活动回归课堂、走向生活,既是青少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的生命表达诉求,又是古诗词教学唤醒文化记忆的有效路径。当下,语文课标已明显改变排斥诗歌写作的风向,主张启发学生用诗意晕染生命,用实践体验古人的风雅情致。为此,可引导学生利用古诗词或以诗的形式参与日常交际,如留言互动、赠诗祝福、表达情感等,或者布置以自创或引用古诗词来进行图文表达的创意作业,并通过在线交流达到群体参与的目的。较为典型的有陕西西安市第七十五中副校长罗亚妮用学生的名字编成诗或词,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联通学生的生活空间,以诗意化的言语实践涵育诗性情感(56)《中学副校长将学生名字编成诗词:既激发学习兴趣,又了解名字含义》,2022年9月16日,http:∥v.hinews.cn/page-1437513.html,2023年3月16日。。值得注意的是,诗以达情言志,并不局限于古诗词,它包括古诗词在内的对诗性智慧的传递与践行。
第二,开展基于学生经验的探究性学习,深抵古诗词文化根脉。“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无限的,永远新鲜的。”(57)朱光潜:《诗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2页。这意味着要抵达古诗词背后深广的文化意蕴,促使价值观内化,必须立足学生生活经验,开展深刻而有新意的探究性学习。除了挖掘生活元素,深入理解古诗词内蕴之外,还应抓取学生常态生活中的场景或关切问题,开展主题式教学或项目式学习。如根据学生兴趣或民间节日、节气等设计不同主题、风格、意象的诗词挖掘或创作活动,使之形成对古诗词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以意象为例,让学生搜集整理典型意象的诗作,探讨其在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笔下的意义形成与更新,把回忆和经验联系起来,以此强化学习者在一个共同文化视野中的交流互动,并使之成为展开文化行动的价值引领。
第三,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拓殖古诗词教学文化记忆空间。除了原创文本,古诗词教学还应借助外部存储媒介和文化实践来建构文化记忆。中华民族有着厚重的文明发展史,形色各异的地区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构建的重要源泉。基于此,可广泛挖掘华夏大地丰富的文化资源,积极吸纳与中华传统文明血脉相通的区域文化充当古诗词教学的核心内容。如湖北房县民歌对《诗经》的化用与传承就是典型代表。此外,历史遗迹也发挥了“重生助产士”的文化记忆作用。各地存留的关于古代诗人或诗人集团的历史遗址、文化名胜等,使过去的精神遗产变得可触可感,为古诗词学习从文字媒介拓展到空间媒介的解读和意义提取提供重要条件。因此,可依托当地古诗词文化资源,以场馆教学或研学旅行、综合性学习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让古诗词所蕴含的民风民俗记忆重新在传统中扎根,使学生在“亲身体悟的知识”过程中自觉融入整个文化规范,从单数的“我”走向复数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