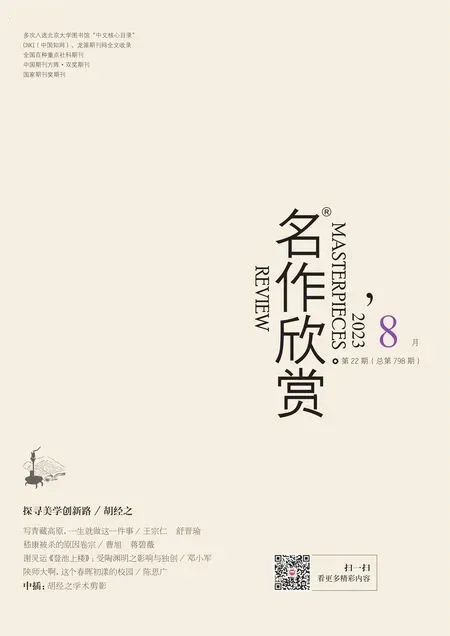《当代作家书简》絮谈
2023-08-17湖北梅杰
湖北|梅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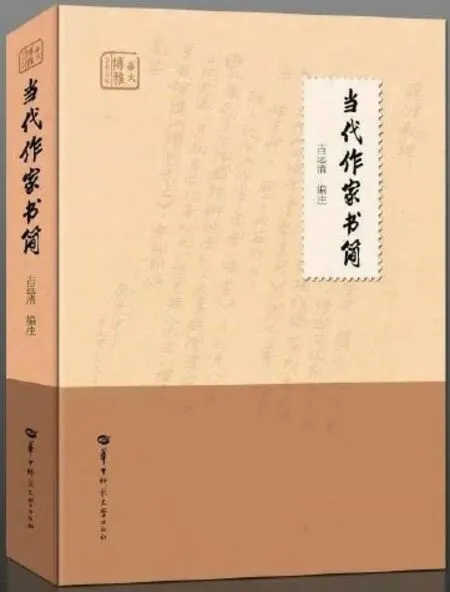
《当代作家书简》
古远清编注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4 月版
当我们谈论一本书的时候,往往是谈一本书的作者。其实,一本书有父也有母。也就是说,一本书既有作者,也有出版者。以古远清先生编注的《当代作家书简》为例,从编辑出版的角度看,古远清是编注者,也就是作者之一,与书简的作者一样,构成了本书的作者。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它的出版者,具体就是由责任编辑完成的。作为《当代作家书简》的责任编辑,我认为我有义务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讲一讲这本书。
《当代作家书简》 的出版之缘
《当代作家书简》作为书名,并不是古远清的创意。早在1943 年,普及出版社就出版了卫明编的《当代作家书简》,该书收录了田汉、鲁彦、胡风、老舍、郭沫若、冰心、张天翼、丁玲等约30 人的书信34 封,成为颇有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资料。而在这之前的1936 年,著名编辑家、杂文家孔另境更是编了一本大名鼎鼎的《现代作家书简》。《现代作家书简》后来不断再版,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著作,更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史料。我研究废名书信,即受益于该书良多。古远清编《当代作家书简》肯定是来自于孔另境和卫明的启发。正如他在《当代作家书简》后记中说“步《现代作家书简》后尘的《当代作家书简》”,可见,书名创意来自孔另境。
古远清之所以要编《当代作家书简》却又与疫情有关。他在编后记中说: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武汉封城已有月余。甘当宅男的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的房子是这么宽,客厅布满四壁的书橱书是这么多,因而我一下床,就成了逛书店;到阳台做体操,就成了逛公园。……
“躲进小楼成一统”后,我生平另一个重大发现是时间竟完全属于我。这时不用外出开会,不用外出讲学,不用外出会友,当然也不用外出应酬,因而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另一位帮我植字的宅女也就是“老秘”一起奋战,完成了为《名作欣赏》杂志编的《古远清八秩画传》,另又编注了海内外作家写给我的近二千封尺牍选出来的《当代作家书简》。在自我隔离的春节,我就这样闲出了成果,“宅”出了花儿,终于将从旧金山来,从悉尼来,从首尔来,从东京来,从曼谷来,从新加坡来,从吉隆坡来,从香港来,从台湾来,从北京来,从上海来的尺牍厚厚一大册,像鲜花一样插在我早已满坑满谷的书房前。
……我也没有收集过别人的日记,但从本书所刊载的书信中,毕竟可看出不同作家和学者的迥异风格……
可见是造化弄人,给了古远清时间和精力,让他去总结和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于是编注出了这么一本“大奇之书”(古远清语)。
2020 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挥辉社长与古远清攀谈,得知其怀有一部“大奇之书”,于是斗胆提出出版。这样的书,当然很难走市场,好在古远清是明白人,不想让出版社赔钱出书,说他找单位适当补贴一些。至此,《当代作家书简》的“父母”才算结合在一起,具备了从“书稿”转为“书”的可能性。那么,有了这个美好的“邂逅”之后,《当代作家书简》能不能正常“呱呱坠地”呢?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责任编辑的作用了。
我成为《当代作家书简》的责任编辑,也是人生一奇缘。2020 年,注定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年。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大转折,即从过去的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转入学术型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既是冒险的,更是充满机遇的。我刚入社不几天,学术出版中心的冯会平主任就找到我,让我审读《当代作家书简》。我不禁眼前放光,先是书名让我明白它的史料价值,其次是古远清的名字让我倍感亲切,这就不得不说到我与古老师的前缘了。
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古先生的大名。那时候,余秋雨红极一时,他的散文在中学生手中辗转流传,而我一向清高、自负,持欣赏和怀疑的双重眼光进行理性阅读。这时,古远清先生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吸引了我,这才知道我们湖北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个教授对余秋雨极为不屑。后来,我又注意到古远清先生是研究中国港台文学的大家,然而长期以来却无缘结识。
在我2011 年北上京城之前,我就对黄梅籍的赴台作家王默人非常关注,只是无法联系上王默人的家人。我曾联系过北京大学“王默人小说奖”的具体经办人,对方却以隐私为由拒绝提供。于是,我就想到了古远清先生,很有结识古先生的冲动,希望得到他的帮助。2010 年12 月15 日,我冒昧给古老师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古远清先生:
久仰先生大名!问候先生。我也研究一点现代文学,还请您多指教。不知先生关注过王默人么?不知他在台湾影响如何?据说梁实秋为他写过书评,这个文章先生见到否?望先生解惑。
后学梅杰敬上,2010 年12 月15 日
古老师不以我是无名小辈而拒之,他很快就答复道:“王氏在台影响不大,梁氏书评未见过,你在哪里高就?”于是,就展开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我到北京工作以后,为了进一步追踪王默人,又给古老师写了一封信:
古老师:
我的笔名眉睫,在北京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曾就王默人问询过先生。据我所知,王也是台湾乡土小说家之一,周伯乃、何欣等人研究过他,不知哪里可以读到周伯乃、何欣的文章?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吗?盼告我。
后学眉睫敬上,2012 年8 月10 日
古老师又立即答复:“何欣已去世,有什么问题再联系。”并告诉了我周伯乃的邮箱。正是古老师的这一次帮助,让我跟台湾文学评论家周伯乃建立了联系。在周伯乃的帮助下,我获得了不少王默人的资料,尤其难得的是,周伯乃还把王默人1968 年赠送给他的处女作《孤雏泪》再版本转赠给了我。后来,我依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研究王默人的小文章,并进一步搜寻到了更多王默人的史料,比如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默人小说全集》等,还与王默人的亲属建立了联系。可以说,如果没有古道热肠的古远清老师的帮助,我是很难打开王默人研究的局面的。
这算是我与古远清先生的前缘。
《当代作家书简》的学术价值
《当代作家书简》是古远清编注的一本当代作家、学者的书信选集。古远清遨游学术界大半生,交游广泛。本书收入约200位当代名人的书简,从年龄看,既有臧克家、李何林、胡秋原、公木、吴奔星、纪弦等民国资深作家,又有邱华栋、杨宗翰等新生代年轻作家、学人。从地域看,既有丁聪、丁景唐、钱谷融、陈子善、流沙河、谢冕、严家炎、钱理群等中国内地学者,又有刘心皇、余光中、向明、痖弦、陈映真、吕正惠、曾敏之、刘以鬯、董桥等中国港台学者,还有许世旭、叶维廉、朴宰雨、王德威、山田敬三等海外学者。从领域看,既有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还有文学史家、报人、编辑、记者等各色人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是一本干货满满能够成为阅读盛宴的著作。若究其大者,约有如下意义:
首先,《当代作家书简》是一部充满史料光芒的“休闲”趣味读物。书信大体是文学作品,具有休闲性、趣味性,乃至猎奇性。《当代作家书简》经过编注者从2000 多封来信中挑出700 封,不管是否最有分量、最有代表性,但整体凸显了史料价值。譬如孙光萱、徐缉熙、胡锡涛等人关于余秋雨早年经历的回忆,披露了当年“余古官司”前前后后的内幕,对世人研究余秋雨无疑是首次公开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这些书简中透露的细节,往往能见出真实的人性。当然,或敝帚自珍,或因人存史,一些并无可读性的“鸡零狗碎”亦行收入,大致可以轻飘翻过,只是无损于全书的史料价值。
其次,《当代作家书简》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编注者古远清是当代中国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学术道路得到哪些前辈的提携、指引?他又是如何开展中国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这些书简所呈现的交往实录,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学人交往实录,本身就形成了学术史,成为当代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书简是承载者、见证者。以本书收入的68 封臧克家来信为例,记录了1982年到1998 年两人长达16 年的学术交往,此后编注者还继续与臧克家的夫人、子女保持书信往还。在臧克家的书信中,我们还能看出臧克家对古远清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有过欣赏,有过疏离,有过鞭策,有过失望,最后归于平淡交往。臧克家对古远清研究新诗是抱有期望的,为古远清的成名作写序,但对他转向研究中国港台文学则充满规劝。其实二人的根本分歧在于文艺观的不同,臧克家主张现实主义风格,强调“反自由化”,排斥朦胧诗等新生事物。但古远清也是聪明的,一开始并未透露出自己的文艺观点,甚至以中立者身份编选“反自由化”的论文集,获得臧克家的支持和激赏。但随后古远清逐渐暴露出自己的文艺趣味倾向,即遭到臧克家疏远。二人十几年的书信往还,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臧克家有一定帮助,也便于我们了解古远清是如何走上学术之路,一步步扩大学术疆域的。
最后,《当代作家书简》是有一定特色、有人文情怀的出版物。民国时期的孔另境编了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成为现代文学领域颇有名气的一本书。《当代作家书简》的序言作者冷剑波称古远清为“当代孔另境”,有称《当代作家书简》效仿、追慕《现代作家书简》之意。应该说,二书的确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出版物,往往不求多大市场,但求在同仁之间形成共鸣。书信往往是友谊的见证,将这种私密性的东西集腋成裘,一朝问世,洋溢着的是浓浓的人文情怀。
《当代作家书简》推出“续编”
《当代作家书简》出版以后,学术界围绕这本书展开了多场学术研讨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邹建军、冷剑波、范军、陈建军等教授的评论文章,陆续在《文学自由谈》《书屋》《名作欣赏》《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一线学术刊物发表,推动了古远清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
2021 年年底,《中华读书报》将《当代作家书简》评为年度百种好书之一、年度二十种不容错过的文学好书之一。2023 年初,《名作欣赏》杂志又将它评为“《名作欣赏》编者和作者眼中的10 本好书”之一。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算是对古老师的鼓舞。《中华读书报》 的评语正是从我的书评文章中摘取的。
学术界的热议、《中华读书报》的推崇,让我想到应该持续打造“当代作家书简”,于是建议古老师再整理一本续编。经过2022 年大半年的努力,到了2022 年10 月12 日,古老师发来了续编书稿。在交稿前两天,古老就提出由我为续编作序。我推辞道:“我哪有资格写呢?”古老执拗地说道:“不讲资格,不要推辞。”后又催我“先把序写好”。一直到12 月9 日,古老还在陆续增补书信,我为他的动作之迅速、工作之仔细感到惊讶,甚至比我这个年轻人还要眼疾手快。我的序言一直未动笔,直到12 月28 日看到古老逝世的消息,才知道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古老逝世,我在朋友圈发布消息说:“惊闻古远清教授逝世!就在最近一个多月里,我们还就他的《当代作家书简续编》签约、审稿等进行探讨,原计划明年开春出版,孰料先生遽归道山!”而这时,压在我心底的序言之托,无比沉重。如果先生在世,我尚且可以写好请他指正,而先生一走,序言变悼文,真让人情何以堪?
《当代作家书简》是我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后接手的第一部书稿,非常合我的胃口,因为我在编辑工作之外,也长期从事现代文学史料和文献的整理工作,有嗜古之癖,在对这本书的打造上,我也倾注了很多心力,所以格外珍视。在某种程度上讲,我是协助作者古远清审读加工了这部书稿,这一点也得到了古老的认可,我们也因《当代作家书简》缔结了一次学术之缘。为了记住这份美好,《当代作家书简续编》我们一定会出版得更好,做出更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