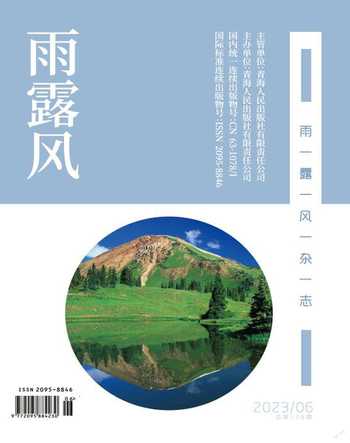在古厝里找一个思念的答案
2023-08-15林昕迪

大约在两年前,我再一次去了位于上杭路与马口交汇处的龙岭顶。
入口破旧的牌匾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褪去了原先夺目的光泽,就如那一段渐渐淡去的历史。牌匾下双龙戏珠的刻纹因为年代久远已有些模糊不清,须得反复细看才见得双龙轮廓,两旁暗橙色的方柱中央镶嵌着一对楹联,我定睛一看,左联写着“江潭水碧诗无尽”,而那右联不知何时已经脱落,徒留背后的灰色石板裸露着,后来查阅资料才得知右边楹联是“台榭花红意自如”。旧时龙岭顶的山光水色被这副以“台江”为嵌头的巧妙之联细细勾画出来。从入口踏入窄小山道的那一瞬间,天幕好像织成了一张大网,我似乎听不见身后嘈杂的车流声,进入了一个与车水马龙截然不同的静谧世界。
可是谁又能想到,如今这因破败残损而被遗忘的地方,曾是老福州城最繁华的市井之地呢?“买厝要买蒙岭顶(龙岭顶),买田要买远洋鼓山边”,老一辈人对这句俗语再熟悉不过了,据说过去台江沿江一带在雨季常遭水淹,龙岭顶因地势高而安然无恙,这使得当时的富商巨贾纷纷在龙岭顶置地建厝,造就了这里的一代繁荣。
我沿着石板道向上走,抬头望去,两侧木质的双层旧屋紧紧相连,这些屋子的主人们早因古厝改造搬迁了。土木尚存,人已远迁。旧宅的窗外挂着的红灯笼并未被主人带走,无声却能言,微风拂过,灯笼轻摇,恍若正安静地将屋内那些积满灰尘的故事娓娓道来。我一转身,看到前面几位头发灰白的老人,拿着相机,试图去定格古厝中一个个细微的角落,他们透过相机的取景器仿佛不是为了看清屋宅,而是去洞穿远方亲切热闹的生活图景。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记忆也开始像幻灯片一般,在心中反复地播放……
“奶奶,我们家很早以前住在哪里呀?”幼时的我有段时间不知看了什么儿童读物,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上盘旋,经常缠着奶奶问个不停。
“上杭路你知道吗,从你的曾祖父那一代开始,我们在那儿住了大几十年,一直到九三年才搬出去,可惜咯,你没有机会去感受以前的老房子,上杭附近还有个地方叫做龙岭顶,我和你爸爸对这一片地方再熟悉不过了。”奶奶说完摸了摸我的头,她也许不会想到,她的回答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连我自己都未意识到的种子,在此后成长的时光里,在无数次交谈中,我循着他们留下的纷乱回忆,拼凑出一件件关于古厝、关于家的往事。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旧时双杭,十里洋场,商帮聚集。我的曾祖父跟随外地商帮从江西临川来到福州做生意,花了十几年时间,从一家裁缝铺的小学徒成为独当一面的布匹行老板。自此,全家才真正在上杭这个商贸之地安下身来。这一路艰辛历程可惜我未能了解,奶奶的记忆也非常模糊。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奶奶还曾有机会目睹双杭一带贸易的繁华,可年幼的孩子哪会去关注做生意的场面呢?奶奶每每提起她生活的这片古厝,重阳“登高”是她念叨最多的。
每逢“九月九”,曾祖母早早地把孩子们叫起来,换上洁净的衣服,孩子们快速吃了早饭,牵着父母的手,一路雀跃着从上杭街油巷下,来到了龙岭顶的石阶,开始“登高”。龙岭顶之所以成为登高的好去处,缘于山顶上的一块“天外奇石”。据说,这块石头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天上掉落在了这里。那时候的人们并不知道这黑色石头叫“陨石”,总认为这石头既然从高高的天空中坠下,那么孩子们踩着它将来一定会长得高大健壮。于是重阳“登高”(又称“蹬高”)的传统也就由此而来。这是孩子们早就谙熟的民间传说。石阶两旁的小商贩兜售着各种有趣的小玩意儿,挠得每个孩子心里痒痒的。奶奶至今还记得小商贩兜售的各种玩物:几尾漂亮的红色小金鱼在玻璃瓶里灵巧地游动,四色的纸风车“嘎吱嘎吱”地转动着,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表情凶厉的老鹰风筝、色彩斑斓的蝴蝶风筝,哪怕是一个普通的长方形风筝,在孩子们的眼中都有着别样的风姿,若是能在这里买到一只风筝,一会儿到达岭顶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放飞了。龙岭顶并不高,不一会儿便到达了顶上的小广场。那时年幼的奶奶却爬不上那黑石头顶部,必须由曾祖父托上去。等站稳后,她便向上“蹦”一下,许下长高的心愿。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琅琅的书声代替了孩童的游戏,在多进式的旧式民居里,和奶奶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也逐渐按部就班踏上了读书之路,老宅的角落、屋子的窗前时常能瞧见求知的身影。东面的天际泛着白色的光晕,晨曦倾泻而出,黎明破晓,铺天盖地的金辉洒向院落。树梢晃动,鸟儿啁啾,伴着清脆鸟鸣同时响起的还有奶奶的朗读声。奶奶最喜欢的科目是俄语,每日清晨六点半,便能准时看到她坐在屋前的门槛上,双手捧着课本,响亮地读着单词。坐累了,她便在院落里踱步一会儿,再站在院子里的两棵茶花树前朗读课文。那时没有今天这样丰富多彩的课外读本,奶奶拥有的也就是几本俄文教科书,但能将书本上的课文流利地朗读已经让她心满意足。一年四季,清晨庭院,诵读声不断。冬去春来,茶花盛放,白色的茶花簇拥在一起,如飘舞的白绸。花瓣垂露,盈盈欲滴,像从水中捞出来的白瓷碗,水灵丰腆,偶有几滴露珠趁着奶奶捧书朗读,悄悄滴落在书页上。两棵白茶花树为晨读送来了不少意趣,夏去秋至,茶花树的种子渐渐成熟,她的梦想也开始悄悄生根發芽。
年轮的漩涡把古厝里的物事交织成新的图景,这院子不仅属于奶奶一辈,在爸爸出生后更是他玩乐的天堂。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喜爱在院子里种花,以兰花和茉莉为主。夏日微风中,茉莉颀长的身姿摇摇摆摆,浅紫色的兰花宛若婀娜的仙女翩然而舞,流出丝丝醉人的茉莉清香,夹杂着兰花的芳馨。渐渐到了黄昏,一阵穿堂风吹来,吹化了不浓不淡的梧桐清香,也吹开了人们夜晚恬淡的生活。等待繁星爬上天际,爸爸和玩伴们熄灭了油灯,倚靠在大竹椅上,吃着切好的甜丝丝的西瓜,静静地等待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来了,来了。”一个男孩捏着嗓子指着花丛对伙伴说。“嘘!”其他小孩暗示他再小声点。夜色渐深,月光的清辉尽情倾泻在院子里。萤火虫越来越多,时机到了,男孩们悄悄捏着手上的玻璃瓶,每人选择一个地方,全神贯注盯着那些在低空盘旋的萤火虫,要是运气不错,一下子便能抓住萤火虫,然后握着玻璃瓶雀跃欢呼。玩伴们乐于共同欣赏,细细观察萤火虫的结构特点,在玻璃瓶中轻轻摆弄一会儿,再将萤火虫放生,让它们回归草丛,等待下一个夜晚的来临。爸爸和这些与他有着“萤火虫”之约的玩伴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假期。
龙岭顶上因为坡太陡而没能摘到的杨梅,一次没能约上的捉迷藏,小广场上的“风筝之战”依然胜负未分,新年时的“摔炮”好像刚从手中丢出就放完了。诸多的遗憾被留在了匆匆逝去的假期,期待下个假期的到来,属于这群孩子们的古厝里,还不知会上演怎样的新鲜事。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与双杭周边现代的高楼大厦相比,小巷、老屋、石阶、旧楼,古厝的一切似乎没能跟上城市发展的步调。在历经了住户搬迁之后,原本繁华的商贸之地,好像忽然被孤独地遗落在了城市的中央,犹如一颗渐渐黯淡的星辰。在新世纪出生的孩子们心里,甚至打上了“破败”的标签,只有零星的居民还住在里面。1993年,我家搬迁出上杭后,新家兜兜转转竟然还是选在了双杭周边,上小学时家人送我去学习书法,机缘巧合之中,我的书法教室居然就在上杭路。听了许多有关古厝故事的我不由感叹,人生中或许有太多如此微妙的际遇,冥冥之中好像有股力量,替我在偌大的福州城中做了一个选择。
上杭多年未经修缮,灰色的墙面斑驳,地上的石板坑坑洼洼尚未填补,此时的上杭自是不能和爸爸、奶奶眼中乐趣横生、念念不忘的古厝相比,但那缕醇厚的墨香,悠然地穿过上杭窄小的巷,一直陪伴了我好几年。那时,每周日晚上,我准时来到书法教室。书法教室就在上杭某条还算宽敞的巷子边,教室的左右侧对称地摆着一张张枣红色的木质桌子,中间留出过道,便于老师指导习字。教室的白墙上挂满了一幅又一幅书法作品,有些字体刚正,有些娟秀,有些墨迹未干,有些年代已久。从学习如何握住毛笔开始,到基本笔画,再到字帖临摹与渐渐能独立书写。我在这间教室里坐了四年,熟悉每一个季节的风混合墨香的味道。春日的风微微潮湿,混合了甘醇的墨香,不疾不徐地环绕在四周;纵使是夏日的晚风也带着一股闷热,须得墨香漫漫晕开,才能渐渐冲散这热浪;秋天的风带着夏季的余韻,但又透着凉爽,与墨香交融后碰撞出属于秋日的馨香;冬日的风自然是刺骨而不留情面地钻进袖口,我哪能闻得到什么墨香呢,鼻子和双手都被冻着了,捂热之后才能顺利练字。在古厝里学书法的这几年,比收获了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长久的定力与耐性,此后在面临很多令人焦灼烦躁的事情时,我时常会回想起在上杭练字的那些夜晚,让自己沉下心,更加冷静与专注。几年之后双杭大改造的计划正式实施,书法教室换了地方,而上了初中的我随着课业越发繁忙,很少再走进那条古旧的小巷……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古厝真的老了,古厝的故人如大树的根系一路分须攀延,伸向城市的各个角落与空间。古厝如同一位长者,是孩子们最可信的依托,他们从古厝的怀抱中走向城市、奔向外省、飞至大洋彼岸,可每当牵挂思念时,他们,又都是古厝的孩子。
那段时间双杭改造计划发布,全家人听闻旧双杭包括周边片区马上要拆了,心中好像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虽然都未直接言说,但奶奶会在中秋时忽然想起当年一同坐在屋前温习功课的三舅公,三舅公赴美求学后定居大洋彼岸,想念之余她随意写着“远渡重洋饱诗书,当年一别事难估。门前梧桐长大树,而今海外家常住”。我知道,她担心想念亲人的舅公回来后不见旧时古厝容颜,崭新的一切会抹去青春温馨的回忆。那时年幼的爸爸永远不会想到,在古厝里肆意玩耍的朋友会在很远的未来也成了事业上的伙伴,长大后的他们在一起聚会时,每当说起那些小时候的糗事,便会互相调侃。他不舍这承载着挚友们欢笑的古厝随着机器的轰鸣消散,提起时总有一点淡淡的伤感。于我而言,幼时心无旁骛闻墨习字的岁月也就此慢慢地消逝了,幻化成勾勒不清的轮廓,一阵风中的烟尘……
一花一木会枯萎,百年古厝又如何能长久地屹立在风雨中不朽呢?人与旧屋之间彻底的告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但转念思考,百年光阴,古厝的香火从不曾断离,一代又一代的子孙散布在更广阔的天地中,依旧惦念着往事,思念老屋与亲人。古厝的生命之根早以另一种方式植于大地,长出结实的根系,拴系亲缘。
古厝里的子子孙孙背负着沉甸甸的行囊,走向远方,在他们的身后,永远有一片魂牵梦绕的回望之地。
作者简介:林昕迪,女,福建福州人,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