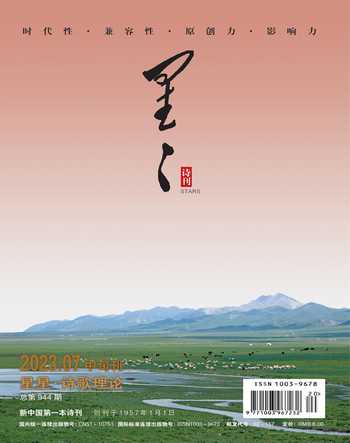让情感得到安放
2023-08-15
访 者:星星诗刊杂志社编辑李斌
受访者:陆辉艳
李 斌:你写诗有多少年了?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写诗的?谈谈你与诗歌的最早接触。
陆辉艳:我是在大学期间开始接触诗歌并开始练习写作的,算起来已经二十余年了。那时的阅读比较随性,零星地读到过曼德尔施塔姆、巴列霍、西川、于坚、海子等诗人的作品,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当时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这本诗集大概有三本,其中一本被我长期“占据”。最初的阅读促使我想去表达,也想自己写下点什么。大学三年级时,终于有一门诗歌创作选修课,导师是鲁西老师,一位优秀的诗人。诗歌创作课虽然只开设了一个学期,却一直影响着我的创作,至今我还保存着鲁西老师用红笔给我批改的诗歌作业。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更需要同行者的支持和鼓励,幸运的是,我受到了许多诗歌前辈和朋友的影响。
李 斌:你经常读哪些诗人的作品?个人的创作受到过哪些诗人的影响?
陆辉艳:刚才说到大學时代读的特朗斯特罗姆,还有扬尼斯·里索斯、辛波斯卡、雷蒙德·卡佛等都是我一直喜欢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的写作。特朗斯特罗姆作品中对事物的敏锐感受力,让我惊叹并启发着我的创作。扬尼斯·里索斯和雷蒙德·卡佛的作品,给我一种提醒,要用最少的语言写出更多的可能性。辛波斯卡能将人与事物之间、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处理得轻盈而巧妙。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的诗歌理念、审美趣味和表现方式。
李 斌:诗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看待生活、职业与你诗歌写作的关系?
陆辉艳:写诗对我来说就像是和自己交谈的过程,是生活的映照,我只是呈现自己所经历的、感受的、思考的,写下它们,是让情感得到一种安放,也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期待并被赋予意义。生活为我的写作提供一种底色和基础,它们之间是反哺与成全的关系。而职业是生活的前提,有新鲜的生活,一份并不无聊的工作,可以为诗歌写作提供更丰富鲜活的素材和灵感。
李 斌:怎样理解你诗中写到的“山川静美,亦是困境”?创作中是否也存在着困境?
陆辉艳:这是我一首诗中的一句,指现实的局限,更想表达一种相对的诗意。因为事物总是相对存在,我们眼中看到的这一面,有可能是他人正经历的反面;我们肯定事物的某部分,事物内部也许正发出否定的声音,就像河水看似自由,却囿于河岸。我的母亲孤独地守着受困其中的田园风景,而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去倾听她内心的声音是如何撕扯。她像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作为旁观者被动地参与历史的进程。我想写出在那片土地上面临的现实尴尬和困境,但显然没能深刻地进入生活现场。这种不在现场的写作,肯定会有它的疏离和隔膜感,会忽略现实乡村的复杂和多元,这也是创作中的困境之一。
李 斌:你对故乡怎么看?在你离开乡村后,重新回望乡村和童年经验,有了哪些新的观察和体悟角度?
陆辉艳:每个人都有自己唯一的故乡,它意味着人生的来路和归宿。我出生、成长在广西灌阳,挂念的亲人在那儿,美好和痛苦的记忆都在那儿,所以会有乡愁。消费时代的故乡一直在变化之中,它的人情味正在慢慢变淡。我离开故乡已经很久,平常说的回老家其实无形中和自己的来路已有了距离感。因此,故乡也意味着和过去渐渐疏离。一个人只有在离开故乡之后才能真正认识和重新发现它对自己的意义。当你跳出故乡的现场,用多种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会更客观、更敏感地看到人与人、人与土地的关系。
李 斌:你的诗中有对乡村的关注,也有对城市的集中书写。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创作中有何精神联系?
陆辉艳:两个地方都滋养过我。乡村,是我的精神之根和创作的精神源头;城市,锻炼我的独立和自省,开阔我的视野。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的“精神故乡”,在创作中会不断思考在乡村的经历和在城市的体验,这两者视角的相互转换,在精神上是可以相互渗透和互补的。
李 斌:诗人的写作过程有的是依赖灵感,有的是依赖经验,对你而言哪种更有效?请谈谈你一首诗的诞生过程。
陆辉艳:说不上哪一种更有效。所谓灵感,也是不断累积、酝酿和思考的结果,它来自个人的生活、记忆、情感和对生命体验的关注。灵感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契机,它需要跟个人的经验共同努力完成一首诗的创作。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们依赖的只能是经验、技巧、想象力等。比如我写《薄暮》这首诗,是在红水河短暂停留后写下的,前面三句几乎是自动地浮现在大脑里,这应该就是神秘而捉摸不定的灵感的到来吧;接下来的句子和结构,是经过几天的思考后才完成的。
李 斌:你写诗是喜欢边写边修改,还是写完后再修改?
陆辉艳:一般都是边写边修改,也有写完后再回过头来动用“手术刀”的。有时翻看以前写的在电脑里沉睡很久的诗,发现那些写坏了的、无从修改的就会果断删除;对于一些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的诗作,则会一遍遍修改,直到面目全非,似乎自己在某个时刻跟这个世界重新相遇了一次。
李 斌:你有遇到写作瓶颈的时候吗?你是如何突破的?
陆辉艳:出现瓶颈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不足而产生的茫然和阻滞。诗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现,保持写作的清醒容易,但一直保持创造力却异常艰难,因此瓶颈会一直都存在。出现瓶颈也是件好事,它意味着转机和新的可能。我目前所做的努力就是保持不断的阅读以及走进生活中去充实新的经验,至于能不能突破,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李 斌:你的家人、身边的朋友知道你写诗吗?他们会如何看待你的诗人身份?你的诗人身份对你生活有影响吗?这种心态会阻碍诗歌的创作吗?
陆辉艳:我父母知道我在写东西,但并不知道是在写诗。我的兄弟姐妹和身边的朋友知道我写诗,但很多不一定读过。他们有两种态度:一种觉得写诗这样的行为离他们的生活有点远,但还是保持理解和认同;一种表示不太能理解,在他们看来,在这个物质时代人们不需要诗,写诗也不能真正改变生活,在不远的某一天诗歌会被其他事物取代。我一直很珍惜自己“诗人”的这个称谓。十多年前我从某少儿报刊社离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写诗这件事,似乎写作者与他的处境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尽管文学的慢正在遭遇现实的尴尬,但从诗歌是为内心的失败和自我观照而写的意义上来说,反而可以激发我的诗歌写作动力。
李 斌:你的诗中是否倾向女性经验的书写?
陆辉艳:我自己作为女性,创作视角本身就带着性别因素,但我没有刻意地去描述女性经验。事实上,在我的创作中常常会不经意地淡化性别意识,我将这种精神理解成物理学中的“中性”,它们的正电荷和负电荷数量相等,那里面同时居住着男性和女性。
李 斌:你怎么看待诗歌的平民立场,以及平凡個体和诗歌的关系?
陆辉艳:诗歌创作中的平民立场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和对平凡个体的观照。诗意就藏在普通人的生活和个体体验中,和每个平凡的个体息息相关,不写作的人永远意识不到这一点;写作的人一定要具备独特的观察和发现能力,并能将这些真实的瞬间转化为诗歌。
李 斌:你认为自己的诗歌中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吗?
陆辉艳:我理解的地域性是一个诗人在作品中的现场感。我们总是借助自己生活中感受到的空间物象来表达所思考的东西,我的创作肯定会受地域经验和文化的影响,但情感的表达和审美是普遍性的,不能被地域所局限。
李 斌:你的诗中经常写到自然给你带来的启示,你是如何处理自然题材的?
陆辉艳:大自然的丰富性对我有永恒的启示,呈现的一切都在教诲着我。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乡村度过,零距离与大自然的接触,既对我的成长进行着重要的生死教育,也无声地成全了我。和自然相遇的经历让我着迷并记忆深刻,它们在很多年后成为我写作的资源库。而近十来年我定居于南宁市郊,这儿离邕江和旷野都很近,它敞开的一切常让我有意外的发现和收获,也让长期独处的我有更多机会在自然中享受那份难得的安宁和孤独。隐秘的自然会启示另一种惊喜和美妙的想象力,当我凝视自然,从不同视角去观照它时,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就会慢慢转化,让我感到自己同时也被凝视和观照。大自然作为一个“艺术家”,用它的耐心呈现和力量校正着我的思维及语言,并启发我写出一首可以被感受的诗。这个过程似乎有一种神秘的距离,让人想去靠近,去表达。
李 斌:你会将你的情绪带到一首诗中吗?
陆辉艳:诗歌主情,本身是处理情绪的一种方式,但它同时还是理性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一首诗中的情绪,是经过了冷静处理后的呈现和表达,所以它是抑制的、滞后的,而非肆意倾吐,只有这样,才更能客观地、纯粹地描写一种生命体验。我很多时候在触发某种情绪时会先记录下来,而后去琢磨当时的感受,厘清它的来源,慢慢才会形成一首诗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