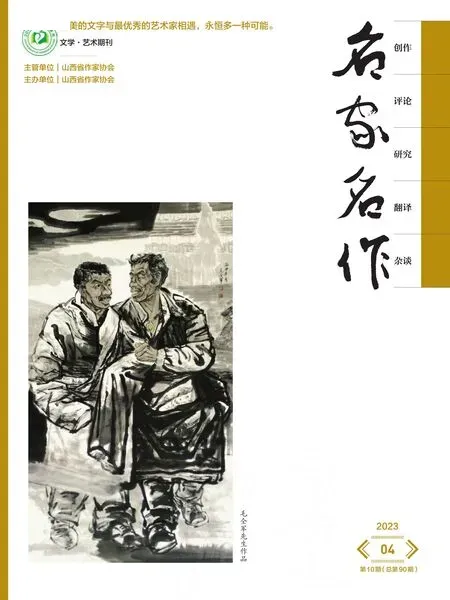论《快乐基因》中的伦理选择
2023-08-14李佳轩
李佳轩
作为最具科学素养的小说家之一,理查德·鲍尔斯以其“信息小说”享誉文坛,《快乐基因》是其又一部人文情感与科学技术相碰撞的作品。该小说将时空背景置于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描写了物质富足的美国人深陷心理危机、渴望精神生活幸福的生存境况。
《快乐基因》讲述了追寻幸福密码的故事,小说分为两条平行的故事线:一条线是罗素·斯通在临时任教的写作课上被异常快乐的萨沙所吸引,因此寻求心理咨询师坎迪斯的帮助,一同探索萨沙的幸福秘密;另一条故事线则是借助不盲从科学的电视主持人托尼娅·谢夫与研究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家汤马斯·科顿之间的对话,展现了一场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冲突。两条故事线相遇,萨沙与科顿发生了联结:科顿的团队发现了一组与情绪相关的基因,而萨沙成为该研究成果的有效例证。但在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下,萨沙最终不堪重负,酿成了自杀的悲剧。本文将通过文学伦理学进行解读,深入阐释“追求快乐”的伦理内涵。
一、罗素的伦理选择:对他者的绝对责任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罗素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不同阶段的伦理身份逐步呈现,由此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写作事业不得志的罗素只得从事于编辑行业,之后又被聘用为写作课的临时教员。然而他并非无可替代,因此也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他承担起了教师的责任,身体力行地实践了对应的伦理选择。
在任课的过程中,罗素逐渐被萨沙异常快乐的特质所吸引。本来自卑的他备受萨沙的鼓舞,找到了自我定位和自我价值,开始满怀激情地书写萨沙的故事。他写道:“她站在门口,笑得就好像刚去过迪士尼乐园一样。‘真是不可思议!太奇怪了’”。随着罗素对萨沙的不断观察,二者间的伦理关系也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罗素和萨沙约见面谈,探讨她的生活经历,他甚至尾随萨沙了解其住处,被她发现后而心跳加速。罗素在内心里已经萌发了对萨沙的情愫,但是身为教师的他没有打破伦理禁忌。由于担忧萨沙患有轻度躁狂症,他向本学院的心理医生坎迪斯寻求咨询。坎迪斯的外貌酷似罗素前女友格蕾丝,罗素对她一见倾心。二人原本只是同事关系,可萨沙成为罗素和坎迪斯之间的沟通纽带,他们两人结为萨沙的同盟,立志以教师和朋友的身份保护她。但当萨沙被卷入强奸未遂案,罗素跟警方透露了她的异常状况,怎料信息迅速传播到公众平台,他的擅自判断给萨沙贴上了“情感增盛”的标签。罗素深感自责,却因为自己的懦弱一直没有做出实际行动来抵抗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公知,畏缩在道德冷漠状态中。
担负对他者的绝对责任是后现代西方伦理学所推崇的,所谓“他者”是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物。它暗示了一切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狂热又冷漠的公众肆意消费萨沙的信息,几近崩溃的萨沙向罗素和坎迪斯寻求帮助。大众媒体通过虚构萨沙的形象,加剧了她与他人的心理隔阂,使她的“脸”被抹去。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坎迪斯一直认为萨沙的抗压能力很强,既然战乱之痛、丧亲之殇都不能摧毁她,公众的舆论对她来说不算什么。他者之“脸的本质是道德的”[1],真正的关怀是要放弃自我对他人的判断,倾听他人的呼唤,回应他人的需求,对他人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2]罗素不再将萨沙视为“情感增盛”的恒定体,而是时刻关注她的心理变化。“人不能仅只是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且还要明确地履行实践自己的责任,并将此当成真正实现自身本质的必由途径。”[3]当全世界都唾弃萨沙时,罗素站了出来,愿意帮助她逃离美国。这是有担当的伦理选择,履行了身为教师的义务。“责任类似于人质的回应……它不要求相互性的回报。这就是友谊和为他人赎罪这些观念的基础。”[4]此刻,罗素与萨沙的伦理关系已超越师生、恋人的伦理关系,而更倾向于亲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罗素陪同萨沙一起逃往加拿大的旅途中,二人的关系也愈加亲密。最终,萨沙将罗素的药都一饮而尽,罗素发现之后懊悔不已,埋怨自己为何没有时刻陪伴在萨沙身边,为何没有好好守护她的幸福秘密……
罗素的多重伦理身份,使他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他与萨沙和坎迪斯之间伦理关系的转变,推动着故事的进程,也由此构成了故事的一条伦理脉络。
二、萨沙的伦理困境:自为与自在的对抗(孤独—焦虑—迷茫)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5]萨沙经历了阿尔及利亚的战乱后,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将其作为她的避难所。“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6]萨沙乐观的本质是由自己的主观意志创造出来的,身处新环境的她积极进行自我调适,与同学们构建良好的伦理关系。“她尽量不出于悲伤讲述自己的经历,履行了移民的‘幸福义务’。”[7]通过这样的努力,萨沙“快乐女孩”的伦理身份才得以确立。
萨沙第一次伦理身份的转变,是她从一个真实鲜活的生命变成公众所追求的幸福符号。媒体夸大宣传萨沙的虚拟形象,以煽动民众情绪。萨沙的快乐在公众的狂欢中被极度放大,与此同时,她的真实身份也被极度缩小为没有实质的符号。在公众眼中,萨沙是抚平他们伤痛的“神”,但是萨沙作为一个普通女孩与神之间构成了伦理悖论,也由此形成了她的伦理困境,“是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对于这些精神匮乏的白人来说,萨沙特殊的“快乐难民”伦理身份使其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他者”。在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冲突中,萨沙感受到了孤独。人们忽略了她的自为存在,以为她的情绪是恒定的,即使萨沙对他们的信件一一回复,企图纠正他们的认知。
在与日俱增的信息轰炸中,萨沙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身份发生了不可逆的转变:“他们使我如同一个为爱马仕生产的生物加工厂。”在科学商业化的社会中,她作为个体的存在被扼杀,只能被动地接受外界赋予的角色和身份。焦虑的她渴望能够在这荒诞的世界中塑造自我的伦理身份,并获得存在的意义。
为了摆脱异化、主宰自己,她决心上欧娜秀来澄清自己的幸福秘密,以重建伦理身份。萨沙直言科顿基因工程毫无意义,这惹恼了“技术拜物教”的狂热信徒。在观众的倒彩声中,萨沙陷入了迷茫。“我只是在享受这世间的生活而已。他们为什么要拿我当作治疗人类文明的一帖药?”一方面,萨沙作为个体必须不存在,她真实的情绪遭到忽略;另一方面,她必须以幸福符号的形式存在,这是她义不容辞的伦理责任。在这般伦理悖论中,萨沙感到无所适从,选择了暂时逃离美国社会,然而她避难的灯塔却遭到了记者的入侵与扰乱。
萨沙第二次伦理身份的转变,是她决定出卖自己的卵子。当人们疯狂竞标她的卵子,此刻她已经成为幸福商品而被明码标价。不管是尝试否定自在,还是暂时逃离自在与自为的冲突,萨沙都难以摆脱被物化的命运。无能为力的她只得屈服于资本主义的亵渎逻辑,售卖卵子以资助弟弟的学业。这时,公众对她的态度出现了两极分化:在科技迷信的刺激下,人们膨胀的消费欲望涌向了萨沙,有经济能力的人对她的卵子疯狂竞标;而其他人发现自己无法购买幸福时,便恼羞成怒。公众对她恶意的攻击让萨沙陷入了终极伦理困境,她从无辜者逐渐变为众矢之的。在自在与自为存在的张力中,萨沙发现自己无法在她的意志和现实之间的冲突中平静下来,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萨沙重构伦理身份的想法化为泡影,最终选择自杀。
三、科顿的伦理选择:对科研的绝对自由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在祛魅的世界中,“技术拜物教”取代了宗教神权,资本统治与技术理性共谋,变成了非理性的意志力量,促使科顿宣扬超人类主义的幸福幻想。“一旦兽性因子超越了人性因子,伦理意识就会丢失,就会使人失去理智,甚至变得不道德。”在利益的诱惑下,科顿体内的兽性因子不断膨胀,这导致他不切实际地追求所谓的基因幸福工程。
在“超越极限”的电视节目上,科顿化身为坚定不移的传教士,随心构建自己的超人类主义话语。在偶尔谨慎的理性包装下,他企图将狂热的信念冒充为真理,而且为其赋予道德的合法性。我们的道德和政治责任是尽我们所能防止公民“比其他情况下更不快乐”。在自在与自为存在的对立中,科顿将二者进行了巧妙的组装。一方面,他抚慰了公众:是“快乐基因”这样的自在存在让我们缺乏幸福;另一方面,他鼓舞了公众:而人类可以借助基因改造技术获取幸福,实现自在到自为的升华。而这其实构成了伦理悖论:基因决定论是相信本质限制存在;而自由修改基因又意味着存在颠覆本质。前者将个体物化,贴上了标签;后者忽略了自在的客观存在,陷入了绝对自由的误区。在人的自由选择中,萨特提出了“绝对的责任”“它直接是我们自由的结果的逻辑要求”[8]。在自由选择的同时,必须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内涵是一种善良行为、动态意向或道德向度。科顿固然可以自由做出选择,但是也必须要为自己、为他人负责。
由于资本和传媒的鼓动,兽性因子打败了人性因子,他逃避了作为科学家的伦理责任。“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为全人类做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9]采访中,他句句驳斥主持人托尼娅·谢夫的质疑,而在镜头之外,却对自己的信口开河感到愧疚。他在镜头内外的态度形成的对比,体现了体内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一直在做激烈的斗争。
当高扬主体性的人无比崇高地宣称自己的自由,并愿意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时,他却突然发现,当他真想去行动时,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10]。科顿的研究打着全人类幸福的旗号,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行为会给萨沙带来的后果。他对欧娜秀上萨沙的抗争感到不解,更无法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对她的责任。因为萨沙于他而言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实验样本,甚至是一个待价而沽的牟利工具。当萨沙为了扶助自己的家庭决定拍卖卵子时,他却只想索要自己的知识产权,并不在乎萨沙的决定对她自己的意义。看似敬业的科顿用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一次次错误的伦理选择,使他成为一个狂热的超人类主义梦想家以及一个冷漠的唯功利主义资本家。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记者托尼娅·谢夫,她坚守媒体人的道德准则,不满于媒体对萨沙的诱导性报道而愤然离职。“这场闹剧把她毁了。你们把那一段访谈切掉了,那本来可以让她看起来——”托尼娅因为自己长期以来和节目组的串通合谋而自责不已。而科顿直到最后,伦理意识也没有被唤醒,只是感叹大环境下的科技实用主义却不考虑人类的幸福,殊不知自己从未考虑过萨沙作为个体的喜怒哀乐,更从未关注过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天灾人祸。
四、结语
在漫长的自然进化中,人类无法摆脱自然规律的控制。可是基因工程打破了人类对生命的敬畏感,擅自扮起了上帝的角色,企图创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在人类理性与欲望的斗争中,一旦欲望占据绝对上风,科技就会完全沦为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可见,科技的迅猛发展虽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如果不受伦理的约束,便会引发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
因此,科学家应该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规避伦理风险,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是通过伦理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立足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通过分析人物的伦理选择,可以揭示基因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为技术发展提供伦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