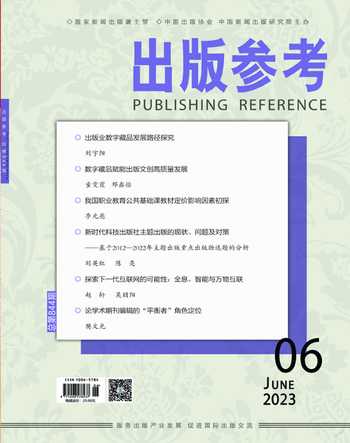外国作家译名考辨及编辑出版的考量
2023-08-10姚翠丽
姚翠丽
摘 要:外国作家译名的规范和统一,一直是翻译界、学术界与出版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出版物中同一人出现多个译名的情况依然很常见。本文以美国当代诺贝尔奖作家Louise Glück的几种中译名为例,结合该作家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分析这几种译名的翻译理据及接受情况,并探讨译名统一的可行性办法和编辑出版的考量。
关键词:译名规范 Louise Glück 中译名 翻译理据 编辑出版
外国作家译名的规范和统一,一直是翻译界、学术界和出版界所关注的问题,虽然呼吁译名规范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各种出版物中,仍能见到同一人有多种译名的乱象。规范译名,从大处说,事关文化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效率;从细处说,涉及读者接纳信号和理解信息的便捷和融通。具体到编辑出版领域,译名的规范与否,不但是对读者负责的问题,还经常会牵涉书稿编辑工作中多个层次文本的相互牵制关系。譬如,正文译名尚可规范,引文和注释却用了不同的译名——因为所引用作品的译者如此翻译。既是引用,就无法做与正文统一的修改,而正文又不可能向不规范的译名统一,这样就导致同一页中存在两种以上译名的困境。笔者因编辑一本文学史而接触到美国当代诺贝尔奖女作家Louise Glück(1943— )[1]。作为第十二届(2003—2004)美国桂冠诗人、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名字被载入文学史是必然。然而,这位作家的匈牙利裔身份背景,及其姓氏的个性化发音,使其中文译名具有了复杂性。笔者在对作家译名做查证时发现,到目前为止,有资料可考的该作家的译名就有多种,且抛开姓名中“名”的部分,只聚焦于在指称功用上更为重要的“姓”的部分,就有“格拉克”“格吕克”“格丽克”“格里克”“格利克”这五种。因为文学史的严肃性和学术性,其中的作家译名经常会为翻译界和学术界所参考,所以译名一定要准确、规范。本着这样的宗旨,笔者对上述几种译名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探究这些译名的翻译理据,分别从译理上,从多原则交叉重叠的辩证关系上,综合考量做出选择;继而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探讨该如何应对译名规范和统一的问题。
一、结合译介与传播、基于译名原则的译名考辨
当一个外国作家的名字进入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时,他的作品至少已经在国内传播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传播的过程离不开译介和发表。Louise Glück正是如此,她的作品从1989年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至今有三十多年了。这期间,她的名字被不同的译者翻译成不同的中译名,发表在各种期刊上,从零碎的几首诗歌,到十几首,再到几十首,最后以诗集的形式出版。诗人的名字随着被翻译的作品出现在刊物上、图书里,被传播、阅读、接受,然后再传播,等到其进入文学史时,已经有了多个备选形式。所以说译名的形成和译介与传播的关系密不可分。
根据熊辉教授所撰《露易丝·格丽克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2]一文,可以看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译者/文章作者对这位作家姓名的翻译之不同。而作为严肃的译者或研究者,在确定一位作家的中译名时,应该会依据一定的译名原则。一般来说,外国人名汉译主要遵循三个原则:约定俗成、行业标准、名从主人。这几个原则在使用中是有优先顺序的,这个顺序跟时间有关,也與译介、传播和接受的历程相关。
1.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是指某个人名的翻译结果经过长时间的应用后,被人们广泛认可,并固定下来,不再变更。[3] 如大家所熟悉的作家萧伯纳(Bernard Shaw)、赛珍珠(Pearl Buck)、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等,这些译名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应用,被人们广泛认可,并固定下来。即使不符合现行的行业规范或发音原则,也不会再做变更,即定名不咎。一般来说,初次接触一个外国人名,译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查考一下此人名是否有约定俗成的译名,如果有,就需要遵循已有的译名。如果没有,再考虑遵从其他原则。
Louise Glück作为当代作家,其作品被初次引入中国时,尚无约定俗成的译名,所以译者需要依据一定的翻译原则给出译名。1989年,彭宇在他所翻译的《在疯狂的边缘——美国新诗选》[4]一书中第一次将Louise Glück译介给中国的读者,书中收录了77位诗人的355首译诗,其中Glück的诗只有4首,她的名字被译为“路易丝·格拉克”。“格拉克”这个译名暂时找不到翻译理据,它既非约定俗成,也不符合行业规范,因为,它与行业标准所规定的任何一本工具书里的译名都不符。客观上,当时工具书不足[5],互联网还没有开始使用[6],对翻译的查考带来局限性;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望形生音”的可能性。即使在不缺少工具书的时代,不经过查考就根据自己猜测的发音给出译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譬如美国女作家Ursula Le Guin,她的中译名就有“勒古恩”“勒奎恩”“勒吉恩”等“音译”。
在这种情况下,译名翻译中遵守行业标准和遵循行业规范就显得尤为必要。
2.行业标准
为了做到译名规范统一,更加准确而高效地传播文化和信息,出版行业在外国人名汉译方面是有统一的行业标准的。它要求实行我国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写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及其附录“世界各国及地区语言、民族、宗教和人名翻译主要依据”等行业标准,同时还有行业内统一使用的人名查考工具书,如辛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法、德、俄、意、西班牙、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等。有了明确的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译者在翻译外国人名时,就有据可依,有工具书可考。这一点在Louise Glück译名的变化中明显可见。
1996年7月,脱剑鸣在《兰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论格律的回归与美国“新形式主义”诗歌》[7],文章的结尾部分提到了“路易丝·格吕克”。2003年,《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了杨锏的文章《路易丝·格吕克:美国的新桂冠诗人》[8]。2004年,“诗生活”网站发表了周瓒翻译的《露易丝·格吕克诗选》(5首)和金舟翻译的“路易丝·格吕克的诗30首”。2004年,《诗刊》发表了周瓒翻译的《露易丝·格吕克诗三首》[9]。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第8卷)附录“诗人的传记”里有“路易丝·格吕克”。2009年,舒丹丹在《诗歌月刊》第1期上发表了她翻译的《露易丝·格吕克诗选》,并附文《露易丝·格吕克:〈暮色中的鸢尾〉》。2010年,《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10]提到“路易丝·格吕克”。2014年《英语世界》第5期刊登了杨金才、顾晓辉翻译的“路易丝·格吕克”的诗歌《晚祷》[11]。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文学大词典》在“美国桂冠诗人”词条下,列有“路易斯·格吕克(2003—2004)”[12]。2016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编美国女性文学史》[13]里用的译名是“露易丝·格吕克”。2019年,《文学港》第12期刊登了黄继平翻译的《格吕克诗选》,诗人的名字翻译为“路易丝·格吕克”。从上述Louise Glück译介和传播的载体可以看出,从20世纪末起,至今将近三十年,“格吕克”这个译名被清晰确定,并广泛传播,其中包括几部重要的文学史和数家业界知名报刊。
“格吕克”这个译名的翻译符合行业规范。根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1993版),Glück对应的译名为“格吕克〔德、捷、匈、瑞典〕”,译名之后还标注了适用的国家,Glück作为匈牙利裔,她的姓氏的发音适用于这个范围。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格吕克”的译名是符合行业标准和规范的。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遵从行业标准,是解决译名规范和统一的有效途径。这个原则值得推广。
3.名从主人
译名原则中的“名从主人”,是指人名翻译一般采用音译,即按照其所在国家的官方或通用语言的标准为准音进行翻译。对于具有明显民族特征的外国人名,如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人名,则参照其原民族语言译名规则进行汉译,不可一律按照英语发音来译;有时还需要遵从主人的意愿,或者主人自己认可的发音。实际上,出版行业指定参考的所有工具书,都是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翻译的,所以这两条是一致的,其中有相互重叠的成分。对于一般的人名翻译来说,符合行业规范的,也都是符合“名从主人”原则的。但是,当人名的“主人”对自己的姓名发音有了特殊的、个性化的规定时,译名情况就会变得复杂。Louise Glück就属于这种情况。上文中说“格吕克”的译名符合行业标准,即符合“名从主人”原则的第一个层面,Glück作为匈牙利移民,其姓氏发音符合其所源自的母国语言,符合普遍性的音译。然而,身居美国的Glück一家将自己的姓氏发音做了美式规定,于是就需要关照“名从主人”原则的第二层含义,即音译还要遵从人名“主人”的意愿。
随着2003年Louise Glück成为美国桂冠诗人,其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热度大增,且对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变得深入。一些之前不为人知的信息也被发现,原来Louise Glück姓氏的发音有个性化的规定,这个信息主要来自互联网:
Louise Glück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and raised on Long Island. Her father,Daniel Glück,an immigrant from Hungary,wa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who helped develop and market the familiar household X-Acto Knife.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pronounce their name as “Glick”.
译文:Louise Glück出生于纽约市,在长岛长大。其父名叫Daniel Glück,是匈牙利移民,曾经帮助开发和销售熟为人知的X-Acto 牌家用刀具,是一位成功的商人。Glück一家把自己的姓氏念为Glick。
这段英文资料的最后一句特别指出“Glück家人称呼自己姓氏的发音是Glick”。另外,维基百科上也有一处英文资料可以支持这一点:“Louise Elisabeth Glück (/ɡl?k/ GLIK; born April 22, 1943) is an American poet and essayist. She won the 2020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Louise Elisabeth Glück (/ɡl?k/ GLIK;生于1943年4月22日),美国诗人、散文家,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关于Glück的这段文字,在她的名字后面特别标注了Glück的发音为/ɡl?k/,相当于英语里的GLIK。
从译介和发表的资料可以看出,柳向阳从2007年在《诗选刊》第7期“外国当代诗人作品特别专号”上发表译作《路易丝[14]·格丽克诗歌》起,到2016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柳向阳主译的两部Glück诗集[15] ,这期间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Glück诗歌译作和评论几十次,一直都使用“格丽克”这个译名。至2020年Louise Glück获诺贝尔文学奖,译名“格丽克”因先前出版的柳译诗集而开始传播和被引用。
根据名从主人原则的第二层含义,译名翻译要遵从“主人”的意愿,或者“主人”认可的发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格丽克”这个译名,更贴近作家姓氏实际上的发音,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类似情况,还有美国当代作家安妮·普鲁(Annie Proulx):译名手册中Proulx对应的译名为“普罗克斯”,而互联网上的英文资料却显示“Annie Proulx's name is pronounced as: Proo”(Annie Proulx的姓氏发音为Proo)——像这类特殊情况,并不罕见。
然而,“格丽克”这个译名有它的不足,就是“丽”字的选用。从同源资料可以看到,女诗人的名字是Louise Glück,其父名为Daniel Glück,其祖父名為Henrik Glück,也就是说Glück应该是家族姓氏,男性亲属也共用这个姓氏。而在中文里“丽”字则偏向女性化,如果按照译名统一的原则,将诗人的父亲和祖父也翻译成中文,都称为“格丽克”先生,笔者认为这种将家族姓氏赋予女性色彩的译名方法不妥。
在“格丽克”译名出现四年之后,“格里克”和“格利克”这两个译名也出现在刊物上。如:毛凌滢于2011年发表在《中国诗歌》第8期上的《路易斯·格里克诗选》,译作后附有题为《桂冠诗人格里克及其诗歌》的文章;殷晓芳于2013年在《外国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她翻译的“路易斯·格里克”的《诗九首》,同时作为Glück诗歌的研究者,她先后发表了三篇研究文章,文章的题目里全都用了“格里克”[16][17][18]。赵娜于2021年发表于《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第9期上的文章《“此像非我所愿”:格里克诗中的女性形象》中也用了译名“格里克”。而“格利克”的出现更晚一些: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的由付海钲主编的《忍冬信札》中提到一句:“最后,把前些天读到的一首诗分享给大家,诗的名字叫《海棠》,作者是露易丝·格利克。”
从发表的时间链条看,“格里克”和“格利克”出现得比较晚,可以看作是对“格丽克”在用字上的修正。
“格里克”这个译名既符合/ɡl?k/的发音,同时作为家族姓氏,在性别指称上也比“格丽克”更具包容性。那么,“里”字是否准确?这就涉及音译中的汉字选字问题。译名翻译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需要以专业、权威的工具书为依据,而不是随心所欲、凭自己的喜好去选,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同一个人名的译名是统一的。在译名选字方面比较全面的工具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辛华编写的《译音表》[19]。Glück转音之后的Glik/ɡl?k/适用于“英汉译音表”,其中的国际音标/i/与它前面的/l/搭配,/li/的发音对应的汉字为“利”,而“里”字对应的发音则是/r/与/i/的搭配/ri/。
由上推论:在“名从主人”的自定义发音原则之下,Glück的译名,既符合读音,又符合译音用字规范的是“格利克”——遗憾的是,用者极少。
名从主人的译名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有其复杂性,首先是族裔层面的普遍性关照,即符合一般的行业规范;其次还要关照到人名主人的个性化特征,即自定义发音。在第二个层面上,除了发音贴近,还需要选字准确,符合译入语境的文化传统。
4.三个原则的辩证关系
译名翻译的三个原则之间,经常会有交叉和矛盾。在这些交叉和矛盾的关系中,总有一种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
“约定俗成”是优先于其他原则的,约定俗成的译名首先是出现时间早于其他译名,在实践中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被广泛接受和沿用,这样的译名,确定之后则不再改变,即定名不咎。“行业标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含的是一个系统的行业规范和指定的参考书目,既有方法,也有原则。这其中就包含了“名从主人”的音译的普遍原则,所以“行业标准”与“名从主人”两者是有交叉和重叠的。“名从主人”的原则分两个层面,第一层是符合行业规范的,可以纳入译名音译的普遍性范畴,符合工具书上的规定;第二层则是一种个性化的特殊规定,即主人的自定义发音,这一层因为信息经常是隐没不见的,所以比较容易被忽略。虽然从译理上讲,当“名从主人”原则中第一层与第二层发生冲突时,应该遵从第二层的规定,即遵从主人的个性化发音。然而,如果第二层的信息一开始不为人知,而第一层面所发生的译名早已出现并沿用多年,已经广为认可和接受,那么,第二层所发生的个性化译名即使更符合“名从主人”的译名原则,也要服从之前的定名。这样才不至于造成混乱。
在Glück的五个译名中,“格吕克”是最早出现且符合行业规范的译名,至今已通行近三十年,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使用者包括几部重要的文学史和多家业界知名报刊。可以说,“格吕克”在符合行业规范的前提下,同时最为接近“约定俗成”的社会效果。相比十余年之后出现的“格丽克”,以及更晚时候出现的“格里克”和“格利克”,“格吕克”作为社会性的语言符号,具有更稳定的特性,指称明确,便于统一使用。“格丽克”“格里克”尚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具有不稳定性,且在用字上各有不足,不便于统一使用。而“格利克”虽然发音和用字都符合译理,却受众很少,不便通行。至于Louise Glück的教名Louise,译名手册里的规定非常明确:男子名为“路易斯”,女子名为“路易丝”。所以综合考量,“路易丝·格吕克”是考辨之后的选择。
从上述译名考辨,可见实际翻译中译名规范的复杂性和规范、统一的难度。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译者的自觉守范,还需要编辑出版环节的努力。
二、编辑出版的考量与对策
1.译名规范,编辑有责
既然译者是传播的源头,而报刊和图书是传播的媒介,那么责任编辑在译名传播过程中就起着重要的把关作用。如果能從源头上做到译名规范,大范围的统一就不会那么难。只有做到译名统一了,才会提高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效率。所以说译名翻译绝非小事。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引进,一般都是独家授权,只有一个入口,所以第一家翻译引进作品的报刊/出版社对作家译名的传播负有重要的责任。如果作家译名不符合规范,出版之后必然会引起各种争议和纠正,如此很容易造成译名的混乱。所以说,译名规范,编辑有责,报刊、图书编辑首先要从意识上重视译名的规范问题。
2.勤查考,不怠惰
有了责任意识,还需要有方法。其实,要做到译名规范并不难,一般的、常规性的译名,只需要查行业内指定的译名工具书,都可查得。个别查不到的,可根据其相邻单词的相似度,比对《译音表》(商务印书馆,1973),也可以得到发音相近的译名。同时,可利用互联网,进一步关照作家信息,探查作家的身份背景,这类文化信息对译名的准确性很重要,尤其是对约定俗成的译名,要避开知识的误区。一旦有被忽略的作家信息,就可能导致译名不准确。设想,如果Louise Glück的译名一开始就关照到了作家姓名发音的特殊性,做到从发音到用字都准确,很可能就不会造成后期传播中的乱象。所以,对于来稿中的译名,编辑要勤查考,不怠惰,做到一开始就准确。
3.遵循行业标准,不盲从
面对并非首译且已有多种译法的译名,既不能盲从、一味跟着时下流行的译名走,也不能随心所欲、根据自己的喜好起名,而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按照译名翻译细则来定。正规的出版机构一般都会有自己的编译体例细则,这个细则是编辑与译者共同使用并遵守的,其中对人名翻译有明确的规定,包括指定使用的工具书和参考书,以及当出现译名不一致时要遵循的优先顺序。有了这样的编译体例细则,译者和编辑就有了可遵守的准则,有规可依,有据可查,就可以从源头上规范和统一译名了。
有了上述三方面的考量,编辑就可以综合多个因素,大致做出符合出版规范的译名核定了。
(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