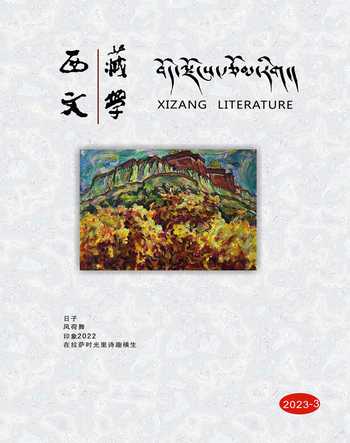风荷舞
2023-08-09唐咏梅
一
兜兜转转,凉风牵引着我,来到一条清浅小溪边。河风,带来花香的味道。
河谷青山深处,还藏着一个秘密花园?
沿河山谷狭长、幽深,阳光爬上东山顶,半山腰上照着,路面沾染露水,潮湿、阴凉,如初秋清冷。骑行一小时许,河湾处,忽现几枝艳红的花,在绿叶间摇晃着,远远地,分外抢眼。一阵河风迎面吹过来,往鼻孔里猛灌,呀,是花香,真好,荷花的香,清新醉人的荷花香!
十里外,河风中醉人的花香,原是从几百亩拾阶而上,满山满谷的荷田中漫溢出来的。沐浴金色晨光的村子,融进了花香的海洋。小溪北岸,六七栋楼房,两层、三层高的,果树林中露出红色尖顶。李子树、梨树、桃树,暗绿的叶子下,挂满累累青果。屋后山林上空,飘浮几炷炊烟。
不见一个人影。
树荫下,清溪旁,只有阳光,只有清风,只有花香。
右边,一条小沟渠,从马蹄形山坳里流淌出来。浓阴覆盖的水柳下,清水漫过两边的荷田,流进村口小溪里。渠边窄些的小路,荷叶探上来,一枝一枝雪白的莲,撒落绿叶间;左边沿河,水泥乡路绕着荷塘,莲叶深处,一朵一朵红莲、粉莲怒放。
站立岔路口,闻著阵阵花香,犹疑着,不知该走哪一边。阳光斜照身后山顶,我的半个身影印在水泥路面。村子一半沉浸明净朝晖里,一半笼罩大山阴影里。我决定从亮得晃眼的左边开步,迎着东边的太阳光芒,沿河边宽些的水泥乡道走起。
一丛一丛盛开的红莲,向我扑面迎来。
绿海中,一枝白莲怒放,离人三五丈远。荷叶挤爆荷田,淹没一道道田埂,凭着田垄间隐约错落的折线,拨开荷叶钻入底下,寻找田间小路。攀越几道田坎,从青青圆叶间又钻出来,踮起左脚,倾斜身子,伸手想去触摸那朵白莲,够不着。她站在一丘大圆田水中央,任你从哪个方向探身,伸手都够不着。仿佛特意选的,只许人隔空看着,隔水闻着她的香。
她静静地立于团团碧玉间,脚边留下三尺见方空隙,小丛嫩叶围成一圈儿,低低地,为她托举着裙摆,远些,几枝绿伞高擎,又大又圆,为她遮挡渐渐灼热的阳光。雪白的十二个花瓣,飘浮重重绿叶之上,从花萼底部向花瓣尖儿,全是玉白色,高远蓝天下,晨曦中,泛出美玉无瑕的清辉。最可人的是,瓣尖儿上一抹胭脂红,恰似古代闺中少妇的樱桃小口,娇俏,妩媚,春意浓,无意点染的国色天香,浑然天成。叫你呼吸急促,心口发烫,要往那玉质清辉的美人儿脸上,亲一亲她甜香醉人的小 嘴儿。
一枝盛放的白莲,晨风里忽儿向左,忽儿向右倾倒,娇软腰肢低垂,招人伸手去扶,她的圣洁,清雅,又使人胆怯,不忍出手,怕弄脏了她。她是春天的白玉兰,肌肤胜雪,细腻光滑,触手处,定清凉无比;雪白的十二个瓣儿,尖瓣一点点胭红,含着鹅黄花蕊,半露半隐,送出阵阵浓香。风来了,她掩嘴,羞涩地笑。“我那么香,你可恼了?我可不是故意的呀!”又一阵风扫过,花瓣儿散开,又聚拢,将花心拥紧,隐藏。
贪恋着一枝白莲的美,一次次拉近、推远,镜头里收藏的她,风情无限。她在我心湖起舞,仙袂飘飘,含羞带娇,送我醉人迷香。想象着,指尖触摸着她似雪如玉的肌肤,到底是怎样的清凉、丝滑,隔着丛丛碧叶,绕着大圆田,转了一圈又一圈,总没能够着。凭你遗恨千载,一眼万年,她自无知无觉。风吹过,仍静静伫立荷塘水中央,不摇,不动,脚下清波里,她的倒影玉洁冰清。她的身后,更多的白莲闪现荷田间,半开的,全开的,已落半边的,星星点点,数也数不过来,像一束束白色的光焰,点亮绿色的海。
九点多,太阳照得村庄明亮清朗。荷塘中央闷热起来,回转河边水泥乡路上,溪水轻缓的浪尖闪着银亮的光。沿小溪溯流而上,身子挨擦过田田荷叶,一朵接一朵,绿叶间闪亮的花儿,点燃心中激情。瞧,一朵红莲,侧身倚于肥硕绿叶下,满身通红,那可遮挡一个人的绿伞,都被她映红;十二瓣花儿簇拥着金黄花蕊,香腮绯红,腻云低亸,多嫌着茎叶挤了她娇柔身子。这近旁一枝红莲,花瓣儿比大圆田中央那枝白莲短,瓣尖儿钝圆,花心金黄,比白莲深许,一枝金芙蓉,隐隐透出高贵、庄严相;更浓烈的花香,一阵接一阵打过来,香得鼻子酸酸的,真有点难受,可恋着她的香,来来回回地,不忍离去,渐渐适应了她的浓烈。
“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此言非虚。水中暗红的嫩叶钻出,茎根还带着一点淤泥,叶儿光洁如洗,纤毫未染,一枝一枝出水的红莲,洁净芬芳,荷叶凝结露水,滴滴洒落花儿身上,也未曾染著,干净得很,何须拂拭?她心口燃起的火,艳艳的红,身后,是一百朵,一千朵,无数朵红莲,“一灯燃百千灯”,明明无尽,直抵天际碧霄;她的光和热,是否来自亿万年前钻木取火时,借得远古天神一星火种,深埋心底,在这近午炽热的阳光里,千万缕金丝银线将她点着,生发?十几丘四五亩宽的大田,成百上千枝红莲散落绿叶间,盛开着,十一点的白热太阳光照射下,恰似一盏盏点着的灯焰。
一湾碧绿荷塘燃烧着。
二
田坎边沿,一枝花苞高挺,粉色的,心脏形,结实苞子独立群芳。她朱唇微启,一点朱砂红,尖俏,连着茎干的花萼青绿,花苞中部膨起,丝带状粉红脉络,水纹一样撒开,一张欲说还羞的脸,美得叫人心慌。身旁几张荷叶,大得像蒲扇,为她遮阳,挡雨。拨开两枝高过头顶的荷叶,靠近她身旁,手握带刺青茎,将她微启的秀口拢向鼻端,一股香,清甜古雅,缓缓流溢浸蚀,入心田,沁肺腑,有点晕。这是妙龄玉女情窦初开的体香啊,怎可久消受,怎敢将她揽入胸怀?两枝绿叶俨然护花使者,阻挡我更放肆的亲昵。
这一枝粉莲花苞,半开未开,生在路旁田坎下,乍看并无多少风致,远不如一朵朵盛开的红莲白莲,百媚千娇招人疼;可她微微张开的小嘴儿,吐气如兰的娇模样,将我秒杀。伸手扯她过来的当儿,仍怀疑她的心香,还紧紧包裹在心底,才闻过艳溢香浓,只道这半开的一枝,楚楚可怜,不承想,却给我从未有过的惊喜。
她初发的香,浓烈、沉郁、绵长,仿佛埋藏地底的女儿红,沉睡了十八年,灼热阳光下一朝释放,毫无保留,只待有缘的你,靠近,低头,俯身,用心来嗅,方明白她的深意。任她慢慢开放吧,她轻抿的尖俏小嘴儿,可别掰开,怕她倾吐香的烈焰,将我燃烧,无烟无尘,化作一抹灰烬。
往上走一长段,田坎边青草丛中,一枝小花苞刚探出头来,青绿中带点深红,青衣包裹着,尖嘴儿抿得够紧的,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高傲得不得了,——一个还未长开的青涩女孩。指尖触一下,她微微鼓起的小脸儿,嫩滑、清爽,尖嘴儿紫红,裂开一丝细缝,花萼带着荷茎清香,但闻一闻,总无妨;小花苞尖缝儿对准鼻孔,吸一口,呀呀呀,差点没把我呛死:一股浓烈的香,带苦,猛地冲进喉咙,灌进内腑,毫无防备地冲撞着,头脑一片空白。接连打了几个喷嚏,倒退几步,半蹲下身子,甩头,手掌捂紧口鼻。
这是豆蔻年华青涩少女的香,浓烈、甜美、迷醉。一枝青涩莲苞儿,她浓烈的香,青涩的苦,惊扰了我,我的狎昵,可曾把她吓着?风中,她悠悠颤着身子,我远远地看着,怪她香得过了分,刺得鼻头痒,难受,想再打几个响亮喷嚔,又堵在鼻咽里,憋得辛苦。她冲我摇头晃脑,似乎确是恼了。嘿,谁叫你招我惹我来着?你走你的道儿,我吹我的风,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大家都舒服。我自尊受损,挺直身子,庄严迈步,从今往后,决心痛改前非,对此类半大小子敬而远之,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嘛!
荷塘中央,空中一条观景木栈道,穿过花海,搭上村中心一个浑圆小山包。水泥路右侧,跨上几级木台阶,脚尖沾染一滴露水,好凉,低头一瞧,哈,一朵红莲,从荷田底下伸出来,硕大花冠斜倚栏边,无力低垂,真真一个醉眼迷离,娇艳无比的美人。她体态丰腴,躺卧灼热阳光里,懒洋洋地,整个儿一介情思睡昏昏,娇软模样儿,教我停下脚步,蹲下,右手轻托她绵软身子,细看她绯红香腮,鹅黄心蕊。她是喝醉了酒的,通体血管艳红,嗞嗞响着,浑身着了火,花瓣微卷,倦意沉沉的媚眼,一枝娇憨香浓的睡美人。
我想将她送回荷叶深处,让她清凉入梦,不扰这醉酒贵妃一晌安眠。可她实在太丰满,她的身子挤不出栅栏,她得留在这儿,艳惊一个个探花人的眼眸,香染一双双行走的足尖。当日,离了荷田,好奇地钻进栅栏时,她还是一枚少女,清瘦,如今她已成为浓装艳抹的倦慵少妇,再回不去当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那么美。我伸手折来一枝荷叶,给她挡挡灼烫的阳光。
正午,太阳垂悬头顶,身上热汗淌流。不知不觉,已在花海徜徉两个时辰。正要举步登上栈道尽头的小山包,一片李子树底下,圆石墩子上坐坐。十二点的骄阳照在脸上,火辣辣地疼。忽然,脚底传来“嘎!嘎嘎!”几声,吓我一跳,栅栏侧边,窜出来一只青头鸭子,头顶一片荷叶,一身羽毛麻灰,梗起脖子看我,青绿的扁嘴巴,衔一颗田螺,抖落遮挡另一只眼的荷叶,又定定地看我,一脸好奇。我冲它做个鬼脸,“嘎!嘎!你住在凉棚里,荷叶搭的窝,舒服啊!嘎,嘎。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幸福啊。”
越过荷田中央的圆形小山包,往东北群山望,广阔田塅中,一层层阶梯逐级而上,莲叶铺展,缠绕山脚下一排楼房前,红、白、粉的莲,半开的、怒放的;转过身,折返右侧花海,走向一条长长的田埂,拨开密密匝匝的荷叶,踩着毛茸茸的杂草,底下蒸腾起一股潮热水汽。暑溽曛人,时时要钻出来透气,趔趄前行,又有条小沟渠,右边傍着更窄的一条水泥路。
小路边,水柳覆盖着小沟渠。顺着小沟渠哗哗的水流,沿着小路,朝进村的岔道口方向走着。宁静的正午,没有一丝风。右边平整整的荷塘,全是盛开的白莲,伫立荷叶间,一动不动。清亮水面,荷叶投下重重暗影,一个挨一个,水里的圆,不偏不倚,以茎梗为圆心,画映泥田,光与影,明与暗,奇妙的黑白世界,凝然不動。此刻,花与叶,都已入定。边看,边走,刚抵达时,斜照半个村子的桔红色太阳,已高悬天心,万道光束,白炽如芒,照彻群山拥簇中的青青荷塘。
跨过当中一道田埂,蹲坐荷叶底,抬头,仰视。一枝红莲,高高立于荷田上空,她的身姿,映在澄净无染的蓝天。微风起,茎梗处四个瓣儿飘洒、起落,花瓣摇曳,裙裾飞扬;向上托举的八个重瓣合成花冠,阳光照得雪亮,瓣儿粉中透白的脉管,吸饮清泉,条纹分明,丝丝缕缕,清晰可鉴。凝神,仿佛听到汁液在流淌,嗞嗞地响,玉体澄明。有光,在金色花蕊间回旋,营造辉煌梦幻,许是大日佛从天而降,在她心里点起一盏灯。一刹那光明,我见。
三
展眼望去,远处荷田中四朵白莲,如亲昵的四姐妹,高低站成一排,次第开放。最高最大的一朵,花瓣儿舒展,搭在几枝绿叶上,风来,十二个瓣儿起起落落,冰雪洁白的瓣尖儿,边缘一抹胭红,如此惨淡,几近于无。“玉颜不及寒鸦色”,说的便是她,青春已逝,恩宠尽失,只剩一点清高,只欠一次风吹雨打,她便要去了。无力的媚眼,带一点幽怨:你呀,你来得太晚了,我都熟得快要掉了,再迟来一刻,怕是看不到我了……恰有一股长风,自西南边狭长深谷猛扫过来,她一身白裙瓣,忽啦啦掉落一半,她急忙扯起另一半儿。风,掉转头,又横扫过来,她的白裙子全褪下了,露出腰间一圈儿黄丝带。
吹走的花瓣,一片片粉色尖头小船儿,悠悠荡荡,飘落飞散,打几个旋,几瓣浮在轻薄水面,光的斑驳碎影下,衬得明艳动人;几瓣在田沟游走,跌入小沟渠,水草牵绊住了,捡一瓣,闻闻,还是清甜,还是香啊,玉一样的颜色,在掌心里透明,鲜润,净爽,连渠沟中一滴水也未染着,何况污泥?还有几瓣,落在更远处,躺卧玉盘似的荷叶上,像调皮的娃娃,坐着摇椅,风来,悠悠地转。
第二朵全开的,花冠水粉红中漾出雪白,向天空轻举,双手温暖合掌,恭敬地掬起一捧光明。正午阳光点燃了她,粉白四壁透出清辉,是元宵月夜哪一个天真少女手提的莲灯,一朝遗落花田?还是上元节放河灯时,漂流水中渐行渐远,消失的那一盏,托生转世,出落成一枝出水的红莲?花无语,她只顾盛开着,灼热阳光里,清香漫溢,纵情挥洒,紧紧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她独有的,骄傲的青春。
老三儿又矮一截,朱红色小嘴儿半开,向晴空倾吐花香。青萼边,四个瓣儿还带点青绿纹理,错落低垂,微风中袅娜生姿,似观音菩萨纤纤玉手,温暖,馨香。最小的一枝青荷,踮起脚尖,往姐姐们看齐,一身紧裹的青衣,恨不得快快褪下。眼瞅着三个姐姐美得招摇,她还不能穿起蓬蓬裙,加入盛大舞会,还得安静地等待,等待阳光的手,将她抚弄,伴她长养,成熟,开花,结果。她要和所有开过的花儿一样,释放她的青春和美。
更远的碧叶花海间,一枝枝莲蓬,嫩黄的,花瓣儿刚被风吹落,花叶碎阳下,闪着明黄的光,照人眼花,花萼高举处,一溜儿触须,风中轻拂,仿佛一群芭蕾少女轻盈起舞,娇美,高贵,优雅。阳光扎眼,穿行于一条条蜿蜒田埂,无穷无尽张开的碧玉巨伞下,隐身,静坐,乘凉。满川荷花,在艳阳蓝天下静立,阴凉中暗香浮动,风暖,花明,一阵一阵清风摇动绿叶,全身热汗渐渐干爽。
透过重重碧叶间隙,仰望千万朵莲花,七彩阳光将花心点亮,一盏接一盏,眼前的光亮,一朵一朵,汇集成一片光明的海洋。今日午间,大日佛——这太阳之子,无限慈悲,乘着万道金光降临下土,照拂着花的海,香的国。“一灯能灭千年暗,一智能破万年愚”,这无数闪闪发光的韾香灯盏,被头上万古常新的太阳摸顶,吸取山间林泉精气,污泥浊水中涌身而出。她脚下的泥,她喝过的水,都变得干干净净;她绽放生命,展露风华,给天空的飞鸟,水中的游鱼,有缘的行者,以甜美 ,以芬芳,给有灵的万物,以慰藉,以洗礼。
一朵朵半开的,怒放的莲,红的、白的、粉的,纤纤花瓣低处垂落,恰似观音菩萨的莲花妙手。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她有一千只玉手,一千只手掌心里,闪着一千只光明的眼,智慧的眼,怜悯的眼。她听得人间疾苦呼喊,循声而来,随处现身,搭救受苦受难的灵魂出离生死海,抵达自由解脱彼岸。她是佛的化身,她将佛的智慧、悲悯与光明,以慈母般的胸怀度化、护佑悲喜人间。
观世音菩萨,是中国民间普遍信仰、供奉的神,她端坐佛堂正殿,现身山野小庙。她的慈谒容颜,如春风拂面,天真的孩子也愿匍匐足下,拜上几拜,抬眼看她的善美笑容,孩子也跟着笑了。观音娘娘,中国人再造的神,她看起来太像慈爱的母亲,绝不使人生畏;她的一千只莲花妙手,玉臂舒展,交错打开,手指微翘,多像眼前满池鲜艳的莲瓣伸张,热情、沉静、美好,让你放心,将重重心事与难言悲苦交出来,交给她,她将给你抚慰。她的手指,带着温暖的光,染着莲花的香;她若轻启朱唇,开口说话,必是口吐莲花,妙法随花香流溢,滋养你焦躁心田。
她的宝座,底缘盘刻着莲瓣,层叠缠绕,似一只只微笑的眼,一片片扬起的帆,一朵朵盛放的心香——传说观世音菩萨从海上来,她乘坐一朵莲花来,不远万里,不辞辛劳;她的莲花宝座,怕是古老佛国、佛寺内院池塘中常见的王莲所化?王莲的叶子边缘竖起,微卷,巨大如盆,浮在水面,坚硬、沉稳,叶面光洁,可安坐一人。
佛的王国,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左胁侍,西方三圣之一。她度众生,觉有情,她莲步轻盈点过水面,她是莲的化身。她是从幽深海底涌现的仙子,犹如一朵出水的莲,从污泥深处挺身而起,不染纤尘,开启光明、智慧、善美的眼;在普度苍生,救苦救难中,不折不从,不蔓不枝,手持金莲,欢喜前行,花开花落中,清凉观自在,功德自圆满。
此刻,一粒凡尘,藏身光明世界海,于千万朵莲的簇拥中,内外明彻,花香迷醉,叶底清圆,她的身,她的心,注满光明,充满福乐,化作荷田下一只青头鸭,无忧无烦;化作游弋泥田中一尾红鲤鱼,不惊不扰;与这神赐的福田,永不分离。周遭,千万朵莲的风姿,是佛的千百亿化身,护佑此方世界,洒下清凉甘露,令一切忧苦焦灼灵魂,重获安宁。一花,一叶,小风,清泉,当下便是福田,净地为我所有。
四
走出荷塘,回返阳光灼射的水泥路上,眩目的白,热气熏得脸发烫,胸口窒息,眼睛酸涩。小水沟边,柳树卷起修长叶子,粘在枝头的蝉儿,知啊知啊,喧嚷,烦躁,单调的回声满村子激荡,随风送远。
绕回进村道路岔口,紧跟溪流往山坡上走,洄水弯曲处一座单拱石桥,穹窿两侧爬满木莲老藤,藤蔓挂着一串串凉粉籽,青绿,小铃铛似的。
站在桥上,北岸一棵古樟伸出一枝粗臂盖过桥面。倚身横躺的树干,吹够了从身后赶来的山风。过了桥,山径阴凉,一片香樟林遮挡了太阳光。没上最后十几级陡立台阶,脚酸了。山腰横路上停下,双肩背包当枕头,仰面躺下,眯起眼睛。山风穿过林子,穿过平躺地上的人;树叶窸窸窣窣,相互拍打着,溪水哗啦啦轻响。寂静山村,吹奏出一支催眠天籁,舒缓,轻盈。睡神,扑扇着翅膀,拂扫全身,轻轻柔柔。一会儿,疲累一扫而光,沉沉入梦。午后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光影在身上、脸上飘移,酣睡的人,并不知晓。
午梦清甜,醒来,耳朵也变得灵光。坐起身,揉揉眼,一时发痴,变傻:我这是在哪?是早晨,还是傍晚?看看头顶,光线变暗,云影阴沉,似乎只闭了闭眼,看钟点,已是下午三点。睡前的一切,全忘了。
上坡,青青竹林下,一栋雪白小屋,大门紧闭,没上锁。绕过屋场边小路,下坡,深入小村东北山脚下。一步一步,走下层叠田埂,跻身荷塘深处。天上乌云不断聚集,堆积,瞬间遮蔽了长椭圆形村子上方的天穹。午后四点,大风来了。打东北山顶呼啸着,俯冲下来,扫过脚下梯级缓坡,碧叶繁花,掀起层层浪涛,涨潮般的,一波一波翻卷,直翻卷至西边山坳尽头,送到村岔路口小河边。一溪清流喧闹起来,呼啦啦,呼啦啦,和着浪海中花叶的唆唆声,急急地,忽起忽落,回荡远山深谷间。身后传来农妇呼儿唤女的声音,伢儿!归家嘞!下雨来!河水轰响着,依稀有孩子应答着。
也许没有,只是风。
风,一阵紧似一阵,一片一片肥硕高挺的绿叶,被千万只无形的手打翻,齐刷刷地,忽地掀起,忽地放下,节奏明快,绿浪一波一波推展,一会儿向北翻滚,千万枝叶掀起浅绿背面,盖在花儿头上。红的、白的、粉的莲,绿浪中起伏扑腾,忽隐忽现,风卷过来,打个旋,又向南翻滚,仿佛聽着号令,应着鼓点,一齐跳起摇摆舞。一朵朵散落青圆荷叶中的花,风中狂舞,成熟的花瓣儿一片一片飞起来,撒落碧玉盘中,滴溜溜飞旋,和站立水中的千万风荷,同频律动,跳起空中芭蕾。
狂风呼呼地响,横扫过几阵,大雨点洒落下来,打在荷叶上,噼噼啪啪乱响,奏起一支宏大交响乐。雨点砸向花儿,叶儿,散开,飞珠溅玉,弹跳着落入荷田,水中激起无数个泡泡儿,滴滴嗒嗒,花叶下,水泡儿跳跃,奔跑,你追 我赶。
荷田升起白濛濛的水雾。雨荷,娇美。一朵朵沾染水珠,玉露莹莹,花蕊含羞,鲜润欲滴。荷叶张开巨大手掌,托举水珠儿,硕大,透明,水银似的,风抛起叶儿,忽右忽左,摇啊摇,躺叶面上的水珠儿,滚来滚去,不分散,一不留神,一半儿滑出,一半儿残留叶片掌心,任风儿戏弄,抛撒,荡秋千似的。伸手,摘一片肥美碧叶,戴在头上,挡住整个身子,惟觉清气满怀,凉爽。绿叶,不染著一丝水汽,仿佛一粒水分子不曾耗损,任它滑落泥田,回归来处。
风,舞动荷田,雨,洒落荷田。
五
风停,雨歇。太阳已偏西,稀疏云缝里金光散射,阴沉沉的天,忽又明亮起来,荷塘一片澄明清晖。转身,沿近处几道田埂走出荷田,拐上林木葱茏的圆形小山包,又回到了木栈道上,脚下躺着一枝红莲——这“醉酒的贵妃”,她含珠吐玉,香腮带雨,无限风情,真是爱煞人。我亲手为她折的那枝荷叶,已被大风吹落荷塘。
正午阳光下,通体透明的一盏盏红莲,阵雨过后,变得幽清,娇美,收敛几许香,少了几分霸道,风中,只是清甜,只是芬芳。放眼望,曾在风中舞蹈的千万朵荷花,重归沉静,一支支青茎伫立;她,原本就这么挺直于虚空,风雨过,无摧,无折,不动,不摇。
高贵,从骨头里生长出来的。
白鹭,从荷叶深处振趐飞起,绕荷塘一圈,飞越南山脚下,回转,又绕飞一圈,滑翔,俯身,羽翼低垂,轻触水面,仿佛在巡视它的美丽王国。又一只,从同一个地方飞出,紧随其后,身姿轻盈,双翼点染荷香,沾濡清气,徐徐掠过一朵朵雨荷,空中抛下它的轻吻,一触,旋又分离;良顷,一只隐入荷塘,另一只跟进,散入花海,都不见。水中,有它们的爱巢。茎荷,筑在水中的小屋,多想有一间这样的小屋,月光下,嗅着花香,团团荷叶送清凉,水中撒落满天星子,让荷风,摇摆着身子入梦——我愿如夏荷,心底干净,足下清凉,风中舞蹈。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我想,苏子笔下的花蕊夫人,定是荷花仙子转世。不曾和玉洁冰清的人相交,又怎能发觉一身粗鄙、浊气?惟愿在诗书礼乐浸润中,在月光流水打磨下,我这个乡下野丫头,也会“粗鲁得更好一点儿”,渐渐抵达一个文化人应有的斯文境地,不枉日日浸染花田叶下,濯洗心尘。
身在深山荷田。山村里暗下来。夕阳酡红色的圆脸擦着西边山崖沉下去,余晖染红清溪水,返照荷塘。一半绯红,一半暗影。
山村的夜晚来得很快,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围青山的暗影挤向荷田。恋着这花香之地,我留下来。静待月亮从东山顶上升起。
夜归的母亲,抬手拧亮屋檐下的灯,灯光昏黄,照出河边蓬松树影。女人高喊河里贪玩的孩子,招呼树下的鸡鸭进笼。
山村里的人语声,鸡鸭进笼的聒噪声,狗昂昂的吠叫声,都停歇了。
东山顶上的月亮露出半张脸,清冷如玉。山雾从西北田垄间升起,飘向乡道、田塅中央,漫过荷塘,调和着渐渐明亮起来的月光。一片绿海罩上白纱,轻盈,透明,飘飘漾漾,摇荡着一川荷田。一叶一花,浸染月光、水雾,撒开的花瓣儿沾染细密水珠,映衬雪白月光,一粒粒,碎钻般的,莹莹生辉。一枝枝半开的花儿,收拢了花苞,颔首低眉,香气内敛,夜风里一点一点弥漫开来,若有似无,仿佛睡前深甜呼吸,意味 深长。
来来去去,在日间已走过几回的乡路上,我徘徊复流连。
夜露打湿头发,鼻孔吸吮花香,眸子映现山间的月光,水底的星光。全身浸润夜风清凉,千万个毛孔都舒张开来。走着走着,不知不觉,重又钻入密密荷叶间,惊起一对鹭鸟,从沉静花田扑棱棱起飞,雪白身姿闪过夜空。
荷叶间,传来更大的声响,心里暗暗一惊;月光下,花海中,一只尖顶竹笠,慢慢向我移过来。近了,眼前,一张汗湿的脸,采莲的女人冲我笑了。
你在找什么?
她摘下竹笠,手拢额头乱发。背篓里躺着新挖的藕,还有几枝青绿莲蓬。她抬手递给我一枝嫩莲蓬。
一整天,在花前,在叶下,田垄间,乡路上,小河边,老樟树下,她都看见了吧?我冲她一笑。她朝河岸边的屋子走去,身后跟着一只青头鸭;还有一只麻灰的,身子微胖,腹部很肥。它们是一对儿,结伴归家了。
坐回田埂上,透过重重荷叶,看无染无著的深邃蓝天,明净天宇闪着蓝幽幽的光,像一块擦洗过的蓝宝石。心底一切烦闷倾倒去了,眉间,心上,是花的影,花的香。捧一把花田的水,冰凉,浑身一颤。“抬脚踏翻香水海”,是的,这倾泻着月光的流水,染着花香,一刹那,我心已在福田落了根。
夜已深。山村四边散落的屋子。灯,一盏接一盏熄灭了,昏黄灯光照出来蓬蓬树影,一片一片融入墨一样的黑暗中,月光下浮现朦胧的不规则轮廓,渐渐消失。
人睡了,狗睡了,鸡鸭睡了,花睡了。花香更清和,月光雪白,照彻群山,照拂花海。我也打瞌睡了。仰身,双手枕脑后,身子放倒田埂上,伸长两条腿,想筑一间荷屋,就在这水边安眠,与花儿一同睡去,太阳醒来,我也 醒来。
我不过是肉身凡胎,我的尘缘还在。我,并非了无牵挂。
早闻着村子里家家飘出的夜饭香,肚子已不听话地咕咕叫唤,我想,随便走进哪一栋灯光温暖的小屋,屋里的主妇都会热心招待我(难免会露出惊讶、好奇神色:看起来,我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可我不忍心叨扰。她们劳累一天的身子,早早睡下了。
起身,坐直,仰头,从花叶间向东北山脚望。桥头,一栋小屋漂浮荷塘,天青色的外墙,借来荷叶的清爽,门楣、窗框描一道深红,与花海相依相融。月光下,山村静静地沉睡,风摇叶动,小屋仿佛也在花海中摇晃着。
屋里浓睡的人,梦里也飘着荷香。
编辑导语:这篇散文以优美的文笔,对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进行了虔诚的颂赞,风中、雨中,丽日下、月光里,其形、其姿、其香、其韵,莫不生动鲜活而又意蕴无穷,作者对莲花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形神兼备,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唐咏梅,出生于70年代,江西遂川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西省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艺术报》《短篇小说(原创版)》《生态文化》等报刊。有作品入选《江西新世纪女作家作品选》《红豆》等文学杂志年度选本,偶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