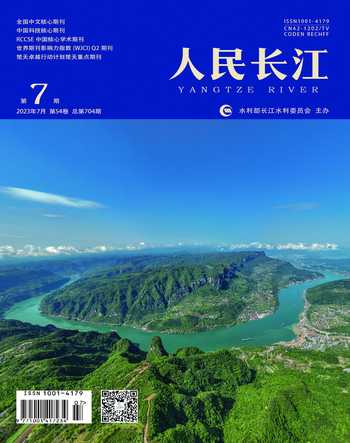跨界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协同治理策略研究
2023-08-08王俊杰何寿奎梁功雯
王俊杰 何寿奎 梁功雯



摘要:
针对跨界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的横向治理评估体系不完善、治理主体主动施策意愿低的问题,从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改善、生态价值实现角度探索治理主体协同决策的动力机制。分别构建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以及协同合作博弈模型,分析流域上下游政府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策略,并建立基于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发现:在非协同合作下,上下游政府努力程度不足;协同合作在经济层面上比非协同合作更加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上下游政府自发达成协同合作比较困难,通过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能够有效促进上下游达成合作并能提高跨界流域生态环境合作治理效益。研究成果可为跨界流域府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及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跨界流域; 生态环境脆弱性; 横向生态补偿; 协同治理; 决策行为博弈
中图法分类号: F062.2;X32
文献标志码: A
DOI:10.16232/j.cnki.1001-4179.2023.07.004
0 引 言
近年来,国内在流域水环境治理方面投入巨大,2016~2020年,全国财政用于推动开展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资金达1 298亿元,同时,中央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包括《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财资环〔2021〕25号等政策文件。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支持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在整体上取得了不错成效。然而,当前流域生态环境依然脆弱,地方层面流域监管及治理力度不足问题形势严峻。全国七大水系中辽河与海河受到严重污染,淮河水资源匮乏,黄河形势不容乐观,松花江流域自然灾害频发。跨界河流协同与监测监管能力薄弱,长江上游生态环境联保共治有待加强。如四川省南充市在嘉陵江流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违规采砂、侵占岸线、废旧船舶滩涂拆解等问题长期存在,使嘉陵江南充段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造成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整体受损。在当前跨界流域地方政府治理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下,研究如何提高政府对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动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可持续角度来看,中国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动力仍有待提升。一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关流域治理的政策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政策制定时没有考虑到上下游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造成部分政策落地时“水土不服”[1-2],并且国内流域涉及行政区划众多,流域待治理面广,导致看似充足的专项资金下发到各个行政区后便显得“捉襟见肘”。目前,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仍存在协调机制不健全,决策动力不充分等问题,流域治理仍处在“指标不治本”状态。另一方面,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不断深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内涵逐渐由单目标环境治理向多目标生态价值实现转化,由条块化、分割式治理向多主体、跨区域协同治理转化[3-5]。多维度治理需求与当前分权式环境管理制度和条块化分割的行政体系间产生了矛盾,造成各方利益协调困难,无法为地区流域治理提供长效动力,流域治理仍处在“治理不经济”状态。如上所述,尽管国内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面对治理边际成本不断增加的现实桎梏,仍存在地方政府主动施策意愿低、中央财政负担大等困境,如何利用生态治理效益和横向补偿实现由被动的纵向央-地链式治理向可持续的横向地-地协同治理飞跃,提升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策略与机制方面。刘亦文等[6]、马军旗等[7]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别定量分析了湘江流域“河长制”的生态环境治理效应、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均得出当前政策能促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结论;从整体上看,我国流域生态环境在相关政策支撑下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经历以较差环境基础获得短期治理的显著边际效应阶段,而随着环境治理进入深水区,当前政策体制机制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贾先文[8]认为河长制在流域治理中作用突出,但其本质仍是传统官僚管控体制以强权威推动的“自上而下”治理制度,仍存在公众和基层组织参与路径缺失,跨省流域生态环境碎片化治理等问题;李灵芝等[9]通过国控监测点水质数据和河长制演进数据分析了河长制在跨界污染问题中存在的“搭便车”问题,并给出了优化当前河长制的政策建议;杨志云[10]提出当前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受到“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制约,中央政府在推动流域水环境治理体系整合改革中不仅要做到职能整合,还应做到水生态和水环境的职责整合。
关于跨界流域的协同治理机制。徐松鹤和韩传峰[11]通过微分博弈模型发现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能够有效提高流域整体收益,促进上下游地区政府合作治理。例如,浙皖两省创新推出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通过环境绩效考核将上下级补偿与上下游补偿相结合,在上级政府生态补偿基础上,上下游政府联合考核下游水质。水质达标的,下游政府即向上游政府支付补贴,水质不达标上游政府即向下游政府支付罚金,实现了新安江流域的协同治理。而在“新安江”模式的成功经验下,部分省市开始主动探索跨界流域的府际协同治理实践。如2018年,川渝两省市河长制办公室签署《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合作协议》,提出重点流域共治、河流信息共享等协定。四川省财政厅、重庆市财政局又于2020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财政协作推进机制第二次会议上签订了《长江流域川渝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两省市每年共同出资设立川渝流域保护治理资金,专项用于相关流域的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环保能力建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新安江”模式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需要探索一种长效化机制来实现生态补偿制度的可持续发展[12-13]。部分学者[14-15]认为流域协同治理不仅需要府际间协同,还要激发公众个人、社会组织及市场主体活力,以顶层制度为支撑,以利益驱动为抓手,以路径引领为保障,促进流域生态环境多主体协同治理。跨界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应注重流域生态环境整体性,而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程度能够体现流域生态环境整体质量水平,因此,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应以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为目标。
总体来看,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围绕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展开了广泛而有成效的研究,但目前多数研究仍突出分析中央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较少从博弈角度定量分析上下游地区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策略选择的内在逻辑,以及缺少生态环境脆弱性对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影响的系统分析,同时具有针对性的府际协同利益协调机制研究也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基于生态环境脆弱性,构建流域上、下游地区政府的博弈理论模型,分析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决策问题,对比分析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和协同合作博弈3种情形,并建立基于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横向生态补偿“怎么补、补多少”的补偿机制构建问题,为跨界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1 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内涵及特点
生态脆弱性理论最早由Clement于20世纪初提出的生态过渡带理论演变而来[16],经过不断的深化与发展,生态脆弱性逐渐与气候[17]、城市[18]、经济等要素联系起来,并延伸到人文地理学、人类生态学等领域。Adger[19]认为脆弱性是系统对扰动或外部压力的敏感性以及适应能力,或系统承受环境与社会政治压力的程度。因此,生态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在遭受外部干扰时缺乏适应能力而变得容易受到损害的一种状态[19]。从生态脆弱性定义上看,不同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水平会随外扰度和自适性变化呈现出时空异质性。但流域生态脆弱性表现又有所不同。首先,从流域自适性来说,流域是个完整的生态系统[20],其内部要素会自发产生交换和流动,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其次,将分布在流域周围的人类聚居地视作流域水系網络节点,流域作为具有自运动属性的网络,其所受外部扰动具有传递性,即在流域某节点生态环境受到外部扰动时,由扰动带来的破坏会从局部传导到整个系统,并随着传导范围迁移而逐渐达到一个稳定状态,流域上下游生态环境变化过程与热传递原理类似。因此,宜将流域上下游生态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考虑其脆弱性,并按照上下游协同治理的思想来治理流域生态环境。
2 跨界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政府行为及生态脆弱性基本假设
考虑流域横跨两个行政区域,以上游地区政府(U)、下游地区政府(D)作为流域治理主体。当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侵袭或人类活动扰动等生态安全事故时,由流域连接的上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均会遭受到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并给地区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而地区遭受损害程度与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密切相关,因此,需要通过生态环境治理优化人地关系、提高生态系统抗灾能力以降低生态环境脆弱性,从而加快实现“绿水青山”隐性价值向“金山银山”显性价值转化。
假设1:上、下游地区政府治理流域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为h(h>0),代表政府为治理流域生态环境在人力、资金、时间等要素上的付出程度。
假设2:政府治理流域生态环境的努力程度是决定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量的关键因素,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量K代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则满足关系式:K=αUhU+αDhD,αU和αD分别表示上、下游地区政府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努力程度对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量的影响系数。
假设3:政府治理生态环境成本C与其努力程度h呈正相关关系,则满足C′(h)>0,故可知:C(h)=βh,β为努力成本系数。
假设4:优质的生态环境能够产生一定的生态价值,为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这些效益统称为社会福利效应。假设社会福利效应:Q=μUhU+μDhD+τK,其中μ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努力程度对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系数,τ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量对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系数。令社会福利效应收益系数为λ(λ>0)。则总收益为R=λQ,设上、下游政府生态产品收益分配比例为ω、1-ω。
5 基于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上下游政府治理决策数值分析
由于在3种不同情形下,上下游政府最优努力程度、最优收益以及横向生态补偿值均受到模型中多个参数影响,各个参数的量化与评估过程相对繁琐,且在现实情况中,将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作为连续变量收集数据较为困难。因此,为了研究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对上下游政府治理投入决策的影响,本文将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来探究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与上下游政府最优努力程度、最优收益以及横向生态补偿间关系,从而刻画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对跨界流域中上下游政府治理投入决策所产生影响。假设基准参数为:αU=2,αD=0.02,βU=18,βD=44,μU=3,μD=1,τ=4.1,λ=2,ω=0.5,δU=0.065,δD=0.087,LU=1000,LD=1500,φ=0.4。
5.1 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对最优努力程度影响
图1(a)、(b)分别刻画了不同水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对上、下游政府最优治理努力程度的影响。从图1(a)中可以看出,在Nash非合作博弈情境下,上游政府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随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降低;在Stackelberg博弈情境下,当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q≤0.157时,上游政府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最小,最小值为零,当q>0.157时,上游政府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随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逐渐增加;在协同合作博弈下,上游政府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随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增加。
在图1(b)中,下游政府在Nash非合作博弈情境下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随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逐渐降低;在Stackelberg博弈情境下,当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q<0.085时,下游政府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随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逐渐增加,当q>0.085时,下游政府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随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降低,当q=0.085时,下游政府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最大;下游政府在协同合作博弈情境下达到收益最大化状态所需付出的治理努力程度随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增加。
结合图1(a)、(b)可以看出,协同合作情境下,下游政府对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的敏感程度比上游政府更强,但上游政府治理努力程度高于下游政府治理努力程度。在Stackelberg博弈情境下,上游政府和下游政府均存在一定程度“搭便车”现象,具体表现为上游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较低时不付出努力,以及下游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较高时降低努力程度。在Nash非合作博弈情境下,上、下游政府面对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态度是消极的,因为降低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所需边际努力投入是呈递增趋势的,从而导致双方都不愿意增加自身努力程度,最终造成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不足。
5.2 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对最优治理收益及政府决策的影响
从图2(a)可以看出,上游政府在3种情境下的治理收益均随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降低而增加,这说明改善生态环境脆弱性能够使生态效益得到提升。上游政府选择协同合作博弈收益与选择Nash非合作博弈收益均小于选择Stackelberg博弈收益,这说明在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下,上游政府会倾向于占据在流域治理中的主导权。当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q<0.942时,上游政府选择协同合作收益小于选择Nash非合作收益;当q>0.942时,上游政府选择协同合作收益大于选择Nash非合作收益;当q=0.942时,上游政府选择协同合作收益与选择Nash非合作收益相等,这说明上游政府在无法占据流域治理主导权的情况下,会更加倾向于在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较高时选择协同合作。
从图2(b)可以看出,下游政府选择协同合作收益对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敏感程度较低,基本不隨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而改变;下游政府选择Stackelberg博弈收益随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呈先减少后增加趋势,且在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q=0.027时,收益最小;下游政府选择Nash非合作收益随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逐渐减少。从整体上看,协同合作收益高于Nash非合作收益与Stackelberg博弈收益,同时,随着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协同合作收益与Nash非合作收益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与Stackelberg博弈收益之间差距先增加后减少,在q=0.027时,差距达到最大,这说明在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下,下游政府更加倾向于与上游政府协同合作治理流域生态环境。在非协同合作两种情景中,当q=0.955时,下游政府选择Nash非合作收益等于Stackelberg博弈收益,当q<0.955时,下游政府选择Nash非合作收益大于Stackelberg博弈收益,反之小于Stackelberg博弈收益,这说明只有在生态环境脆弱性比较高的情况下,下游政府才会选择以从属地位参与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从图3可以看出,上下游政府协同合作总收益要优于其他两种情形下总收益,这说明协同合作决策在整体上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相比其他两种情景更加有利。但对比图2可知,在没有附加条件加入的情况下,上、下游政府想要自发达成协同合作状态比较困难。究其原因,上游政府在地理位置上较下游地区更具有高程优势,并且在我国上游地区经济落后于下游地区经济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无论是从污染物流动规律还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上游地区政府更加有动机选择不合作,同时希望通过“地理强势区位”或“经济弱势地位”获得流域治理中的主导权;同时,下游政府既有合作动力又不希望被上游政府“牵着鼻子走”,因此在不能与上游政府达成协调合作的情况下,下游政府会更加倾向于选择Nash非合作决策。鉴于此,要想促成上下游两地协同合作,需要引入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及中央政府通过环境保护奖励政策(如财建〔2018〕6号文)来协调两地利益。
5.3 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对横向补偿的影响
图4展示了在不同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下,上下游政府横向生态补偿支付额变化规律。从图中可以看出,横向生态补偿支付额随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增加而增加。当q>0.413时,横向生态补偿额为正值,说明此时下游政府向上游政府支付补贴以激励上游政府协同合作;当q<0.413时,横向生态补偿额为负值,说明此时下游政府向上游政府收取罚金以调控上游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当q=0.413时,横向生态补偿额为零,在当前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下,上下游政府协同治理效率达到最佳,上下游政府可自发形成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格局。
当q<0.067时,Nash非合作收益大于Stackelberg博弈收益,此时补贴额为ΠNU(hNU,hCD)-ΠNU(hCU,hCD);当q≥0.067时,Nash非合作收益小于Stackelberg博弈收益,此时补贴额为ΠSU(hSU,hCD)-ΠNU(hCU,hCD)。
6 结论与建议
跨界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上下游协同合作治理流域生态环境将缓和治理主体间责任冲突,减少因“口水战”带来的资源浪费等负面影响。本文基于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上下游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过程,分析比较了上下游政府在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协同合作博弈3种情境下的均衡结果以及决策者最优努力投入,并建立了促进上下游协同合作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Nash非合作决策情景中,上下游政府治理努力程度随着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增加而降低,并且在该情景下存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不足现象;在Stackelberg主从博弈决策情境中,上游政府收益高于纳什非合作决策收益,因此在有成本分担情况下,上游政府愿意承担起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责任,而下游政府在自身遭受损失的概率过高或过低时则会出现“偷懒”行为,说明此时中央政府建立上下环境治理标准有利于促进下游政府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在协同合作决策中,流域治理主体努力程度随生态环境变化方向与相邻治理主体努力程度取值相关,当相邻治理主体努力程度大于某个值时正向变化,小于某个值时负向变化,且协同合作总收益优于其他两种情景下总收益。在协同治理协调机制中,建立根据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的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机制,有利于提高跨界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益。
根据结论提出如下相关建议:中央政府可以综合考虑各省经济状况、治理能力等因素分类施策。对有条件达成上下游协同治理局面的流域段,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将纵向生态补贴转变为协作治理成果奖励并加快完善生态补偿立法,以此实现部分地区纵向生态补贴退坡,并鼓励相关省际政府积极签署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从而倒逼省内市县级政府寻求横向府际合作。同时,可以考虑以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作为横向生态补偿额的支付指标,以此更加全面和长期反映流域治理成效。另一方面,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要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利用市场化手段加快生态价值超前实现,通过共同打造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世界级自然生态及文化旅游长廊构建跨界流域协作的治理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格局,从而提高横向生态补偿“造血”能力。在暂时没有条件达成上下游协同治理局面且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流域段,中央政府可适当倾斜相关财政补贴并建立严格合理的环境治理绩效考核机制,以此激励该流域段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决策行为;或者在上游政府愿意承担起治理责任时,以上游政府掌握治理主导权,下游政府分担上游政府部分治理成本作为横向生态补偿的过渡策略,同时建立上下环境治理标准并严格监管上下游治理责任履约行为。最终时机成熟后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广到全流域施行。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针对跨界流域协同治理合作困境,在考虑生态环境效益的前提下,从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角度量化分析非合作、主从关系、合作三种情境下流域治理主体投入逻辑,建立契合当前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协同治理协调机制,从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角度回答了横向生态补偿“怎么补、补多少”的理论值问题,并适用于上下游边界清晰、治理主体明确的丘陵山区流域,可以为促进跨界流域府际合作,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纵向生态补贴退坡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童坤,孙伟,陈雯.长江经济带水环境保护及治理政策比较研究[J].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3(1):5-16.
[2] 李云生,王浩,王昕竑,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瓶颈及对策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2020,33(5):1262-1267.
[3] 王金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思考[J].环境保护,2020,48(增1):18-21.
[4] 付景保.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多主体协同治理研究[J].灌溉排水学报,2020,39(10):130-137.
[5] 韩建民,牟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以甘肃段为例[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2):112-123.
[6] 刘亦文,吴荆,蔡宏宇.湘江流域“河长制”的生态环境治理效应研究[J].软科学,2022,36(3):75-82.
[7] 马军旗,乐章.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检验[J].资源科学,2021,43(11):2277-2288.
[8] 贾先文.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探索与机制改良:以河长制为例[J].江淮论坛,2021(1):62-67.
[9] 李灵芝,羊洋,周力.河长的边界:对流域污染治理行政力量的反思[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6):147-154.
[10] 杨志云.流域水环境治理体系整合机制创新及其限度:从“碎片化权威”到“整体性治理”[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2):63-72.
[11] 徐松鹤,韩传峰.基于微分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9,27(8):199-207.
[12] 陈方舟,王瑞芳.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长效化研究[J].人民长江,2021,52(2):44-49.
[13] 莊超,陈健.论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法律调控[J].人民长江,2022,53(11):14-19.
[14] 杨志,牛桂敏,郭珉媛.多元环境治理主体的动力机制与互动逻辑研究[J].人民长江,2021,52(7):38-44.
[15] 夏函,彭振阳,刘国强.新时期推动沅江流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若干思考[J].人民长江,2022,53(10):1-7.
[16] 张学渊,魏伟,周亮,等.西北干旱区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分析[J].生态学报,2021,41(12):4707-4719.
[17] NELSON R,KOKIC P,CRIMP S,et al.The vulnerability of Australian rural communities to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Part I—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vulnerability[J].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2010,13(1):8-17.
[18] PENG B H,HUANG Q Q,ELAHI E,et al.Ecological environment vulnerability and driving force of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J].Sustainability,2019,11(23):6623.
[19] ADGER N W.Vulnerability[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16(3):268-281.
[20] 蔡庆华.长江大保护与流域生态学[J].人民长江,2020,51(1):70-74.
(编辑:黄文晋)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ulnerabilit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rategy of cross-border watershed
WANG Junjie1,2,HE Shoukui2,LIANG Gongwen3
(1.Powerchina Eco-environment Group Co.,Ltd.,Shenzhen 518100,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74,China; 3.Chongqing Urba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Group) Co.,Ltd.,Chongqing 401121,China)
Abstra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ross-border watersheds still faces the problems of incomplete horizontal govern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low willingness of governance entities to actively implement policies.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decision-making among governance entities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watersheds and realizing ecological value.We constructed the Nash non-cooperative game,Stackelberg master-slave game,and collaborative cooperative game models to analyz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governments in the watershed,and established a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watersh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ffort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governments are insufficient under non-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 the economic level than non-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It is difficult fo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governments to spontaneously achiev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Through a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ross-border watersh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cross-border river basin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ies.
Key words:
cross-border watershed;ecological environment vulnerability;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collaborative governance;decision behavior g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