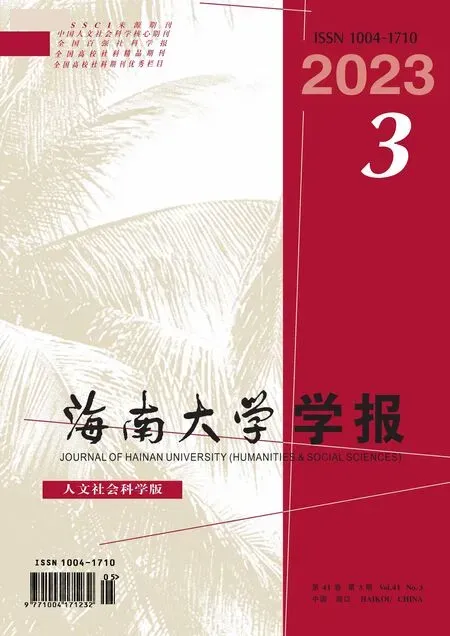塞涅卡的申辩
2023-08-07徐健
徐 健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塞涅卡,这位著名的晚期廊下派代表,无疑是西方历史上因集哲学与财富于一身而最受物议的思想人物。据塔西佗《编年史》所述,公元58年,一位名叫苏伊利乌斯(P. Suillius Rufus)的职业控告人因受元老院弹劾,在私底下大肆抨击作为尼禄顾问和元老而处于个人权力巅峰的塞涅卡,特别是指责他通过网罗无嗣者的遗产和投放高利贷而积累了巨额财富,“是靠着什么样的智慧、哪一派的哲学训导,可以让他在取得皇帝宠信的四年当中搜刮到三万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1]后来,苏伊利乌斯的指控传到了塞涅卡耳里。追求知行合一理应属于哲人的本分[2]236-239,因此,学界广泛认为,作为哲人的塞涅卡很可能正是为回应苏伊利乌斯的责难而创作了《论幸福生活》[3-4]①本文引用《论幸福生活》时随文标注章节,译文则采自穆启乐等人的中译本,并据Basore的拉英对照本改动。,尽管回应未必是及时的且题赠人是自己的兄长,《使徒行传》中的科林斯总督盖利欧(L. Iunius Gallio Annaeanus)。
除了其他少许小缺损外,今存《论幸福生活》文本的突然终止令人难以确定结尾处缺损的程度。但就现有篇幅而言,文本可分成三个部分:幸福生活的领路人(1.1-3.2);关于幸福的诸定义(3.3-16.3);塞涅卡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辩护(17.1-28.1)。我们自然会疑惑:面对苏伊利乌斯这种智识水准的人,何必拉扯前两部分的内容呢?在最后一部分中,塞涅卡特别安排了苏格拉底出场,这不免让人联想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哲人遭受种种指控,又借着申辩的契机来仔细检讨众人及其背后的某些智识人的意见。因此,如果考虑到第一部分表明廊下派式哲人而非众人在幸福生活方面的权威,而第二部分则将众人的愿欲与伊壁鸠鲁派的愿欲相勾连,那么可以说,“塞涅卡的申辩”并非限于最后那部分,而是整篇文本的基调。由此入手,我们能够深入阐发塞涅卡对哲学传统的创新性挪用,进而明晓其思想的纹理和品质,以期重新认识这篇具有持久魅力的申辩词。
一、众人与哲人:谁才是幸福生活的真正领路人?
在《论幸福生活》开篇,塞涅卡对盖利欧兄长说道:“所有人都想幸福地生活,然而对于看清楚是什么创造了幸福的生活,他们却处于迷雾之中。”因此,有必要首先确定什么是幸福,然后寻找一条通往幸福的最便捷的道路。而相比其他追求,这里尤其需要富有经验的领路人,而不能追随众人的足迹:
当问题涉及幸福生活时,你不可以以分立表决的方式回答我:“这一方看起来更多。”正因为如此,这是更坏的一方。人类事务并没有安排得那么好,以至于更好的东西取悦更多的人。(2.1)
分立表决(discessio)是罗马元老院采取的一种表决方式。元老们如果支持哪一位的议案,就各自走到哪一位身边,最后首席元老就用“这一方看起来更多”这句话来宣布表决结果。在民主政治决断中,“势众”意味着“更强”,“更强”又意味着“更好”。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开篇中,民主人士珀勒马科斯仗着自己这边人多从而“更强”(keittous),而阻断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向上”的回城之路。形容词keittous的原型是“好”,所以该词还具有“更好的”意思。可见,“更强”和“更好”被珀勒马科斯糅合了起来。但它们又被苏格拉底暗中撕扯开,因为苏格拉底最终是为了教育格劳孔而非因为受到强制才留在了港口[5]。类似地,塞涅卡也打算重新审视这种糅合。在他看来,众人“反复无常”,是“真理最坏的阐释者”(1.5,2.2);如果我们模仿他们的幸福之道,就会被手手相传的错误弄得晕头转向以致被掀翻在地。
塞涅卡接着指出:“我称为群氓的既有那些穿着袍子的,也有那些戴着冠冕的,因为我并不关注装扮身体的衣服的颜色。”既然政治人和常人一样也被视为群氓或众人,那么知晓幸福之知识的人就至少是哲人了。如果说苏格拉底会“下到”城邦以教化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潜在的政治青年,那么塞涅卡则似乎并没有着意突出政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为了彻底摆脱错误观念从而恢复健康或理性,我们必须“脱离”(separemur)一切众人,“退回”(recedere)即“崇拜”心灵自身。而心灵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自己“坦白”(fatebitur)真相(1.4,2.2,8.3-4)。在这份长长的自白中,心灵以第一人称“我”,控诉自己过去像众人那般只顾追求表面上的善,比如口才、财富、影响力、权力,而忽视了真正的善;结果是,“除了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并为妒忌指明能刺痛我的地方外,我又得到了什么呢?”(2.3)看起来,这心灵既可以泛指任何人的心灵,也可以暗指塞涅卡的心灵。换句话说,塞涅卡在这里,如同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提醒听众和自己:要自知无知,以便取得哲学上的进步[6]222-223。
那如何寻找真正的善?塞涅卡说:“让我们来发掘这一事物吧,它的位置并不遥远:它将被发现,只要你知道应该朝哪儿伸出手;然而现在我们就像在黑暗里从附近的东西旁边走过,侥幸碰上我们渴求的事物。”(3.1)在《理想国》第四卷中,苏格拉底在带领格劳孔进入密林深处以围猎正义时也有类似的描述,但要冗长许多,以至于急着捕获正义的格劳孔有些不耐烦。而塞涅卡似乎不想盖利欧也有如此抱怨,所以描绘得更简短,甚至还说:“我不会带你兜圈子,我将略过其他人的观点,因为一一列举和反驳它们需要很长时间——接受我们的观点吧!”(3.2)这意味着,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塞涅卡对细腻的观念辨析从而对心智的辩证式攀升兴趣不大;他更愿意像智术师忒拉绪马科斯那样直接抛出他觉得最正确的观点,并要读者先行接受。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如同医术,其目的仅仅在于为不幸福的个体心灵开出富有疗效的药方(1.4)。
这药方是什么呢?是廊下派的幸福论。但塞涅卡通过再次调用元老院的政治议程,来表明自己可能会支持某位廊下派哲人的提议,也可能会支持他的部分提议,还有可能会进一步说“我做此补充”(3.2)。显然,第三种探讨方式并没有排除塞涅卡借鉴或采纳非廊下派的观点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后两种探讨方式反映出塞涅卡必将对廊下派幸福论作出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幸福生活的真正领路人乃塞涅卡的廊下派。
二、幸福生活:与伊壁鸠鲁派论辩
塞涅卡认同整个廊下派的基本原则:遵循“万物的自然”(rerum naturae)。由此,他给出了幸福生活的第一个定义:“与自身的自然(naturae suae)相一致的生活。”(3.3)据载,廊下派创始人芝诺有时将幸福视为“与[普遍的]自然一致地生活”[7]395,而他的重要门生克律希珀斯(Chrysippus)则扩展了芝诺定义中的“自然”,认为它同时指“人所特有的自然”,因为“我们自身的自然乃整个自然的组成部分”[7]395。看来,塞涅卡所说的“自身的自然”乃克律希珀斯的双重“自然”,既然他也谈到了“万物的自然”。
这还反映在他随即讲到的如此理解下的幸福生活的实践中。首先,心灵要确保自身的健康。根据前述,这意味着它首先要隔绝并在自身中清除群氓的意见,以便追随理性。然后,它要在主宰万物的无常命运面前,表现出“勇敢”(fortis)以及附属于勇敢的有力和忍耐[7]380,也就是说要“顺应时势”(apta tem⁃poribus)。因为,身体和身外之物不过是机运供我们使用而非所有的礼物,它们渺小脆弱,虽需留意但不必为之焦虑。男子气概或德性(virtus)就是顺从命运、蔑视苦乐。而心灵也因德性而产生与快乐相对的、“巨大的愉悦(gaudium)①gaudium[愉悦]对译希腊词chara,本该是廊下派的专业术语;但作为修辞行家的塞涅卡还将其与hilaritas[欣悦]、laetita[欢喜]、delec⁃tabitur[欣喜]甚至vera voluptas[真正的快乐]混用。,稳定而平正”,再是产生永恒的“宁静”(tranquillitatem)或“自由”(libertatem)。但这样一副内聚性的强大心灵并非没有外延,因为它还拥有一种指向他人的“不乏温和的伟大”。
随后,关于幸福生活,塞涅卡通过聚焦或延伸第一个定义及其实践之某方面,又作出了若干不同的定义。他说,所有定义只是根据不同的场合,给幸福换上不同的“面貌”,而无损它的“效力”,犹如一支军队根据需要变换各种阵型,其力量不减,其意志不变(4.1,4.3)。这种富于变化的重复是塞涅卡灵魂治疗术惯用的修辞,也是《论幸福生活》关键的行文特征。在给出那强调机运、德性和欢喜之关联的第二个定义之后,他提出了第三个定义,其中强调了“对于事务富有经验”以及“丰沛的人道和对与之交往之人的关怀”(4.2)。这里再次指向克律希珀斯的普遍自然视角,因为他曾说幸福是“根据对自然所发生之事的经验来生活”[7]395。还有,humanitas[人道]是希腊语词philanthrōpia[博爱]的拉丁译法,这两个词都是廊下派的重要术语;如此,塞涅卡所教导的是对人类的普遍的爱,而不是对罗马人的爱。苏格拉底即使是在接受审判时仍然表露出对雅典同胞的偏爱[8]112-116。
在第五个定义中,塞涅卡首先以不同的语词表达了第四个定义的要旨之一:“唯一的善是高尚,唯一的恶是羞耻,而其他的不过是既无损又无益于幸福生活的事物的琐碎集合。”(4.3)这里明确摆出了廊下派对事物的三分法,德性及含有德性的事物与恶德及含有恶德的事物各执一端,非善非恶的中性物(in⁃differents)则居于中间。幸福由德性构成,其本身与数目众多的无常之物无关。其次,塞涅卡解释了第四个定义中的另一个要旨,即“真正的快乐将是对快乐的蔑视”。他说,发自心灵深处的欣悦和欢喜“源源不断”地随着作为善的德性而来,“巨大而恒定”;而快乐却源于“渺小身体的卑微、琐碎而变幻无常的活动”(4.2,4.4-5)。愉悦与快乐的对峙是廊下派的标准学说,但愉悦在塞涅卡那里是德性“永恒的”(22.3)而非“可能的”“副产物”[9]24,27。直到第六个也即最后一个定义,塞涅卡才强调了似乎应该首先强调的理性:“幸福生活建立在正确而可靠的判断(iudicio)之上,且稳定不变。”在无常的事物面前应当无欲无惧,这不是出于岩石般的麻木,也不是出于动物般的无知,而是得益于对幸福的真知。大众与动物几乎无异,他们的理性不过是堕落乖张的“机巧”(sollers),正因此他们不可能幸福(5.1-3)。
但廊下派式的幸福难免会让人觉得不过是一种严苛而乏味的理想。在此,塞涅卡设想了一名来自伊壁鸠鲁派的反对者——“但是,心灵也会有它自身的快乐”(6.1)。塞涅卡给出的回应是,心灵的快乐源于对身体性快乐的回忆、体验尤其是期待,所以,被取悦感官的事物所塞满的心灵是败坏而多变的。但伊壁鸠鲁派显然不会认为快乐能与德性相分离,而是会说德性作为工具生成了快乐,进而实现了幸福。塞涅卡料到了这一点,从而置身于廊下派与伊壁鸠鲁派的持久论战之中,现在他必须证明德性本身足以成就幸福。
首先塞涅卡说德性与快乐是不同甚至对立的事物,因为事实表明,一些事令人快乐却不正派,一些事正派但要通过痛苦来达成,可见“德性经常缺乏快乐,也从不需要它”(7.2)。但这也意味着德性有时是与快乐并存的。塞涅卡并没有彻底否定快乐,而是紧接着要求快乐像援军一样在幸福生活中服从自然,也就是服从自然的必要需求,诸如饥饿、口渴和性。它是随这些受到节制的需求的满足而来;一旦僭越,它就会堕落成“放纵”[2]462。这样,塞涅卡不仅区分了愉悦和快乐,还区分了两种快乐。在廊下派那里,愉悦是一种“好的情感”,是“合理的昂扬”;而快乐则常被分成自然需求的“副产物”和“不合理的昂扬”,后一种快乐是需要彻底治疗的“激情”之一[9]105-107。能与德性相伴的既有愉悦也有位阶较低的自然快乐,但“让德性领头,让它举着旗帜”(14.1)。因为恰如廊下派所言,人在心智渐趋成熟后会生成更高级的自然:虽然理性后于感官并需要受到感官的刺激,但理性及其产生的德性要比原本的需求更自然。
然而,反对者不依不饶,针对塞涅卡个人发起了攻击:“但是你培植德性也无非是因为希望从中获取某种快乐。”(9.1)他质疑的是,如果德性领导快乐,那这位统帅又为自己图什么呢?塞涅卡回答,既然德性是至高的存在,没有任何比它更好的东西了,那么德性本身就是对“我”的回报。“快乐不是德性的报酬也不是其原因,而是它的副产物(accessio),并且德性不是因为它取悦人而被赞成,而是如果它被赞成,它也取悦人。”(9.2)这里的快乐明显指自然快乐,在塞涅卡看来,它就像庄稼地上附带长出的一些花朵,尽管赏心悦目,但终归不是农人劳作的初衷。对德性的追求必须是因为德性自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任何快乐,否则难免会本末倒置甚至伤及根本。不过,反对者抱怨塞涅卡曲解了他的意思:“快乐的生活除非有德性相伴,否则不会降临。”(10.1)言下之意,让快乐统领德性不见得就会出现纵情享乐,因为统帅不该肆意践踏辅助者。但塞涅卡反驳道,只要快乐取代德性成为“至善”,对快乐的节制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善不得消减;并且,这容易助长伪善,即给种种扭曲的快乐穿上道德的外衣。他说,正是“那些最愚蠢的人”充溢着你所说的快乐。伊壁鸠鲁派的幸福论不仅难以教化众人,反而会使众人理直气壮地追求“放纵”:
他们奉承了最坏的人。那沉湎于快乐中的人,一直打着酒嗝,酩酊大醉,因为他知道自己生活在快乐中,所以当他听说快乐不能和德性分离时,他相信自己也生活在德性中;然后他为自己的恶德铭刻上智慧之名,并且宣扬本该掩饰的行为。(12.3)
类似地,苏格拉底说智术师们把众人的一切冲动和欲望都揣摩尽了,进而迎合或“豢养着一头巨大的、强壮的畜牲”[10]。显然,伊壁鸠鲁派或伊壁鸠鲁主义不能完全等同于伊壁鸠鲁。但在这方面呢?据塞涅卡所述,大多数廊下派哲人认为伊壁鸠鲁派的创始人也难辞其咎。但塞涅卡本人却有同情的理解,说只要深入内里就能发现:“伊壁鸠鲁的那种快乐是多么清醒和节制——凭赫库勒斯,我是这么看的。”(12.4)换言之,伊壁鸠鲁说的是自然快乐,它止于自然的身体需求,能与德性相结合。因此,“伊壁鸠鲁的教诲是神圣而正直的”。但那些不愿深究的享乐之徒却只因快乐被颂扬而齐聚伊壁鸠鲁的菜园(Gar⁃don)。他们追随的不是“所听到的快乐”,而是“所带来的快乐”(13.1-2)。所以说,他们不是在伊壁鸠鲁的鼓动下放纵,而是原本就已放纵。可毕竟他们被诱人的称号所吸引,因此塞涅卡依旧认为:“称扬快乐是有害的,因为正派的训导潜藏于内,而使人败坏的训导显扬于外。”(12.5)
可见,虽然伊壁鸠鲁本人通过分辨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快乐而不让自己被快乐所裹挟,但他将快乐抬至首位的做法本身却容易被人滥用。塞涅卡对伊壁鸠鲁及其学派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并且可以说,他实则颠倒了伊壁鸠鲁的训导秩序:让德性显扬于外,而让自然快乐和愉悦潜藏于内。“然而,有什么能禁止德性和快乐融为一体并构成至善,以至于同一事物既正派又令人快乐?”(15.1)那位反对者如是质问,他似乎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不再将至善等同于快乐,尽管德性和快乐在至善中必然是不对等的。为此塞涅卡指出,愉悦固然是善,但并非至善的一部分,它只是至善的永久追随者。另外根据前述的“花朵喻”,自然快乐只是至善的间歇性追随者。总之,唯有德性才是幸福的达成者。
三、在众人面前自辩:苏格拉底的出场
塞涅卡的最终结论让那位佯为众人导师的伊壁鸠鲁主义者颇感吃惊,后者怀疑这种廊下派式的幸福是不可臻达的。类似地,塞涅卡紧接着设想了“那些对着哲学狂吠的人中的某位”所惯用的攻击:“为什么你说得比你活得更加勇敢呢?”(17.1)这位攻击者显然属于和哲人相对的众人。他随即列数了一长串指控,诸如对上级低声下气、因失去而被触动、被闲言碎语所影响,尤其是颇为具体地质问了塞涅卡如何视金钱和奢侈为必需:家什光鲜、炫耀金器、遮阴的树木、用餐考究、童仆衣着昂贵等等。塞涅卡不仅没有否认所有这些控诉,反倒就奢靡生活交代了进一步的证据:多到自己都没数的海外财产和奴隶。
之后,塞涅卡就像在回应那位伊壁鸠鲁主义者的震惊时那样来为自己的“恶行”辩解。他沿用了廊下派对人的三分法:圣人或智者(sapiens)、恶人或众人,以及居于中间的道德进步者。首先,塞涅卡坦言“我不是智者”且将来大概也不会成为智者,因为自己的灵魂疾病未能甚至永远不能得以“根治”。尽管如此,“跟你比起来,跛足的人啊,我无异于赛跑选手”(17.3-4)。即他承认“我”是已然取得明显道德进展的人。但他旋即又否认了这样的自我定位:“我说这些并非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那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人,因为我深陷于各种恶习之中。”(17.4)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塞涅卡的“我”是一个滑溜的用词。这里他采用了自谦的辩护策略,似乎将“我”归入跛足的众人之列——只是“我”仍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跛足或无知,从而有机会向德性进发。
无论塞涅卡离德性到底有多少距离,指控者都不能责备作为非圣贤的他言行不一。正如先前援引伊壁鸠鲁来驳斥伊壁鸠鲁派,塞涅卡现在将与那些追求哲学的伟大人物结盟来回击众人的代表。他不仅引柏拉图、伊壁鸠鲁、芝诺等人为援;还特别突出了犬儒派的德谟特里俄斯(Demetrius)和伊壁鸠鲁派的狄俄多儒斯(Diodorus),前者极端贫穷却仍被众人认为不够贫穷,后者因那违背伊壁鸠鲁信条的自杀行为而遭到众人轻蔑。塞涅卡说:
你们这些憎恨德性及其培育者的人,没有做任何新的事情。因为,病弱的眼睛惧怕太阳,而夜行的动物躲避明亮的白昼——它们在破晓时惊慌失措,到处寻找自己的巢穴,躲藏在某条缝隙之中,对光明畏惧不已。(20.6)
这个譬喻颇似《理想国》第七卷中描绘的洞穴场景。可以说,盲瞎的众人就像夜行的动物依赖自己的洞穴或城邦,习惯于影子或意见,而惧怕太阳或善本身。因此,当观看过太阳的爱智者被迫下到洞穴众人之间,难免不会引起他们的嘲笑、诽谤,乃至辱骂——塞涅卡还将众人比作狂吠不止的狗。正如引文首句暗示的,众人与真正的爱智者之间或者城邦与真正的哲学之间的冲突是永恒的。但不像柏拉图,塞涅卡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冲突与哲学本身对意见世界的根本性威胁有关,而只注意到它归根究底是众人对爱智者天然的“嫉妒”造成的:“因为无人被视为好人于你们有利,仿佛他人的德性是对你们缺点的指责一样。”(19.2)看起来,太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灼伤众人的双眼,洞穴也无须哲学的审慎。
塞涅卡告诫指控者要多留意和赞扬伟大灵魂们的高贵努力,尤其是他们的伟大事业本身。但塞涅卡以第一人称“我”来描述这样的伟大事业。可以想见,它将是廊下派式的。首先,要不动心地(indifferently)看待死亡和财富等中性物的得与失;其次,要慷慨地施予任何他人以应得之物。这暗示出中性物与德性虽存在本质差别,但仍有某种重要的关联。最后,“我的祖国即是世界,而它的主宰即是诸神,他们立于我之上,在我的周围,做我言行的监察官”(20.5)。这应该指的是西塞罗时代的廊下派宇宙城邦(cosmos-city):所有的神和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受自然法和博爱支配的宇宙城邦中,但神和神样的圣人因具有同等德性而共享宇宙公民权,统治着作为潜在宇宙公民的其他人[11]。那么,世界主义与德性从而与中性物又有何关联?
然而,指控者似乎没法理解作为塞涅卡哲学事业之首要部分的哲人对中性物的态度。故而他首先重述了最初控诉的核心部分:“为什么那人既热衷于哲学,却又过着如此富裕的生活呢?”即,钱财怎能既被轻视又被占有。之后他谈到了流放和生命,说二者如何在被轻视的同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或“如果没什么阻碍的话”,又被避免或追求(21.1)。令指控者不解的是,如果说中性物无关乎幸福从而应当受到轻视,那么对它们的追求或回避又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塞涅卡在设计这份指控和随后的回应时都用了第三人称,但均明显隐射其本人;并且,在两种情况下都特别关注财富。“他”暗中遵循芝诺的观点,回应道:中性物自身有一定的价值,并且其中一些本身就比相反的另外一些“更可取”(potiora)。首先,财富和贫穷都可以作为德性的“材料”(materia)[9]27,46,但财富提供的材料要更加丰富:贫穷有利于勇敢方面的德性的实践,而财富使得节制、慷慨、谨慎、条理和高迈等更多的德性有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其次,财富能够给自德性而生的愉悦“增添点东西”,就像航行时的顺风和冬日里的暖阳。不管怎样,这两项证明似乎基本属于塞涅卡自己的发挥,许是因为正在自辩的他特别想凸显财富与德性的关联。
但这样一来,说“财富属于更可取的事物”和说“财富属于善的事物”又有何分别呢?换作指控者的大众化表述就是:“你为什么嘲笑我,既然财富在你那里和在我这里占据着同样的位置?”(22.4-5)这时,塞涅卡的辩解策略从探讨追求时的动机转向了探讨失去后的态度,或者说从强调更可取性转向了强调中性。他说,如果财富从身边流走,他不会像众人那样焦虑,而是会不动心地送别。可见,更可取不等于更好,因为只有被视为善的事物才会激起人心的波澜。由此,我们可以对那两项证明作进一步的理解。塞涅卡没有说财富能够增添愉悦;因为,正如德性,伴随德性而来的平滑的愉悦本身并不缺乏什么。但就像财富能够为德性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在财富之中愉悦也能更加宽广。塞涅卡在《道德书简》中做过形象的描绘:当太阳被云层遮挡时,其本身不会变小或变慢,只是在我们眼里显得不那么明亮了,同样,在不利的境况下,德性和愉悦本身不会被削弱,但不像原先那般耀眼了[6]250-252。
我们已看到,指控者在涉及流放和生命时用了两个意思一致的假设从句。在廊下派那里,这类用法意指某中性物的更可取性是就通常境况而言的,当出现某些特殊境况时,相反的中性物反倒更可取;唯有善之价值是绝对的[7]355,369。因此,财富的更可取性取决于环境,尽管指控者在提到财富时没有用那类假设从句。对境况的甄别依赖于理性;正如当理性要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会选择自杀(20.5),当理性要我舍弃财产时我也有能力做一个穷人。哲人比非理性的众人更懂得如何对待财富。所以塞涅卡说,“不要再禁止哲人拥有钱财了,无人曾判智慧以贫穷之刑”(23.1),只要取之有道——财富就是“德性的果实”(23.3)。就像自然快乐,财富并非德性的原因或报酬,但却是德性所应得的。在此,财富与德性的关联再次得到了强调[6]249。如同钱财的流入,钱财的流出在哲人那里也是正派的。为此塞涅卡花了不少笔墨来谈论慷慨,并且是基于一种世界主义的视域。慷慨(liberalitas)的德性出自“自由的心灵”(libero animo),但并非必须指向“自由之人”(liberis)——具有社会身份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哪怕是奴隶也可成为资助对象,只要他是好人或能够变好的人。“自然令我造福所有人”(24.3),所有符合那唯一的、超政治的甄选标准的人。
塞涅卡就这样向众人解释了自己的哲学目标。现在,他将召唤一个言行一致的智者来为自己的哲学生活作最终的申辩。这位智者一开始是匿名的——“一个已经登上人类善的顶峰的人”(24.4),其言辞的结构与塞涅卡对那位众人的代表所作的回应基本一致。该智者先是嘲讽这位代表的邪恶动机;接着,在表明财富的更可取性之后,通过预见贫穷的来临,转向财富的中性,并承认自己更愿意富有而非贫乏,其间几乎覆盖了这位代表在第一次指控中罗列的关于塞涅卡奢靡生活的证据;最后,在预见广义的逆境的情况下,仍认为“节制我的愉悦要比抑制悲伤更可取”。通过赋予这个智者以名字——“那著名的苏格拉底”(25.4),塞涅卡终于提到了苏格拉底,尽管在《论幸福生活》开篇就暗示了他的出场。仅从结构上看,接下来的苏格拉底讲辞恰好是对智者讲辞的颠倒。
众所周知,几乎整个希腊化哲学都在争辩苏格拉底的道统问题。塞涅卡也不例外。在《论幸福生活》中,苏格拉底不再是具有无知之知的哲人,而是已然获得智慧的圣人;并且,他还偏爱更可取的中性物。在柏拉图的《欧绪德谟》中,苏格拉底处理过非善非恶的事物,并宣称,当且仅当与德性结合时,诸如健康或财富就比其反面具有“更大的善”;或许正是对“更大的善”的不同理解引发了芝诺和廊下派中的异端阿里斯通(Ariston)之间的论战,后者拒不认为苏格拉底会承认某些中性物本身就“更可取”[12]。且不论谁的解释更符合苏格拉底的立场,芝诺的观点成了廊下派的正统,而塞涅卡承袭之,并以此塑造苏格拉底的形象。
塞涅卡的苏格拉底不仅是廊下派化的苏格拉底,还是罗马化的苏格拉底。他请求成为普世万民的征服者,坐上黎伯(Liber)的战车,从东到西,跨越整个世界行凯旋式。也就是他想要被视为罗马君主或神,为世界立法。正如前面涉及廊下派宇宙城邦时所示,圣人和神在德性上无甚差别。但正当此时,苏格拉底尤其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人;在罗马凯旋仪式中,凯旋者也会被身旁的奴隶所这般提醒。另一方面,苏格拉底还设想了作为人的他被置于征服者的游行囚车中,并说自己也能坦然接受这样的境遇。但是,他认为“征服要比被俘更可取”。总之,他鄙视整个“机运王国”,但更愿意处于“轻松欢愉的”环境中而非“血与汗”之中(25.4-5,25.8)。相应地,苏格拉底区分了两类德性:像勇敢这样的直面困苦的德性被归作上坡的德性,需要鞭策;慷慨、节制、温和等则被归为下坡的德性,需要束缚。他更希望运用的是后一类而非前一类德性。那么,他就更愿意在财富之中实践下坡的德性,而非在贫穷之中实践上坡的德性。现在,塞涅卡又让智者而非苏格拉底发言,向众人的代表解释财富的更可取性并非善性:“正当身处财富之中时,智者尤其会预想(meditatur)贫穷。”这就像将军应在和平时为战争做准备,“这战争即使尚未进行,却已经宣布”(26.1-2)。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尤其是在幸运之时预想将来的不幸,不仅认为它们必然会来临,而且会立即来临。如此,未来及其开放的可能性被封闭了,也即被当下化了[13]363-367:智者“满足现状地活着,对未来无忧无虑”(26.3)。那么,当他损失财富时,他仍安于心灵这一真正的财富,从而没有真正的损失。
这时,苏格拉底重新登场,“那位苏格拉底,或是另一位在人类事务上具有同样心态和能力的人”(26.4)。苏格拉底与这另一位人或智者的切换不仅能保留具体的苏格拉底,更能彰显苏格拉底作为典范的智慧形象。在这部分讲辞中,言说者自比朱庇特,说群氓的抨击伤害不了他,如同诗人的愚昧故事伤害不了朱庇特。但他还是愿意去治愈众人。他将德性比作诸神,将智者比作大祭司;每当神谕所甚至某些疯狂的东方宗教崇拜者——苏格拉底还被东方化了——提及神圣的经文或神谕时,都要施予“唇舌之惠”(fauete linguis)。该宗教用词取义于“保持缄默”,以“让祭仪能够有序进行,没有不祥的声音打扰”(26.7)。同样,众人在哲学教诲面前首先切莫“饶舌”而要“缄默”,进而“聆听”德性之声[13]258-264。哲学治疗对沉默的强调类似于前文讲到的它对细致思辨的削减。
最后,塞涅卡将苏格拉底从神谕所移至雅典人的牢狱,让他从这个因他的净化而比元老院更正派的地方向罗马人发言。在其他著述尤其是《道德书简》第104封信中,塞涅卡推崇苏格拉底容忍监禁和毒药等不利因素,同时还称赏他对贫穷的忍受。而现在我们将会看到另一幅苏格拉底图景。苏格拉底说,自打给阿里斯托芬提供笑料起,一帮谐剧诗人用恶毒的俏皮话攻击他,但他如同海中孤岩那般不惧海浪的冲击。现在,他从海洋上升至高空,远眺哲学的敌人们,劝其不要再徒劳地责问:“为什么这个哲人住得如此宽敞?为什么这个哲人晚餐吃得如此讲究?”(27.4)这个匿名哲人显然指塞涅卡。苏格拉底告诫众人要立刻转向关心自身,审视自己败坏的灵魂,否则会被即将到来的灾难所毁灭:“就是现在,虽然你们几乎意识不到,不也正有一场旋风旋转着你们的心灵,在你们逃避和希求同样的事物时席卷着你们,一时被抬至天穹,一时被摔在深渊?”(28.1)现存文本到此结束,最终苏格拉底成了众人的“审判者”。他的预言也就有些类似《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临别告白:“不过,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去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了神。”[8]145但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显得谦卑,从而不带任何“诅咒”。
四、塞涅卡的意图
就这样,塞涅卡在众人及其支持者伊壁鸠鲁派面前,尤其是化用苏格拉底的权威,公开回应了苏伊利乌斯的私下指控,对自己的哲学追求和财富获取之相容作出了廊下派式的辩护。在他看来,德性而非快乐才是幸福的构成部分,但这一观念并没有严苛到否定一切快感,因为它容许愉悦和自然快乐的存在;而作为更可取的中性物,财富能够为种类更多的下坡德性以及愉悦提供宽广的实现空间。这番关于如何生的自辩当然是《论幸福生活》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意图。
然而塞涅卡笔下的苏格拉底强调,在取得财富的同时尤其要预想失去财富;换言之,财富的更可取性所具有的力量取决于它的非善性或中性。可见,训练灵魂不动心地看待财富损失或人生逆境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更需要召唤的是上坡的德性而非下坡的德性[14]。这就是为什么塞涅卡在谈幸福生活的首要定义之实践时将德性等同于男子气概,也是为什么他在《论幸福生活》中的两次发誓均以大力神赫库勒斯为证。
不过,在谈那实践时塞涅卡还暗示,德性是不被苦乐打扰的自由——德性简直等同于自由,等同于心灵做外物之主人的状态。他说这是对宇宙神朱庇特之作为的模仿:“作为宇宙指引者的神虽然也会延伸至外物,但是仍然会从各处向内回到自身。”(8.4)这里牵扯到塞涅卡在别处细述的廊下派宇宙论。随着宇宙大火的结束,朱庇特或创造之火经一系列变化生成四元素,进而产生并渗透宇宙万物;最终万物在大火中又分解成元素并归于创造之火或朱庇特,以此精确地循环往复[4]94-97。可见,原本渗透宇宙的朱庇特退回自身或完全成为外物之主是发生在他焚毁宇宙但尚未再造宇宙的“短暂”间歇[2]43。那么无论是神还是人,其充分的自由只能位于躯体的死亡与重生之间。死亡而非德性才是自由的最高保证,因此,自由不仅不等于德性,还高于德性。对塞涅卡来说,模仿神,实际上最终是要践行这条原则。这样,我们就该期待死亡乃至勇敢地自杀,以便挣脱尘世命运的桎梏。事实上,在阐述自己的哲学事业时,塞涅卡在讲完宇宙城邦之后随即谈到死亡或自杀同自由的勾连。或许,宇宙公民犹如漂浮空中的亡灵轻蔑而又绝望地“俯视”着渺小而溃败的地球[4]88-97。恐怕《论幸福生活》的隐秘意图就在于为何以死而辩。塞涅卡让将要服毒自尽的狱中苏格拉底做最后的发言;而他自己则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乘着尼禄要重建火灾后的罗马之际,归还大部分尼禄早年间的馈赠,而后随着皮索密谋的败露,又异常坚定地服从尼禄所下的自缢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