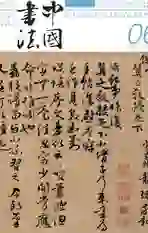试论清流时尚与避『俗』
2023-07-25王登科
王登科
关键词:宋代 清流时尚 避俗
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特殊的观念与范畴,它始终代表着正统与规范。所谓俗,盖指习俗、风气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平庸、凡俗等。雅与俗的连属,本就社会现象中的时尚与世俗而言,与文学艺术批评不相干系。对此,丛文俊先生有过明确的表述:
雅俗的概念最初是针对时尚流俗而言,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批评标准,如唐代尊王羲之为书圣,人争习之,张怀瓘《书断》称其楷书学锺而『古雅不逮』,韩愈《石鼓歌》则称『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都是出于古今、质妍的比较,以雅俗名之。[1]
而雅俗观真正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标准,并运用到文学艺术,特别是书法的批评中来,则肇始于有宋一朝。这与宋代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有关。在此,我们仅就普遍反映于宋代士风中的避『俗』对于书法的影响为线索,略加阐述。黄庭坚《论书》云: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黄氏在此率先指出俗人与俗书的关系,并进一步道出『俗』为士大夫处世的大弊。黄氏此般断言,盖出于他也曾被因俗诟病。《独醒杂志》云:
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张,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
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黄氏草书近俗的病因为『未见怀素真迹尔』,意为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临古与取法。这的确是早期黄氏草书的问题所在。《山谷题跋·锺离跋尾》中他自己透露了这一点:
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时,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识也。
比来更知所作韵俗,下笔不浏离,如禅家『粘皮带骨』语,因此不复作。时有委缣素者,颇为作正书。正书虽不工,差循理尔。
山谷初学书不学古人,所谓的『管中窥豹』『推类为之』即是大概模拟古人,或凭感觉『意临』,即所谓的『便以意成』。黄氏在此也勿加讳言地坦诚了自己少时学书的『想当然耳』是『所作俗韵』的原因。同时也更加证明了钱穆父对于黄氏书法的批评是颇中肯綮的。黄氏在《跋与徐修德草书后》自己也提到这件事:
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悟,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德修来乞草书,至十数请而无倦色愠语,今日试为之,亦自未满意也。[4]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尖锐的批评,使黄氏刻骨铭心,以至于使他一生中始终坚持以避『俗』为宗旨,并形成了他独特的书学思想。他曾无不遗憾地说道学周越书是个错误,对其负面影响太大。如: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5]
一旦选择便积习难改,这的确是黄氏的郁结所在。而他后来一再主张的以『韵』观书,应当看作是『抖擞俗气』的矫枉之举。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黄山谷论书中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6]依此可见,黄氏所言之韵,盖与雅类同。日本学者村上哲夫《雅俗考》中谓:
宋人的雅俗观与六朝及唐人颇不一样,六朝及唐之所谓『雅』乃与士族阶层的门第家世观念相联系,所谓『雅俗』殆同『士庶」,是含有严格的阶层等级意义的;而宋人之『雅』则被理解为纯粹个人人格的含义。
王水照也作:『宋代文人的尚「雅」,比之魏晋文人之常用「雅」以品评人物来,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在一切精神领域中的成熟稳定的重要尺度了。[8]』以上所说的『个人人格的含义』与『在一切精神领域中的成熟穩定的重要尺度』,皆是就『雅』的概念从单纯的社会属性向人格属性的转变而言。而黄氏『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9]的『仿佛』之属,便是指在人与书、雅与韵之间的互换与对言。
丛文俊先生曾指出:『米芾的审美观念是宋代市民思想的产物。』[10]也就是说米氏评书的标准是建构在『市俗化』基础上的一种理论言说,是一种以『俗』为『雅』的观念体系。如冯班《学书钝要》云:『鲁公书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米元章以为恶俗,妄也,欺人之谈也。』[11]从中我们看出米芾独特的雅俗观。『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12]『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13]米氏在此所诟病的『俗』,是以『干禄』为目的的经生书以及刻意而为的『画字』,他们这种『安排费工』都与『适情足意』的书写相去甚远,因而便落入了『俗格』的窠臼。在此,米氏是以『市俗』来反对『世俗』,或者说是『努肆』与『谐气』来对立『心端』与『典实』。《书概》云:『米元章书脱落凡近,虽时有谐气,而谐不伤雅,故高流鲜或訾之。』[14]这是说米氏书法脱俗,即脱『世』之『俗』。而以个性寓于『市谐』之中,即所谓的『放笔一戏空』。米氏的确是以平民的视角观世事,以自我的感知写天真的典范,至于他『近古为雅』的主张与实践,其意未必在『古』。就其『想当然』的临写来看,恐怕还是一种逞天资、适情性的『借尸还魂』而已。
此外,姜夔也有着与米氏相类观点的言说。如: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
真书就应该是以平实端正为最高境界,这种因讹而来的凡庸之见,在姜氏看来,这是唐人始作其俑。并指出唐人楷书有『科举习气』的成因。句中,姜氏虽仅就『真书以平正为善』而指其为『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但姜氏还是道出了『唐人书俗』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在以『潇洒纵横,何拘平正』的比较言说中,晋唐之属,雅俗互见,此意不待言明。后面姜氏接着对魏晋书法的评价,进一步说道:『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16]各尽其态,自然逞露,不加刻意人为的铺排,这是魏晋书法『风流蕴藉』的根本所在。亦如孙过庭所谓的『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自然、天成成为姜氏论书的标准,是『雅』的表现。反之,造作、铺排便入俗,便为『干禄』的『科举习气』。这种观点与米芾的『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的『适性足情』是一致的。
当然,有宋以来士人观念中关于雅与俗标准的确立,并非一成不变的。但就其总体的趣味大致表现为以俗为雅、俗中求雅、亦俗亦雅的基本倾向。同时,那些书法批评中所谓的古与今、质与妍、韵与不韵等对立的观念,都属于雅与俗的问题的换言与变现。其具体的指向或寓意,正如丛文俊先生所谓的『随其时变而略有不同』罢了。
此外,宋代士人书家无论在其日常生活里,还是在思想观念中,对于避『俗』而言,开出了更多的良方以及实践中的努力。如黄庭坚对王著、周越的评价,便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云:
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智永)周散骑《千文》皆绝妙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17]
黄氏在此指出了二位『病韵』的原因是不读书与『随世碌碌』所谓的『胸次之罪』。但也还是『客气地』抑扬了一下二者的『美』与『劲』,这或许是黄氏的为人风格。但对向来『性不忍事』好『快口语』的苏轼,他对李建中的评价却是毫不留情了。云:
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
今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绶),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
这恰恰也是苏轼的性格,一时兴起,直言不讳。而所指谬处,也正是所谓『格韵卑浊』的『俗』。
苏轼高迈一世,卓尔不群,从『不随人观场』是其个性所在,他也是主张读书避『俗』的重要代表。如:『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言外之意应当是:『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除此,欧阳修的『学书消日』,朱长文的『儒者工书,所以自游息焉』等等,都是『俗流』对面的『雅人深致』,它如一泓清湍,涌动在士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