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哥布林化”,Z 世代青年生活新选择
2023-07-19孙琳梁静乌咪画船小羽
孙琳 梁静 乌咪 画船 小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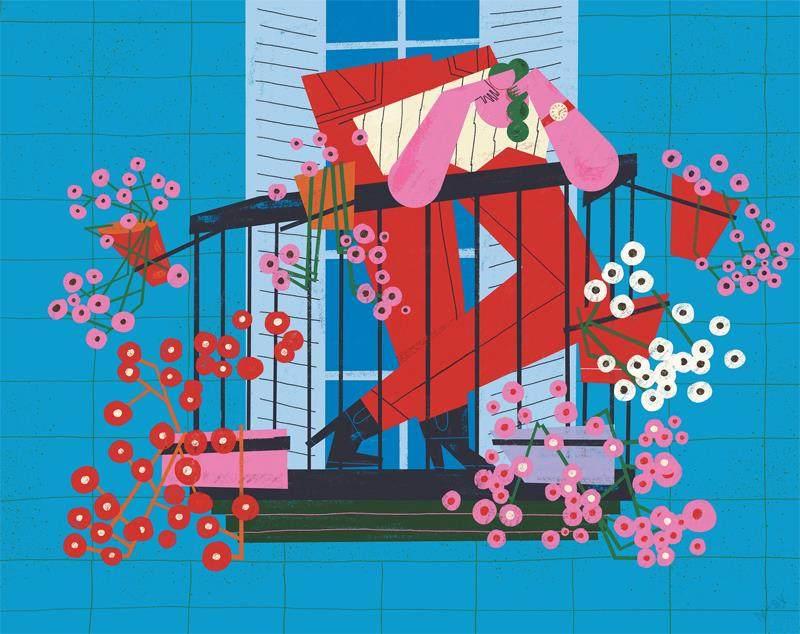
偶尔做个地精,也挺好的
什么才是人生的正确答案,由你来定义。
“我认为‘哥布林模式代表了时代精神。”美国语言学家本·齐默(Ben Zimmer)说。
“哥布林”,指欧洲奇幻小说中出现的住在土地里的小妖精,他们不爱修饰、喜欢自由、享受慵懒,总被崇尚“秩序”“自律”“得体”的人类嘲笑,是各种文学作品中陪衬的小角色。
然而,风水轮流转,近年来,“哥布林模式”成为全球青年人推崇的生活方式。2022年底,该词还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举办的活动中,被各国网友票选为年度词汇。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哥布林模式”的兴起并非偶然,更多的是社会变化过快,令很多年轻人对于“永无止境地升级自己,一定能获得理想幸福”的价值观感到怀疑,开始渴望更简单、更合适自己的生活。毕竟,谁不想做个舒适自在的小妖精呢?
这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社交平台TikTok上体现最明显,年轻人认同的典型“地精”特质,大体是“爱咋咋地”,拒绝按照“大众标准”要求自己。《华盛顿邮报》更进一步指出“哥布林模式”背后的社会现实,“比起前几年网上精心构建的完美正确,现在的青年人更愿意接受生活中的凌乱、刺痛、不堪和真实。”
抛去这个词背后的流行意义,简单来理解,“哥布林模式”,就是在疲惫的时候,停止照搬社交网络与书本里的“正确答案”,面对自己真實的困境,正视欲望,毫不愧疚地做一次自己,自己摸索出正确答案。毕竟,什么才是适合我们的人生方向,由我们自己来定义。
(资料来源:英国《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
德式青年的“落后”生活:摘掉网络滤镜,享受原始快乐
25岁的菲菲是一个上海生、上海长的女孩,2019年到德国巴伐利亚的城市帕绍念研究生。在菲菲的故乡,人们很自然地被快节奏工作、时尚消费、全方位智能化的“先进生活方式”包围。
当菲菲来到德国留学,发现这个被当成发达国家典范的欧洲大国与她想象的完全不同,这里年轻人的生活非常质朴与落后。是的,“落后”,这对她来说,是个相当意外的文化冲击。
真我宣言
我们是否真的一定要按某种够高效、够入时、够高科技的方式来生活?答案是:不用。

人物介绍:菲菲
学生,日常爱好是观察社会,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
滤镜?修图?我们为什么需要它?
美图秀秀、美颜相机之类的P图神器几乎是中国年轻人手机里的必备软件,“拍照一分钟,修图半小时”是菲菲在国内和朋友们聚会时的常态,她可以自信地说,自己已达到十级美颜专家水平,每张精修社交照片都能带来满满的点赞。
到了德国后,她的第一个“发现”,是身边的德国同学基本对“修图”这件事一窍不通。很多人在她说要修修图的时候问:修图?日常拍个照还要修图?那不是去摄影工作室专拍时花钱购买的服务吗?
“德国可是徕卡相机的生产地,各种先进的成像设备和技术都在这里诞生,但我认识的德国人,对拍美照这件事完全没在关心!构图、光圈、角度……统统不在他们拍照的考虑范畴,至于精心摆拍,不存在的,只要看到目标人或物在镜头内了,就直接快门咔嚓一按,一张张无限真实甚至有些丑的照片就出现在了相机里。”菲菲说。
被无数次现实教训后,现在菲菲请路人帮忙拍照时,都会尽量避开德国人,选择亚洲长相的路人一般就没问题,因为她知道,德国人拍照,真的只为了留个念,与精致的打卡文化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真实啊!”问及德国人不喜欢美颜的深层次原因,他们会这样回答。在德国文化中,强调个人的真实性和自然状态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也体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因此,很多德国人认为“美颜”会掩盖或改变人的真实面目,与他们理想中的自然状态相悖。“你已经够美了,怎么还要修图呢?”无数次被身边的德国人问起这个问题,菲菲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菲菲曾和一些德国朋友对此事进行过更深的讨论,他们说,他们注重尊重个人的差异,使用美颜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公平的优越感,这也是他们不太喜欢用美颜的原因之一。
“落后”的社交模式,没什么互联网沉迷
不爱P图,只是德国人“朴实”生活态度的一个缩影。
菲菲还发现,身边的德国同学很多都没有个人社交账号,有些人甚至都没有智能手机。家里没有联网的人也不在少数,她的德国房东Slezak还会為电视节目付费,家里网络也按照每个月50G的流量封顶,“村网通”的网络梗,在德国竟然是现实。
“你都不上网冲浪吗?”菲菲问朋友。得到的回答是:“浏览新闻、收发邮件、搜索资讯,就是我上网的全部目的。”想娱乐怎么办?出门去,与朋友见面;想看电影怎么办?那就去电影院,或者租DVD。“要知道国内租赁DVD可是流行于上个世纪,眼下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商店了,而德国大街小巷还经常能够见到。”菲菲感叹道。
比起网上交流,德国人更喜欢通过面对面的交往来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菲菲说:“以前在国内,下了课,我们都爱在宿舍里各自上网,学新东西、娱乐、做一些兼职工作,朋友们互动的方式首推联机打游戏,而在德国,同学们没事都在野餐、踢球、晒太阳……互联网对他们来说只是工具,在生活中的存在感没那么强。”
德国人也不爱在网上发自己的状态,他们会顾虑信息泄露问题。如果说全世界哪个国家的人最注重隐私,德国人肯定榜上有名。他们保护隐私的警惕性,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他们与很多社交媒体、互联网工具的亲密接触。
“很难想象,在电子支付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多德国餐厅仍然只接受现金,因为刷卡、电子支付让一些人担心泄露隐私。”
德国政府对于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有着较为严格的监管和管理制度,在社交媒体使用方面也有相关的限制和规定,这直接影响了德国人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
德国人的“呆”:钝感与不内卷
在德国待久了,菲菲感受到了德国人这种质朴生活背后的舒适。在德国的小镇和乡村,能看到古老的房屋、自然的景色,人们大多骑着自行车出行,衣着简单,谈吐平和。
她注意到,德国青年更愿意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比如买高质量食物,优质面包、奶酪和蔬菜等,他们倾向于选择当地产品,这些东西通常没啥可“炫”的,但对健康与环境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比起唱K、玩剧本杀、相约打卡网红地标等中国年轻人喜欢的社交活动,德国年轻人明显更喜欢骑自行车、野餐、徒步之类的户外活动,而且,不打卡。
德国的生活文化也“简单粗暴”,对德国人来说,能安排足够的休闲时间,才是有“生活质量”的证明。
德国人对宠物的态度,也让菲菲充分体会到他们的“朴实”。菲菲在上海时,养猫的过程像在不停“升级”,网络风行的“萌宠文化”带火了相关生意,从衣食住行到美容医疗。要做一个优秀的猫主人,不仅猫粮要做功课,猫玩具、猫抓板、化毛膏等用品也不能忽视,甚至还要给猫拍美照、建一个社交账号……面面俱到,才觉得自己达标了。
但在德国,她发现邻居家的猫不仅不会穿衣服、戴饰品,还时常在院子里、房顶上跑来跑去,在雪地里打滚,蹲在路边喝雨水,时不时给主人叼回来一只麻雀、一只老鼠当礼物。主人说,除了必要的疫苗、驱虫、体检、治疗,自己几乎没给猫花过什么钱。当菲菲展示自己在国内给猫咪配备的自动饮水机、自动猫砂盆、自动喂食器时,这位德国铲屎官觉得大开眼界,但欣赏过后,她表示自己不会去尝试这些产品,“我的猫是家庭成员,我觉得要尊重它的天性,我可以花时间陪着它,也可以让它自己在院子里玩耍,但我不想靠一些高科技的用品将它圈养。”
“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总的来说是简单而有意义的。”菲菲渐渐习惯了德国人对时尚、网络、消费的钝感,他们这种“落后”的生活方式,对很多外国留学生来说是种新鲜的体验,也是一种思想的启示。
“我开始思考,我是否真的一定要按某种够高效、够入时、够高科技的方式来生活?我是否可以追求一种更简单、更不在意别人眼光的生活?未来有一天,我是否尝试以更自由的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以一种看似落后的方式来追求更加健康、自由和有意义的人生?”菲菲说。
出走的公主
闷C还记得,四年前那个下午,她到社区的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证件照。摄影师问她,证件照的用途是什么,她小声应:“离婚。”
“大声点。”摄影师没听清。
“离婚!!!”
闷C的声音,回荡在工作室,吓到了同一时间正在那里拍摄结婚照的一对年轻人。
而这张拍摄过程略带尴尬,被闷C称为“美到不像自己”的离婚证件照,最后成了她的作品《最美自由意志》里的第一张照片。
离婚,也许是伤感的。但是,闷C在照片上看到的,却是一个有关自我的思考:“这张通过后期编辑,感官上并不像自己,但是却能证明是我的照片,究竟是自由意志,还是社会的趋同性审美?”为此,闷C特地跑到不同的工作室拍了十二组证件照,得到了十二张完全不同的“自己”。
在三十多年的人生里,她不断和“规则”较劲,面对世俗标准与真实自我的冲突,总想露出自己不光滑却真实的一面,跟这个世界聊聊天。她不想做童话里的公主,娇柔又受人宠爱;她举起心中的利剑,挑战那些限制女性的规则,结果往往是,那铜墙铁壁的限制,一捅就破。
我不想成为精英人士
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家庭的闷C,起初更像是“别人家的小孩”,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几名,无论学习还是生活,都不需要父母操心。
那时,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去考清华北大之类的大学,但在高三那年,她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参加艺考,当美术生。闷C并没有任何系统学习画画的经历,她第一次接触素描,是在高二,她看到一个女生在画,觉得蛮酷的。也是从那时起,她发现,原来人生除了当律师、医生、老师,还有别的路。
因为不想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精英人士”,闷C选择了艺术,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别人眼中决定人生的志向填报,闷C就这么莽撞地更改了。她这样的人,也许天生就适合搞艺术,即便是在美院,她也是一个“异类”。
闷C所在的版画系,是美院当中偏传统的一个学科。木刻版画这类工艺,很多人都会画比较具象、精细的图像,闷C却在毕业展上非常大胆地做了一个抽象的版画作品,和传统版画大相径庭。因为实在太不像是版画系的作品,在展览的前一天,闷C的作品被系主任从最显眼的中心位调到了展厅最里面的位置。那时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挑战了常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闷C是不自觉的,并非故意,但“人有时候忠于自己,就是在冒犯别人的常规”。


我不想成为面目模糊的妈妈
尽管闷C总喜欢走不一样的路,但她起初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她的“自我”,是在磕磕绊绊中长大的。毕业后,闷C并没有坚定地要成为一个艺术家,直到艺术在她最低谷时像信仰一样拯救了她,她才认定艺术。
结婚的第七年,她生了二胎,在家里当全职妈妈,那一年,她陷入强烈的身份焦虑当中。一方面,她是妈妈,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白天的生活被琐事填满;另一方面,她渴求得到一些“妈妈”以外的成就感,然而,她的情感需求总是被身边人忽略。白天的焦虑,化作深夜的创作欲,那时,闷C一到晚上就疯狂画画。她说:“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自己在画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去画。我需要画画这样一种属于自我的东西,去稳住自己的人生。因为有了画画,我才能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继续生活下去。”
很多人不理解,她白天都那么累了晚上为什么还要画画,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画画是她守住自我的一个方式,她“不想要”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妈妈。
那个阶段,闷C画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她画的大多是一些小清新的插画,那段焦虑的时间,她用一幅幅抽象又狂乱的画作表达自己。那些画中,不时会出现一些类似的图像,比如牌坊,那是闷C心中家的符号,有时带给她伤害,有时又让她感到温暖;那些尖尖的三角形,是闷C藏在心里的棱角,它的尖锐,不会刺痛人,但需要被看到。

深夜创作两年后,终于攒够“自我”的闷C决定离婚,然后就有了那张漂亮的离婚证件照,以及因为证件照而创作的《最美自由意志》,那组作品的名字,是闷C那个阶段的注脚:一个通过画笔拯救自己的女性,从“不想要”走向了“想要”。
真我宣言
我需要画画这样一种属于自我的东西,去稳住自己的人生。

人物介绍:闷C
艺术家,文创工作者。关注个人经验与社会文化、世界的关系,试图通过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达,在各种矛盾的现实中找到出口和平衡。“公主请卸妆——闷C艺术作品展”正在广州LOWLOWLAND展出。
我不要成为画框中的空白
如今的闷C,自我变强大了,创作也更自由了。她说现在的自己,就像《瞬息全宇宙》里的杨紫琼,每天都在不同的身份中穿梭:首饰品牌的主理人,两个孩子的妈妈,想法很多的艺术家……
2023年4月,闷C在广州办了一个艺术作品展“公主请卸妆”,展出了她过去几年创作的作品。那里面,有因为离婚而带来靈感的《最美自由意志》,也有她在身份焦虑时画的各种带着情绪的画作。这是目前最能代表她想法的一个展览,她把“公主”当作主题,是因为每个女性在成长中都会深陷各种粉红泡泡的诱惑,她自己也曾在某个阶段,相信“公主和王子会永远幸福生活在一起”。
但现实不是童话,这个展览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请卸妆”,这个妆,不是化妆品的妆,而是社会附加在女性身上的各种“合格标签”——柔顺、漂亮,好妻子、好妈妈等,仿佛具备了这一切,女性才配称为“合格”,否则,就要忍受陌生人的指指点点。
闷C不否认那些美好的名词背后有很多幸福的女性,但是,她觉得大家不需要刻意把那些标签放在自己、别人身上,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标准,每位女性,都是独一无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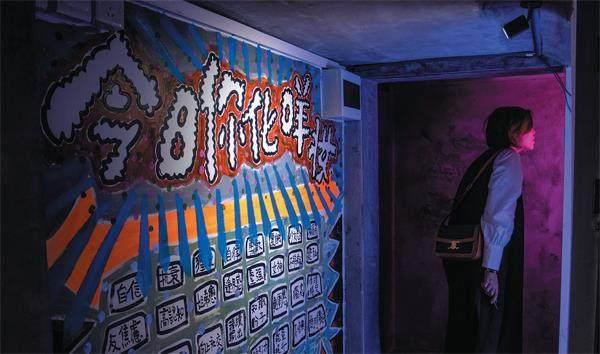
走过身份焦虑期的闷C,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身边依然有很多女性被困在规则当中。四年前,闷C曾联合五位当妈妈的女性,组成一个临时合作小组,通过艺术创作,去探讨女性身份的变化与感受。但在创作期间,一位成员因为丈夫的阻止,不得不退出。在那个原本应该六个人共同创作的项目中,闷C留下了一个空白的画框,她说,“那是留给缺席的她,也是留给其他消失的女性。我们身边很多女性,都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
闷C时常会感激那个在深夜创作的自己——她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但是她需要画,否则,她就会成为画框中的一个空白,不被任何人记起。
我,偶尔休憩在童年的树洞里
收集各种童话书与沉迷游乐园,是贯穿我童年的一个主题。
但童年沉迷的童话与乐园,年纪稍长,就带来了羞耻感。幼稚,在我们的生活里,总是一个负面大于正面的词。后来总有人对我说,你应该长大了,不要再看童话,不要沉迷游乐场,学会与人寒暄,不然这么幼稚以后要怎么办。
但是,成熟,是唯一的选择吗?

真我宣言
我想去游乐园找一棵最隐蔽的大树,在上面挖一个树洞,把所有幼稚的秘密都倾倒进去,然后自己也跳进去,睡一个长长的午觉。

人物介绍:布丁
写作者,游乐园十级爱好者,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候补学员”。
乐园,童年不断重复的梦
我小时候反复做一个梦:自己顺着一条细细的小路向远离家的方向走,一直走一直走,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
这个梦与我的现实生活完全相反,我小时候是一个每天关在家里看书的孤独小孩,不擅长与同龄人游戏,也没去过比自己的小学更远的地方。我在杂志彩页上看过很多五彩缤纷的儿童乐园,但我几乎没机会去——像游乐园这种“玩物丧志”的地方,只有六一儿童节我才能去。
相比很多成年人给自己定下的“高级快乐”,游乐园真是个充满“幼稚快乐”的地方。比起由玩具摊、零食摊、棉花糖、彩虹泡泡构成的花花世界,我其实更渴望坐摩天轮和旋转木马,只要有这两个项目,我就兴奋得几天睡不着,沉浸在眩晕的喜悦中。但一年最多两次的游玩频率,实在太容易让人遗忘当时是什么感觉了,反而是,童年一个人在屋子里,看着天空做白日梦时的渴望那么清晰。
在小时候的那个梦里,我走了很远的路,并且会一直走下去,因为我不知从哪里确信,路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园,我一直没有走到过,但是我相信。
当我有了一个女儿之后,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的渴望藏在一个真正的小孩子背后,以她的名义,去尽情地买各种玩具、各种彩色绘本、各种童话书。
当然,也带她去各式各样的游乐园。
乐园,是成年世界的休止符
母女夜聊的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一起回忆起那些乐园时,我会发现,得到快乐的不仅是我的孩子,还有另一个童年时的我。
我曾经策划过一场夏天去日本的旅行,名义上是赶在签证过期前完成一场家族旅行,真实目的是要赶在女儿超龄之前,去一次东京的吉卜力美术馆,因为听说6岁以下的孩子可以自由登上猫咪公共汽车,我想通过女儿,实现自己童年时的梦想。
但因为疏忽没订上票,这个隐密愿望没能达成。不死心的我,又马不停蹄地给女儿安排了另一场宫崎骏美术展,因为听说那里也有猫咪公共汽车!我在排队(专门排了两次)进入毛茸茸的猫咪公共汽车享受属于自己的5分钟合影后,遗憾又庆幸,遗憾在与二十个人一起匆忙拍照的过程里,不可能有从容跌入童年的体验;庆幸的是,终于触摸到了代表着童年的吉祥物。

我还专门“翘班”去过“环球影城”,跟着一群小孩子进城堡里玩“哈利·波特禁忌之旅”。扣紧安全带,戴上3D眼镜,随飞天扫帚上天入地的那几分钟,过瘾吗?当然。但更让我沉浸其中的,却是手持一杯黃油啤酒游游逛逛时,亲眼见到魔法世界的细节边角。我与自己的小孩,以及无数小孩一起,在奥利凡德魔杖商店里挑花了眼,沉迷在蜂蜜公爵糖果店大罐彩色糖果之间,花最长时间坐在猫头鹰棚屋数到底有多少只猫头鹰。
“游乐园中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我总是问自己。也许是它所传递出的未经修饰的童年感,扔掉一切成人世界的标准,在孩子的世界里,不需要通过虚假的强大来证明自己,一样也会得到善待与祝福。从这方面,对于疲惫追逐“要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成年人来说,游乐园是一个可以心安理得喘息的地方,而且四顾周围,你会发现身边的成年人还真不少,原来,我并不是一个人。
来,到小熊家里做客吧
有一年,女儿迷上了《三只熊》的故事,听说哈尔滨有“三只熊乐园”,接连好几周,都求我带她去。
《三只熊》,是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童话:小姑娘去森林里玩,走进一间小木屋,发现桌前有高椅子、中椅子、小椅子,桌上有大木碗、中木碗和小小蓝色木碗,小姑娘每个椅子都坐了坐,每个碗里的粥都尝了尝,觉得小椅子坐起来最合适,小蓝碗里的粥最好吃。吃完粥,她走进卧室,在大中小三张床上各试躺一下后,发现小床最舒服,就在上面睡着了。木屋的主人,一家三口熊回来,问谁坐了它们的椅子、喝了它们的粥,小熊来到卧室,看到小姑娘躺在自己床上,尖叫起来……
结尾我不记得了,到底是小姑娘跳出窗户跑掉了,还是和三只熊一起坐下喝茶,变成了好朋友?不过不要紧,当我真的带女儿去了这个“三只熊乐园”,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乐园里,滑梯是真正原木搭成的高架滑梯,栏杆上立着颜色鲜艳的松鼠,在周围墨绿色松树的掩映下,它活泼得就像要跳起来玩耍。站在滑梯旁边,能闻到木头的清香,好像就在森林里一样。女儿很喜欢,滑个不停,我坐在旁边的秋千上,轻轻地荡,微风吹过头发,很自在。
乐园里还有一间小木屋,按四百年前俄罗斯传统农舍的方式布置。屋里摆着婴儿摇篮、织布机、壁炉床,窗边的桌子上摆着茶壶、面包。
这一次,故事里的森林小屋在我心中活了过来,不再是一幅插画的样子,而是真的房子,它干净、明亮,有树木香味和许多美丽的装饰。而我和女儿,就像不小心闯进来的小姑娘,忍不住要试试每把椅子,端起每一个茶杯……



我问她,如果你是《三只熊》里的小姑娘,要逃跑吗?
她说,为什么要逃跑?我就是小熊姑娘啊!我要留下来和熊爸爸、熊妈妈、熊宝宝一起喝茶一起玩,你都猜不到有多开心!
“对,不知道有多开心,就像现在这样。”我在心里悄悄地说。
我和甲方,一起“逃”进山里
作为一个身负“业绩KPI”的打工人,“有用社交”一度是我的梦魇词汇,我必须抓住每一次展会、交流会,甚至是朋友孩子满月宴上的机会,结识一切“有用”的人,但我偏偏不擅长如此。
真我宣言
逃到一個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喘一口气。

人物介绍:浅浅
小区爬山协会“理事长”,养生群“唱反调艺术家”。
我总想哭,又找不到人哭
半年前,我才发现,自己像条不停吐丝的蚕,被工作丝茧包裹得透不过气,周末也得不到休息,各路“王姐”“张哥”在微信上催问工作进度,让人烦闷不已。有一段时间,我总想哭,又找不到人哭。
老妈看我状态不对,让我跟她去寺庙做义工,转换一下心情,她周末在寺庙做义工已有一段时间。那个寺庙在半山腰,手机没信号,为了省电,我干脆将数据关了。大概是我佛缘浅,没喜欢上做义工,却莫名喜欢上了山间的宁静。
下山后,连上数据,看着微信上的红点,我突然生出一种隔世之感。消息还是要回复的,工作还是要做的,但是能不能偶尔,哪怕一周只有一天,让我逃离一下有点吵闹的人脉圈,去山里静一静?
爬山局,不谈工作
山里经常没信号,让我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突如其来的工作说NO——有时是山里真的没有信号,有时是我看到了消息,假装没有收到。
大家渐渐知道了我周末爬山的新爱好,竟不太在周末找我说工作了。当然,我平时也会主动把工作安排好,或者提前告知合作方“周末我要进山,有事儿提前给您处理”,居然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蛮出乎我的意料。

进了几次山后,开始有同事、同行,甚至甲方问:能不能带上我?
爬山局,就这么组起来了。
那是一个春天,山里树木才开始泛绿,很多鲜花却已经争先恐后开放,一路上能看到棣棠花、西洋梨、毛樱桃,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为了认出更多的花花草草,朋友还下载了辨识植物的APP,一群成年人围着手机辨识路边花草的样子,像小学生一起上自然课,大家肆意地大笑,而且很有默契地“不谈工作”。
后来,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带上了各自的家属。三四个家庭一起到山间徒步,少了功利,多了惬意,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围着水沟的小水蛇、树林里的蘑菇、路边的小野果子,就能欢笑成一团,完全不用大人看着,这简直是彼此的一种解放。
山中流动着善意
爬山时,我还有个意外的发现,陌生人之间,格外喜欢来一段即兴社交。
有人在山中唱歌剧,完全无惧一群人围观,对着镜头气势如虹唱咏叹调,唱完了骄傲接受大家的鼓掌;有人在山间吹萧,吹完跟大家解释他吹的这曲87版《红楼梦》中的插曲《枉凝眉》中的深意;有人爬到山顶大声吟诵《论语》,旁边一群裤腿儿有泥巴的小孩子跟着瞎起哄,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还有人在山顶煮白茶,我们厚脸皮凑过去,对方豪爽地邀请我们入席品茶,虽然不太會品,但眼前山野茫茫,手里的茶都多了几分清雅。
有一次,儿子不小心擦破了手掌,忍不住抽泣,被路过的爬山团注意到,有人递过来创可贴,有人给他一瓶饮料,还有人给他很大的巧克力,鼓励小朋友勇敢——这可是儿子前所未有的受宠待遇,小时候他在人流密集的地铁吓得哭,只引来乘客的白眼。我想,也许是山里空旷,大家的爱心、耐心、交流欲望都成倍地增加。


善意是流动的,我们也曾把背的水分给口渴的陌生人、加入捡垃圾小分队的临时公益、为一个个迷路的登山客指路——再经过两次爬坡、三个转弯、四个水沟就到了,对了,路边紫色的野果子是奶油瓜子味道的,但有毒,千万别摘哦。
在山中,我们也遇到过大山真正的主人——各种生灵,最常见的是昆虫、鸟、野兔子,还有山民散养的狗或猫,它们习惯了被投喂,有时会为了一块小饼干,毫不提防地跟在游客身边,为他们开路,成为他们的临时旅伴。
爬山成了我的心情调解器,当双脚脱离柏油路、水泥路,踩上山间土路时,节奏都不自觉地变慢了,遇到有兴趣的事物,随时停下来,观赏、感受。爬山的过程,是一个五感打开的过程,也是一个忘记烦恼的过程,可以听鸟鸣、吹山风、闻花草香,还能看大树小草野花,浮躁的心会逐渐变得沉静。
爬山回来,工作量没变,同事没变,甚至甲方都没变,可是我的状态没有那么紧绷了,不耐烦和焦虑也逐渐减少。
爬山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职场“精英”,他们到了山里就是一群膝盖不灵活、走三步喘五步的 “登山老菜鸟”,为了放松、健康、假装手机没信号(我的甲方居然也这么干),聚在一起,彼此鼓劲,向山顶进发,其间难免有“气喘如狗”的时候,这时什么社交面具都顾不上戴,一根递来的登山杖、一个有力的搀扶,才是最原始且有用的关怀。
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较理想模式:向着共同的目的进发,在艰难的时候,互相搭把手。放下心中的目的性,才不会让旅途过于沉重,如同广告里说的那样:轻履者远行。一个人、一群人,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