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十五)
2023-07-11满族关纪新
[满族] 关纪新
径先与永忠结为莫逆的,当推他的两位宗兄,永㥣和书諴。二人在当时,也是饶有名气的宗室诗手,文学功力均不在永忠之下。三人所以契合,也有深刻的原因。
永㥣,字嵩山,较永忠年长六岁,是康修亲王崇安之子。其兄永恩袭了亲王爵位,他终身只作到“镇国将军”,郁郁而不得志,加之生性率真不阿,使他与尸位素餐的衮衮诸公,保持着明显的间距。
书諴,号樗仙,与永㥣同庚。其六世祖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曾是清初叱咤风云的角色。而该支宗室,后来却很少得到皇权的青睐。书諴只是援例袭了“奉国将军”虚名,但性守狷介,不欲婴世,年甫四十,即托疾辞爵,逍遥自保。
乾隆三十五年左右,永忠与他们二人相识,直至终生,维系着密切的过从。
关于他们的关系,永忠写道:“嵩山外朴内含真,樗仙孤介不受尘,余也肩随二公后,有如东坡月下对影成三人。”[1]言外之意,分则三人,合便一体,是极为亲近的。在永㥣、书諴的诗中,歌颂情谊和彼此推重的句子也不少。书諴以至于自夸他们是“峩冠鼎峙惟三人”[2],把世间芸芸之众都有些不放在眼中。
永忠一生处在睽睽众目之下,稍有闪失,便可能惹出祸端,须时刻打点些谦谦唯唯,不肯轻越雷池半步。永㥣、书諴则不必,他们还够不上为当局重点监控的“危险分子”,用不着装出敦厚和平之态。与永忠不同,他们的作品讽喻时事锋芒外向,抒发郁闷性灵毕现。
书諴在他的诗中说:“长安车马如水流,出门泥土增烦忧”;[3]又说:“骄阳炙地气腾火,百计娱心无一可”;[4]还说:“世间万事无如酒,醉眼看花花尽丑。惟有梅花恶独醒?直使《离骚》不能取”。[5]可见其胸中郁闷也是层叠沉积的。
永㥣是能更多袒露胸怀的诗人。他的《早秋过太液见残荷有感》诗,竟敢拿皇家池塘“太液”当中的残荷做比拟,来描述宗室贵胄们难免遭受的枯荣衰兴际遇:
旧日相知在五湖,托根偶尔寄皇都。知君亦有升沉感,未是逢秋便觉枯。
永㥣的家世并没有像永忠那样跌宕,他能获得这份感时喟世的悟性,是难得的。再来看他的一些歌行体诗句,对他的认识会更为深刻:“呜呼大地为高丘,蚁穴纷纷争王侯……贤愚到头无复别,人生扰扰何时休!”[6]“君不见伏波晚岁心犹壮,明珠犀玉遭谗谤?又不见淮阴一日大功成,狡兔未尽狗即烹?”[7]
这比永忠的表达可是清楚多了。他们的愤懑,是冲着薄情寡恩的同宗主宰者去的,是冲着尔虞我诈的列位掌权人去的,也是冲着崎崛险巇的官场政治去的。这种情绪在他们那里,既是切肤铭胸的,也是彼此与共的。
永忠诗中有一些“白鸟[8]潜缘幔,青虫暗扑窗”,[9]“飞蚊更结羽,竟夕振雷音”[10]之类的费解句子,在这里,它们的注脚被发现了。
为了逃避炎势,消极抗拒他们痛恶的封建弊政,永忠采取的生存方式,正是他们协调行动的一部分:
一为各自谢世读书。永㥣之侄昭裢在《神清室稿跋》中,记载了叔父常年“独处一斗室中”读书吟诗的情形。书諴的一首《题臞仙云阴欲雪图》诗,也描摹了永忠的一帧自绘像:
前山后山云垂垂,大木小木长风吹。欲雪不雪尽如晦,湖影吞空静游滁。水阔凭空随人指,此公读书声未已。彼美盈盈间一水,臞仙自画琨林子。[11]
二为相约互邀,对酒当歌,唱予和汝。此种篇什在他们的集子里占有可观的比重。永忠曾有一首《过嵩山见神清室壁悬长剑戏作》:“笑君长铗光陆离,日饮亡何空尔为。怀铅提椠老蠹鱼,行年四十犹守雌。我少学剑壮无为,英雄气短风月辞。不如乞我换美酒,醉歌《金缕》搏纤儿。”永㥣深领其自嘲自道之意,和之一首《重为长剑篇戏示臞仙兼以自嘲》:“壁上宝剑蛟龙子,拔渊真有风云起。嵩山留此亦何愚,四十无闻心不死。男儿当作万夫豪,学书学剑真徒劳!拍浮自足了一世,剑换美酒书换螯。”
在他们眼里,世上万物不足道,只有相互的理解与情谊,才是最真挚和最富吸引力的:“风雨初涤天日朗,潇洒襟怀气逾爽。剩有黄花三两枝,人约东篱欣共赏。下车不解叙寒温,触目琳琅歌慨慷。”[12]“九月十日风物清,登高已罢心未平。陶公篱菊正烂漫,折简招我偕酒兵。”[13]他们不聚则已,每聚必醉。酒酣耳热,便慷慨狂歌是以为哭,以阮籍、刘伶自况,以太白、长吉互喻。这样的诗酒唱和,远远突破了旧时文人间的空虚酬酢,呈现出一抹抹政治色调。
三为浪迹山水,吟风赋月,陶冶情志。他们对归隐山林,种过西畴田亩的陶渊明,羡慕得很。然八旗制度限制着自由,对名山大川向往了一辈子,终归没有福分成游。于是,他们把足迹洒遍了京郊的每片山水。书諴诗云:“住山固无缘,游山遂无度。屈指惜秋残,趋之若公务。”[14]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才感到一洗平素的躁虑,赏心悦目。
永忠还同他的挚友,在自己选定的理想之岸——政治漩涡冲刷不到的地方,构筑起广泛的生活情趣。琴棋书画,无所不操,无所不通。永忠儿时即善抚琴,能弹奏《平砂》《静观》等曲目[15]。刚成年的书法,便得晋人骨力,“友人见其片纸只字,辄夺去藏蓄”。[16]他和书諴,都是长于画梅的绘画高手,风格各呈千秋:“臞仙写梅梅似火,道人游戏朱门可;樗仙写梅梅似冰,心已成灰身未果。”[17]习射、酿酒、种蔬、养花、植竹、蓄砚,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快事。
乾隆时节,汉族古代文化习尚更深地濡染着满洲上层。而永忠这类闲散文人,与强权格格不入,在诸多技艺上反倒苦心孤诣地追索,又怎能不一展才华?从清初到康、雍、乾时期,满洲人多以昂扬姿态介入社会,其中的得势者会将才干发挥在政治与军事上;而失势者们不甘潦落,也顽强地选择施展自我的方向。永忠等人在各门技艺上的成就,包孕着的,是燃烧生命的蓬勃生机。
永忠、永㥣和书諴共同营造的朋友圈子,不是封闭的。乾隆朝宗室贵族文人日多,社会生活大浪淘金,断断续续地,又往他们周围,推过来一些思想情感相仿佛而艺术上又志同道合者。这样,一个以人生近似体验为纽带、彼此之间或紧密或松散的满族文人集团,便逐步形成。在这个文人集团(或称为作家群体)中间,比较引人注目的身影有:敦诚(字敬亭)、敦敏(字懋斋)、额尔赫宜(字墨香)、曹霑(字雪芹)、和邦额(字䦵斋)、成桂(字雪田)、兆勋(字牧亭)、永恩(字惠周)、永璥(字文玉)、弘晓(号冰玉道人)、弘旿(号瑶华道人)、明义(号我斋)、庆兰(字似村)……他们不但个个锦心绣口才华横溢,不少人还有过沧桑沉浮的家世经历。
敦诚、额尔赫宜和成桂,在这些人中,与永忠更亲近些。敦敏、敦诚兄弟俩,是努尔哈赤子阿济格的五世孙,额尔赫宜是他们的幼叔。阿济格于顺治朝遭难之后,他们这支沦为了宗室平民,到了“不辞种菜身兼仆,无力延师自课孙”[18]的程度,与执政者结下了宿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敦诚刚一结识永忠,便把这位“貌臞心自冷”的宗弟引为同调;而永忠,“耳熟敬亭有年”,一朝邂逅,相见恨迟,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额尔赫宜,是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武士,偏爱浏览情诗情文,遇上了“情种”永忠亦属求之不得,二人时常交换各自欣赏的文学作品。永忠把自己的“情诗”交给他,再三叮咛:“再无副本,人亦未见,幸速见还,若致遗失,性命所关也!”[19]而额尔赫宜转交永忠阅读的作品当中,更包括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成桂,也许是这个文人集团中处境尤告可怜的一位。他姓爱新觉罗却非宗室,属于觉罗身份。[20]他文墨在胸却一贫如洗,靠永忠收留赡养,其关系可见一斑。
人们自然是未曾领略过无来由的爱恨。在乾隆朝这批相互连络着的文友们笔下,我们随处可以读到与永忠、永㥣、书諴作品相接近的选题与意象。
客来无貌更无文,真率相投气自熏。不善逢迎应恕我,但须谈笑总由君。公荣饮酒胸诚阔,阮籍看人眼太分。蕉鹿梦园同戏局,未来过去总浮云。
——敦敏:《客来》
槎枒病骨卧苔茵,力薄摩宵空望云。无分乘轩过凤阙,自甘俯首向鸡群。病魂虽怯秋来警,清唳犹能天上闻。丁令不归华表在,成仙往事讵堪云!
——敦诚:《病鹤》
江静晚鸥多,斜阳挂女萝。淡烟迷古渡,骤雨乱春波。远岸飞黄蝶,当窗绾翠螺。韶华看冉冉,小泊感蹉跎。
——和邦额:《泊江村》
九天何处恣超忽,此日凄凉亦自叹。大野风来飞侧力,高林雨后立孤寒。将同老骥怜筋骨,肯向苍雕借羽翰?稍待深秋双翮健,排云万里逐鹏抟。
——成桂:《病鹰》
不咏《大刀头》,忧怀怅未休。一村黄叶雨,千里白云秋。空馆留渔伴,寒溪饮牯牛。浩歌谁共赏?斗酒妇能谋。
——兆勋:《暮秋即事》
骤雨初晴五夜中,纤云不见点清空。喜无烦热兼尘气,恰有微凉荐好风。杳杳钟声催晓日,亭亭月色送孤鸿。此时此景真堪画,借问丹青若个工?
——永璥:《五月十四日五更出阜成门》
君马黄,我马白,马色虽参差,同君共大陌。论心投分应交人,如何交富不交贫?世情轻薄都若此,贫富移心复可耻。君不见洛阳市上数家楼,五陵裘马少年游。千金一掷不回顾,豪情百尺谁堪俦?一朝冷落繁华已,贫富原来无定耳!
——弘晓:《君马黄》
水亭苍莽隔烟霞,淡淡孤村处士家。溪上松风亭畔竹,一行新雁远山斜。
——弘旿:《自题山水画册》
劳劳尘世叹华胥,拟托幽斋静起居。千里折腰五斗米,三年作宦一囊书。已当奴散家贫后,莫再情伤齿落初。更有蹉跎如我辈,半生眉宇未曾舒。
——庆兰:《呈三兄》
堰仰驰驱别有因,归真返朴是全身。不贪五斗折腰米,免却九州扑面尘。赵女秦筝堪乐岁,青鞋布袜好寻春。平明钟鼓严寒际,不负香枕更几人?
——明义:《和庆六似村韵》
透过前面对永忠、永㥣、书諴等的介绍,以及此处集中摘引十位诗人的诗作,可以看出,先前康熙时期满族书面文学在诗歌创作上的既有风尚与倾向,到了乾隆朝,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异。康熙前期满人奋起于政治追求的姿态与尚武崇功的用世精神,此时在满族作家们的作品里不再那么彰显,或者变换成了别样的表达形式;当初纳兰性德单兵突进身陷汉族文化腹地所诱发的个体文化心理失衡,以及岳端因过于突出地追摹和交往汉族文人而遭到惩处的情形,都因此时满人上层研习汉文化不但蔚成风气并且走进了这种文化的内里,不大容易被找见了。而朝堂斗争日趋激烈错综,产生了颇多的政治角逐牺牲品——即疏离于核心权力的倒运贵族,他们一方面对现实持怀疑和贬斥态度,另一方面又深感人生无他路可循,便将先前由岳端、文昭等人踩踏出来的退居自处、冷眼时政、玩味艺术的蹊径,趟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道。满族文学,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一番看似避开政治笼罩实则与政治脱不开干系的流向偏移,而本民族旧时追求自然天成的传统审美定势,在这种逃逸政治压力的气氛下,也得以长足的推进。
乾隆朝满族书面文学新出现的基本特点是——
一、文学活动的规模性与群体性。即京师满洲上层文人作家群的形成,以及作家群成员们彼此倚撑与呼应的文学活动。
二、人文心态的避时性与抗时性。本阶段满族最有成就的作家,均已不具有身兼政治、军事要员之身份,他们或为政治漩涡所甩弃,或有感于衷,表达出厌倦于官场名利纷争的悟性,文学创作也往往能抒写出避世抗时的主观态度。[21]
三、艺术诉求的多样性与深刻性。经过了清前期百年左右民族上层文化的演变过程,满族作家们到乾隆时期,羽翼空前丰满,他们的艺胆越来越大,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所有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方向;他们苦心孤诣地写作,处心积虑地想要回赠给世上更多、更为厚重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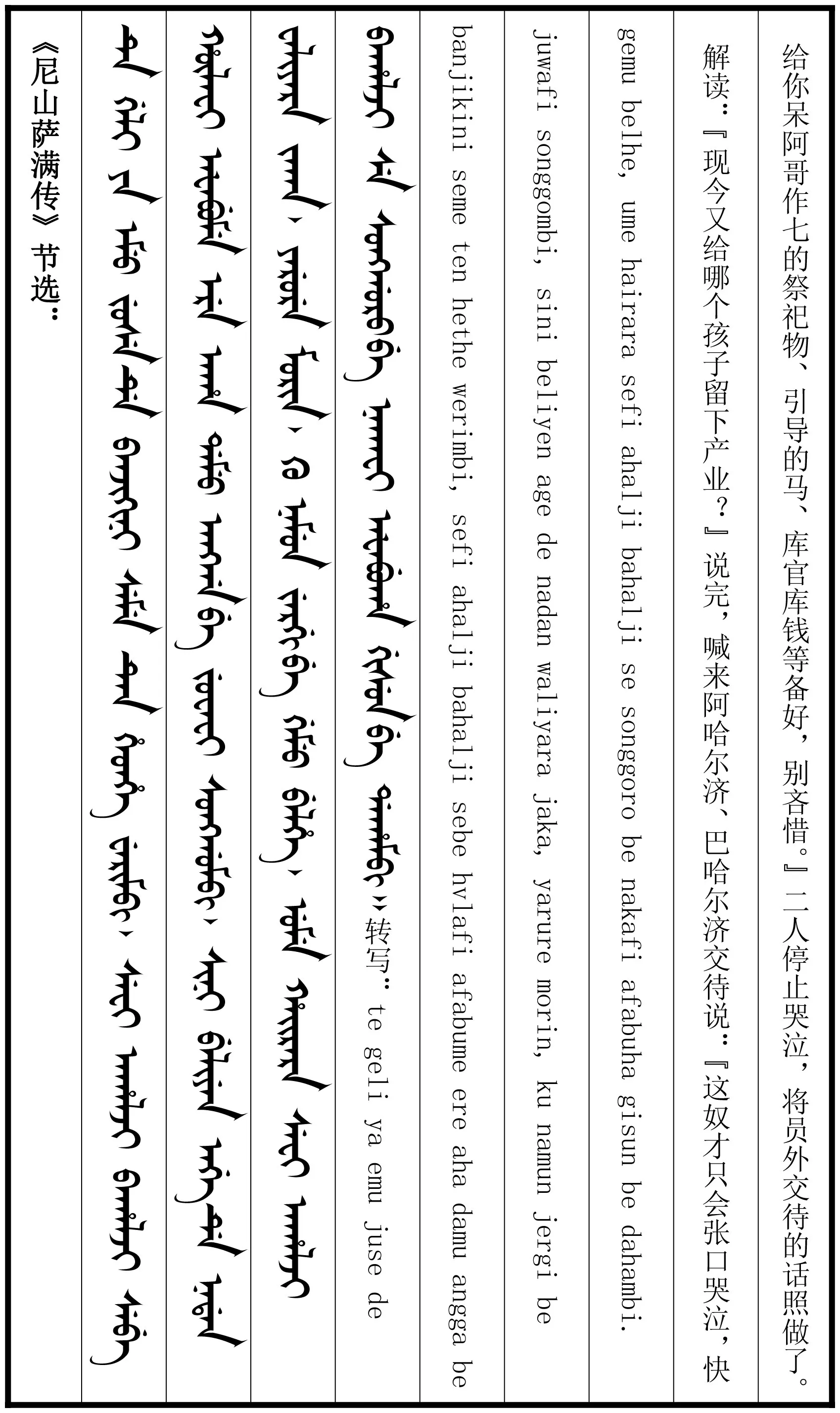
注:
[1]见永忠《醉歌行次樗仙谢嵩山招饮》。
[2]见书諴《醉歌行谢嵩山饮兼呈臞仙》。
[3]见书諴《次韵水云道人画竹兼呈栟櫚道人》。
[4]见书諴《嵩山以二扇索写梅各题一首》。
[5]同上。
[6]见永㥣《狂歌行》。
[7]见永㥣《醉歌行》。
[8]诗人原注:“蚊,一名白鸟”。
[9]见永忠《夜坐杂感》。
[10]见永忠《夜坐杂兴》。
[11]琨林子,为永忠别号。
[12]见永㥣《重阳后一日樗仙手酿潇湘春招臞仙与余同饮》。
[13]见永忠《重阳后一日樗仙招集静虚堂同嵩山赋》。
[14]见书諴《九月十四日再游罕山道院题壁》。
[15]见永忠《延芬室集残稿》壬申初稿本。
[16]见永忠《延芬室集残稿》戊寅稿本。
[17]见永㥣《和樗仙画扇原韵》。
[18]见敦敏《春日杂兴》。
[19]见永忠《延芬室集残稿》戊子稿。
[20]清代,努尔哈赤祖父塔克世直系子孙可称宗室,旁系后代只能称为觉罗。
[21]这里似可再提供一个同样是乾隆初年却出在京师满族作家群之外的例子。满洲诗人长海,那拉氏,先世为乌拉部长,前辈有功于清廷。其家人为他谋得了一个官职,他“坚卧不肯起”,表示自己是“逃死,非逃富也”,终以平民身份度过一生。其《白翎雀》诗为:“白翎雀,巢寒沙,上都城外河之涯。雌雄携子乐复乐,大漠秋风生雪花。元时避暑上都中,峨峨金紫凌高空。可怜一旦沉烟草,牧马群嘶归驰道。白翎雀,何所栖?汝巢不徒踏为泥,汝子携向笼中啼!”另《苦雨》曰:“白眚夜见缠太阴,阳景壁藏天四沉。天将伸芒河鼓暗,倾注无处无秋霪。横流倒泻深泥滓,当轩半落秋江水。东家西家似鱼舟,我屋直如鸥鹭浮。日愁蒸薪爨难给,夜移床榻避淋湿。儿女房中且莫啼——天乎!天乎!毋使秋原绝民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