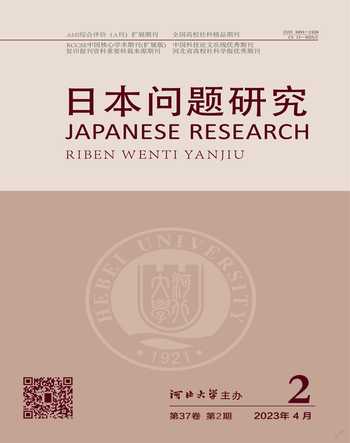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的选举政治实践
2023-07-07张艳茹
摘 要: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及民间对选举政治展开了较活跃的理论探讨。随着理论探讨的逐步深入,在政治思想领域,“选举”一词的内涵逐渐从明治初年的官员选拔、举荐转变为专指议会的议员选举。与理论探讨相伴行,在频繁的制度调整中,日本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也试行了一些选举举措及选举制度调查。中央政府的议政官上下局、公议所、集议院、左院、元老院等,均具议政机构性质,且它们間有一定承袭关系。从其成员遴选及所进行的制度调查来看,具有扩大参政人群、选拔议政人才的目的,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的保守的选举政治实践。同期伴随地方制度改革,特别是受自由民权运动推动,政府在地方层面进行了比较开放的选举政治实践。各类地方民会的议员选举实践,为后来开设国会时的选举制度设计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议政人才。在这些早期选举政治探讨及实践中,既能看到西方政治观念与传统政治文化的杂糅与碰撞,又能看到官方和民间各种不同政治思潮、政治诉求、政治探索的交织与纠葛,显现了明治初期的复杂政治实相。
关键词:日本;选举政治;议政机构;地方民会;府县会
中图分类号:K313.4;D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2-0070-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7
受中文影响,古代日语中也使用“选举”一词,与中文意思接近,主要在描述政治领域选拔人才的相关活动时使用。只是到近代后,伴随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及对政治模式探讨的逐步深入,“选举”的词义及其所指的政治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刘斌在《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古代“选举”一词的运用及内涵,指出随着西方选举概念的输入,“选举”逐渐脱离中文传统涵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相对应的概念,并特别指出日本“选举”一词的输入对中国产生的影响[1]62。实际上,在政治思想领域,先于中国,日本“选举”一词经历了类似转变,其内涵逐渐从明治初年的官员选拔、举荐转变为专指议会的议员选举。日本学者泽大洋在《明治最初期选举制度论的发展》一文中结合明治初期发行的几版英日词典等材料,指出在英译日中,到1872年前后,基本将“election”固定译作了“选举”[2]29-30。
日本学界关于近代早期选举政治的既有研究不多,在研究自由民权运动、《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及西方政治思想输入时多会提到选举制,但单独讨论选举政治的著述较少。尾佐竹猛、藤井甚太郎、河村又介等早期研究宪政及选举制度的学者,对公议、选举等有一定论述,特别是尾佐竹猛把日本走向宪政的历史延伸至幕末时期,关注到当时各势力对参与政治决策的迫切要求[3]。二战后,内藤正中、渡边隆喜等通过分析地方个案探讨了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地方民会、府县会的活动(参见:内藤正中.自由民権運動と府県会(I)—とくに明治十五年以降について[J].経済論叢,1961,87(1):74-96;内藤正中.自由民権運動と府県会(II)—とくに明治十五年以降について[J].経済論叢,1961,87(5):362-382;渡辺隆喜.民権結社の成立と地方民会論[J].大学史紀要,2005(9):8-54。)。近几年,前述泽大洋的《明治最初期选举制度论的发展》一文,主要介绍了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对西方宪政思想中的议会制、选举制的引介等[2]29-50。中国相关研究很少,已有成果主要侧重研究明治宪法体制下的选举制度及其运行(相关研究可参见:许晓光.19世纪后期日本关于议会职能的论争[J].日本学刊,2015(1):139-158;张东.近代日本“一君万民”构造下选举权观念的流变及其特质[J].世界历史,2020(4):15-30。)。通观日本幕末至明治初期的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关于选举政治,日本政界及民间均有活跃的理论探讨及丰富的相关实践,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选举实践的关注尤其不足。明治初期制度改革频繁,政府内外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及权力斗争,所展现的复杂政治表象难以尽述,因此,本文仅尝试运用明治初期相关政府文件及自由民权运动史料,对该时期选举政治实践做一线索性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中央政府议政机构设置及相关人员选拔机制的摸索
幕末至明治初期,“合议”“公议”“公论”成为被各政治势力普遍讨论的话题。日本学者佐佐木克指出建立合议体制是幕末日本国家面临的三大课题之一[4]1-17。尽管不同政治势力的政治诉求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这些讨论的核心要素是扩大政治参与群体。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看,诸多政治势力是以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决策为目标开展活动的。如何能让更多人的意志反映到政府施策中,如何选拔合适人才参与政治,这些问题均和选举政治相关。在此背景下,一些政治势力已开始思考扩大参政群体的方式。
幕末时期,在土佐藩已有初步的扩大参政群体范围的制度探索。英国外交官萨道义的《明治维新亲历记》中记述,1866年9月(公历)他在土佐藩与后藤象二郎、前藩主山内容堂会面时,对方就询问了宪法、国会、选举制度等事宜[5]253-256。1867年土佐和萨摩结成的“萨土盟约”也包括如下内容:朝廷拥有大政全权,皇国的一切制度、法令应由议事堂发布。
议事堂费用由诸藩提供。
分上院和下院,从上至公卿、诸侯、陪臣,下至庶民中选举正义纯粹之士为议员,诸侯因其执掌,组成上院。
将军职不再是最高官,德川庆喜辞职回归诸侯之列,政权归于朝廷。[3]66这一设想虽然未突破藩制,文中所说的“选举”也不同于西方议会制的选举,但其反映的选拔人才、组织议事机构的政治意愿,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该藩的坂本龙马,1867年11月(日本在旧历明治五年12月施行改历,改用公历。旧历明治五年12月3日为公历1873年1月1日。本文为叙述方便起见,除有特殊说明外,所标示的1873年1月1日前的时间均为旧历。)在从长崎赴京都的船上,同后藤象二郎讨论了后来被称为“新政府纲领八策”的政治构想,其中也包含设立“上下议政所”的内容[6]。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土佐藩的公议政体目标虽未实现,但其不少制度构想通过该藩出身的福冈孝弟、后藤象二郎等的政治活动,反映在了明治初期的制度设计中,如《五条誓文》就是在福冈孝弟、由利公正等草拟的政治意见书基础上修改而成。该誓文内容与“新政府纲领八策”及山内容堂劝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意见书,有共通的希望扩大参政人群、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公议政治的思想。
庆应三年(1867年)12月9日王政复古政变之后,维新政府根据王政复古“大号令”,设立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制。12月15日,新任参与职的福冈孝弟、后藤象二郎就提出了设立上下议事所的建议。建议上议事所为皇帝、宫、公卿、诸侯会议之所,下议事所为诸藩征士、贡士及都鄙有才者会议之所[7]。明治元年(1868年)2月5日维新政府制定了征士、贡士选举之法,命各藩藩主选派藩士到下议事所任贡士,为议事官,执掌公议舆论。关于各藩推举人数,规定40万石以上大藩推举3人,10万石~39万石中藩推举2人,1万石~9万石小藩推举1人。贡士为定员,无任期年限,由藩主决定其进退,并且可因其才能进而被选举为征士[8]。1868年2月,天皇行幸东京期间,维新政府又在东京设立了议事所,主要是“公卿诸侯在官二等以上”集会议事,相当于前述的上议事所[9]。
庆应三年闰4月21日,维新政府发布《政体书》,初步建立太政官制。在太政官机构设置中,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三权分立思想。根据《政体书》,太政官内分为七官两局,其中议政官负责立法,由上局、下局组成,上局官员包括议定、参与、史官、笔生,下局除议长外,就是由前述贡士组成。同年5月24日,在京都府菊亭家宅邸内设置了贡士对策所,为构成下局的贡士们的办公地。贡士们每月5日、15日、25日出勤议事,接受政府的政事咨问,协商后的对策形成公文上奏。因此时尚未实施废藩置县,这些下局贡士由各藩藩主选任、推荐并决定其进退,无任期限制。从形式和内容看,征士、贡士选举名称虽和中国古代的“贡士、征士”相同,但选拔形式和选举目的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选拔、荐举官员制度,也不同于西方的议会选举制度。维新政府初期,议政机构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选拔人才及进行制度建设的紧迫课题。
因政府内频繁的制度调整,议事所、议政官上下局存在时间都很短,且很多政府内大事并未交付其审议。从其职制来看,上局的议定由行政官中的辅相兼任,行政官的弁事兼任下局议长,完全没有体现出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离,实际政治运行中还是行政占绝对主导地位,议政多流于形式。
鉴于议事所等不能起到其应有效能,1868年11月维新政府又在东京设立了“议事体裁调研所”,进行议政体制调研,同时管辖各藩“公议人”[10]。在调研基础上,明治政府决定在议政体裁调研所下设公议所,同年12月6日,向各藩发出设置公议所的谕示[8]。公议所具有一定的立法权,议员仍是由各藩推荐的代表组成。12月10日,政府又向各藩发出推荐公议人的布告,推荐人数原则上是大藩3人,中藩2人,小藩1人,每藩可先推荐1人。“公议所”也是在制度摸索中设立的。与前述征士、贡士不同的是,公议人任期为4年,每2年改选其半数,议员年龄须在25岁以上[11]。1869年1月,在议事体裁调研所中,由神田孝平制作了政府最初的具有近代议会性质的法案“公议所法则案”[8]。公议所于1869年2月开始运行,每月逢2日、7日集会,就政府提出的咨询进行商议,并书面上呈意见,且有一定提出议案的权限。
公议所在设置之初被看作是立法、议政机构,但实际上在运行过程中,亦未实现议政、行政分离。构成上局的议定、参与等多由行政官兼任,下局的公议人也仅限于从各藩的执政、参政级别的官员中选出,且后来改为了每藩限定1人。公议所从1869年2月开所到同年6月被改组为集议院,仅存在了三个多月时间,期间共开会22次。公议所改组为集议院后,权能进一步缩减,由原来参与议政变为了太政官的咨询机构,且集议院议员遴选范围进一步缩小,基本是从作为各地方要员的大参事(明治初期施行府藩县三治制时,大参事是地方的职位仅次于府、藩、县知事的官职。)中选出,每府、藩、县各1人,任期4年,每2年改选其半数,在议事中主要代表地方意向。集议院在1871年随着太政官左院的设立而被并入左院。
除设立了上述公议所、集议院外,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是1869年朝廷内举行了一次要职选举。当时政府调查了美国等的选举制度,在此基础上有不少人提议朝官公选。1869年5月,依据大久保利通的提案,首次在政府内试行了辅相、议定、知事、参与等的选举。这也是明治政府唯一一次要职选举。“此际悉解朝官之职,依公选法选举其人,圣上亲临政厅,颁赐三等官以上公选之诏,诏书称:‘朕思治乱之本在于任用得其人,故今敬告列祖之灵,设公选之法,进而登庸辅相、议定、参与,神灵降鉴,勿以为过,汝众须体斯意。后以投票之多数就任官职,辅相为三条实美,议定为岩仓具视、德大寺实则、锅岛直正,参与为东久世通禧、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共选出了29名。但投票选举之举在实行之初,就有提出反对者,认为不合国体,恐为祸端。亦有过虑论者……”[12]35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收藏的太政官类典草稿中,有关于这次选举的部分记载,可与上文的描述相参照。文书中记载辅相、议定、六官知事、内廷职知事四职自公卿诸侯中选举产生,“采取凡三等官以上总集合投票之方式”。文书还详细记录了辅相、议定、参与等选举时投票、开票、计票的程序与过程[13]。在太政官类典草稿中未找到关于投票统计结果的具体记载,明治政府中央官僚的选举也仅此一次。从选举前颁发的诏敕来看,是向祖宗神明报告的形式,很难与近代议会政治联系起来,但从选举形式及程序看,有一定严密性。这也是当时尚无多少执政经验的明治政府的一种尝试吧。
二、伴随机构变迁中央政府选举政治实践渐趋保守化
1871年7月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改革了太政官,在太政官内设左院和右院。左院吸收了集议院,主要负责政府内的立法调查、咨询,其议员为官选。1872年,左院受正院之命开始进行宪法调查。同年4月25日,左院提交名为“设立下议院之议”的建议,文中称“西洋强盛之诸国在施政官之外必设上下议院,皇国亦效仿而成立了议事院,今日已改为左院,所谓类似于法国国议院,但未得其精髓,因未能广采下方之众议。故应速设下议院,集全国之代议士代人民议事,施上下同治之政,确立全国之基础”[14]77。左院还做了相当多的关于选举的调查。“以中议官松冈时敏为核心编纂、以欧洲宪法为藍本起草的《国会议院程序调查》及《别册》提交给了左院。在《别册》中列举了选举人的年龄、财产、教育等资格要件,并详细列举了选举区制、记名投票、任期等要素,建议采取有限选举。”但该方案未被上奏。1873年,松冈时敏在马屋原彰等帮助下,又起草了《国会议员规则》,其第一篇第一款即是“国会议院议员选举之事”,规定享有选举权须年满21周岁,被选举权须年满25周岁,是具有一定财产资格限制的有限选举,并列举了选举人投票、开票、议员退任等规则。这一草案最终也因1873年10月“明治六年政变”引发政府内人事动荡而成为废案[2]35。
“明治六年政变”后,板垣退助等下野的参议随即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木户孝允也因反对征台下野。这些政治变动引发政局动荡。1875年2月,为了再次整合政界力量、缓解政府危机,在伊藤博文、井上馨的斡旋下,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在大阪就日本未来发展走向及政府施策等进行了会谈,史称“大阪会议”。会谈后,大久保利通将三人达成的一致意见提交给了时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3月,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复任参议。根据三人的意见,4月14日明治天皇颁发了“渐次立宪政体树立之诏”,并决定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召开地方官会议,目标是分阶段建立立宪政体。同年,伴随元老院的设立,左院被废止。元老院设立时的定位是立法咨询机构,成立后开始进行宪法调查。地方官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地方民会的大量开设。
对近代日本的宪政发展来说,“大阪会议”是一个重要节点。首先,政府内部开始进行宪法讨论、宪法调查;其次,“渐次立宪政体树立之诏”发布后,自由民权运动越发高涨,民间围绕宪法的讨论剧增;再次,与上述两种情况相伴,地方民会作为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其实践意义越来越重大。但另一方面,政府内不同政治势力围绕宪法性质的意见之争也日趋显现。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前,政府内负责调查和草拟宪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所做的宪法调查也深受这种意识之争的影响,其制定的与宪法相关的草案大多未被采纳。实际上元老院制定的各版宪法草案中,涉及选举制度的内容并不多,且颇为保守,主张对选举人及被选举人资格做财产等方面的严格限定。
在元老院1877年草拟及修订的宪法草案中,几乎都仅提及了元老院的权限和成员选拔制度等,未涉及任何民选内容。如1877年草案中议会的“立法权”部分,规定“帝国议会由元老院及其他议会组成”,但仅列举了元老院议员构成成员资格。
第一条 元老院议官为定员,由皇帝从下列人选中选出担任。
皇族、华族、曾担任敕任官者、为国建功者、有政治法律之学识者。
第二条 亲王有任元老院议官之权,位议官上席,满18岁进入院中,满20岁有公议之权。
第五条 元老院议长及副议长由皇帝从议官中选任。[15]181-182
到1878年5月《日本国国宪按》修订版本,“第四编”增加了与“元老院及其权利”并列的“代议士院及其权利”和“两院通则”两部分,并增加了“第七编 州会及邑会”,内容涉及国会及地方议会的选举制度。
在“代议士及其权利”部分,具体规定如下(引文原文未标注第几条,只显示“第 条”的,本文都用“第*条”表示。):
第*条 代议士院由依遵循法律规定之选举程序选出的代议士组成,每15万人至少可选1名。
第*条 代议士通过投票选举,且可重复当选。
第*条 符合代议士资格者须是日本人,满25岁,缴纳选举法中规定的税额且具备成为代议士之要件者。
第一条 代议士之任期为4年,每两年更选其半数。
第*条 代议士院在会期间从议员中公选议长及副议长各5名,将姓名列表呈奏皇帝,由皇帝决定具体人选。
第*条 代议士按法律规定接受旅费及旅居费用。[15]193
在“第七编 州会及邑会”中,只有简短的两条内容:
第一条 每府县设府县会,每区设区会,其议员选举之法由法律规定。
第二条 府县会及邑会之权利义务由法律规定。[15]195
元老院宪法草案的不断完善和修改,反映了其对于具体制度的调查在不断深化、细化。不过,从草案内容来看,对于议会和选举还是持比较戒备的态度,所列各条规定都比较模糊。即使如此,1880年12月元老院呈递“国宪按”后,仍因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的反对而未被采用。
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后,在宪法意见书中主张立即召开国会、实行英国式政党政治、由国会审议宪法的大隈重信一派被驱逐出政府。政府确定了渐进、钦定、仿照普鲁士模式的立宪基调。伊藤博文开始负责宪法调查及制定工作,政府中设置了参事院,井上毅、伊东巳代治等辅助伊藤博文进行宪法调查及草拟工作。从宪法调查的内容看,虽然立宪政治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但选举制度调查并非重点。井上毅曾向德国法学家罗斯勒咨问选举权的财产限制问题,但与皇室制度、内阁权限等问题相比,关于选举的问答内容不多。对于选举,最终采取了另外制定《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措施。
公议所、集议院、左院、元老院都有作为议事机构的性质,它们之间有一定承袭关系[16]3,公议所、集议院、左院存续时间不长,且整体来看,政府在其权限及成员选拔上的基本走向是渐趋收紧,但对于选举政治来说,其构成成员的选拔、所进行的制度调研等,仍具有一定试行意义。特别是公议所、集议院、左院,设立这些机构的基本设想是通过它们扩大参政人群、推举贤能等,反映了明治初期设立议政、立法机构的探索,其成员选拔可以看作是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的选举实践。
三、明治初期地方民会的选举实践探索
在幕末至明治前期政府及民间对公议、宪政、国会等问题的讨论之下,为稳固统治,政府一方面在太政官体制下进行前述制度调整,另一方面,伴随历次地方制度改革,在地方实施了较开放的选举政治实践。
1868年闰4月,日本依据《政体书》,将旧幕领改为府县。同年10月27日,制定了藩治職制,规定各藩无论大小,均设执政、参政、公议人三职,执政及参政主要负责藩内行政事务,公议人和前述中央所设公议所的公议人职能接近。在此制度下,各藩大多设置了类似“藩议会”的机构,其名称各异,如议事所、议事局、公议局、集议所、会议堂、议政堂等。这些藩议会大多设上、下两局,上局由原藩上层组成,下局议员多从平民中公选产生。和公议所在中央政府的地位类似,这些藩议会也近似行政咨询机构,后伴随废藩置县而废止。
1869年6月“版籍奉还”后,政府于7月8日公布《职员令》,规定了地方官职制和权限,形成所谓府、藩、县三治之制。各级地方因名称不同,地方长官分别称为府知事、诸侯、县知事。1871年制定户籍法后,在全国设区(行政区划),实行大区制、小区制。各区设户长、副户长,主要负责户籍管理。同年7月14日废藩置县后,免知藩事,全国行政区划演变为府、县二治,在全国设3府302县,并制定了府县官制,府县分别设府知事、县知事(后改为县令),同年11月又合并为3府72县。伴随废藩置县,新任地方官取代了旧藩主,不少新任地方官对开设民会抱有热情,一些府县陆续开设“地方民会”(因时期、地域的不同,对地方召开的类似地方议会的机构称呼不一。学界为研究方便,通常将明治初期的早期民会、府县会、大小区会、町村会等总称为“地方民会”。),如兵库县令神田孝平就积极在兵库县设立了民会。1872年8月,兵库县在所辖的19个区中,首先让民众选举了区长、户长,选举不论门第,公选有威望、有才能的人。1873年9月又发布“兵库县民会议事方法撮要”,该规则分6章:第1章为总则,第2-4章为町村会规则,第5章为区会规则,第6章为县会规则[17]255-284。同年11月,神田孝平将第2-4章做了修改,并略去了第5章、第6章,以“民会议事章程略”为名在《日新真事志》上发表,成为了当时各地民会章程的一个范本。
当时各府县对如何召开民会、采取何种规则等还处在摸索阶段,内务省也在进行相关调研。北条县在1872年1月就曾向内务省请示如何开设民会,并上报了他们草拟的议事规则、民会条例、选举规则等,请示审批。北条县制定的《民会议事略则》共分十章,另外制定了《议员选举略法》,两者内容均十分详细。时任参议的大久保利通在审阅北条县等地方呈报的材料后,很是担忧,认为在全国性相关法令未制定之际,各县有滥制条例之虞,因此有必要制定全国性的规则。他希望左院尽快研究编订民会议院规则,颁布各县,令其参照执行[18]。对于北条县的请示,内务省也下达了暂缓实行的指示。
尽管政府对设立民会有种种顾虑,但开设民会的府县还是越来越多。1874年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后,伴随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地方民会的活动更为活跃。政府中也有一部分人对民会寄予厚望,如木户孝允。在1875年2月木户孝允关于“大阪会议”的日记中,就提到他力主开设民会,并得到了大久保利通等人的认可。“(明治八年2月)9日,晴,九时以后伊藤和大久保至,余陈述了平生一直主张的渐起民会以开国会之基等主张,大久保亦表示同意,余前日已同板垣讨论过此主张,皆同意余说,今日大久保能同意此说,实是为国家及人民开拓前途之一大幸事,余窃欣悦。”[14]80在其2月10日的日记中也记载去井上馨宅邸会见板垣退助、古泽滋、冈本健三郎等人时,又陈述了前述主张,井上馨等也表示赞成。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木户孝允认为兴民会是开国会之基础。他在诸多意见书中都提出地方分权主张,特别是1876年5月曾向政府提出“关于速行町村会及开设国会意见书”。木户孝允虽然认为开设民选议院不可操之过急,但町村会的开设事关民众切身利益,比较迫切,并且认为“他年整备后,渐进以至于府会县会,遂至于国会”[19]96。
这一时期大力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板垣退助等也和木户孝允持相近观点,认为地方民会积累的经验可为开设全国性国会所用。西南战争期间,板垣退助在高知县开展了活跃的提倡自由民权的活动。在土佐州会的开幕式上,板垣退助说:“土佐一州之议会起,为开一国议会之端绪者。”[20]58当时的植木枝盛在高知县也创办了《海南杂志》和《土阳杂志》,并在杂志上否定武力叛乱说,主张建立地方民会,他认为地方民会即地方议会,并认为町村民会的设立,可以促进代议政治的发展,为实现代议政体做准备[20]48。植木枝盛自己出席小区会,进而成为大区会的议员,和板垣退助一起致力于设立县会及土佐州会(州会于次年8月设立)。板垣退助和植木枝盛意在以地方民会促中央议会的发端。他们和木户孝允一样,期待地方民会能为开设国会做制度及人才准备。
前已述及,“大阪会议”后政府决定召开地方官会议。1875年6月第一次地方官会议得以召开,此次会议后,各地府县会甚至町村会的开设都达到了一个高潮。第一次地方官会议时,任会议议长的木户孝允在讲话中称:“今全国府县召开民会者有7县,召开区户长会的有1府22县,无议会的有2府17县,其余情况不明。”而“到明治九年6月,当时所有府县的约80%都开设了民会。全国制定的府县会、大小区会、町村会的会议规则的数量,明治八年时约是明治七年时的1.5倍,明治九年时约是明治七年的2倍”[20]59。
各方对地方民会寄予各种期望,而民会的实际参与者也是想法各异。特别是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不少地方民会成为自由民权势力争取民权之地,与地方政厅形成一定对抗。也因为如此,民众希望扩大选举权范围的愿望就比较迫切。以当时的浜松县为例,该县在1876年设立民会。“该县民会以解决地租改正问题为目的开设,抵抗行政权的色彩很强。即使戶主是女性,其选举权也被认可。议员的选出方法是间接选举,首先居民选出小区的民会议员,再由小区的正副议长就任大区的民会议员,进而从大区民会议员中选出县民会议员。浜松县民会的意义在于由公选选举代表,没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议员,当时有‘远州民会值千金之名声,在全国得到很高评价,也很受其它县瞩目。”[21]28-29同年,浜松县合并入静冈县,静冈县民会选举方式就和浜松县有较大不同。静冈县民会议员中包括特选议员和公选议员,特选议员是由县令从县、町的职员中选出12名,任命为议员,另任命1名新闻记者代表,公选议员52人由各大区选举产生(当时静冈县分12大区,每区各分配几个名额)。拥有选举权资格的是18岁以上70岁以下的、持有不动产的男性,先从每10户中选出1名选举人,这些选举人再选举小区会议员,小区会议员选举大区会议员,大区会议员再选举县会议员,整个程序颇为复杂。尽管静冈县有特选议员,但因公选议员中的近半数是出身原浜松县,他们有浜松县民会的经验,因此在1876年召开的静冈县民会上,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废止特选议员”,还形成了“为确立县民会的权限,县税及其它赋税均应经县民会审议”的决议[21]28-29。县会将这些决议提交给县令,给县政厅带来不小的压力。其它地方民会多有类似情形。地方民会就在这种与政厅的摩擦、碰撞中向前发展。
四、府县会规则的制定与地方议会的发展
废藩置县(1871年)、实施户籍法(1871年)及大区小区制(1872年)等改革,均带有一定仓促性,也存在诸多弊端,在各地方引发不少矛盾冲突。1877年西南战争后,明治政府再次改革地方制度,1878年发布了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地方税规则,即所谓“三新法”。根据郡区町村编制法,废大区、小区,府县下设郡、区、町村,相应的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为郡长、区长、户长。根据府县会规则,在府县设立由公选议员组成的府县会。“府县会规则”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选举法规。在制定府县会规则之前,虽然有前述府知事、县令等召集地方民会的实践,但并无全国性法规规定其法律地位,而府县会规则确立了府县会的地方议会的法律地位。
府县会规则规定:“(1)府县会拥有议定由地方税支出的经费预算及地方税征收方法的职权,但须经府知事、县令的认可方可施行。若府知事、县令不认可该会决议,则将详情具呈内务卿,请求指示。(1881年2月进行了修订,府知事、县令在不认可决议时,因时宜可再议,再议之后仍得不到认可时,请求内务卿的指示。)(2)府县会议员选举采取记名投票方式。拥有选举权者须是20岁以上的男子,本籍须在该郡区内,在府县内须是缴纳地租10元以上者。(3)議员的数量,根据郡区的大小有不同,每郡区5人以下。(4)议长、副议长从议员中互选,经府知事、县令认可后报告给内务卿。(1880年4月修订为可不经府知事、县令的认可。)(5)府县会中有常会和临时会,均由府知事、县令发案召集。(6)议员任期4年,每2年改选其半数。”[21]25自不必说,当时能够缴纳5元、10元地租的一定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府县会规则颁布后,通过选举产生地方议会成为全国性制度。也是这一时期,“选举”一词正式写入了法律条文。
根据府县会规则,各地纷纷制定地方性的议员选举规则。各府县制定选举规则或在议员选举中遇到难题时,多会请示内务府,不少当时的请示文件被保留了下来。从各府县与内务府间往返信息看,府县会规则是指导性原则,各地细则因地方情况不同存在一定差异[22]。府县会规则颁布后,各地均先后设立了府县会。如长野县1878年公布了县会规则,1879年2月20日根据府县会规则进行了首次县会议员选举;高知县也于1878年制定了府县会规则,开设县会,进行议员选举。在明治政府成立后才着手开发的北海道,1881年3月1日也在函馆区役所召开了函馆区会,这是北海道最早的地方议会。实际上在此之前,该地就有施行“总代人”(代表人)公选的制度,从后来该区地方议会制定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及选举流程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总代人”选举时的惯例。在“函馆区会规则”中,规定区会议员共30名,将区内各町划分为6大部,每部选举5人组成议会。议长、副议长从议员中公选产生。对于被选举人和选举人资格做了详细规定,可担任议员的须是年满20岁以上的男子,户籍在区内,有固定居所并拥有土地者。若区内无符合此项条件者,可选举中等以上身家的不动产拥有者。并规定疯癫白痴、有犯罪记录者等无被选举权资格。对选举权资格也做了严格规定,须是满20岁以上的男子,户籍在区内,有固定居所,拥有不动产者,并规定符合上述条件的寄留在该区一年以上者也有选举权。关于疾病等剥夺选举权的条件和对被选举人的资格限定基本一样[23]96。
除府县会外,1880年政府又发布“区町村会法”,规定在区町村设立由公选议员组成的区町村会,议定公共事务及经费的支出和征收方法。该法主要内容包括:(1)区町村会议定该区町村公共事务相关经费支出、征收方法;(2)区町村会规则因地制宜,须经府知事、县令的裁定;(3)可另设数区町村的联合会,由各地方因地制宜,但须经府知事、县令裁定;(4)区会的决议由区长施行,町村会的决议由户长执行,当决议不合理时,区长、户长可中止施行,请府知事、县令指示;(5)郡区长认为町村会有违法行为时,可中止该会,认为决议不适当时可停止施行,请府知事、县令指示;(6)府知事、县令认为区町村会及联合会有违法行为时,可中止该会,并且可令其解散改选。
这一时期的府县会非常活跃,虽然政府颁布府县会规则的初衷是稳定地方形势,但因当时正处于自由民权运动高涨时期,不少地方议会成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据点。内藤正中在《自由民权运动与府县会》一文中,较详细地分析了明治十五年前后岛根县的县会、町村会的选举实况及议员构成,指出自由民权运动中结成的石见立宪改进党、石见立宪自由党、山阴自由党等,通过活跃的选举活动,几乎控制了该县各级地方议会(具体情况参见:内藤正中.自由民権運動と府県会(Ⅰ)—とくに明治十五年以降について[J].経済論叢,1961, 87(1): 74-96;内藤正中.自由民権運動と府県会(Ⅱ)—とくに明治十五年以降について[J].経済論叢.1961, 87(5): 362-382。)。一些府县会和地方官之间形成了一种颇为紧张的对抗关系。“在各地的县会中,有的做出决议提出郡长公选,或建议政府扩大府县会议员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范围等,以及反对保护大政商的政府政策等,府县会的反政府色彩逐渐显著。”[21]30另外,还须指出的是,地方议会不仅和地方官厅间有矛盾,地方议会内部不同党派、不同派系间也有势力之争。福泽谕吉在观察到此种状况后,就提出过批判,指出“府县会议员的目的就是否决县厅侧的提案,府县会的权限及郡区长公选问题等的论战,已脱离了现实利害,不过是单纯的政争”[20]62。
上述状况更引起中央政府及部分地方官的极大忧虑。1882年,在伊藤博文赴欧洲进行宪法调查后接任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对地方进行大量调研后,也认为府县会并未如他所预期成为选拔、培养人才,提高地方行政效率的机构,而是有不少成为了党争和权力斗争之所[24]98。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内部自1882年左右,开始出现了府县会中止论。1882年12月,岩仓具视提交“中止府县会意见”,他在意见书中称“自明治七八年以来人心趋于燥急,渐呈上下乖离之状,政府之权威亦稍有衰退”,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府县会开设过早。府县会开启了人民犯上之道,使他们容易产生蔑视政府之思想。岩仓具视指出要恢复政府权威,挽回民心之颓势,应断然中止府县会[14]172-173。岩仓具视的意见代表了政府中保守势力的观点,认为府县会开设过早,导致产生难以控制的局面,危害了政府权威及政令统一,主张应中止府县会,强化皇权及行政权的权威性。
针对前述状况,政府不断修订“府县会规则”,加强行政的监督统制作用,目的是建立支持中央集权的地方制度。特别是在1881年2月和1882年12月的修订中,分别新附加了县令的原案执行权和府县会停止权,很明显是抑制府县会的权能,确保内务卿、府知事、县令等行政官员的绝对优势地位。
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后,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强化了镇压和安抚两种手段,运动开始陷入低潮,地方府县会中的自由民权色彩也逐渐弱化,议会和地方官间的对抗相应减弱。1884年,政府对“区町村会法”进行修订,主要修正之处包括:(1)拥有区町村会议员的选举权者为满20岁以上的男子,居住在该区町村内,在该区町村缴纳地租。被选举人要求25岁以上,其余条件与选举人相同。(2)区会的议长由区长担任,町村会的议长由户长担任。(3)区町村会分别由区长、户长召集,且提出议案。(4)会期、议员人数、任期、改选等规定,皆由府知事、县令决定[21]27。1888年,日本地方制度又进行了改革,改为了市制、町村制,承认市町村的独立法人资格,承认地方有处理公共事务、委任事务的权力,并赋予其制定条例、规则的权力。市町村会由公民通过等级选举制公选产生的名誉职议员构成,议决有关市町村的一切事务及委任事务。执行机关在市一级为市长及市参事会(由市长、助理、名誉职参事会员构成),在町村级为町村长。市长由内务大臣从市会推荐的人选中选任,其他由市会、町村会选举产生。这些修订逐步增加了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地方议会的权限。这既是为抑制自由民权运动,也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过程中行政权优位的指导思想有关。
也是在“明治十四年政变”后,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宪法,在宪法起草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井上毅和在地方制度设计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山县有朋,都十分重视地方选举的经验,做了大量相关调查。日本国会设立前,民会、府县会、市町村会等的开设及议员选举为后来国会议员选举制度设计及地方自治的实施打下了实践基础。
结 语
幕末至明治初期,伴随各种政治势力对“公议”的追求,民间及政府逐渐展开对议会政治及与之相关的选举制的讨论。随着理论探讨的逐步深入,在政治思想领域,“选举”一词的内涵逐渐从明治初年的官员选拔、举荐转变为专指议会的议员选举。
除理论探讨外,明治初期在频繁的制度调整过程中,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有一定选举政治实践。中央层面,太政官制度施行初期设立的议政官上下局,之后的公议所、集议院,再到左院、元老院,都有议政机构的性质,且它们之间有一定承袭关系。它们的构成成员的选拔、所进行的制度调查等,具有扩大议政人群、选拔议政人才的目的,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的保守的选举政治实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整体来看,这些举措呈逐渐保守化趋势。这些机构的成员始终是在政府内部经举荐产生,且其选拔范围不断收缩,与现代“选举”精神及程序并不相符,而是更多糅合了传统的人才录用手法。并且,它们作为议政机构的独立性也不断减弱,终至被架空为立法咨询机构。左院、元老院等虽然都进行了法律、宪法相关调查,但在当时激烈的人事及制宪构想争端之下,其调研成果多未被采用。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机构的开设仍推动了政府内部及民间对于选举政治的关注。
在民间及政府中部分势力对选举政治的呼吁之下,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下,伴随明治初期地方制度改革,明治政府在地方层面进行了比较开放的选举政治实践。地方民会及之后的府县会、市町村会,乃至区长、户长的公选等,为后来开设国会时的选举制度设计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议政人才,打下了实践基础。当然,和中央层面的实践一样,伴随中央集权体制的日益巩固,地方层面的实践也渐趋保守。通过多次修订“府县会规则”等,政府不断强化府知事、县令等行政人员对地方议会的掌控,抑制自由民权派在地方民会的影响,在地方民会和地方行政官僚间的种种角力中支持地方行政官僚。在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也着力强化了行政权的优势地位。
近代日本在走向立宪制过程中,深受西方各类宪政模式及政治思想影响,同时,其传统政治文化潜流亦无处不在。在日本早期选举政治探讨及实践中,也是既能看到西方政治观念的猛烈冲击和巨大影响,又能看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并且,始终存在官方和自由民权两种政治动向、政治诉求、政治探索的交织和纠葛,也夹杂政府内不同政治势力的理念之争及权力斗争,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以及明治维新剧烈政治变革下政治理念及实践的多样性、在地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刘斌.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J].安徽史学,2018(2):61-67.
[2]澤大洋.明治最初期の選挙制度論の発展[J].選挙研究,1990(5):29-50.
[3]尾佐竹猛.維新前後に於ける立憲思想の研究[M].東京:中文館書店,1934.
[4]佐佐木克.戊辰戦爭への道:幕末の国家的課題をめぐって[J].人文学報,2000,83:1-17.
[5]萨道义.明治维新亲历记[M].谭媛媛,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
[6]国立国会図書館.亡友帖·新政府綱領八策[EB/OL].[2022-05-10].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3856383.
[7]国立公文書館.参与福岡孝弟後藤元燁等上下議事所ヲ設ケン事ヲ建議ス[EB/OL]//太政類典 第一編(慶応三年—明治四年) 第二十一巻 官制·文官職制七.[2022—05—10].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file/1340394.
[8]国立公文書館.公議所設置及開議ノ旨趣ヲ諸藩公議人ニ諭示ス[EB/OL]//太政類典 第一編(慶応三年—明治四年) 第二十一巻 官制·文官職制七.[2022—05—10].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1342186.
[9]国立公文書館.議事取調局ニ命シ議事所規則ヲ調査セシム[EB/OL]//太政類典 第一編(慶応三年—明治四年) 第二十一巻 官制·文官職制七.[2022—05—10].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tem/1342190.
[10]国立公文書館.諸藩公議人ヲ議事体裁取調所ニ於テ管轄セシム[EB/OL]//太政類典 第一編(慶応三年-明治四年)第二十一巻 官制·文官職制七.[2022-05-10].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M0000000000000827314.
[11]国立公文書館.公議所法則案ヲ議員ニ付ス[EB/OL]//太政類典 第一編(慶応三年—明治四年) 第二十一巻 官制·文官職制七.[2022—05—10].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tem/1342185.
[12]細川広世.日本国会紀原[M].東京:博聞社,1889.
[13]国立公文書館.輔相議定参与等ヲ投票選挙ス[EB/OL]//太政類典草稿 第一編(慶応三年-明治四年)第十六巻 官制·文官職製1.[2022-05-10].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image/M0000000000000875816.
[14]大久保利謙.近代史史料[M].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
[15]島善高.元老院國憲按の編纂過程(上)[J].早稲田大学自然科学研究,1995,47:135-198.
[16]久保田哲.元老院の研究[M].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社,2014:序論.
[17]渡辺久雄.尼崎市史(第7巻)[M].尼崎:尼崎市役所,1976:255-284.
[18]国立公文書館.北条県具陳民会議事ノ儀ニ付伺[EB/OL]//公文録·明治七年·第五十五巻(明治七年六月)内務省伺(二).[2022-05-10].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M0000000000000092992.
[19]郭冬梅.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0]小川原正道.福沢諭吉の議会論:民会論から国会論へ[J].法学研究,2010,83(11):45-69.
[21]都丸泰助.地方自治制度史論[M].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2.
[22]国立公文書館.府県会規則ノ部[EB/OL]//単行書·行政説明録五乾(正本).[2022—05—10].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1129392.
[23]清水昭典.北海道における地方制度の形成について(3)[J].北大法学論集,1968,18(4): 55-101.
[24]長井純市.山県有朋と地方自治制度確立事業:参事院議長就任を中心として[J].法政史学,1993,45:88-119.
[责任编辑 孙 丽]
Practice of Japanese Electoral Politics from the End of Edo Period to the Early Meiji Period
ZHANG Yanru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Edo Period to the Early Meiji Period, there were activ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on electoral politics.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 in the realm of political thought, the meaning of election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official selection and recommendation to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ccompanied by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ve also tried out some election measures and electoral system investigation in the frequent system adjustment. The Gisei-kan, The kogisho, The shugiin, The Sain and The Genroin all had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s that discuss politics,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selection of the constituent members of those institu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igation carried out by them are all aimed at enlarging the scope of political participants and promoting talents. It can be seen as a conservative electoral political practic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accompanied by the local system reform, especially driven by the freedom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relatively open electoral political practice at the local level. The practice of election of members of the local assembly ha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the design of the election system when the assembly was later established, and cultivated talents for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the discussions and practices of early election politics, we can see not only the mixture and collis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ideas and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but also the interweaving and entanglement of different political trends, political demands, and political explorations. The complex political reality of the early Meiji era is revealed.
Key words: Japan; electoral politics; institutions that discuss politics; local assembly; the prefectural assembly
收稿日期:2022-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日本近代史学的形成研究”(20BSS022)
作者简介:张艳茹,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政治史、日本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