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返乡路良知激荡:发小坠亡,我逃了六年
2023-07-06张守广
张守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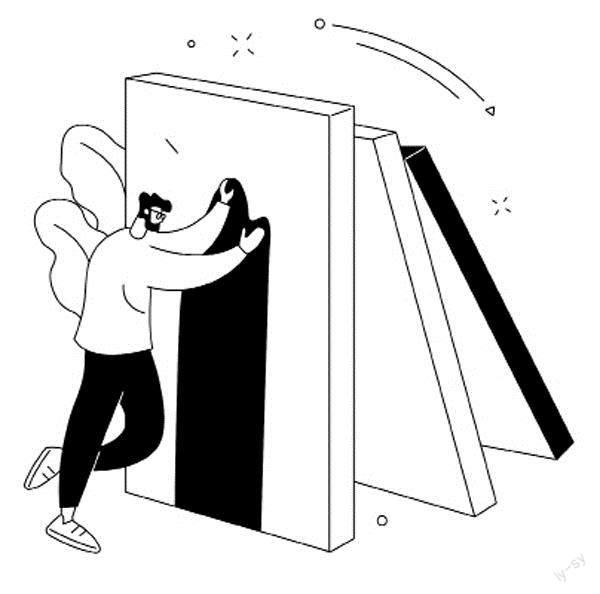
2012年,一起创业的伙伴陈海意外坠亡,张强主动认赔了50万的赔偿款。为了这笔钱,他和妻子“逃”了6年,一家人的命运彻底改写。
以下是张强的自述。
发小坠亡,我主动认赔50万
2012年7月的一天,我趴在顶子的方钢梁上,一手拿着电焊面罩,一手拿着焊把子正焊接时,突然听见“嘭”的一声。我心里一紧,往下一看,是小海面朝下趴在水泥地面上。
洪生在下面切割方钢管,小海负责往上拉材料,等我固定住几个点,他再继续拿绳子往上拽材料,我就埋头焊接。可小海怎么突然就掉下去了?
四米的顶子说高不高,说矮不矮。我赶紧扔下手里的东西往下爬,洪生也往这边跑。
我叫张强,1988年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一个农村家庭。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因体弱多病,以放羊为生。小伙伴们经常嘲笑我一身的羊粪味,我又羞又恼,却不知道怎么回嘴,他们就变本加厉喊我“憨二”。
我性格内向又自卑,在学校里经常被欺负,一进教室就感到紧张,成绩自然可想而知。陈海是我的发小,比我小一岁。他是唯一一个不嫌弃我还拿我当兄弟的人。对嘲笑我的人,小海上去就干架,可他也占不到便宜,结果就是我们俩一起被揍得鼻青脸肿。
小海特别会安慰人,他常说:“等咱哥俩长大了,一定挣大钱,让那些看不起咱哥俩的人都傻眼。到时候买宝马,去欺负咱俩的人家门口使劲按喇叭,想按多少下就按多少下……”每次牛皮一吹完,我们俩也就忘记了不快。其实没有人欺负他,我知道小海只是为了给我出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还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哥哥,早早就去县城的修车铺打下手混生活了。读完初中,我就辍学去县城学电焊。
那几年我玩命干,挣了些钱。
2012年1月16日,我结婚了。结婚前,小海比我还兴奋,张罗着贴喜字、端盘子、招呼客人。
婚后不久,我媳妇怀孕了。考虑到孩子出生后的各种花销,我萌生了单干的想法。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和小海商量,小海没考上大学,也在家乡打零工。听我一说,小海又找来了洪生,洪生比我还大四岁,我们仨一合计,干呗!
这一试,还真成了!半年后,我们一算账,不比打工时挣得少。之后,我们认识的人慢慢多了,曾经服务过的客户还会给我们介绍活干。
有个叫杨光的工头,承包了一个厂子的厂房建设,他把钢结构方面的活交给了我们仨。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活干完,至少顶我们一年多的收入。
哪里想到,小海出了意外,打得我措手不及。小海翻了下身子,靠着工字钢的柱子坐着,地面上也没有血迹。“吓死我了,你没事吧?”洪生走到小海跟前说。小海没有说话,脸色很难看。我急忙打了120,小海的脸色越来越白。等待中,小海突然吐了一口血,呼吸急促,喘不上气来。
急救车赶到时,医生边抬人边问他:“能不能听见说话,能不能看清我伸了几根手指?”小海没有任何反应,我也傻了。洪生推了我一把:“你赶紧回去凑钱,我跟着去医院。”
我是怎么开着摩托车,怎么过的大桥,连怎么撞到树上的都不知道。我满脑子都是小海,越想越不对劲。就在这时,洪生打来电话,哭着说:“小海没了。”他说,在救护车上,还没到医院呢,医生就说没救了。他跪下求人家医生,都没法……
小海的母亲和姐姐来了,在院子里撕心裂肺地哭喊,我躲在里屋,不敢出去,甚至不敢出聲。小海是跟着我出去干活的,他们家只能找到我。
我仅存的一点感觉是生不如死。
我跪在小海母亲面前,她抓住我头发,使劲晃了两下,继而就像身体被抽空了力气,瘫坐了下来。小海的姐姐怒喊着抽了我几个耳光,被邻居们拉开。小海家人的每一声哭喊,都像刀子一片一片割我的肉,每一刀都刺心地痛。
我不仅仅害怕面对小海的家人,我害怕见到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安慰的话语也会异常刺耳。
洪生和父亲每天跑县城弄赔偿的事,厂子的大老板连面都没有见着,说这个活是打包包给了工头杨光的,跟厂子没关系。杨光的态度是,这个活介绍给我,我找谁或和谁一起干的,和他都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任何纸质合同证明,不存在雇佣关系。
我不知道洪生和父亲是怎么和杨光争执的,反正杨光后来给了八万块钱,说再要一分钱也没有了。后来,我找杨光也找不到了。
我最关心的是,小海的后事怎么处理。但我张不开嘴问任何人,这就像是问责自己。
事后几天,小海的姐姐来了,她说:“这种情况至少要赔50万,小海是跟你出去的,是你跟杨光去要还是你自己出,我们不管。”
出事十多天没有开过口的我,答应了她。虽然剩下的42万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我现在连2万都拿不出来,但是这样会让我好受一点。
那几天,我一直在做梦,梦到我被人欺负,小海给我出头,梦见小海要买宝马。我唯一从小到大的好兄弟离开了,我无比难受,而他的离开和我有脱不开的关系,更让我愧疚得寝食难安。
我决定承担小海姐姐说的赔偿,无关法律、无关数字,是我觉得亏欠兄弟的,一辈子都无法偿还。
打工还债,不料良心债最难偿
我应该感谢小海的姐姐,给了我一个数字,至少让我有一种方式去补偿,我心里会好受一些。虽然我知道多少钱都无法弥补小海兄弟的命。我甚至偷偷搜索了哪里有收人体器官的。
妻子回来后,我支吾地张不开嘴。这个时候,凡是跟我有关系的人,好像都会被我连累。“你回娘家吧!”我没有直说离婚,既开不了口,也舍不得。妻子努力挤出一丝笑:“回娘家干吗?我刚回来。没事,有事咱俩一起扛。”“我应了小海的姐姐,剩下的42万我来赔,可能后半辈子都要挣钱赔付了,你再跟着我,连累你后半辈子。”这个时候如果她选择离开,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妻子眼睛泛红:“两个人都还不上的话,你一个人就行了?”“滚!”我咬紧后槽牙。这是癞蛤蟆第一次吼天鹅,她的善良,让我更加愧疚。
“我跟你说,强子,当初跟我相亲的人,哪个不比你强?我比你白,比你高,文化程度比你好,跟我爹妈吵翻也要嫁给你,不就是看中了你人老实敢担事?我实话跟你说,你要是不管小海家的事,我还真跟你离婚。你要敢担着,我就敢陪着,不就42万么?咱俩……咱俩……”说着说着,妻子也没有了底气,给我打气的她,自己也委屈得哭了起来。
见她哭了,我终于也哭了出来,憋了这些天的情绪,终于有了出口。妻子安慰道:“你别胡思乱想,为了咱爹娘,还有我跟孩子,你得像个爷们扛着,有人在就行,有人在,多大的坎都能过去。”
于是,我开始想办法。那段时间,我几乎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凑了二十七万三千六百块。我让父亲送到小海家,让他带话,剩下的我会尽快还。
我跟父亲说,我和妻子要去大城市打工,那里挣钱多,也好尽快还账,家里的事就辛苦二老了。父亲说了句:“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去吧!”
第一站,我去了天津,进工厂还需要至少会英文字母和基础单词,这对我来说太难。而或许是从小营养不良,我只有1.6米的身高,一百斤出点头的体重。这样的外形,去工厂也干不了体力活。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想去当服务员。端盘子,是我们老家最基础的生存技能工作。
只是没有想到,端盘子的活,人家也不要我。那老板对我说:“看着又瘦又小,被人说用童工就不好了,而且长得也太黑了,形象也不行。”
我是要什么没什么,兜里只有一张身份证,证明我叫张强,已成年。我也去找劳务中介,但他们要押金,要押身份证。我第一没钱交押金;第二身份证是我唯一的身份证明了,交给中介不放心。
好在后来,找到一个卸水泥的活,老板狐疑地看着我,我说:“试试,如果不行我就立马走人,不要一分钱,白给你卸一袋你少一袋。”这一试,试到最后只剩下我。但是抵不住给的多,一吨10块,有二十吨我卸二十吨,有三十吨我卸三十吨。
原来真正累到极致是吃不下饭但你又不得不吃,而手连筷子都抓不住。但这有一个好处,睡死过去没有力气做梦,也就可以避免哭醒。我梦到不止一次抱着小海给他磕头说对不起,没有看好他。
因为之前也没有干过这种活,我累了就张着嘴喘粗气,没一小会儿,就感觉嗓子给糊住了一样,咽唾沫都咽不下去,鼻子也感觉吸不进去气一样。老板问我:“你怎么不戴个口罩?”我摆摆手说不用。不是不用,是舍不得,妻子把不到一岁的孩子放下,跟着我出来挣钱,我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花。
她住宿舍,我找了最便宜的一个隔间,我们每个月发了工资见一次面,工资留下一点开销,剩下的都打回去,先给小海家,当初借的亲戚朋友的钱之后再还。妻子的记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她精打细算到几毛钱的入账和出账。但是刨去必需的花销,两个人的收入每个月都对账,账目依然很高,这让人很崩溃。但好在它总是在一点点地往下减。
我打趣问妻子:“你说咱们这辈子还能翻身吗?”她说只要人在,账就有还完的那天。每次还完一笔账,她总是欣慰得像个孩子,像是鼓励我又像在鼓励自己。短暂的开心后,她就又哭起来。
因为太想孩子,有时候在街上看见和闺女差不多大的孩子,她也会突然哭起来。出了事以后,我想过去死,她都没有哭过。但这么一个坚强的女人,承受不了想孩子和愧对孩子带来的痛楚。我也想孩子,却不敢回家,因为没脸回家,更不知如何面对小海的母亲。但是妻子不该不回,我好不容易劝说她别舍不得车票钱,放假了就回家看看孩子。可回来后,她却哭得更厉害了。
她说,两年没回家,孩子根本不认识她了,不让她抱。我们夫妻俩抱头痛哭。
在天津四年,我给妻子只过了一次生日,买了一碗十块钱的米线。妻子在那种生产隔音棉的工厂上班,因为里面有纤维,那个东西会刺进皮肤里,我看着她挠得胳膊通红,心里愧疚不已。
水泥厂的活越来越少,我跟老板去告别。老板挽留我,但我不得不走,跟这位老板无奈念叨了一下我的家庭和小海的事。老板听后一阵唏嘘,又说敬佩我是个爷们,得知我会钢结构的活,推荐我去他老家安徽,是他亲戚开的公司,亏待不了我。
良知激荡,勇担责任风雨返乡
开始干的时候,还没有爬架子,一握焊机把子,我就扶着柱子吐了,但我不得不再次握住让我有些畏惧的钢结构。这份工作是绩效制的,我喜欢这样。
许是当初水泥厂的老板打了招呼,許是我的追星赶夜让领导赏识,我很快就做了生产管理班长,可以带领团队了。
即便我马不停蹄地赶工,活仍是催得急。我想到了洪生,想让他来。虽然工资高,但我心里没谱,毕竟当年那事他也亲身经历过。
我婉转地让父亲告诉还在老家的洪生,没想到他痛快地就来了。虽然我们刻意回避有关任何小海的事和话语,但有次酒后,洪生还是抓着我的手说:“强子,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那天我跟着救护车去医院路上,走到半道时,小海突然意识很清晰,他说他不行了。”我喝了口酒,假装已经放下:“回光返照吧?”洪生点了点头:“他说他肯定是不行了,让我们照顾他娘,还说要是自己走了,都别怪你,是他不听话没系安全带,话没说完就走了。”我低头不语,有眼泪糊上眼眶。
“强子,你说说,那也不高啊,怎么就那么寸……怎么就没了?”洪生趴桌子上哭了出来。
洪生的话提醒了我,这几年我玩命挣钱想弥补小海的家人,但小海最大的心愿应该是他娘有人照顾。而我因为害怕,一直在逃避。借着酒劲,我跟洪生说,今年过年,我一定去看小海他娘,她就算打死我,我也认了。酒壮怂人胆,酒醒了就不行了,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迈出去那一步。
也许是苦尽甘来,又或许是老天爷看弄不死我,就跟我握手言和了。总之,我的人生开始好起来。
2018年我当了主管,不仅工资提高了很多,还能参与分红。也是在这一年,我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外债,甚至还有了存款。那个厚厚的记账本我划下了最后一道时,如释重负,我才感觉活了过来。妻子也从纤维厂辞了职,来到我身边。
2018年底,我终于回家了。大年三十,我準备贴春联。父亲说:“去给你大娘看看,用不用帮忙。”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小海娘。母亲停下正在擀着的饺子皮:“去吧,憨二。事都过去了,你这几年在外面也不容易,你大娘都知道。刚出事那两年啊……”母亲擦了一下眼角的泪,继续道:“你们两口子都出去挣钱了,我在家看孩子,难得很,孩子病了也不敢跟你们说。小妮那年发烧不退,大夫让去县城医院,是你大娘给送来两千块钱,她不让跟你说……你大娘啥样人我知道,你得去看看她。”
我拎着东西就要出门,父亲喊住了我,让我放下了手里的礼物,递过来一盆贴对联用的糨糊说:“别拿那个,拿这个吧,看看你大娘用不用贴春联。”
我有点不解地看着父亲,妻子说听爹的吧。路上我想明白了,拎着礼物去,味儿就变了,大娘没法收,收了就等于原谅了我,而她能不能原谅我,都不能让她为难。
小海家的大门是锁着的,我想了想,刷糨糊开始贴上春联。回过头时,大娘就站在身后看着我。大娘的头发更白了些,腰身也更清瘦。
我低下头,不敢跟她有任何眼神对视,她平静地说了句:“进屋吧。”我一步步跟在大娘身后,走到堂屋门口,大娘又说:“去偏房吧,偏房暖和。”
我抬头看了一眼,可能不是因为偏房暖和,而是堂屋有小海的照片。我端着大娘递过来的水,坐立难安,没滋没味地一口接一口喝,大娘也不说话,我喝完就续上,续上我就喝。大娘拎起第二个暖瓶时,我忍不住说:“大娘,我喝不下了。”
大娘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说:“憨二,你能来看看大娘,大娘该高兴。你这几年在外面也不容易,事过去就过去了,你也是老实孩子,不能怪你,大娘也想通了,都是命啊……”
我再也压不住愧疚,跪在她面前:“大娘,我给你养老送终,你拿我当儿子吧!”大娘把我赶了出来,说自己有闺女,用不着别人管。虽然大娘没说原谅我,但有了这个开头,我心里也敞开了不少。
听说大娘腿疼,冬天出门不便,我买了带棚子的电三轮,大娘没有要。给她买补品之类的,大娘也从来不肯收。那我就干活,逢地里春播秋收时,无论工作多忙,我也要回家给大娘干活。
2022年底,大娘感染了新冠病毒,小海姐姐在外地,大娘烧到下不了床。担心她夜里有什么不便,我想让妻子去大娘家住着,方便照顾。大娘死活不肯。我便在她里屋的门前偷偷打了地铺。那几天大娘发烧吃不下饭,连褥子都被浸湿了,妻子每天三顿都要做好新的送来,给大娘换被子擦身体。
五天以后,大娘才能下床,半夜开门,一脚踢到了我的头上。我一看大娘下床了,高兴地说:“大娘你能起来了?喝水不?”大娘怔怔地问我:“这几天你一直在这睡的?”我点点头,大娘笑着骂了一句:“真是个憨二。”大娘眼睛一红,抱着我哭了。那次之后,大娘也不再拒绝我的好意。
大年三十,大娘还来我家吃了饺子。我抱着一碗饺子,吃的那个知足。和妻子商议之后,我们选择了在镇上买房。虽然比不上城里的教育资源、交通等优势,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在这片土地上,关键是我也能够照顾到小海娘。
孩子问我:“别人都去城市买房,我们却在镇上买房,这和在村里不一样吗?”我告诉她:“学会做人,承担起要承担的责任,远比上名校更重要。”
去收房时,妻子感慨:“恭喜你,奇迹真的出现了。”我抱着妻子:“就算奇迹垂青我,我也要能坚持到奇迹到来才行。老婆,谢谢你。”
编辑/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