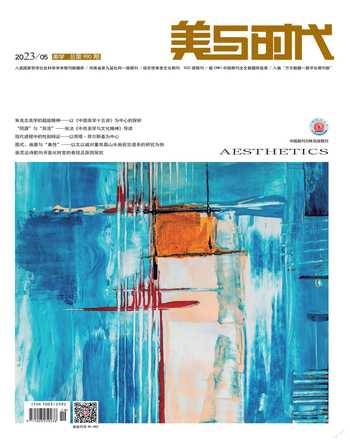转向自身:福柯对“关心自己”的概念新解
2023-06-28田秀伟
摘 要:在《主体解释学》一书中,福柯梳理了“关心自己”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希腊化罗马时期和基督教时期不同的向度,将希腊化罗马时期“关心自己”的内涵聚焦在“转向自身”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上,它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认识世界的精神化、真话坦白的主体化和修身目标的自身化。通过对“转向自身”内涵的揭示,福柯试图帮助主体个人确立超越规定的自在性,从而建立属于自身独特的生存美学。
关键词:主体解释学;关心自己;转向自身;希腊化罗马时期
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由“权利理论”“性经验”转向了对“修身技术”“关心自己”等问题的思考。在1982年法兰西学院的授课内容《主体解释学》一书中,福柯以解读柏拉图的《阿尔西比亚德篇》为起点,对“修身理论”即“关心自己”在西方历史上的衍变进行了诠释。他发现从古希腊时期到笛卡尔时代,获得真理的方式演绎成“认识自己”(笛卡尔时期),这一方式使主体进入了永无止境的探索之路,真理的获得犹如虚无主义的渺茫。因此,福柯要求重新回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修身”伦理,以获得对当下主体存在的思考。“关心自己”的概念出现在柏拉图《阿尔西比亚德篇》,福柯把它作为一个修身概念,梳理了“关心自己”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希腊化罗马时期和基督教时期不同的向度,以此来说明真理的主体化问题。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到希腊化罗马时期,“关心自己”呈现了三个方面的演化。一是主体由行使权力的年轻贵族转变为不以出身为条件的所有人;二是目标由为了统治治理的关心他者变成为了自身,要实现自身的目的化;三是“关心自己”的主要形式“认识自己”弱化,拥有了比“认识自己”(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更广泛的范围。嬗变的最终结果是“关心自己”成为了一种面向所有人,形式多样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自主实践。相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修身向度在希腊化罗马时期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修身突破了教育学的范畴,等同于“生活艺术”,这种修身的艺术不再局限于师生关系的完成,而被纳入到各种不同的社会交往中,或许是朋友,或许是雇佣的家庭顾问。二是修身突破了政治活动,其他人和城邦不再是“关心自己”的目标核心,主体与他人的关系被弱化、隐含在自身对主体的关系中。福柯指出,在对希腊化罗马时期修身范畴的分析中,“关心自己”指向一种核心——“转向自身”,即“必须在整个一生中,把注意力、目光、精神以及整个生存都转向自身。把我们从一切让我们远离自己的东西那里转向我们自己”[1]244。福柯对“转向自身”——这个以自身为中心,关于“关心自己”概念的新解——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含义:认识世界的精神化、真话坦白的主体化和修身目标的自身化。
一、认识世界的精神化
“转向自身”围绕的核心是“自身”,中心点在于从外部世界转向自己,但这个中心并不是要求完完全全与外部世界脱钩,仅仅只在自己的身上探求修身的内涵。“当他们坚持必须把一切知识都纳入‘生活艺术之中和关注自己时,他们是把这种转向、反观自身与对世界秩序及其一般内在结构的把握联系在一起的。”[1]304-305福柯指出,在公元1-2世纪,斯多葛主义强调的“反观、转向”是与认识世界相关联的,主要以塞涅卡和马克·奥勒留的文本作为分析的立足点。在塞涅卡的文章《自然问题》中,福柯关注了两个问题。一是塞涅卡为什么撰写离我们很远的自然问题,二是修身和自然问题有什么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回答,因为要修身所以关注了自然问题。因此,修身和自然问题的关系成为了主要的探讨点。
福柯指出,在塞涅卡的文本中,直接回答了修身与自然问题的关系,“伟大的东西就是把他的灵魂置于唇边,准备离开;人不是因为城邦的法律而自由的,而是因为自然法而自由的”[1]317-318。研究自然可以让我们摆脱自己对自身的奴役,从而获得灵魂的自由,通过对事物本性的观察、审视,达到对自身的解放,这种解放也恰恰是修身的目的。对自然的观察和审视是以一种“精神体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观察和审视的结果是在把握了整个自然事物体系后,站在了理性的最高点,从而获得了一种“上帝视角”。而“上帝视角”并没有把观察者从世界秩序中抽离出来,而是内化在他的精神中,使他既能够把握一切现象的卑微和人为的鼓吹的虚假,又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所处的完全实在的生存只是宇宙体系的一个空间点和时间点。因此,福柯在此基础上认为,只有在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之下才可以认识到自己,把自己的生存与世界的秩序、必然性联系在一起,才能在自己的行为与思想方面控制自己,确保“反观自身”。
在对马克·奥勒留《沉思录》的分析中,福柯认为,他也以一种把有关事物的知识模式化的方式来认识自己,这种模式通过三个训练获得了有關我们自身自由的认识。一是界定描写事物形象在精神中出现的对象。这种界定应当是连续的、有意的、系统的,这样人才能在界定的基础上以逻辑的方式毫不迟疑地把握对象;二是测定对象的价值。即通过考察这个对象对于它所属的宇宙有什么作用,来确定相对于这些事物,主体需要哪种德性;三是贬低性描述。立足于人的生存,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减弱对象的存在,得到“我们自身多么自由”的结论。通过对以上两个文本的分析,福柯指出,在希腊化罗马时期,“转向自身”包含这样一种对世界认识的模式化:把握事物的实际和价值,反省自己以认识自己的实际情况,从而发现主体自身的自由,在自由中发现一种让自身获得幸福和完善的生活方式。这种模式化过程就是对世界认识的精神化,它试图使主体“抛开任何普遍法则的支撑,建立他自己的自制模型”,从而要求“平息自身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抗——就是说,创造自身,把自己当成主体生产出来,寻找他自己特定的生存艺术”[2]。认识世界的精神化类似于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从对世界的认识中获得自身的某种精神胜利,而谋求主体发展的平衡,获得主体的自在性与自为性。但两者的行为主体存在着不同之处。一是转向自身对世界的认识结果是多样的。塞涅卡认识的是伟大,马克·奥勒留认识到的是贬低,而精神胜利法只会得到对事物贬低的结果;二是转向自身在对事物有了认识结果后要对自身做出反省。认识自己的真实状况,而精神胜利法只会对自身进行虚假的伪装;三是转向自身的精神价值是在对自身做出某种方式的纠正后获得的,而精神胜利法没有修正,只有对自身的欺骗。
二、真话坦白的主体化
福柯认为,“在自我技术中,面向发现和形成自己真理的技术是极其重要的”[3]204。而“真话坦白的主体化”就是希腊化罗马时期发现和形成自己真理的技术。如果认识世界的精神化是“转向自身”理论层面的含义,那么真话坦白的主体化就是“转向自身”在实践层面的内涵。“转向自身”在实践层面对修身的要求是一方面让人获得真实的话语,另一方面让人成为这些真话的主体,并通过真话而改变形象本身。“真实的话语”存在两个维度,大的维度而言就是真理理性,小的维度而言是以现代社会定义的每一条道德法律所隐含的精神与行为含义。在希腊化罗马时期,“转向自身”的要求是“真话的主体化”,无论是真理理性,还是道德法律都要内化在主体自身中,变成主体的一部分以达到这样的形式——自身行事不是因为法律的要求,而是主体自发的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类似于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福柯指出,真话主体化的修行以听、阅读和写作、说话的方式进行训练,听的要求是缄默不说话,阅读和写作要求沉思回忆,对听到的进行理解和消化,说话要求“坦白”(parrêsia)。
坦白的原则主要是针对说话者老师而言的,接受的一方即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是不能说话的。坦白就是全部说出来,保持一种不强加的开放方式,福柯对坦白的含义进行了否定与肯定两方面的阐释。从否定面来说,首先,坦白是反奉承。“奉承是用来从上级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语言。奉承者就是不让人真实地认识自己的人”“被奉承者的修身关系是一个依赖他人的不充分的关系,而且是一个依靠他人谎言的虚假关系”[1]442。坦白就是要修正听者对他人的依赖,使听者把真话记在心中,使其与自身确立一种“独立、自主、充分、满意”的关系,在特定的时刻不再需要别人的话语。其次,与修辞相比,坦白不是能够说谎的艺术,而是要求能完全传达真理;不是步骤严苛的艺术,而是依据审慎灵活,根据人们相处的处境,改变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不是为了说话者的最大利益,而是为了让听者与自身培养一种主权关系。在对坦白肯定面的论述中,福柯主要对塞涅卡的信件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坦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坦白使用的话语要把修饰降到最低,以纯粹简单的思想进行传递,不要掺杂为了目的而夸张不实的修辞;二是坦白传达的思想应是真的属于传达者自己的思想,不是要说出某个思想,而是把属于自己的思想展现出来;三是坦白的说话主体与行为主体应是一致的,说话主体传达的同时应是行为主体在生活中所践行的,说话主体与行为主体要合二为一在一个主体中;四是坦白是進行真话传递,目标是改变听者的生活方式,使其与自身确立一种“独立、自主、完满”的关系。
这些关于坦白的特征性定义也是在具体的操作环境中对坦白者的准则要求,主要立足于“真”的要求,“真”一方面保持着一贯的知识性要求,说话者的说话内容必须真实,客观理性,另一方面获得了道德性要求,说话者的行为必须真实,保持与言语表达的一致性。“转向自身”的实践要求就是“真”,而“真”的中心点是围绕“真话坦白的主体化”展开的。在坦白中,对于说话者而言,传达的真话已经主体化在自身中,真话是属于说话者自己的,不依赖他人,言行一致的;对于听者而言,要理解的不仅是传达的真话,还要在说话者言行一致、主体展现真理的熏染下把真话内化在自身的主体中,实现与说话者一样的真话主体化。真话主体化实现的“自我”不是现代哲学中的理性“自我”,而是指具体的、实践中的和绝对不可替代的“自我”[4],它要求真话不是被束之高阁作为理想存在于主体自我之中,而是真切地被践行在生活内容里。
三、修身目标的自身化
希腊化罗马时期,修身概念“转向自身”在理论层面上提出“认识世界的精神化”,从对世界的认识中获得实现自身自由的精神形式,在实践层面提出“真话坦白的主体化”,要求在坦白中通过展现说话者的真话主体化实现听者自身的真话主体化。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的要求,“转向自身”作为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修身指向,它的目标,也即修身的目标都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他人,修身目的实现了自身化。从“认识世界的精神化”而言,自身从对世界的认识中获得的精神形式是为了自身赢取自由而服务的。这种精神形式要为主体的灵魂做准备,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一切人生境况,获得勇气去面对强加的信仰,正视人生的危险与想控制他人的权威,确立对依赖于自身的东西的绝对控制,变成一个自由的主体,只依赖于自己。从“真话坦白的主体化”而言,实现真话的主体化就是要把真话内化在自己的心中,通过记忆、回忆、交流,把真话刻在自己的灵魂中。这种主体化的目的是要与自身确立一种“自主、独立、充分、满意”的关系,使真话内化在主体精神中,成为主体意识的一部分。需要这些真话的时候,真话已经做好了随时发挥作用的准备,不再以他人的话语作为自己的精神价值或行为准则。从“转向自身”的目的而言,它已然成为福柯所言“自我技术”的一种,即“允许个人通过做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行为,以一种方式改变自己,达到某种完美、幸福、纯洁、超自然力量的状态等等”[3]203。
希腊化罗马时期“转向自身”实现的自身目标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这个自由的主体具有以下的特征。首先,主体能够进行自我纠正,成为没有成为的人。纠正是以错误、恶习和养成的依赖性必须改正为基础的,纠正的结果就是成为了以前从来没有成为过的人,近似于医学治疗疾病,纠正要治疗灵魂和身体,纠正后再次成为的人是正面的、向上的、正确的。其次,主体的一生朝向老人化的价值。“人必须为了变老而组织好自己的生活,必须赶紧变老,必须在生活方面变得老成持重,即便人还年轻”[1]132-133。“老人化”不是以年龄作为界定标准,而是以老人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作为存在的准绳。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达到了自身,人重新回到了自身,而且与自身保持一种既控制又满足的完满关系”[1]130,也可以称之为“从心所欲不逾矩”。最后,主体解除了与他人的关系,能够实现自救。“自身”是修身主体确切且唯一的目标,一方面修身不再是为了关心他人,另一方面修身不再依赖他人而实现自救。自救的含义,也可以被称为自救的要求和目标。一是摆脱一种危险,击退一切攻击;二是避免被统治奴役,确保自己的自由;三是保持常态面对身边发生的所有;四是达到自己一开始没有的善境。对以上四方面简而言之的总结就是做到不动心与自给自足,“主体用一生来完成的活动,目的是不会招致不幸和麻烦,不会让灵魂受到外在实践的干扰。”[1]218
福柯所分析的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修身目标指向的是一个理性主体的建构,但这个理性主体并非是被自然与社会准则所要求的主体,而是由主体自身建立起的未被约束的自在与自为的个体。这个个体通过自己内化的修身技术,形成不会也不应该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的主体,“必须明白,天上、星辰和气象中的所有光辉,大地的美丽,平原、大海、群山,所有这些都是和身心的枷锁、战争、掠夺、死亡、痛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333因此,要保持自身的理性,在对外在世界的考察中将“人生所有的遭遇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内化在主体精神中,要提前通过关心自己把理智摆在危险痛苦面前,将人生的不可控性和失序性降到最低,保持主体自身的自由完满。
四、结语
福柯认为,当代以规范为导向的道德“通过不同的规范机制的中介被给予个人和群体”[5]140,由于这种道德传播方式的不同与分散,在这一活动领域内存在盲点使人得以规避,所以我们需要“以伦理为导向”的道德。“这些道德强调的是各种与自我发生关系的方式、人们为之设想的各种方法与技术、为使自我成为认识对象而做出的各种努力,以及使个体得以改变自己存在方式的各种实践”[5]144,这就是福柯所强调的修身技术,它在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代名词就是“转向自身”。当代责任伦理道德的缺失或许成为了当代人受到束缚控制的责任点,“把责任这个伦理概念法律化或科学化了”[1]6人对于责任,只是出于对法律、科学的服从,良心在法律面前不再受到谴责。因此,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向我们揭示的是可以在希腊化罗馬时期的修身向度中获得某种改正的启示。希腊化罗马时期以“转向自身”为核心点的修身向度,通过认识世界的精神化、真话坦白的主体化与修身目标的自身化展示了当代责任伦理所缺失的道德责任。自身只有把真理、真话内化在主体中,避免外在的控制,才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找到完美幸福的生活方式,“如果不通过‘主体化的方式、一种‘禁欲活动或者各种支持它们的‘自我的实践,那就无法塑造出道德的主体”[5]143。福柯从时代构造的社会环境出发,通过种种考察发现了权力关系对人类生存造成的规训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人类处于一种不自由的形态中。人是社会的动物,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人类所面对的自由也不仅仅是权力关系的桎梏,正如黑格尔所说:“主体在认识的关系上是有限的,不自由的,……在实践的关系上也是有限的不自由的”[6]。福柯正是从突破“限性状态”出发,试图为人类破除规范性束缚,建立自由完美的主体提供一种生存美学,他重新思考希腊化罗马时期“关心自己”的概念,揭示了主体修身的一种方式既“转向自身”,通过认识世界的精神化、真话坦白的主体化和修身目标的自身化以达到主体对自身的支配。这种方式并非福柯对修身技术所作的规定性准则,而是选择性启迪:通过主体修身,“转向自身”以获得超越普遍法则规定的自在性,在破除奴性与压抑之上建立属于自己的生存美学。
参考文献:
[1]福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
[3]Foucault M, Blasius M.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Two lectures at Dartmouth[J].Political theory,1993(2):198-227.
[4]李晓林.审美主义:从尼采到福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4.
[5]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4.
作者简介:田秀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