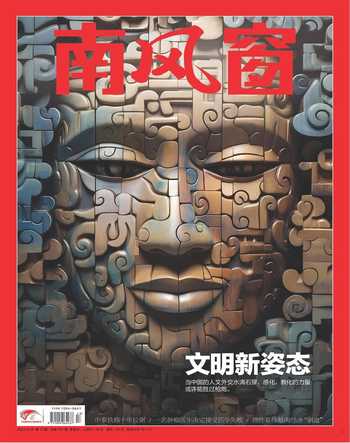最后一门植物课
2023-06-27张旦珺
张旦珺

文学院的张箭飞教授要退休了,今年是她最后一次讲《植物人类学》,等她退休之后,這门课程也会从武汉大学的课表消失。
有学生为此在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传到了社会上,也反响热烈。
这让张箭飞小小地“网红”了一把—出乎她的意料,她说,文学院、植物这些安静的事物,很少受到外面世界的关注。
张箭飞的家,对面就是武汉大学附属医院。2020年,疫情期间上网课的时候,她把教授的其中一门课改成了《瘟疫与文学》,学生们却显得不太有兴致。与之相对的是植物课班群的热闹,学生们把家中植物的照片发在群里,兴奋地讨论着花草的生长状态,甚至还有人把听课笔记画成了精致的手账。
人类与植物的紧密联系,在特殊的环境下重新显现。
物资匮乏的时候,每一根萝卜、每一颗大白菜都显得格外珍贵,没错,人们需要依靠植物获取生命的能量;疫情期间,许多人在家中研究自种蔬菜,土栽生菜,水培大蒜,智慧生物可以增加栖息环境的承载能力,这是人对植物的驯化。更别说植物大都长得美丽,茂叶丛花,环绕身侧,人的心情也会好起来。这些年,人们对于植物的兴趣似乎正在变得浓厚。
今年有另一件令张箭飞感到惊讶的事,作为一门文学院的选修课,《植物人类学》以前的学生顶多三四十个人,这学期选课人数却超过了一百。上课地点不得不从文学院改到了距离珞珈门更远的信息学部,只有那里有大教室。为此,不开车的张箭飞要特意走上20分钟。
不过也好,武大校园内树木遮天蔽日,经常有学生陪着张老师一起在这条路上来回,这是一段与植物相伴的路程。
一堂植物课
教室的投影幕布中,沾着水珠的白色栀子花缓缓开放。
“太性感了,”张箭飞发出感叹,“要是新娘穿上一套栀子花开的婚纱,简直美爆。”
5月下旬,杨梅、荔枝还没熟透,夏天刚刚开始,但大学的一个学期已经走向尾声。这学期《植物人类学》的倒数第二堂课上,张箭飞邀请了学生林翠云博士讲“香气”。

林翠云曾在巴黎拜师全球唯三的嗅觉文化学者,对香水颇有研究—这种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香气制品,在人类世界成为了权力与情欲的象征。
课上,林博士说了一个秘密:文学院一位中年男教授最钟爱的香水是阿玛尼寄情,用光了好几瓶,她揶揄道:他喜欢的都是“街香”。
听闻“秘密”,张箭飞笑:“我还以为本院男老师不会用香水呢。看来,我也有性别傲慢和嗅觉偏见。”
介绍到时下流行的BYREDO香水“无人区玫瑰”(ROSE OF NO MANS LAND)时,张箭飞说,这款香水应该翻译成“没有男人之地”,叫“女子学院”最好。
台下学生又笑。
今年是她最后一次讲《植物人类学》,等她退休之后,这门课程也会从武汉大学的课表消失。
早在2016年,张箭飞为英语系研究生开过一门《植物与文学》讨论课,后来改成《植物人类学》,“下沉”到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张箭飞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没有人排斥植物,学生们如果以后在海外教授中国文化,讲植物是不会出错的选择。
香气是这门课的一部分,张箭飞自己讲课时,喜欢讲乡土植物,特别是乡土植物与民族记忆、文化认同的关系。开这门课之前,文学院里有一位老师研究方言的消失,张箭飞就想,乡土植物其实和方言一样,也在消失。
张箭飞研究的是景观与文学,当一个文学教授喜欢起植物,就会把植物也当作研究对象,比如她研究过原生于澳大利亚的桉树如何因为经济效益侵蚀了广西大片的原生林。
许多乡土植物因长满田野,沦为微贱的“杂草”“杂树”。一些本土花木,比如生于滇、藏、川、陕、鄂诸省山地的报春花在国内没有得到重视,却在英国园林中大放异彩,这让张箭飞十分痛惜。
张箭飞鼓励学生写家乡的植物小传。其实人类还在依赖野生植物作为食物、建材的时候,对于当地植物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但随着传统文化的流失,这些知识在逐渐被人遗忘。

在乡村社会,植物的利用算得上实用主义的典范。在张箭飞的课上,一位叫冯冬顺的学生是贵州仁怀人,他在作业里写到,向日葵与玉米套种在本地是常见的种植方法,向日葵产量虽少,但葵花籽可以待客,花盘可以入药,茎干可以照明。
“盛夏过后,将收割的花杆泡在楼顶的水中,日数随意,它也不腐烂。家里随时预备着几根捞起晾干的,若遇着夜里出行,点上一根,不易被风吹灭,且明亮耐燃。”这样的生活场景落在纸上,文学与植物的魅力相辉映,也令张箭飞欣喜。
植物的实用性建构起我们的生活,田野间也有叫“野花”“野草”的,没有人特意栽种它们,“有的甚至与人并无交集,只是组成乡间的风景”。
用学术的话说,这些花草构成了童年的“景观”。若学生来日远走他乡,再在别处遇见,人会想起自己的来路。
每一种植物都平等
有人在武大微信公众号下面留言:因为《植物人类学》这门课,人生有了唯一的种花体验。
种花不算太特别的,文学院的大一学生张润上了《植物人类学》之后,在学校的家属区里找了一块地,他们求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在上面种起了生菜、西红柿、黄瓜和辣椒。
每天路上迎面相逢的一草一木,里面都有一个自在的宇宙,寻常人不会特意钻进去打探,但一钻进去就会发现别有洞天。
“少時曾经在一块有主的地上挖坑,一直挖一直挖,便喜欢上了挖坑的那种沉浸的感觉。”没有真正种过地,一直是张润心中的一大遗憾,这回她终于得偿所愿,故而干起活儿来格外卖力。
“地就在学校里面,旁边还有一个幼儿园……每次去种地的时候,总是能赶上幼儿园下午放学,我们伴随着幼儿园里放的各种儿歌一起种地,心里顿觉快活无比,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感觉。”
亲手耕种,才知道每种植物的特别之处,比如生菜要定植,辣椒根系弱、病害多,黄瓜对水分需求量大。明明都是绿叶,但张润就是觉得辣椒叶比番茄叶好看,看起来亮亮的,摸起来嫩嫩的。
抛开学术性的知识,如果《植物人类学》这门课给学生带去什么实际的变化,那估计就是觉得植物更美妙了,与植物的关系更密切了。每天路上迎面相逢的一草一木,里面都有一个自在的宇宙,寻常人不会特意钻进去打探,但一钻进去就会发现别有洞天。
一位学生最近经常跑到一棵开花的树前久久驻足。她以前没见过这种植物,白色花苞覆满枝头,如同落了千百只蝴蝶般璀璨夺目,她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好奇:这个花,到底叫什么名字?
在植物分类学家杜巍眼中,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姓名,都在“生命树”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因此它们是平等的。即便草坪上的草也不是“无名小草”,而是“中华结缕草”,一种阳性喜温的木兰纲禾本目禾本科结缕植物。
喜欢植物的人理解不了,武大校园里很多植物都很美,怎么只有樱花成了人人争相一睹的网红。
杜巍也是张箭飞请来给《植物人类学》讲课的青年学者之一。她称呼杜巍是武汉大学“末代”植物分类学家,知道记者来访,请记者不要花太多笔墨在将要退休的自己身上,务必多讲杜巍老师的故事,和杜巍老师所教课程的必要性。

植物学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一门冷门学科,旗下的分类学更甚。杜巍的导师退休之后,整座武大,研究植物分类学的学者就只有杜巍一人。
初夏的武汉,与一位活生生的识花君走在中国最美的校园里,体验可以很新奇。
一栋建筑楼的墙角种着火棘和石楠,二者都是蔷薇科植物,外观相似,一般人难以分辨。杜巍摘下两片叶子放在手心,叶片的模样显得清楚:边缘光滑的是石楠,有小锯齿的是火棘。
他还把叶子从中间掰断,放到鼻子前闻了闻,两种叶子的气味也截然不同。
杜巍说,“跟着植物学家饿不死”。路过一处无人照料的草丛,他眼尖地发现一株“宝贝”,随手拔起,“这个可以吃”。果然,咀嚼植物的根部,一股清新的酸味涌入口腔。
喜欢植物,眼神得好。2021年年底,张箭飞去“诗经故里”房县开会,回程专门选了省道慢行,岔起走。在乡间小路边的杂木林,她看见一株开着紫花的野草:花朵很像诸葛菜属的二月兰,但叶子又长得不像。
她立马拍下照片,在微信上问杜巍。
杜巍查阅了好几种文献,最后判断:这是最近刚刚录入湖北当地植物名册的新物种。为此,两人特意到武汉植物园标本馆调阅标本。
张箭飞很兴奋,要是早点看到这种植物,他们两人也许会捡个大宝:为一个新种命名。
最近这些年,张箭飞一直在研究植物交换史的一个分支:湖北植物在海外。每每提到那些以湖北地名命名的植物,她都会手舞足蹈。
张箭飞喜欢在山间慢走缓行,沿路观察花草。学生“刷分”“刷题”,她把这个叫“刷山”。“其实我是近视老花眼,走路常常茫然失措,”她说,“但是只要一刷山,眼力格外细腻。”
花 痴
人为什么会喜欢植物呢?杜巍说,小时候在山里,天天看草看树,自然就喜欢。现在他出去野外调查,和小时候的“玩”没什么区别。
人喜欢植物是天性,就像站在旷野之中就想要呐喊,这是自然的召唤。
张箭飞敬佩杜巍老师的专业和敬业。杜巍任教数十年,曾参与12个自然保护区的植物多样性调查,经常带学生去食宿条件很差的地方摸家底。然而,在考核压力巨大的高校,植物分类学和科普很难做出高引用的“学术业绩”。眼看又到了评职称的时候,她很想问杜巍,这回评上没有,又不敢问。
除了张箭飞,文学院里爱植物的老师不少。一位研究宋代文学的教授极爱花,是个“花痴”。2021年4月中旬,武汉植物园种了30年的珙桐首次开花。得到这个“密报”,张箭飞心想,自己无论如何要当第一个看到珙桐的人,但她念及“花痴”教授,还是把消息告诉了他,并说:你可要让我一个子儿呀。
沈卓民的专业兴趣是“植物猎人”,个性签名写着:我的丑脸已被密林遮住。
当时两人都在学校,张箭飞立刻动身前往植物园,谁知对方还是比她更早一步。
喜欢植物的人,身上确实都有点“痴”。但这份喜欢与别的东西无关,只是纯粹用来讨好自己的。
张箭飞便认识一个学生,放弃了名师博士生的身份,跑到武汉一个公园给市民讲解植物知识。其实,这也算是一份好工作—如果工资更高点的话。
还有一个叫沈卓民的人,去年在武大拍了681张植物照片后得出一个小心的结论:“武汉大学植物多样性一般,应该没有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种类多。”
他把这些照片上传到一个叫“自然标本馆”的网站,在那里,他共上传了165757张植物的照片,涵盖4642个物种。
个人页面里,沈卓民的专业兴趣是“植物猎人”,个性签名写着:我的丑脸已被密林遮住。
城市的角落里,还有很多像沈卓民这样的人。
和人一样,不会动、不会说话的植物有时难逃厄运。
武汉大学振华楼西侧有一座建筑渣土堆积而成的小山,常有五条野狗在林中撒野,一位研究敦煌学的老师随口称它们为“振华五杰”,因此这座小山就被叫做了五杰山。
如今,野山“五杰”要被改造为园林景观,引来一片扼腕叹息。
城市制造了买卖的规则,也催生出富有与匮乏的假象,让人忘记人之所需本在自然之中,造化早已馈赠了一切。
夏天到了,张箭飞退休前剩下的工作,用手指头就能掰清楚。她说,虽然这节课是目前武大最后一节《植物人类学》课,但她不担心没有人把她的植物课讲下去。“我认识的几位年轻老师就可以。”
这一门课,是有人喜欢的。因为人与植物的关系太密切了,人类认识植物的过程,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人类贴近植物,就是在贴近自身。就像动物永远喜爱土壤的质感,我们也会在注视一株小小植物时想起:我和眼前的“生物”是一样的,不过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共生在这颗伟大又孤单的蓝色星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