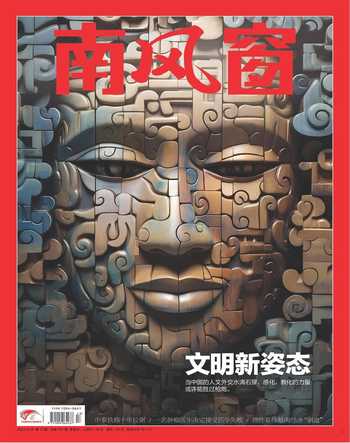导演王沐,拍一段精神受困者的爱情
2023-06-27何焰
何焰

杀青那一天,演员王子文哭得很惨。那是2020年泉州的冬天,她正结束电影《温柔壳》的拍摄,将赶往《三体》远在东北的片场。那一晚,她向人诉说对这部电影的不舍,她说,是这部电影好像将她洗了一遍。
《温柔壳》中,王子文确实有一双像被洗过的清澈双眼。不止是她,还有男主角尹昉。他在一间亮室中奔跑,直到人群之中的那个女孩也笑了,才结束一场恶作剧。三十多岁,在演员中也罕见的,一派天真。
王子文演觉晓,尹昉演戴春。他们在一间精神受困者的疗养院里,开始了恋爱。—这部名叫《温柔壳》的电影,在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一口气拿下了三个奖项,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和费穆荣誉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是王子文,最佳男演员是尹昉,而最佳导演的奖杯,是王沐的。
王沐是一名中年男性,大连人,微胖、不脱发、讲话慢,性格直率。《温柔壳》是他的处女作。
拿了奖,但其实是一股忐忑,贯穿着王沐过去的五年。从2018年筹备剧本,2020年冬天拍摄完成,再到今年5月26日电影《温柔壳》在全国院线上映,这个漫长的战线,已经拉了整整五年。
还好,口碑不错。
这五年来,世界几乎天翻地覆般地改变,王沐的生活也一样,他有亲人离世,也迎接了一个崭新的小生命,他振作又受挫,受挫又振作。但还好,五年前起草、三年前拍完的电影《温柔壳》,仍旧在2023年受到了认可。
6月伊始,王沐导演接受了南风窗的采访,讲叙了他因为拍摄电影《温柔壳》所窥见的精神受困者的爱情与世界的一角。王沐承认一部处女作的局限性,但也愿意告诉观众,自己如何用人生的一个五年,来决心平视一群人。
他们是精神受困人群,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恋人、家人,甚至是我们自己。
推开门
“过年好。”2018年的盛夏,大连国礼医院里,一个男孩反复对刚进来的王沐打招呼,“过年好。”
王沐礼貌回复:“你也过年好啊。”对方狡黠一笑,转身就向同伴炫耀。—好坏。原来他是来试探王沐的。王沐也笑了,但突然就被抚平了紧张。
这是一家精神专科康复中心。这一年,王沐因为决心要拍摄一部精神受困者的爱情电影,托了朋友,得以进入精神专科康复中心的住院部采风。
这也是王沐走近精神受困者的第一天。
这一天的故事,从一扇门开始。
国礼医院的一扇大铁门,没有上锁。王沐在犹豫:是等院长来接,还是直接推门进去?他好奇为什么这里不锁门,也没有人从里面跑出来。王沐站在门外打量着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也偶尔回看他。
他推了门进去。
进去之后,王沐慢慢放松下来。在今年5月底电影上映后,王沐写下一篇长文《温柔之必要》,讲叙了许多自己采风第一天的经历。
而《温柔壳》电影的男女主角原型,就来自王沐在国礼医院见到的一对女孩和男孩。
那一天,王沐推开铁门,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女孩,“她身后一直跟着一个男孩,健康的肤色,眼神专注坚定,他永远和女孩保持着固定的距离,从来不打扰她的生活”。
国礼医院是男女分住的,但院长告诉王沐,这里经常会有人谈恋爱。“他们并不避讳,也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这里的工作人员,便不会多加干涉。“不过这样的恋情总是短暂的,一旦有一个人出院了,这种关系也就戛然而止,他们似乎很难得到家人的认同,尽管这些家人,大多数时间从未来看过他们。”
探访国礼医院之后,接下来的十几个月里,王沐持续着采风工作。他看了十几本相关书籍,走访了五家相关机构,拜访了一些心理学和精神科的专家。
在一年多时间的采风里,王沐有一些发现:相比于过去“精神病院”这种粗暴的称呼,现在的机构名称要温和、五花八门得多。有的叫心理医院,有的叫第几人民医院,有的叫康复中心,有的叫疗养院。甚至有一些地方的福利院里,也居住著许多精神受困者。不同的名称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环境,王沐印象中,叫疗养院的地方往往环境会稍好一些,但这些机构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护工总是不够,“1比8甚至1比16。”
院长告诉王沐,这里经常会有人谈恋爱。“他们并不避讳,也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王沐去过的机构里,居住环境是很参差的。一些机构给王沐留下的印象是温暖的,“似乎永远能感受到有阳光透进来,有人很平静地在其中生活,吃饭和散步”。而另一些机构,有封闭生活的场景,8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还有没有遮挡的卫生间,能够看见里面的每一个坑位,也给王沐留下深刻的印象。
环境的参差,也在电影《温柔壳》中有所呈现。
男女主角相爱的疗养院,选址在福建泉州的鲤城福利院,那里的环境是温和的,大门是敞开的,住在那里的人也几乎没有攻击性。福利院里的真实住户和工作人员也在电影中出镜,大多数人的状态平静,神色天真;
而电影里,男主角精神受困的父亲,他所居住的则是民间经营的无名收纳所。那里房间狭小,收费便宜,有着被数倍放大的“老人味道”。
虽然从一开始,《温柔壳》便定位是一部爱情电影,即便选定了“精神受困者”这个群体,王沐也从没有野心要为这部电影做一个缜密的社会学田野调查,但他仍旧花了很多时间去亲近他们,试图在电影里放进一些生活的细节。
在忐忑中
其实是一股忐忑,贯穿着王沐拍《温柔壳》的这几年。
从2018年初决定从编剧转行做导演,并选定要拍精神受困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身边就有人告诉王沐,这是一个勇敢又危险的决定。
一方面是个人发展上的忐忑,一方面是关于电影的忐忑。
《温柔壳》制片人告诉南风窗,中国的电影圈似乎有一个怪事。摄影转导演、执行导演转导演、演员转导演都很常见,但是感觉一个编剧转行做导演的争议就有很多,因为大家常说:“写剧本和镜头呈现,完全是两件事。”
但是王沐想转行,原因不是别的,他只是想表达。
在转行之前,王沐曾经跟国内非常知名的导演合作过剧本,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搁浅,作品无法和观众见面。写一个剧本将近一年的时间,作品中承载着他的情感和一个人生阶段的感悟,连续两三轮合作踩空之后,一个青年编剧的两三年努力都变成无用功。
在没有产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沐都很焦虑。“恨不得自己去做一点手工。至少是看得见的,有一个东西摆在我面前。”
想要表达,被看见,三十出头的王沐一股冲劲儿,决定干脆自己拍。
拍什么呢?
最开始,王沐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想法,“要拍一个爱情故事”,最后锚定到精神受困者身上,王沐说是“命中注定”。
2017年他身边有一位编剧前辈因为抑郁症轻生。“只是一个短暂的工作接触,大概两个月,我觉得他身上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他很酷,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但是有一天,王沐突然听到,这个人离开了人世。
这件事对王沐产生了冲击。
他开始去关注精神疾病的话题。慢慢地,他发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的人都有精神困扰或者情绪困扰。这些朋友的遭遇,在王沐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那年年底,王沐逛书店,恰巧看到一本五年手账。那是一本有趣的日记本,每一页上都可以看到五年今日,这样的安排让王沐对时间的流逝有了实感。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好奇:“我从想拍一个电影,到它拍出来,再到它上映,将会用多长时间?”
一个普通人想拍电影的梦想,一部电影从出生到与人见面,这一段历程有多长?王沐真的很想知道。
十几年没有写过日记的他,买下了这一本手账。
但当时的王沐并没有预料到,这一本日记,将会伴随他整整四年。伴随他去精神专科康复中心采风,伴随他拿到2019年平遥国际电影节的创投奖金,伴随他又去海南电影展拿下电影的启动资金,伴随着他的孩子出生,伴随着疫情三年电影行业的持续萧条,伴随《温柔壳》开拍……而到他停笔封本的那一天,这部电影才刚刚定剪。
王沐本想接着写的,按照原计划,把日记写到电影上映那一天。
但王沐害怕了。
他担心—这本五年手账如果不够用怎么办?为了一部电影的诞生,这一本日记中已经记满了他的忐忑和努力,如果写到最后一页,电影还没有上映怎么办,“会不会显得我太可怜了?”
王沐决定封存了它。
再一次打开这本日记,是2023年5月24日。《温柔壳》的首映礼结束之后。
五年多时间过去了,电影终于上映了。
在没有产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沐都很焦虑。“恨不得自己去做一点手工。至少是看得见的,有一个东西摆在我面前。”
这一天,伴随着一部电影从0到1,王沐在豆瓣写下那篇长文:“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
得的什么病
直到今年6月初,接受南风窗采访的时候,王沐说自己仍旧在这种忐忑之中。
而王沐最大的忐忑就是:“如果我没有做好,可能会冒犯大家。或者说他们会误会我在消费一个群体。”
当南风窗询问王沐,他内心是否有一个答案,《温柔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不冒犯精神受困者人群呢?
视频对话框里的王沐,立刻表现得有点无奈。一部电影出生之后,评价的权利就交由给了他人。导演没有办法。
如果非要有一个办法,王沐的办法是“平视他们”。
如何平视一个精神受困者,在王沐的生活中,或许他从自己的大姨的身上学习到了一些。
从王沐记事起,他的大姨就已经被诊断出有精神障碍。她的脸上总是挂着一股笑,处在一种不太清醒的状态。家里长辈对大姨的病因,向来讳莫如深。“因为当年受刺激,似乎是和姥姥有关系。”
成长的过程中,王沐也只是远远地看着自己的这个亲人,和她鲜少接触。
直到2019年9月,姥姥在大连去世。王沐作为家中这一辈唯一的男性,回家给姥姥主持葬礼,在葬礼上,他见到了大姨生的两个女儿,自己的表姐们。
表姐告诉王沐,在葬礼的前一天,才敢让大姨得知姥姥去世的消息。
但大姨似乎比想象中更冷静。她只是说:“那以后再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原来,在姥姥人生的最后两年,她每一天都和大姨保持着通话。
王沐无法不去想象那个画面,春夏秋冬从眼前划过,一个年迈耳背的老人,和她语速很慢的大女儿,每一天聊天的样子。
王沐甚至会想:最后这两年,大姨和姥姥是不是以这种方式和解了?但他又觉得,对于生活在“故事”中的家庭来说,不管是精神受困者,还是精神受困者的家人,“和解”这个词,都太轻简了。
王沐似乎走近了大姨一点,也更贴近了自己的电影《温柔壳》一点。
他似乎也把从大姨身上感受到的情感、对亲情的体悟,盛放在了自己的电影中,放在了电影主角的亲子关系上。
从编剧转行而来的导演王沐,在片场很少对演员讲戏。如果他哪里覺得不对,他会去和演员讲故事。他用一个故事去向演员沟通,请对方体味故事中的情感,由演员自己来发挥饰演。

为了把真实的经历勾出的情感,灌注到电影中。王沐还找了两个朋友,他们几乎和电影中觉晓、戴春有着一样的经历。王沐请他们念一遍电影的台词,录下来,送给王子文和尹昉听。让演员去感受,现实中有类似经历的人,在这样的场景下,会是这样讲话的。
王子文听了录音,问王沐,她说这个人听起来怎么不像是生病了。类似的提问王子文也在一些采访中讲过,她说她问过导演,觉晓到底生的什么病?
王沐说:“觉晓没有病。她只是不高兴。”
这样的问题,南风窗记者也追问王沐,男主角戴春到底生的什么病?
《温柔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不冒犯精神受困者人群呢?
王沐最开始不想回答,他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你们看到一个人,不是看他爱什么,想做什么,要解决什么困难,而是一直追问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但后来追问着追问着,王沐告诉南风窗,最开始他也想要设定清楚,戴春到底生的什么病,但是他看了很多书、电影之后发现,同一种疾病可能在不同的书上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同一种病人在两个不同的电影里会有两种面貌。而几乎探访过的每一个专业的医生也都告诉王沐,精神障碍患者通常是千人千面的。
后来,王沐索性不想在电影里讲戴春生了什么病了。
“这部电影不是要为戴春治病的。我要写的只是两个人,他们相爱、就业、结婚、生育。他们的爱很美,很珍贵,和我们一样。”王沐维护他们,或许已不单是一个导演维护自己的作品,更像是维护一个老朋友。
王沐打定了主意,《温柔壳》要讲两个精神受困者的爱情故事,但要讲他们身上更贴近普通人的那部分。
为觉晓和戴春这样的人去维护一份普通的爱,其实更难,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