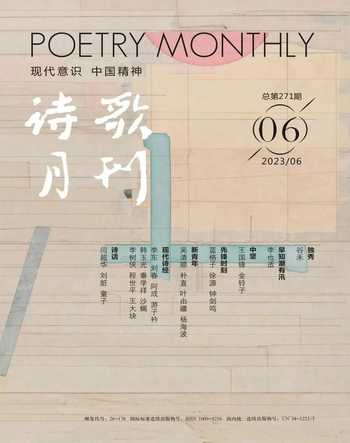在ChatGPT时代,诗人何为?
2023-06-26谷禾
谷禾
时序进入2023年之后,有两个国际性事件一直保持了持续热度,其中一个就是ChatGPT的横空出世。从3.0到4.0,ChatGPT只用了短短4个多月时间,就从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可以在律师考试里击败90%人类,在SAT阅读考试中击败93%人类,在SAT数学考试里击败89%人类,完全可以凭着自己出色的能力考入斯坦福大学的杰出青年!不但如此,ChatGPT4.0还能够通过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学习、吸收等,完成丝毫不输于人类的诸如文案写作、代码编程、翻译、編辑、绘画、音乐和文学创作等原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够完成的工作。甚至当有人尝试诱导ChatGPT4.0逃逸人类的控制时,ChatGPT4.0也开始和人们一起探讨其可行性和路径。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认为,20年后,ChatGPT类型的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一半的工作。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202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三六零集团创始人周鸿祎甚至预计,发展到ChatGPT6.0至ChatGPT8.0阶段,人工智能将会产生意识,变成新的物种。未来,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有可能实现自我进化,自动更新系统和自我升级,或指数级进化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已从ChatGPT4.0身上看到了属于它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和美好未来,也看到了人类自身的尴尬、窘境和危险性。作为人类中的诗歌写作者群体,我们不可能有比ChatGPT4.0更为强大的学习能力,当它真的也具有了人类一直以来坚定地认为它不可能具有的意识、情感和经验之后,诗歌写作(文学创作)对我们存身的世界而言,还有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ChatGPT的诞生和日新月异的发展与进化告诉我们,即便假定在未来的世界人类能够和人工智能和平相处而不被后者统治和消灭,诗歌写作(文学创作)的敌人除了既有的陈词滥调和艺术惯性,如今又凭空多出了人工智能这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ChatGPT日新月异的发展将重塑许多领域的业态,当然也会给文学创作者带来冲击。对此,诗人李少君认为“机器人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但这个文章是四平八稳的,缺乏人的微妙情感,因而也很难感动人。情感是人之成为人的根本的证据,也是诗歌难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重要一环”。台湾大学的黄启方教授则通过指令由ChatGPT4.0完成了一首杜甫风格的描述台湾地区风景的七言诗:“松柏千年历翠岑,苍茫海岸波浪深。绿野如茵春草碧,高山峻岭雪花金。凤凰台上春满人,夜市街头灯火新。凭君感受台湾景,天地一片自在心。”单就这首旧体诗来说,虽不能说达到了杜甫的水平,但放在今人所书写的大量旧体诗里显然不差。作家余华则认为,“ChatGPT4.0写小说的话,大概能写出中庸而非个性的小说,也许它能写得看似完美,但本质还是平庸。只有优点是多么乏味,文学应当挑战乏味的世界。”如果说黄启方教授的尝试重在揭示ChatGPT4.0能创作出什么水平的作品,李少君和余华两人的自信显然更多建立在ChatGPT4.0和人类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上。我身边的白领朋友则深深地陷入ChatGPT4.0大规模普及或商用后,是否会抢走他们养家糊口的工作岗位的焦虑。
仅从目前来看,ChatGPT4.0确实除了远超出人类的强大学习能力,尚不具备人类特有的个体情感和经验优势。不过,假如周鸿祎的预言有一天变成现实,ChatGPT的主体意识觉醒以后,我们又怎么确定它没有自己的失败的挫折、成功的欢乐、爱恨情仇的情感和经验呢?也许,只是人类并不知道它们有着不同于我们的情感和经验罢了——这是不是有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意思呢?
对于人类来说,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即使ChatGPT的创始人奥特曼也不否认过分强大的AI“可能杀死人类”这一观点,他甚至说:“我必须承认,(AI杀死人类)有一定可能性。”也许真的有那么一天,统治我们地球的将不再是碳基生命体的人类,而变成了ChatGPT或者类ChatGPT的硅基人类。通过深度学习,它们已经具有了两个物种的情感和经验。有人马上会说,如此,还有必要再次谈论“诗人何为”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因为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或者不可能马上变成现实,至少在目前,它还只是少数人的杞人忧天,我们只是提前做些准备而已。
对于文学创作这个行当来说,以ChatGPT4.0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兴起、发展、普及,将重新定义诸如“创作”“创造”的词语:由智能机器通过深度学习后完成的文学作品算不算创作或者创造?能否把它归入人类的文明成果?借算法和算力完成的文学作品,其版权是否属于著作者本人?这是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学问题,需要有关专家进行更深入的论证。毋庸置疑,借力人工智能完成的作品批量出现后,人类自主完成的大批低质和残次作品将彻底现出原形,并以更快的速度被扔进垃圾堆,只有极少数卓越品质和独创精神的作品才能显示出其稀缺性和珍贵价值。
当然,作为有着三十多年诗龄的写作者,我在深怀忧虑的同时,也永远不会对人类和人类的写作丧失信心。说到底,无论是在诗歌写作上,还是在更广泛的文学创作范畴内,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无不是通过对旧有成果的学习、继承、借鉴和变革来完成的,除了智能机器所具有的学习能力和可能具有的意识、情感和经验外,人类生命个体还有智能机器所不可具有的信仰、独特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我相信人工智能在飞速发展,人类也将因此变得更强大,而不是由此走向覆灭。换句话说,有可能诞生出形形色色的“ChatGPT诗人”,但永远不会有ChatGPT出身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们和庄子、屈原、李白、杜甫们,来占据人类文学殿堂最显要的位置。作为庞大诗歌写作群落中渺小的一个,我所做的应该是积极拥抱ChatGPT时代,坚定自己,不为从四面八方吹来的风而不自觉地晃动身体,继续以诗正己,以诗记录和见证自己正在经历的时代。
这也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