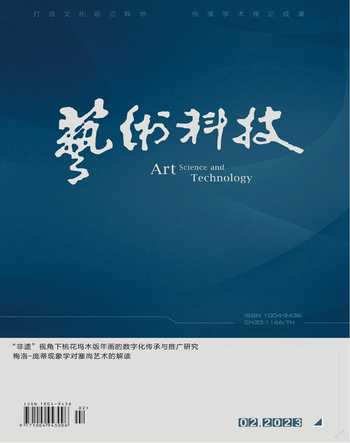《都柏林人·两个浪汉》的意象、留白和隐喻分析
2023-06-22黄若衡
摘要:乔伊斯曾说,他写作《都柏林人》的初衷是想写一部关于祖国的道德史,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作为都柏林人,乔伊斯怀着冷峻的沉痛揭示了民族的劣根性,他认为青年人的颓废是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最危险的信号,然而乔伊斯在表现黑暗的同时,也在寻找光明的未来。文章分析《都柏林人》中的短篇《两个浪汉》的意象、留白和隐喻,解读乔伊斯小说的艺术技巧和精神内涵,探究喬伊斯作品带给读者的精神启迪。
关键词:《都柏林人》;《两个浪汉》;意象;留白;隐喻
中图分类号:I56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2-00-03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最早的作品集,完成于1904年,首版于1914年。在这10年间,其遭到22家出版社退稿。除了作家年轻时名气不大,被退稿还有什么原因呢?笔者阅读作品后发现,这15个故事不仅反映了都柏林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毫不留情地毁灭着人的理想和希望,而且表现了都柏林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的颓废气质。乔伊斯在《都柏林人》开篇就阐明了写作的初衷:“我的目的是为我的祖国谱写一部道德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1]1
青年人的颓废是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最危险的信号。短篇小说《两个浪汉》选取两个浪汉日常生活的一个截面,冷静地揭示了他们道德丧失、精神瘫痪的心理状态。浪汉莱尼汉夸夸其谈,不仅他的言说无意义,他无所事事的人生也缺乏意义。他曾有一瞬间的焦虑,31岁的他还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家,但吃完一碗热豌豆,已经饱腹的他就“不再厌倦自己的生活”[1]63。如果说莱尼汉的生活无意义,那么另一个流浪汉科利则是无廉耻,他装模作样,通过勾引女人获利寻求满足感,并将其作为资本向同伴炫耀。那么,乔伊斯想通过这两个流浪汉的颓废心理和无意义行为传递怎样的思考呢?
1 背景:颓废的根源
小说置景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都柏林,当时的爱尔兰在英国议会的统治之下,因马铃薯晚疫病发生了大饥荒。马铃薯是当时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加上社会与经济因素,广泛的歉收严重影响了贫苦农民的生计。灾荒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饥荒期间废除了《谷物法》,阻止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了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进一步破坏了爱尔兰的农业经济。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无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爱尔兰人都在饥饿、贫穷和绝望中苦苦挣扎。乔伊斯也在这样的困境中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见证了都柏林人无序又荒谬的公共生活。
《两个浪汉》中的两个主人公莱尼汉和科利带着他们的“荒谬”走来,让读者得以拨开乔伊斯的烟雾,窥见真实的都柏林。
2 意象:乔伊斯的魔杖
乔伊斯善用意象,《都柏林人》中的诸多意象在冷静叙述下传递着价值表达。如《姐妹们》中的圣杯被打破,暗示着都柏林人信仰崩塌;《泥土》的主角玛利亚在万圣节抓阄环节摸到了“又软又湿”的泥土和祈祷书,泥土象征死亡,祈祷书象征希望,这组意象象征都柏林人向死而生……这些意象都隐喻着都柏林人的精神世界。
《两个浪汉》的故事发生在“灰色温暖的八月的夜晚”,“星期天商铺都已歇业”,但“街上着装鲜艳的行人熙熙攘攘”,街灯“形状和色彩不断变幻,将轻柔连绵的耳语声,拋向温暖的、灰蒙蒙的夜
空”[1]57。都柏林的夏天已过,夜空笼罩的灰色是挥之不去的压抑,但变幻的灯光、轻柔的耳语令都柏林人沉醉,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至于有何意义,熙熙攘攘的人群不会给出回答。
故事开端的几个意象——变幻的街灯、温暖灰色的夜空、着装鲜艳的行人,将都柏林的日常呈现给了读者。互相影响又相互矛盾的意象带给读者的是隐约的不适和疑惑:都柏林人的欢乐从何而来?
“高高在上”的灯既是都柏林人沉醉在虚假希望中的象征,又是都柏林人受殖民者和教会双重迷惑和压迫的悲惨现实的隐喻[2]。夜空也是灰色压抑的,但都柏林人仍沉醉其中,精神麻木,思想瘫痪。
科利手中的金币也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意象,它似乎给了莱尼汉一个答案:你看我又骗到了钱。所谓恋爱,本质是金钱的游戏。
而莱尼汉的雨披和女佣手里的伞,既暗示都柏林八月山雨欲来的压抑,又隐喻人们期待一场改变整个爱尔兰的风暴和变革。莱尼汉“始终盯着那一轮又大又圆、有两个晕圈的昏黄月亮。他热切地注视着黎明的灰网从月亮的脸庞掠过”[1]62。此处“又大又圆、有两个晕圈的昏黄月亮”象征着英国殖民者和教会给爱尔兰人民的虚假希望。而莱尼汉内心自发地渴望一场暴风雨,渴望“黎明的灰网”掠过“月亮的脸庞”,渴望一场席卷全社会的变革。然而,最后“天上落下几滴小雨。他觉得这雨滴是在警示他什么”,警示什么?乔伊斯没有讲,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和想象。
3 留白:走进都柏林
留白原指书画艺术创作中有意留下的空白,给观者以想象的空间。小说中的留白,同样给了读者再创造的空间,从而彰显审美趣味。乔伊斯的留白即通过没有讲完的、没有讲清的意识流和断崖式结尾设置悬念,带领读者揣摩人物的心理及故事的来龙去脉。
3.1 意识流
乔伊斯是意识流大师,虽然《两个浪汉》写于其年轻时,但该作品已展现出《尤利西斯》的写作风格。莱尼汉和科利的一问一答,很好地展现了人物意识的流动状态。科利的夸夸其谈,完全是为了出风头,而且为了出风头,其还不择手段地吹牛;莱尼汉在假意相信科利并极力恭维的同时,也想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因而语气中带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两人颓丧瘫痪的样子活灵活现。科利的瘫痪表现在经济和情感上,经济瘫痪表现为不务正业、靠女人获利,情感瘫痪则体现在扭曲畸形的恋爱观和恋爱关系上[3];而莱尼汉的瘫痪主要表现在精神和经济上,他想看科利的女孩的急迫行为和仔细观察女孩的行径揭示了他自主意识的丧失,他几乎没有自我,只活在朋友的生活中,可见精神上的无力,他依赖别人的施舍度日,而且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奉承每个请他喝酒的所谓“朋友”,可见其经济上的麻痹、行为上的无意义。
作品运用意识流没有说完和没有说清的内容吸引读者猜测、想象都柏林人的生活。但就像米洛斯的维纳斯,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维纳斯的手臂。最有趣的是莱尼汉“觉得这雨滴是在警示他什么”,警示什么?现实总是与愿望背道而驰,暗示希望落空?暗示内心的渴望徒劳无功?告诉他“潇洒地披在肩头的雨衣”从而青春洋溢也是虚妄?或者这是上帝对他无所事事的警告?警告他与其焦虑不如行动?告诉他爱尔兰的改变已经开始?无论哪一个答案都能让读者看到都柏林人的精神现状。
3.2 断崖式结尾
“‘怎么样?(莱尼汉)他问。‘成功吗?
……
‘难道你不能告诉我?他说。‘你到底试过她没有?”[1]69
作为科利恋爱的旁观者,莱尼汉急切地用逼迫的声调询问,而科利没有回答,面容镇定平静,大有“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架势,在结尾处设置悬念是乔伊斯的高妙之处。两人急切与平静的落差对比,引导读者浮想联翩,在产生意味无穷的阅读效果的同时,也能让读者感受到都柏林人情感生活的荒谬无序。
小说以科利“以一种严肃的手势把手伸向灯光,微微地笑着,慢慢地把手打开,让他的信徒细看。一枚小小的金币在他的掌心里闪烁”收束,含蓄隽永。莱尼汉急切想问的应该是,科利向女仆求婚了没有?或者究竟求婚或求爱成功了吗?但科利却答非所问,得意扬扬拿出了一枚金币,戛然而止的结尾没有告诉读者答案。
这种断崖式的结尾会使读者产生强烈的虚无感。科利和莱尼汉是小说推进的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一起出发,分开后若即若离,在最终交汇的时候,全文到达了高潮部分。因为两条线并行交织,科利和女仆的那条线隐藏起来了,他们的交往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此处同样留白,只能根据最后科利手中的那枚金币来猜测:科利花言巧语,诉说自己的爱情;女仆含情脉脉,心底盘算着这场赌博的胜算,“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感情中充斥着利益的考量和博弈,利用情感攫取金钱或许是都柏林人的生活常态。再结合背景和其他短篇会发现,因为生活艰难、前途渺茫,《都柏林人》大有大龄青年逃避婚姻责任的现象,爱情在情感瘫痪的都柏林人那里早已物化。而这种现象在莫泊桑和卡夫卡笔下也比比皆是,那么当今生活中这种待价而沽的两性关系是否存在?这引发了读者的思考。伟大的作品常常超越时代、跨越民族。
4 隐喻:黑夜与光明
在《都柏林人》中,乔伊斯用丰富而又深刻的细节隐喻都柏林人难以言说的精神秘史。例如,短篇《姐妹们》中打破圣杯导致神父死亡这一事件,隐喻都柏林人信仰的崩塌,而将一只无用的圣杯放在已故神父的胸脯上,隐喻都柏林人的精神已经瘫痪,宗教已经陷入困境。虽然《都柏林人》被认为是爱尔兰人的精神死亡断代史,但笔者认为这部作品也是这个民族的觉醒史,那些向死而生的或暗示救赎的意象,揭示着改变爱尔兰现状的出路——根除精神瘫痪。例如,《泥土》的主角玛利亚在万圣节抓阄环节中摸到了在爱尔兰文化中象征死亡的泥土后,重新抓阄,摸到了祈祷书,这隐喻了她将来的选择,更隐喻了爱尔兰人对未来的追求。
《两个浪汉》的隐喻也让读者触摸到了都柏林人的精神秘史。首先出场的莱尼汉“身材矮胖,脸色红润,一顶游艇帽戴得高高的,露出前额”“他的眼睛闪着狡猾的愉悦”,可他“腰部臃肿,头发灰白又稀疏,脸上的表情褪去后,显出一副沧桑的面孔”[1]57。这些形象描写反映出这个都柏林青年已失去年轻人应有的朝气,说其精神瘫痪也不为过。有时他也对自己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很沮丧,但他从没有试图改变这一切。只要有饭吃、有酒喝,遭受任何侮辱对他而言都无所谓。莱尼汉这一人物前途渺茫,精神无所皈依,是当时被动和颓废的都柏林社会底层民众的缩影,他偶尔的焦虑也隐喻了爱尔兰的群体焦虑。
令人奇怪的是,在还未下雨的夜晚,他穿着雨披,“有一两次,他调整了身上那件轻薄雨衣的位置,之前他像斗牛士那样把雨衣斜披在肩头。他的马裤、白胶鞋,和那潇洒地披在肩头的雨衣,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1]58。这个细节说明他内心也向往青春的朝气和激情,隐喻都柏林人也在探寻缓解焦虑、摆脱困境的出路,当社会变革到来,他们也将心里有火,眼里有光。这个违背常理的细节暗藏着乔伊斯内心的希冀——都柏林人终将觉醒,迎接光明。
而关于莱尼汉对科利和女仆的恋爱进展那种“太监”式的操心,隐喻作者的价值取向。虽然知道科利是个花花公子,会游戏姑娘感情,也会被人游戏,科利的恋爱掺杂着太多算计和利用的成分,而女仆多少也有经济考虑,莱尼汉羡慕却也不屑,但仍旧希望看到科利和女仆能有一个结果,或许这个结果可以是纯粹的。莱尼汉贯穿始终的与己无关的急迫追问看似荒谬,却是乔伊斯留给都柏林人的颜面,也是为他们点的灯——虽然整个社会充斥着物质主义和精神麻木的迷雾,但是道德的爱情观应当反抗当时唯利是图的物质的婚恋观。
由此,不妨把流浪汉莱尼汉看作超越现实和庸俗的一个典型人物,虽然他无所事事,但他有一刻的觉醒;虽然他的精神可能继续瘫痪,但他内心已对社会变革有所期待;或许仅是无聊地关注他人的爱情,但他的价值观里已有了道德的觉醒。不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那般特立独行,他也迎合世俗;也不完全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狂妄自大、自欺欺人,他也有人间清醒的时候;更不像《复活》里的聂赫留多夫那样实现了彻底的人性复苏,他无法改变科利,也无力改变自己。虽然他还是那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浪汉,但思想的萌芽就是星星之火,必将燎原。精神萎靡的都柏林人,终究是要挺起脊梁的。
5 结语
《两个浪汉》的故事发生在黑夜中,科利和莱尼汉一个在现实中沉醉,一个在沉醉里复苏,呈现出了人们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既并道而行,又分道扬镳。都柏林是乔伊斯的故乡,对青年人的精神困境,作家有冷静的审视,也有冷峻的批判,更可贵的是,其在微芒中发现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前途。黑夜之后就是光明,乔伊斯在唤醒精神,反抗现实,体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的宝贵价值。事实上,对全世界而言,乔伊斯就是爱尔兰的代名词。《都柏林人》不仅是一部爱尔兰人的道德史,更是一部爱尔兰民族的启蒙史和觉醒史。
參考文献:
[1]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王逢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57-58,63,69.
[2] 薛海燕.《都柏林人》中的“灯”意象[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7.
[3] 韩立娟,张健稳,毕淑媛.情感瘫痪:评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的主题[J].唐山学院学报,2006(4):51.
作者简介:黄若衡(2003—),女,江苏常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评论。